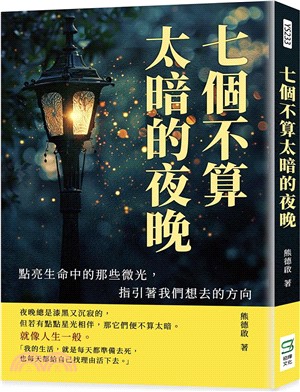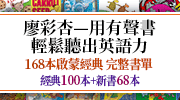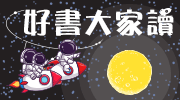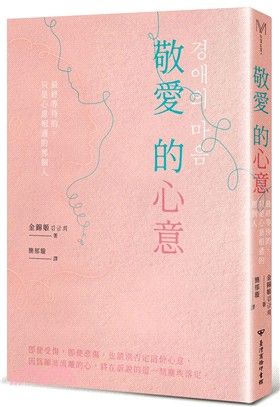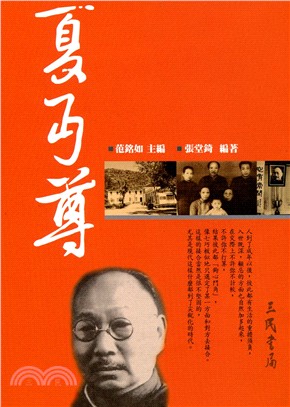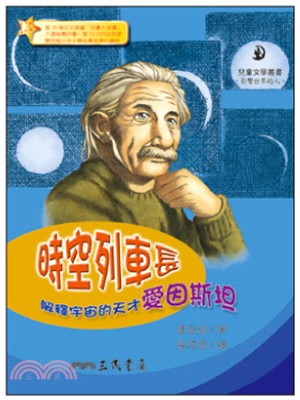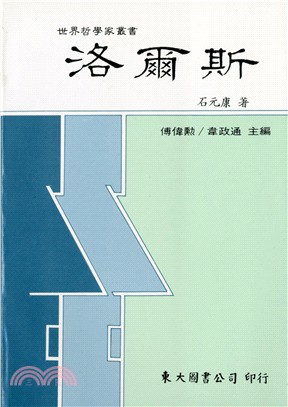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夜晚總是漆黑又沉寂的,
但若有點點星光相伴,
那它們便不算太暗。
就像人生一般。
「我的生活,就是每天都準備去死,
也每天都給自己找理由活下去。」
▎沒有光的房間
──「沒事的,你會好起來的。我聽見了。」
她忽然意識到,如果張井禾此刻不在了,她幾乎可以料理關於張井禾的一切後事──他家門的密碼、他的車、他媽媽的病歷、他那些保值的奢侈品……這些東西已經根植在蘇梅的腦中,如那些曾經日復一日撥打過的電話號碼一般,要伴隨她一生。
蘇梅顫抖著拿出手機打給張井禾,張井禾沒接。掛掉電話後蘇梅發現在通訊錄裡「張井禾」的名字下面不知何時多出了一個名字:張井禾媽媽。這電話是什麼時候有的呢?好像就是前兩天,張井禾說找不到手機了,拿蘇梅的手機說要給自己打電話。
▎江城子
──「你咋成這個樣子了!你咋成這個樣子了!」
從很多年前見到自己的整條左腿被橫擺在面前的那一天開始,王常友在這世上就成了一個徹底的局外人。他一早就知道,也慢慢接受了這個事實──這世界沒有他也一樣歌舞昇平,沒有他也一樣殘忍無情,他王常友已經影響不了這世界的一分一毫。
如今就連殺人,似乎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縫隙下刀,殺不進這被一道透明結界嚴絲合縫地遮罩起來的世界。
▎詩的證言
──「最後一個為我鼓掌的人,會不會是你?」
夜晚總是難過的,那個唯一能嘮叨幾句的愛人早已永別,不敢再想,但念頭一空便孤獨起來。洪童覺得此刻自己是需要一首詩的,不是魯大的詩,而是一首真正的關於生命的詩。他想起來了──「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他現在沒有「我們」,也沒有另一隻杯子與他的碰在一起,他的生活可能早就以另一種方式瓦解了,換了個紙杯子,碰也碰不出聲響來。
▎鏡中鵝
──于大雪終究是到了異鄉,任這裡風景如畫空氣清新,這都不是他于大雪的家。
「我哥沒了。」于大雪的妹妹輕輕扶著郭建新的肩膀啜泣,郭建新呆坐在那把屬於探病親屬的木椅上,始終沉默。于大雪早年離婚後與前妻已沒了情誼,跟了前妻的女兒也直到此刻收到訊息才答應過來奔喪。
護士說于大雪一直艱難地維持著呼吸,直到聽見那句「老郭來了」才走,前後不過幾秒鐘。
坐在那把木椅上,郭建新覺得自己慢慢變輕了,回憶的縫隙中每一個于大雪的身影都被宇宙收回了造物的魔盒中。過去四十七年的生活在此刻坍塌成一個點壓在他心口上,他好像一張被巨人踩在地面的紙,足夠輕盈,輕盈到可以飛起來,卻不得絲毫自由。
▎月亮成熟時
──「你喜歡今天的月亮窩?那我就給你摘下來!」
回想到那個夜晚,即便苟姐已經年過五十,依然是滿面潮紅。
她已經想不起來上一次和丈夫親密是什麼時候,或許再仔細想想還能勉強記起。但再上一次呢?上上次呢?手中那塊阿穆送給她的石頭,就像回憶裡他的觸感,堅實而粗糙。
或許記憶的用處便在於此,在生命漫長的枯萎中提醒自己,曾經豐盛的樣子。
本書特色:本書為熊德啟所著,收錄七篇短篇小說。他在自述裡說:「故事裡有發著光的生命,可以點亮那些過於黑暗的夜晚。」這些故事訴說了很多人的人生,有令人難受的地方,也有令人惆悵的回憶。但那些生命中的微光,就算只有一點點,也能使漫漫長夜多一些溫暖。
但若有點點星光相伴,
那它們便不算太暗。
就像人生一般。
「我的生活,就是每天都準備去死,
也每天都給自己找理由活下去。」
▎沒有光的房間
──「沒事的,你會好起來的。我聽見了。」
她忽然意識到,如果張井禾此刻不在了,她幾乎可以料理關於張井禾的一切後事──他家門的密碼、他的車、他媽媽的病歷、他那些保值的奢侈品……這些東西已經根植在蘇梅的腦中,如那些曾經日復一日撥打過的電話號碼一般,要伴隨她一生。
蘇梅顫抖著拿出手機打給張井禾,張井禾沒接。掛掉電話後蘇梅發現在通訊錄裡「張井禾」的名字下面不知何時多出了一個名字:張井禾媽媽。這電話是什麼時候有的呢?好像就是前兩天,張井禾說找不到手機了,拿蘇梅的手機說要給自己打電話。
▎江城子
──「你咋成這個樣子了!你咋成這個樣子了!」
從很多年前見到自己的整條左腿被橫擺在面前的那一天開始,王常友在這世上就成了一個徹底的局外人。他一早就知道,也慢慢接受了這個事實──這世界沒有他也一樣歌舞昇平,沒有他也一樣殘忍無情,他王常友已經影響不了這世界的一分一毫。
如今就連殺人,似乎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縫隙下刀,殺不進這被一道透明結界嚴絲合縫地遮罩起來的世界。
▎詩的證言
──「最後一個為我鼓掌的人,會不會是你?」
夜晚總是難過的,那個唯一能嘮叨幾句的愛人早已永別,不敢再想,但念頭一空便孤獨起來。洪童覺得此刻自己是需要一首詩的,不是魯大的詩,而是一首真正的關於生命的詩。他想起來了──「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他現在沒有「我們」,也沒有另一隻杯子與他的碰在一起,他的生活可能早就以另一種方式瓦解了,換了個紙杯子,碰也碰不出聲響來。
▎鏡中鵝
──于大雪終究是到了異鄉,任這裡風景如畫空氣清新,這都不是他于大雪的家。
「我哥沒了。」于大雪的妹妹輕輕扶著郭建新的肩膀啜泣,郭建新呆坐在那把屬於探病親屬的木椅上,始終沉默。于大雪早年離婚後與前妻已沒了情誼,跟了前妻的女兒也直到此刻收到訊息才答應過來奔喪。
護士說于大雪一直艱難地維持著呼吸,直到聽見那句「老郭來了」才走,前後不過幾秒鐘。
坐在那把木椅上,郭建新覺得自己慢慢變輕了,回憶的縫隙中每一個于大雪的身影都被宇宙收回了造物的魔盒中。過去四十七年的生活在此刻坍塌成一個點壓在他心口上,他好像一張被巨人踩在地面的紙,足夠輕盈,輕盈到可以飛起來,卻不得絲毫自由。
▎月亮成熟時
──「你喜歡今天的月亮窩?那我就給你摘下來!」
回想到那個夜晚,即便苟姐已經年過五十,依然是滿面潮紅。
她已經想不起來上一次和丈夫親密是什麼時候,或許再仔細想想還能勉強記起。但再上一次呢?上上次呢?手中那塊阿穆送給她的石頭,就像回憶裡他的觸感,堅實而粗糙。
或許記憶的用處便在於此,在生命漫長的枯萎中提醒自己,曾經豐盛的樣子。
本書特色:本書為熊德啟所著,收錄七篇短篇小說。他在自述裡說:「故事裡有發著光的生命,可以點亮那些過於黑暗的夜晚。」這些故事訴說了很多人的人生,有令人難受的地方,也有令人惆悵的回憶。但那些生命中的微光,就算只有一點點,也能使漫漫長夜多一些溫暖。
作者簡介
熊德啟,作家,媒體人。2013年起發表短篇小說作品,見於網路與文學期刊,著有《這一切並沒有那麼糟》。
序
序
多年前,我在電視臺工作,出差去南方縣城。
入夜的國道一片漆黑,本在車上昏睡的我被一束微光喚醒。
是國道邊的水站,那種給大貨車加水降溫的地方。門口掛著牌子,一面寫著「加水」,一面寫著「賣麻鴨」,在風裡來回搖擺。空地上坐著一個赤膊的男孩,抱著一盞檯燈,在看一本書。
身為寫作者,我問自己:他在看什麼樣的故事?
如果能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意味著某種暢銷的密碼──當時我是這麼認為的。
那個男孩曾無數次出現在我因為寫作不順而焦慮煩躁的腦海裡。他到底愛看什麼呢?他到底會因為什麼而感動?我寫的這些東西他會喜歡嗎?至今沒有答案。
於是我對自己提出另一個問題:他有什麼樣的故事?
這個問題最後變成了一篇小說,叫《詩的證言》,也收錄在這本小說集裡。
這或許是他的故事,或許是我的故事,或許也是你的故事。
說到底,我們都需要故事。
故事裡有發著光的生命,可以點亮那些過於黑暗的夜晚。
熊德啟
多年前,我在電視臺工作,出差去南方縣城。
入夜的國道一片漆黑,本在車上昏睡的我被一束微光喚醒。
是國道邊的水站,那種給大貨車加水降溫的地方。門口掛著牌子,一面寫著「加水」,一面寫著「賣麻鴨」,在風裡來回搖擺。空地上坐著一個赤膊的男孩,抱著一盞檯燈,在看一本書。
身為寫作者,我問自己:他在看什麼樣的故事?
如果能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意味著某種暢銷的密碼──當時我是這麼認為的。
那個男孩曾無數次出現在我因為寫作不順而焦慮煩躁的腦海裡。他到底愛看什麼呢?他到底會因為什麼而感動?我寫的這些東西他會喜歡嗎?至今沒有答案。
於是我對自己提出另一個問題:他有什麼樣的故事?
這個問題最後變成了一篇小說,叫《詩的證言》,也收錄在這本小說集裡。
這或許是他的故事,或許是我的故事,或許也是你的故事。
說到底,我們都需要故事。
故事裡有發著光的生命,可以點亮那些過於黑暗的夜晚。
熊德啟
目次
序
江城子
詩的證言
鏡中鵝
沒有光的房間
鐵蛋
月亮成熟時
聽見貓聲
江城子
詩的證言
鏡中鵝
沒有光的房間
鐵蛋
月亮成熟時
聽見貓聲
書摘/試閱
江城子
無夢的一夜,醒來萬事如常。王常友決定去殺一個人。
如果王常友有個足夠親密的人可以分享這件事,那人或許會對他說:你精神有問題吧?
但他沒有了。
作案工具已經選好,那把平時用來削萵筍的菜刀,刀頭拐彎,能吃得上勁兒。姿勢也選好了,從側頸砍下去,利刃入肉,斜著一拉,肯定活不了。
後續也有了安排,刀找個魚塘扔掉,趁著事情沒敗露的時候趕緊坐車回老家。等回到小縣城,再想個辦法把自己搞死。倒也算是個計畫,就是「想個辦法把自己搞死」這最後一步有些模糊。說來也好笑,殺別人的思路還挺清晰,殺自己反而沒什麼想法。
服毒不可靠,王常友見過喝二氯松被救回來的人,那真是生不如死。而且退一萬步說,現在這世道,二氯松也不知道是不是假貨,萬一吃錯了藥,人沒死成還進了醫院,連住院費都結不起。跳樓是個選項,可惜老家的縣城裡一片荒蕪,別說高樓,完整的樓也沒剩幾棟。找個矮地方跳下來萬一不小心再殘了一條腿,以後連樓都上不去了。
媽的,還是讀書讀少了,沒文化,連自殺的辦法都如此匱乏。
菜刀別在腰後的皮帶上,穿上衣兜最多的一件外套,揣上身分證、菸、打火機,抓了一把火腿腸和散碎的紙鈔,喝下一大碗水,出門。
王常友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殺誰呢?
「老王!出門啦?我今天要晚上才上班哈!」
這是一個四十來歲的男人,叫金老二,在街對面二樓的公共陽臺上遠遠地對王常友喊著。這縣城雖不大,但王常友並沒什麼說得上話的人,金老二算一個。王常友抬起眼皮和他打了個哈哈,撩起左邊的褲腿給他看了看。
「哎喲!今天不開張啊?那你過來打牌嘛!缺幾塊錢菸錢,等你湊起!」金老二叼著根菸露出一臉痞笑,向王常友招手。
「呸!」王常友一口濃痰噴射出去。
王常友不是武俠小說裡吐棗核殺人的怪胎,這一口痰只是他與世界相處的方式。痰自然是噴不到金老二的身上,落在了馬路中央,日光照射下還有些亮眼,全然不似渾濁的汙穢,倒像是誰遺落的硬幣,一輛車碾過去,終於匯入爛泥。也不再理仍在叫囂的金老二,王常友直接往前走,搖搖晃晃的樣子像隻企鵝。走了幾步,舉起右手,遙遠地朝金老二豎起一根中指。
「要不然我輸你點兒?拿去鉸個頭!看你一副鬼樣子,嚇死個人!」金老二還在嘟囔著。
王常友一邊走一邊想:金老二這個人,殺不殺?
也不知想了些什麼,最後決定,算了。隨後又想:為什麼算了?是不是因為金老二這個人雖然嘴碎,但其實對自己還算過得去,不是個壞人?可是放眼望去,這街上來來往往的,誰又是個壞人呢?
這到底算不算是個理由?王常友不知道。
金老二一根菸還沒抽完,怎麼也想不到,笑罵之間,自己已經去鬼門關敲過一次門。
王常友住的地方離高速公路的出口不遠,出口的收費站下面是個陡坡,下坡就是個急彎,雖然好幾處都裝了凸面鏡,也攔不注意外時常發生。
這些意外裡,一小半都和王常友有關。
王常友的左腿從大腿根以下全沒了,裝了支義肢。也正是這義肢,賦予了他和其他碰瓷者不一樣的競爭力。
普通的碰瓷,最難的是傷情鑑定,往往都說自己被撞出了內傷,但內傷這個事情太主觀,可大可小,總是扯皮。而如果像王常友一樣有義肢加持就不同了,義肢這東西很明確,壞了就是壞了,褲腿一拉,一眼就能看出來。清晰,毫無爭議,明碼實價。
當然,王常友有兩支義肢,平日生活裡用好的那支,「做生意」的時候,直接戴那支壞掉的。起初還真傷到過自己,後來稍微注意點姿勢,摔得漂亮,起來後褲腿一拉,直接要錢。
本地車王常友堅決不碰,只找外地車,因為這畢竟是個長久生意,外地車一般都是過客,在本地毫無根繫,撞了就認栽,不至於回來找碴兒。撞完了從地上起來,先熱情地表示自己人沒事,叫對方別擔心,司機往往在此刻就放鬆了警惕。然後再假裝要走,再次摔倒,直到這時候王常友才亮出其實本就損壞的義肢。
司機一看,完蛋,認栽。
這時候就要學會看車要價,一兩百,四五百,七八百,要是遇上個穿一身好牌子又慌慌張張的菜鳥,能要到一千。
王常友的日子雖不富裕,但好在過得輕鬆,生意好的時候也能抽上一包十九塊的黃鶴樓,喝上一壺精裝二鍋頭。
這樣的好日子,王常友今天不過了。殺人去。
王常友想殺人很久了,他只是一直想不好殺完了人該怎麼辦,以及到底要殺誰。
從很多年前見到自己的整條左腿被橫擺在面前的那一天開始,王常友在這世上就成了一個徹底的局外人。他一早就知道,也慢慢接受了這個事實──這世界沒有他也一樣歌舞昇平,沒有他也一樣殘忍無情,他王常友已經影響不了這世界的一分一毫。如今就連殺人,似乎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縫隙下刀,殺不進這被一道透明結界嚴絲合縫地遮罩起來的世界。
那就隨便殺吧,總之是要殺一個。
按城裡人的話說,王常友屬於「移動辦公」,沒事的時候就到處轉悠。殺人地點他已經盤算了很久:一處偏僻的橋洞,二三十公尺的長度,沒有燈,沒有監控。
下午的陽光斜斜地把橋洞兩端劃出了兩道黑白分明的界限,好像邁出一步,就要從日光踏入深淵。王常友猥瑣地蹲在暗處,絲毫沒有殺手的氣質,活脫脫像個乞丐,要討一條命。
等,是王常友擅長的事情。他享受這樣的感覺──不過是一次簡單的相逢,對方的生活就因此發生改變。雖然這改變大多時候也就是幾百塊的事情,但這種對他人命運的主宰、這種自己去選擇的感覺、這種自己有選擇的感覺,讓他上癮。
一根菸抽完,撩起褲腿,把義肢和鞋子縫隙裡的菸灰吹乾淨,就好像平時一樣。也不知道會是哪個瓜娃子今天選擇了這條死路,王常友暗暗想著。可惜直到天光散盡,橋洞以外的世界也被劃入黑暗,菸抽完了,火腿腸也吃完了,王常友還是沒等來他要殺的人。
或許是他選的這個地方太偏了,幾個小時裡只有一輛汽車從這裡疾馳而過,車速太快了,像王常友這樣的「專業人士」也來不及反應,甚至都沒看清楚是哪個品牌。其實就算反應過來了也無濟於事,人在車裡,在鋼筋鐵皮之中,憑王常友一把削萵筍的菜刀,憑王常友一雙殘了一半的腿,刺不穿,追不到,殺不成。
熱鬧的地方人多,但王常友不敢去,因為跑不掉。那些地方都是紅塵,他覺得自己殺不了紅塵,反而紅塵會殺了他。
不行,王常友心想,如果再遇上一輛車,還需要把人從車裡搞出來,才好殺。
再一想,這事情簡單啊,本行!
沒了菸,等待也焦躁起來,又過去一個多小時才遠遠地看見一輛車過來,王常友終於打起了精神,右手摸著腰間的刀柄,像在盤玩著一塊木頭。
車雖尚遠,但這車燈一看就知道是鄉下最常見的小麵包車,鏽掉的鐵皮「哐啷哐啷」地響著,昭示著車主多半不是一個有錢人。好在王常友最終的目的也不是碰瓷,有錢沒錢也不在意了。或許沒錢還更好一點,沒錢就沒那麼重要。
入夜以後,人在暗處,車卻在明處。
這樣的情況下,碰瓷是個技術活,因為司機的視野並不開闊,車速也快,一不留神就容易真的把自己撞死。王常友是有打算去死,但畢竟壯志未酬,至少也是「弱志未酬」,身還得留著。
菜刀挪到了腰前,刀面橫向前方來反射燈光,算是警示,同時需要在車子離自己尚有一段距離的時候提前發出尖銳的哀號,給足司機煞車的空間。
其實還有一個疑問:萬一這車裡不止一個人怎麼辦?但王常友殺心沸騰,也管不了那麼多了。
沉默的夜晚,這世上一定有誰並不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至,但這人到底是誰?
車進橋洞,王常友從麵包車的右前方斜殺出來,一邊哀號著一邊隨時準備隱蔽地躲閃。但那車就好像看不到他一般,遲疑了幾個瞬間才做出反應,煞車踩晚了,急轉方向,一頭扎向了橋洞一側的牆壁。王常友被扎實地撞飛了幾公尺遠,身體的疼痛讓腎上腺素噴湧而出,全身的血液都湧上頭來,滿臉通紅。
正欲起身拔刀,忽然間胯下一空,腎上腺素驟然退潮。面朝泥濘,王常友意識到,自己唯一一條完好的義肢,斷了。
無夢的一夜,醒來萬事如常。王常友決定去殺一個人。
如果王常友有個足夠親密的人可以分享這件事,那人或許會對他說:你精神有問題吧?
但他沒有了。
作案工具已經選好,那把平時用來削萵筍的菜刀,刀頭拐彎,能吃得上勁兒。姿勢也選好了,從側頸砍下去,利刃入肉,斜著一拉,肯定活不了。
後續也有了安排,刀找個魚塘扔掉,趁著事情沒敗露的時候趕緊坐車回老家。等回到小縣城,再想個辦法把自己搞死。倒也算是個計畫,就是「想個辦法把自己搞死」這最後一步有些模糊。說來也好笑,殺別人的思路還挺清晰,殺自己反而沒什麼想法。
服毒不可靠,王常友見過喝二氯松被救回來的人,那真是生不如死。而且退一萬步說,現在這世道,二氯松也不知道是不是假貨,萬一吃錯了藥,人沒死成還進了醫院,連住院費都結不起。跳樓是個選項,可惜老家的縣城裡一片荒蕪,別說高樓,完整的樓也沒剩幾棟。找個矮地方跳下來萬一不小心再殘了一條腿,以後連樓都上不去了。
媽的,還是讀書讀少了,沒文化,連自殺的辦法都如此匱乏。
菜刀別在腰後的皮帶上,穿上衣兜最多的一件外套,揣上身分證、菸、打火機,抓了一把火腿腸和散碎的紙鈔,喝下一大碗水,出門。
王常友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殺誰呢?
「老王!出門啦?我今天要晚上才上班哈!」
這是一個四十來歲的男人,叫金老二,在街對面二樓的公共陽臺上遠遠地對王常友喊著。這縣城雖不大,但王常友並沒什麼說得上話的人,金老二算一個。王常友抬起眼皮和他打了個哈哈,撩起左邊的褲腿給他看了看。
「哎喲!今天不開張啊?那你過來打牌嘛!缺幾塊錢菸錢,等你湊起!」金老二叼著根菸露出一臉痞笑,向王常友招手。
「呸!」王常友一口濃痰噴射出去。
王常友不是武俠小說裡吐棗核殺人的怪胎,這一口痰只是他與世界相處的方式。痰自然是噴不到金老二的身上,落在了馬路中央,日光照射下還有些亮眼,全然不似渾濁的汙穢,倒像是誰遺落的硬幣,一輛車碾過去,終於匯入爛泥。也不再理仍在叫囂的金老二,王常友直接往前走,搖搖晃晃的樣子像隻企鵝。走了幾步,舉起右手,遙遠地朝金老二豎起一根中指。
「要不然我輸你點兒?拿去鉸個頭!看你一副鬼樣子,嚇死個人!」金老二還在嘟囔著。
王常友一邊走一邊想:金老二這個人,殺不殺?
也不知想了些什麼,最後決定,算了。隨後又想:為什麼算了?是不是因為金老二這個人雖然嘴碎,但其實對自己還算過得去,不是個壞人?可是放眼望去,這街上來來往往的,誰又是個壞人呢?
這到底算不算是個理由?王常友不知道。
金老二一根菸還沒抽完,怎麼也想不到,笑罵之間,自己已經去鬼門關敲過一次門。
王常友住的地方離高速公路的出口不遠,出口的收費站下面是個陡坡,下坡就是個急彎,雖然好幾處都裝了凸面鏡,也攔不注意外時常發生。
這些意外裡,一小半都和王常友有關。
王常友的左腿從大腿根以下全沒了,裝了支義肢。也正是這義肢,賦予了他和其他碰瓷者不一樣的競爭力。
普通的碰瓷,最難的是傷情鑑定,往往都說自己被撞出了內傷,但內傷這個事情太主觀,可大可小,總是扯皮。而如果像王常友一樣有義肢加持就不同了,義肢這東西很明確,壞了就是壞了,褲腿一拉,一眼就能看出來。清晰,毫無爭議,明碼實價。
當然,王常友有兩支義肢,平日生活裡用好的那支,「做生意」的時候,直接戴那支壞掉的。起初還真傷到過自己,後來稍微注意點姿勢,摔得漂亮,起來後褲腿一拉,直接要錢。
本地車王常友堅決不碰,只找外地車,因為這畢竟是個長久生意,外地車一般都是過客,在本地毫無根繫,撞了就認栽,不至於回來找碴兒。撞完了從地上起來,先熱情地表示自己人沒事,叫對方別擔心,司機往往在此刻就放鬆了警惕。然後再假裝要走,再次摔倒,直到這時候王常友才亮出其實本就損壞的義肢。
司機一看,完蛋,認栽。
這時候就要學會看車要價,一兩百,四五百,七八百,要是遇上個穿一身好牌子又慌慌張張的菜鳥,能要到一千。
王常友的日子雖不富裕,但好在過得輕鬆,生意好的時候也能抽上一包十九塊的黃鶴樓,喝上一壺精裝二鍋頭。
這樣的好日子,王常友今天不過了。殺人去。
王常友想殺人很久了,他只是一直想不好殺完了人該怎麼辦,以及到底要殺誰。
從很多年前見到自己的整條左腿被橫擺在面前的那一天開始,王常友在這世上就成了一個徹底的局外人。他一早就知道,也慢慢接受了這個事實──這世界沒有他也一樣歌舞昇平,沒有他也一樣殘忍無情,他王常友已經影響不了這世界的一分一毫。如今就連殺人,似乎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縫隙下刀,殺不進這被一道透明結界嚴絲合縫地遮罩起來的世界。
那就隨便殺吧,總之是要殺一個。
按城裡人的話說,王常友屬於「移動辦公」,沒事的時候就到處轉悠。殺人地點他已經盤算了很久:一處偏僻的橋洞,二三十公尺的長度,沒有燈,沒有監控。
下午的陽光斜斜地把橋洞兩端劃出了兩道黑白分明的界限,好像邁出一步,就要從日光踏入深淵。王常友猥瑣地蹲在暗處,絲毫沒有殺手的氣質,活脫脫像個乞丐,要討一條命。
等,是王常友擅長的事情。他享受這樣的感覺──不過是一次簡單的相逢,對方的生活就因此發生改變。雖然這改變大多時候也就是幾百塊的事情,但這種對他人命運的主宰、這種自己去選擇的感覺、這種自己有選擇的感覺,讓他上癮。
一根菸抽完,撩起褲腿,把義肢和鞋子縫隙裡的菸灰吹乾淨,就好像平時一樣。也不知道會是哪個瓜娃子今天選擇了這條死路,王常友暗暗想著。可惜直到天光散盡,橋洞以外的世界也被劃入黑暗,菸抽完了,火腿腸也吃完了,王常友還是沒等來他要殺的人。
或許是他選的這個地方太偏了,幾個小時裡只有一輛汽車從這裡疾馳而過,車速太快了,像王常友這樣的「專業人士」也來不及反應,甚至都沒看清楚是哪個品牌。其實就算反應過來了也無濟於事,人在車裡,在鋼筋鐵皮之中,憑王常友一把削萵筍的菜刀,憑王常友一雙殘了一半的腿,刺不穿,追不到,殺不成。
熱鬧的地方人多,但王常友不敢去,因為跑不掉。那些地方都是紅塵,他覺得自己殺不了紅塵,反而紅塵會殺了他。
不行,王常友心想,如果再遇上一輛車,還需要把人從車裡搞出來,才好殺。
再一想,這事情簡單啊,本行!
沒了菸,等待也焦躁起來,又過去一個多小時才遠遠地看見一輛車過來,王常友終於打起了精神,右手摸著腰間的刀柄,像在盤玩著一塊木頭。
車雖尚遠,但這車燈一看就知道是鄉下最常見的小麵包車,鏽掉的鐵皮「哐啷哐啷」地響著,昭示著車主多半不是一個有錢人。好在王常友最終的目的也不是碰瓷,有錢沒錢也不在意了。或許沒錢還更好一點,沒錢就沒那麼重要。
入夜以後,人在暗處,車卻在明處。
這樣的情況下,碰瓷是個技術活,因為司機的視野並不開闊,車速也快,一不留神就容易真的把自己撞死。王常友是有打算去死,但畢竟壯志未酬,至少也是「弱志未酬」,身還得留著。
菜刀挪到了腰前,刀面橫向前方來反射燈光,算是警示,同時需要在車子離自己尚有一段距離的時候提前發出尖銳的哀號,給足司機煞車的空間。
其實還有一個疑問:萬一這車裡不止一個人怎麼辦?但王常友殺心沸騰,也管不了那麼多了。
沉默的夜晚,這世上一定有誰並不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至,但這人到底是誰?
車進橋洞,王常友從麵包車的右前方斜殺出來,一邊哀號著一邊隨時準備隱蔽地躲閃。但那車就好像看不到他一般,遲疑了幾個瞬間才做出反應,煞車踩晚了,急轉方向,一頭扎向了橋洞一側的牆壁。王常友被扎實地撞飛了幾公尺遠,身體的疼痛讓腎上腺素噴湧而出,全身的血液都湧上頭來,滿臉通紅。
正欲起身拔刀,忽然間胯下一空,腎上腺素驟然退潮。面朝泥濘,王常友意識到,自己唯一一條完好的義肢,斷了。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