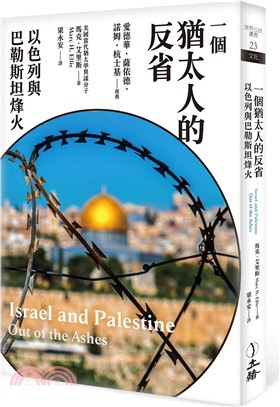一個猶太人的反省: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烽火
- 系列名:世界公民叢書
- ISBN13:9789863602194
- 替代書名:Israel and Palestine:Out of the Ashes
- 出版社:立緒文化
- 作者:馬克.艾里斯
- 譯者:梁永安
- 裝訂/頁數:平裝/336頁
- 規格:21cm*15cm*2cm (高/寬/厚)
- 版次:初版
- 出版日:2023/11/28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以色列、巴勒斯坦烽硝萬里,
美國當代猶太學異議分子馬克.艾里斯,超越大屠殺及受難者角色的觀點,
別有識見地省思猶太認同與以巴衝突複雜難解的文化脈絡。
.一個關乎報復、寬恕、正義與道德的問題。
超越主流媒體政治分析,開啟猶太人意義命題新視野,更揭櫫以色列好戰本質。
.知名文化評論家愛德華.薩依德、諾姆.杭士基推薦!
「身為猶太人,我們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壓迫他人的民族?我們是否已經忘卻自己一再努力宣揚的大屠殺教訓?難道我們日以繼夜用武裝直昇機、火箭威嚇甚至攻擊巴勒斯坦城鎮,為的是給後代子孫建立榜樣?」――本書作者馬克.艾里斯
在全世界懷著驚恐目睹以巴對峙引爆的各種衝突之際,本書作者馬克.艾里斯以其猶太裔美籍學者的身分,別有識見地深入探討此一猶太認同的危機時刻。
他提出猶太人唯有勇於面對軍事化的以色列及美國猶太領導階層視而未見的問題,才能創造出以巴未來的和平願景。
本書作者是一位美國猶太學異議分子,受到猶太道德傳統與大屠殺結束後的猶太生命矛盾影響至深且鉅,並在面對日益具有侵略性的以色列提出各種要求時,設法挽救猶太道德傳統。他指出:「每一個文化與傳統的消失,對人類來說都是一種減損,有時候去哀悼已消失的文化傳統比去著手打造一個新的更容易。」
「在我們曾經繼承的那個猶太歷史已經死亡的今天,猶太人喜歡在猶太會堂和公眾場所哀悼死者,就像只有透過留在過去,猶太人才有辦法肯定人生。一個死亡與摧毀的循環只要一被經歷過,它就會自動運轉,直到哀悼本身成為一種生活而後已。」
今天大部分的猶太人,正是以這樣的態度在生活,正是以被迫害者的身分對巴勒斯坦人進行迫害。在以美國為主的強勢媒體主導下,許多人並不知道以色列不斷在擴張,以及慢性阻斷巴人生機的事實。知名文化評論家愛德華.薩依德為此多年在國際間奔走呼號,但他所代表的畢竟是他自己的族人。
本書所難能可貴的是,馬克.艾里斯以猶太知識分子的身分,超越媒體慣於提供的政治分析,延伸及於精神發展的本質,檢視個人在大屠殺落幕未幾猶存的震撼中,試圖為猶太生命的未來樹立典範,不但超越大屠殺及將猶太人定位為受難者或加害者的觀點,也為當今身為猶太人的意義命題開啟了新的視野。
許多具備良知的猶太知識分子(如第一任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校長Judah Magnes、知名聖經學家與神學家Martin Buber、政治與人類學家Hannah Arendt等),皆認為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將導致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流離失所,而讓阿拉伯人無家可歸,等於是讓猶太人在整個歷史裡無家可歸的狀況重演。他們主張兩民族共存,成立一個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共同組成的聯邦國家。一位猶太受難者後裔也說:「雖然吃過種種苦,我們仍然得堅持正義。只有正義而非報復才是出路,大屠殺的教訓是暴力的循環必須予以終止,沒有別的出路。」
本書代表許多具備自覺的猶太知識分子的思維,帶領讀者走出直線思考,跳脫加害者與受害者角色,唯有如此,才能找到新的自由。持續多年的以巴烽火,至今追求和平無蹤,更值得我們深深反思。
※舊版書名:遠離煙硝
美國當代猶太學異議分子馬克.艾里斯,超越大屠殺及受難者角色的觀點,
別有識見地省思猶太認同與以巴衝突複雜難解的文化脈絡。
.一個關乎報復、寬恕、正義與道德的問題。
超越主流媒體政治分析,開啟猶太人意義命題新視野,更揭櫫以色列好戰本質。
.知名文化評論家愛德華.薩依德、諾姆.杭士基推薦!
「身為猶太人,我們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壓迫他人的民族?我們是否已經忘卻自己一再努力宣揚的大屠殺教訓?難道我們日以繼夜用武裝直昇機、火箭威嚇甚至攻擊巴勒斯坦城鎮,為的是給後代子孫建立榜樣?」――本書作者馬克.艾里斯
在全世界懷著驚恐目睹以巴對峙引爆的各種衝突之際,本書作者馬克.艾里斯以其猶太裔美籍學者的身分,別有識見地深入探討此一猶太認同的危機時刻。
他提出猶太人唯有勇於面對軍事化的以色列及美國猶太領導階層視而未見的問題,才能創造出以巴未來的和平願景。
本書作者是一位美國猶太學異議分子,受到猶太道德傳統與大屠殺結束後的猶太生命矛盾影響至深且鉅,並在面對日益具有侵略性的以色列提出各種要求時,設法挽救猶太道德傳統。他指出:「每一個文化與傳統的消失,對人類來說都是一種減損,有時候去哀悼已消失的文化傳統比去著手打造一個新的更容易。」
「在我們曾經繼承的那個猶太歷史已經死亡的今天,猶太人喜歡在猶太會堂和公眾場所哀悼死者,就像只有透過留在過去,猶太人才有辦法肯定人生。一個死亡與摧毀的循環只要一被經歷過,它就會自動運轉,直到哀悼本身成為一種生活而後已。」
今天大部分的猶太人,正是以這樣的態度在生活,正是以被迫害者的身分對巴勒斯坦人進行迫害。在以美國為主的強勢媒體主導下,許多人並不知道以色列不斷在擴張,以及慢性阻斷巴人生機的事實。知名文化評論家愛德華.薩依德為此多年在國際間奔走呼號,但他所代表的畢竟是他自己的族人。
本書所難能可貴的是,馬克.艾里斯以猶太知識分子的身分,超越媒體慣於提供的政治分析,延伸及於精神發展的本質,檢視個人在大屠殺落幕未幾猶存的震撼中,試圖為猶太生命的未來樹立典範,不但超越大屠殺及將猶太人定位為受難者或加害者的觀點,也為當今身為猶太人的意義命題開啟了新的視野。
許多具備良知的猶太知識分子(如第一任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校長Judah Magnes、知名聖經學家與神學家Martin Buber、政治與人類學家Hannah Arendt等),皆認為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將導致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流離失所,而讓阿拉伯人無家可歸,等於是讓猶太人在整個歷史裡無家可歸的狀況重演。他們主張兩民族共存,成立一個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共同組成的聯邦國家。一位猶太受難者後裔也說:「雖然吃過種種苦,我們仍然得堅持正義。只有正義而非報復才是出路,大屠殺的教訓是暴力的循環必須予以終止,沒有別的出路。」
本書代表許多具備自覺的猶太知識分子的思維,帶領讀者走出直線思考,跳脫加害者與受害者角色,唯有如此,才能找到新的自由。持續多年的以巴烽火,至今追求和平無蹤,更值得我們深深反思。
※舊版書名:遠離煙硝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馬克.艾里斯(Marc H. Ellis)
美籍猶太裔學者,1952年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北邁阿密灘區,就讀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宗教暨美國研究所期間,受教於大屠殺神學家理查.魯本斯坦及美國歷史學家威廉.米勒門下;1980年取得馬奎特大學的當代美國社會暨宗教思想學博士學位。1988年擔任紐約瑪利諾神學院教授;1995年擔任哈佛大學「世界宗教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隨後轉任哈佛大學「中東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及佛羅里達大學客座教授。1998年,獲聘為拜勒大學的美國暨猶太研究所教授,翌年創辦拜勒大學的美國暨猶太研究中心。
著有《歐洲猶太主義》、《以色列獨立報》等著作十餘種,廣受愛德華.薩依德、諾姆.杭士基、圖圖大主教等人推薦。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台灣大學文化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班肄業。目前為專業翻譯者,譯著包括《心靈的棲地:愛德華.薩依德傳》(Places of Mind: A Life of Edward Said / Timothy Brennan)、《文化與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 / Edward W. Said)、《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 Peter Gay)、《現代主義》(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 / Peter Gay)等。
馬克.艾里斯(Marc H. Ellis)
美籍猶太裔學者,1952年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北邁阿密灘區,就讀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宗教暨美國研究所期間,受教於大屠殺神學家理查.魯本斯坦及美國歷史學家威廉.米勒門下;1980年取得馬奎特大學的當代美國社會暨宗教思想學博士學位。1988年擔任紐約瑪利諾神學院教授;1995年擔任哈佛大學「世界宗教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隨後轉任哈佛大學「中東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及佛羅里達大學客座教授。1998年,獲聘為拜勒大學的美國暨猶太研究所教授,翌年創辦拜勒大學的美國暨猶太研究中心。
著有《歐洲猶太主義》、《以色列獨立報》等著作十餘種,廣受愛德華.薩依德、諾姆.杭士基、圖圖大主教等人推薦。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台灣大學文化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班肄業。目前為專業翻譯者,譯著包括《心靈的棲地:愛德華.薩依德傳》(Places of Mind: A Life of Edward Said / Timothy Brennan)、《文化與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 / Edward W. Said)、《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 Peter Gay)、《現代主義》(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 / Peter Gay)等。
序
自序 ◎馬克.艾里斯(Maec H. Ellis)
大屠殺成了猶太生活的避風港;
猶太人因它而可以自稱獨一無二、清白無辜和享有特權。
我們是來自大屠殺之後、來自以色列建國之後的,
但弔詭的是,兩個事件卻仍然活在我們記憶中和受到利用。
我們該怎麼對待猶太人的歷史與猶太人的現在呢?
我們怎樣才能自稱擁有一種忠於過去和現在的猶太品性?
在這個猶太人把一切揮霍於瘋狂競逐國家權勢的時代,
我們又要怎樣見證猶太歷史上有過的價值觀和連綿不斷的奮鬥?
------------------------------------------------------------------------------------------------
儘管已有的一些轉變會繼續發揮作用,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以巴地區的「地圖」基本上將會維持今貌。巴勒斯坦人的建國也許是無可避免的,但這不但不會動搖我此說,反而會加強它。因為即使巴勒斯坦人建國,從台拉維夫到約旦河一片地域的控制權仍將掌握在以色列手中。以色列不只已經征服了該區,還會透過直接管轄和代理人繼續控有它,而且會對那些沒有多少巴勒斯坦人口的土地進行佔領、屯墾與開發。
對於這種征服,除以色列內外有少數猶太人會發出異議外,猶太社群將不加批評地接受。在以色列和美國兩地,猶太社群將會繼續重申他們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主要民族,擁有各種歷史、政治、文化和宗教上的權利。儘管猶太民族人數不多(世界六十億多人口裡只佔一千四百萬),它還是會繼續宣稱猶太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猶太歷史與倫理將會繼續被教導給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繼續被說成是一神信仰的發源者,因此是世界值得學習的楷模。納粹大屠殺將會繼續被猶太人說成是獨一無二的事件,是真正大苦大難的象徵:它是無可比擬的,只有大屠殺受難者的後代子孫能了解其深重程度。
因為對世界有過種種貢獻和經歷過重大苦難,猶太人將會在其大權在握的情況下繼續深信自己清白無辜。儘管以色列的權勢多年來備受爭議,但其權勢大得足以讓它不理會批評,繼續保護和投射大屠殺作為猶太人、猶太教和猶太世界主要認同對象的角色。
大屠殺成了猶太生活的避風港;猶太人因它而可以自稱獨一無二、清白無辜和享有特權。諷刺的是,這個避風港雖然被反覆搬出來和受到公開紀念,但大屠殺的恐怖所帶給猶太人的心理創傷卻並未因此得到撫平。這是因為此避風港是以向國家與權力同化為本質的,是以向摧毀與殘暴同化為本質的,也因此是與大屠殺留給後人的每一個警告、每一個教訓唱反調的。當體現這個警告的民族利用大屠殺的教訓來壓迫其他民族時,大屠殺事件的意義就會被矮化。
我相信,整個猶太民族的歷史如今已經因猶太人對巴勒斯坦人的征服而被矮化。身為猶太人,我們是來自大屠殺之後、來自以色列建國之後的,但弔詭的是,兩個事件卻仍然活在我們記憶中和受到利用。我們這種生活在之後的處境,讓二十一世紀猶太生活的困難性和可塑性變得格外突出。
我們該怎麼對待猶太人的歷史與猶太人的現在呢?我們怎樣才能自稱擁有一種忠於過去和現在的猶太品性(Jewishness)?在這個猶太人把一切揮霍在瘋狂競逐國家權勢的時代,我們又要怎樣見證猶太歷史上有過的價值觀和連綿不斷的奮鬥?
在本書中,我嘗試建構一個敘事性的論證,希望它可以指出一個值得我們留給子孫的未來。然而,落實這個未來的工作,我(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只能留給後代子孫去做,只能希望他們可以見證到猶太教和猶太生活目前正在消失中的一面。
在把此書呈獻給廣大讀者時,我意識到書中的調子是參差的。有些部份是用第一人稱寫的,要藉我的個人經歷作為一些困難問題的引子。有些部份是分析性的,利用「地圖」和「公共政策」去戳破神話和說明議題。有些部份是哲學和宗教性的,會詮釋一些觀念和《聖經》中的主題,把它們應用到當代世界,特別是應用在後大屠殺和後以色列時代的猶太身份認同的問題。
本書的調子參差也反映出一件事。與猶太身份認同相關的各種議題極少是可以單獨透過個人經歷、觀念或政治的領域爬梳的。相反地,任何想釐清這些議題的作品都必須進行經驗與思想的複雜綜合,而即使它這樣做了,得到的解決方案仍是權宜性的。
在世界上當猶太人牽涉到一種讓人目迷的複雜性,它有時會讓人氣餒,但常常也輸入了幹勁。因為別人對猶太人的看法,加上猶太人內部對猶太品性問題的關心,讓一個猶太人很少可以有沈默的時候。整個猶太歷史都體現出,當猶太人是件全職的工作,會帶來巨大的內部和外部後果。我們貧窮和被壓迫時是如此,今天我們已經變富裕、被接納和擁有權力時也是如此。
我感激所有陪伴過我,給予我力量摸索一個不同於今日的猶太未來的人。我把本書獻給太太安妮,為她多年來對我的愛和穩定支持。我也要特別感謝拉森(Matthew Larsen)在這本書出版過程中給我的技術和編務上的協助。
未來會帶來什麼,只有時間才能分曉。我始終相信,猶太生活和猶太教是可能在世界上開闢出一條合乎倫理道德的道路的。儘管我不低估實現這個願景的困
難度,但我仍然強調這個願景的重要性。在我看來,投身這種困難任務正是猶太人之所以為猶太人的理由。這就是我的忠誠(fidelity)。
大屠殺成了猶太生活的避風港;
猶太人因它而可以自稱獨一無二、清白無辜和享有特權。
我們是來自大屠殺之後、來自以色列建國之後的,
但弔詭的是,兩個事件卻仍然活在我們記憶中和受到利用。
我們該怎麼對待猶太人的歷史與猶太人的現在呢?
我們怎樣才能自稱擁有一種忠於過去和現在的猶太品性?
在這個猶太人把一切揮霍於瘋狂競逐國家權勢的時代,
我們又要怎樣見證猶太歷史上有過的價值觀和連綿不斷的奮鬥?
------------------------------------------------------------------------------------------------
儘管已有的一些轉變會繼續發揮作用,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以巴地區的「地圖」基本上將會維持今貌。巴勒斯坦人的建國也許是無可避免的,但這不但不會動搖我此說,反而會加強它。因為即使巴勒斯坦人建國,從台拉維夫到約旦河一片地域的控制權仍將掌握在以色列手中。以色列不只已經征服了該區,還會透過直接管轄和代理人繼續控有它,而且會對那些沒有多少巴勒斯坦人口的土地進行佔領、屯墾與開發。
對於這種征服,除以色列內外有少數猶太人會發出異議外,猶太社群將不加批評地接受。在以色列和美國兩地,猶太社群將會繼續重申他們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主要民族,擁有各種歷史、政治、文化和宗教上的權利。儘管猶太民族人數不多(世界六十億多人口裡只佔一千四百萬),它還是會繼續宣稱猶太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猶太歷史與倫理將會繼續被教導給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繼續被說成是一神信仰的發源者,因此是世界值得學習的楷模。納粹大屠殺將會繼續被猶太人說成是獨一無二的事件,是真正大苦大難的象徵:它是無可比擬的,只有大屠殺受難者的後代子孫能了解其深重程度。
因為對世界有過種種貢獻和經歷過重大苦難,猶太人將會在其大權在握的情況下繼續深信自己清白無辜。儘管以色列的權勢多年來備受爭議,但其權勢大得足以讓它不理會批評,繼續保護和投射大屠殺作為猶太人、猶太教和猶太世界主要認同對象的角色。
大屠殺成了猶太生活的避風港;猶太人因它而可以自稱獨一無二、清白無辜和享有特權。諷刺的是,這個避風港雖然被反覆搬出來和受到公開紀念,但大屠殺的恐怖所帶給猶太人的心理創傷卻並未因此得到撫平。這是因為此避風港是以向國家與權力同化為本質的,是以向摧毀與殘暴同化為本質的,也因此是與大屠殺留給後人的每一個警告、每一個教訓唱反調的。當體現這個警告的民族利用大屠殺的教訓來壓迫其他民族時,大屠殺事件的意義就會被矮化。
我相信,整個猶太民族的歷史如今已經因猶太人對巴勒斯坦人的征服而被矮化。身為猶太人,我們是來自大屠殺之後、來自以色列建國之後的,但弔詭的是,兩個事件卻仍然活在我們記憶中和受到利用。我們這種生活在之後的處境,讓二十一世紀猶太生活的困難性和可塑性變得格外突出。
我們該怎麼對待猶太人的歷史與猶太人的現在呢?我們怎樣才能自稱擁有一種忠於過去和現在的猶太品性(Jewishness)?在這個猶太人把一切揮霍在瘋狂競逐國家權勢的時代,我們又要怎樣見證猶太歷史上有過的價值觀和連綿不斷的奮鬥?
在本書中,我嘗試建構一個敘事性的論證,希望它可以指出一個值得我們留給子孫的未來。然而,落實這個未來的工作,我(就像我們所有人一樣)只能留給後代子孫去做,只能希望他們可以見證到猶太教和猶太生活目前正在消失中的一面。
在把此書呈獻給廣大讀者時,我意識到書中的調子是參差的。有些部份是用第一人稱寫的,要藉我的個人經歷作為一些困難問題的引子。有些部份是分析性的,利用「地圖」和「公共政策」去戳破神話和說明議題。有些部份是哲學和宗教性的,會詮釋一些觀念和《聖經》中的主題,把它們應用到當代世界,特別是應用在後大屠殺和後以色列時代的猶太身份認同的問題。
本書的調子參差也反映出一件事。與猶太身份認同相關的各種議題極少是可以單獨透過個人經歷、觀念或政治的領域爬梳的。相反地,任何想釐清這些議題的作品都必須進行經驗與思想的複雜綜合,而即使它這樣做了,得到的解決方案仍是權宜性的。
在世界上當猶太人牽涉到一種讓人目迷的複雜性,它有時會讓人氣餒,但常常也輸入了幹勁。因為別人對猶太人的看法,加上猶太人內部對猶太品性問題的關心,讓一個猶太人很少可以有沈默的時候。整個猶太歷史都體現出,當猶太人是件全職的工作,會帶來巨大的內部和外部後果。我們貧窮和被壓迫時是如此,今天我們已經變富裕、被接納和擁有權力時也是如此。
我感激所有陪伴過我,給予我力量摸索一個不同於今日的猶太未來的人。我把本書獻給太太安妮,為她多年來對我的愛和穩定支持。我也要特別感謝拉森(Matthew Larsen)在這本書出版過程中給我的技術和編務上的協助。
未來會帶來什麼,只有時間才能分曉。我始終相信,猶太生活和猶太教是可能在世界上開闢出一條合乎倫理道德的道路的。儘管我不低估實現這個願景的困
難度,但我仍然強調這個願景的重要性。在我看來,投身這種困難任務正是猶太人之所以為猶太人的理由。這就是我的忠誠(fidelity)。
目次
自序/馬克.艾里斯(Marc H. Ellis)
導言 基督城的蠻牛
1|後大屠殺時代的猶太記憶
記憶、毀滅與抵抗
第六一五條誡命
盤旋在猶太歷史核心的武裝直昇機
2|清白無辜、屯墾者與國家政策
君士坦丁式猶太教的來臨
原住民的權利、公民權與新耶路撒冷
繪製大屠殺和以色列的地圖
3|後大屠殺時代的先知傳統
當代世界的先知
聖約在歷史中的發展演化
今日的先知事工
4|體現在放逐的猶太見證
我們命運的邊界
改造猶太教與猶太生活
革命性寬恕
體現在放逐的猶太見證
結語 走出灰燼
導言 基督城的蠻牛
1|後大屠殺時代的猶太記憶
記憶、毀滅與抵抗
第六一五條誡命
盤旋在猶太歷史核心的武裝直昇機
2|清白無辜、屯墾者與國家政策
君士坦丁式猶太教的來臨
原住民的權利、公民權與新耶路撒冷
繪製大屠殺和以色列的地圖
3|後大屠殺時代的先知傳統
當代世界的先知
聖約在歷史中的發展演化
今日的先知事工
4|體現在放逐的猶太見證
我們命運的邊界
改造猶太教與猶太生活
革命性寬恕
體現在放逐的猶太見證
結語 走出灰燼
書摘/試閱
導言:基督城的蠻牛
A Bully in Christchurch
身為猶太人,我們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壓迫他人的民族?我們是否已經忘卻自己一再努力宣揚的大屠殺教訓?難道我們日以繼夜用武裝直昇機、火箭威嚇甚至攻擊巴勒斯坦城鎮,為的是給後代子孫建立榜樣?
以色列不斷擴張的事實,它的領土已經從台拉維夫延伸到約旦河而其中包含三百萬巴勒斯坦人的事實,都是大部份美國人與猶太人所不知道的。
猶太人在二十世紀對巴勒斯坦人伸出援手,意義將等同於異教徒在納粹時期對猶太人伸出援手。
不久前,我自澳洲雪梨搭機轉往紐西蘭的基督城(Christchurch)──我的「追尋公義」全球巡迴演說之旅的最後一站。在此之前,我陸續在英國、德國、印度等地,針對不久前爆發的阿克薩抗暴運動發表演說,最後兩站是澳洲和紐西蘭。我想要提醒世人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之人權與民族權的事實。
身為在美國出生的猶太人,我與同世代的其他後大屠殺時代猶太人一樣,自幼接受公平正義的價值觀薰陶,眼見以色列一再變本加厲的好戰姿態,深感沮喪。以色列動用武裝直昇機對付不設防的巴勒斯坦城鎮、村落、難民營的行徑使我憤怒。我無法保持沈默。
的確,我開始明白,唯一用途只是摧毀與殺人的武裝直昇機已經成為當代猶太生活的界定者。在腦海裡,我看到約櫃裡的《托拉》(Torah)經卷──它代表的是上帝、正義與和平──已經被挪走,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力量與權勢、不問道德不問是非的武裝直昇機。畢竟,行為就是信仰的反映。
於是,我有了這趟巡迴演說之旅。在短短兩個月內,我向每場數以十計的聽眾抒發個人有關這個問題的看法,只有少數幾個人試圖打斷演說。事實上,演說之旅給我一個強烈印象:各地的人們非常擔心以色列政府的舉動。他們對發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一切同樣深以為憂。
在這趟旅途中,我曾經向幾個猶太團體發表演說,其中包括英國的自由派猶太教拉比團體、墨爾本的猶太團體,以及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的猶太研究班。此外,我也會晤了一些猶太人,包括以色列的猶太人。他們的憂慮和我相同:身為猶太人,我們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壓迫他人的民族?我們是否已經忘卻自己一再努力宣揚的大屠殺教訓?難道我們日以繼夜用武裝直昇機、火箭威嚇甚至攻擊巴勒斯坦城鎮,為的是給後代子孫建立榜樣?
這樣的巡迴演說是費時又費力的,趕路時間多,睡眠時間少。不過卻也值得。我經常和其他猶太同胞進行深入的感性討論,也曾經和熱愛聖地的非猶太人討論一些問題,當然也曾和身家性命捲入其事的巴勒斯坦人相互討論。
雖然此行收穫豐富,但我記得最清楚的卻是一些刺耳的音調,一些言語性與非言語性的對峙,而對方往往是猶太人;他們總不忘提醒我:以巴衝突攸關猶太歷史的核心與前途。
我在基督城的坎特伯雷大學就有過一次這樣的經驗。在到訪的第一天,接待者邀我旁聽以色列籍的猶太訪問學者兼政治活躍份子尤塞.歐莫特(Yossi Olmert)的演講。在演講結束後,我和他共進午餐。當天晚上,我被安排和他共同出席一個以以巴衝突為主題的座談會。
我稍後得知,原來尤塞.歐莫特博士是耶路撒冷市長艾胡德.歐莫特(Ehud Olmert)的兄弟。兩人都是民族主義者,政治立場傾向於比金(Menachem Begin)、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和夏隆(Ariel Sharon)的右派陣營。以色列駐紐西蘭大使館函請他來訪,做為他亞太訪問行程的一站。他亞太行的目的是反駁國際社會批評以色列武力鎮壓阿克薩抗暴運動的聲浪。
在上午的演講中,歐莫特首先談及要把以巴衝突放在中東地區這個更大的背景來檢視。他正確地指出,想要了解較小的以巴地區,就得先了解較大的中東地區。而這個較大脈絡的有趣之處──至少歐莫特是這樣認為的──是它的毛病多多。根據他的說法,中東地區的幾個主要問題包括人口過多、低度發展、缺少民主和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高張。這些因素的糅合助長了惡性的暴力循環:一九八○年代的兩伊戰爭、伊拉克一九九○年代初入侵科威特,以及不斷盤旋上升的軍備競賽皆是明證。
歐莫特對這些事實感到難過,指出暴力與戰爭是一種只會帶來動亂的浪費。不過令我感到訝異的是,他的分析相當浮面。他把中東地區籠統視為一整體,對它提出一些抽象的概括,對中東各國的差異性幾乎隻字不提。在他對細節的省略中,甚至在他的抽象概括中,在在讓人覺得阿拉伯國家都失敗得可以,而走向不穩定、獨裁和恐怖主義則是它們的宿命。
隨後他把焦點移到以巴衝突本身。歐莫特不諱言自己是民族主義者和右翼主義者,他認為以色列的國土不只應該包含耶路撒冷,還應該包含約旦河西岸──他稱之為「猶太與撒瑪利亞」(Judea and Samaria)。歐莫特事實上是要主張一個大以色列,而他認為這是於《聖經》有據的。至於巴勒斯坦人長久以來住在這地區的事實,歐莫特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頂多只會對落實大以色列的目標構成小小不便。巴勒斯坦人以此提出的土地權利主張,是完全無法與猶太人提出者較量的。
至於耶路撒冷,他指出猶太人在兩千多年流離的歲月裡,未嘗有一天不為失去它而哀痛,未嘗有一天不祈願可以回到這聖城。所以,現在猶太人對耶路撒冷的主權主張是沒有商量餘地的。巴勒斯坦人有權在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做禮拜,但也僅止於如此。夏隆政府曾坦承,暗殺巴勒斯坦人確實是其政策之一,方法包括利用手機引爆炸彈、出動武裝直昇機等等。歐莫特認為,這些都是針對以色列平民承受的恐怖攻擊所採取的報復。它們不但站得住腳,而且應該延續甚至加強。
值得吃驚的並不是歐莫特的觀念。他的論述──一種把對阿拉伯世界的浮面分析和猶太人對以巴地區主權主張過簡肯定加在一起的論述──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就是以色列國內民族主義右派圈子裡的老生常談。雖然歐莫特小心翼翼把自己和拉賓(Yitzhak Rabin)遇刺事件畫清界線(他稱此事件是「令人不恥的」),我卻認為,他的觀點和兇手艾米爾(Yigal Amir)相當接近。也就是說,艾米爾對阿拉伯人與巴勒斯坦人的看法和歐莫特的看法無大不同。
演講進入發問階段後,歐莫特的情緒愈來愈高昂,概括的言詞更加鋪天蓋地。他以更加否定性的措詞形容阿拉伯人與穆斯林,同時奚落包括紐西蘭與美國在內的中東事務局外人(當然包括住在以色列之外的猶太人),竟然膽敢越以色列代俎,提出以道德選項作為今日應對之道。他說這些「局外人」批判以色列是容易的,因為他們並不住在以色列,也不用付出血淚代價。他認為應該讓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自行解決問題,至於「以色列應該接受國際法的約束」和「以色列迄今仰仗美國財政與軍事支援」之說,他皆嗤之以鼻。
隨著晚間座談會的時間愈來愈接近,我開始擔心,座談會不會變成他的獨腳戲,而對猶太教來說具有核心性的正義和道德原則會不會被他形容為烏托邦和奚落為愚蠢。或是他會說堅持這些原則只會為以色列和居住其中的猶太人帶來災難。
因為,不管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破壞了多少秩序和禮節,但如果阿拉伯人得勢,他們不是會做一樣的事,不是會把猶太人趕到大海裡去嗎?難道這不就是街上每一個阿拉伯人和每一個阿拉伯政府從今直到永遠想做的事嗎?難道為巴勒斯坦人請命的道德論證不是虛矯的,只會帶來另一次大屠殺?這樣,我和其他批判以色列的人,不是只在助長一場暴力和復仇的風暴,而這風暴會帶給猶太人的災難,將不亞於甚至超過他們在二十世紀所遭受的集體屠殺?
不幸的是,我對座談會完整性的擔憂果然應驗。歐莫特主控全部的討論過程,彷彿這只是一場獨白的說教。他的發言時間不但超過規定,甚至多次抗拒旁人請他打住的提醒。隨著發言的時間愈來愈長,他的情緒更加激動、高昂。
歐莫特一提再提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之前的年代,說當時約旦佔有東耶路撒冷,任由古代猶太聖殿的最後一處殘跡哭牆淪為各種動物便溺和人們堆積垃圾之所。當然,今天的猶太人已經控制這個地區,並允許穆斯林享有在這裡禮拜的權利。然而,當我們問他以色列為什麼禁止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巴勒斯坦人接近耶城,為什麼有系統地把老人逐出(這些政策都是歐莫特的市長哥哥執行的)?如此一來,穆斯林究竟還有什麼自由可言,歐莫特只是以更堅定的語氣重申,阿拉伯人一再褻瀆猶太聖地。
在晚間的座談會結束後,我返回住宿的地方,反覆回想座談會的發言內容,幾乎覺得自己受到肉體侵犯一般。我是不是因為歐莫特展現與許多擅於言詞激昂的以色列人一樣的辯論技巧而感到痛苦?我是不是在言詞交鋒方面敗下陣來,只能無奈地自怨自艾?
到了翌日上午,我對前一個晚上又產生另一種不同的感覺。我覺得,歐莫特並未以他的辯論技巧或就事論事的態度主控全場,而是以強詞奪理的方法主控。這種對於他或擁有武力優勢地位的以色列之理解令人聯想到懦夫的行為,並使我在想到以色列及它的未來前途時,油然興起更濃厚的傷感。以色列人並非全部都是恃強凌弱或強詞奪理,問題是,以色列大使館為何出面邀請他踏上這一次的巡迴演說之旅?為什麼以色列大使館的一名女性官員會出現在會場?為什麼歐莫特的談話內容會使她顯得那麼高興?
歐莫特在致結語時再次強調,住在以色列之外的猶太與非猶太異議者的言行只會對以色列帶來破壞作用和負面效果。他又以蔑視的語氣談到我的批評。在他的批評中,有一句話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他甚至不是講我們的話的。」
這話讓我很受傷──不過只是在剛開始的時候。因為後來仔細一想,他此語比他自己所以為的還要正確。年輕時我就學過禮儀用的希伯來語,能讀和寫這種希伯來語。在猶太歷史的大部份時期,希伯來語就是那樣的語言──一種美麗而深刻的禮儀用語言。隨著以色列建國,希伯來語變成了一種現代口語,帶有許多變異與採借。就像大部份住在以色列之外的猶太人一樣,我並不會說這種口語。在歐莫特看來,這一點讓我對猶太教與猶太生活的置喙資格產生疑問。顯然,他認為貨真價實的猶太人都是住在以色列的,而且會主張和他一樣的立場。
但我相信,要是座談會上有任何進步派(progressive)的以色列猶太人在座,他從歐莫特得到的對待一定會和我得到的如出一轍。因為就在同一天,以色列的進步派猶太和平組織「和平集團」(Gush Shalom)才呼籲國際社會派出和平部隊監督佔領區的情況和保護巴勒斯坦人。難道這個團體的成員的猶太成份會比歐莫特少嗎?這些猶太人雖然操現代希伯來語,但歐莫特會認為他們是講「我們」的話嗎?
我好奇歐莫特講的語言到底是以希伯來語還是以強詞奪理為本質。現代希伯來語會有這個創新的方面,是因為它被從禮儀的領域移植到民族國家的領域嗎,是因為它不再那麼常用來讚美上帝而是用來投射國家權力的關係嗎?這種原來謙遜的語言現在受到一種瀆武主義的徵召,配合武裝直昇機去教訓一個沒有抵抗力的民族。
我確實不是和歐莫特講同一種語言,我也不想講他的語言。我懷疑,世俗化而又把猶太教誡命(一些以道德與正義為導向的誡命)拋諸腦後的歐莫特,是否代表操希伯來語的異教徒已經降臨人間。而我是不是一群不講希伯來語的猶太餘民(remnant)之一,追求的是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相互扶持,是彼此權利的互相承認?「我們」那種暴烈的語言──一種代表權力與權勢的語言──是不是標誌著猶太人已經重回隔都(ghetto)的心靈狀態,唯一不同只是這一次已經擁有核子武器?
我和歐莫特交手僅僅一個月後,紐約和華府就驚傳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在很多人看來,這攻擊只是印證了一個以色列人知之已久的道理:阿拉伯人都是恐怖份子。有些人認為,歐莫特想要教給我們的一課,現在我們「親自」上到了。另一些人則相信,我們現在需要採取的是一種暴力與復仇的語言,因為這是「他們」聽得懂的唯一語言。
然而,我卻覺得那個「基督城的蠻牛」有如一扇窗,可以讓人看見猶太世界過去幾十年來已經發展變化成什麼樣子。隨著以色列國家力量的擴張以及美國猶裔菁英勢力的急劇膨脹,全世界的猶太生活已經動員化(mobilized)與軍事化。
不過,這種變化的軌跡卻經常被誤判,被解釋成是猶太基本教義派和在耶路撒冷四周或約旦河西岸屯墾的右翼宗教性猶太人所煽的風、點的火。然而,儘管這些人不是沒有責任(他們顯然讓本來難解的局面雪上加霜)但猶太基本教義派在以色列和猶太世界裡其實是後來者(latecomer)。
歐莫特是猶太基本教義的同路人,不過他同樣是後來者。事實上,離開了一種自由派―歐洲脈絡―世俗性的猶太論述(liberal-European-secular Jewish narrative),以色列的持續擴張是無法理解的,也正是這種論述讓作為民族國家的以色列得以創建和鞏固。
這種論述結合了一個歐洲的脈絡和一種被發展出來的後大屠殺意識。所謂歐洲的脈絡,是指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作為少數民族的歐洲猶太人意識到,他們想要在現代歐洲過上安樂日子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難重重。後大屠殺意識則是指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之後,世人(特別是美國人)開始紀念大屠殺,並把以色列視為對猶太苦難的補償和猶太人存續的維繫者。如果我們把歐洲的
猶太脈絡簡稱為「錫安主義」(Zionism),把美國的猶太脈絡簡稱為「大屠殺/以色列認同」(Holocaust/Israel identification),那我們就掌握住了以色列得以建國和維持的基本動力。
顯然,「錫安主義」和「大屠殺/以色列認同」兩者的內容無論在最初或後來都是複雜和分歧的。歷史地說,錫安主義有許多種,包括主張復國的錫安主義、主張建立家園的錫安主義,以及兩者中間許多程度各異的折衷版本。「大屠殺/以色列認同」在五○和六○年代都不強,但在六○年代後期和七○年代則轉趨強勁。今天,隨著美國猶裔經濟和政治菁英的節節得勢,「錫安主義」已完全為「大屠殺/以色列認同」蓋過。
讀者需要知道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歐洲和美國,「錫安主義」和「大屠殺/以色列認同」的動力全然是世俗性的,儘管那是一種猶太式的世俗性。其內容包括對猶太民族的忠誠奉獻,把《聖經》解讀為一種持續上演中的歷史敘事,以及對國家與民族有一種歷史命運感。
另一方面,「錫安主義」和「大屠殺/以色列認同」的發展應該放在一個自由派的架構下理解,這架構有時帶有社會主義的成份,而且常常帶有非宗教或反宗教的情感。以色列的創建者都是徹底的世俗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他們的動力來自一種最廣義的猶太倫理:他們自視為追求人道主義大業的國際主義者。那些在美國率先推動「大屠殺/以色列」論述的人也是自由派,擁護民權和一個對所有人開放的社會。
他們會提出這種論述,是因為知道正統派猶太教對美國的猶太社群殊少意義,這一方面是美國生活的現代化所致,另一方面是大屠殺衍生的宗教難題所致。雖然反思大屠殺的人對上帝在大屠殺期間或之後是否臨在(presence)的問題意見不一,但卻一致同意,大屠殺之後猶太人的主要宗教任務在於記住大屠殺和建立以色列國。一九六八年,加拿大猶裔哲學家法根海姆(Emil Fackenheim)在作品中重申這種觀點,並稱之為第六一四條誡命(614th commandments),認為它可以補充甚至取代猶太教本來的六百一十三條誡命。
另一件我們必須知道的事情是,在一九六七年的以阿戰爭之後,隨著主張復國的錫安主義的勝利與「大屠殺/以色列認同」在美國的熱烈化,兩件次要(但愈來愈重要)的事情之基礎被奠定了:一是宗教性的屯墾運動,一是世俗性的極端民族主義。要從這時候起,也就是在以色列佔領、兼併了東耶路撒冷和在約旦河西岸推行屯墾政策開始,如今被稱為猶太基本教義派才開始欣欣向榮。
耶路撒冷對宗教猶太人和世俗猶太人兩者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然而,在以色列獲得戰爭勝利後的那些歲月,耶路撒冷被強調的是它宗教方面的意義。就像耶路撒冷一樣,被宗教猶太人稱為「猶太與撒瑪利亞」的約旦河西岸也包含許多古代的宗教遺址。耶路撒冷擁有古代聖殿西牆的殘跡,約旦河西岸則擁有亞伯拉罕、撒拉(Sarah)、拉結(Rachel)等人的墓穴。對憧憬在應許之地重建猶太生活的猶太人來說,這些遺址具有非凡的宗教與歷史意義。
然而,軍事上的勝利和隨後展開的屯墾計畫卻讓圍繞耶路撒冷的宗教運動無用武之地。在緊接六日戰爭之後那段關鍵時期,以色列政府基於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考量,決定兼併和擴大耶路撒冷,並在其四周建立屯墾區,以資防護。由於基本教義派在當時還不能左右以色列政府,所以,兼併耶路撒冷和在約旦河西岸實施屯墾之舉,應該被視為是出於國家經過盤算後制定的擴張政策。
(全文未完)
A Bully in Christchurch
身為猶太人,我們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壓迫他人的民族?我們是否已經忘卻自己一再努力宣揚的大屠殺教訓?難道我們日以繼夜用武裝直昇機、火箭威嚇甚至攻擊巴勒斯坦城鎮,為的是給後代子孫建立榜樣?
以色列不斷擴張的事實,它的領土已經從台拉維夫延伸到約旦河而其中包含三百萬巴勒斯坦人的事實,都是大部份美國人與猶太人所不知道的。
猶太人在二十世紀對巴勒斯坦人伸出援手,意義將等同於異教徒在納粹時期對猶太人伸出援手。
不久前,我自澳洲雪梨搭機轉往紐西蘭的基督城(Christchurch)──我的「追尋公義」全球巡迴演說之旅的最後一站。在此之前,我陸續在英國、德國、印度等地,針對不久前爆發的阿克薩抗暴運動發表演說,最後兩站是澳洲和紐西蘭。我想要提醒世人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之人權與民族權的事實。
身為在美國出生的猶太人,我與同世代的其他後大屠殺時代猶太人一樣,自幼接受公平正義的價值觀薰陶,眼見以色列一再變本加厲的好戰姿態,深感沮喪。以色列動用武裝直昇機對付不設防的巴勒斯坦城鎮、村落、難民營的行徑使我憤怒。我無法保持沈默。
的確,我開始明白,唯一用途只是摧毀與殺人的武裝直昇機已經成為當代猶太生活的界定者。在腦海裡,我看到約櫃裡的《托拉》(Torah)經卷──它代表的是上帝、正義與和平──已經被挪走,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力量與權勢、不問道德不問是非的武裝直昇機。畢竟,行為就是信仰的反映。
於是,我有了這趟巡迴演說之旅。在短短兩個月內,我向每場數以十計的聽眾抒發個人有關這個問題的看法,只有少數幾個人試圖打斷演說。事實上,演說之旅給我一個強烈印象:各地的人們非常擔心以色列政府的舉動。他們對發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一切同樣深以為憂。
在這趟旅途中,我曾經向幾個猶太團體發表演說,其中包括英國的自由派猶太教拉比團體、墨爾本的猶太團體,以及雪梨新南威爾斯大學的猶太研究班。此外,我也會晤了一些猶太人,包括以色列的猶太人。他們的憂慮和我相同:身為猶太人,我們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壓迫他人的民族?我們是否已經忘卻自己一再努力宣揚的大屠殺教訓?難道我們日以繼夜用武裝直昇機、火箭威嚇甚至攻擊巴勒斯坦城鎮,為的是給後代子孫建立榜樣?
這樣的巡迴演說是費時又費力的,趕路時間多,睡眠時間少。不過卻也值得。我經常和其他猶太同胞進行深入的感性討論,也曾經和熱愛聖地的非猶太人討論一些問題,當然也曾和身家性命捲入其事的巴勒斯坦人相互討論。
雖然此行收穫豐富,但我記得最清楚的卻是一些刺耳的音調,一些言語性與非言語性的對峙,而對方往往是猶太人;他們總不忘提醒我:以巴衝突攸關猶太歷史的核心與前途。
我在基督城的坎特伯雷大學就有過一次這樣的經驗。在到訪的第一天,接待者邀我旁聽以色列籍的猶太訪問學者兼政治活躍份子尤塞.歐莫特(Yossi Olmert)的演講。在演講結束後,我和他共進午餐。當天晚上,我被安排和他共同出席一個以以巴衝突為主題的座談會。
我稍後得知,原來尤塞.歐莫特博士是耶路撒冷市長艾胡德.歐莫特(Ehud Olmert)的兄弟。兩人都是民族主義者,政治立場傾向於比金(Menachem Begin)、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和夏隆(Ariel Sharon)的右派陣營。以色列駐紐西蘭大使館函請他來訪,做為他亞太訪問行程的一站。他亞太行的目的是反駁國際社會批評以色列武力鎮壓阿克薩抗暴運動的聲浪。
在上午的演講中,歐莫特首先談及要把以巴衝突放在中東地區這個更大的背景來檢視。他正確地指出,想要了解較小的以巴地區,就得先了解較大的中東地區。而這個較大脈絡的有趣之處──至少歐莫特是這樣認為的──是它的毛病多多。根據他的說法,中東地區的幾個主要問題包括人口過多、低度發展、缺少民主和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高張。這些因素的糅合助長了惡性的暴力循環:一九八○年代的兩伊戰爭、伊拉克一九九○年代初入侵科威特,以及不斷盤旋上升的軍備競賽皆是明證。
歐莫特對這些事實感到難過,指出暴力與戰爭是一種只會帶來動亂的浪費。不過令我感到訝異的是,他的分析相當浮面。他把中東地區籠統視為一整體,對它提出一些抽象的概括,對中東各國的差異性幾乎隻字不提。在他對細節的省略中,甚至在他的抽象概括中,在在讓人覺得阿拉伯國家都失敗得可以,而走向不穩定、獨裁和恐怖主義則是它們的宿命。
隨後他把焦點移到以巴衝突本身。歐莫特不諱言自己是民族主義者和右翼主義者,他認為以色列的國土不只應該包含耶路撒冷,還應該包含約旦河西岸──他稱之為「猶太與撒瑪利亞」(Judea and Samaria)。歐莫特事實上是要主張一個大以色列,而他認為這是於《聖經》有據的。至於巴勒斯坦人長久以來住在這地區的事實,歐莫特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頂多只會對落實大以色列的目標構成小小不便。巴勒斯坦人以此提出的土地權利主張,是完全無法與猶太人提出者較量的。
至於耶路撒冷,他指出猶太人在兩千多年流離的歲月裡,未嘗有一天不為失去它而哀痛,未嘗有一天不祈願可以回到這聖城。所以,現在猶太人對耶路撒冷的主權主張是沒有商量餘地的。巴勒斯坦人有權在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做禮拜,但也僅止於如此。夏隆政府曾坦承,暗殺巴勒斯坦人確實是其政策之一,方法包括利用手機引爆炸彈、出動武裝直昇機等等。歐莫特認為,這些都是針對以色列平民承受的恐怖攻擊所採取的報復。它們不但站得住腳,而且應該延續甚至加強。
值得吃驚的並不是歐莫特的觀念。他的論述──一種把對阿拉伯世界的浮面分析和猶太人對以巴地區主權主張過簡肯定加在一起的論述──過去幾十年來一直就是以色列國內民族主義右派圈子裡的老生常談。雖然歐莫特小心翼翼把自己和拉賓(Yitzhak Rabin)遇刺事件畫清界線(他稱此事件是「令人不恥的」),我卻認為,他的觀點和兇手艾米爾(Yigal Amir)相當接近。也就是說,艾米爾對阿拉伯人與巴勒斯坦人的看法和歐莫特的看法無大不同。
演講進入發問階段後,歐莫特的情緒愈來愈高昂,概括的言詞更加鋪天蓋地。他以更加否定性的措詞形容阿拉伯人與穆斯林,同時奚落包括紐西蘭與美國在內的中東事務局外人(當然包括住在以色列之外的猶太人),竟然膽敢越以色列代俎,提出以道德選項作為今日應對之道。他說這些「局外人」批判以色列是容易的,因為他們並不住在以色列,也不用付出血淚代價。他認為應該讓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自行解決問題,至於「以色列應該接受國際法的約束」和「以色列迄今仰仗美國財政與軍事支援」之說,他皆嗤之以鼻。
隨著晚間座談會的時間愈來愈接近,我開始擔心,座談會不會變成他的獨腳戲,而對猶太教來說具有核心性的正義和道德原則會不會被他形容為烏托邦和奚落為愚蠢。或是他會說堅持這些原則只會為以色列和居住其中的猶太人帶來災難。
因為,不管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破壞了多少秩序和禮節,但如果阿拉伯人得勢,他們不是會做一樣的事,不是會把猶太人趕到大海裡去嗎?難道這不就是街上每一個阿拉伯人和每一個阿拉伯政府從今直到永遠想做的事嗎?難道為巴勒斯坦人請命的道德論證不是虛矯的,只會帶來另一次大屠殺?這樣,我和其他批判以色列的人,不是只在助長一場暴力和復仇的風暴,而這風暴會帶給猶太人的災難,將不亞於甚至超過他們在二十世紀所遭受的集體屠殺?
不幸的是,我對座談會完整性的擔憂果然應驗。歐莫特主控全部的討論過程,彷彿這只是一場獨白的說教。他的發言時間不但超過規定,甚至多次抗拒旁人請他打住的提醒。隨著發言的時間愈來愈長,他的情緒更加激動、高昂。
歐莫特一提再提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之前的年代,說當時約旦佔有東耶路撒冷,任由古代猶太聖殿的最後一處殘跡哭牆淪為各種動物便溺和人們堆積垃圾之所。當然,今天的猶太人已經控制這個地區,並允許穆斯林享有在這裡禮拜的權利。然而,當我們問他以色列為什麼禁止住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巴勒斯坦人接近耶城,為什麼有系統地把老人逐出(這些政策都是歐莫特的市長哥哥執行的)?如此一來,穆斯林究竟還有什麼自由可言,歐莫特只是以更堅定的語氣重申,阿拉伯人一再褻瀆猶太聖地。
在晚間的座談會結束後,我返回住宿的地方,反覆回想座談會的發言內容,幾乎覺得自己受到肉體侵犯一般。我是不是因為歐莫特展現與許多擅於言詞激昂的以色列人一樣的辯論技巧而感到痛苦?我是不是在言詞交鋒方面敗下陣來,只能無奈地自怨自艾?
到了翌日上午,我對前一個晚上又產生另一種不同的感覺。我覺得,歐莫特並未以他的辯論技巧或就事論事的態度主控全場,而是以強詞奪理的方法主控。這種對於他或擁有武力優勢地位的以色列之理解令人聯想到懦夫的行為,並使我在想到以色列及它的未來前途時,油然興起更濃厚的傷感。以色列人並非全部都是恃強凌弱或強詞奪理,問題是,以色列大使館為何出面邀請他踏上這一次的巡迴演說之旅?為什麼以色列大使館的一名女性官員會出現在會場?為什麼歐莫特的談話內容會使她顯得那麼高興?
歐莫特在致結語時再次強調,住在以色列之外的猶太與非猶太異議者的言行只會對以色列帶來破壞作用和負面效果。他又以蔑視的語氣談到我的批評。在他的批評中,有一句話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他甚至不是講我們的話的。」
這話讓我很受傷──不過只是在剛開始的時候。因為後來仔細一想,他此語比他自己所以為的還要正確。年輕時我就學過禮儀用的希伯來語,能讀和寫這種希伯來語。在猶太歷史的大部份時期,希伯來語就是那樣的語言──一種美麗而深刻的禮儀用語言。隨著以色列建國,希伯來語變成了一種現代口語,帶有許多變異與採借。就像大部份住在以色列之外的猶太人一樣,我並不會說這種口語。在歐莫特看來,這一點讓我對猶太教與猶太生活的置喙資格產生疑問。顯然,他認為貨真價實的猶太人都是住在以色列的,而且會主張和他一樣的立場。
但我相信,要是座談會上有任何進步派(progressive)的以色列猶太人在座,他從歐莫特得到的對待一定會和我得到的如出一轍。因為就在同一天,以色列的進步派猶太和平組織「和平集團」(Gush Shalom)才呼籲國際社會派出和平部隊監督佔領區的情況和保護巴勒斯坦人。難道這個團體的成員的猶太成份會比歐莫特少嗎?這些猶太人雖然操現代希伯來語,但歐莫特會認為他們是講「我們」的話嗎?
我好奇歐莫特講的語言到底是以希伯來語還是以強詞奪理為本質。現代希伯來語會有這個創新的方面,是因為它被從禮儀的領域移植到民族國家的領域嗎,是因為它不再那麼常用來讚美上帝而是用來投射國家權力的關係嗎?這種原來謙遜的語言現在受到一種瀆武主義的徵召,配合武裝直昇機去教訓一個沒有抵抗力的民族。
我確實不是和歐莫特講同一種語言,我也不想講他的語言。我懷疑,世俗化而又把猶太教誡命(一些以道德與正義為導向的誡命)拋諸腦後的歐莫特,是否代表操希伯來語的異教徒已經降臨人間。而我是不是一群不講希伯來語的猶太餘民(remnant)之一,追求的是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相互扶持,是彼此權利的互相承認?「我們」那種暴烈的語言──一種代表權力與權勢的語言──是不是標誌著猶太人已經重回隔都(ghetto)的心靈狀態,唯一不同只是這一次已經擁有核子武器?
我和歐莫特交手僅僅一個月後,紐約和華府就驚傳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在很多人看來,這攻擊只是印證了一個以色列人知之已久的道理:阿拉伯人都是恐怖份子。有些人認為,歐莫特想要教給我們的一課,現在我們「親自」上到了。另一些人則相信,我們現在需要採取的是一種暴力與復仇的語言,因為這是「他們」聽得懂的唯一語言。
然而,我卻覺得那個「基督城的蠻牛」有如一扇窗,可以讓人看見猶太世界過去幾十年來已經發展變化成什麼樣子。隨著以色列國家力量的擴張以及美國猶裔菁英勢力的急劇膨脹,全世界的猶太生活已經動員化(mobilized)與軍事化。
不過,這種變化的軌跡卻經常被誤判,被解釋成是猶太基本教義派和在耶路撒冷四周或約旦河西岸屯墾的右翼宗教性猶太人所煽的風、點的火。然而,儘管這些人不是沒有責任(他們顯然讓本來難解的局面雪上加霜)但猶太基本教義派在以色列和猶太世界裡其實是後來者(latecomer)。
歐莫特是猶太基本教義的同路人,不過他同樣是後來者。事實上,離開了一種自由派―歐洲脈絡―世俗性的猶太論述(liberal-European-secular Jewish narrative),以色列的持續擴張是無法理解的,也正是這種論述讓作為民族國家的以色列得以創建和鞏固。
這種論述結合了一個歐洲的脈絡和一種被發展出來的後大屠殺意識。所謂歐洲的脈絡,是指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作為少數民族的歐洲猶太人意識到,他們想要在現代歐洲過上安樂日子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難重重。後大屠殺意識則是指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之後,世人(特別是美國人)開始紀念大屠殺,並把以色列視為對猶太苦難的補償和猶太人存續的維繫者。如果我們把歐洲的
猶太脈絡簡稱為「錫安主義」(Zionism),把美國的猶太脈絡簡稱為「大屠殺/以色列認同」(Holocaust/Israel identification),那我們就掌握住了以色列得以建國和維持的基本動力。
顯然,「錫安主義」和「大屠殺/以色列認同」兩者的內容無論在最初或後來都是複雜和分歧的。歷史地說,錫安主義有許多種,包括主張復國的錫安主義、主張建立家園的錫安主義,以及兩者中間許多程度各異的折衷版本。「大屠殺/以色列認同」在五○和六○年代都不強,但在六○年代後期和七○年代則轉趨強勁。今天,隨著美國猶裔經濟和政治菁英的節節得勢,「錫安主義」已完全為「大屠殺/以色列認同」蓋過。
讀者需要知道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歐洲和美國,「錫安主義」和「大屠殺/以色列認同」的動力全然是世俗性的,儘管那是一種猶太式的世俗性。其內容包括對猶太民族的忠誠奉獻,把《聖經》解讀為一種持續上演中的歷史敘事,以及對國家與民族有一種歷史命運感。
另一方面,「錫安主義」和「大屠殺/以色列認同」的發展應該放在一個自由派的架構下理解,這架構有時帶有社會主義的成份,而且常常帶有非宗教或反宗教的情感。以色列的創建者都是徹底的世俗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他們的動力來自一種最廣義的猶太倫理:他們自視為追求人道主義大業的國際主義者。那些在美國率先推動「大屠殺/以色列」論述的人也是自由派,擁護民權和一個對所有人開放的社會。
他們會提出這種論述,是因為知道正統派猶太教對美國的猶太社群殊少意義,這一方面是美國生活的現代化所致,另一方面是大屠殺衍生的宗教難題所致。雖然反思大屠殺的人對上帝在大屠殺期間或之後是否臨在(presence)的問題意見不一,但卻一致同意,大屠殺之後猶太人的主要宗教任務在於記住大屠殺和建立以色列國。一九六八年,加拿大猶裔哲學家法根海姆(Emil Fackenheim)在作品中重申這種觀點,並稱之為第六一四條誡命(614th commandments),認為它可以補充甚至取代猶太教本來的六百一十三條誡命。
另一件我們必須知道的事情是,在一九六七年的以阿戰爭之後,隨著主張復國的錫安主義的勝利與「大屠殺/以色列認同」在美國的熱烈化,兩件次要(但愈來愈重要)的事情之基礎被奠定了:一是宗教性的屯墾運動,一是世俗性的極端民族主義。要從這時候起,也就是在以色列佔領、兼併了東耶路撒冷和在約旦河西岸推行屯墾政策開始,如今被稱為猶太基本教義派才開始欣欣向榮。
耶路撒冷對宗教猶太人和世俗猶太人兩者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然而,在以色列獲得戰爭勝利後的那些歲月,耶路撒冷被強調的是它宗教方面的意義。就像耶路撒冷一樣,被宗教猶太人稱為「猶太與撒瑪利亞」的約旦河西岸也包含許多古代的宗教遺址。耶路撒冷擁有古代聖殿西牆的殘跡,約旦河西岸則擁有亞伯拉罕、撒拉(Sarah)、拉結(Rachel)等人的墓穴。對憧憬在應許之地重建猶太生活的猶太人來說,這些遺址具有非凡的宗教與歷史意義。
然而,軍事上的勝利和隨後展開的屯墾計畫卻讓圍繞耶路撒冷的宗教運動無用武之地。在緊接六日戰爭之後那段關鍵時期,以色列政府基於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考量,決定兼併和擴大耶路撒冷,並在其四周建立屯墾區,以資防護。由於基本教義派在當時還不能左右以色列政府,所以,兼併耶路撒冷和在約旦河西岸實施屯墾之舉,應該被視為是出於國家經過盤算後制定的擴張政策。
(全文未完)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