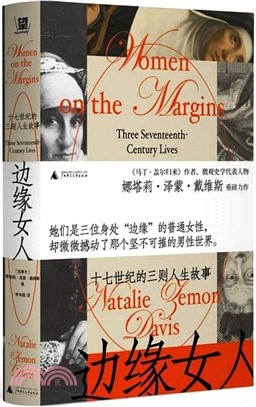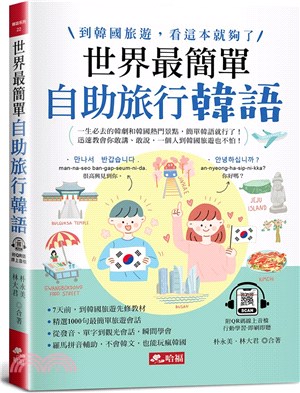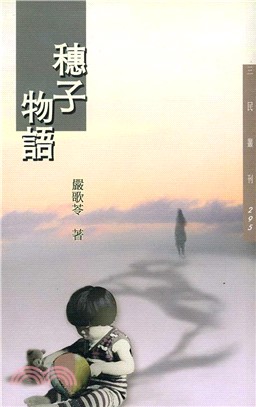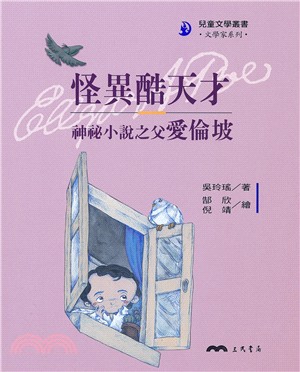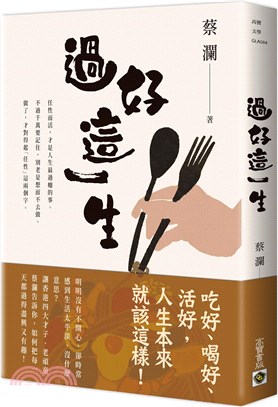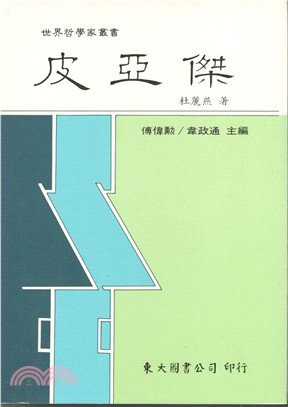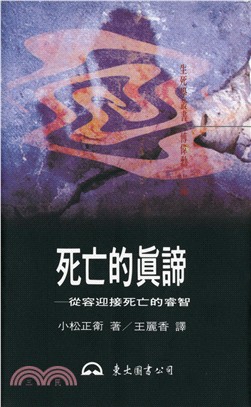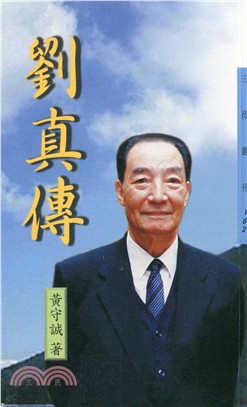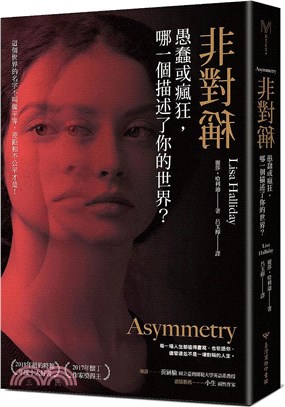邊緣女人:十七世紀的三則人生故事(簡體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邊緣女人》是一部集中於個體的十七世紀歐洲社會史、文化史研究。以微觀史學代表人物著稱的娜塔莉·澤蒙·戴維斯通過流傳於世的回憶錄、自傳、著作等歷史文獻,梳理了十七世紀歐洲三位女性(商人格莉克爾、訓導者瑪麗、藝術家兼博物學家梅裡安)的人生經歷,進而研究十七世紀的社會歷史,是頗具代表性的文化史、社會史著作。其中,格莉克爾寫下了七卷本帶有教導訓育色彩的回憶錄,瑪麗寫下了諸多的書信和自傳,梅裡安留下的則是昆蟲和植物的博物學著作以及大量的水彩畫。她們都不是一舉一動都為我們熟知的女王或貴族女性,而是生活在歐洲、北美和南美的“邊緣地帶”。作者根據她們的回憶錄、手稿等,重構這三位身份差別甚大的女性的生活,展示了十七世紀女性生活的多樣性。她們既不是貴族,也不是誰的繆斯,她們從未淹沒在母親的身份中,也從未作為妻子而被抹殺。她們三位身處“邊緣”的普通女性,卻微微撼動了那個堅不可摧的男性世界。
作者簡介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加拿大歷史學家,新文化史、微觀史代表人物。曾就讀於哈佛大學,並於1959年獲得密歇根大學博士學位,主攻歐洲近現代史領域。現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與人類學客座教授、中世紀研究教授。她的著作最初聚焦於法國,之後逐步拓展、延伸至歐洲其他國家、北美,以及加勒比地區。其最受贊譽的著作《馬丁·蓋爾歸來》目前已經被譯成24種語言並在全球範圍內出版發行。2010年,她被授予挪威郝爾拜獎(Holberg Prize),稱讚她為“當代最有創造力的史學家之一”;2012年她被授予加拿大總督功勛獎。另有《檔案中的虛構》《行者詭道》等多部重要作品。
名人/編輯推薦
- 17世紀的歐洲,當女性離開家庭、工場和教堂,離經叛道的她們面臨怎樣的命運?
格莉克爾·萊布,離經叛道,擅長經商,撰寫了七卷本的自傳。
瑪麗·居雅,投身教育和慈善,在新世界開墾精神與物質的荒原。
瑪利亞·梅裡安,藝術家、博物學家,每日研究她心愛的毛毛蟲。
《邊緣女人》中的三位主人公,她們既不是貴族,也不是誰的繆斯,
她們從未淹沒在母親的身份中,也從未作為妻子而被抹殺。
- 突破“正統”,揭示被歷史敘述邊緣化的女性世界,打開理解世界歷史的一扇新窗
《邊緣女人》挖掘了歷史上的無名之輩,為我們理解早期近代世界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
埋首檔案、回憶錄、自傳,乃至帳本、畫作,在戴維斯巧妙的敘述中,我們了解了關於早期近代歐洲生活的更多信息,遠超一般的“正統”歷史書寫。
- 和《奶酪與蛆蟲》一樣好看,《馬丁·蓋爾歸來》作者、微觀史代表人物娜塔莉·澤蒙·戴維斯 重磅力作
非專業讀者也能讀懂的歷史學著作,即使相隔幾個世紀,我們與她們仍然面臨同樣的困境。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加拿大歷史學家,新文化史、微觀史代表人物。2010年,她被授予挪威郝爾拜獎(Holberg Prize),稱讚她為“當代最有創造力的史學家之一”;2012年她被授予加拿大總督功勛獎。
目次
序 幕
與上帝爭辯
新世界
蛻 變
結 語
注 釋
致 謝
書摘/試閱
結 語
她們人生各異,但都在公共領域中有所成就。瘟疫風險、疾病苦痛、親人早逝—所有這些都影響了格莉克爾·巴斯·猶大·萊布、瑪麗及瑪利亞·西比拉·梅裡安的人生。她們三人都曾見證城市風格和印刷文字的蓬勃發展。她們三人都曾體驗額外重壓在女人身上的等級結構。她們三人也都曾被意外出現的精神機遇鼓舞,期許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哪怕只是暫時的。她們的生命軌跡有某些共通點,包括精力充沛及長壽的好運。使得她們走上不同道路的因素來自機會與性情,但更多則來自17世紀宗教文化和職業期望所設立的模板。
三人最相似之處在於其工作方式,都是一種女性版本的手工—商業風格。她們都有一技傍身:除去其他鑒別能力,她們或能甄別珠寶,或能品鑒刺繡紋樣,或能區分昆蟲標本好壞。她們都精於財務,能夠依據場合需要,或記錄放貸金額和孩子的嫁妝,或記錄圖書、畫作和標本的銷量;從記錄馬匹、馬車和馬車夫,轉為記錄教堂裝飾品、食品供應、修女捐贈的嫁妝,以及隨著她們職業和地點改變而進行的土地交易。她們總是雷厲風行,不管什麼技能,只要有用,就立馬拿來應對當下需求,無論是處理信貸損失或是火災損毀的危機,還是聽從渴望展開新冒險。
對城市男人來說,工作技能上的變通適應能力往往會被認為是因為貧苦:說明這個男人必須放棄固定行業才能生存下來;他是一個雇傭日工,心甘情願從事任何工種。對於城市女人而言,無論貧富,適應能力都必不可少,且教養她們的方法也鼓勵如此。1與兄弟相比,女孩更多接受普通手藝和家務技能教育,而不是幾年的正式學徒訓練;她們在父母、男主人或女主人的家務中學習任何能觀察到的手藝技術。有朝一日若以妻子、仆人或第二任妻子的身份進入家庭,她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力適配其家庭生活。格莉克爾·巴斯·猶大·萊布及瑪麗·居雅正是以此方式生活,她們的適應能力從宗教中獲得了額外的推動力量。在基督教歐洲的不確定性中,猶太人需要善於隨機應變;而一個英勇的天主教徒也必須時刻待命,無論何時何地,只要天主召喚,就必須去服侍。
瑪利亞·西比拉·梅裡安則略微不同,因為即便她自學了繁育昆蟲和觀察昆蟲的技能,她的藝術技能也來自多年家庭訓練。也許,在與拉巴迪教派上帝選民一同生活的歲月中,她的變通適應能力延伸到了農業耕作,但她的大部分技能都屬於17世紀全才藝術家工鋪裡的那類。她成了畫家、雕刻家、出版商、藝術商,以及像她欽佩的父親梅裡安和繼父馬雷爾那樣的教師,像她母親那樣的刺繡師。
精深的技藝是工匠的特質,對男人來說,專長往往會通過行會組織的認可來鞏固。某些女性從事的行業也有女人行會,還有些女人屬於男女混合行業的行會會員。不過,出於種種原因,格莉克爾、瑪麗和瑪利亞·西比拉跟許多女人一樣,都沒有加入這種組織。在漢堡,基督徒有貿易行會,但猶太人(更不用說猶太女人)則沒有;圖爾市這位幫姐夫經營運輸生意的女人也不可能屬於哪個行會,盡管她的姐夫有所屬的行會。梅裡安作為畫家,最有可能成為行會成員,但實際上她屬於紐倫堡圈子裡試圖建立藝術學院的一員。因此,對於格莉克爾、瑪麗和瑪利亞·西比拉來說,她們青年時期的專業意識來自相應環境中的親身實踐,而在這個環境中,她們還需操勞家務—毛蟲繁殖箱散落在炊具間,在哺乳孩子的同時還要給出甄選珍珠的建議。獲得認可(比方說,來自修道院修女或博物學家同儕的認可),都是後來的事。
也許,這三位女性在寫作與描繪中投入的專注力,也體現出她們的手藝意識。梅裡安顯然把她的書看作是繪畫和觀察的延伸,而瑪麗的教學書則將她的教學過程落在紙頭。但瑪麗與格莉克爾都在沒有受過修辭學、語法或文本結構的正式訓練的情況下走上這條寫作道路。雖然她們都有榜樣—講故事的人、布道、暢銷書,以及(在瑪麗的情況下)烏爾蘇拉修道院的交流語言—但撰寫手稿需要對敘事及對話加以甄選。也許,如瑪麗所稱,“聖靈恩寵”使她自發地書寫;但如果真是這樣,那也需要通過她的神經和肌肉的技巧來實踐。
宗教對這三位女性皆影響深遠。在基督教歐洲,格莉克爾的猶太人身份使她處處受限、朝不慮夕。身為以色列子民的自我想象又給予她深刻的身份認同,其他身份(女人、商人、德語區居民)也會通過這個自我認同來彰顯。她充分利用了分散而治的拉比猶太教留給女人的空間:祈禱、家務聖潔、作為已婚婦女的身體聖潔、善舉、閱讀,就她而言還包括寫作。在17世紀令歐洲猶太社區興奮的宗教新事件中—沙巴泰·澤維、卡巴拉、激進思想—只有第一件影響了她的生活。這也可能關乎性別。人人企盼的彌賽亞消息可以飛馳到每個人身邊,無論男女;但卡巴拉思想、有關斯賓諾莎的辯論、改宗者的異端邪說,都沒有散播至女人可接觸的文本(或至少看起來是這樣;也許相較於我們所知道的,妻子們事實上聽說了更多這類消息)。
印刷業和意第緒語譯者擴大了格莉克爾所能接觸到的猶太思想核心內容。我們已經看到,這不僅滋養了她的道德觀念,也滋養了她自身的主體性。思考《約伯記》,就幫助她認識到自己身上多年來存在著躁動不安的焦慮。
瑪麗利用了公教改革後教階為女性敞開的道路中的兩條:當她在俗世中作為妻子和寡母生活時,她可以詳細講述聖潔事物;以及在為獨身女人新開放的修道會中,她發展了教育職業。她將每一項都做到極致,先在苦修紀律和神秘異象中開花結果,後將教學擴展到遠方的英雄主義的使徒事業中。
從一開始,這些實踐就陸續影響了瑪麗的文才及自我意識。身體懲戒、與基督交流和神學異象早就轉化為她與神師的對話,以及有關“我”的書寫(這個書寫從強烈主動轉向被動)。在這個過程中,宗教讓她書寫,讓她得以解釋她為何遺棄兒子,以及她的周期性沮喪。最後,她創作了一個既主動又被動的“我”的故事,她還學會用四種語言去談論與書寫天主奧義。接近人間樂園的願望—這是格莉克爾不得不早早放棄的—對瑪麗來說,在她故世於加拿大叢林中的那一刻,都還沒有完全熄滅。
新教激進的靈修形式—對男人和女人都開放—在瑪利亞·西比拉·梅裡安三四十歲的時候,以特殊的力量在她的生活中迸發。首先是對自然界中上帝存在感到狂喜—這種感覺注入了她那些關於低等爬行生物的作品。然後是她皈依拉巴迪教派,同丈夫、家庭財產及俗世驕傲決裂。之後她離開拉巴迪社區,扎入對自然神論更冷漠的超然中,多年後,一種類似拉巴迪教派的力量和信念激勵了她前往蘇裡南叢林進行勘察的離奇計劃。
當然,這些宗教變更也引導瑪利亞·西比拉進行自我反思和內心對話。拉巴迪派不正是要求每個成員評論自己作為懺悔者和重生者的狀態嗎?但從字面上來看,她似乎只留下了那本附有講述過去研究的序言的研習手冊,而不是一部像安娜·瑪利亞·範舒爾曼的《善途》那樣的自傳。在拉巴迪派這段歲月過後,她講述了符合大眾興趣的那些生活片段:她的梅裡安血統、她的自然研究和旅行。但至於她在婚姻和宗教上的實驗,她只模糊指代、錯誤陳述,甚至隱瞞說謊。
在格莉克爾·巴斯·猶大·萊布和瑪麗身上,自傳寫作都不曾威脅她們的商業事業或教學職業。敏感事件僅被隱約提及,抹掉了有損母親名譽或使孩子難堪的細節,有些事情則完全被略過。2對瑪利亞·西比拉·梅裡安來說,給人生打上烙印的“流言蜚語”從來不是無關緊要的。把它們說出來可能會威脅到她作為博物學家、畫家和女性的身份。她也可能認為,她的孩子們無須她記錄人生經歷。克洛德·馬丁從瑪麗那裡求問他從未了解過的父親的秘密,而梅裡安的女兒們則不同,她們全程在梅裡安身邊目睹了一切。我曾說過,她的自我隱瞞是她自由的一個前提。
家庭關係及經歷塑造了17世紀生活的核心形態,但在實踐中又表現出極大不同。三個女人的生育率就顯示了文化和個人選擇如何影響了近代早期的生育狀況。格莉克爾懷孕了十四次,生了十二個孩子;年輕的寡婦瑪麗,生了一個兒子,從未再婚;瑪利亞·西比拉在長達二十多年的婚姻中只生了兩個女兒(據我們所知,她也只懷孕了兩次)。格莉克爾和哈伊姆驚人的多產,部分原因在於17世紀猶太人極早結婚的習俗。當格拉夫夫妻決定採用某種形式的節育措施時,日內瓦和英格蘭的新教夫婦也在進行類似嘗試。
相對來說,在這三個女人的婚姻中,那種常見的夫唱婦隨的等級並不那麼明顯,因為他們都是夫妻共同經營事業:漢堡的珠寶和貸款業務、圖爾的絲綢商鋪、紐倫堡和法蘭克福的雕版及出版業。瑪麗·居雅的說法是,她的丈夫給她閑暇,讓她有空投入宗教信仰;而約翰·安德烈亞斯·格拉夫顯然尊重妻子的昆蟲探索。但是,這樣的陪伴並不一定就能成就美滿婚姻。只有格莉克爾—她在訂婚那天首次見到丈夫—描述了多年來恩愛有加的親密關係。瑪麗雖在他們短暫的一兩年相處中“愛”著丈夫,但這相處也籠罩著丈夫與另一個女人的“恥辱”烏云。至於瑪利亞·西比拉,與一個相識多年的男人的婚姻終究成了場災難,原因也許有性欲方面的極度不合,但必然包括她宗教上改宗皈依的嫌隙。
近代早期的家庭,經常會出現無情冷漠的父母,但在這幾個家庭中都沒有這種情況。不過,她們做母親的有所不同。格莉克爾希望依靠早婚而不是延遲繼承來讓孩子們擔起猶太人的生活,因此她頻繁公開表達愛、焦慮、憤怒和悲傷,讓孩子明白她的感受和對他們的要求。這不是一個緘默的家庭。瑪麗·居雅裝作疏遠兒子,但並不成功,她與神師反復談論兒子及她對兒子的責任,最後她通過書信這一安全媒介與兒子交流。他們倆共同回憶起來的場景是,兒子哭著反對,而她則平靜地陳述聖召。瑪利亞·西比拉的母性音調很難聽到,不過,在她過世後,多蘿西婭在談到她時帶有的感情,或許能反映出瑪利亞·西比拉自己的聲音。可以肯定的是,梅裡安贏得了女兒們的忠誠,與父親對立;與此同時,她也給予了她們按照自己心意生活的必要手段。
梅裡安還讓女兒們對她們的藝術家和博物學家角色一直感到舒適。除了這一點和她自己令人印象深刻的榜樣之外,她沒有再將這種女性能力普及化。瑪麗走得更遠,她不僅激勵侄女瑪麗·比松成為烏爾蘇拉修女,而且還為法國烏爾蘇拉修女和美洲印第安女性皈依者描繪了一幅又一幅肖像,將她們視作使徒傳教士和教師。格莉克爾·巴斯·猶大·萊布充滿愛心,也“學識淵博”,正如紀念她的訃告所說的那樣,在那“與上帝爭辯”的文字實驗中,她超越了大多數猶太女人所謹守的界限。但她對女兒的讚美,只針對以斯帖的慷慨和虔誠。只有在兩百年後,在一個親屬後代身上,格莉克爾才成為女權革新的一個刺激因素。
對17世紀的某些同時代人來說,提高女性地位是一切改革的核心。沙龍文化激發了女性價值的許多主張,緊接著,1673年,笛卡爾主義者弗朗索瓦·普蘭·德拉巴爾(Fran.ois Poullain de La Barre)在巴黎出版了《兩性平等》(De l’égalité des deux sexes),這是在瑪麗於魁北克故世的一年後。1694年,瑪麗·阿斯特爾(Mary Astell)的《為增進女士真正最大利益而向她們提出的嚴肅建議》(Serious Proposal to the Ladi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ir True and Greatest Interest)在倫敦出版,她主張建立一所學院,為女性提供“學問教育”。3
格莉克爾、瑪麗和瑪利亞·西比拉雖然對女性朋友和女性親屬都很熱忱,但她們並沒有將提高女性地位本身作為首要目標。然而,她們的故事揭示了17世紀生活方式的其他可能性,因為她們在邊緣地帶開辟出了新奇的生活方式。
何種意義上的“邊緣”?首先,格莉克爾是猶太女人,瑪麗和瑪利亞·西比拉是非貴族女人,她們都遠離無論皇室的、民間的、還是參議院的政治權力中心。誠然,她們在一些重要方面受到了國家及其統治者的影響。格莉克爾·巴斯·猶大·萊布和其他猶太人的生存需要依賴保護猶太人的君主或政府。與維也納的奧本海默家族等宮廷猶太人簽訂的信貸協議,既可以給格莉克爾的生活帶來破壞,也可以帶來好處;在與梅斯經營王室生意的商人希爾施·萊維再婚後,她的經濟穩定一度與法國國王聯繫在一起。如果沒有歐洲人在魁北克和蘇裡南的政治存在,瑪麗和瑪利亞·西比拉·梅裡安都不可能在這些土地上實現她們感受到的呼召。梅裡安想知道《蘇裡南昆蟲變態》能否得到英國安妮女王的贊助,是否能在阿姆斯特丹那些市長和鎮長中間找到讀者;在她去世前,她想必會感激沙皇彼得對她的作品有興趣。至於實際的政治層面的影響,只有瑪麗有機會向總督們提出建議—而且是她在加拿大以非正式方式提出的。格莉克爾僅限於向宮廷猶太人求助。
從文化定義上來說,這些女人也在相當程度上遠離正規的學習中心及機構。格莉克爾與塔木德學者們的交談大多就在餐桌旁,聽他們布道也是在女座區。瑪麗會在懺悔過程中、在修道院庭院中,或在信件中(如她的兒子)與神學博士交談,會坐在修道院小堂裡聽他們布道。梅裡安的學問來自家族圖書館的圖書,之後來自紐倫堡的學者式贊助人。晚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她,更接近學術交流中心—植物園、珍奇柜—但她仍不能經常去大學。在她們三人的例子中,文化願景和手藝作品—傳奇自傳、神秘經驗表述和新世界寫作、昆蟲在植物上的生命史—都是從邊緣地方創造出來的。但那個邊緣之處,並沒有現代經濟學以利潤為中心的用法中“邊緣”所暗指的內容貧乏或低質量;相反,它是文化沉澱之間的交界地帶,允許新的增長,蘊含令人驚嘆的混合。
每位女性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或擁抱邊緣地帶,將其重構為一個局部定義下的中心。對格莉克爾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猶太人社交網和猶太社區。對瑪麗來說,是她在加拿大叢林裡的烏爾蘇拉修道院和庭院,裡面都是印第安人和法國人,遠離法國的文雅。對於瑪利亞·西比拉來說,那是一個位於尼德蘭森林邊緣的拉巴迪派定居點,然後是蘇裡南的河流和雨林—雖然不是永久住所,但改變了生活。在每個例子中,個人通過規避,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歐洲等級制度的束縛。
誠然,邊緣不僅針對女性。許多歐洲男性由於出身、財富、職業和宗教等,也遠離權力中心;男性有時也主動選擇或被動接受邊緣的位置。這就包括我們在本書中遇到的男性猶太人(宮廷猶太人除外)和耶穌會傳教士、拉巴迪主義者和狂熱的博物學家。但是,“邊緣女人”—這種受到更多壓迫的情況—可以特別清楚地揭示出與男性女性皆利害攸關之事。
人無法完全逃離中心及等級制度。米歇爾·福柯對17世紀權力之所在就頗具洞見,他說,不應僅僅“在某一中心點的原初存在中、在唯一的最高權力中心”中尋找權力,權力在整個社會的“力量關係”中無所不在。4格莉克爾·巴斯·猶大·萊布、瑪麗和瑪利亞·西比拉·梅裡安也都攜帶著權力關係。就格莉克爾而言,我們考察了她與非猶太人的關係;就這三位女性而言,我們都考察了想象中或現實中她們與非歐洲人的關係。格莉克爾將精力投入到闡述一個有界的領域,一個文字的“移入紋”,這就允許她支撐起她自己、她的家庭和她的猶太同胞,他們所處的是一個基督教統治的危險世界。對她來說,這就是“虔誠的塔木德學者”這個故事的核心所在,她甚至設計了一個顛倒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猶太人處在頂端。她在講故事的過程中並沒有進一步延伸自己,沒有重新思考歐洲人對“野蠻人”那想當然的優越感。她對苦難的同情也並沒有延伸至“移入紋”以外不可見之處。[假若她是蘇裡南種植園的猶太女人之一,被描述為整天和非洲家奴“喋喋不休”;或假若她是18世紀蘇裡南猶太教團體(那裡有相當數量的猶太人屬於有色自由人)成員之一—她有沒有可能重新勾勒出這樣的故事?]5
瑪麗和瑪利亞·西比拉·梅裡安都發現,邊緣地區承載著與非歐洲人的真正的權力關係:瑪麗是印第安人的女家長式教師,瑪利亞·西比拉是非洲人、加勒比人和阿拉瓦克人奴隸的主人。從她們的女性經驗(包括與女人的對話)和職業態度(一個是傳教熱情,另一個是科學作風)出發,她們詳盡闡述了如何思考非歐洲人—瑪麗的普遍主義,瑪利亞·西比拉·梅裡安的民族志觀察對野蠻/文明分類的漠視—這些途徑都緩和了她們同時代的男性所提出的歐洲人優越的主張。
一些歷史學觀點可能會敦促我們去找尋一套知識或表征的單一原則,以當作這三個女人的方法途徑的基礎。或者,如果找不到,那就把這三種方法安放在一個尺度上,區別出“較舊的”和“較新的”,或者多多少少在時間尺度上進行分析。應該拒絕這樣的闡釋,確切來說,這三種模式是同時發生的。不同的模式提醒我們去留意歐洲文化當中的流動性、混合性和競爭性。它們也為嵌入那些非歐洲人的目光留下了空間,這些目光響應了歐洲人的凝視,我們在重建愷昂和烏德勒奇對瑪麗的看法,以及加勒比人、阿拉瓦克人和非洲婦女對梅裡安的反應時就看到了這種目光。
本書的敘述順序—從格莉克爾·巴斯·猶大·萊布到瑪麗,再到瑪利亞·西比拉·梅裡安—不同於歷史時間順序:圖爾的那個女人至少比漢堡和法蘭克福的那兩個女人早一代。基督徒生活的矛盾已然擴大到大西洋對岸,進入與印第安人、非洲人的不確定關係當中。在思考這些矛盾之前,先描繪一下猶太人在歐洲令人不適的限制中的生活策略,似乎頗有益處。不過,這種分析順序並非“女性發展”,並非好像一種生活方式取代了另一種生活方式,就像基督徒認為教會取代了猶太教堂、《新約》取代了《舊約》。每個人生都是個例,都有其優點、進取之處和缺點,而且17世紀歐洲的母題貫穿其中:憂思、增強的自我意識、好奇心、末世論的希望、對上帝在宇宙中的存在和意圖的思考。我並不偏愛哪個。
* * *
在某一時期內,她們曾是血肉之軀;之後,留下回憶、肖像、著作和藝術品。當瑪麗被包裹起來準備入殮時,她所有的祈禱書、念珠、聖牌和衣物都被當作珍貴的遺物取走。在大西洋彼岸的圖爾修道院,她的侄女瑪麗·比松在幻象中最後一次見到了她。6她想燒掉的精神自傳被烏爾蘇拉修女抄錄下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由她的兒子克洛德·馬丁編輯、補充,並與她的信件及其他作品一起出版。因此,這些作品傳播到了烏爾蘇拉修會和其他宗教團體中,如玫瑰道明會和加爾默羅會的修女中間;在收藏於修道院圖書館和珍本室的那本書的扉頁上,就裝飾有她們的簽名。71734年,一位年輕的法國敘爾皮斯修會(Sulpician)修士皮埃爾·薩特隆(Pierre Sartelon)來到蒙特利爾時,包裡就有這本自傳的抄本;1806年一場災難性的大火後,這份抄本傳給了三河市的烏爾蘇拉修道院。8一個多世紀後,阿爾伯特·賈梅特神父(Dom Albert Jamet)出版了三河市的抄本,但他是被瑪麗的神秘主義所吸引,而不是她的教師角色。至於休倫人、阿爾岡昆人和易洛魁人,瑪麗的使命是拯救他們的靈魂。9
瑪麗用阿爾岡昆語、休倫語和易洛魁語寫的手稿,這些她與叢林人群關係的最重要證明,在19世紀被交給了加拿大北部的傳教士—這個說法來自蓋·烏裡神父(Dom Guy Oury),他寫的關於瑪麗的文章很有研究分量,也沒有賈梅特的種族主義色彩。10我希望這些手稿能交到印第安人手中。也許它們存在於某個地方,就像保羅·薩旺基基(Paul Tsaouenkiki)寫在肖蒙神父的休倫—法語詞典手稿上的家族史:“這份手稿是我父親保羅·塔霍倫奇(Paul Tahourhench)留給我的,他是1697年在魁北克附近的洛裡特聖母院(Notre Dame de la Jeune Lorette)所建立的休倫部落的偉大酋長。我父親是從他的母親拉·歐尼恩濟(La Ouinonkie)那裡得到這份手稿的,她是保羅·昂達恩豪特(Paul Ondaouenhout)之妻,大約在1871年去世,享年八十四歲。”11
在瑪利亞·西比拉·梅裡安去世前,她的水彩畫和出版物就已在歐洲廣為人知,隨著《毛蟲》及《蘇裡南昆蟲變態》的荷蘭文、法文和拉丁文版本相繼問世(其中有兩種晚至18世紀70年代才出版),這種認可也隨之傳播開來。12林奈提到了她的書,在他的分類中用“梅裡安”(Merianella)作為一種蛾類的俗名,並稱許王後路易絲·烏爾莉卡(Queen Louisa Ulrika)收藏的梅裡安的昆蟲畫。他還將梅裡安的銅版畫版本列入因其高價而對自然科學發展不利的書冊;“在平凡家庭長大的植物學之子,都無可避免必須購買這種高價書。”13
彼得大帝和他的繼任者無須考慮成本,1736年,他派多蘿西婭·瑪利亞·格塞爾回到阿姆斯特丹,為聖彼得堡科學院收藏更多她母親的水彩畫。14梅裡安的畫作與倫勃朗的畫作一起在珍奇博物間展出,這無疑激發了後來俄國軍官及文官精英對鱗翅目生物的興趣。事實上,這些畫作還激勵了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熱情,他一生都在收集蝴蝶。1907年他大約八歲,在距離聖彼得堡不遠的鄉間別墅的閣樓上翻箱倒柜時,他發現了一些屬於外婆的書,他外婆本人也算是某種程度上的博物學家。納博科夫“把一堆堆妙極了的非常吸引人的圖書”抱到樓下,其中就有瑪利亞·西比拉·梅裡安寫的那本關於蘇裡南昆蟲的書。15
約翰娜·海倫娜·赫洛特最後定居的蘇裡南,也保存了她母親的一些作品。今天,在蘇裡南國家博物館的圖書館裡藏有兩個版本的《蘇裡南昆蟲變態》。該機構的源頭是18世紀的珍奇柜,1975年蘇裡南獨立後,它在著名的17世紀建築澤蘭迪亞堡中得以延續。但在1982年,當兩年前奪權的軍事政權接管了澤蘭迪亞堡並下令清理時,博物館中物品和書籍的保存就並非易事了。館員們不得不匆忙收拾一切,保護他們的藏品不被偷盜。從那時起,博物館不得不在窄小的臨時角落開展工作,至少有一次,門外還發生了暴力事件。不管怎樣,梅裡安的書卷現在與懷亞納蜂墊、薩拉瑪卡人(Saramaka)** 蘇裡南河上遊的薩拉瑪卡黑人(Saramaka Maroons),也就是逃亡黑奴的後代。
的“說話鼓”和爪哇人.. 爪哇裔蘇裡南人,是指生活在蘇裡南的爪哇族,他們最早出現在19世紀後期,由荷蘭殖民者從荷屬東印度引入。
的皮影戲放在一起,蘇裡南的學者將這些藏品視作多民族後殖民社會的“國家遺產”的一部分。16
格莉克爾的自傳也頗具傳奇色彩。其手稿以家庭副本的形式流傳下來,1896年,這份自傳由學者大衛·考夫曼(David Kaufman)以意第緒語原文出版。之後,1910年,貝莎·帕朋罕(Bertha Pappenheim)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出版了德譯本。她是法蘭克福的猶太女權主義者、社會工作者和改革運動者。17帕朋罕經歷豐富,年輕時曾接受約瑟夫·布洛伊爾(Josef Breuer)的精神療法,布洛伊爾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895年的《癔症研究》中以“安娜·O.”(Anna O.)為代稱發表了她的病例。幾年後,她將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為女權辯護》(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譯成了德語。18隨後就輪到格莉克爾這本自傳。帕朋罕稱她為“Glückel von Hameln”(遵循1896年的意第緒語版本),格莉克爾是帕朋罕的旁系親屬:帕朋罕的母親是哈伊姆·哈默爾恩的姐姐葉恩特(Yenta)的後代。19更重要的是,格莉克爾是積極獨立和履行家庭義務的楷模,帕朋罕希望借此鼓勵20世紀早期德國的猶太女人。並且,與格莉克爾一樣,帕朋罕也相信講故事的用處,她曾於1890年出版了一本兒童家庭故事書,在1929年又出版了意第緒語《故事集》的德譯本。也許她自己的心理痛苦及治癒痛苦的努力,讓她對那些猶太故事當中的暴力、激情和洞察持開放態度。貝莎·帕朋罕如此認同格莉克爾,她甚至在請人繪製肖像時,穿著她想象中格莉克爾的裝束。20
帕朋罕的譯本由她的弟弟及表親在維也納出版,這個譯本完整譯自意第緒語版。帕朋罕偶爾也會將格莉克爾德國化,例如,“我拒絕了與整個阿什肯納茲猶太社區最杰出的男人再婚的機會”中,“整個阿什肯納茲猶太社區”變成了“整個德意志”(in ganz Deutschland)。21但她很細心留意格莉克爾的文字,保留了意第緒語的諸多特色。
三年後,猶太歷史專家阿爾弗雷德·菲爾欣費德(Alfred Feilchenfeld)出版了格莉克爾自傳的另一份譯本。由於他認為該自傳的重要性只在於它所揭示的猶太家庭及其在日耳曼地區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刪掉所有“反復打斷”這部傳記的民間故事及道德評論。22作為替代,他將兩個從語境中剝離出來的故事放在附錄中作為例子。[弗洛伊德圈子裡的一位精神分析學家西奧多·賴克(Theodor Reik)就從這一版本中引用了那個鳥的故事。]23菲爾欣費德還省略了格莉克爾的套話(如“願他的功德澤被後世”),並改變了一些書卷之間的劃分。這種對格莉克爾文本的肢解可能並不會給那些被同化的德國猶太中產階級讀者及“猶太教科學”學者帶來困擾。他們或許有興趣探索一個德國家族的過去,但對一個17世紀女人的意第緒語的質問則無所適從。24
至於是什麼構成了現代德國猶太女人的身份認同,貝莎·帕朋罕有不一樣的看法。她一定會對這另一版本的格莉克爾自傳的廣為流傳感到遺憾,這本由柏林猶太出版社出版的書到1923年為止就重印了四個版次。25然後在納粹時期,格莉克爾自傳的所有版本—節本、全本、意第緒語的、德語的—都和其他“不良書籍”一起被裝進“有毒庫房”。1990年3月,我很高興在東、西柏林的圖書館書架上都找到了它們。我認為這是一個良好信號,如同“鳥的故事”中的第三只雛鳥一般,這些書成功抵達彼岸。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