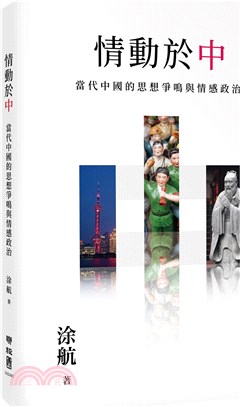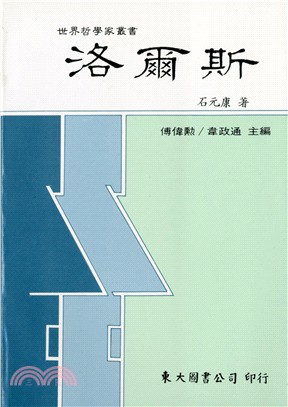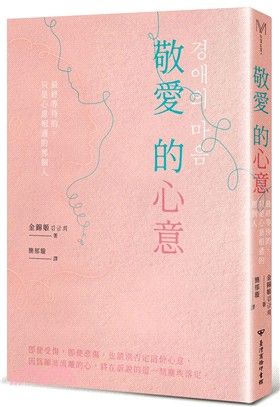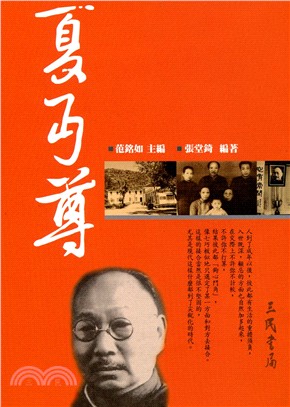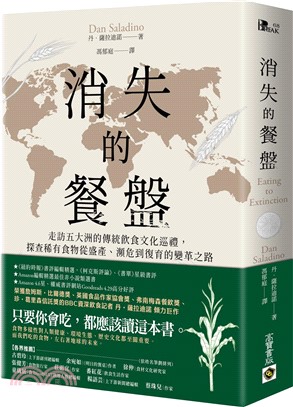商品簡介
與傳統的觀念史研究不同,本書關注的問題是:情感如何參與「思想體系」的構築、影響各種「學理」的闡發、乃至塑造形形色色的「政治立場」?換言之,思想不只是綱舉目張的思辨過程,也牽涉思維主體的癡嗔與愛憎。全書以一九四九為「情動於『中』」開端,講述一段又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陳寅恪五○年代的「心史」寫作成為世紀末自由主義者的懷想對象;李澤厚歷盡文革創傷,力求從廢墟中重建美學價值、塑造情本體;陳映真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嚮往紅色天堂,終必須面對後革命時代的「左翼憂鬱」;劉小楓八十年代從基督神學找尋救贖,遍尋「拯救與逍遙」而不得後,發現殺伐果斷的「政治神學」才是他的歸宿……。這些學者作家的思想根植生命,原是有血有肉的。作者不僅意在描摹個人的歌哭與悲歡,更要觀察他們字裡行間所生的情感如何凝為一種信號,一種召喚與回應,引導讀者體會一個時代「思」與「信」與「感」的取捨。
作者簡介
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思想與文學,中英論文散見於《思想雜誌》、《南方文壇》、Critical Inqui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MCLC等刊,另為《明報月刊》等雜誌撰寫文化時評。長於中國南方的九零後,先後求學於中山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哈佛大學。自小好讀閒書,酷愛小說,嘗試過創意寫作,未果,而後遊走於學術與生活之間,亦能怡然自得。
名人/編輯推薦
專業推薦
《情動於「中」》從情感政治角度,勾勒當代中國思想版圖:啟蒙者從「罪」與「樂」重探現代人學與仁學譜系;自由主義者重讀陳寅恪的悲情以見證獨立與自由之必要;左翼作家藉由憂鬱敘事反思革命成敗是非;保守主義者結合政治與神學召喚深不可測的聖寵。這些線索相互鏈接,不僅著眼當代,而且回應了近三百年來情理之辨的大問題,在在可見此一課題的深度和廣度。
——王德威(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
這本書是探究中國當代思想複雜圖景的力作。涂航以「情動」做為切入的分析範疇,深入討論了幾個代表人物的論述,展現出的是這個思想圖景的分歧與複雜,也顯示理性言說的驅動力和個人的情感記憶與生活經驗緊密相連而難以切割。作者揭示出當代中國在經歷改革開放之後,革命幽靈為什麼仍然徘徊不去,並為「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哉問提供了繼續追索的可能路徑。
——丘慧芬(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教授)
本書試圖回答過去一個世紀困擾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問題:何為(中國)革命?從陳獨秀到李澤厚的幾代仁人志士都以「感時憂國」情懷介入有關革命與啟蒙的思想論戰。九十年代以來海內外學界眾聲喧嘩,王德威、汪暉等學者心憂「未完成的啟蒙」議題,發掘革命的唯情向度以及「向下超越」的政治潛能。涂航承前啟後,通過細膩的文本分析討論近百年來激盪中國的各色「主義」如何同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現實發生碰撞,從而產生廣泛、持久的影響。
——柏右銘 (華盛頓大學人文學學系洛克伍德講座教授‧電影與媒體研究系教授)
序
王德威
情感,思想,與政治的互動是現當代中國研究最值得重視的課題之一。一般所見,學界談思想、論政治總是大言夸夸,一旦觸及情感,立刻扭扭捏捏起來。我們的現代性論述一向以啟蒙、革命是尚,以此為啟迪民智,創造新政的要項;對於情感如何與之掛鉤,其實缺乏細膩深刻的論述。等而下之者,甚至認為情感無非是小悲小喜,必須鍛煉導正甚至壓抑排斥。隱含其中的性別、知識、意識形態偏見,不言可喻。
然而「革命」、「啟蒙」一百多年後,回顧所來之路的滿目瘡痍,我們不能不反省是否錯過了什麼節點?從民國肇造的拋頭顱、灑熱血到共產革命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從知識分子的感時憂國到市井百姓的穿衣吃飯,從文化大革命的酷烈狂熱到新時代的內卷躺平,幾代中國人歷經思想和政治顛撲,卻還是無從安頓情感的位置。我們的社會既無情又濫情,既矯情又煽情,難道不正是思想、政治缺陷的起因,或是結果?大人先生高談中國現代思想結構從「天理」化為「公理」,卻忽略了「情理」的轉圜,無疑是關鍵所在。
我們需要情感教育。從語源學角度言,「情」不僅意味喜怒哀樂、七情六慾,也意味外在事物與主體交會的狀態(情況,情境),存有的條件(盡得其情),真實與真理(道始於情)。作為動詞,情有斟酌,判斷的含義(情之以理;情不情)。從身體到義理,情的多義性難以駕馭,傳統論述的反應也是莫衷一是。從孟子的「四端」、莊子的「逍遙」,玄學的聖人「有情」╱「無情之辯」,到程朱的「存天理、滅人欲」,可見一斑。晚明王學以來,情的思辨有了典範性轉變,也成為中國主體現代性開端之一。
西方啟蒙運動之後的情感轉向同樣歷歷在目。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的倫理學、休謨(David Hume)的情感論、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懺悔錄無不質疑政教權威、真理統御,預示了「感性時代」(age of sensibility)的來臨。時至今日,情感研究從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拉崗(Jacques Lacan)式的心理分析,到左翼的慾望、解放辯證 (Erich Fromm、Herbert Marcuse),自由派的情感倫理(Martha Nussbaum),以及後現代情動論(Gilles Deleuze),各成一家之言。當下AI智慧引起熱烈討論,殊不知情感反而可能是人類最後的防線。
是在這樣的知識譜系裡,涂航博士的《情動於「中」》出版堪稱此其時也。如本書副題所示,涂航將焦點置於當代中國的思想鳴放與情動政治。他所謂的當代應有兩重含義,一為上個世紀末以來我們對當下此刻的敏銳時間感受;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刻意打造的歷史觀,以1949年為「當代」開始,而且邁向永恆。兩種「當代」在書中交錯,演繹出一段又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陳寅恪五○年代的隱微寫作成為世紀末新自由主義者的懷想對象;李澤厚歷盡文革創傷,力求從廢墟中重建美學價值、塑造情本體;陳映真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嚮往紅色天堂,終必須面對後革命時代的「左翼憂鬱」;劉小楓八十年代從基督神學找尋救贖,卻在新時代發現毛澤東才是他膜拜的偶像……。
根據這些案例,涂航可以寫出一本知識分子如何歷經政治狂潮,磨煉思想邏輯,堅守或改變理念信仰的專書―這是思想史的路數。但他顯然以此為不足,而希望從中梳理出更複雜的線索,如陳寅恪的史論如何「痛哭古人」;李澤厚的儒家「樂感」文化如何導向「告別革命」;陳映真的憂鬱如何啟發後革命行動;劉小楓的「海洋性激情」如何接軌古典公羊學說……。換句話說,思想不只是綱舉目張的思辨過程,也牽涉思維主體的癡嗔與愛憎;政治不只是公眾運動或權力取予,也牽涉行動主體的希望與悵惘。更進一步,情感不僅源自個人,也是一種公共意向投射和意象流傳,直通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謂的「感覺結構」。
涂航花了相當篇幅處理情感作為現代論述的來龍去脈,因為明白這一關鍵詞太容易望文生義,引起誤讀。情感作為「論述」,已經隱含二律悖反的聯想:如果情感是內蘊流動的,何能述之論之?但另一方面,正由於情感啟動了思想論述,或甚至思想論述觸發了情感,我們更有必要正視兩者的共生關係。涂航對「情動」(affect)與「情感」(emotion)作了基本區分,謂前者指涉人本中心以外,超理性或非理性的動能或反應,後者指涉社會場域流動或制約的愛恨悲喜。他的立論基本得自西學啟發,如果嫁接到古典中國論述,反而更有發揮餘地。如前所述,「情」不論從觀念論或倫理學而言,都涉及情動和情感,自發和後設等層面,甚至饒富歷史(「觸事興詠,尤所鍾情」)、政治(「發憤以抒情」)喻意。台灣和海外漢學界的「抒情」傳統研究即始於此。本書書名《情動於「中」》語帶多義,足以顯現作者是明白其中道理的。
本書的另外一個關鍵詞是「文」。此處的「文」泛指物象與文采,氣性與書寫,彰顯與隱喻;我們所熟悉的「文學」僅是廣義的文的現代詮釋之一。涂航所處理的文本包羅廣泛,從文史述作到小說虛構,哲學思辨、文藝批判、再到政治文章,甚至旁及政論宣言。他看出現當代中國的思想與情感論爭難以被簡化為西方言說模式,古典的文反而可能是更多元載體。儒家所謂的「興、觀、群、怨」就深富思想與政治意涵,而其表達形式是詩;荀子論禮,強調「情文具備」, 其辯證面的「發憤」或「怨毒」著書則影射禮崩樂壞的時代裡,文,或微言,或大義,成為最後的歸宿。當然,文的扭曲、湮沒也必須是變數之一。當文只剩下一種「痕跡」,它呼應了字源的根本,那(章太炎所謂)文明有無的臨界點。
面對「文化」大革命之後的中國,涂航選擇「文」的消長作為討論當代情感、思想、政治交會的平台,飽含個人對共和國歷史的感喟:那是文明的,還是野蠻的歷史?本書分為四章,仔細討論了關鍵人物如劉再復、李澤厚、余英時、陳寅恪、陳映真、王安憶、劉小楓等人的思想轉折與歷史經驗。這些學者作家不再是一本正經的思想史或文學史人物,他們的思想根植生命,原是有血有肉的。值得注意的是,涂航不僅意在描摹個人的歌哭與悲歡,更要觀察他們字裡行間所生的情感如何凝為一種信號,一種召喚與回應,引導我們體會一個時代「思」與「信」與「感」的取捨。
涂航首先討論劉再復和李澤厚面對革命遺產的「隱秘對話」。劉、李兩人與革命傳統關係深厚;李早在五十年代末期即因參與美學大辯論名噪一時、劉則是共產黨栽培的文學評論家。文革之後,李澤厚糅合康德與馬克思學說,號召回歸美學,成為一代青年思想導師;劉再復在文藝界扶搖直上,直奔第一把交椅。即在彼時,他們的思想已經開始出現變化;李對革命壓倒啟蒙的反思,劉對性格「多元組合」的倡議,引來官方不安。六四之後他們流亡海外,生命的困蹇逼出了思想的蛻變。劉再復從基督教和儒釋兩家立場反思「罪」和「懺悔意識」;李澤厚從儒家「樂感文化」體悟生命俗世性,從而發展出「情本體」。「罪」與「樂」的情感取向何其不同,兩人卻殊途同歸,以此「告別革命」。
本書第二章處理「民國史學第一人」陳寅恪最後二十年境遇,以及世紀末的「陳寅恪熱」。1949年世變,陳氏選擇留在大陸,未料噩夢自此開始。他由史學轉向非今非古的文化詩學,深埋一己塊壘。其時遠在哈佛的留學生余英時偶得陳詩、文稿,為之震動,由此展開長達六十年的「心史」考證。天安門事件後知識分子苦無出路,從陳標榜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找尋寄託,未幾,新自由主義學者又奉陳為自由主義前行者,以之與新左抗衡。「陳寅恪熱」蘊含三代知識分子的鬱憤與悲情,也直指千百年來知識與政治難以媾和的困局。而參透這一兩難,有賴「文學」工程:藉此喻彼,引譬連類,成為思想者不得不然的技藝。隱於其下的則是陳氏「痛哭古人,留待來者」的悲願。
第三章轉向「左翼憂鬱」辯證,焦點為台灣最重要的左翼作家陳映真與大陸女作家王安憶。陳早自六十年代即傾心左翼思想,為此付出巨大代價;王安憶出身紅色家庭,但未能免於文革動亂波及。八○年代初因緣際會,兩人在北美遭遇。回顧三十年共產革命的暴虐和創傷, 「美帝」社會的資本與豐饒,兩代作家不能不有所惑。陳承認革命的挫敗,卻無怨無悔,貫徹始終,王則從傷痕和幻滅中,掙扎反思社會主義願景的消長。以此,涂航檢視近年西方學院內流行的「左翼憂鬱」論述,叩問何以源自個人的「憂鬱」蔓延為左翼知識分子的通病?筆下的台灣與大陸案例是否也適用同一判準?不論如何,比起目前既姓「社」又姓「資」的國家體制,或又當又立的新左宣傳隊,陷入左翼憂鬱者以「自嚙其心」的姿態,咀嚼「俱往矣」的憂傷與不捨,反而為革命帶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動能。
本書以劉小楓如何由基督神學轉化為政治神學來到高潮。劉從德國浪漫主義起家,經由文革動亂來到新時期百家爭鳴,但在遍尋「拯救與逍遙」而不得後,他轉向基督神學,企圖從彼岸獲得救贖。但這還是故事前半場。九○年代後劉號召漢語神學運動,強調中華文化本位信仰,之後他受到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施密特(Carl Schmitt)啟發,發現政治神學,自此從彼岸又回到此岸。他援引公羊學說,終奉毛澤東為國父。劉的尋道過程充滿曲折,不變的是革命喚起他洶湧澎湃、「情深似海」的感覺(oceanic feeling),一種渴求超越世俗,政教合一的終極情懷。在愛智(logos)和律法(nomos)間,劉畢竟以感性,與感應,作為起點與終點。
《情動於「中」》從情感政治角度,勾勒當代思想版圖:啟蒙者從「罪」與「樂」重探現代人學與仁學譜系;自由主義者重讀(或誤讀)陳寅恪的悲情以見證獨立與自由之必要;左翼作家藉由憂鬱敘事反思革命成敗是非;保守主義者結合政治與神學召喚深不可測的聖寵。這些線索相互鏈接,在在可見此一課題的深度和廣度,也引領我們作出如下聯想。
思想與情感的辯證非自今始,而應視為漫長的「現代性」過程的要項,至今仍然律動不已。如前所述,現代西方情感論述隨十七世紀啟蒙時代開啟,自始即和理性人文思維相互應和,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因休謨、盧梭等人的倡議大放異彩。盧梭的浪漫主體情懷和感性行動預示了未來革命、解放憧憬。另一方面,休謨以經驗主義出發的情感論述,強調感同身受的共情,而非道德或宗教真理,才是社會倫理的基礎。稍晚的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則企圖調和理性與感性,並另啟「遊戲」論作為審美活動的開端。他們的對話對象不是別人,正是理性主義大師康德。
中國傳統的情感論述未必能完全與西方對應,但足供後之來者參照。晚明湯顯祖的情教論眾所周知。王學大家劉宗周提倡「即情即性」,重純情,貶「鑿智」,打破此前程朱「性即理」的執念。這是儒學情感論述的轉折點。劉的從人黃宗羲、陳確等更強調「離情無以見性」;「天理皆從人欲」,情理並論。而總其成者則為十八世紀的戴震―康德、休謨、盧梭的同代人。戴震主張「達情遂欲」、「以情絜情」,為道德情感布置新局:欲、情、知形成的「氣」化主體即是道德主體。戴震獨重情理之辨,梁啟超稱之為兩千年一大翻案。
晚明清初士人將情感與思想相提並論,除了知識譜系(程朱學與王學)的變動外,歷史、政治形勢也有以致之。戴震的情理之辨隱含對官學恪尊天理、墨守成規的批判,這類批判再傳到清末,反映在龔自珍的「尊情」論述上。誠如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所論,中國現代性的基礎無他,就是情性的解放,唯以此為基礎,革命和啟蒙才能成其大。從魯迅到郭沫若,從朱謙之到胡風,都曾強調情感、思想與革命三者的聯動關係。民國與共和國的建立如果沒有摧枯拉朽的「民氣」作用―或鄂蘭(Hannah Arendt)所謂革命開新的激情(pathos of novelty)―不會成功。但曾幾何時,一個號稱「解放」的政權居然如此避談情理,代之以毛版「存天理,滅人欲」。扭曲的情感、壓抑的欲望反而炮製出種種大鳴大放的運動,「以理殺人」的亂象。
《情動於「中」》雖著眼當代,其實回應的是三百年來情理之辨的大問題。各章所論情感政治來自人倫欲望與宗教信仰,也來自革命動力與自由思想,所凸顯的複雜度比起過去任何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原因無他,我們所面臨的中西知識及情感衝擊前所未見,與此同時,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因為生命和科技政治(biopolitics, technopolitics)的加持,更是變本加厲。
即便如此,涂航強調當代思想的「情感考古」之必要,持續思辨情與志,情與理等命題之必要。的確,如果不能理解左翼憂鬱和毛記國父神學的來龍去脈,我們如何與革命歷史真正「和諧」?不能直面罪與懺悔意識和樂感文明始末,我們又如何保證中國有「夢」的品質?而涂航仔細研讀各類文本,強調從「文」的實踐上進入情理思辨過程,不啻向「情動而辭發,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龍》)的古典教誨致意。
作為九○後學者,涂航其實沒有經過「革命洗禮」甚至天安門事件,但卻似有著老靈魂。以他在哈佛堅實的西學訓練,大可以從事最前沿的研究課題,但他對當代中國何去何從及知識分子的命運獨有感觸。他以《情動於「中」》作為新書標題,既點明他為中國研究另闢蹊徑的意圖,也蘊含個人海外深造多年的心情。我有幸見證此書從無到有的過程,也享受教學相長的樂趣。爰此為序,並與涂航共勉:問學之道就是有情的事業。
目次
導論 思想的「情動力」
一、革命之後
二、思想的「情動力」
三、對證革命╱與過去和解
四、章節概要
第一章 「樂」與「罪」的隱秘對話
一、前言
二、樂感文化:由巫到禮,釋禮歸仁
三、罪與文學:從「性格組合論」到「罪感文學」
四、結語:樂與罪的交匯:告別革命
第二章 自由主義的記憶政治:民國熱視野下的陳寅恪
一、「情動」陳寅恪
二、文化遺民說
三、凸顯的學問家
四、自由主義的殉道者
五、結語:後世相知或有緣
第三章 左翼的憂鬱
一、世紀末的社會主義
二、市鎮小知識分子
三、烏托邦詩篇
四、結語:(後)馬克思主義的幽靈
第四章 從漢語神學到政治神學:劉小楓與保守主義的革命
一、偶像的黃昏
二、拯救與逍遙
三、人神之間
四、革命的微言大義
五、結語:信仰之躍
尾聲 昨日的世界
一、總結
二、中國向何處去
三、多餘的話
書成後記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一、前言
1981年,李澤厚的《美的歷程》行世,隨即在校園和文化界掀起一陣「美學熱」。李著以迷人的筆觸描繪了中華文明起源之初的諸多美學意象:從遠古圖騰的「龍飛鳳舞」,到殷商青銅藝術中的抽象紋飾,再到百家爭鳴時期的理性與抒情,這幅綿長的歷史畫卷如暖流般撫慰著飽受創傷與離亂之苦的莘莘學子的心靈。李澤厚早先以其獨樹一幟的「回到康德」論述著稱,然而啟蒙思辨不僅關乎繁複的哲學論證,也得負起終極價值的使命。康德人性論的提綱掣領背後,是幾代中國美學家的關於審美與宗教的深思與求索。五四運動之初,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首倡用美學陶冶性靈以代宗教教化之說。相形之下,李著異彩紛呈的美學意象背後,隱約流動著其對儒學情感倫理學的重新闡釋。在李澤厚隨後描繪的「由巫到禮,釋禮歸仁」的儒學情理結構中,先秦儒學以此世之情為本體,孕育了與西方救贖文化截然不同的「樂感文化」。這種既具有民族本位主義又內含終極價值維度的審美主義試圖為文化轉型時期的中國提供一種安身立命的根基。
八十年代的啟蒙運動以美學的朦朧想像,重新啟動了五四時期的美育論,以感性詩意的方式呼喚文化和政治新命。面對新的政治想像,批評家劉再復以「文化反思」為出發點,將李著的啟蒙理念闡釋為一種高揚「文學主體」與「人性」的文藝理論,為重思現代中國文學打開了一個嶄新的視野。然而劉說並非僅僅局限於簡單的控訴暴政和直覺式的人道主義,更旨在叩問已發生的歷史浩劫中「我個人的道德責任」。換言之,文化反思並非以高揚個人主義為旨,而必須審判晦暗不明的個體在政治暴力中的共謀。受巴金《隨想錄》之啟發,劉再復以「懺悔」與「審判」為線索反思中國文學中罪感的缺失。劉著受到西洋啟示宗教的原罪意識啟發,卻並非意在推崇一種新的信仰體系。他希望另闢蹊徑,思考文學如何對證歷史,傷悼死者,追尋一種詩學的正義。罪感文學實質上是一種懺悔的倫理行為,通過勾勒靈魂深處的掙扎和彷徨來反思劫後餘生之後生者的職責。
本章以李澤厚的「樂感文化」和劉再復的「罪感文學」為題,通過重構兩者之間的隱秘對話,來勾勒新時期文化反思的兩種路徑。李澤厚在大力頌揚華夏美學的生存意趣和人間情懷的同時,毫不猶豫地拒斥神的恩寵以及救贖的可能。而劉再復則將現代中國文學對世俗政治的屈從歸咎於超越性宗教的缺失。二者凸顯的共同問題是: 新啟蒙運動為何需要以情感倫理的宗教維度為鑒來反思毛澤東革命的神聖性(sacrality)?簡而言之,對威權政治的批判,為何要以儒學之「樂」與基督教之「罪」這兩種道德―宗教情感為切入點?
在這裡,我需要引入「政治神學」(political theology)這一理論框架,來解釋政治神聖性(the sacralization of politics)與啟示宗教(revealed religion)之間的複雜張力。在其始作俑者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看來,理性化進程在驅逐宗教幻象的同時,也導致了「規範性價值的缺失」(normative deficit of modernity)。以技術理性為內驅力的自由民主制不僅無法掩飾其內在的道德缺失,而且在危急時刻不得不求助於高懸於政治程序之上的主權者以神裁之名降下決斷,以維護其根本存在。施密特的決斷論不乏將政治美學化的非理性衝動,然其學說要義並非推崇回歸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而在於借用神學要素來維護世俗政治之存有。由此可見,「政治神學」一詞內含無法調和的矛盾:它既喻指重新引入超越性的宗教價值來將現代政治「再魅化」,又意味著將神學「去魅化」為工具性的世俗政治。不同於施密特對政治「再魅化」的偏愛,二戰後的德國思想家往往以神學的政治化為出發點反思現代政治對宗教的濫用。在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等人的論述中,極權主義往往祭起宗教的術語、儀式、和情感來神聖化其世俗統治。現代政治權威不僅借用宗教的組織和符號,也從基督教的救贖理念和末世論中汲取靈感。在沃格林的筆下,現代全能政治源於靈知論(Gnosticism)對正統基督教救贖觀的顛覆:靈知主義者憑藉獲取一種超凡的真知在此岸世界建立完美的天國。洛維特則更進一步探討了共產主義理念和基督末世論的親和性:暴力革命的進步觀、烏托邦的理念和社會主義新人的三位一體均是基督救世思想的世俗形式。誠然,這種闡釋學的局限性顯而易見:現代政治進步觀與基督末世論之間的概念親和性(elective affinity)並不等同於歷史因果關係(historical causality),把神學理念直接推衍到對現代革命思想和社會運動的闡釋,其解釋效力值得懷疑。例如,中國政治學者雖然注意到毛澤東崇拜與宗教儀式之間的類似性,卻更傾向於強調世俗政治對於宗教符號的「策略性借用」(strategic deployment)。換言之,政治的神化僅僅是一種對宗教元素的功能主義利用。
我以為,這種功能主義的判斷無法解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宏大敘事賦予世俗政治的一種富於宗教情懷的「海洋性感覺」(oceanic feeling)。革命的神聖化本身蘊含了一種相互矛盾的雙向運動:在以世俗政治對宗教信仰的「去魅化」的同時,試圖將宗教的神聖性注入以「革命」、「社會主義」和「民族國家」為圖騰的世俗變革中。此文旨在以政治神學為切入點來重構李澤厚的「樂」與劉再復的「罪」之間的隱秘對話。我將論證,兩者的論述均以一種隱喻的方式構築宗教意識和政治專制的聯繫,並提出了相應的啟蒙路徑。李澤厚在大力頌揚華夏美學的生存意趣和人間情懷的同時,毫不猶豫地拒斥神的恩寵以及救贖的可能,而劉再復則將現代中國文學對世俗政治的屈從歸咎於宗教性的缺失。對於基督教超驗上帝(transcendental God)的文化想像導向了兩種看似截然不同卻隱隱相合的啟蒙路徑:以此岸世界的審美主義來消解共產革命的彼岸神話,或是以超驗世界的本真維度來放逐世俗國家對寫作的控制與奴役。
值得一提的是,我所指的「隱喻」並非狹義的修辭策略,而是以錯綜複雜的文辭、審美和想像力生成哲學論述的獨特路徑。不論是德里達等後結構主義者關於文字與思之「再現」(representation)的立論,還是Hans Blumenberg 以哲學人類學為出發點梳理概念性邏輯背後根深蒂固的「絕對性隱喻」(absolute metaphor)的嘗試,這些論述均將流動性的言說和星羅棋布的審美意象看做創生性哲學話語的源泉。更不必說,中國傳統中的「文」與「政」的相繫相依,早已超出了西學語境下的模仿論,而蘊含著道之「蔽」(concealment)與「現」(manifestation)的複雜律動。正因如此,單單從觀念史學或是從文學史的角度梳理李與劉的論述,都無法細緻地追蹤和指認政治―宗教批判與文學╱文化批評之間看似毫無關聯,但卻以嬗變的「文」為媒介相互闡發的能動過程。因此,八十年代的啟蒙話語「荊軻刺孔子」式的隱喻政治正是我們闡釋李澤厚之「樂」與劉再復之「罪」的起點。
從另一方面來看,隱喻政治也凸顯「文」的歧義性:與狹義的(現代)文學之「文」不同,四處流串的「文」似乎缺乏有機統一,四處彌散,消解了「文化」、「文理」或「文統」本來具有的批判意義。在這裡,我關心的並不是是大而化之、無所不包的「文」的概念演化,而是重在討論新啟蒙知識分子如何以「文」―從李澤厚糅雜中西的美學、哲學實踐到劉再復天馬行空的文化批評―彰顯「情」的倫理教化之功。「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一詞源自十八世紀的西歐啟蒙運動。與高揚理性主體的康德不同,大衛‧休謨(David Hume)、亞當‧斯密(Adam Smith)等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極為強調感性教育的維度,提出培育「同情心」之必要。同一時期的法國啟蒙作家亦把小說作為熏陶情感、塑造道德激情、進而傳播啟蒙理念的重要媒介。與此類似,晚清以來的中國啟蒙知識分子將「文」視為情感教育、聯通啟蒙人性論的關鍵性媒介。例如,陳建華認為,《玉梨魂》這樣的「傷情―艷情」小說旨在「祛除暴力及其情感創傷」,通過「情教」來「重建一種現代國民主體與家庭倫理」。同理,在從「革命」到「啟蒙」的轉型語境中思考情感教育,意味著理解李澤厚與劉再復如何以文學和美學實踐批判毛時代的「階級仇恨」教育,為後革命時代提供普世人性的基礎,進而重塑後革命時代的公民主體性與感覺結構。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