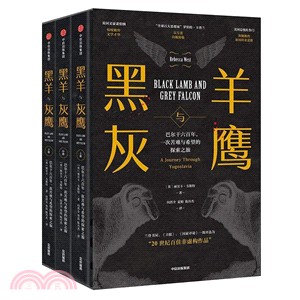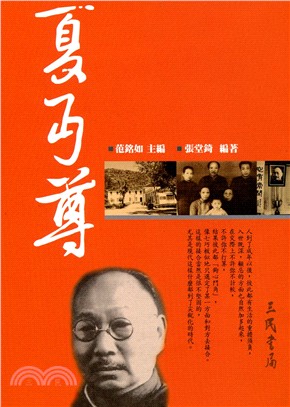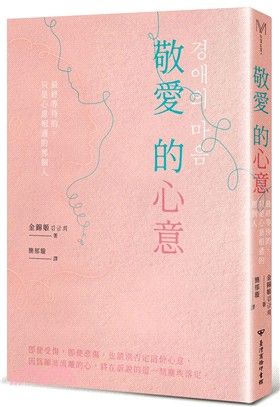商品簡介
史詩級的紀實文學典範
逾半世紀歷久不衰的巴爾幹必讀文本
蘭登書屋、《衛報》、《國家評論》一致評選為“20世紀百佳非虛構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新舊歐洲的轉折點,作為歐洲火藥桶的巴爾幹,在 20 世紀 40 年代前後的命運截然不同。 本書觀照了自 14 世紀中葉至“二戰”爆發這漫長歲月中的巴爾幹歷史。 這片土地經歷過什麼?為什麼會蛻變為浸透鮮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連串難解的謎團和苦難又是否有跡可循?
本書以作者巴爾幹之行的沿途見聞為線索,追溯了巴爾幹歷史上緣於民族、宗教、地緣等因素的內外政治糾葛與軍事衝突;也在對當地居民生存現狀的見證中,力圖揭示當地各民族命運的悲劇之謎——巴爾幹苦難之人的內心始終湧動著一股為神聖犧牲的、如鷹般洶湧的渴望,他們祈盼著,猶如被獻祭的羔羊以毀滅的姿態達至永恆。 這種獨特的精神稟賦,指引巴爾幹人超越苦難,也滑向了悲劇的深淵。
作者簡介
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1892—1983)
英國文豪、文學評論家、記者、旅行作家。韋斯特曾被譽為“毫無爭議的世界第一女作家”、“在世的最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她終身致力於女權與自由主義的社會改革運動,2004年以來,其生平事蹟被兩次改編並搬上話劇舞臺;1959年憑藉文學成就獲封大英帝國爵級大十字勳章,1950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榮譽院士。
韋斯特著作等身,另有《叛逆的意義》《溢出的泉水》《思想的蘆葦》《真實的夜晚》《士兵的歸來》。《黑羊灰鷹》被公認為韋斯特的代表作品,《士兵的歸來》於1982年被改編為同名電影。其作品被譯為多國文字暢銷世界。
名人/編輯推薦
- 相比旅行文學,《黑羊與灰鷹》更近於一部史詩。三度遊歷之外,作者投入了五年時光,“殫精竭慮”,將盤根錯節的歷史和現狀、不同視野下的記憶與情感,連同最幽邃的精神剖析一同編入這部宏大的文本,構成一幅闊大的、層次豐富的圖景。韋斯特的寫作是一股思想的洪流,觀察與玄思無時無刻不錯雜而行,其間更深藏著對人類及其無盡的愚蠢和悲劇的理解與同情。
- 它也是一幅“二戰”邊緣的歐洲畫像。從作者的遊歷到成書,世界歷史從“一戰”後的暗流湧動最終滑入了新一輪戰局;就在作者寫作的收尾時刻,巴爾幹深陷納粹炮火,再次經歷苦痛抗爭和各方抉擇。它以強烈的在場感,見證了一個一切要素彼此撞擊的時刻。
- 作為一份對世界上民族、地緣狀況最複雜地區的調查,這部巨著不僅記錄了遙遠過去,也照亮了正在發生的歷史。今日再讀,我們不只是在遠望斯拉夫人身畔濃厚的陰影,也是在檢視當下世界裡那些鬥爭的陰雲、仇恨的火種。
- 《黑羊與灰鷹》是巴爾幹歷史與民族志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成為其後的寫作者、研究者反復回溯的文本。半個世紀後,著名地緣政治學家、作家羅伯特•卡普蘭將此書視作自己巴爾幹之行的隨身指南,並在書中以專文致敬,“我的那本《黑羊與灰鷹》已被翻閱了無數次,寫滿了注釋,我寧願丟失護照與金錢,也不願意把它給弄丟了。”
序
導讀
1921 年,麗貝卡•韋斯特去佛羅倫薩拜訪諾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時,道格拉斯開玩笑說,勞倫斯只需要在市鎮逗留幾小時,可能就已經構思好一篇文章,“將那裡人們的脾氣個性描寫得淋漓盡致”。在韋斯特看來,這似乎“顯然是在幹一件傻事”。不過道格拉斯說得沒錯:他們去勞倫斯落腳的賓館看他,發現他正奮筆疾書。韋斯特當時認為,勞倫斯並不真正瞭解佛羅倫薩,不足以“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見”。直到勞倫斯去世後,她才意識到,勞倫斯“那時所寫的是他自己在那一刻的心靈情狀”,這情狀只能用象徵性的語詞才能表達。因此,“佛羅倫薩以及其他城市,都是一種象徵”。
韋斯特寫下這些話的時間是1931 年。那時,她還不曾踏上孕育《黑羊與灰鷹》這本書的第一次南斯拉夫之旅,但對於她的這部巨著來說,因勞倫斯而起的,對遊記寫作邏輯的認識卻意義非凡。事實上,這部鴻篇巨制中,她在南斯拉夫的經歷可謂微乎其微。正如知名的巴爾幹專家伊迪絲•達勒姆(Edith Durham)當時的惡意評論所言:“小說家韋斯特小姐寫下的這部鴻篇巨制所依託的不過是一次愉快的南斯拉夫之旅,而此前她對那片土地和那裡的人民一無所知。”確切地說,韋斯特小姐曾三次前往南斯拉夫:第一次,1936 年春,應英國文化委員會之邀,前去做講座;第二次,1937 年春,與丈夫亨利•安德魯斯同行;第三次是1938 年初夏。最初,她希望快筆寫出一本“速記”,可惜第二次旅程的四個月後,這一可能令其名利雙收的冒險之作卻變得“面目可憎、繁複纏結,激不起任何人的興趣”。
在研究南斯拉夫“漫長而複雜的歷史”的過程中,韋斯特掌握並梳理了她本人關於南斯拉夫的認識—同時也瞭解到很多其他東西。用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評價羅伯托•卡拉索(Roberto Calasso)《卡什之毀滅》(The Ruin of Kasch)的話來說,《黑羊與灰鷹》有兩個主題:一是南斯拉夫,二是其餘一切。至該書出版(兩卷本,共計五十萬英文詞匯)韋斯特才略帶茫然地發現,自己“從1936 年起投入了五年時光,花費鉅資,殫精竭慮,以一種從任何尋常的藝術或商業眼光看都極不明智的方式,列清單似的將一個國家的林林總總記錄下來,從頭到腳直至最後一顆馬甲紐扣也不放過”。因為“(她的)海量材料”內容不斷增加,量變引起質變,以致這“清單”成了一幅巨型的、極其複雜的圖畫—不僅是她自己心靈的畫像,更是處於“二戰”邊緣的歐洲畫像。其結果是此書成為20 世紀最最優秀的傑作之一。(她曾擔心“單是此書的篇幅,就幾乎不會有人願意看”。)
一如該書本身的不尋常,其聲名更是不同尋常。韋斯特被認為是英國的一位重要作家。假如有人覺得她算不得一流作家,那主要是因為確立她聲望的多數作品所採取的文體被認為不像小說那樣適於表現宏大的主題。而作為小說家,韋斯特的重要性顯然不及勞倫斯、詹姆斯•喬伊斯(他在《尤利西斯》中天才般地“創造一種藝術形式,同時窮盡了它的所有可能性”),或者福斯特。
韋斯特最優秀的作品散落在報告文學、新聞報道和遊記之中—在傳統看來,這些文體都屬�左道旁門。《黑羊與灰鷹》的成功,極大地歸功於作者高超的創造力,她順其自然,將這種創造力發揮到極致。該書很顯然是一部文學作品,但因為在英語裡,文學(至少包括散文類別)與小說是同義語,因此這本書被默默地從本該歸屬的範疇裡挪了出來並歸於小說類。(當我向一位寫小說的朋友提及自己正在寫這篇導讀時,她問我這本書是否是以南斯拉夫為背景的;她以為這是一本小說。)很明顯,如果以評價小說的標準去看《黑羊與灰鷹》,即使它的品質上乘,其寫作形式也並不符合小說的體例。所以可能一些次等的小說作品可以安然穩居榜單之中;而一部尷尬的大部頭,因其本質上不屬�這個序列,所以難以適應這種評價以確定其不凡的品質,它被安放在什麼地方都不合適。為免於將其他卷冊從頂級經典的書架上擠下來—或者說得更極端點,為免於將整個書架掀翻—《黑羊與灰鷹》從它應有的位置跌落下來,被默默地存放在一個較低的、不重要卻安穩的位置。
一些評論家雖聲稱該書為傑作, 卻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在《域外》(Abroad)中,保羅•福塞爾(Paul Fussell)一篇關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英國文學旅行”的調查得到了高度評價。然而,與伊夫林•沃(Waugh)、勞倫斯或者格林(Greene)不同,在這份調查中沒有獨立的一章對韋斯特做出評價,她的書也只是被順口提及而已。維多利亞•格倫迪寧(Victoria Glendinning)在其關於韋斯特的傳記裡充分肯定《黑羊與灰鷹》是“韋斯特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在這一著作中,麗貝卡•韋斯特闡明了她對於宗教、道德、藝術、神話和性別的看法”。除此外,格倫迪甯對《黑羊與灰鷹》便再無話可說。對於所以努力表達它所激起的敬畏之情的嘗試,難道這本書註定要拒斥嗎?
為彌補這一缺憾,也為免於爭議,我們姑且先這樣說吧:這本書是關於南斯拉夫的一部極為重要的作品。1993 年,我在訪問過塞爾維亞之後(湊巧跟韋斯特當年一樣,也是因為英國文化委員會的緣故),為瞭解南斯拉夫,開始閱讀這本書。這本書在那之前的幾年間為回應一次局部衝突而重印發行,此次衝突恰恰被韋斯特以某種方式所預見。在《序章》裡,韋斯特回憶說,自己“盯著”關於南斯拉夫國王的一部舊電影片段,“就像一個老婦細數她杯子裡的茶葉殘渣”。該書的預言特質不出十頁便顯露出來,當韋斯特說“人們的習慣是,當一個不善經營的老人一死,其事業隨之分崩離析時,會說:‘啊,看這是怎樣的怪事啊!生前一切都穩穩當當的,可人家前腳剛一走,現在就成啥樣子了!’”我仍記得,1993 年讀這本書時我心中的迷惑,因為當時的局勢極其複雜,讓人不禁懷疑她筆下所寫的並非弗朗茨•約瑟夫而是鐵托。在這本書較後的科索沃部分中,韋斯特所雇的司機德拉古廷,擰著一個克羅地亞男孩的耳朵,語氣裡混雜著諷刺與威脅地說:“總有一天我們要把你們趕盡殺絕。”甚至在我本人僅有的關於塞爾維亞共和國與黑山共和國經歷中,也曾多次親見《黑羊與灰鷹》所描繪的場景。而作為一部關於南斯拉夫的著作,它更有著“極大的用途”,相當於一部形而上的《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而且永遠不用更新版本。【如韋斯特本人所言,“有時,我們有必要知曉我們所處的位置,在永恆,在當下”。】這部書的使用價值在新聞記者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身上得以清楚地展示。
他回憶道,自己在南斯拉夫,無論走到哪裡,都與這本書寸步不離。“我寧可丟失護照、錢,也不想丟了被我翻舊的、寫滿注釋的《黑羊與灰鷹》。”如果你不在巴爾幹半島,或者對其毫無興趣,那麼書中大量談及該地區歷史的篇幅可能令你厭煩。不過,這卻是只有雷沙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或加布裡爾•加西亞•馬爾克斯才可能寫出的史書。且看看1914 年薩拉熱窩那非比尋常的景象—那一年,就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前不久,他站在接待廳,發現裡面擠滿了自己狩獵生涯中所殺戮的大約五十萬隻野生動物(據他自己估計):
你能想像,那麼一個空間,從地上直至深紅與金色的穹頂,各種毛皮與羽毛的幽靈充塞其間,仿佛是直達穹頂的鐘乳石,因為實在是太多了:一頭頭雄鹿,它們鹿角的空隙裡擠滿山鷸、鵪鶉、野雞、鷓鴣、雷鳥,等等;一頭頭野豬,毛髮豎立,脅腹貼著脅腹,寬闊的肚腹下面的空間裡,層層疊疊擠壓著各種兔子。這些動物的眼睛清澈且漆黑如水,它們將歡快地看著屠殺它們的人的生命一步步走向終結,一如當初它們自己那副模樣。
薩拉熱窩被圍困的時候,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正在那裡執導貝克特(Beckett)的《等待戈多》,人們普遍覺得,舞臺上的景象正是對劇場外面局勢的某種荒誕主義的解說。20 世紀30 年代,在莫斯塔爾(該地以與薩拉熱窩同樣的方式,將國際社會紮了一下,使國際社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境況)某咖啡館,一個類似的寓言也曾展現在韋斯特面前:
一束束白亮的燈光下,年輕軍官在有節奏地來回穿梭。燈光傾瀉在酸性綠的檯球桌上,檯球發出冷淡的碰撞聲。房間裡彌漫著一種巴爾幹情緒,怠惰苟且,順從命運。似乎可能有這樣的情形出現:一個人進屋,掛起他的土耳其氊帽,然後解釋說—措辭剛好足以讓人理解,讓人不致覺得是瘋言亂語—所有桌前的人務必在原地等待,直到兩位正在玩檯球的軍官打完一百萬局比賽,並且眾人永恆的命運將由球局的結果而定;而這樣的要求卻被人們接受了,人們一面看報,一面安靜地坐著等待。
韋斯特的目的是要“讓過去與它所創造的現實並肩而行”。她的一部分成就就是試圖揭示了,即便是明顯不具歷史性的知覺—比如被掐下的一朵花的香氣—都飽含著過往的氣息。
地理與歷史,其道理更是如此,常常難以分割。因此,特定的地域便會“給土地上的民眾打上同樣的烙印,不管歷史帶給這片土地的是怎樣的民眾—即便是為了征服而將當地的人口滅絕,就像潑水一樣把他們倒出去,再灌入種族、哲學截然不同的另一群人”。不耐煩的讀者,往往會跳過歷史敘述的部分,但他們是在冒著很大的風險,因為過去—被敘述的歷史—可能悄無聲息地化入眼下的現實。最為引人注目的例證是在一番長篇大論之後才被提出的(讀到這裡時我覺得這論證確實有點太長),那是14 世紀塞爾維亞國王史蒂芬•杜尚統治期間,發生在普裡什蒂納的一件事。
在大約二十頁之後,我們得知了他的死亡:
在生命的第四十九年裡,他死在一個普通的小村莊裡,村莊小得今天已無跡可尋。他在痛苦中死去,似乎中了毒。由於他的死,一些不合意的事情就發生了。比如,我們坐在普裡什蒂納一家餐館,手肘下的桌布仍帶著污漬,盤子裡的雞瘦得像麻雀。一男一女朝我們走過來,女的背上扛著一個犁頭。
啊!這豈非所曾見過的最大膽的跳切、最大膽的時間移位、最出乎人意料的推演?韋斯特並沒就此打住。這對男女的出現,將她的思緒又拉回到這本書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即男人與女人之間讓人欲說還休的關係:
在大男子主義不受限制的地方,女性被驅使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卻沒有權利實踐自己的意願。這種狀況令人作嘔,說它噁心,並不是因為工作對於女性的影響—她們總能從工作中學到東西—而是因為它讓男人變成了廢物。
韋斯特仍未就此打住—又回想到史蒂芬•杜尚的死,然後才從餐桌旁起身,來到“一個土耳其式的廁所”:
地板上那黑乎乎的洞,以及廁所逼仄的空間裡顯得詭異的某種東西,讓人覺得,似乎糞便—男人所排泄的—也樹立起一種新的權力元素,充滿敵意且具有魔力,能將其暗黑的濁流與惡臭的潮濕氣息覆蓋滿整個世界……我感覺那地方正用它的穢物將我玷污,而且永遠無法再洗滌乾淨,因為那污穢的實質比溫和的肥皂和水更加頑固。
韋斯特仍然沒就此打住……我們且繞回去片刻。為了檢視所有涉及的問題的內在含義,這本書中無窮無盡的自我證明式的討論,是韋斯特創作結構與寫作風格的核心特色。她的所有結論都與過程(這本書的關鍵詞)緊密相連。
在此過程中,這些結論被一一梳理出來。任何能引起韋斯特注意的東西—比方說書的第507 頁1 的一件小事,在一家餐館裡,收音機播放著一首莫紮特交響樂—都會被作者生動直觀地傳遞出來。當韋斯特仔細描述和處理這一小插曲時,她會帶著我們踏上一段偏離主題的旅程,直到推思默想至最幽深處,再準確無誤地返回我們藉以出發的地點或場景。刺殺弗朗茨•斐迪南的普林西普以此成為作者意圖的積極代言人:“他將自己全身心地獻給每一個大事件,以便徹底領悟這一事件如何揭示宇宙之本質。”
以此看來,《黑羊與灰鷹》除了是一部浩大之作,還能是什麼呢?即便是羅伯特• 費斯克(Robert Fisk) 的《文明大戰》(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的忠實讀者,也可能覺得這令人一見難忘的大部頭之所以厚重的唯一原因是其豐富的積累以至於裡面所包含的材料太過龐大。《黑羊與灰鷹》作為一件藝術作品,其承載如此厚重。如威斯坦•休•奧登(W. H.Auden)在“給拜倫爵士的信”(“Letter to Lord Byron”,1936)中提到的,韋斯特需要“一種足夠宏大的形式,以遊弋其間”。作品思想的尺度,蘊含在它的詞句和結構之中。經編輯節選的《麗貝卡•韋斯特精簡本》(The Essential Rebecca West)看似方便,且頗具吸引力,卻感覺像是一種對美的強暴。實際上,將這樣一部作品精減到只剩要點是極不妥當的。我懷疑,其中的某些刪減恰恰是我最喜歡的部分,卻可能被刪減者認為並非精華所在。
這種刪減制約了敘述的清楚度,也是韋斯特所一再公開反對的。我不想貶低《黑羊與灰鷹》作為一部關於南斯拉夫的著作的重要意義,它基於“南斯拉夫西部與南部地區的自然構造和色彩,與(韋斯特)想像力的內在構造與色彩,實現了近乎巧合的一致”。不過,雖然我所珍視的諸多部分源自南斯拉夫,它們卻並非專屬�世界的那一個部分。這樣的例子成百上千,舉幾個便已足夠:一匹馬“情欲熾盛而焦躁不安”,它“因為恐懼,也因為享受,眼珠兒直轉,胃口好極地從食物中尋得安撫,馬也明顯知道可以從中獲得安撫,並且追尋它所宣稱的自己所恐懼之物”;一個女人,“貌美若伯恩•瓊斯的畫,同時,她握緊的粗糙指關節,可以將她可愛的臉蛋揉擦出窟窿”;那些穆斯林,“禁酒也不過是為了沒了酒精照樣能夠陶醉興奮罷了—這實在沒有任何邏輯可言”。
《黑羊與灰鷹》的文思河奔海聚,支流蜿蜒—你永遠不會知道接著會發生什麼—但這並不是說它結構混亂。它可能枝葉蔓延—這是事實,但請記住,首先,一部表面上描述一次旅行經歷的書,實際上卻是三次不同的旅行天衣無縫的糅合。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漸漸熟悉了《荒涼山莊》或《尤利西斯》的複雜結構;在當代,我們讚賞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小說繁複纏結的情節、人物及主題。而《黑羊與灰鷹》卻對讀者的期望值提出了另一種要求。它是散文體的連續即興創作,集統一性與流暢性於一體。就如同薩克斯手或號手的即興演奏那樣,韋斯特信筆漫遊卻不曾迷失路途的控制性因素是她的“基調”。“基調”在某些結構之承載上的大膽展現是這本書創新意義的關鍵所在。憑藉總體上保持一致的基調,韋斯特能夠輕鬆地在各個音區之間自由徜徉。她可以機智地說:“訪問極為愉快,雖然一無所獲—根本算不得訪問。”亦可戲謔:
“那我們幹嗎不帶上那本書呢?”我丈夫問道。“噢,那書簡直比石頭還重,”我說,“我在盥洗室的磅秤上稱過。”“你稱它幹嗎?”我丈夫問。“因為有一天我突然想起,除了自己這堆骨肉外,我已經不再知道任何別的東西的重量,”我說,“因此我拿起它來,以便讓我的心思別有所寄。”
韋斯特的文字可以詩情繾綣(“當我們駛近岸邊,船身下的水體如淡綠的寶石,陽光灑落,可見到水底的沙子”),同時又那般奇異華美:
橋的前方,河面變得寬闊,水上長著一片黃色睡蓮。兩岸邊緣像鑲了明鏡,垂柳立岸,樹的正下方,倒影映入水中。那驚人的綠,那千尾貓尾般下垂的柳枝,仿佛靜態的禮花,讓我們驚奇不已。
另一方面,當她鄙夷在波斯尼亞一家賓館遇見的一個女人時,韋斯特也會出言不遜:“她就是殘忍,她就是污穢。”(第438 頁)最讓人驚奇的是,如此的一部長篇巨作中,韋斯特展現出敘事簡潔的天賦:“(我們)再次置身於具有瑞士風情的鄉間”,“一帶裸露的山脈漆黑如夜,高聳的山脊上白雪點綴如星”(第734 頁),“一陣便士硬幣大小的暴雨”。
這篇導讀的進程正被它的長篇累牘所妨礙,但終而言之,到底必須騰出一些空間,以便一瞥韋斯特的思想。《黑羊與灰鷹》出版幾年後,韋斯特考慮過她的美國編輯本•休伯什的建議—寫一本關於大英帝國的書。她本有心採納這一建議,但“只能是在宗教與形而上學方面,我可以胡言亂語,提出隻言片語的見解”,她於是斷定,于如此一項研究,自己沒什麼新的東西可奉贈。
當然,正是這點兒“胡言亂語”,才使得《黑羊與灰鷹》成為一部極具思想性的巨著。在《尾聲》中,韋斯特談起她十多歲時,易蔔生以他的方式“糾正了英國文學中的嚴重不足,即在認識思想動力方面的失敗”。以其典型的熱切語言,她後來認定,“易蔔生對於思想觀點的呼喚,就如人對於水的渴求,恰恰是因為缺這東西”。若說韋斯特只擁有一加侖水,那是低估了她。《黑羊與灰鷹》除了其他種種,更是一股思想觀點的洪流。一如對於勞倫斯,你很難分清作者的知覺止於何處,思考又於何處發端。觀察與玄思,思想與對於“生活的本真意義”的即時反應,無時無刻不相互錯雜而行。
這本書最大的思想恰恰是它的簡潔,如此簡單以至於別無他物:“願合意之物勝於違逆”。
我們只有部分人心智正常,這部分人喜好快樂,喜好幸福的時日能更悠長,希望能活到九十多歲,然後安然地死去;希望死在自己建造的屋簷下,而這屋宇又將為後來者遮風擋雨。我們另有一半的人幾近精神失常。他們偏好違逆的東西勝過合意如願的東西,喜好痛苦,以及比黑夜更暗沉的絕望,希望暴死橫逆,致使生活回到原點,使我們的房屋一無所存,除了被煙火熏黑的地基。
當韋斯特寫下這些文字時,歐洲正一頭栽向那樣的災難。1993 年,我第一次讀到《黑羊與灰鷹》時,電視畫面上到處是熏黑的房屋地基,而且那裡正是韋斯特曾描述過的地方。韋斯特內心受夠了她本性厭惡之事的折磨,她意識到,要想得償所願,必須經過不懈的內心掙扎與政治鬥爭。她對於這一思想的堅持與信心,在奧登附於其十四行詩《戰爭時刻》(In Time of War,發表於1938 年,當時韋斯特正埋頭寫作本書)的評論中得到回應:
理智勝於瘋狂,為人所愛勝過為人所懼;
坐下來享受美餐,勝於胡亂填飽肚子;
兩人同眠勝於孤枕獨眠;快樂更合人心願。
在兩個案例中,謙遜的結尾都是智慧的明證—反之亦然。《黑羊與灰鷹》是一部浩瀚的、雄心勃勃的、繁複的巨著。它反復強調了普遍真理與樸素真理的親緣關係。韋斯特堅信,“這只是敲出的一個低階音符,換作貝多芬和莫紮特,彈奏出來的音節會高得多”。在黑山共和國,韋斯特遇到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努力想弄明白降臨在她身上的種種不幸。這次相遇使韋斯特相信,只要“在之後的千秋萬代,每代中至少有一個人永不停歇地探尋命運的本質,甚至在命運拋棄他、打擊他的時候仍不停歇,那麼終有一天我們會解開宇宙之謎”。如果一個世紀裡能有一本或兩本,像《黑羊與灰鷹》這樣的書,那麼,那一天將指日可待。
傑夫•戴爾(Geoff Dyer)
2006年
目次
旅 途
克羅地亞
達爾馬提亞
遠 行
黑塞哥維那
波斯尼亞
中冊
塞爾維亞
馬其頓
下冊
老塞爾維亞
黑 山
尾 聲
書摘/試閱
... ...
我們坐進車裡時,康斯坦丁朝著繡線菊的芬芳殘片做了個鬼臉。那是從枯萎的花上掉下來的幾片玫瑰色的花瓣,花在午飯前已經被我扔掉了。“真搞不懂,”他說,“你假裝熱愛這些漂亮的東西,然而你摘花的時候明知道它們會枯萎,會死,會被扔掉。”“為什麼不摘呢?”我回答,“長在這裡的花有千百朵,沒有人會去懷念它們。而我們,至少有兩三個小時都很欣賞它們啊。”
他聳了聳肩:“噢,好吧,你要這麼想就這麼想吧。”然後他蜷縮在自己的座位上,頭向後一甩,閉上眼睛,嘴角露出一點沉思的笑容。“你和我妻子真不一樣,”他說,“她比較神秘。她會圍著路邊的野花跳舞,而不是把它拽下來。你不會理解,你們英國人可沒這麼溫柔。”我心裡默默地想,格爾達圍著路邊的野花跳舞,不知道要給周圍的生物造成多少不溫柔的傷害呢。我還想起,她對花一樣的吉卜賽男孩女孩們心懷憎恨。“她跟土耳其人一樣‘溫柔’,”我自言自語道,“熱愛自然但也曾發起戰爭。”我們一言不發地坐著。道路從普裡什蒂納所在的低窪處向上延伸。回頭看,新近粉刷過的大樓像人的下巴似的從廣場上凸起;在它周圍,老城雜亂無章地擺在那裡。向前看,是暗綠色的平原。緊密晦暗的草地質感讓它看起來有些失真,好像是為了什麼特殊目的而準備的,就如同我們的跑道、高爾夫球場,或者錫爾伯裡的土丘—它因我們的史前祖先某種不為人所知的用途而存在。
我試圖抵制那些單調枯燥的誇張,說很多不可挽回的損失已經被造成。我假裝這裡的破壞無傷大雅。如果斯拉夫文化曾經存在于現實,塞爾維亞帝國就不至於在從史蒂芬•杜尚去世到科索沃戰爭之間的三十四年內土崩瓦解。
這是反塞爾維亞的史學家們的觀點。他們指出,在極短的時間裡,杜尚的帝國分崩離析,於是土耳其人面對的不再是一個團結的民族,而是封建貴族和追隨者們的鬆散聯合。他們重複這些觀點時,我明白這是一派胡言。如果伊麗莎白死時不是七十歲而是四十八歲,英國也可能因為派系內鬥而墮入荒廢期。有很多原因致使塞爾維亞尤其容易陷入無序狀態。首先,一個不幸的遺傳學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應該對文明的不穩定性負責。
和一些偉人一樣,史蒂芬•杜尚遺忘了他那個對父親的天賦承襲很少的兒子。他兒子和他一樣非凡、細緻,但缺乏應有的體量和魄力。史蒂芬•烏羅什繼位時年僅十九歲,但他的缺陷已暴露出來。他能幹的母親海倫皇后不想讓他掌權,似乎確有其事。她曾經一度自己親理朝政,甚至率軍上陣;哪怕是退隱至修道院,成為伊麗莎白修女時,她都還繼續管理一部分領土。史蒂芬•杜尚死後八年,拜占庭皇帝約翰急於和塞爾維亞結盟,以對抗土耳其人。於是他派出大主教做些必要的前期安排,以便撤銷他曾下達的、將塞爾維亞教會革除教籍的命令。任務本來是指向在女修道院的皇后,結果大主教在途中去世,命令也就作廢了。皇帝沒有再另派他人繼續執行。思路不連貫和朝令夕改在那個時代很普遍。
塞爾維亞衰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史蒂芬•杜尚死後不久發生的一次災禍。它對國家造成了極大損害,也動搖了其後繼者的,不論其能力有多強。它被描述為奪走許多人命的饑荒,也可以被視為是某種瘟疫的侵襲。之後,它還吞噬了君士坦丁堡的人口。這場流行病讓大片良田荒蕪,損毀了手工業中心,也廢棄了對易。這場浩劫必定影響了之前積極擴張長達七八十年的帝國,就像1929 年的經濟衰退影響了美國一樣。在那個年代,經濟理論還未成形,完全一般人的理解範疇。人們對物質的不滿常常表達為神學或政治上的爭端,儘管這和正在經歷的困難並無多大關係。
那時的拜占庭人將痛苦發洩為宗教狂熱分子間的爭議。但塞爾維亞人不像知識分子,更像是藝術家。他們喜歡就所見的進行爭論,於是爭論起他們的統治者。如果他們討論的是,耶穌在三個門徒前變容的神光會不會為肉眼所見這類問題,則要好得多,因為那只會滿足對於無形力量的虛榮。對於激起有形力量,塞爾維亞則應非常小心。它仍然在創造自己的貴族,即它的管理階層,創造時需要有獲得認可的。我們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知道君主在將軍事或民事掌控權賦予一個貴族時,會授予他武器和戰馬;貴族去世時,新舊東西必須歸還君主,由君主決定把它們還給死者的子嗣,還是授予其他家族。這就要求有一個具備教會的君主,他的意志就是神法。如果他的凡人天性讓他在做決定時搖擺不定,一群封建貴族便會對他施壓,質疑他的統領地位,並企圖據為己有。斯拉夫社會總有這個特殊的悲劇: 在危機時刻,湧現出的具有掌控力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在史蒂芬•烏羅什繼位後的頭幾年裡,相當多的人在覬覦其權力。其中有:他的母親;他父親的兄弟西美昂及其女婿;他的兩個兄弟烏格裡耶沙和武卡欣,即之前他的斟酒人和行政官,後來背叛了他,並竊取了大片土地;還有幾個小族長,其中包括一些強勢人物,他們後來在保加利亞製造過分裂。過了一陣子,在科索沃戰爭之前,這些對手都已經銷聲匿跡。史蒂芬•烏羅什被流放,然後被謀殺。如今,他的君子聲名讓忠誠於他的人在他墓前讚歎不已。
在弗魯什卡•格拉山上的亞紮克修道院,那個俄羅斯修士跟我們說起的就是他—“不,這裡沒什麼有趣的,只有一位塞爾維亞皇帝的遺體”。武卡欣和烏格裡耶沙在帶領軍隊對抗土耳其人的時候被殺,武卡欣死在一個叛變的僕人手裡。且不說那些因為自然死亡或戰爭失利而被遺忘的人,其餘的人在兩個能力卓越的王子面前也黯然失色。
一個是特弗爾特科,波斯尼亞王,尼曼雅家族的旁系子孫,奪取了達爾馬提亞和塞爾維亞的大片領土;另一個是拉紮爾王子,我在弗爾德尼克碰觸了他棕色的戰敗之手,這是同一個拉紮爾,他是塞爾維亞北部和東部土地的領主。特弗爾特科表現出自己的軍事天賦,而拉紮爾至少可以被稱為軍事效率極高。他們為了團結斯拉夫人對抗土耳其人而簽訂協議。協議反映出他們的政治家才能。這二人的素質說明,塞爾維亞帝國在史蒂芬•杜尚死後的衰落只是波峰過去之後的波谷,跟隨其後的,也許又是另一波大浪。歷史學家們力圖證明,巴爾幹基督教文明在遭受破壞之前,已經被自己的厄運詛咒。
歷史學家們勢利而膽怯,不想說命運這位老紳士的壞話。科索沃戰爭對於文明的損毀,可能相當於都鐸時代後英國積攢的總和。
我們身處的世界不過是一艘在滲漏的船,傾覆隨時可能發生,這想法令人痛苦。康斯坦丁說:“瞧,我們現在得步行,我要給你們展示我們所有的悲劇。”我聽了真不想下車。但下了車,站在路上時,我也沒察覺出什麼。面前不過是綠色的高地,和威爾特郡山谷邊上那些差不多。銀白色的高空讓景色裡的所有異國風情都消失無蹤。地平線上的皚皚白雪,在天色的映襯下,像是閃亮的雲朵。還有蜿蜒的道路和零星的建築。在這裡我看不到曾經發生的事件。在格拉查尼察時,我在現存的服裝裡看到了中世紀的塞爾維亞,如同遊客在漢普頓宮看到都鐸王朝,或者在波茨坦看到腓特烈大帝時代一樣。但是,1389 年聖維特斯節前夕駐守在這裡的軍隊,甚至都沒來我的腦海裡遊蕩一下;他們只是停留在書上的文字裡。得到這樣的“赦免”,我其實感到愜意。
我還記得曾有一件讓人不快的事降臨到我頭上,時隔一年之後,我仍感到恐懼,驚醒時只覺得空虛,徹底的空虛。我離開汽車,朝著生長在一百碼以外的粉紫色花簇走去,任憑康斯坦丁叫我也沒轉身。但德拉古廷在我後面跟來,慢聲說話,以便讓我聽懂:“像個小孩,像個小孩。”他把一隻手掌在離地兩三英尺的位置展平,另一隻指向康斯坦丁。“他就像個小孩啊!不過他有個壞妻子。上山去吧,挺有意思的。別理他。”
“不、不,不是因為這。”我說,又覺得沒法解釋。於是跟著他走過草地,和我丈夫以及康斯坦丁走在一起。我們沿著道路走上一座小山,山頂上有座粉刷過的六角形建築,覆蓋著灰藍色的金屬圓頂。周圍的草坪上到處可見穆斯林墳墓,上面的白色柱子東倒西歪。還有一些野玫瑰叢和一棵果樹,懸著一個棕色的花環,花已枯死。地形起伏的景色本來看著很空曠,等我們剛走到建築那裡時,忽然出現幾個人,聚集在我們面前。其中有一個帶著面紗的婦女,黑色的棉質衣服覆蓋著厚厚的一層夏日塵土,顏色詭異,像幽靈一般。她走路悄無聲息,懷裡抱著一個嬰兒,腳邊還站了倆小孩,讓人想起魚子醬一成不變的黑滑,以及其中蘊含的繁殖力。有一個精瘦的男子,面容透出些野性,牧羊人打扮。他的雙頰凹陷,好像平時是戴假牙的,現在去掉了;仿佛不是有什麼東西撐起的話,他的肚子也會凹下去。有一個十四歲左右的基督教女信徒,她好也戴上面紗,因為她的臉上固定不變的,是由饑餓而產生的空洞眼神。她完全被餓壞了。她身上穿著條短裙,就是從布上裁下的一塊,用一條布邊當腰帶,裙擺挺在膝蓋處,像粗製濫造的芭蕾舞裙。還有幾個男孩,都戴著土耳其氊帽,都是羅圈兒腿。面紗婦女帶著她的孩子們,悄聲地走進了六角形建築的破舊回廊裡。康斯坦丁簡單地解釋:“這是他們的聖地。”她的樣子,的確像是在從事某種既滿足衝動又履行責任的任務,比如購物或打電話。她們的程度更深,是穆斯林婦女在宗教典禮中的那種投入。牧羊人打扮的男子盯著德拉古廷看,這是對英俊青年的仰慕。孩子們把幾束花遞向我們,動作灑脫得像有貴族風度。康斯坦丁說:“這是科索沃的罌粟,別處沒有。
它們被認為是從被屠殺的塞族人的鮮血裡發芽的。後來整個平原都成了紅彤彤的一片。但是你看見的這個還小,它們還只是花蕾。”它們像一種非常美麗的野生牡丹,有金色的雌蕊和粉色的雄蕊。我丈夫從女孩手裡買了些,德拉古廷從男孩們手裡買了些;他在科索沃的舉止,猶如在春天裡,在教堂中一樣,有著某種軍人般的神秘的振奮,像是在向英勇的神聖靈魂致敬。
康斯坦丁開始講述軍隊是怎樣集結上戰場的。拉紮爾王子的軍營就駐紮在這裡,而土耳其人也在此守候。“噢,不是的!”德拉古廷打斷他。他慢慢地叫起來,並不帶怒氣,好像是被愛國熱情驅動。“他們怎麼可能守候在西北!不是這裡,是那裡,他們那些走狗!那裡,烏克•布蘭科維奇本來應該帶著部隊來的,結果他轉身離開了戰場。”“烏克•布蘭科維奇,”康斯坦丁說,“是我們故事裡的猶大。他是拉紮爾王子特別親近的姻兄。他肯定是把自己出賣給了土耳其人,在關鍵時刻,帶著部隊離開了戰場,從而使拉紮爾兩面受敵。
但現在歷史學家認為並沒有什麼背叛,說可能是其中一個塞爾維亞王公沒能及時收到前去支援拉紮爾的信息,所以讓他吃了敗仗。但是我們都知道,並不是背叛讓我們失去了科索沃,而是我們內部的分裂。”“是的,”德拉古廷說,“我們的歌裡是這樣唱的,我們被布蘭科維奇出賣了。但我們知道其實不是,我們打敗仗是因為我們不齊心。”我問:“你說你們知道是什麼意思?是說是這樣教的嗎?”“不,”他說,“我們上學前就知道了。這是我們民族的記憶。”
我又一次見證了斯拉夫思維中奇妙的誠實。掩飾歷史的相互矛盾,以便讓它們可以勉強通過理性審查。他們拒絕這樣做。他們虛構出一個故事,用自己階層內的背叛來解釋戰敗,讓自己心裡好受些,正如同德國人“一戰”後所為;但當他們頭腦中的批判性思維指出故事不過是故事時,他們也不會去壓抑這種思維。這種不一致已被承認,所以並不危險,他們就讓故事和對故事的批判在腦海裡共存。
……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