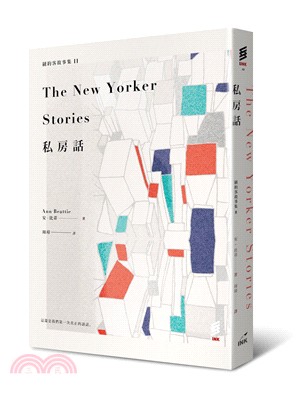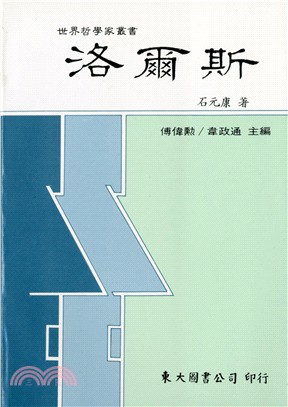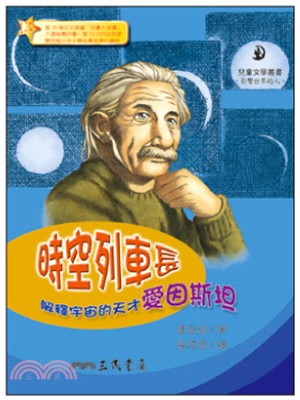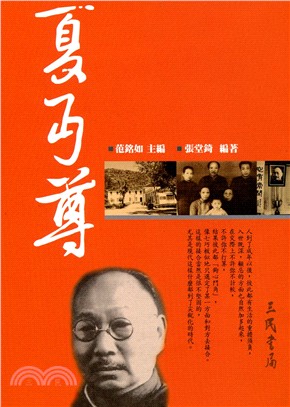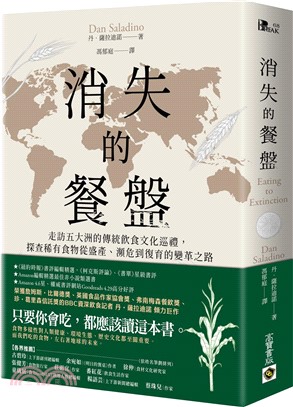紐約客故事集II:私房話
- 系列名:Link
- ISBN13:9789863871613
- 替代書名:The New Yorker Stories
- 出版社:印刻
- 作者:安‧比蒂 Ann Beattie
- 譯者:周瑋
- 裝訂/頁數:平裝/296頁
- 規格:21cm*14.8cm*1.6cm (高/寬/厚)
- 版次:1
- 出版日:2017/04/21
定 價:NT$ 330 元
優惠價:90 折 297 元
領券後再享88折
領
團購優惠券A
8本以上且滿1500元
再享89折,單本省下33元
再享89折,單本省下33元
領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可得紅利積點:8 點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紐約時報》年度十大好書
美國中産階級的精神路標,為迷失的心靈作傳
與卡佛同領極簡年代的短篇小說聖手 :安‧比蒂
聽唱片,做糕點,修草坪,
有情人,愛喝酒,抽大麻。
他們看書,唱迪倫的歌,說一兩句海明威……
在《紐約客故事集I:一輛老式雷鳥》裡,比蒂描述一群七○年代的年輕人,如何看待愛情、如何在學業與就業當中取得平衡,以及如何面對上一代家庭關係的維繫。筆下的人物總是在輟學、逃離、分手,愛情是他們的渴求,可一旦進入婚姻,卻又三心二意。
到了《私房話》,七○年代的年輕人已步入中年,任性與不願意負責任的行為,似乎漸漸遠離;反而婚姻、親子與家庭關係變成所有生活重心。有和同志交心的家庭主婦、期待與老情人見面的熟男、面對獨生女逝去的老夫妻……
然而不變的是,他們依舊聰明卻玻璃心;渴望安全感,卻深怕坐困愁城且拒絕落定。他們心思細膩卻又脆弱無比,在被傷害或傷害別人之間游移。
比蒂再次以簡潔有力的對話以及平凡的細節,精采呈現美國這年代的人們對傳統世界隱忍不言的渴望。
美國中産階級的精神路標,為迷失的心靈作傳
與卡佛同領極簡年代的短篇小說聖手 :安‧比蒂
聽唱片,做糕點,修草坪,
有情人,愛喝酒,抽大麻。
他們看書,唱迪倫的歌,說一兩句海明威……
在《紐約客故事集I:一輛老式雷鳥》裡,比蒂描述一群七○年代的年輕人,如何看待愛情、如何在學業與就業當中取得平衡,以及如何面對上一代家庭關係的維繫。筆下的人物總是在輟學、逃離、分手,愛情是他們的渴求,可一旦進入婚姻,卻又三心二意。
到了《私房話》,七○年代的年輕人已步入中年,任性與不願意負責任的行為,似乎漸漸遠離;反而婚姻、親子與家庭關係變成所有生活重心。有和同志交心的家庭主婦、期待與老情人見面的熟男、面對獨生女逝去的老夫妻……
然而不變的是,他們依舊聰明卻玻璃心;渴望安全感,卻深怕坐困愁城且拒絕落定。他們心思細膩卻又脆弱無比,在被傷害或傷害別人之間游移。
比蒂再次以簡潔有力的對話以及平凡的細節,精采呈現美國這年代的人們對傳統世界隱忍不言的渴望。
作者簡介
美國著名短篇小說家,與瑞蒙‧卡佛齊名的「極簡主義」大師。《紐約客》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作品四次被收入歐‧亨利短篇小說獎作品選集,並入選約翰‧厄普代克編輯的《二十世紀最佳美國短篇小說選》。比蒂善於描畫美國一代城市人的情緒狀態與生活方式,幫助中產階級認識了自我,對於他們的成長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乃至被視為其精神路標。
序
她指出了完全與衆不同的寫作道路──約翰‧厄普代克
至少,故事中的人在追求幸福時依然記得幸福的樣子。──瑪格麗特‧愛特伍
在過去五十年並不亞於任何人的……安‧比蒂畢生定義了故事可以做些什麼,包含人類的生活程度。──強納森‧列瑟(《布魯克林孤兒》作者)
在安‧比蒂最好的小說中,我們發現的是一種荒誕感,對那些我們用來安慰自己、逃避恐懼、壓制疑慮的虛妄希冀深深懷疑。從這一點來說,只要這虛妄希冀不死,安‧比蒂的小說就未必過時。──梅根‧歐魯爾克(Slate)
安‧比蒂是一位觀察複雜人際關係的大師,最開心的事就是看她在小說裡如何運作——即便故事並非運行在完全合理的軌道上。──大衛‧米恩斯(《祕密金魚》作者)
比蒂精闢的故事中充滿著諷刺趣味、令人難以忘懷,而且非常明智,是一部精采的結集。──《書單》(Booklist)
她語法俐落,輕描淡寫的散文風格,操作觀點極具天賦,以一種新的方式觀察讓衝突點進入新的境界。──《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比蒂完美地抓住了時代環境……深入文化並表現充沛驚人的情感。 ──《娛樂週刊》(Entertainment Weekly)
情感充沛,巧妙的細節豐富。──《聖彼得堡時報》(St. Petersburg Times)
讓人無法錯過!──The Kansas City Star
就說故事者而言,安‧比蒂是一個重要且不朽的社會評論家。──The Virginian-Pilot
至少,故事中的人在追求幸福時依然記得幸福的樣子。──瑪格麗特‧愛特伍
在過去五十年並不亞於任何人的……安‧比蒂畢生定義了故事可以做些什麼,包含人類的生活程度。──強納森‧列瑟(《布魯克林孤兒》作者)
在安‧比蒂最好的小說中,我們發現的是一種荒誕感,對那些我們用來安慰自己、逃避恐懼、壓制疑慮的虛妄希冀深深懷疑。從這一點來說,只要這虛妄希冀不死,安‧比蒂的小說就未必過時。──梅根‧歐魯爾克(Slate)
安‧比蒂是一位觀察複雜人際關係的大師,最開心的事就是看她在小說裡如何運作——即便故事並非運行在完全合理的軌道上。──大衛‧米恩斯(《祕密金魚》作者)
比蒂精闢的故事中充滿著諷刺趣味、令人難以忘懷,而且非常明智,是一部精采的結集。──《書單》(Booklist)
她語法俐落,輕描淡寫的散文風格,操作觀點極具天賦,以一種新的方式觀察讓衝突點進入新的境界。──《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比蒂完美地抓住了時代環境……深入文化並表現充沛驚人的情感。 ──《娛樂週刊》(Entertainment Weekly)
情感充沛,巧妙的細節豐富。──《聖彼得堡時報》(St. Petersburg Times)
讓人無法錯過!──The Kansas City Star
就說故事者而言,安‧比蒂是一個重要且不朽的社會評論家。──The Virginian-Pilot
目次
灰姑娘的華爾滋
燃燒的日子
等待
格林威治時間
重力
奔跑的夢
漂浮
私房話
如同玻璃
慾望
流動的水
康尼島
電視
高處
一天
夏夜的天堂
時代
白色的夜
避暑的人
兩面神
骨架
你會找到我的地方
燃燒的日子
等待
格林威治時間
重力
奔跑的夢
漂浮
私房話
如同玻璃
慾望
流動的水
康尼島
電視
高處
一天
夏夜的天堂
時代
白色的夜
避暑的人
兩面神
骨架
你會找到我的地方
書摘/試閱
私房話
芭芭拉坐在躺椅上。游泳池某處有點問題─但游泳池處處都有問題─所以現在還沒注水。刷了綠漆的池底散落著黃花和天竺葵的花瓣。鄰居的貓坐在一棵小小的合歡樹下舔爪子,小合歡樹栽在泳池一角的花槽裡。
「拍張照。」芭芭拉說,她手搭在她丈夫斯萬的手腕上。他是她第四任丈夫。他們結婚兩年了。她跟他說話的方式和跟她第三任丈夫的完全一樣。「斯萬,替那隻舔爪子的小貓拍一張。」
「我沒帶相機。」他說。
「你平常總是隨身帶的。」她說。她點了一支印尼香菸─丁香菸─劃完火柴把它扔到一個滿是櫻桃核的綠色小碟子裡。她轉向我說:「要是上週五他帶了相機,就能拍下那輛撞到那叫什麼─就是高速公路中間那水泥東西─的車了。他們在清洗血跡。」
斯萬站起來。他趿著白色人字拖,踢踢踏踏走過石板路去廚房。進去後便關上了門。
「你的工作如何,奧利佛?」芭芭拉問。奧利佛是芭芭拉的兒子,不過她難得見到他。
「有空調了。」奧利佛說,「今年夏天他們終於把空調調到合適的溫度。」
「你的工作如何?」芭芭拉對我說。
我看看她,又看看奧利佛。
「你在說什麼工作,媽媽?」他說。
「哦─將柳條刷上白漆,或別的顏色。把牆刷成黃色。要是你已經做過羊膜穿刺,你就把它們刷成藍色或粉色。」
「我們準備貼牆紙。」奧利佛說,「為什麼三十歲的女人要做羊膜穿刺?」
「我討厭柳條。」我說,「柳條是拿來做復活節籃子的。」
芭芭拉伸了懶腰。「注意到是怎麼回事了吧?」她說,「我就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他都要替你回答,好像你懷孕了就一無所用了,這樣你就有時間琢磨一個犀利的答案。」
「我看你是犀利女皇。」奧利佛對她說。
「像冰淇淋界的皇帝?」她放下手中的荷蘭偵探小說。「我從來沒搞懂過華萊士‧史蒂文斯,」她說,「你們有誰懂?」
斯萬帶著相機回來了,正在對焦。貓已經走開了,不過他反正也沒照貓,而是合影:芭芭拉穿著她那件白色緊身比基尼,奧利佛穿著牛仔短褲,褲腿邊參差不齊的白線垂在他古銅色的腿上,我穿著短褲和肥大的繡花上衣,鼓出的肚子緊緊貼著衣服。
「笑一笑。」斯萬說,「難道我非得說笑一笑嗎?」
這是芭芭拉六十歲生日的週末,奧利佛同母異父的哥哥克雷格也為此回家了。他提前給她禮物:一件印有「60」字樣的粉色T恤。奧利佛和我買了Godivas巧克力和一把上面黏有一朵絲綢百合的髮梳。斯萬會送她一張生日卡,一些從遙遠的不可思議的地方運來的蘭花,還有一張支票。她看到支票後會表示吃驚,然後不給任何人看上面的數目,但她會把生日卡傳遞一圈。晚飯的時候,蘭花會插在花瓶裡,斯萬會說些他從前在一些遙遠國度打獵的軼事。
克雷格出人意料地帶了兩個女人來。她們高,金髮,不說話,看起來像雙胞胎,卻又不是。她們的衣服上都是大麻味。介紹她倆的時候,一個戴著索尼隨身聽,另一個戴了一枚烏龜形狀的玳瑁髮飾。
天色變黑,我們都在喝汽酒。我喝了太多汽酒,覺得每個人都在看別人的光腳丫。不是雙胞胎的雙胞胎有著像嬰兒般往裡彎曲的腳趾,所以你只能看到四個腳趾上的深紅色指甲油。克雷格的腳指甲呈方形,腳後跟長繭,是打網球造成的。奧利佛古銅色的長腳在摩挲我的腿。他乾乾的腳底讓人覺得很舒服,他的腳上上下下地擦著我小腿肚上的汗,黏黏的汗水已經乾了。芭芭拉的長指甲塗成黃銅色。斯萬的大腳趾是橢圓的,沒什麼特定形狀,像是你剛開始吹氣球的時候氣球膨脹模樣。我的腳趾沒塗指甲油,因為我幾乎彎不下腰。我看著奧利佛的腳和我的腳,試圖想像一隻綜合兩人特點的嬰兒的小腳。斯萬倒酒的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我的酒已經沒了,而我一直在嚼冰塊。
在臥室裡,奧利佛的手環繞在我硬硬的肚子上,我側躺著,臉轉向另一邊。他從頭髮下面吻著我,沿著我的脊椎慢慢吻下去,嘴唇最終停在我的髖骨上。
「我的冰水杯子剛在床頭櫃上留下一圈印。」他說。他喝了一小口水。我聽到他嘆氣,然後把杯子放回床頭櫃。
「我想結婚。」我對著枕頭含混地說,「我不想最後滿懷苦澀,像芭芭拉那樣。」
他哼了一聲。「她苦澀是因為她結個不停。前一個丈夫死的時候,幾乎把所有東西都留給了克雷格。她現在又厭倦了斯萬,因為他的照片沒人買了。」
「奧利佛。」我說,吃驚地聽到自己的聲音如此無助,「你剛才說話的口氣跟你媽一樣。起碼跟我認真一點吧。」
奧利佛的臉頰貼上我的臀部。「記得第一次你按摩我的背,我舒服得笑起來嗎?」奧利佛說,「可你不知道我在幹什麼,還生氣了?還有那次你喝醉了,隨著艾迪‧費雪唱〈希望你在這裡〉,唱得那麼棒,我笑得都咳嗽了。」他翻過身。「我們結婚了。」他說。他的臉頰移到我後背中間。「我來告訴你上星期跨城巴士上發生了什麼事。」他說下去,「一個信使上了車,二十歲左右,拿著一摞信封。對著他旁邊坐在女人腿上的嬰兒說起民用電台那套話。那女的跟小孩在麥迪森下了車,從那到第三大道,他開始跟全車人說話。他說:『每個人都聽說過天上的餡餅。他們說天上的斯莫基。他們把員警叫斯莫基熊。但是你們知道我說什麼嗎?我說天上的熊。就像〈露西在點綴著鑽石的天空〉─LSD。LSD就是酸。』他穿著跑鞋和牛仔褲,一件領尖扣著鈕扣的白襯衫,脖子上還繞著領帶。」
「你為什麼跟我講這個故事?」我說。
「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出沒思考的事來。那個信使剛一下車,就把領帶繫好,開始發他手裡的東西。」他又側過頭去,嘆氣,「我無法在這個瘋狂的房子裡討論婚姻。我們去海灘上散步吧。」
「太晚了。」我說,「一定已過午夜。我累了,坐了一整天,喝酒,無所事事。」
「我跟你說實話吧。」他輕輕地說,「我受不了聽芭芭拉和斯萬做愛。」
我聽著,懷疑他可能在開玩笑。「那是老鼠穿牆的聲音。」我說。
星期天下午,芭芭拉和我在海灘上散步,吃完野餐午飯後我們都有點醉意。我好奇如果我告訴她她兒子沒有跟我結婚,她會怎麼想。她給人的印象是沒有經歷過的她都想像過了。而她說的大部分事情也終會成真。她說泳池會裂開;她警告克雷格那兩個女孩不可靠,果然,今天早上她們不見了,拿走了她放檸檬和萊姆的那個大銀碗、蛇形盤繞把手的銀盤,還有四把長柄銀湯勺─簡直就像是她們要為自己計畫一場詭異的茶會。他說,他會在紐約的奧登餐廳裡碰到她們的。這就是他的解釋。克雷格是我唯一認識會早上起床,刷牙,吃一顆藍色煩寧(Valium)的人。現在我們把他留給斯萬,讓他們在泳池邊玩一個叫做「公共援助」的遊戲。我十一點下樓時,奧利佛還在睡。「我會跟你結婚。」我爬下床時他軟綿綿地說,「我做了個夢,夢到我們沒結婚,後來一直不開心。」
我差點要沒頭沒腦地跟芭芭拉說出這些,告訴她奧利佛的夢讓我吃驚。那些夢像是一種情感狀態,本身不含任何象徵,或者甚至沒有時間所指。他醒過來,他的夢已經做了總結。我想跟她坦白:「我們幾年前對你撒謊了。我們說我們結婚了,其實沒有。我們吵了一架,輪胎漏了氣,又下雨了,我們就找了間旅館住下,後來一直沒有結婚。」
「我第一任丈夫,卡德比,他收集蝴蝶。」她說,「我永遠也無法理解。他會站在我們臥室的一扇小窗戶旁邊─我們在劍橋有個地下室公寓,就在戰前─他會把畫框中的蝴蝶標本朝著光看,好像光線射在牠們身上的某個角度會告訴他一些即使牠們飛過而翅膀也不會顯露的資訊。」她往遠處的海上望去。「倒不是說劍橋到處飛著蝴蝶。」她說,「我這才意識到。」
我笑了。
「根本不是你剛才在說的?」她說。
「我不知道。」我說,「最近我發現自己講話只是為了分散注意力。除了身體,沒什麼感覺是真實的,我的身子又這麼重。」
她對我微笑。她有紅棕色長髮,夾雜著銀絲,鬈髮四處飛揚,像水湧進泳池時的泡沫。
兩個兒子都是意外,她剛跟我說。「現在我太老了,生平頭一回我想再生一個。我嫉妒男人們到了晚年還可以有孩子。你知道那張畢卡索和他兒子克勞德的照片吧?羅伯特‧卡帕拍的。斯萬的暗室裡有─是明信片,釘起來的。他們在海灘上,孩子被舉到前面,比他爸爸還大,揉著一隻眼睛。被畢卡索舉著,就那麼微笑著,揉著一隻眼睛。」
「我們喝的是什麼酒?」我說,大腳趾在沙子上畫出一個心形圖案。
「農莊世家白葡萄酒。」她說,「沒什麼特別。」她撿起一枚貝殼─是一個小小的貽貝,外面黑色,裡面乳白色。她把它小心地放進她那件小比基尼的一個罩杯裡。她房裡有很多蕨類植物,花籃裡,地板上,植物周圍的花土上擱著一些小小的珍寶:玻璃片,碎首飾,貝殼,金線。其中最美的是一棵文竹,枝葉披垂,蓋在插在土裡的一大圈裸露的閃光燈泡上;每個夏天我都輕輕地掀起枝條看下面,如同以前我去祖母的避暑別墅,總要打開她的衣櫥,看那些標誌她孫輩身高的淡淡鉛筆劃痕還在不在。
「你愛他嗎?」她說。
五年來,這還是我們第一次真正的談話。
是的,我點頭。
「我有過四個丈夫。我肯定你知道─這是我會永遠為此出名,或遭人恥笑的地方。第一個很年輕的時候就死了。何杰金氏症。我相信現在這種病有百分之七十的治癒率。第二個丈夫為了一個女心臟病專家離開我。你知道哈樂德。而現在你也知道斯萬。」她又把一枚貝殼放在比基尼裡,放在乳頭上。「其實我只有四分之二的機會。斯萬想有一個他能在海灘上抱在眼前的小嬰兒,可是我太老了。一個三十歲人的身體,而我太老了。」
我踢著沙,望向大海。我覺得自己太飽滿,太腫脹了,可是我又極想走動,想走快一點。
「你覺得奧利佛和克雷格哪天會喜歡上對方嗎?」我說。
她聳聳肩。「哦─我不想說他們。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說點女人的私房話。也許我再也不會跟你這麼說話了。」
「為什麼?」我說。
「我一直都有……對事情有預感。當我說游泳池會在耶誕節的時候裂開,那時斯萬嘲笑我。我兩次懷孕的時候都知道會生男孩。我特別不想要第二個孩子,但現在我很高興我生下他。他比克雷格聰明。我死的時候,克雷格可能帶個會偷被子的女人回來。」她彎下腰撿起一枚閃亮的石子,扔進水裡。「我不愛我的第一任丈夫。」她說。
「為什麼不愛?」
「他的心奄奄一息。在生病和去世以前他的心就奄奄一息了。」她的手按著光肚皮,「你們這個年齡的人不這麼說話,對吧?我們吵架,後來我離開他,那年代年輕女人是不會離開年輕男人。我在紐約租了一間公寓,多少個星期我還過得不錯─我母親派她認識的所有好心女士來陪我玩,不用應付那些真是輕鬆。那也是年輕男人不會哭泣的年代,而他會把頭伏在我胸前,為一些我不明白的事情哭。看我現在這個樣子,這個身體。這種諷刺讓我覺得尷尬─乾的游泳池,沒有用的身體。這明顯得都不用說。我聽起來像艾略特吧,他那種銀行小職員式的自憐,是不是?」她注視著大海。「當我以為一切按部就班的時候─我還有了個新情人呢─我有天早上要掛一幅畫:一片灌木的原野上,一隻小鹿從中走過。我定好一個合適的位置,然後把它掛在牆上,後退,但我還是不確定,因為我不能後退太多。我沒有一個丈夫來幫我把畫掛在牆上。畫掉在地上,玻璃碎了,我哭了。」她把頭髮攏到後面,用戴在手腕上的橡皮筋把頭髮束住。透過她的比基尼我能看到貝殼的輪廓。她的雙手垂在兩邊。「我們走了這麼遠。」她說,「你不累嗎?」
我們幾乎走到戴維斯家了。也就是說我們已經走了約三英里,我身子重,有點頭暈目眩。我在想:我累了,但那沒關係。結了婚也沒關係。知道怎麼說話才是重要的。我沉沉地坐在沙子上,好像一個新受洗的基督徒。芭芭拉看起來有點擔心,後來,帶著幾分醉意,我看到她的臉色變了。她認定我只是在做出回應,休息一下。一隻海鷗俯衝下去,抓到牠想要的。我們面朝海水靠著對方坐著,她平坦的棕色腹部像一面鏡子對著大海。
入夜了,我們還在外面,在游泳池旁邊。斯萬的臉上有種閃爍幽暗的神色,好像萬聖節的傑克南瓜燈。一根香茅油蠟燭在他椅子旁邊的白色金屬桌上燃燒。
「他決定不報警。」斯萬說,「我也同意。既然那兩個年輕女士很明顯不缺你的爛銀器,她們身上還背滿了所謂的海盜寶藏,而我們都知道,海盜船是要沉沒的。」
「你要等下去嗎?」芭芭拉對克雷格說,「那你怎麼把我們的銀器追回來?」
克雷格正在上下拋著一顆網球。它消失在黑暗中,又啪的一聲打在他的手上。「你知道嗎?」他說,「有一晚我會在奧登碰到她們的。事情就是這樣─沒有什麼會永遠是終點。」
「嗯,這是我的生日,我希望我們不用討論什麼終點。」芭芭拉穿著她那件似乎因下水而縮水的粉色T恤。能看到衣服下她小小的乳房。她穿著白色緊身運動中褲,踢掉她的黑色漆皮涼鞋。
「生日快樂。」斯萬說,握住她的手。
我伸手過去握住奧利佛。第一次見他家人的時候我哭了。我睡在折疊沙發上,喝香檳,看電視上播放的《貴婦失蹤案》,夜裡他偷偷摸摸到樓下來抱我,我正在哭。我那時留短髮。我記得他的手攏住我的頭髮,揉捏著。現在頭髮長了,稀疏了,他輕輕地把它拂到旁邊。我不記得上一次哭是什麼時候了。我最初見到芭芭拉的時候,她讓我很吃驚,因為她說話如此刻薄。現在我明白了,是乏味的生活讓他們開始語出傷人。
我回頭看夜裡的海灘─沙子被月光洗得潔白,起沫的海浪靜靜地沖刷著海岸,四周有一種來自風中的空洞聲音,就像把海螺貼緊耳朵時的回聲。我腦中的咆哮聲全因身體的疼痛。一整天,嬰兒一直踢個不停,現在我知道了,早先感覺到的沉重,那種不安,一定是因為陣痛。幾乎早了一個月─這是伴隨著危險的陣痛。我把雙手從肚子上移開,好像它自己能夠平息。斯萬打開一瓶蘇打水,水噴到桌子上高高的玻璃水壺裡,桌子就在他和芭芭拉的椅子中間。他開始擰一瓶白葡萄酒的木塞。我身體裡的嬰兒轉身,讓我的肚子鼓動了一下。我竭力專心盯住看到的第一件東西。我盯著斯萬的手指,數數,好像我的寶貝已經生下來,現在我要尋找完美。我的寶貝有無數被愛的可能,被關懷,長大會變得像這些人裡的一個。又一陣宮縮,我伸手去抓奧利佛的手,但又及時停住,輕輕摸著,不去擠捏。
我真的是在一個人跡罕至的海邊別墅,跟一個沒娶我的男人在一起,跟一群我不愛的人在一起,在生孩子。
斯萬把檸檬汁擠進壺裡。煙霧似的水滴落進蘇打水和酒裡。我微笑著,第一個舉起我的杯子。痛苦是相對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
芭芭拉坐在躺椅上。游泳池某處有點問題─但游泳池處處都有問題─所以現在還沒注水。刷了綠漆的池底散落著黃花和天竺葵的花瓣。鄰居的貓坐在一棵小小的合歡樹下舔爪子,小合歡樹栽在泳池一角的花槽裡。
「拍張照。」芭芭拉說,她手搭在她丈夫斯萬的手腕上。他是她第四任丈夫。他們結婚兩年了。她跟他說話的方式和跟她第三任丈夫的完全一樣。「斯萬,替那隻舔爪子的小貓拍一張。」
「我沒帶相機。」他說。
「你平常總是隨身帶的。」她說。她點了一支印尼香菸─丁香菸─劃完火柴把它扔到一個滿是櫻桃核的綠色小碟子裡。她轉向我說:「要是上週五他帶了相機,就能拍下那輛撞到那叫什麼─就是高速公路中間那水泥東西─的車了。他們在清洗血跡。」
斯萬站起來。他趿著白色人字拖,踢踢踏踏走過石板路去廚房。進去後便關上了門。
「你的工作如何,奧利佛?」芭芭拉問。奧利佛是芭芭拉的兒子,不過她難得見到他。
「有空調了。」奧利佛說,「今年夏天他們終於把空調調到合適的溫度。」
「你的工作如何?」芭芭拉對我說。
我看看她,又看看奧利佛。
「你在說什麼工作,媽媽?」他說。
「哦─將柳條刷上白漆,或別的顏色。把牆刷成黃色。要是你已經做過羊膜穿刺,你就把它們刷成藍色或粉色。」
「我們準備貼牆紙。」奧利佛說,「為什麼三十歲的女人要做羊膜穿刺?」
「我討厭柳條。」我說,「柳條是拿來做復活節籃子的。」
芭芭拉伸了懶腰。「注意到是怎麼回事了吧?」她說,「我就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他都要替你回答,好像你懷孕了就一無所用了,這樣你就有時間琢磨一個犀利的答案。」
「我看你是犀利女皇。」奧利佛對她說。
「像冰淇淋界的皇帝?」她放下手中的荷蘭偵探小說。「我從來沒搞懂過華萊士‧史蒂文斯,」她說,「你們有誰懂?」
斯萬帶著相機回來了,正在對焦。貓已經走開了,不過他反正也沒照貓,而是合影:芭芭拉穿著她那件白色緊身比基尼,奧利佛穿著牛仔短褲,褲腿邊參差不齊的白線垂在他古銅色的腿上,我穿著短褲和肥大的繡花上衣,鼓出的肚子緊緊貼著衣服。
「笑一笑。」斯萬說,「難道我非得說笑一笑嗎?」
這是芭芭拉六十歲生日的週末,奧利佛同母異父的哥哥克雷格也為此回家了。他提前給她禮物:一件印有「60」字樣的粉色T恤。奧利佛和我買了Godivas巧克力和一把上面黏有一朵絲綢百合的髮梳。斯萬會送她一張生日卡,一些從遙遠的不可思議的地方運來的蘭花,還有一張支票。她看到支票後會表示吃驚,然後不給任何人看上面的數目,但她會把生日卡傳遞一圈。晚飯的時候,蘭花會插在花瓶裡,斯萬會說些他從前在一些遙遠國度打獵的軼事。
克雷格出人意料地帶了兩個女人來。她們高,金髮,不說話,看起來像雙胞胎,卻又不是。她們的衣服上都是大麻味。介紹她倆的時候,一個戴著索尼隨身聽,另一個戴了一枚烏龜形狀的玳瑁髮飾。
天色變黑,我們都在喝汽酒。我喝了太多汽酒,覺得每個人都在看別人的光腳丫。不是雙胞胎的雙胞胎有著像嬰兒般往裡彎曲的腳趾,所以你只能看到四個腳趾上的深紅色指甲油。克雷格的腳指甲呈方形,腳後跟長繭,是打網球造成的。奧利佛古銅色的長腳在摩挲我的腿。他乾乾的腳底讓人覺得很舒服,他的腳上上下下地擦著我小腿肚上的汗,黏黏的汗水已經乾了。芭芭拉的長指甲塗成黃銅色。斯萬的大腳趾是橢圓的,沒什麼特定形狀,像是你剛開始吹氣球的時候氣球膨脹模樣。我的腳趾沒塗指甲油,因為我幾乎彎不下腰。我看著奧利佛的腳和我的腳,試圖想像一隻綜合兩人特點的嬰兒的小腳。斯萬倒酒的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我的酒已經沒了,而我一直在嚼冰塊。
在臥室裡,奧利佛的手環繞在我硬硬的肚子上,我側躺著,臉轉向另一邊。他從頭髮下面吻著我,沿著我的脊椎慢慢吻下去,嘴唇最終停在我的髖骨上。
「我的冰水杯子剛在床頭櫃上留下一圈印。」他說。他喝了一小口水。我聽到他嘆氣,然後把杯子放回床頭櫃。
「我想結婚。」我對著枕頭含混地說,「我不想最後滿懷苦澀,像芭芭拉那樣。」
他哼了一聲。「她苦澀是因為她結個不停。前一個丈夫死的時候,幾乎把所有東西都留給了克雷格。她現在又厭倦了斯萬,因為他的照片沒人買了。」
「奧利佛。」我說,吃驚地聽到自己的聲音如此無助,「你剛才說話的口氣跟你媽一樣。起碼跟我認真一點吧。」
奧利佛的臉頰貼上我的臀部。「記得第一次你按摩我的背,我舒服得笑起來嗎?」奧利佛說,「可你不知道我在幹什麼,還生氣了?還有那次你喝醉了,隨著艾迪‧費雪唱〈希望你在這裡〉,唱得那麼棒,我笑得都咳嗽了。」他翻過身。「我們結婚了。」他說。他的臉頰移到我後背中間。「我來告訴你上星期跨城巴士上發生了什麼事。」他說下去,「一個信使上了車,二十歲左右,拿著一摞信封。對著他旁邊坐在女人腿上的嬰兒說起民用電台那套話。那女的跟小孩在麥迪森下了車,從那到第三大道,他開始跟全車人說話。他說:『每個人都聽說過天上的餡餅。他們說天上的斯莫基。他們把員警叫斯莫基熊。但是你們知道我說什麼嗎?我說天上的熊。就像〈露西在點綴著鑽石的天空〉─LSD。LSD就是酸。』他穿著跑鞋和牛仔褲,一件領尖扣著鈕扣的白襯衫,脖子上還繞著領帶。」
「你為什麼跟我講這個故事?」我說。
「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出沒思考的事來。那個信使剛一下車,就把領帶繫好,開始發他手裡的東西。」他又側過頭去,嘆氣,「我無法在這個瘋狂的房子裡討論婚姻。我們去海灘上散步吧。」
「太晚了。」我說,「一定已過午夜。我累了,坐了一整天,喝酒,無所事事。」
「我跟你說實話吧。」他輕輕地說,「我受不了聽芭芭拉和斯萬做愛。」
我聽著,懷疑他可能在開玩笑。「那是老鼠穿牆的聲音。」我說。
星期天下午,芭芭拉和我在海灘上散步,吃完野餐午飯後我們都有點醉意。我好奇如果我告訴她她兒子沒有跟我結婚,她會怎麼想。她給人的印象是沒有經歷過的她都想像過了。而她說的大部分事情也終會成真。她說泳池會裂開;她警告克雷格那兩個女孩不可靠,果然,今天早上她們不見了,拿走了她放檸檬和萊姆的那個大銀碗、蛇形盤繞把手的銀盤,還有四把長柄銀湯勺─簡直就像是她們要為自己計畫一場詭異的茶會。他說,他會在紐約的奧登餐廳裡碰到她們的。這就是他的解釋。克雷格是我唯一認識會早上起床,刷牙,吃一顆藍色煩寧(Valium)的人。現在我們把他留給斯萬,讓他們在泳池邊玩一個叫做「公共援助」的遊戲。我十一點下樓時,奧利佛還在睡。「我會跟你結婚。」我爬下床時他軟綿綿地說,「我做了個夢,夢到我們沒結婚,後來一直不開心。」
我差點要沒頭沒腦地跟芭芭拉說出這些,告訴她奧利佛的夢讓我吃驚。那些夢像是一種情感狀態,本身不含任何象徵,或者甚至沒有時間所指。他醒過來,他的夢已經做了總結。我想跟她坦白:「我們幾年前對你撒謊了。我們說我們結婚了,其實沒有。我們吵了一架,輪胎漏了氣,又下雨了,我們就找了間旅館住下,後來一直沒有結婚。」
「我第一任丈夫,卡德比,他收集蝴蝶。」她說,「我永遠也無法理解。他會站在我們臥室的一扇小窗戶旁邊─我們在劍橋有個地下室公寓,就在戰前─他會把畫框中的蝴蝶標本朝著光看,好像光線射在牠們身上的某個角度會告訴他一些即使牠們飛過而翅膀也不會顯露的資訊。」她往遠處的海上望去。「倒不是說劍橋到處飛著蝴蝶。」她說,「我這才意識到。」
我笑了。
「根本不是你剛才在說的?」她說。
「我不知道。」我說,「最近我發現自己講話只是為了分散注意力。除了身體,沒什麼感覺是真實的,我的身子又這麼重。」
她對我微笑。她有紅棕色長髮,夾雜著銀絲,鬈髮四處飛揚,像水湧進泳池時的泡沫。
兩個兒子都是意外,她剛跟我說。「現在我太老了,生平頭一回我想再生一個。我嫉妒男人們到了晚年還可以有孩子。你知道那張畢卡索和他兒子克勞德的照片吧?羅伯特‧卡帕拍的。斯萬的暗室裡有─是明信片,釘起來的。他們在海灘上,孩子被舉到前面,比他爸爸還大,揉著一隻眼睛。被畢卡索舉著,就那麼微笑著,揉著一隻眼睛。」
「我們喝的是什麼酒?」我說,大腳趾在沙子上畫出一個心形圖案。
「農莊世家白葡萄酒。」她說,「沒什麼特別。」她撿起一枚貝殼─是一個小小的貽貝,外面黑色,裡面乳白色。她把它小心地放進她那件小比基尼的一個罩杯裡。她房裡有很多蕨類植物,花籃裡,地板上,植物周圍的花土上擱著一些小小的珍寶:玻璃片,碎首飾,貝殼,金線。其中最美的是一棵文竹,枝葉披垂,蓋在插在土裡的一大圈裸露的閃光燈泡上;每個夏天我都輕輕地掀起枝條看下面,如同以前我去祖母的避暑別墅,總要打開她的衣櫥,看那些標誌她孫輩身高的淡淡鉛筆劃痕還在不在。
「你愛他嗎?」她說。
五年來,這還是我們第一次真正的談話。
是的,我點頭。
「我有過四個丈夫。我肯定你知道─這是我會永遠為此出名,或遭人恥笑的地方。第一個很年輕的時候就死了。何杰金氏症。我相信現在這種病有百分之七十的治癒率。第二個丈夫為了一個女心臟病專家離開我。你知道哈樂德。而現在你也知道斯萬。」她又把一枚貝殼放在比基尼裡,放在乳頭上。「其實我只有四分之二的機會。斯萬想有一個他能在海灘上抱在眼前的小嬰兒,可是我太老了。一個三十歲人的身體,而我太老了。」
我踢著沙,望向大海。我覺得自己太飽滿,太腫脹了,可是我又極想走動,想走快一點。
「你覺得奧利佛和克雷格哪天會喜歡上對方嗎?」我說。
她聳聳肩。「哦─我不想說他們。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說點女人的私房話。也許我再也不會跟你這麼說話了。」
「為什麼?」我說。
「我一直都有……對事情有預感。當我說游泳池會在耶誕節的時候裂開,那時斯萬嘲笑我。我兩次懷孕的時候都知道會生男孩。我特別不想要第二個孩子,但現在我很高興我生下他。他比克雷格聰明。我死的時候,克雷格可能帶個會偷被子的女人回來。」她彎下腰撿起一枚閃亮的石子,扔進水裡。「我不愛我的第一任丈夫。」她說。
「為什麼不愛?」
「他的心奄奄一息。在生病和去世以前他的心就奄奄一息了。」她的手按著光肚皮,「你們這個年齡的人不這麼說話,對吧?我們吵架,後來我離開他,那年代年輕女人是不會離開年輕男人。我在紐約租了一間公寓,多少個星期我還過得不錯─我母親派她認識的所有好心女士來陪我玩,不用應付那些真是輕鬆。那也是年輕男人不會哭泣的年代,而他會把頭伏在我胸前,為一些我不明白的事情哭。看我現在這個樣子,這個身體。這種諷刺讓我覺得尷尬─乾的游泳池,沒有用的身體。這明顯得都不用說。我聽起來像艾略特吧,他那種銀行小職員式的自憐,是不是?」她注視著大海。「當我以為一切按部就班的時候─我還有了個新情人呢─我有天早上要掛一幅畫:一片灌木的原野上,一隻小鹿從中走過。我定好一個合適的位置,然後把它掛在牆上,後退,但我還是不確定,因為我不能後退太多。我沒有一個丈夫來幫我把畫掛在牆上。畫掉在地上,玻璃碎了,我哭了。」她把頭髮攏到後面,用戴在手腕上的橡皮筋把頭髮束住。透過她的比基尼我能看到貝殼的輪廓。她的雙手垂在兩邊。「我們走了這麼遠。」她說,「你不累嗎?」
我們幾乎走到戴維斯家了。也就是說我們已經走了約三英里,我身子重,有點頭暈目眩。我在想:我累了,但那沒關係。結了婚也沒關係。知道怎麼說話才是重要的。我沉沉地坐在沙子上,好像一個新受洗的基督徒。芭芭拉看起來有點擔心,後來,帶著幾分醉意,我看到她的臉色變了。她認定我只是在做出回應,休息一下。一隻海鷗俯衝下去,抓到牠想要的。我們面朝海水靠著對方坐著,她平坦的棕色腹部像一面鏡子對著大海。
入夜了,我們還在外面,在游泳池旁邊。斯萬的臉上有種閃爍幽暗的神色,好像萬聖節的傑克南瓜燈。一根香茅油蠟燭在他椅子旁邊的白色金屬桌上燃燒。
「他決定不報警。」斯萬說,「我也同意。既然那兩個年輕女士很明顯不缺你的爛銀器,她們身上還背滿了所謂的海盜寶藏,而我們都知道,海盜船是要沉沒的。」
「你要等下去嗎?」芭芭拉對克雷格說,「那你怎麼把我們的銀器追回來?」
克雷格正在上下拋著一顆網球。它消失在黑暗中,又啪的一聲打在他的手上。「你知道嗎?」他說,「有一晚我會在奧登碰到她們的。事情就是這樣─沒有什麼會永遠是終點。」
「嗯,這是我的生日,我希望我們不用討論什麼終點。」芭芭拉穿著她那件似乎因下水而縮水的粉色T恤。能看到衣服下她小小的乳房。她穿著白色緊身運動中褲,踢掉她的黑色漆皮涼鞋。
「生日快樂。」斯萬說,握住她的手。
我伸手過去握住奧利佛。第一次見他家人的時候我哭了。我睡在折疊沙發上,喝香檳,看電視上播放的《貴婦失蹤案》,夜裡他偷偷摸摸到樓下來抱我,我正在哭。我那時留短髮。我記得他的手攏住我的頭髮,揉捏著。現在頭髮長了,稀疏了,他輕輕地把它拂到旁邊。我不記得上一次哭是什麼時候了。我最初見到芭芭拉的時候,她讓我很吃驚,因為她說話如此刻薄。現在我明白了,是乏味的生活讓他們開始語出傷人。
我回頭看夜裡的海灘─沙子被月光洗得潔白,起沫的海浪靜靜地沖刷著海岸,四周有一種來自風中的空洞聲音,就像把海螺貼緊耳朵時的回聲。我腦中的咆哮聲全因身體的疼痛。一整天,嬰兒一直踢個不停,現在我知道了,早先感覺到的沉重,那種不安,一定是因為陣痛。幾乎早了一個月─這是伴隨著危險的陣痛。我把雙手從肚子上移開,好像它自己能夠平息。斯萬打開一瓶蘇打水,水噴到桌子上高高的玻璃水壺裡,桌子就在他和芭芭拉的椅子中間。他開始擰一瓶白葡萄酒的木塞。我身體裡的嬰兒轉身,讓我的肚子鼓動了一下。我竭力專心盯住看到的第一件東西。我盯著斯萬的手指,數數,好像我的寶貝已經生下來,現在我要尋找完美。我的寶貝有無數被愛的可能,被關懷,長大會變得像這些人裡的一個。又一陣宮縮,我伸手去抓奧利佛的手,但又及時停住,輕輕摸著,不去擠捏。
我真的是在一個人跡罕至的海邊別墅,跟一個沒娶我的男人在一起,跟一群我不愛的人在一起,在生孩子。
斯萬把檸檬汁擠進壺裡。煙霧似的水滴落進蘇打水和酒裡。我微笑著,第一個舉起我的杯子。痛苦是相對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