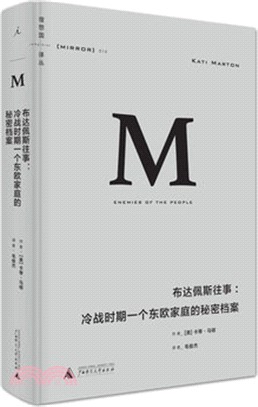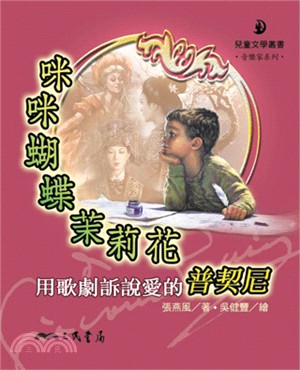布達佩斯往事:冷戰時期一個東歐家庭的秘密檔案(簡體書)
商品資訊
人民幣定價:59 元
定價
:NT$ 354 元優惠價
:87 折 308 元
絕版無法訂購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通過冷戰時期匈牙利秘密員警長達20年的檔案,所揭開的一部隱藏了幾十年的家庭歷史和時代側記。
冷戰時期,蘇聯集團中的匈牙利,秘密員警通過龐大的告密網,試圖全面滲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作者的父母原是匈牙利著名記者,他們的報導是西方瞭解匈牙利的重要資訊來源。因此他們被視為“人民的敵人”,長期受秘密員警的監控,終因叛國和間諜罪而先後入獄。一家移居美國後,匈牙利政府卻又異想天開地試圖招募他們當間諜,而美國也對他們進行了幾年的監控。書中不只還原了馬頓夫婦被告密者包圍的經歷和遭遇,他們的抗爭、堅守、脆弱和勇氣,也展現了他們情感和內心的矛盾——夫妻之間相互的感情背叛與災難中的支撐,父母子女之間的愛與親情,人性的堅強與軟弱,從而使得這本書更為豐富、複雜,具有血肉。
冷戰時期,蘇聯集團中的匈牙利,秘密員警通過龐大的告密網,試圖全面滲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作者的父母原是匈牙利著名記者,他們的報導是西方瞭解匈牙利的重要資訊來源。因此他們被視為“人民的敵人”,長期受秘密員警的監控,終因叛國和間諜罪而先後入獄。一家移居美國後,匈牙利政府卻又異想天開地試圖招募他們當間諜,而美國也對他們進行了幾年的監控。書中不只還原了馬頓夫婦被告密者包圍的經歷和遭遇,他們的抗爭、堅守、脆弱和勇氣,也展現了他們情感和內心的矛盾——夫妻之間相互的感情背叛與災難中的支撐,父母子女之間的愛與親情,人性的堅強與軟弱,從而使得這本書更為豐富、複雜,具有血肉。
作者簡介
卡蒂•馬頓(Kati Marton),美籍匈牙利人,幼年隨她的父母移居美國,獲匈牙利政府最高文職獎。著有六部作品,包括《紐約時報》暢銷書《隱藏的權力:塑造我們歷史的總統婚姻》《大逃亡》等。
毛俊傑,1952年生於上海,1978年入復旦分校中文系,1981年後定居紐約,譯作有法蘭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奧蘭多•費吉斯《耳語者》、傑克•凱魯亞克《吉拉德的幻象》等。
毛俊傑,1952年生於上海,1978年入復旦分校中文系,1981年後定居紐約,譯作有法蘭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奧蘭多•費吉斯《耳語者》、傑克•凱魯亞克《吉拉德的幻象》等。
名人/編輯推薦
編輯推薦
1,著名學者徐賁專文導讀,“見證冷戰歷史的家庭故事”,以及在遍佈秘密員警、告密網的國度裡,卡在兩個世界中間的人們生活與命運的另一個典型樣本。
2,一切從一份意外收到的匈牙利秘密員警檔案袋開始。這是一個監視、告密、出賣、背叛、審判、囚禁、信仰、堅守、勇氣、釋放、抗爭、逃亡,而後刻意隱藏、遺忘的故事。
3,面對不堪回首的歷史,該“讓睡著的狗繼續躺著”,還是要“打開潘朵拉魔盒”?遮蔽幾十年的秘密員警幽靈檔案一朝揭開,呈現出一個守住*後的道德底線——不出賣、不背叛、不當告密者的真實案例。《布達佩斯往事》,是一個重新“發現”自己父母的歷史的過程,更是那個陰暗、恐怖國家沉重如山的歷史。
4,秘密員警監視、迫害作者的父母,但她既怨恨、譴責,卻又真心感謝秘密員警,因為是他們所記錄的巨細靡遺的檔案讓她看見了父母刻意隱藏的歷史。有時候,真實的歷史,比故事、小說更為詭異、荒誕,也更感人。
5,梁文道、劉瑜、熊培雲、許知遠連袂主編——理想國譯叢(MIRROR)系列之一(014)——保持開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1,著名學者徐賁專文導讀,“見證冷戰歷史的家庭故事”,以及在遍佈秘密員警、告密網的國度裡,卡在兩個世界中間的人們生活與命運的另一個典型樣本。
2,一切從一份意外收到的匈牙利秘密員警檔案袋開始。這是一個監視、告密、出賣、背叛、審判、囚禁、信仰、堅守、勇氣、釋放、抗爭、逃亡,而後刻意隱藏、遺忘的故事。
3,面對不堪回首的歷史,該“讓睡著的狗繼續躺著”,還是要“打開潘朵拉魔盒”?遮蔽幾十年的秘密員警幽靈檔案一朝揭開,呈現出一個守住*後的道德底線——不出賣、不背叛、不當告密者的真實案例。《布達佩斯往事》,是一個重新“發現”自己父母的歷史的過程,更是那個陰暗、恐怖國家沉重如山的歷史。
4,秘密員警監視、迫害作者的父母,但她既怨恨、譴責,卻又真心感謝秘密員警,因為是他們所記錄的巨細靡遺的檔案讓她看見了父母刻意隱藏的歷史。有時候,真實的歷史,比故事、小說更為詭異、荒誕,也更感人。
5,梁文道、劉瑜、熊培雲、許知遠連袂主編——理想國譯叢(MIRROR)系列之一(014)——保持開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目次
導讀:見證冷戰歷史的家庭故事/徐賁
中文版自序:送給我的中國讀者
引言
第一章 從熱戰到冷戰
第二章 幸福的童年
第三章 媽媽和爸爸
第四章 美國人
第五章 罪上加罪
第六章 緩刑
第七章 童年的終止
第八章 囚犯
第九章 我們仨
第十章 可怕的夏天
第十一章 父親的屈服
第十二章 我們的新家庭
第十三章 父母的審判
第十四章 大洋彼岸
第十五章 重聚
第十六章 革命
第十七章 美國
第十八章 “花”
第十九章 往返布達佩斯
第二十章 又一驚奇
尾聲
致謝
譯名對照表
中文版自序:送給我的中國讀者
引言
第一章 從熱戰到冷戰
第二章 幸福的童年
第三章 媽媽和爸爸
第四章 美國人
第五章 罪上加罪
第六章 緩刑
第七章 童年的終止
第八章 囚犯
第九章 我們仨
第十章 可怕的夏天
第十一章 父親的屈服
第十二章 我們的新家庭
第十三章 父母的審判
第十四章 大洋彼岸
第十五章 重聚
第十六章 革命
第十七章 美國
第十八章 “花”
第十九章 往返布達佩斯
第二十章 又一驚奇
尾聲
致謝
譯名對照表
書摘/試閱
【導讀:見證冷戰歷史的家庭故事 /徐賁】
匈牙利裔美國記者卡蒂•馬頓(KatiMarton)在《布達佩斯往事》裡講述了父母和她自己童年時在蘇聯時代匈牙利的生活故事,許多關於她父母的往事都是從匈牙利秘密員警的檔案裡抽取出來的。羅馬尼亞前政治犯齊爾伯(Herbert Zilber)說:“社會主義的第一事業就是建立檔案。……在社會主義陣營裡,人和事只存在於他們的檔案裡。我們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檔案者手裡,也是由那些設立檔案者們所編造的,一個真人不過是他檔案的鏡影罷了。”檔案是權力統治的工具,是權力為一個人建立和保留的“客觀記錄”,但它的素材卻是由那些受人性卑劣因素和齷齪動機——嫉妒、恐懼、諂媚、背叛、出賣——所支配的“告密者”偷偷提供的。因此,檔案裡的“那個人”——蘇聯文化史專家希拉•菲茨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稱之為“檔案人”(file-self)——是一個幽靈般的陰暗存在。
檔案人是一個被簡略化和符號化了的概念,卡蒂的父母也是這樣,她說:“我發現,不停地閱讀這數千頁的秘密員警記錄,給我心靈帶來極大壓抑。……秘密員警的記錄都是如此——全然超脫於血肉之軀之外。活人被壓縮成簡易符號”。她在檔案裡看到的父母是被意識形態壓縮簡略的罪人,“秘密員警關於他們的每一份檔,都是以‘高級資產階級出身’起頭”。留在檔案裡的正式裁決是“政權不共戴天的敵人,又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忠實信徒,雖然公開從事自己的職業,但其報導對我們的國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滿敵意”。
然而,在政治意識形態定性的“人民之敵”後面,卻有著不少日常生活的細節,包括秘密員警以什麼手段、通過什麼人獲取了這些生活細節。這些偶然保留下來的細節成為卡蒂瞭解她父母的珍貴歷史材料,也為她的家庭故事提供了具體的歷史背景。卡蒂父親晚年時,新匈牙利政府向他頒發匈牙利的最高文職獎,外交部長帶給他的特殊禮物就是前匈牙利秘密員警關於他的一大袋檔案資料,他卻“從沒打開那個檔案袋”。卡蒂說:“對他而言,歷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歷史如此;對我而言,卻是探索的出發點。”在《布達佩斯往事》中,我們讀到的不僅是她從父母幽靈檔案記錄中探索到的一些真相,而且更是那個陰暗、恐怖國家沉重如山的歷史。
一、恐怖與暴力
孟德斯鳩是最早把恐怖確定為一種政治體制標誌的。他把不同的政府區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獨裁專制,並且指出,每一種社會政治組織形態都必須具備某種對維持它的體制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ethos)或文化傾向,維持君主政治是“榮譽”,維持共和政治是“德行”,而維持專制獨裁則是“恐怖”,用人民的恐懼來統治他們。恐懼是人在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脅時的基本反應,對人的傷害可以是肉體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徵意義的。
在政治權力有所公開制約,暴力行為受到法律約束,寬容和多元文化成為普遍倫理規範的社會中,恐懼會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導為一種個人的心理感覺或者超越性的經驗(如對神、上蒼、大自然、死亡的恐懼)。在這樣的社會中,儘管有時會出現集體性的驚恐,恐懼不會長久成為公眾生活的基本心態。然而,在實行秘密員警恐怖統治的國家,如納粹時期的德國、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當然會有程度的差別),普遍的無安全感、朝不保夕、驚恐猜疑及擔驚受怕便成為普遍的公眾生活狀態。恐懼因此也就成為這些國家人民夢魘般的創傷性心理特徵。這一意義上的恐懼已經不再是個人情緒的變動或者甚至那種埋藏在人類心靈深處的關於存在的超越體驗(對死亡的恐懼),而是一種在特定社會環境下形成和長久維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內容的心理機制。這是一種由政治制度製造和維持的結構性恐懼,一種必須從暴力統治的政治壓迫關係來理解的社會心理。
1950年代初,卡蒂的父母活躍于布達佩斯的新聞界,他們分別是兩家美國通訊社的記者。這時候,匈牙利人已經生活在拉科西政權的恐懼之中,記者們戰戰兢兢、噤若寒蟬,不敢越官方宣傳規定的雷池一步。匈牙利的新聞自由迅速消失,還能夠真實報導匈牙利現實情況的只剩下為外國通訊社供稿的記者,“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國記者;由於逮捕、逃離、恐嚇,到1953年僅剩三名。其中兩人,就是安德列•馬頓和伊洛娜•馬頓,剩下的第三人還是秘密員警的告密者”。
這兩位馬頓便是卡蒂的父母。他們穿著講究,生活優渥,一副“高等匈牙利人”的派頭。那時候全匈牙利一共才有兩千輛私家車,而馬頓家卻開一輛白色敞篷的斯圖貝克美國車,就像“是在乘坐一枚火箭”。這是不是太招搖顯眼,太危險了?“隨著檔案吐出的一個又一個秘密,我被另一種困惑攫住:父母為何要承擔這麼大的風險?冷戰期間,大多數匈牙利人特意穿街過巷、繞道而行,為的是避免讓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國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國外交官和新聞人。我認識的每一個匈牙利成年人都學會了竊竊耳語,而我父母卻在響亮地發表意見”。
其實,馬頓夫婦這麼做,不是因為沒有恐懼,而恰恰是因為感到恐懼。招搖顯眼、公開與美國人來往不過是他們自我保護的策略。幾年後,卡蒂的母親被捕,秘密員警逼她承認是美國間諜的時候,她說,間諜只能悄悄地做,我們到美國使館去,每次都是公開的,有這麼當間諜的嗎?當然,罪名是早就做實了的,這樣的辯護就像馬頓夫婦早先的故意招搖一樣,是不能為他們免除牢獄之災的。
馬頓夫婦不過是美蘇冷戰中的一枚棋子,他們越是在美國人那裡吃得開,匈牙利當局迫害他們就越是有所顧忌,需要三思而行。但是,他們越是與美國人來往甚密,官方也就越是懷疑他們是為美國服務的間諜。馬頓夫婦對此心知肚明,匈牙利當局也知道他們心知肚明,彼此不捅破這層窗戶紙,是因為雙方都在玩一場特殊規則的遊戲。而且,也正是因為馬頓夫婦與美國人的特殊關係,匈牙利當局認為他們可能有利用價值,給予他們特別的待遇,也許可以交換他們的某種合作。卡蒂在秘密檔案裡發現,秘密員警曾經把她父母當作“告密者招募”的物件。這是典型的冷戰滲透。
匈牙利人充滿恐懼,這不僅是因為國家鎮壓的暴力手段,更是因為他們明白,神通廣大的秘密員警在他們周圍布下了一張由無數告密者構織而成的大網。這是匈牙利執行蘇聯化的結果,它依靠的是制度化的恐怖。作為恐怖統治的主要執行者,匈牙利秘密員警“直接彙報于史達林的特務機關——內務人民委員會及後來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下設十七個科,發揮各自的特別功能。大家都知道,蘇聯紅軍是它的後臺。事實上,它是匈牙利共產黨內的蘇維埃黨派”。卡蒂心有餘悸地回憶,“我在長大過程中漸漸認清,其[秘密員警]主要特徵是殘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為都對之束手無策。它的第一科試圖通過龐大的告密網,來滲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嚇:秘密員警會在深更半夜把對象從床上帶走;他只要甘願充當告密者,就可獲釋。我現在知道,這個告密網包括我家的大部分親友;有些比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獲得優厚報酬”。
蘇聯式的秘密員警是從俄國革命後的“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發展而來的,但是,“契卡”的創始人,素以正直、清廉著稱的捷爾任斯基似乎早就察覺到,秘密員警是一個需要惡棍,也生產惡棍的體制。他說,為契卡工作的只有兩種人,“聖人和惡棍,不過現在聖人已經離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惡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敗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傢伙……不管一個人看上去多麼正直,心地如何純淨……只要在契卡工作,就會現出原形”。蘇聯將軍,曾在葉利欽總統任期內擔任俄羅斯總統特別助理的德米特裡•沃爾科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說,1930年代中期蘇聯政治員警(NKVD)軍官裡只有兩種類型的人,“冷酷無情的犬儒和喪失了良心的虐待狂”。蘇聯間諜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憶道,他負責招募新手時,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維爾•蘇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給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運或天性受過傷的人——那些性格醜陋、有自卑情結、嗜權、有影響欲但又屢遭挫折和不順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雖不至於受凍餓之苦,但卻因貧困而感到羞辱的人……這樣的人會因為從屬於一個影響大、有權力的組織而獲得優越感……他們會在一生中第一次嘗到自己很重要的甜頭,因而死心塌地地與權力結為一體”。
秘密員警統治使得整個國家的人民陷入一種近於歇斯底里的焦慮、捕風捉影的猜疑和非理性的恐懼之中,對他們有長久的道德摧殘(demoralizing)作用。秘密的暴力比公開的暴力更令人恐怖,它會使人失去思考能力、道德意識和抵抗意志,因此退化到最低等原始的動物保命本能中去。為了保命求生、避免肉體折磨,人會變得全無廉恥、奴性十足、無所不為。秘密統治對政府權力的正當行使和合道德性同樣有著嚴重的腐蝕作用。美國倫理學家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在《秘密》一書裡說,行政統治運用秘密手段,這會增加官員,“尤其是在那些自以為有使命感,因此罔顧常規道德考量的官員,濫用權力的可能性”,“一旦國家發展出秘密員警力量或實行全面審查,濫用權力的危險就會增高。秘密本身就會變成目的,行使秘密權力的人也會不知不覺發生變化”。秘密政治迫害的卑劣和敗壞,及其對全體國民的良心摧殘,正是蘇聯式統治給所有前東歐國家和其他類似國家帶來的一大禍害和道德災難。
二、無處不在的“告密者”
希瑟拉•博克在《秘密》一書裡還說:“權力來自對秘密和公開的控制力:它影響著人們思考什麼,並影響他們選擇做什麼;而反過來,越有權力,也就越能控制什麼是秘密,什麼可以公開。”匈牙利這種統治是一種對“秘密”和“公開”擁有絕對控制的權力。它可以強行規定什麼是不能對外國人洩漏的“國家機密”,也可以用各種手段,特別是利用告密者和強制“交心”、“坦白”、“認罪”來強迫人們公開自己所有的隱私。卡蒂的父親以間諜罪被逮捕,是因為他向美國人傳遞了一份匈牙利的國家預算,這種在民主國家裡公民知情權之內的資訊足以在一個極權國家成為“非法獲得”和“出賣國家”的重罪證據。
……
三、極權統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卡蒂是一個在極權統治下長大的孩子。她說,“我們是政治化了的孩子”,“在這種國家長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與國家權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機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頭來只是掌中的玩物”。卡蒂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決定閱讀她父母的檔案的。既然每個人都可能在這樣的環境中背棄自我、喪失良心,那麼,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又會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匈牙利秘密員警檔案部門的主管庫特魯茨•卡塔琳博士向準備前去閱讀檔案的卡蒂幾乎帶有溫情地建議,“這次,你如果能單獨來,會更好”。這讓卡蒂覺得不安,她徹夜未眠。她會在檔案裡看到自己怎樣的父母呢?她擔心、憂慮和害怕,是有理由的,“前不久,一位備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獲得他父親的檔案,旋即發現一連串令人驚歎的陰謀和背叛,有的甚至來自家人”。卡蒂申請要看父母的秘密檔案,秘密員警的首席歷史學家提醒她,這是在冒“打開潘朵拉魔盒”的風險。卡蒂也知道,一旦打開父母的檔案,也許就會看到他們“某種妥協或叛變的證據,從而永遠打碎父母的形象”,“這風險是實實在在的。從君特•格拉斯到米蘭•昆德拉,蓋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檔案已陸續披露出長達半個世紀的背叛。我理解,為什麼這麼多的人不願直面過去;他們對我說:讓睡著的狗躺著吧,不要自找麻煩”。
……
【中文版自序:送給我的中國讀者】
我的回憶錄譯成中文,在一個引起我獨特共鳴的國家中與讀者見面,這深深打動了我的心。我第一次來到中國,是在1973年秋天。其時,我剛剛大學畢業,來華拍攝費城交響樂團訪華紀錄片,那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美中之間第一次重大的文化交流。這次歷史性的訪問,讓有幸躬逢其盛的我們大開眼界,認知大為改觀。當然,那時的中國是個完全不同的國度,美中人民的相互隔絕已有二十多年。我觀察(並拍攝)到,在共通的音樂語言面前,我們之間的差異——語言、文化、政治和地理——幾天之內就渙然冰釋了。美國的音樂家和三名新聞人,中國東道主,以及每晚來聆聽貝多芬、莫札特和海頓的美妙樂聲的數百名中國觀眾,即使沒有言語往來,也已獲得了大量溝通。很簡單,在被迫的多年隔絕之後,雙方都燃起了重新交往的熱望。這一次旅行從來沒有在我的記憶中消失,也徹底改變了我的職業軌跡。我當即就下定決心,當一名駐外記者:從攝像機的背後,來觀看盡可能多的世界;在人類大家庭的遙遠成員中,交上盡可能多的朋友。我還承諾有朝一日會回來,對中國作進一步的探索。
我在1999年兌現了這一承諾,陪伴丈夫理查•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對中國作正式訪問。理查在自己外交生涯的初期就有改善美中關係的激情,從1970年代起,又在華盛頓和北京的和解中發揮關鍵作用。與我丈夫一起走進中國的外交部大樓,是另一次難以忘懷的經歷。許多高級官員從辦公室裡湧出,口中高叫“迪克!”(他的昵稱),與他擁抱相賀,像大學同學重聚時一樣。在過去三十年中,這些人與我丈夫一起,努力克服歷史和政治上的分歧,使美中人民走得更近。這一次,他們又有機會在一起並肩工作,為此而感到興奮。理查一直對外交事務情有獨鍾——在特定時間內與一名對手折衝樽俎——尤其是美中外交,他對中國懷有深深的依戀。
我眼前的一大喜悅是,隨著我的回憶錄在中國出版,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中國。這雖是我自己的故事,但也是經歷過冷戰特定時期的數十萬人的普遍遭遇,前車之鑒,值得銘記。
我的童年結束於六歲,其時,匈牙利秘密員警將我父母從我身邊奪走(這是孩子的直觀感受)。那是1950年代,冷戰凍結了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個人和家庭——父母和我——都變得微不足道。我將近兩年看不到父親,整整一年看不到母親——非常漫長的一年。他們被指控和定罪為美國間諜,關在看守最嚴密的監獄中,無法看到彼此和他們的女兒。他們的真正“罪行”,其實不是偷竊情報,而是做了盡職的好記者——誠實無畏地報導日常發生的真實事件。當時有太多的壞消息——政治和經濟上的肆意迫害——父母被認作危險分子,即國家的敵人。然而,他們是驕傲的匈牙利人,熱愛自己的祖國,從來沒有想去他國避難。(父親認為,以匈牙利語來上演莎士比亞戲劇,會更精彩!)他們還堅信,如果害怕人民的不同意見,如果視異議為犯罪行為,如果將不贊同高官的人打入監獄,一個國家就不能自稱是偉大的。
《布達佩斯往事》涉及國家發起的殘酷。為了征服我父母,匈牙利當局故意封鎖他們兩名幼女的任何資訊(父母被捕前不久,祖父母突然獲得去澳大利亞與我叔叔團聚的移民許可,從而確保我們姐妹孤苦伶仃)。甚至在監獄裡,父母都無法享有內心深處的思維或情感。父親的牢房難友/告密者彙報:“[馬頓]說他已不抱希望,他對孩子們的處境一無所知……在審判時,他將使用最後的發言機會來保護妻子,希望給她的案件提供轉機。對自己的案件,他則不存丁點的奢望。”
當我父母在十年前先後去世時,強加於我們過往經歷的禁忌終於解除。我回到自己的故國,直奔那個黑暗時代的心臟——匈牙利秘密員警的檔案。所找到的監視記錄觸目驚心,幾近全方位,這促使了這本回憶錄的問世。我父母不會喜歡這本書,因為它袒露了他們最為隱私的秘密。但這是一個國家的所作所為,他們是在收集不利於我父母的證據,而我是在尋找真相。在這過程中,我翻譯了數千頁監視記錄:當父母以為自己“自由自在”時,他們的每一通電話和信件,其實都在受嚴密的監視。我在這個研究過程中,真正認識了父母:不再是我兒時推崇的高大人物,而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既有缺點又有失敗——猶如我們每一個人。我現在覺得,自己離他們更近了。例如我瞭解到,超脫、矜持、不動聲色的父親,其實是非常關愛自己女兒的——在開學的第一天,他因為不知道我們能否上學,而在牢房中向隅而泣。事實上,我曾考慮過將此書獻給匈牙利秘密員警,以感謝他們巨細無遺的監視,讓我真正認識了自己的父母。理查提出明智的反對,他擔心有些讀者可能會誤讀其中的諷刺。
那是一個可怕的年代,我們姐妹與雇來照看我們的陌生人同住,沒人提及我們的父母,好像他們從人間蒸發了。小孩子是富有韌性的生物,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愛,我就在那兩年中轉向了宗教。一名天主教修女,當時只能被叫作“阿姨”,不得穿修女袍、戴十字架,卻向我傳授了教義問答,以及對聖母馬利亞的禱告。我一整天咕噥這樣的禱告,希望受到不公正囚禁的犯人(如此之多!)能得到佑護。等到父母終於出獄,我反而有點失望,因為他們並沒有對我的禱告表示感謝。一旦我們抵達美國,當地人星期日都去教堂,宗教失去禁果的魅力,我也就變得興趣索然。
儘管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我家有機會在美國開創新生活——但幼時被迫與父母分離,卻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討厭例行的告別,無法克服自己取悅于他人的難民心態,亟欲證明自己無愧於美國的熱情好客。流亡不是自然狀態,孩子應在自己的國家長大;周遭的人不但知道如何叫出小孩的名字,而且熟悉小孩的家族軼事。
眾多的秘密在讀者面前暴露無遺,對此,父母可能不盡滿意;但我認為,他們最終還是會准許的。在《布達佩斯往事》中,父母是20世紀人類最糟糕的試驗中的英勇倖存者。寫出他們的故事,又讓中國讀者獲悉這一切,我希望為確保那些黑暗日子的一去不復返,略盡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
卡蒂•馬頓
美國紐約,2015年8月15日
匈牙利裔美國記者卡蒂•馬頓(KatiMarton)在《布達佩斯往事》裡講述了父母和她自己童年時在蘇聯時代匈牙利的生活故事,許多關於她父母的往事都是從匈牙利秘密員警的檔案裡抽取出來的。羅馬尼亞前政治犯齊爾伯(Herbert Zilber)說:“社會主義的第一事業就是建立檔案。……在社會主義陣營裡,人和事只存在於他們的檔案裡。我們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檔案者手裡,也是由那些設立檔案者們所編造的,一個真人不過是他檔案的鏡影罷了。”檔案是權力統治的工具,是權力為一個人建立和保留的“客觀記錄”,但它的素材卻是由那些受人性卑劣因素和齷齪動機——嫉妒、恐懼、諂媚、背叛、出賣——所支配的“告密者”偷偷提供的。因此,檔案裡的“那個人”——蘇聯文化史專家希拉•菲茨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稱之為“檔案人”(file-self)——是一個幽靈般的陰暗存在。
檔案人是一個被簡略化和符號化了的概念,卡蒂的父母也是這樣,她說:“我發現,不停地閱讀這數千頁的秘密員警記錄,給我心靈帶來極大壓抑。……秘密員警的記錄都是如此——全然超脫於血肉之軀之外。活人被壓縮成簡易符號”。她在檔案裡看到的父母是被意識形態壓縮簡略的罪人,“秘密員警關於他們的每一份檔,都是以‘高級資產階級出身’起頭”。留在檔案裡的正式裁決是“政權不共戴天的敵人,又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忠實信徒,雖然公開從事自己的職業,但其報導對我們的國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滿敵意”。
然而,在政治意識形態定性的“人民之敵”後面,卻有著不少日常生活的細節,包括秘密員警以什麼手段、通過什麼人獲取了這些生活細節。這些偶然保留下來的細節成為卡蒂瞭解她父母的珍貴歷史材料,也為她的家庭故事提供了具體的歷史背景。卡蒂父親晚年時,新匈牙利政府向他頒發匈牙利的最高文職獎,外交部長帶給他的特殊禮物就是前匈牙利秘密員警關於他的一大袋檔案資料,他卻“從沒打開那個檔案袋”。卡蒂說:“對他而言,歷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歷史如此;對我而言,卻是探索的出發點。”在《布達佩斯往事》中,我們讀到的不僅是她從父母幽靈檔案記錄中探索到的一些真相,而且更是那個陰暗、恐怖國家沉重如山的歷史。
一、恐怖與暴力
孟德斯鳩是最早把恐怖確定為一種政治體制標誌的。他把不同的政府區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獨裁專制,並且指出,每一種社會政治組織形態都必須具備某種對維持它的體制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ethos)或文化傾向,維持君主政治是“榮譽”,維持共和政治是“德行”,而維持專制獨裁則是“恐怖”,用人民的恐懼來統治他們。恐懼是人在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脅時的基本反應,對人的傷害可以是肉體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徵意義的。
在政治權力有所公開制約,暴力行為受到法律約束,寬容和多元文化成為普遍倫理規範的社會中,恐懼會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導為一種個人的心理感覺或者超越性的經驗(如對神、上蒼、大自然、死亡的恐懼)。在這樣的社會中,儘管有時會出現集體性的驚恐,恐懼不會長久成為公眾生活的基本心態。然而,在實行秘密員警恐怖統治的國家,如納粹時期的德國、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當然會有程度的差別),普遍的無安全感、朝不保夕、驚恐猜疑及擔驚受怕便成為普遍的公眾生活狀態。恐懼因此也就成為這些國家人民夢魘般的創傷性心理特徵。這一意義上的恐懼已經不再是個人情緒的變動或者甚至那種埋藏在人類心靈深處的關於存在的超越體驗(對死亡的恐懼),而是一種在特定社會環境下形成和長久維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內容的心理機制。這是一種由政治制度製造和維持的結構性恐懼,一種必須從暴力統治的政治壓迫關係來理解的社會心理。
1950年代初,卡蒂的父母活躍于布達佩斯的新聞界,他們分別是兩家美國通訊社的記者。這時候,匈牙利人已經生活在拉科西政權的恐懼之中,記者們戰戰兢兢、噤若寒蟬,不敢越官方宣傳規定的雷池一步。匈牙利的新聞自由迅速消失,還能夠真實報導匈牙利現實情況的只剩下為外國通訊社供稿的記者,“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國記者;由於逮捕、逃離、恐嚇,到1953年僅剩三名。其中兩人,就是安德列•馬頓和伊洛娜•馬頓,剩下的第三人還是秘密員警的告密者”。
這兩位馬頓便是卡蒂的父母。他們穿著講究,生活優渥,一副“高等匈牙利人”的派頭。那時候全匈牙利一共才有兩千輛私家車,而馬頓家卻開一輛白色敞篷的斯圖貝克美國車,就像“是在乘坐一枚火箭”。這是不是太招搖顯眼,太危險了?“隨著檔案吐出的一個又一個秘密,我被另一種困惑攫住:父母為何要承擔這麼大的風險?冷戰期間,大多數匈牙利人特意穿街過巷、繞道而行,為的是避免讓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國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國外交官和新聞人。我認識的每一個匈牙利成年人都學會了竊竊耳語,而我父母卻在響亮地發表意見”。
其實,馬頓夫婦這麼做,不是因為沒有恐懼,而恰恰是因為感到恐懼。招搖顯眼、公開與美國人來往不過是他們自我保護的策略。幾年後,卡蒂的母親被捕,秘密員警逼她承認是美國間諜的時候,她說,間諜只能悄悄地做,我們到美國使館去,每次都是公開的,有這麼當間諜的嗎?當然,罪名是早就做實了的,這樣的辯護就像馬頓夫婦早先的故意招搖一樣,是不能為他們免除牢獄之災的。
馬頓夫婦不過是美蘇冷戰中的一枚棋子,他們越是在美國人那裡吃得開,匈牙利當局迫害他們就越是有所顧忌,需要三思而行。但是,他們越是與美國人來往甚密,官方也就越是懷疑他們是為美國服務的間諜。馬頓夫婦對此心知肚明,匈牙利當局也知道他們心知肚明,彼此不捅破這層窗戶紙,是因為雙方都在玩一場特殊規則的遊戲。而且,也正是因為馬頓夫婦與美國人的特殊關係,匈牙利當局認為他們可能有利用價值,給予他們特別的待遇,也許可以交換他們的某種合作。卡蒂在秘密檔案裡發現,秘密員警曾經把她父母當作“告密者招募”的物件。這是典型的冷戰滲透。
匈牙利人充滿恐懼,這不僅是因為國家鎮壓的暴力手段,更是因為他們明白,神通廣大的秘密員警在他們周圍布下了一張由無數告密者構織而成的大網。這是匈牙利執行蘇聯化的結果,它依靠的是制度化的恐怖。作為恐怖統治的主要執行者,匈牙利秘密員警“直接彙報于史達林的特務機關——內務人民委員會及後來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下設十七個科,發揮各自的特別功能。大家都知道,蘇聯紅軍是它的後臺。事實上,它是匈牙利共產黨內的蘇維埃黨派”。卡蒂心有餘悸地回憶,“我在長大過程中漸漸認清,其[秘密員警]主要特徵是殘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為都對之束手無策。它的第一科試圖通過龐大的告密網,來滲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嚇:秘密員警會在深更半夜把對象從床上帶走;他只要甘願充當告密者,就可獲釋。我現在知道,這個告密網包括我家的大部分親友;有些比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獲得優厚報酬”。
蘇聯式的秘密員警是從俄國革命後的“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發展而來的,但是,“契卡”的創始人,素以正直、清廉著稱的捷爾任斯基似乎早就察覺到,秘密員警是一個需要惡棍,也生產惡棍的體制。他說,為契卡工作的只有兩種人,“聖人和惡棍,不過現在聖人已經離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惡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敗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傢伙……不管一個人看上去多麼正直,心地如何純淨……只要在契卡工作,就會現出原形”。蘇聯將軍,曾在葉利欽總統任期內擔任俄羅斯總統特別助理的德米特裡•沃爾科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說,1930年代中期蘇聯政治員警(NKVD)軍官裡只有兩種類型的人,“冷酷無情的犬儒和喪失了良心的虐待狂”。蘇聯間諜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憶道,他負責招募新手時,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維爾•蘇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給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運或天性受過傷的人——那些性格醜陋、有自卑情結、嗜權、有影響欲但又屢遭挫折和不順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雖不至於受凍餓之苦,但卻因貧困而感到羞辱的人……這樣的人會因為從屬於一個影響大、有權力的組織而獲得優越感……他們會在一生中第一次嘗到自己很重要的甜頭,因而死心塌地地與權力結為一體”。
秘密員警統治使得整個國家的人民陷入一種近於歇斯底里的焦慮、捕風捉影的猜疑和非理性的恐懼之中,對他們有長久的道德摧殘(demoralizing)作用。秘密的暴力比公開的暴力更令人恐怖,它會使人失去思考能力、道德意識和抵抗意志,因此退化到最低等原始的動物保命本能中去。為了保命求生、避免肉體折磨,人會變得全無廉恥、奴性十足、無所不為。秘密統治對政府權力的正當行使和合道德性同樣有著嚴重的腐蝕作用。美國倫理學家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在《秘密》一書裡說,行政統治運用秘密手段,這會增加官員,“尤其是在那些自以為有使命感,因此罔顧常規道德考量的官員,濫用權力的可能性”,“一旦國家發展出秘密員警力量或實行全面審查,濫用權力的危險就會增高。秘密本身就會變成目的,行使秘密權力的人也會不知不覺發生變化”。秘密政治迫害的卑劣和敗壞,及其對全體國民的良心摧殘,正是蘇聯式統治給所有前東歐國家和其他類似國家帶來的一大禍害和道德災難。
二、無處不在的“告密者”
希瑟拉•博克在《秘密》一書裡還說:“權力來自對秘密和公開的控制力:它影響著人們思考什麼,並影響他們選擇做什麼;而反過來,越有權力,也就越能控制什麼是秘密,什麼可以公開。”匈牙利這種統治是一種對“秘密”和“公開”擁有絕對控制的權力。它可以強行規定什麼是不能對外國人洩漏的“國家機密”,也可以用各種手段,特別是利用告密者和強制“交心”、“坦白”、“認罪”來強迫人們公開自己所有的隱私。卡蒂的父親以間諜罪被逮捕,是因為他向美國人傳遞了一份匈牙利的國家預算,這種在民主國家裡公民知情權之內的資訊足以在一個極權國家成為“非法獲得”和“出賣國家”的重罪證據。
……
三、極權統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卡蒂是一個在極權統治下長大的孩子。她說,“我們是政治化了的孩子”,“在這種國家長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與國家權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機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頭來只是掌中的玩物”。卡蒂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決定閱讀她父母的檔案的。既然每個人都可能在這樣的環境中背棄自我、喪失良心,那麼,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又會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匈牙利秘密員警檔案部門的主管庫特魯茨•卡塔琳博士向準備前去閱讀檔案的卡蒂幾乎帶有溫情地建議,“這次,你如果能單獨來,會更好”。這讓卡蒂覺得不安,她徹夜未眠。她會在檔案裡看到自己怎樣的父母呢?她擔心、憂慮和害怕,是有理由的,“前不久,一位備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獲得他父親的檔案,旋即發現一連串令人驚歎的陰謀和背叛,有的甚至來自家人”。卡蒂申請要看父母的秘密檔案,秘密員警的首席歷史學家提醒她,這是在冒“打開潘朵拉魔盒”的風險。卡蒂也知道,一旦打開父母的檔案,也許就會看到他們“某種妥協或叛變的證據,從而永遠打碎父母的形象”,“這風險是實實在在的。從君特•格拉斯到米蘭•昆德拉,蓋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檔案已陸續披露出長達半個世紀的背叛。我理解,為什麼這麼多的人不願直面過去;他們對我說:讓睡著的狗躺著吧,不要自找麻煩”。
……
【中文版自序:送給我的中國讀者】
我的回憶錄譯成中文,在一個引起我獨特共鳴的國家中與讀者見面,這深深打動了我的心。我第一次來到中國,是在1973年秋天。其時,我剛剛大學畢業,來華拍攝費城交響樂團訪華紀錄片,那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美中之間第一次重大的文化交流。這次歷史性的訪問,讓有幸躬逢其盛的我們大開眼界,認知大為改觀。當然,那時的中國是個完全不同的國度,美中人民的相互隔絕已有二十多年。我觀察(並拍攝)到,在共通的音樂語言面前,我們之間的差異——語言、文化、政治和地理——幾天之內就渙然冰釋了。美國的音樂家和三名新聞人,中國東道主,以及每晚來聆聽貝多芬、莫札特和海頓的美妙樂聲的數百名中國觀眾,即使沒有言語往來,也已獲得了大量溝通。很簡單,在被迫的多年隔絕之後,雙方都燃起了重新交往的熱望。這一次旅行從來沒有在我的記憶中消失,也徹底改變了我的職業軌跡。我當即就下定決心,當一名駐外記者:從攝像機的背後,來觀看盡可能多的世界;在人類大家庭的遙遠成員中,交上盡可能多的朋友。我還承諾有朝一日會回來,對中國作進一步的探索。
我在1999年兌現了這一承諾,陪伴丈夫理查•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對中國作正式訪問。理查在自己外交生涯的初期就有改善美中關係的激情,從1970年代起,又在華盛頓和北京的和解中發揮關鍵作用。與我丈夫一起走進中國的外交部大樓,是另一次難以忘懷的經歷。許多高級官員從辦公室裡湧出,口中高叫“迪克!”(他的昵稱),與他擁抱相賀,像大學同學重聚時一樣。在過去三十年中,這些人與我丈夫一起,努力克服歷史和政治上的分歧,使美中人民走得更近。這一次,他們又有機會在一起並肩工作,為此而感到興奮。理查一直對外交事務情有獨鍾——在特定時間內與一名對手折衝樽俎——尤其是美中外交,他對中國懷有深深的依戀。
我眼前的一大喜悅是,隨著我的回憶錄在中國出版,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中國。這雖是我自己的故事,但也是經歷過冷戰特定時期的數十萬人的普遍遭遇,前車之鑒,值得銘記。
我的童年結束於六歲,其時,匈牙利秘密員警將我父母從我身邊奪走(這是孩子的直觀感受)。那是1950年代,冷戰凍結了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個人和家庭——父母和我——都變得微不足道。我將近兩年看不到父親,整整一年看不到母親——非常漫長的一年。他們被指控和定罪為美國間諜,關在看守最嚴密的監獄中,無法看到彼此和他們的女兒。他們的真正“罪行”,其實不是偷竊情報,而是做了盡職的好記者——誠實無畏地報導日常發生的真實事件。當時有太多的壞消息——政治和經濟上的肆意迫害——父母被認作危險分子,即國家的敵人。然而,他們是驕傲的匈牙利人,熱愛自己的祖國,從來沒有想去他國避難。(父親認為,以匈牙利語來上演莎士比亞戲劇,會更精彩!)他們還堅信,如果害怕人民的不同意見,如果視異議為犯罪行為,如果將不贊同高官的人打入監獄,一個國家就不能自稱是偉大的。
《布達佩斯往事》涉及國家發起的殘酷。為了征服我父母,匈牙利當局故意封鎖他們兩名幼女的任何資訊(父母被捕前不久,祖父母突然獲得去澳大利亞與我叔叔團聚的移民許可,從而確保我們姐妹孤苦伶仃)。甚至在監獄裡,父母都無法享有內心深處的思維或情感。父親的牢房難友/告密者彙報:“[馬頓]說他已不抱希望,他對孩子們的處境一無所知……在審判時,他將使用最後的發言機會來保護妻子,希望給她的案件提供轉機。對自己的案件,他則不存丁點的奢望。”
當我父母在十年前先後去世時,強加於我們過往經歷的禁忌終於解除。我回到自己的故國,直奔那個黑暗時代的心臟——匈牙利秘密員警的檔案。所找到的監視記錄觸目驚心,幾近全方位,這促使了這本回憶錄的問世。我父母不會喜歡這本書,因為它袒露了他們最為隱私的秘密。但這是一個國家的所作所為,他們是在收集不利於我父母的證據,而我是在尋找真相。在這過程中,我翻譯了數千頁監視記錄:當父母以為自己“自由自在”時,他們的每一通電話和信件,其實都在受嚴密的監視。我在這個研究過程中,真正認識了父母:不再是我兒時推崇的高大人物,而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既有缺點又有失敗——猶如我們每一個人。我現在覺得,自己離他們更近了。例如我瞭解到,超脫、矜持、不動聲色的父親,其實是非常關愛自己女兒的——在開學的第一天,他因為不知道我們能否上學,而在牢房中向隅而泣。事實上,我曾考慮過將此書獻給匈牙利秘密員警,以感謝他們巨細無遺的監視,讓我真正認識了自己的父母。理查提出明智的反對,他擔心有些讀者可能會誤讀其中的諷刺。
那是一個可怕的年代,我們姐妹與雇來照看我們的陌生人同住,沒人提及我們的父母,好像他們從人間蒸發了。小孩子是富有韌性的生物,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愛,我就在那兩年中轉向了宗教。一名天主教修女,當時只能被叫作“阿姨”,不得穿修女袍、戴十字架,卻向我傳授了教義問答,以及對聖母馬利亞的禱告。我一整天咕噥這樣的禱告,希望受到不公正囚禁的犯人(如此之多!)能得到佑護。等到父母終於出獄,我反而有點失望,因為他們並沒有對我的禱告表示感謝。一旦我們抵達美國,當地人星期日都去教堂,宗教失去禁果的魅力,我也就變得興趣索然。
儘管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我家有機會在美國開創新生活——但幼時被迫與父母分離,卻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討厭例行的告別,無法克服自己取悅于他人的難民心態,亟欲證明自己無愧於美國的熱情好客。流亡不是自然狀態,孩子應在自己的國家長大;周遭的人不但知道如何叫出小孩的名字,而且熟悉小孩的家族軼事。
眾多的秘密在讀者面前暴露無遺,對此,父母可能不盡滿意;但我認為,他們最終還是會准許的。在《布達佩斯往事》中,父母是20世紀人類最糟糕的試驗中的英勇倖存者。寫出他們的故事,又讓中國讀者獲悉這一切,我希望為確保那些黑暗日子的一去不復返,略盡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
卡蒂•馬頓
美國紐約,2015年8月15日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