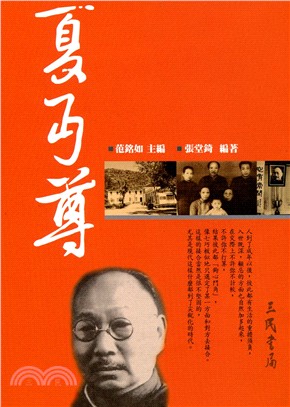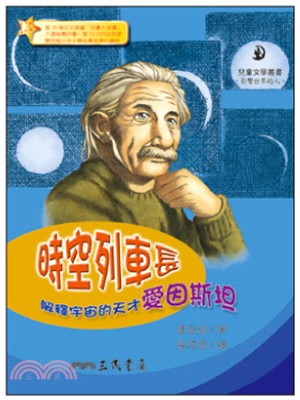再享89折,單本省下38元
商品簡介
每一個人都是一棵樹 每一棵樹都在行走
行走的樹環抱年輪 行走的人直視生命
丘延亮、林瑞明、孫大川、黃春明、尉天驄、陳芳明 盛情推薦
真正的傷痕是無法告別的。
對待傷痕的最好方法是把它修補得更為完整。
小說家季季以個人的生命轉折和文壇經歷為軸,串連起台灣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白色恐怖案,以及藝文界幾起重要事件和人物逸話。
那一年間的書寫,身心確實備受煎熬……往事紛擾糾結,更常常讓我寫至半途在電腦前俯案痛哭。我哭的是一個被扭曲的時代︰在那時代的行進中被扭曲的人性,以及被扭曲了的愛,被扭曲了的理想。曾經在那個時代裡同行的友人︰涉及「民主台灣聯盟」案的畫家吳耀忠,以及中輟的醫科生陳述孔(單槓),早已走完了灰暗的人生;涉及「密告」的楊蔚,也在二○○四年九月病逝印尼東爪哇農村。
我也痛哭被「民主台灣聯盟」案牽累的、傷痕纍纍的自己。那些記.憶.書寫,銘刻著在情感與婚姻之路上,深深傷害過我的人,以及深深撞擊過我的事件。我所描摹的往事,也許只是那個時代的一幅小小拼圖;然而,那是我所親歷的,瘡疤緩慢形成的過程。在淚眼之中,我目送年輕無知的生命遠去,並且看見當下的自己,血脈裡猶有熱情未熄。──季季
作者簡介
本名李瑞月,1944年12月生,台灣省雲林縣二崙鄉永定村人。
1988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作家。
1963年自省立虎尾女中高中畢業,放棄大學聯考,參加「文藝寫作研究隊」獲小說組冠軍。1964年起專業寫作14年。1977年進入新聞界服務,曾任《聯合報》副刊組編輯、《中國時報》副刊組主任兼「人間」副刊主編、時報出版公司副總編輯、《中國時報》主筆、《印刻文學生活誌》編輯總監。2007年底自媒體退休,任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創作坊」指導教師,蘆荻社區大學「環島文學列車」講師。2012年起專事寫作。
出版小說《屬於十七歲的》、《異鄉之死》、《拾玉鐲》等13冊;散文《夜歌》、《攝氏20--25度》、《寫給你的故事》、《我的湖》等5冊;傳記《我的姊姊張愛玲》(與張子靜合著)、《休戀逝水─顧正秋回憶錄》、《奇緣此生顧正秋》等3冊;主編年度小說選、年度散文選、時報文學獎作品集、《四十歲的心情》、《說夢》、《鮮血流在花開的季節—六四.歷史的起訴書》、《紙上風雲高信疆》等十餘冊。
序
自序:
地球上真的有一種會行走的樹
《行走的樹》出版已十年。這次增訂版有三個重點。一是增補了六萬多字;包括楊蔚遺稿(小說)三篇及其相關判決書。二是修改副題。三是調整目錄;新增一章〈亡者與病者〉。
.血脈裡猶有熱情未息
二○○五年九月至二○○六年九月在《印刻文學生活誌》撰寫「行走的樹」專欄期間,許多友人給我各種讀後意見,歸納而言是以下三種。
一、妳有那麼多痛苦往事,我們以前怎麼都不知道?妳為什麼都沒說?妳為什麼不早點寫出來?
二、那些痛苦的事情過去就算了,妳還提它幹嘛?
三、妳怎麼那麼勇敢,經過那些事還敢寫出來?
三種意見,三種人生態度。那一年間的書寫,身心確實備受煎熬;包括寫完〈阿肥家的客廳〉後全身劇痛發冷,割除膽囊取出半個雞蛋大的結石,從此成為無膽之人。而往事紛擾糾結,更常讓我寫至半途在電腦前俯案痛哭。我哭的是一個被扭曲的時代︰在那時代的行進中被扭曲的人性,以及被扭曲了的愛,被扭曲了的理想。曾經在那個時代裡同行的友人︰涉及「民主台灣聯盟」案的畫家吳耀忠,以及中輟的醫科生陳述孔(單槓),早已走完了灰暗的人生;涉及「密告」的楊蔚,也在二○○四年九月病逝印尼東爪哇農村。
我也痛哭被「民主台灣聯盟」案牽累的、傷痕纍纍的自己。那些記.憶.書寫,銘刻著在情感與婚姻之路上,深深傷害過我的人,以及深深撞擊過我的事件。我所描摹的往事,也許只是那個時代的一幅小小拼圖;然而,那是我所親歷的,瘡疤緩慢形成的過程。在淚眼之中,我目送年輕無知的生命遠去,並且看見當下的自己,血脈裡猶有熱情未熄。
.一年行走二十公分的樹
撰寫「行走的樹」專欄第一篇時,我即寫了這樣的引言:
每一個人都是一棵樹
每一棵樹都在行走
行走的樹環抱年輪
行走的人直視人生
這引言是一種文學的想像與隱喻,也是一種生命態度。
當時並未想到真實與否的問題。
二○○六年十一月《行走的樹》出版後,我面對的讀者問題之一就是他們對書名與真實的懷疑:
為什麼妳的書名叫行走的樹?
真的有一種會行走的樹嗎?
另外兩種,則是學者對書名迥然有別的闡釋。
二○○七年二月,李奭學在《文訊》雜誌二六五期發表〈何索震盪─評季季著《行走的樹》─向傷痕告別〉;以下是他的解讀:
「行走的樹」這四個中文字,在英國文學史上有出典:莎劇《馬克白》中馬氏惡貫滿盈,一朝醒來,柏南森林的樹木居然會走動,來到居址所在的丹新南城堡。他懵懂於英軍喬裝圍城,自己已陷入了險境,還以為天降異相。放在季季的上下文中,莎士比亞的意象有道理:《行走的樹》全書所寫,殆陷入人生險境的季季,而其重點所在,正是她和楊蔚間幾近40年的坎坷婚旅,可謂步步驚魂。
文學的想像無所不能,但是很慚愧,我沒細讀莎翁名劇,不知有此典故,實在不敢以此高攀。
然而,氣象學家彭順台的說法則非文學典故,而是地球上實際存在的自然景象;藉此也回答了讀者的疑惑。
彭順台(1952─)是從事日本文學翻譯數十年的黃玉燕(1934─)之女。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系畢業後赴美留學,獲紐約奧本尼大學「大氣物理」博士,任職美國海軍科學實驗室(註),也喜愛閱讀與寫作。二○○六年十二月,她在美國讀完《行走的樹》,打電話回台灣跟母親交換讀後心得。第二天,玉燕姊來電轉告,說彭順台每年都到南美洲做氣象研究,在哥斯達黎加的熱帶雨林,真的有一種樹會拖著根部緩慢行走;「為了爭取陽光和養分,一年行走二十公分。」─它的名字就是「行走的樹」(Walking Tree)。
原來,彭順台的「大氣物理」研究與我的「文學想像」是不謀而合的。
然而,一年行走二十公分,多.麼.緩.慢.的.移.動;多.麼.艱.難.的.生.存。
.傷痕也該有它們的尊嚴
專欄結集出版前,印刻編輯部提醒我書名最好加個副題。我立刻想到「定位不明」的問題。據說,羅青一九七二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吃西瓜的方法》,被書店放在「食譜」類。依此「類推」,《行走的樹》很可能被放在「森林」類、「生態」類、「自然保育」類等等。為免後患,倉促之間即以寫專欄時的心情起伏加了副題:向傷痕告別。
然而,我.錯.了。
書出之後我即發現,那個副題只是一種精神宣示;真正的傷痕是無法告別的。同時我也領悟,對待傷痕的最好方法是把它修補得更為完整。所以,這麼多年來,我不時在做的功課就是「修補」。其間因電腦硬碟故障,修補的文稿及創作中的長篇等等皆蕩然無存,讓我一度心灰意冷。
然而,我始終沒忘記「修補」,這重要的生命課題。幸而印刻留有檔案,請編輯部傳來後奮力重來,把以前寫錯的,寫漏的,有缺憾的,重新查明,盡力補正。這段過程中,與「民主台灣聯盟」案人物有密切關聯的朋友:蒙韶同學陳立樹,妻子鄒曉梅(見第五章〈烤小牛之夜〉);陳映真婚前摯友裴深言(見第十二章〈亡者與病者〉),也都參與修補,情義感人。劉大任、向陽同意轉載他們的書評(見附錄);李禎祥提供「高晞生判決書」等資料(見第十一章〈暗屜裡的答案〉),在此一併致謝。這些文字與史料的增補,讓傷痕在時光裡更為完整,也更有尊嚴。──是的,我越來越確信,傷痕也該有它們的尊嚴。
所以,十年之後,我決定捨棄那個精神宣示,換了更貼近那些傷痕本質的副題: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
.祝福二度「遠行」的老友
關於目錄調整,我把初版第一章〈搖獎機.賽馬.天才夢〉提為序章,讓結構仍維持十二章。最後一章〈亡者與病者〉是新稿:悼念「民主台灣聯盟」案的老友吳耀忠與陳述孔;懸念如今仍在北京臥病的聯盟精神領袖陳映真。
二○○六年十月,陳映真在北京二度中風昏迷,一度病危插管,震驚海內外文學界。幸而後來轉危為安;住院迄今,已近十年。經過持續復健,聽說狀況已稍好轉,偶而可以坐著輪椅由妻子麗娜推到外面透透氣。
祝福二度「遠行」的老友。
二○一五年六月十四日‧台北
註:彭順台現為「美國氣象學會」院士。
目次
自序─地球上真的有一種會行走的樹
序章:搖獎機.賽馬.天才夢─九月,以及它的文學獎故事
第1章:大盆吃肉飯碗喝酒的時代─追憶一個劫後餘生的故事
第二章:朱家餐廳俱樂部
第三章:阿肥家的客廳(上)
第四章:音樂派與左派的變奏
─阿肥家的客廳(下)
第五章:烤小牛之夜
插曲:一九六×年之冬─ 楊蔚遺作
1.等待果陀與烤牛大會
2.走到街上去
第六章:走進林海音的第一個客廳(上)
第七章:我的再生母親
─走進林海音的第一個客廳(下)
第八章:我家的文化革命
第九章:暗夜之刀與《夥計》年代
第十章:失蹤的《何索》與台灣何索
第十一章:暗屜裡的答案
第十二章:亡者與病者
1.沉默的高音─「小頭」吳耀忠
2.低音小喇叭─「單槓」陳述孔
3.宏遠的中音─「大頭」陳映真
附錄
1.生死皆為君─讀季季《行走的樹》/劉大任
2.逝去的年代‧感傷的歌─評季季散文集《行走的樹》/向陽
3.我是台灣笨蛋/楊蔚最後遺作
後記:張愛玲翻譯的四句話
發表與出版索引
書摘/試閱
第十二章 亡者與病者
1.沉默的高音─「小頭」吳耀忠(1937.8.17─1987.1.6)
從我認識楊蔚以迄所謂「民主台灣聯盟」案爆發的四年間,我從沒聽吳耀忠說過一句話。在阿肥家的客聽,在烤小牛之夜,人多嘴雜鬧哄哄的,沉默不語者不只吳耀忠一人,對他也就不以為奇。阿肥說,他在國立藝專當助教,和陳映真是死黨:兩人從初一到初三都一起坐火車上學;他們喊陳映真「大頭」,喊吳耀忠「小頭」…。
一九六六年夏天,某個星期日下午,陳映真帶著尉天驄、七等生、吳耀忠、王小虹等人來我家,說他們要辦一本同仁雜誌《文學季刊》;「楊大哥,你可是我們的典範哦,」陳映真對楊蔚說:「第一期得給我們寫篇小說……,不過沒有稿費呃……。」
我家在永和中興街四十四巷三弄底,客廳很小,兩張書桌兩個書櫃四把椅子。我去後面餐廳搬圓凳,三隻太擠,勉強放兩隻,還缺一個位子。那時我懷孕半年,陳映真要我坐下來,七等生、吳耀忠則靠在門邊站著如門神。七等生也很少話,據說為了專心寫小說辭去小學教職,太太在皮鞋店做店員供養他。吳耀忠還是老樣子,一句話也沒有。楊蔚說起「文星書店」老闆蕭孟能送我兩張書桌的曲折故事,侃侃而談有點炫耀;穿著白襯衫米黃長褲的吳耀忠,雙手交握於胸前,微笑的對我點個頭。─那算是他那天唯一的語言。
在我家坐不到一小時,陳映真帶我們穿過我家旁邊的窄巷,到對面竹林路巷內的姚一葦家,也是要去談《文學季刊》的事。姚先生住的是台銀配的日本宿舍,看不出裡面有多大,也許沒客廳,陳映真和他坐在門邊榻榻米上說話,兩隻腿還得放在外面。我們其他人就站在門邊旁聽。
雖然如此,那排日本宿舍前面倒有一片寬敞的空地,矗立著七八棵茂密的龍眼樹,垂著一串串開始暈黃的果實。樹下一群花色華麗的紅花雞,間雜著幾隻白母雞,帶著吱吱叫的小雞們低頭在地裡啄來啄去找蟲吃……。陳映真和姚先生才開始說兩句話,隔壁宿舍前突然喀喀喀響起木屐聲,一個穿碎花蓬裙的漂亮女孩左手拿隻鋁盆亮聲叫著:「嗨,雞媽麻雞小妹雞小弟來吃米喲,來吃米喲……。」邊叫邊以右手不斷的抓米往下撒。姚先生壓低了聲音說:「喏,那就是甄珍。」─—啊,甄珍,當紅的「國聯五鳳」耶,竟在我們面前撒米餵雞。我悄聲跟站旁邊的吳耀忠說:「真的好漂亮耶。」他還是雙手交握於胸前不說話,定定的望著那個彎腰撒米的背影。
─—那年他二十九歲,師大美術系畢業,在藝專當助教,父親是牙醫,也許內心很傲慢,不屑於和我這個沒讀大學的鄉下人說話吧?當時我是這麼想的。
●
後來我向他說起這些「沉默的」往事時,長我七歲的吳耀忠竟揚起酒瓶高聲道:「哎喲,我不是不跟妳說話啦,是不敢跟妳說嘛,妳那時候已經很有名,我還是無名小卒呢……。」
那是一九七八年,我初入新聞界不久。從永和到忠孝東路五段《聯合報》上班,必須搭254公車過福和橋,到光復南路國父紀念館側門那站下車;對面就是新開幕的「春之藝廊」,吳耀忠在那裡當經理。
那之前三年,我輾轉聽說陳映真、吳耀忠、陳述孔這三個判刑十年的老友已經「減刑」歸來。只有陳映真,施叔青聯絡我和他見了一面。吳耀忠、陳述孔則沒有人來聯絡。楊蔚與他們之間的那道陰影,始終籠罩著我的內心,即使不是我的錯,也讓我深覺羞恥、膽怯,不敢讓人知道,更不敢對任何朋友說想見他們。─—尤其吳耀忠,那麼沉默傲慢,見了面要說些什麼呢?
大大出乎意料的,竟是吳耀忠來聯絡我了。
「喂,是季季嗎?」從《聯合報》的電話分機裡傳來一聲高吭的男聲。我說是啊。「妳猜我是誰?」─—對這種猜謎電話,我通常直截了當回答:「猜不出來」。但我還沒說出口,那高音已自我回答:「啊,妳一定猜不出來啦,我是吳耀忠啦,在你們《聯合報》附近上班,算是鄰居啦,離得這麼近,要不要來看看老朋友?……。」─—原來他在「春之藝廊」當經理,我立即向他道恭喜,他嘿嘿的笑了,「唉,什麼喜?混口飯吃嘛。」─—坐牢回來的吳耀忠,怎麼變得這麼多?認識他十幾年,第一次對我說話,一說就這麼多,這麼興致高昂。他叫我去,真正的目的是不是要問楊蔚和他們的事?我免不了這樣懷疑著。
第二天是周末。那時還沒周休二日。平時下午兩點上班,周末晚點去沒關係。於是上班之前先去看他。
「春之藝廊」在地下室,順著迴旋狀樓梯往下走,右手邊有個雅致的池塘,咕咾石堆砌著斜坡狀小山,姑婆芋寬闊的綠葉挺立其間,金魚、大肚魚在清澈的水裡優游;左轉進去是寬敞的長方形展廳,看起來約有四十多坪。
那時我好激動啊。吳耀忠能在這樣的地方上班,真讓人欣喜而羨慕。展廳有開幕酒會,衣香鬢影,笑語喧嘩,可我被接下來的影像嚇得忘了那是誰的畫展:我在那些酒會貴賓間走來走去找吳耀忠,偶而跟幾個認識的文化界朋友打招呼說兩句客套話,就是沒看到那個已經會對我高聲說話的人。他不是打電話叫我來嗎?他是這藝廊的經理,怎麼能不在開幕會場?我無心賞畫也不好意思問人,走來走去找不到,靈機一動踱到展廳旁側的辦公室門前,探頭往裡一望,哇,一個握著酒瓶的男人,坐在椅子上對我微笑。
「哎喲,妳終於來了,呵呵呵。」吳耀忠站起來,仍然握著酒瓶。我不喝酒不懂酒,不記得他握的是什麼牌子的酒。總之那絕不是一瓶醋。
深藍西裝白領結,吳耀忠依然是修長而斯文的,只是臉孔的英氣淡薄了,好像敷上一層深色油彩,有點陰鬱。
「你怎麼可以坐在這裡喝酒?」我竟然先問罪了:「你是經理,應該在外面招呼客人呀。」
「我幹嘛要去招呼那些人?」他含糊的說:「都是些有錢沒水準的。」
「哎呀,你還是這麼傲慢。」
我忍不住說起當年的「沉默」往事,他也解釋了從不對我說話的原因。然而,那些都不重要了。他已「遠行」歸來,在這麼好的藝廊當經理,以後我可以在上班之前來看看他。歷經那場劫難之後,他願意主動打電話給我,願意大聲的對我說話,這份情誼是讓我感動而且感激的。他如果問楊蔚的事,我會仔細說的。
然而,在後來的開幕酒會裡,我依然必須時常到裡面的辦公室找他。他依然穿著西裝,握著酒瓶,坐在那裡喝得醺醺然,痛罵一些他看不起的現代畫家,御用畫家,御用文人。
一九七八年八月,《雄獅美術》第九十期登了陳映真以筆名許南村發表的〈人與歷史─—畫家吳耀忠訪問記〉。兩個青春期一起成長,青壯期同時入獄七年的老友,光就這點來看,這篇訪問就備受矚目;對現代派與抽象畫的抨擊更是轟動一時,讓我對吳耀忠的歷史與繪畫有了比較廣面的了解。其中兩個段落,一說童年,一說現實,是我當時最留意的。
在我們十個兄弟姊妹中,我排行第五,卻是父母頭生的男孩。……據說,只要把我往門檻上一擺,我就能安安靜靜的在門檻上坐上一天,默默地、興味十足地看著往來的人群……。
數月前我來到「春之藝廊」工作,換取生活費用,求個安定,然後希望很快就開始畫畫。嚴格意義上的「藝廊」的營作是藝術文化的一環。藝廊不可免的需要注意生意、業務,一切都應該按照經營的法則去做。必須先有這個認識,才能在業務展開中連帶地做些有益於繪畫向上的事。……
前一段回憶童幼時期的安於沉默與觀察。後一段則表述他作為「春之藝廊」經理的業務理念。至於坐牢回來後的多話、憤怒、罵人,以及在辦公室握著酒瓶醺醺然的畫面,在那篇訪問記裡是隱而不顯的。
雖是如此,清醒的時候他還是很努力工作的,策畫了不少轟動繪畫界的展覽和講座活動。有時工作忙,我也不是每一場都去參加。一九七九年七月,洪瑞麟第二次個展「三十五年礦工造型展」的開幕酒會,我看到了神采飛揚的吳耀忠,風度翩翩的穿梭於賓客間解說洪瑞麟的人與作品。如果吳耀忠能一直這樣,該有多好啊。在他的辦公室裡,不是喝得很醉的時候,他也會談起他尊敬的李梅樹老師,談起洪瑞麟這樣的「礦工畫家」;尊敬他筆下那些被現實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沉鬱無告的勞動者。在陳映真訪問記刊出的十多幅吳耀忠畫作裡,那五幅「建築連作」也都是沉鬱無告的勞動者。即使是他自稱出獄後為了「糊口」而畫的那些作家─—陳映真、鍾理和、吳濁流等等─的作品封面,也大多帶有那種厚重的暗鬱風格。
那段近兩年在「春之藝廊」的見面,如今回憶起來有點像是時空倒置:吳耀忠話多了,我的話少了。他的話,幾乎都是酒沫與口沫齊飛的。他罵那些在牢裡要他畫國父遺像、領袖畫像的,「駛伊娘的走狗」,罵那些現代派畫家的抽象畫,「不知在塗什麼碗糕?」罵創作思維僵化的政工派畫家,「面皮比圍牆還要厚好幾層……。」有時他甚至也罵起了陳映真,「大頭仔啊,就是有大頭病。」─—奇怪的是,他沒罵過楊蔚,甚至也沒問起過;也許不好意思,也許,更重要的,即使喝醉了,他的內心仍保留著他很在意的君子氣度。
他不太醉的時候,也會痛罵某些年輕畫家急於求名求利,例如有個美術新人獎在春之展覽,首獎已被藏家訂走,某商界人士找到那個得獎人,指定他「畫一幅一模一樣的,也是二十萬。」那位新人真的畫了,「就為了二十萬啊!」他怒拍著桌子,「畫有畫格,人有人格,每一幅畫都該是獨一無二的創作嘛……。」
我中斷他的話說:「年輕人都可以在春之展覽作品了,你也該準備在春之辦個個展。」
「那怎麼可以?」他說:「我自己在這裡做經理,這是起碼的職業道德……。」
「你不是跟大頭說,很快就開始畫畫嗎?大家都希望你早點開個嘛。」
「有啊,我有在畫,」他把酒瓶往桌面用力一放,「再等兩年吧。」
那個動作彷彿下了大決心,說完默默瞪著我,兀自笑起來了。
一九八○年初,我轉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班。報社在西區,周末很難再去東區的「春之藝廊」。半年多之後,聽說吳耀忠也離開那裡了。
●
一九八七年七月中旬,我為第二本散文集《攝氏20─25度》寫了一篇後記:〈妳這十一年只有這二十篇散文嗎?〉;開頭四分之一篇幅寫的是一個畫家。
我有個畫家朋友說要開畫展,說了七、八年都不見動靜。他受過嚴謹的學院美術教育,有深厚的素描基礎;所畫作品有寫實的靈動,也有寫意的情趣。愛他才華的朋友,每每為畫展之事責怪他的疏懶,他都一笑置之。
在這個越來越講求立即效益的時代,「疏懶」常被某些積極人士視為「不求上進」的同義詞。但我的畫家朋友無視一切現實利益者的責難,仍然每天喝酒、抽菸、漫步、冥想,過著我行我素、在別人看來近乎頹唐荒蕪的生活,只有興之所至才在畫架前畫幾筆。
兩三年前的某一天,我和另一個朋友去看他。他住在中央果菜公司附近一座老舊而簡陋的公寓裡。見到老友來訪,他興奮的喋喋不休,談美術,談文學,談音樂,還不時引吭高歌,唱些他最喜歡的民謠。
後來我們無可避免的又談起開畫展的事,他仍是一笑置之,卻是沉默下來了。
然後,他的眼光慢慢移向窗子的外面。在那裡,隔著狹窄巷子的對面,一幢新起的公寓正在施工。有的工人挑磚,有的工人砌磚,有的工人攪拌水泥,我們陪著他沉默的凝望了兩分鐘,他才回過神來,對我們綻開一抹神秘的笑容。
「我有在畫啊。」他說。
他啜著酒,喃喃說起日常的生活。每天清晨,他一定漫步到中央果菜公司,這裡走走,那裡走走,看工人卸貨,拍賣,搬運,裝菜…。
「每一種勞動者都有不同的姿勢和表情。」他說。
然後他在附近的巷弄散步,看早起的人做晨操;看醬菜車停在巷口搖鈴吆喝;看少年學生穿著齊整的制服站在公車站牌旁邊…。
「這些不都是畫嗎?」他問道。
然後他回家,坐在客廳望著對面的建築工人,看他們工作,聽他們說話,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
「我有在畫啊,」他又笑著:「畫在這裡!」他指著他的心,有點激動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觀察」。細微、深刻的觀察本是一切藝術創作的前奏,但我的畫家朋友把它視為創作的一部分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感動的傾聽他的描述,而且完全了解他的心情。最近的八、九年來,因著工作、子女等等現實責任的無可推卸,以及生活瑣碎事務的繁雜與對創作的一些自我省思,我幾已暫停發表小說創作,甚至散文也常常一年只發表兩三篇。……
我完成這篇後記時,吳耀忠已辭世半年多。在悲痛餘緒中為吳耀忠寫的悼文,其實也哀悼著我的小說寫作。
如今我必須說,這悼文並沒有完全觸及事實的核心。─當時的大環境,以及我們周邊的許多事,都還是必須遮掩的。
在我停止小說寫作的一長段時間裡,確實有很多人問起「為什麼」。那時我怎敢說「為了楊蔚」?如果說出「為了楊蔚」,就必須說起「民主台灣聯盟」案,我哪敢說出來?只能以工作、子女等理由作些不切實際的搪塞之詞。人們以為離婚之後的我已經解脫,不知楊蔚仍然階段性的,無止盡的對我恐嚇、騷擾、需索,使我一直活在憂懼與懷疑之中。這樣的日子,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停止?過這樣的日子,生命有什麼意義?對於那些碰觸生命意義的小說題材,我陷入懷疑、灰心、無力之中。小說寫作與生命意義是一體兩面,我那時的內心有一塊黑暗地帶是近乎死亡的;努力工作只是為了子女、父母、還債。偶而素描一些生活現實的散文,也只是為了安慰父親,讓他知道我還能寫作。
至於吳耀忠,我所描述的那些白日所見的生活場景,都是出自他的轉述;我與友人去他家的時間,其實是晚上十點半之後,將近午夜時刻了。
一九八三年,我從永和永利路搬到福和路,面對福和國中校園,把國小畢業的女兒從永定接回永和,方便她上學。那年年底,吳耀忠不知從哪裡打聽到我的新家電話,竟然在晚上十二點半,我下班回家剛換好衣服就接到他的電話。他沒再說「妳猜我是誰?」直接就說「我是吳耀忠啦……。」啪啦啪啦說了半個多小時,又是醺醺然的一長串囈語。綜合言之,那通電話有兩個重點。其一是他已不住三峽民權路老家,搬到長順街九十七號四樓,「就在你們中國時報後面,很近啦。」其二是他打聽到我去「人間副刊」上班的時間是下午五點,「妳可以早一點出門,先來我家兩小時,我要幫妳畫一張像……」。
他不了解我所承受的生活壓力,我也不便對他明說楊蔚之事,只能客氣的說:「對不起啦,最近比較忙,等我過一陣比較有空……。」
然而這樣的午夜電話不時響起。那時沒有「來電顯示」,我的工作也偶而會(因時差)在午夜接到美國地區的作家電話,習慣了電話一響就接起來。不管如何,我不敢抱怨「難友吳耀忠」的午夜電話,也總是耐心的聽他吟唱絮絮叨叨的「酒後心聲」。他仍然說要為我畫像,我仍然說等有空再說。如此七八次之後,他生氣了,好像用酒瓶敲著桌面,「幹,妳很驕傲耶,不讓我畫就坦白講嘛,什麼等有空再說?妳什麼時候才有空啊?算了,不給妳畫了,以後不說啦……。」
他的謾罵對象,也開始轉向了。他不再罵那些現代畫家、政工畫家,竟然罵起他的青春夥伴了:「幹伊娘駛伊娘咧,這粒大頭仔,幹,給我你丟我撿咧,你丟我撿,妳敢有了解?妳有聽人講過啦,幹伊娘大頭仔……」(他說話夾雜著國台語)
我靜靜的聽著,淚水漸漸滲出眼眶。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