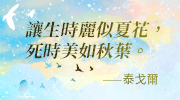人民幣定價:22 元
定價
:NT$ 132 元優惠價
:87 折 115 元
絕版無法訂購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瓜豆集》收錄周作人一九三六年五月至十二月的作品。較之此前之作,內容上有些新的成分。正如作者所說,';‘聖像破壞’與‘中庸’夾在一起';,這使我們想起他講的自己身上兼有';紳士鬼';和';流氓鬼';來。這里';關于鬼神,家庭,婦女特別是娼妓問題,都有我自己的意見在';,周氏以由性心理學建立的道德觀涵蓋男女兩性,但女性沒有社會保障,多處受害者地位,所以尤其關注這一方面,而對女性之不幸遭遇,無論是經歷上的還是心理上的,特別予以同情。
作者簡介
周作人(1885-1967),他原是水師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學者,他的工作只是打雜,砍柴打水掃地一類的工作。如關于歌謠,童話,神話,民俗的搜尋,東歐日本希臘文藝的移譯,都高興來幫一手,但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時候才行,如各門已有了專功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來,另去做掃地砍柴的勾當去了。因為無專門,所以不求學但喜歡讀雜書,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點事情而已。所讀書中于他最有影響的是英國藹里思的著作。
名人/編輯推薦
作者周作人生前親自編定,學者止庵窮數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補從未出版作品,為市場上最全面最權威的周氏文集。
目次
題記
關于雷公
談鬼論
家之上下四旁
劉香女
尾久事件
鬼怒川事件
談日本文化書
談日本文化書(其二)
懷東京
東京的書店
北平的好壞
希臘人的好學
談七月在野
常言道
常談叢錄
常談叢錄之二
藤花亭鏡譜
關于試帖
關于尺牘
關于童二樹
關于邵無恙
關于魯迅
關于魯迅書後
關于魯迅之二
自己的文章
結緣豆
談養鳥
論萬民傘
再論萬民傘
再談油炸鬼
老人的胡鬧
關于貞女
關于謔庵悔謔
附敘謔庵悔謔抄
悔謔
關于雷公
談鬼論
家之上下四旁
劉香女
尾久事件
鬼怒川事件
談日本文化書
談日本文化書(其二)
懷東京
東京的書店
北平的好壞
希臘人的好學
談七月在野
常言道
常談叢錄
常談叢錄之二
藤花亭鏡譜
關于試帖
關于尺牘
關于童二樹
關于邵無恙
關于魯迅
關于魯迅書後
關于魯迅之二
自己的文章
結緣豆
談養鳥
論萬民傘
再論萬民傘
再談油炸鬼
老人的胡鬧
關于貞女
關于謔庵悔謔
附敘謔庵悔謔抄
悔謔
書摘/試閱
題記
';寫《風雨談》忽忽已五個月,這小半年里所寫的文章并不很多,卻想作一小結束,所以從《關于雷公》起就改了一個新名目。本來可以稱作‘雷雨談’,但是氣勢未免來得太猛烈一點兒,恐怕不妥當,而且我對于中國的雷公爺實在也沒有什么好感,不想去惹動他。還是仍舊名吧,單加上‘後談’字樣。案《風雨》詩本有三章,那么這回算是瀟瀟的時候也罷,不過我所喜歡的還是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一章,那原是第三章,應該分配給‘風雨三談’去,這總須到了明年始能寫也。';
這是今年五月四日所寫,算作';風雨後談';的小引,到了現在掐指一算,半個年頭又已匆匆的過去了。這半年里所寫的文章大小總有三十篇左右,趁有一半天的閑暇,把他整理一下,編成小冊,定名曰';瓜豆集';,';後談';的名字仍保存著另有用處。為什么叫作瓜豆的呢?善于做新八股的朋友可以作種種的推測。或曰,因為喜講運命,所以這是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吧。或曰,因為愛談鬼,所以用王漁洋的詩,豆棚瓜架雨如絲。或曰,鮑照《蕪城賦》云,';竟瓜剖而豆分';,此蓋傷時也。典故雖然都不差,實在卻是一樣不對。我這瓜豆就只是老老實實的瓜豆,如冬瓜長豇豆之類是也。或者再自大一點稱曰杜園瓜豆,即杜園菜。吾鄉茹三樵著《越言釋》卷上有杜園一條云:
';杜園者兔園也,兔亦作菟,而菟故為徒音,又訛而為杜。今越人一切蔬菜瓜之屬,出自園丁,不經市兒之手,則其價較增,謂之杜園菜,以其土膏露氣真味尚存也。至于文字無出處者則又以杜園為訾,亦或簡其詞曰杜撰。昔盛文肅在館閣時,有問制詞誰撰者,文肅拱而對曰,度撰。眾皆哄堂,乃知其戲,事見宋人小說。雖不必然,亦可見此語由來已久,其謂杜撰語始于杜默者非。';土膏露氣真味尚存,這未免評語太好一點了,但不妨拿來當作理想,所謂取法乎上也。出自園丁,不經市兒之手,那自然就是杜撰,所以這并不是缺點,唯人云亦云的說市話乃是市兒所有事耳。《五代史》云:
';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換一句話說,即是鄉間塾師教村童用的書,大約是《千字文》《三字經》之類,書雖淺薄卻大有勢力,不佞豈敢望哉。總之茹君所說的話都是很好的,借來題在我這小冊子的卷頭,實在再也好不過,就只怕太好而已。
這三十篇小文重閱一過,自己不禁嘆息道,太積極了!聖像破壞(iconoclasma)與中庸(sophrosune),夾在一起,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為我早該談風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談了罷,要談風月了吧!?好像';狂言';里的某一腳色所說,生怕不談就有點違犯了公式。其實我自己也未嘗不想談,不料總是不夠消極,在風吹月照之中還是要呵佛罵祖,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無可如何。或者懷疑我罵韓愈是考古,說鬼是消閑,這也未始不是一種看法,但不瞞老兄說,這實在只是一點師爺筆法紳士態度,原來是與對了和尚罵禿驢沒有多大的不同,蓋我覺得現代新人物里不免有易卜生的';群鬼';,而讀經衛道的朋友差不多就是韓文公的伙計也。昔者黨進不許說書人在他面前講韓信,不失為聰明人,他未必真怕說書人到韓信跟前去講他,實在是怕說的韓信就是他耳。不佞生性不喜八股與舊戲,所不喜者不但是其物而尤在其勢力,若或聞不佞謾罵以為專與《能與集》及小丑的白鼻子為仇,則其智力又未免出黨太尉下矣。
孔子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在莊子看來恐怕只是小知,但是我也覺得夠好了,先從不知下手,凡是自己覺得不大有把握的事物決心不談,這樣就除去了好些絆腳的荊棘,讓我可以自由的行動,只挑選一二稍為知道的東西來談談。其實我所知的有什么呢,自己也說不上來,不過比較起來對于某種事物特別有興趣,特別想要多知道一點,這就不妨權歸入可以談談的方面,雖然所知有限,總略勝于以不知為知耳。我的興趣所在是關于生物學人類學兒童學與性的心理,當然是零碎的知識,但是我唯一的一點知識,所以自己不能不相當的看重,而自己所不知的乃是神學與文學的空論之類。我嘗自己發笑,難道真是從';妖精打架';會悟了道么?道未必悟,卻總幫助了我去了解好許多問題與事情。從這邊看過去,神聖的東西難免失了他們的光輝,自然有聖像破壞之嫌,但同時又是贊美中庸的,因為在性的生活上禁欲與縱欲是同樣的過失,如英國藹理斯所說,';生活之藝術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與舍二者而已。';凡此本皆細事不足道,但為欲說我的意見何以多與新舊權威相沖突,如此喋喋亦不得已。我平常寫文章喜簡略或隱約其詞,而老實人見之或被貽誤,近來思想漸就統制,慮能自由讀書者將更少矣,特于篇末寫此兩節,實屬破例也。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著者自記于北平知堂。
談鬼論
三年前我偶然寫了兩首打油詩,有一聯云,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有些老實的朋友見之嘩然,以為此刻現在不去奉令喝道,卻來談鬼的故事,豈非沒落之尤乎。這話說的似乎也有幾分道理,可是也不能算對。蓋詩原非招供,而敝詩又是打油詩也,滑稽之言,不能用了單純的頭腦去求解釋。所謂鬼者焉知不是鬼話,所謂蛇者或者乃是蛇足,都可以講得過去,若一一如字直說,那么真是一天十二小時站在十字街頭聽《聊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坐在南窗下臨《十七帖》,這種解釋難免為姚首源所評為癡叔矣。據《東坡事類》卷十三神鬼類引《癸辛雜識》序云: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聞者絕倒。';說者以為東坡晚年厭聞時事,強人說鬼,以鬼自晦者也。東坡的這件故事很有意思,是否以鬼自晦,覺得也頗難說,但是我并無此意則是自己最為清楚的。雖然打油詩的未必即是東坡客之所說,雖然我亦未必如東坡之厭聞時事,但假如問是不是究竟喜歡聽人說鬼呢,那么我答應說,是的。人家如要罵我應該從現在罵起,因為我是明白的說出了,以前關于打油詩的話乃是真的或假的看不懂詩句之故也。
話雖如此,其實我是與鬼不大有什么情分的。遼陽劉青園著《常談》卷一中有一則云:
';鬼神奇跡不止匹夫匹婦言之鑿鑿,士紳亦嘗及之。唯余風塵斯世未能一見,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為惡,故無鬼物侵陵,德不足以為善,亦無神靈呵護。平庸坦率,無所短長,眼界固宜如此。';金李登齋著《常談叢錄》卷六有性不見鬼一則云:
';予生平未嘗見鬼形,亦未嘗聞鬼聲,殆氣稟不近于陰耶。記少時偕族人某宿鵝塘楊甥家祠堂內,兩室相對,晨起某蹙然曰,昨夜鬼叫嗚嗚不已,聲長而亮,甚可畏。予謂是夜行者戲作呼嘯耳,某曰,略不似人聲,烏有寒夜更深奔走正苦而歡娛如是者,必鬼也。予終不信。越數日予甥楊集益秀才夫婦皆以暴病相繼歿,是某所聞者果為世所傳勾攝之走無常耶。然予與同堂隔室宿,殊不聞也。郡城內廣壽寺前左有大宅,李玉漁庶子傳熊故居也,相傳其中多鬼,予嘗館寓于此,絕無所聞見。一日李拔生太學偕客來同宿東房,晨起言夜聞鬼叫如鴨,聲在壁後呀呷不已,客亦謂中夜拔生以足蹴使醒,聽之果有聲,擁被起坐,靜察之,非蟲非鳥,確是鬼鳴。然予亦與之同堂隔室宿,竟寂然不聞,詢諸生徒六七人,悉無聞者,用是亦不深信。拔生因述往歲曾以訟事寓此者半年,每至交夜則後堂啼叫聲,或如人行步聲,器物門壁震響聲,無夕不有,甚或若狂恣猖披幾難言狀。然予居此兩載,迄無聞見,且連年夏中俱病甚,恒不安寐,宵深每強出臥堂中炕座上,視廣庭月色將盡升檐際,乃復歸室,其時旁無一人,亦竟毫無影響。諸小說家所稱鬼物雖同地同時而聞見各異者甚多,豈不有所以異者耶。若予之強頑,或鬼亦不欲與相接于耳目耶。不近陰之說尚未必其的然也。';李書有道光二十八年序,劉書記有道光十八年事,蓋時代相同,書名又均稱常談,其不見鬼的性格也相似,可謂巧合。予生也晚,晚于劉李二君總將一百年吧,而秉性愚拙,不能活見鬼,因得附驥尾而成鼎足,殊為光榮之至。小時候讀《聊齋》等志異書,特別是《夜談隨錄》的影響最大,後來腦子里永遠留下了一塊恐怖的黑影,但是我是相信神滅論的,也沒有領教過鬼的尊容或其玉音,所以鬼之于我可以說是完全無緣的了。—聽說十王殿上有一塊匾,文曰,';你也來了!';這個我想是對那怙惡不悛的人說的。紀曉嵐著《灤陽消夏錄》卷四有一條云:
';邊隨園征君言,有入冥者,見一老儒立廡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與寒溫畢,拱手對之笑曰,先生平日持無鬼論,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諸鬼皆粲然,老儒?縮而已。';《閱微草堂筆記》多設詞嘲笑老儒或道學家,頗多快意,此亦其一例,唯因不喜程朱而并惡無鬼論原是講不通,于不佞自更無關系,蓋不佞非老儒之比,即是死後也總不會變鬼者也。
這樣說來,我之與鬼沒有什么情分是很顯然的了,那么大可干脆分手了事。不過情分雖然沒有,興趣卻是有的,所以不信鬼而仍無妨喜說鬼,我覺得這不是不合理的事。我對于鬼的故事有兩種立場不同的愛好。一是文藝的,一是歷史的。關于第一點,我所要求的是一篇好故事,意思并不要十分新奇,結構也無須怎么復雜,可是文章要寫得好,簡潔而有力。其內容本來并不以鬼為限,自宇宙以至蒼蠅都可以,而鬼自然也就是其中之一。其體裁是,我覺得志怪比傳奇為佳,舉個例來說,與其取《聊齋志異》的長篇還不如《閱微草堂筆記》的小文,只可惜這里也絕少可以中選的文章,因為里邊如有了世道人心的用意,在我便當作是值得紅勒帛的一個大瑕疵了。四十年前讀段柯古的《酉陽雜俎》,心甚喜之,至今不變,段君誠不愧為三十六之一,所寫散文多可讀。《諾皋記》卷中有一則云: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初買宅于館娃坊,暇日與弟閑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不知所為。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鏊形,乃火上沃醯,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入坑,投于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亦隨出。才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至死不肯言其情狀。';此外如舉人孟不疑,獨孤叔牙,虞侯景乙,宣平坊賣油人各條,亦均有意趣。蓋古人志怪即以此為目的,後人即以此為手段,優劣之分即見于此,雖文詞美富,敘述曲折,勉為時世小說面目,亦無益也。其實宗旨信仰在古人似亦無礙于事,如佛經中不乏可喜的故事短文,近讀梁寶唱和尚所編《經律異相》五十卷,常作是想,後之作者氣度淺陋,便難追及,只緣面目可憎,以致語言亦復無味,不然單以文字論則此輩士大夫豈不綽綽然有余裕哉。
第二所謂歷史的,再明了的說即是民俗學上的興味。關于這一點我曾經說及幾次,如在《河水鬼》,《鬼的生長》,《說鬼》諸文中,都講過一點兒。《鬼的生長》中云:
';我不信鬼,而喜歡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雖然,我不信人死為鬼,卻相信鬼後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氣之良能,但鬼為生人喜懼愿望之投影則當不謬也。陶公千古曠達人,其《歸園田居》云,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神釋》云,應盡便須盡,無復更多慮。在《擬挽歌辭》中則云,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陶公于生死豈尚有迷戀,其如此說于文詞上固亦大有情致,但以生前的感覺推想死後況味,正亦人情之常,出于自然者也。常人更執著于生存,對于自己及所親之翳然而滅,不能信亦不愿信其滅也,故種種設想,以為必繼續存在,其存在之狀況則因人民地方以至各自的好惡而稍稍殊異,無所作為而自然流露,我們聽人說鬼實即等于聽其談心矣。';(廿三年四月)這是因讀《望杏樓志痛編補》而寫的,故就所親立論,原始的鬼的思想之起原當然不全如此,蓋由于恐怖者多而情意為少也。又在《說鬼》(廿四年十一月)中云:
';我們喜歡知道鬼的情狀與生活,從文獻從風俗上各方面去搜求,為的可以了解一點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換句話說就是為了鬼里邊的人。反過來說,則人間的鬼怪伎倆也值得注意,為的可以認識人里邊的鬼吧。我的打油詩云,街頭終日聽談鬼,大為志士所訶,我卻總是不管,覺得那鬼是怪有趣的物事,舍不得不談,不過詩中所談的是那一種,現在且不必說。至于上邊所講的顯然是老牌的鬼,其研究屬于民俗學的范圍,不是講玩笑的事,我想假如有人決心去作‘死後的生活’的研究,實是學術界上破天荒的工作,很值得稱贊的。英國來則博士(J. G. Frazer)有一部大書專述各民族對于死者之恐怖,現在如只以中國為限,卻將鬼的生活詳細地寫出,雖然是極浩繁困難的工作,值得當博士學位的論文,但亦極有趣味與實益,蓋此等處反可以見中國民族的真心實意,比空口叫喊固有道德如何的好還要可憑信也。';照這樣去看,那么凡一切關于鬼的無不是好資料,即上邊被罵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的那些亦都在內,別無好處可取,而說者的心思畢露,所謂如見其肺肝然也。此事當然需要專門的整理,我們外行人隨喜涉獵,略就小事項少材料加以參證,稍見異同,亦是有意思的事。如眼能見鬼者所說,俞少軒的《高辛硯齋雜著》第五則云:
';黃鐵如者名楷,能文,善視鬼,并知鬼事。據云,每至人家,見其鬼香灰色則平安無事,如有將落之家,則鬼多淡黃色。又云,鬼長不過二尺余,如鬼能修善則日長,可與人等,或為淫厲,漸短漸滅,至有僅存二眼旋轉地上者。亦奇矣。';王小的《重論文齋筆錄》卷二中有數則云:
';曾記族樸存兄淳言,(兄眼能見鬼,凡黑夜往來俱不用燈。)凡鬼皆依附墻壁而行,不能破空,疫鬼亦然,每遇墻壁必如蚓卻行而後能入。常鬼如一團黑氣,不辨面目,其有面目而能破空者則是厲鬼,須急避之。';
';兄又言,鬼最畏風,遇風則牢握草木蹲伏不敢動。';
';兄又云,《左傳》言故鬼小新鬼大,其說確不可易,至溺死之鬼則新小而故大,其鬼亦能登岸,逼視之如煙云消滅者,此新鬼也。故鬼形如槁木,見人則躍入水中,水有聲而不散,故無圓暈。';紀曉嵐的《灤陽銷夏錄》卷二云:
';揚州羅兩峰目能視鬼,曰凡有人處皆有鬼。其橫亡厲鬼多年沉滯者率在幽房空宅中,是不可近,近則為害。其憧憧往來之鬼,午前陽盛多在墻陰,午後陰盛則四散游行,可穿壁而過,不由門戶,遇人則避路,畏陽氣也,是隨處有之,不為害。又曰,鬼所聚集恒在人煙密簇處,僻地曠野所見殊希。喜圍繞廚灶,似欲近食氣,又喜入溷廁,則莫明其故,或取人跡罕到耶。';羅兩峰是袁子才的門人,想隨園著作中必有說及其能見鬼事,今不及翻檢,但就上文所引也可見一斑了。其所說有異同處最是好玩,蓋說者大抵是讀書人,所依據的與其說是所見無寧是其所信,這就是一種理,因為鬼總是陰氣,所以甲派如王樸存說鬼每遇墻壁必如蚓卻行而後能入,蓋以其為陰,而乙派如羅兩峰則云鬼可穿壁而過,殆以其為氣也。其相同之點轉覺無甚意思,殆因說理一致,或出于因襲,亦未可知。如紀曉嵐的《如是我聞》卷三記柯禺峰遇鬼事,有云:
';睡至夜半,聞東室有聲如鴨鳴,怪而諦視。時明月滿窗,見黑煙一道從東室門隙出,著地而行,長丈余,蜿蜒如巨蟒,其首乃一女子,鬟鬢儼然,昂首仰視,盤旋地上,作鴨鳴不止。';又《槐西雜志》卷四記一奴子婦為狐所媚,每來必換一形,歲余無一重復者,末云:
';其尤怪者,婦小姑偶入其室,突遇狐出,一躍即逝。小姑所見是方巾道袍人,白須,婦所見則黯黑垢膩一賣煤人耳。同時異狀,更不可思議。';此兩節與《常談叢錄》所說李拔生夜聞鬼叫如鴨,又鬼物同時同地而聞見各異語均相合,則恐是雷同,當是說鬼的傳統之一點滴,但在研究者卻殊有價值耳。羅兩峰所畫《鬼趣圖》很有名,近年有正書局有復印本,得以一見,乃所見不逮所聞遠甚。圖才八幅,而名人題詠有八十通,可謂巨觀,其實圖也不過是普通的文人畫罷了,較《玉歷鈔傳》稍少匠氣,其鬼味與諧趣蓋猶不及吾鄉的大戲與目連戲,倘說此是目擊者的描寫,則鬼世界之繁華不及人間多多矣。—這回論語社發刊鬼的故事專號,不遠千里征文及于不佞,重違尊命,勉寫小文,略述談鬼的淺見,重讀一過,缺乏鬼味諧趣,比羅君尤甚,既無補于鬼學,亦不足以充鬼話,而猶妄評昔賢,豈不將為九泉之下所抵掌大笑耶。廿五年六月十一日,于北平之智堂。
家之上下四旁
《論語》這一次所出的課題是';家';,我也是考生之一,見了不禁著急,不怨自己的肚子空虛得很,只恨考官促狹,出這樣難題目來難人。的確這比前回的';鬼';要難做得多了,因為鬼是與我們沒有關系的,雖然普通總說人死為鬼,我卻不相信自己會得變鬼,將來有朝一日即使死了也總不想到鬼門關里去,所以隨意談論談論也還無妨。若是家,那是人人都有的,除非是不打誑話的出家人,這種人現在大約也是絕無僅有了,現代的和尚熱心于國大選舉,比我們還要積極,如我所認識的紹興阿毛師父自述,他們的家也比我們為多,即有父家妻家與寺家三者是也。總而言之,無論在家出家,總離不開家,那么家之與我們可以說是關系深極了,因為關系如此之深,所以要談就不大容易。賦得家是個難題,我在這里就無妨堅決地把他宣布了。
話雖如此,既然接了這個題目,總不能交白卷了事,無論如何須得做他一做才行。忽然記起張宗子的一篇《岱志》來,第一節中有云:
';故余之志岱,非志岱也。木華作《海賦》,曰,胡不于海之上下四旁言之。余不能言岱,亦言岱之上下四旁已耳。';但是抄了之後,又想道,且住,家之上下四旁有可說的么?我一時也回答不來。忽然又拿起剛從地攤買來的一本《醒閨編》來看,這是二十篇訓女的韻文,每行分三三七共三句十三字,題曰西園廖免驕編。首篇第三葉上有這幾行云:
犯小事,由你說,倘犯忤逆推不脫。
有碑文,你未見,湖北有個漢川縣。
鄧漢真,是秀才,配妻黃氏惡如豺。
打婆婆,報了官,事出乾隆五十三。
將夫婦,問剮罪,拖累左鄰與右舍。
那鄰里,最慘傷,先打後充黑龍江。
那族長,伯叔兄,有問絞來有問充。
後家娘,留省城,當面刺字充四門。
那學官,革了職,流徙三千杖六十。
坐的土,掘三尺,永不準人再筑室。
將夫婦,解回城,凌遲碎剮曉諭人。
命總督,刻碑文,後有不孝照樣行。
我再翻看前後,果然在卷首看見';遵錄湖北碑文';,文云: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奉上諭:朕以孝治天下,海山陬無不一道同風。據湖北總督疏稱漢川縣生員鄧漢禎之妻黃氏以辱母毆姑一案,朕思不孝之罪別無可加,唯有剝皮示眾。左右鄰舍隱匿不報,律杖八十,烏龍江充軍。族長伯叔兄等不教訓子侄,亦議絞罪。教官并不訓誨,杖六十,流徙三千里。知縣知府不知究治,罷職為民,子孫永不許入仕。黃氏之母當面刺字,留省四門充軍。漢禎之家掘土三尺,永不許居住。漢禎之母仰湖北布政使司每月給米銀二兩,仍將漢禎夫婦發回漢川縣對母剝皮示眾。仰湖北總督嚴刻碑文,曉諭天下,後有不孝之徒,照漢禎夫婦治罪。';我看了這篇碑文,立刻發生好幾個感想。第一是看見';朕以孝治天下';這一句,心想這不是家之上下四旁么,找到了可談的材料了。第二是不知道這碑在那里,還存在么,可惜弄不到拓本來一看。第三是發生';一丁點兒';的懷疑。這碑文是真的么?我沒有工夫去查官書,證實這漢川縣的忤逆案,只就文字上說,就有許多破綻。十全老人的漢文的確有欠亨的地方,但這種諭旨既已寫了五十多年,也總不至于還寫得不合格式。我們難保皇帝不要剝人家的皮,在清初也確實有過,但乾隆時有這事么,有點將信將疑。看文章很有點像是老學究的手筆,雖然老學究不見得敢于假造上諭,—這種事情直到光緒末革命黨才會做出來,而且文句也仍舊造得不妥貼。但是無論如何,或乾隆五十三年真有此事,或是出于士大夫的捏造,都是同樣的有價值,總之足以證明社會上有此種意思,即不孝應剝皮是也。從前翻閱阮云臺的《廣陵詩事》,在卷九有談逆婦變豬的一則云:
';寶應成安若康保《皖游集》載,太平寺中一豕現婦人足,弓樣宛然,(案,此實乃婦人現豕足耳。)同游詫為異,余笑而解之曰,此必妒婦後身也,人彘之冤今得平反矣,因成一律,以‘偶見’命題云。憶元幼時聞林庾泉云,曾見某處一婦不孝其姑遭雷擊,身變為彘,唯頭為人,後腳猶弓樣焉,越年余復為雷殛死。始意為不經之談,今見安若此詩,覺天地之大事變之奇,真難于恒情度也。惜安若不向寺僧究其故而書之。';阮君本非俗物,于考據詞章之學也有成就,今記錄此等惡濫故事,未免可笑,我抄了下來,當作確實材料,用以證此種思想之普遍,無雅俗之分也。翻個轉面就是勸孝,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二十四孝圖說》。這里邊固然也有比較容易辦的,如扇枕席之類,不過大抵都很難,例如喂蚊子,有些又難得有機會,一定要湊巧冬天生病,才可以去找尋魚或筍,否則終是徒然。最成問題的是郭巨埋兒掘得黃金一釜,這件事古今有人懷疑。偶看尺牘,見朱蔭培著《蕓香閣尺一書》(道光年刊)卷二有致顧仲懿書云:
';所論岳武穆何不直搗黃龍,再請違旨之罪,知非正論,姑作快論,得足下引《春秋》大義辨之,所謂天王明聖臣罪當誅,純臣之心惟知有君也。前春原嵇丈評弟郭巨埋兒辨云,惟其愚之至,是以孝之至,事異論同,皆可補蕓香一時妄論之失。';以我看來,顧嵇二公同是妄論,純是道學家不講情理的門面話,但在社會上卻極有勢力,所以這就不妨說是中國的輿論,其主張與朕以孝治天下蓋全是一致。從這勸與戒兩方面看來,孝為百行先的教條那是確實無疑的了。
現在的問題是,這在近代的家庭中如何實行?老實說,仿造的二十四孝早已不見得有,近來是資本主義的時代,神道不再管事,奇跡難得出現,沒有紙票休想得到筍和魚,世上一切都已平凡現實化了。太史公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也。這就明白的說明盡孝的難處。對于孝這個字想要說點閑話,實在很不容易。中國平常通稱忠孝節義,四者之中只有義還可以商量,其他三德分屬三綱,都是既得權利,不容妄言有所侵犯。昔者,施存統著《非孝》,而陳仲甫頂了缸,至今讀經尊孔的朋友猶津津樂道,謂其曾發表萬惡孝為首的格言,而林琴南孝廉又拉了孔北海的話來胡纏,其實《獨秀文存》具在,中間原無此言也。我寫到這里殊不能無戒心,但展側一想,余行年五十有幾矣,如依照中國早婚的習慣,已可以有曾孫矣,余不敏今僅以父親的資格論孝,雖固不及曾祖之闊氣,但資格則已有了矣。以余觀之,現代的兒子對于我們殊可不必再盡孝,何也,蓋生活艱難,兒子們第一要維持其生活于出學校之後,上有對于國家的義務,下有對于子女的責任,如要衣食飽暖,成為一個賢父良夫好公民,已大須努力,或已力有不及,若更欲彩衣弄雛,鼎烹進食,勢非貽誤公務虧空公款不可,一朝捉將官里去,豈非飲鴆止渴,為之老太爺老太太者亦有何快樂耶。鄙意父母養育子女實止是還自然之債。此意與英語中所有者不同,須引《笑林》疏通證明之。有人見友急忙奔走,問何事匆忙,答云,二十年前欠下一筆債。即日須償。再問何債,曰,實是小女明日出嫁。此是笑話,卻非戲語。男子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即此意也。自然無言,生物的行為乃其代言也,人雖靈長亦自不能出此民法外耳。債務既了而情誼長存,此在生物亦有之,而于人為特顯著,斯其所以為靈長也歟。我想五倫中以朋友之義為最高,母子男女的關系所以由本能而進于倫理者,豈不以此故乎。有富人父子不和,子甚倔強,父乃語之曰,他事即不論,爾我共處二十余年,亦是老朋友了,何必再鬧意氣。此事雖然滑稽,此語卻很有意思。我便希望兒子們對于父母以最老的老朋友相處耳,不必再長跪請老太太加餐或受訓誡,但相見怡怡,不至于疾言厲色,便已大佳。這本不是石破天驚的什么新發明,世上有些國土也就是這樣做著,不過中國不承認,因為他是喜唱高調的。凡唱高調的亦并不能行低調,那是一定的道理。吾鄉民間有目連戲,本是宗教劇而富于滑稽的插話,遂成為真正的老百姓的喜劇,其中有';張蠻打爹';一段,蠻爹對眾說白有云:
';現在真不成世界了,從前我打爹的時候爹逃就算了,現在我逃了他還要追著打哩。';這就是老百姓的';犯話';,所謂犯話者蓋即經驗之談,從事實中';犯';出來的格言,其精銳而討人嫌處不下于李耳與伊索,因為他往往不留情面的把政教道德的西洋鏡戳穿也。在士大夫家中,案頭放著《二十四孝》和《太上感應篇》,父親乃由暴君降級欲求為老朋友而不可得,此等事數見不鮮,亦不復諱,亦無可諱,恰似理論與事實原是二重真理可以并存也者,不佞非讀經尊孔人卻也聞之駭然,但亦不無所得,現代的父子關系以老朋友為極則,此項發明實即在那時候所得到者也。
上邊所說的一番話,看似平常,實在我也是很替老年人打算的。父母少壯時能夠自己照顧,而且他們那時還要照顧子女呢,所以不成什么問題。成問題的是在老年,這不但是衣食等事,重要的還是老年的孤獨。兒子闊了有名了,往往在書桌上留下一部《百孝圖說》,給老人家消遣,自己率領寵妾到洋場官場里為國民謀幸福去了。假如那老頭子是個希有的明達人,那么這倒也還沒有什么。如曹庭棟在《老老恒言》卷二中所說:
';世情世態,閱歷久看應爛熟,心衰面改,老更奚求。諺曰,求人不如求己。呼牛呼馬,亦可由人,毋少介意。少介意便生忿,忿便傷肝,于人何損,徒損乎己耳。
少年熱鬧之場非其類則弗親,茍不見幾知退,取憎而已。至與二三老友相對閑談,偶聞世事,不必論是非,不必較長短,慎爾出話,亦所以定心氣。';又沈赤然著《寒夜叢談》卷一有一則云:
';膝前林立,可喜也,雖不能必其皆賢,必其皆壽也。金錢山積,可喜也,然營田宅勞我心,籌婚嫁勞我心,防盜賊水火又勞我心矣。黃發臺背,可喜也,然心則健忘,耳則重聽,舉動則須扶持,有不為子孫厭之,奴婢欺之,外人侮之者乎。故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如能像二君的達觀,那么一切事都好辦,可惜千百人中不能得一,所以這就成為問題。社會上既然尚無國立養老院,本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對于已替社會做過相當工作的老年加以收養,衣食住藥以至娛樂都充分供給,則自不能不托付于老朋友矣,—這里不說子孫而必戲稱老朋友者,非戲也,以言子孫似專重義務,朋友則重在情感,而養老又以銷除其老年的孤獨為要,唯用老朋友法可以做到,即古之養志也。雖然,不佞不續編《二十四孝》,而實際上這老朋友的孝亦大不容易,恐怕終亦不免為一種理想,不違反人情物理,不壓迫青年,亦不委屈老年,頗合于中庸之道,比皇帝與道學家的意見要好得多了,而實現之難或與二十四孝不相上下,亦未可知。何也?蓋中國家族關系唯以名分,以利害,而不以情義相維系也,亦已久矣。聞昔有龔橙自號半倫,以其只有一妾也,中國家庭之情形何如固然一言難盡,但其不為龔君所笑者殆幾希矣。家之上下四旁如只有半倫,欲求朋友于父子之間又豈可得了。
......;
';寫《風雨談》忽忽已五個月,這小半年里所寫的文章并不很多,卻想作一小結束,所以從《關于雷公》起就改了一個新名目。本來可以稱作‘雷雨談’,但是氣勢未免來得太猛烈一點兒,恐怕不妥當,而且我對于中國的雷公爺實在也沒有什么好感,不想去惹動他。還是仍舊名吧,單加上‘後談’字樣。案《風雨》詩本有三章,那么這回算是瀟瀟的時候也罷,不過我所喜歡的還是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一章,那原是第三章,應該分配給‘風雨三談’去,這總須到了明年始能寫也。';
這是今年五月四日所寫,算作';風雨後談';的小引,到了現在掐指一算,半個年頭又已匆匆的過去了。這半年里所寫的文章大小總有三十篇左右,趁有一半天的閑暇,把他整理一下,編成小冊,定名曰';瓜豆集';,';後談';的名字仍保存著另有用處。為什么叫作瓜豆的呢?善于做新八股的朋友可以作種種的推測。或曰,因為喜講運命,所以這是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吧。或曰,因為愛談鬼,所以用王漁洋的詩,豆棚瓜架雨如絲。或曰,鮑照《蕪城賦》云,';竟瓜剖而豆分';,此蓋傷時也。典故雖然都不差,實在卻是一樣不對。我這瓜豆就只是老老實實的瓜豆,如冬瓜長豇豆之類是也。或者再自大一點稱曰杜園瓜豆,即杜園菜。吾鄉茹三樵著《越言釋》卷上有杜園一條云:
';杜園者兔園也,兔亦作菟,而菟故為徒音,又訛而為杜。今越人一切蔬菜瓜之屬,出自園丁,不經市兒之手,則其價較增,謂之杜園菜,以其土膏露氣真味尚存也。至于文字無出處者則又以杜園為訾,亦或簡其詞曰杜撰。昔盛文肅在館閣時,有問制詞誰撰者,文肅拱而對曰,度撰。眾皆哄堂,乃知其戲,事見宋人小說。雖不必然,亦可見此語由來已久,其謂杜撰語始于杜默者非。';土膏露氣真味尚存,這未免評語太好一點了,但不妨拿來當作理想,所謂取法乎上也。出自園丁,不經市兒之手,那自然就是杜撰,所以這并不是缺點,唯人云亦云的說市話乃是市兒所有事耳。《五代史》云:
';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換一句話說,即是鄉間塾師教村童用的書,大約是《千字文》《三字經》之類,書雖淺薄卻大有勢力,不佞豈敢望哉。總之茹君所說的話都是很好的,借來題在我這小冊子的卷頭,實在再也好不過,就只怕太好而已。
這三十篇小文重閱一過,自己不禁嘆息道,太積極了!聖像破壞(iconoclasma)與中庸(sophrosune),夾在一起,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為我早該談風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談了罷,要談風月了吧!?好像';狂言';里的某一腳色所說,生怕不談就有點違犯了公式。其實我自己也未嘗不想談,不料總是不夠消極,在風吹月照之中還是要呵佛罵祖,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無可如何。或者懷疑我罵韓愈是考古,說鬼是消閑,這也未始不是一種看法,但不瞞老兄說,這實在只是一點師爺筆法紳士態度,原來是與對了和尚罵禿驢沒有多大的不同,蓋我覺得現代新人物里不免有易卜生的';群鬼';,而讀經衛道的朋友差不多就是韓文公的伙計也。昔者黨進不許說書人在他面前講韓信,不失為聰明人,他未必真怕說書人到韓信跟前去講他,實在是怕說的韓信就是他耳。不佞生性不喜八股與舊戲,所不喜者不但是其物而尤在其勢力,若或聞不佞謾罵以為專與《能與集》及小丑的白鼻子為仇,則其智力又未免出黨太尉下矣。
孔子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在莊子看來恐怕只是小知,但是我也覺得夠好了,先從不知下手,凡是自己覺得不大有把握的事物決心不談,這樣就除去了好些絆腳的荊棘,讓我可以自由的行動,只挑選一二稍為知道的東西來談談。其實我所知的有什么呢,自己也說不上來,不過比較起來對于某種事物特別有興趣,特別想要多知道一點,這就不妨權歸入可以談談的方面,雖然所知有限,總略勝于以不知為知耳。我的興趣所在是關于生物學人類學兒童學與性的心理,當然是零碎的知識,但是我唯一的一點知識,所以自己不能不相當的看重,而自己所不知的乃是神學與文學的空論之類。我嘗自己發笑,難道真是從';妖精打架';會悟了道么?道未必悟,卻總幫助了我去了解好許多問題與事情。從這邊看過去,神聖的東西難免失了他們的光輝,自然有聖像破壞之嫌,但同時又是贊美中庸的,因為在性的生活上禁欲與縱欲是同樣的過失,如英國藹理斯所說,';生活之藝術其方法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與舍二者而已。';凡此本皆細事不足道,但為欲說我的意見何以多與新舊權威相沖突,如此喋喋亦不得已。我平常寫文章喜簡略或隱約其詞,而老實人見之或被貽誤,近來思想漸就統制,慮能自由讀書者將更少矣,特于篇末寫此兩節,實屬破例也。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著者自記于北平知堂。
談鬼論
三年前我偶然寫了兩首打油詩,有一聯云,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有些老實的朋友見之嘩然,以為此刻現在不去奉令喝道,卻來談鬼的故事,豈非沒落之尤乎。這話說的似乎也有幾分道理,可是也不能算對。蓋詩原非招供,而敝詩又是打油詩也,滑稽之言,不能用了單純的頭腦去求解釋。所謂鬼者焉知不是鬼話,所謂蛇者或者乃是蛇足,都可以講得過去,若一一如字直說,那么真是一天十二小時站在十字街頭聽《聊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坐在南窗下臨《十七帖》,這種解釋難免為姚首源所評為癡叔矣。據《東坡事類》卷十三神鬼類引《癸辛雜識》序云: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聞者絕倒。';說者以為東坡晚年厭聞時事,強人說鬼,以鬼自晦者也。東坡的這件故事很有意思,是否以鬼自晦,覺得也頗難說,但是我并無此意則是自己最為清楚的。雖然打油詩的未必即是東坡客之所說,雖然我亦未必如東坡之厭聞時事,但假如問是不是究竟喜歡聽人說鬼呢,那么我答應說,是的。人家如要罵我應該從現在罵起,因為我是明白的說出了,以前關于打油詩的話乃是真的或假的看不懂詩句之故也。
話雖如此,其實我是與鬼不大有什么情分的。遼陽劉青園著《常談》卷一中有一則云:
';鬼神奇跡不止匹夫匹婦言之鑿鑿,士紳亦嘗及之。唯余風塵斯世未能一見,殊不可解。或因才不足以為惡,故無鬼物侵陵,德不足以為善,亦無神靈呵護。平庸坦率,無所短長,眼界固宜如此。';金李登齋著《常談叢錄》卷六有性不見鬼一則云:
';予生平未嘗見鬼形,亦未嘗聞鬼聲,殆氣稟不近于陰耶。記少時偕族人某宿鵝塘楊甥家祠堂內,兩室相對,晨起某蹙然曰,昨夜鬼叫嗚嗚不已,聲長而亮,甚可畏。予謂是夜行者戲作呼嘯耳,某曰,略不似人聲,烏有寒夜更深奔走正苦而歡娛如是者,必鬼也。予終不信。越數日予甥楊集益秀才夫婦皆以暴病相繼歿,是某所聞者果為世所傳勾攝之走無常耶。然予與同堂隔室宿,殊不聞也。郡城內廣壽寺前左有大宅,李玉漁庶子傳熊故居也,相傳其中多鬼,予嘗館寓于此,絕無所聞見。一日李拔生太學偕客來同宿東房,晨起言夜聞鬼叫如鴨,聲在壁後呀呷不已,客亦謂中夜拔生以足蹴使醒,聽之果有聲,擁被起坐,靜察之,非蟲非鳥,確是鬼鳴。然予亦與之同堂隔室宿,竟寂然不聞,詢諸生徒六七人,悉無聞者,用是亦不深信。拔生因述往歲曾以訟事寓此者半年,每至交夜則後堂啼叫聲,或如人行步聲,器物門壁震響聲,無夕不有,甚或若狂恣猖披幾難言狀。然予居此兩載,迄無聞見,且連年夏中俱病甚,恒不安寐,宵深每強出臥堂中炕座上,視廣庭月色將盡升檐際,乃復歸室,其時旁無一人,亦竟毫無影響。諸小說家所稱鬼物雖同地同時而聞見各異者甚多,豈不有所以異者耶。若予之強頑,或鬼亦不欲與相接于耳目耶。不近陰之說尚未必其的然也。';李書有道光二十八年序,劉書記有道光十八年事,蓋時代相同,書名又均稱常談,其不見鬼的性格也相似,可謂巧合。予生也晚,晚于劉李二君總將一百年吧,而秉性愚拙,不能活見鬼,因得附驥尾而成鼎足,殊為光榮之至。小時候讀《聊齋》等志異書,特別是《夜談隨錄》的影響最大,後來腦子里永遠留下了一塊恐怖的黑影,但是我是相信神滅論的,也沒有領教過鬼的尊容或其玉音,所以鬼之于我可以說是完全無緣的了。—聽說十王殿上有一塊匾,文曰,';你也來了!';這個我想是對那怙惡不悛的人說的。紀曉嵐著《灤陽消夏錄》卷四有一條云:
';邊隨園征君言,有入冥者,見一老儒立廡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與寒溫畢,拱手對之笑曰,先生平日持無鬼論,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諸鬼皆粲然,老儒?縮而已。';《閱微草堂筆記》多設詞嘲笑老儒或道學家,頗多快意,此亦其一例,唯因不喜程朱而并惡無鬼論原是講不通,于不佞自更無關系,蓋不佞非老儒之比,即是死後也總不會變鬼者也。
這樣說來,我之與鬼沒有什么情分是很顯然的了,那么大可干脆分手了事。不過情分雖然沒有,興趣卻是有的,所以不信鬼而仍無妨喜說鬼,我覺得這不是不合理的事。我對于鬼的故事有兩種立場不同的愛好。一是文藝的,一是歷史的。關于第一點,我所要求的是一篇好故事,意思并不要十分新奇,結構也無須怎么復雜,可是文章要寫得好,簡潔而有力。其內容本來并不以鬼為限,自宇宙以至蒼蠅都可以,而鬼自然也就是其中之一。其體裁是,我覺得志怪比傳奇為佳,舉個例來說,與其取《聊齋志異》的長篇還不如《閱微草堂筆記》的小文,只可惜這里也絕少可以中選的文章,因為里邊如有了世道人心的用意,在我便當作是值得紅勒帛的一個大瑕疵了。四十年前讀段柯古的《酉陽雜俎》,心甚喜之,至今不變,段君誠不愧為三十六之一,所寫散文多可讀。《諾皋記》卷中有一則云: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初買宅于館娃坊,暇日與弟閑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不知所為。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鏊形,乃火上沃醯,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入坑,投于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亦隨出。才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至死不肯言其情狀。';此外如舉人孟不疑,獨孤叔牙,虞侯景乙,宣平坊賣油人各條,亦均有意趣。蓋古人志怪即以此為目的,後人即以此為手段,優劣之分即見于此,雖文詞美富,敘述曲折,勉為時世小說面目,亦無益也。其實宗旨信仰在古人似亦無礙于事,如佛經中不乏可喜的故事短文,近讀梁寶唱和尚所編《經律異相》五十卷,常作是想,後之作者氣度淺陋,便難追及,只緣面目可憎,以致語言亦復無味,不然單以文字論則此輩士大夫豈不綽綽然有余裕哉。
第二所謂歷史的,再明了的說即是民俗學上的興味。關于這一點我曾經說及幾次,如在《河水鬼》,《鬼的生長》,《說鬼》諸文中,都講過一點兒。《鬼的生長》中云:
';我不信鬼,而喜歡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雖然,我不信人死為鬼,卻相信鬼後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氣之良能,但鬼為生人喜懼愿望之投影則當不謬也。陶公千古曠達人,其《歸園田居》云,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神釋》云,應盡便須盡,無復更多慮。在《擬挽歌辭》中則云,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陶公于生死豈尚有迷戀,其如此說于文詞上固亦大有情致,但以生前的感覺推想死後況味,正亦人情之常,出于自然者也。常人更執著于生存,對于自己及所親之翳然而滅,不能信亦不愿信其滅也,故種種設想,以為必繼續存在,其存在之狀況則因人民地方以至各自的好惡而稍稍殊異,無所作為而自然流露,我們聽人說鬼實即等于聽其談心矣。';(廿三年四月)這是因讀《望杏樓志痛編補》而寫的,故就所親立論,原始的鬼的思想之起原當然不全如此,蓋由于恐怖者多而情意為少也。又在《說鬼》(廿四年十一月)中云:
';我們喜歡知道鬼的情狀與生活,從文獻從風俗上各方面去搜求,為的可以了解一點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換句話說就是為了鬼里邊的人。反過來說,則人間的鬼怪伎倆也值得注意,為的可以認識人里邊的鬼吧。我的打油詩云,街頭終日聽談鬼,大為志士所訶,我卻總是不管,覺得那鬼是怪有趣的物事,舍不得不談,不過詩中所談的是那一種,現在且不必說。至于上邊所講的顯然是老牌的鬼,其研究屬于民俗學的范圍,不是講玩笑的事,我想假如有人決心去作‘死後的生活’的研究,實是學術界上破天荒的工作,很值得稱贊的。英國來則博士(J. G. Frazer)有一部大書專述各民族對于死者之恐怖,現在如只以中國為限,卻將鬼的生活詳細地寫出,雖然是極浩繁困難的工作,值得當博士學位的論文,但亦極有趣味與實益,蓋此等處反可以見中國民族的真心實意,比空口叫喊固有道德如何的好還要可憑信也。';照這樣去看,那么凡一切關于鬼的無不是好資料,即上邊被罵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的那些亦都在內,別無好處可取,而說者的心思畢露,所謂如見其肺肝然也。此事當然需要專門的整理,我們外行人隨喜涉獵,略就小事項少材料加以參證,稍見異同,亦是有意思的事。如眼能見鬼者所說,俞少軒的《高辛硯齋雜著》第五則云:
';黃鐵如者名楷,能文,善視鬼,并知鬼事。據云,每至人家,見其鬼香灰色則平安無事,如有將落之家,則鬼多淡黃色。又云,鬼長不過二尺余,如鬼能修善則日長,可與人等,或為淫厲,漸短漸滅,至有僅存二眼旋轉地上者。亦奇矣。';王小的《重論文齋筆錄》卷二中有數則云:
';曾記族樸存兄淳言,(兄眼能見鬼,凡黑夜往來俱不用燈。)凡鬼皆依附墻壁而行,不能破空,疫鬼亦然,每遇墻壁必如蚓卻行而後能入。常鬼如一團黑氣,不辨面目,其有面目而能破空者則是厲鬼,須急避之。';
';兄又言,鬼最畏風,遇風則牢握草木蹲伏不敢動。';
';兄又云,《左傳》言故鬼小新鬼大,其說確不可易,至溺死之鬼則新小而故大,其鬼亦能登岸,逼視之如煙云消滅者,此新鬼也。故鬼形如槁木,見人則躍入水中,水有聲而不散,故無圓暈。';紀曉嵐的《灤陽銷夏錄》卷二云:
';揚州羅兩峰目能視鬼,曰凡有人處皆有鬼。其橫亡厲鬼多年沉滯者率在幽房空宅中,是不可近,近則為害。其憧憧往來之鬼,午前陽盛多在墻陰,午後陰盛則四散游行,可穿壁而過,不由門戶,遇人則避路,畏陽氣也,是隨處有之,不為害。又曰,鬼所聚集恒在人煙密簇處,僻地曠野所見殊希。喜圍繞廚灶,似欲近食氣,又喜入溷廁,則莫明其故,或取人跡罕到耶。';羅兩峰是袁子才的門人,想隨園著作中必有說及其能見鬼事,今不及翻檢,但就上文所引也可見一斑了。其所說有異同處最是好玩,蓋說者大抵是讀書人,所依據的與其說是所見無寧是其所信,這就是一種理,因為鬼總是陰氣,所以甲派如王樸存說鬼每遇墻壁必如蚓卻行而後能入,蓋以其為陰,而乙派如羅兩峰則云鬼可穿壁而過,殆以其為氣也。其相同之點轉覺無甚意思,殆因說理一致,或出于因襲,亦未可知。如紀曉嵐的《如是我聞》卷三記柯禺峰遇鬼事,有云:
';睡至夜半,聞東室有聲如鴨鳴,怪而諦視。時明月滿窗,見黑煙一道從東室門隙出,著地而行,長丈余,蜿蜒如巨蟒,其首乃一女子,鬟鬢儼然,昂首仰視,盤旋地上,作鴨鳴不止。';又《槐西雜志》卷四記一奴子婦為狐所媚,每來必換一形,歲余無一重復者,末云:
';其尤怪者,婦小姑偶入其室,突遇狐出,一躍即逝。小姑所見是方巾道袍人,白須,婦所見則黯黑垢膩一賣煤人耳。同時異狀,更不可思議。';此兩節與《常談叢錄》所說李拔生夜聞鬼叫如鴨,又鬼物同時同地而聞見各異語均相合,則恐是雷同,當是說鬼的傳統之一點滴,但在研究者卻殊有價值耳。羅兩峰所畫《鬼趣圖》很有名,近年有正書局有復印本,得以一見,乃所見不逮所聞遠甚。圖才八幅,而名人題詠有八十通,可謂巨觀,其實圖也不過是普通的文人畫罷了,較《玉歷鈔傳》稍少匠氣,其鬼味與諧趣蓋猶不及吾鄉的大戲與目連戲,倘說此是目擊者的描寫,則鬼世界之繁華不及人間多多矣。—這回論語社發刊鬼的故事專號,不遠千里征文及于不佞,重違尊命,勉寫小文,略述談鬼的淺見,重讀一過,缺乏鬼味諧趣,比羅君尤甚,既無補于鬼學,亦不足以充鬼話,而猶妄評昔賢,豈不將為九泉之下所抵掌大笑耶。廿五年六月十一日,于北平之智堂。
家之上下四旁
《論語》這一次所出的課題是';家';,我也是考生之一,見了不禁著急,不怨自己的肚子空虛得很,只恨考官促狹,出這樣難題目來難人。的確這比前回的';鬼';要難做得多了,因為鬼是與我們沒有關系的,雖然普通總說人死為鬼,我卻不相信自己會得變鬼,將來有朝一日即使死了也總不想到鬼門關里去,所以隨意談論談論也還無妨。若是家,那是人人都有的,除非是不打誑話的出家人,這種人現在大約也是絕無僅有了,現代的和尚熱心于國大選舉,比我們還要積極,如我所認識的紹興阿毛師父自述,他們的家也比我們為多,即有父家妻家與寺家三者是也。總而言之,無論在家出家,總離不開家,那么家之與我們可以說是關系深極了,因為關系如此之深,所以要談就不大容易。賦得家是個難題,我在這里就無妨堅決地把他宣布了。
話雖如此,既然接了這個題目,總不能交白卷了事,無論如何須得做他一做才行。忽然記起張宗子的一篇《岱志》來,第一節中有云:
';故余之志岱,非志岱也。木華作《海賦》,曰,胡不于海之上下四旁言之。余不能言岱,亦言岱之上下四旁已耳。';但是抄了之後,又想道,且住,家之上下四旁有可說的么?我一時也回答不來。忽然又拿起剛從地攤買來的一本《醒閨編》來看,這是二十篇訓女的韻文,每行分三三七共三句十三字,題曰西園廖免驕編。首篇第三葉上有這幾行云:
犯小事,由你說,倘犯忤逆推不脫。
有碑文,你未見,湖北有個漢川縣。
鄧漢真,是秀才,配妻黃氏惡如豺。
打婆婆,報了官,事出乾隆五十三。
將夫婦,問剮罪,拖累左鄰與右舍。
那鄰里,最慘傷,先打後充黑龍江。
那族長,伯叔兄,有問絞來有問充。
後家娘,留省城,當面刺字充四門。
那學官,革了職,流徙三千杖六十。
坐的土,掘三尺,永不準人再筑室。
將夫婦,解回城,凌遲碎剮曉諭人。
命總督,刻碑文,後有不孝照樣行。
我再翻看前後,果然在卷首看見';遵錄湖北碑文';,文云: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奉上諭:朕以孝治天下,海山陬無不一道同風。據湖北總督疏稱漢川縣生員鄧漢禎之妻黃氏以辱母毆姑一案,朕思不孝之罪別無可加,唯有剝皮示眾。左右鄰舍隱匿不報,律杖八十,烏龍江充軍。族長伯叔兄等不教訓子侄,亦議絞罪。教官并不訓誨,杖六十,流徙三千里。知縣知府不知究治,罷職為民,子孫永不許入仕。黃氏之母當面刺字,留省四門充軍。漢禎之家掘土三尺,永不許居住。漢禎之母仰湖北布政使司每月給米銀二兩,仍將漢禎夫婦發回漢川縣對母剝皮示眾。仰湖北總督嚴刻碑文,曉諭天下,後有不孝之徒,照漢禎夫婦治罪。';我看了這篇碑文,立刻發生好幾個感想。第一是看見';朕以孝治天下';這一句,心想這不是家之上下四旁么,找到了可談的材料了。第二是不知道這碑在那里,還存在么,可惜弄不到拓本來一看。第三是發生';一丁點兒';的懷疑。這碑文是真的么?我沒有工夫去查官書,證實這漢川縣的忤逆案,只就文字上說,就有許多破綻。十全老人的漢文的確有欠亨的地方,但這種諭旨既已寫了五十多年,也總不至于還寫得不合格式。我們難保皇帝不要剝人家的皮,在清初也確實有過,但乾隆時有這事么,有點將信將疑。看文章很有點像是老學究的手筆,雖然老學究不見得敢于假造上諭,—這種事情直到光緒末革命黨才會做出來,而且文句也仍舊造得不妥貼。但是無論如何,或乾隆五十三年真有此事,或是出于士大夫的捏造,都是同樣的有價值,總之足以證明社會上有此種意思,即不孝應剝皮是也。從前翻閱阮云臺的《廣陵詩事》,在卷九有談逆婦變豬的一則云:
';寶應成安若康保《皖游集》載,太平寺中一豕現婦人足,弓樣宛然,(案,此實乃婦人現豕足耳。)同游詫為異,余笑而解之曰,此必妒婦後身也,人彘之冤今得平反矣,因成一律,以‘偶見’命題云。憶元幼時聞林庾泉云,曾見某處一婦不孝其姑遭雷擊,身變為彘,唯頭為人,後腳猶弓樣焉,越年余復為雷殛死。始意為不經之談,今見安若此詩,覺天地之大事變之奇,真難于恒情度也。惜安若不向寺僧究其故而書之。';阮君本非俗物,于考據詞章之學也有成就,今記錄此等惡濫故事,未免可笑,我抄了下來,當作確實材料,用以證此種思想之普遍,無雅俗之分也。翻個轉面就是勸孝,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二十四孝圖說》。這里邊固然也有比較容易辦的,如扇枕席之類,不過大抵都很難,例如喂蚊子,有些又難得有機會,一定要湊巧冬天生病,才可以去找尋魚或筍,否則終是徒然。最成問題的是郭巨埋兒掘得黃金一釜,這件事古今有人懷疑。偶看尺牘,見朱蔭培著《蕓香閣尺一書》(道光年刊)卷二有致顧仲懿書云:
';所論岳武穆何不直搗黃龍,再請違旨之罪,知非正論,姑作快論,得足下引《春秋》大義辨之,所謂天王明聖臣罪當誅,純臣之心惟知有君也。前春原嵇丈評弟郭巨埋兒辨云,惟其愚之至,是以孝之至,事異論同,皆可補蕓香一時妄論之失。';以我看來,顧嵇二公同是妄論,純是道學家不講情理的門面話,但在社會上卻極有勢力,所以這就不妨說是中國的輿論,其主張與朕以孝治天下蓋全是一致。從這勸與戒兩方面看來,孝為百行先的教條那是確實無疑的了。
現在的問題是,這在近代的家庭中如何實行?老實說,仿造的二十四孝早已不見得有,近來是資本主義的時代,神道不再管事,奇跡難得出現,沒有紙票休想得到筍和魚,世上一切都已平凡現實化了。太史公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也。這就明白的說明盡孝的難處。對于孝這個字想要說點閑話,實在很不容易。中國平常通稱忠孝節義,四者之中只有義還可以商量,其他三德分屬三綱,都是既得權利,不容妄言有所侵犯。昔者,施存統著《非孝》,而陳仲甫頂了缸,至今讀經尊孔的朋友猶津津樂道,謂其曾發表萬惡孝為首的格言,而林琴南孝廉又拉了孔北海的話來胡纏,其實《獨秀文存》具在,中間原無此言也。我寫到這里殊不能無戒心,但展側一想,余行年五十有幾矣,如依照中國早婚的習慣,已可以有曾孫矣,余不敏今僅以父親的資格論孝,雖固不及曾祖之闊氣,但資格則已有了矣。以余觀之,現代的兒子對于我們殊可不必再盡孝,何也,蓋生活艱難,兒子們第一要維持其生活于出學校之後,上有對于國家的義務,下有對于子女的責任,如要衣食飽暖,成為一個賢父良夫好公民,已大須努力,或已力有不及,若更欲彩衣弄雛,鼎烹進食,勢非貽誤公務虧空公款不可,一朝捉將官里去,豈非飲鴆止渴,為之老太爺老太太者亦有何快樂耶。鄙意父母養育子女實止是還自然之債。此意與英語中所有者不同,須引《笑林》疏通證明之。有人見友急忙奔走,問何事匆忙,答云,二十年前欠下一筆債。即日須償。再問何債,曰,實是小女明日出嫁。此是笑話,卻非戲語。男子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即此意也。自然無言,生物的行為乃其代言也,人雖靈長亦自不能出此民法外耳。債務既了而情誼長存,此在生物亦有之,而于人為特顯著,斯其所以為靈長也歟。我想五倫中以朋友之義為最高,母子男女的關系所以由本能而進于倫理者,豈不以此故乎。有富人父子不和,子甚倔強,父乃語之曰,他事即不論,爾我共處二十余年,亦是老朋友了,何必再鬧意氣。此事雖然滑稽,此語卻很有意思。我便希望兒子們對于父母以最老的老朋友相處耳,不必再長跪請老太太加餐或受訓誡,但相見怡怡,不至于疾言厲色,便已大佳。這本不是石破天驚的什么新發明,世上有些國土也就是這樣做著,不過中國不承認,因為他是喜唱高調的。凡唱高調的亦并不能行低調,那是一定的道理。吾鄉民間有目連戲,本是宗教劇而富于滑稽的插話,遂成為真正的老百姓的喜劇,其中有';張蠻打爹';一段,蠻爹對眾說白有云:
';現在真不成世界了,從前我打爹的時候爹逃就算了,現在我逃了他還要追著打哩。';這就是老百姓的';犯話';,所謂犯話者蓋即經驗之談,從事實中';犯';出來的格言,其精銳而討人嫌處不下于李耳與伊索,因為他往往不留情面的把政教道德的西洋鏡戳穿也。在士大夫家中,案頭放著《二十四孝》和《太上感應篇》,父親乃由暴君降級欲求為老朋友而不可得,此等事數見不鮮,亦不復諱,亦無可諱,恰似理論與事實原是二重真理可以并存也者,不佞非讀經尊孔人卻也聞之駭然,但亦不無所得,現代的父子關系以老朋友為極則,此項發明實即在那時候所得到者也。
上邊所說的一番話,看似平常,實在我也是很替老年人打算的。父母少壯時能夠自己照顧,而且他們那時還要照顧子女呢,所以不成什么問題。成問題的是在老年,這不但是衣食等事,重要的還是老年的孤獨。兒子闊了有名了,往往在書桌上留下一部《百孝圖說》,給老人家消遣,自己率領寵妾到洋場官場里為國民謀幸福去了。假如那老頭子是個希有的明達人,那么這倒也還沒有什么。如曹庭棟在《老老恒言》卷二中所說:
';世情世態,閱歷久看應爛熟,心衰面改,老更奚求。諺曰,求人不如求己。呼牛呼馬,亦可由人,毋少介意。少介意便生忿,忿便傷肝,于人何損,徒損乎己耳。
少年熱鬧之場非其類則弗親,茍不見幾知退,取憎而已。至與二三老友相對閑談,偶聞世事,不必論是非,不必較長短,慎爾出話,亦所以定心氣。';又沈赤然著《寒夜叢談》卷一有一則云:
';膝前林立,可喜也,雖不能必其皆賢,必其皆壽也。金錢山積,可喜也,然營田宅勞我心,籌婚嫁勞我心,防盜賊水火又勞我心矣。黃發臺背,可喜也,然心則健忘,耳則重聽,舉動則須扶持,有不為子孫厭之,奴婢欺之,外人侮之者乎。故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如能像二君的達觀,那么一切事都好辦,可惜千百人中不能得一,所以這就成為問題。社會上既然尚無國立養老院,本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對于已替社會做過相當工作的老年加以收養,衣食住藥以至娛樂都充分供給,則自不能不托付于老朋友矣,—這里不說子孫而必戲稱老朋友者,非戲也,以言子孫似專重義務,朋友則重在情感,而養老又以銷除其老年的孤獨為要,唯用老朋友法可以做到,即古之養志也。雖然,不佞不續編《二十四孝》,而實際上這老朋友的孝亦大不容易,恐怕終亦不免為一種理想,不違反人情物理,不壓迫青年,亦不委屈老年,頗合于中庸之道,比皇帝與道學家的意見要好得多了,而實現之難或與二十四孝不相上下,亦未可知。何也?蓋中國家族關系唯以名分,以利害,而不以情義相維系也,亦已久矣。聞昔有龔橙自號半倫,以其只有一妾也,中國家庭之情形何如固然一言難盡,但其不為龔君所笑者殆幾希矣。家之上下四旁如只有半倫,欲求朋友于父子之間又豈可得了。
......;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