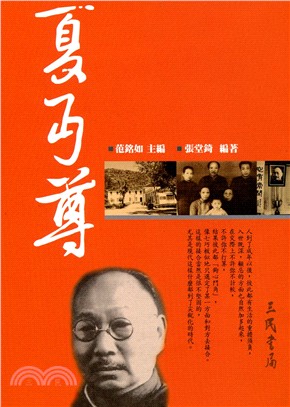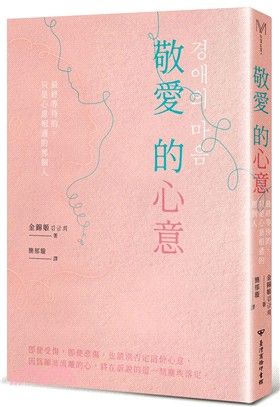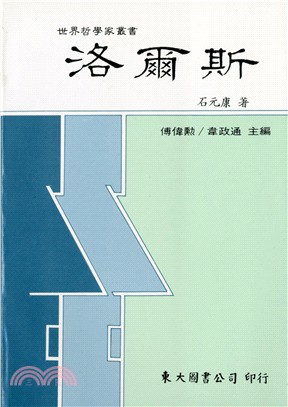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中鋒寶
輕輕一擦
縣長搭臺
狗婆蛇
嗩吶有靈
六狗
英雄老扒鍋的平民生活
書摘/試閱
我們那地方管手槍都叫“短火”,管縣政府的人習慣叫“挎短火的人”。“短火”是土話,古已有之;“挎短火的人”系專指稱謂,歷史卻不長。這有典故。解放初期的湘南山區,殘余的土匪蠻子還很多,他們仨倆成伙,晝伏夜出,四處竄擾。常常在夜深人靜時從縣城背後突然迸出一聲冷槍,“砰——叭”,驚擾得老百姓一夜一夜不敢上床睡覺。為了鞏固政權,保衛安全,上級給縣政府的工作人員都配了槍。從縣長科長到馬夫伙夫通信員,一人一根“短火”挎起。他們都攔腰束一根皮帶,另一根皮帶從左肩上斜斜地掛下來,把“短火”挎住。“短火”都有醬紫色槍套套著,槍把上飄著一縷紅纓子。他們也戴軍帽,打綁腿,穿解放鞋。他們也出早操。每天天亮,他們在縣政府門口的空坪上整好隊,由縣長親自喊口號:立正——稍息——立正!向左轉——齊步走。20多個人列成兩路縱隊,出街口,繞義公祠,到東邊城門口,再折回頭,沿街道南行,一直走到墟坪上,拐彎回到縣政府。他們在街道上行走著的時候,一律操正步,并無喧嘩,只是頭抬得很高,手臂擺動很大,帶動著腰下“短火”上的紅纓子也一蕩一蕩的,特別撩眼,顯得英氣勃發,不同凡響。他們經過的時候,好多小女崽小媳婦都從半開的鋪門里探出半邊臉,火辣辣的眼睛緊追著看。看隊伍里的小後生,看他們“短火”上的紅纓子。他們常常騎了馬在城外的舊城墻上狂奔,踢起一團一團的煙塵,郁積半空,久久不散。他們也有幾次跟隨部隊出城追剿土匪,據傳都十分梟勇,每次都有斬獲。自從縣政府的人挎上“短火”,消滅了幾股散匪,鎮壓了兩批惡霸,我們那一帶果然清靜下來,太平了。老百姓都可以睡落心覺了。“挎短火的人”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一種象征,有了至高無上的威勢。哪家豪紳隱瞞了財產,“去,喊挎短火的人來!”哪里發生了竊案,“趕緊,報告挎短火的人!”鄰里吵架了,吵得不可開交,“好?,請挎短火的人來評個公道!”兩口子黑夜里在床上打抱箍子架(這也是我們那地方的土話,書面語叫“做愛”),有時候老婆矯情,憋足了勁滾來滾去,抵死不從。男人便咬牙威脅道:“你要嫌老子的‘短火’不夠勁,老子去喊個挎短火的人來!”老婆頓時軟下身子,攤手攤腳地隨男人搬弄了。但有時也會相反,老婆聽了那種威脅卻更來勁,突然興奮了,聳著光身子叫道:“好啊好啊,去叫挎短火的人來啊!——不去叫你是我的崽!”有一次,南門口小井巷的打卦婆難產,在家里折騰了一天一夜,接生婆來了幾個,神也跳了,香灰水也喝了,艾也灸了,滾水也熏了,還灌了參湯,打卦婆痛得撕天喊地地嚎,可就是生不下來。家門口的巷子里站了很多人,聽著打卦婆一聲高一聲低的嚎喊,且聲氣漸來漸弱,都在心里想:只怕這人會保不住了。正在這當口,縣政府的伙夫出來挑水路過巷口,一條鮮紅的紅纓子在大腿和水桶之間飄揚。小把戲眼尖,一眼看見,就像看到了天神降臨,高聲叫道:“挎短火的來?!”人們也都跟著叫起來:“挎短火的來?!”聲音轟雷一般。接著就聽到房子里打卦婆猛然厲叫一聲,隨後就有一個接生婆沖出門來報喜道:“生了!生了!——生了個帶把的!”
打卦婆給兒子取個名字叫:火生。
從此,“挎短火的人”成了一個神話。
一
火生長到18歲了。
火生有個諢名:潲桶仔。這諢名也是母親打卦婆取的。
我們那地方,差不多的人都有個諢名,都是依據形體和特性而取。比如干牛肉、雙下巴、塌屁股、疤眼皮、五仔螳螂、二癩子。火生的特點是飯量大。特別大。小時候,打卦婆的奶水是很足的,兩坨奶子脹鼓得像豬尿泡,輕輕一點,奶汁就像箭一樣射出來。可是還不夠喂毛毛。另外還要加喂一碗米湯。稍長,火生棄奶吃飯,飯量大得嚇人。打卦婆從墟上買回一只粗瓷海碗,給他專用。海碗很大,直徑能有半尺,一碗盛得下半斤米飯。半斤米飯又哪里夠?火生三扒兩扒,也不要菜,轉眼就沒有了。打卦婆就將自己碗里的飯再減些給他。一邊減一邊嘮叨:“餓癆鬼!這樣的吃法,只怕要把一個家都吃窮去。”光吃點飯,是不至于把一個家吃窮去的,打卦婆的責罵里其實更多的是憐愛。他們家不富,但也不是很窮。那時候她的男人做點小生意,收入不高,但是穩定。而打卦婆身懷絕技,會打卦(她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說來真是神奇,她只憑一筒米,一枚銅錢,就能把冥冥中的一些事情算得清清楚楚。哪家丟失了東西,哪家走失了小把戲,哪家的老人病了還能活多少時日,哪家的媳婦偷了什么樣的野老公,請她打一卦,就能算得出來。(不過最後一種她是不給人算的。她說,那種事不能做,缺德!)每次算卦,酬金不少,主家都會塞給她一個紅紙封包。此外她還懂挑疳結。小把戲閉食,或是整夜啼哭不止,都來找她。每回人請,不論她是不是正忙,起身就去。到了,撐開小崽崽的嘴巴,看看伸出來的舌苔,點點頭,從袖子上拉下一根針(她的衣袖上長年別著幾口針),在火上燎一燎,叫大人把小崽崽抱緊了,自己攥住了小崽崽左手,大拇指頂在小崽崽中指第一節的節環上,使針在指尖上輕輕一點,一滴血冒出來。那血紫黑。第二天,主家道謝來了,隨手還帶點禮物,那禮物都是很輕的。兩只雞蛋,一筒米,一包點心,一個嫩南瓜,或是半個豬心。如此而已。打卦和挑疳結的事不是天天有,但也隔幾天就有一回。于是打卦婆家的飯桌上,隔三岔五地就會添上一盤炒雞蛋,或是一碟火焙魚。火生剛剛吃了兩年米飯,家里出了點變故,父親死了。父親一死,家里立刻斷了經濟來源。那時候打卦婆的絕技已經不能再干了。政府找她去訓了話,給人算卦屬于封建迷信范疇,必須禁止。如果再干,嚴懲不貸。打卦婆知道,“嚴懲”的意思就是開批判會,戴高帽子游街。她當然不會去找時背。可是他們還得生活。她得把兒子養大成人。打卦婆悲痛是悲痛,卻能想得開。她知道這就是命。人活一世,有時候是要認命的。她也不打算再嫁人了,就靠自己的一雙手,要把倆娘崽的生活托起來。天地這樣大,她不信會混不飽兩個肚子。雞都能找到食,鳥都能找到食,何況她這樣一個大活人哩。打卦婆咬咬牙,把生活的擔子挑起來了。她真是像一只勤快的麻雀子,到處撲棱去找食吃。她槌石頭,挑河沙,背竹子,給人舂米。縣城附近的鐘水河,有一段急水,上行的船常常擱淺,她也去幫忙背纖。她擠在一群年輕後生里邊,一樣地斜著身子,躬腰出力,一樣地喊著號子,一聲不落。春天,她上山扯野筍,撿蘑菇,撿地衣,挖地菜子(她把地菜子和碎米子粉做成粑粑,香氣沖人)。秋天——秋天真是個收獲的季節,她去撿稻穗,撿棉花,捯紅薯,捯花生。冬天,她踏著大雪進到十幾里路以外的南嶺山上,摘毛栗子。她把毛栗子用文火煮熟了,晾干。晚上,她在縣政府門口的街邊上擺個小攤,賣毛栗子。她跟前的團箕里,滿滿一團箕的毛栗子上面,插了一只小竹筒。一竹筒毛栗子,賣一分錢。一個小把戲跑過來了,手里舉著一張一分錢的黃票子。打卦婆抄起一握毛栗子,嘩嘩地傾進竹筒,堆得溜尖了,然後,一手接過票子,一手把毛栗子倒進小把戲兩手合起來的手掌里。打卦婆看著小把戲顛顛地歡喜地離去,她心里也好歡喜。她還在貓公嶺下開出一塊荒地,按季種上白菜、茼蒿、茄子、大頭菜、南瓜、苦瓜、絲瓜,還有蔥、蒜、辣椒。這樣,她家的飯桌上四時都有了新鮮菜蔬。她照舊給小毛毛挑疳結,還是隨叫隨到。但是她不再收受禮物。收錢。三角錢,五角錢,多少不拘,但得是錢。偶爾也有人偷偷來找她算卦,她一口就回絕了。她覺得世道這么好,天地這么大,只要肯出力氣就找得到錢,何必還去做政府禁止的事情。她也不想發橫財,只求入能敷出,身上穿得暖和,一日三餐能吃飽肚子,就滿足了。她一門心思,就是要讓獨伶崽火生吃飽穿暖,趕快長大成人。她真是把兒子當作了掌上明珠。可是她又不能像人家一樣,時時把兒子在手里捧著。她得每天出門做事,得賺錢。于是每天出門前,她煮好一鼎鍋米飯,舀出來在米篩上攤開晾著(我們那里,很多人家習慣早晨做好一天的飯,攤放在米篩上——米篩系竹子編就,有密密細細的洞眼,透氣通風,不會餿飯)。米篩在飯桌上擺著,讓火生隨時可以取食。一鍋米飯,按說倆娘崽一天都夠了。可是傍晚打卦婆回到家,米篩都空了,一家人的飯,讓火生兩頓就吃光了。後來糧食緊張,不能每天一鍋白米飯了,打卦婆就在米篩旁邊再放兩個烤紅薯,或是一碗蘿卜絲。每次火生仍然吃得精光。連烤焦了的、黑黑的、硬硬的紅薯皮都沒有留下。打卦婆覺得這兒子的肚子真是有點不可思議。有時不免會又愛又憐地嘮叨幾句:“崽啊,崽啊,你這肚子哪里裝得下那么多東西?!這真是跟門口的潲桶有得一比啊!”
潲桶仔這個諢名,就叫起來了。
潲桶仔很對得起他的母親。他的身體,像化肥催著一樣,看著看著長起來了。奇怪的是,他那樣能吃,身體卻并不胖,只是長高。十幾歲時,就長到一米七幾了。身材頎長,四肢勻稱,皮膚黝黑,眉眼清秀,一點不像母親(打卦婆是一張圓臉,兩道粗眉,一坨蒜頭鼻)。潲桶仔七歲發蒙,後來又上了中學。他的學習成績不好,總是排在班上最後一名。剛上小學時,他的算術不錯,心算尤好。老師說出兩組數字,別的同學還在紙上加減乘除,攢眉計算,他卻已經在心里把答案計算出來了。他對數字天生有一種敏銳。進了初中,一學代數,他就蠢了。他腦子里就像一團亂草,那些數字和公式怎么也理不清。讀書不如人,他的勞動卻是強項。學校里每個星期有兩天下午是勞動課,每學期還有半個月的學農活動。挖土,鋤草,種菜,種烤煙,平整操場,培育棉花缽,打農藥……他都一學就會。他常常還反過來當老師教同學們怎么做。可是勞動好畢竟替代不了學習成績。他勉強讀完初中,再升不了學,就回家了。
潲桶仔沒有考上高中,打卦婆倒也想得開,沒有說他一句重話。她覺得不讀書了,回家找點事做,照樣過日子。
打卦婆去找了居委會,找了搬運隊,找了竹棕社,找了鑄造廠,他們都同意讓他去。但不是正式的,是臨時工。潲桶仔跑去幾個地方看了。一看之下,大為喪氣。搬運隊是什么?拉板車。鑄造廠做些扒鍋鼎鍋,也叫“廠”。竹棕社一色的老頭子,看一眼都煩,成天坐在一起做事,人都會死。再說,他受不了按點上班下班的規矩。他想著自己正是青春年少,風華正茂得有如一枝柳樹條,隨便插在哪塊地上都能發芽長葉,活得有滋有味,搖曳生津。
他給自己找了個事:挑煤炭。
這是件自由職業,是個體力活。我們那里家家戶戶都燒煤餅。可是縣城里不產煤,挑煤要到去城十五里的張家煤礦,途中還要過一趟鐘水河。縣城里有閑勞力的人家,一般是自己去挑了煤回來,做成煤餅,自產自燒。但更多的人家是買現成的煤餅。這種煤餅,此地獨有。煤餅的做法也是別處少有的。煤炭先要過篩,把塊煤篩出來,另作他用,然後,在煤粉里摻入黃泥少許,澆上水,赤了腳在上面反復踩踏。這也有說法,叫:踩煤炭。我們那里也有專以幫人踩煤炭為業的。踩煤炭也是要有一點技術的。但更多的是要有韌勁。一腳跟一腳踩過去,翻轉來,再又踩一遍過去。如此七八遍,直到煤泥不沾腳了,就是和勻了,踩黏了,再把煤泥耙攏到一堆,一個個團成飯碗大小,拍在墻壁上。是好把式的都會在煤餅上留下清清楚楚的巴掌印,五指張開,深淺有致。巴在墻上的煤餅,往往要三五天,甚至七八天,才能風干,才干得透。所以,在縣城小巷里的一些磚墻上,長年巴滿了煤餅,形成一道黑乎乎并不太雅觀的風景。外地人到這里,總要駐足觀看一陣,捉摸不透那滿墻的煤餅是做什么用的,又是怎樣巴上去的。縣城里有一幫沒有讀書的半大孩子,就是以挑煤炭賣煤餅為生的。潲桶仔經常看到他們挑著一擔煤炭,滿頭大汗飛快地走進城來。經常看到他們打平伙,在豐和墟坪的小攤上吃餛飩,吃油炸?粑,偶爾還喝酒,快活得不得了。
潲桶仔這個年紀的人,都向往快活,向往自在。
打卦婆是個開通的人,想想兒子到搬運隊鑄造廠那些地方做臨時工,實在比挑煤炭好不了多少。雖然那樣名義上好聽一點,可是他們這種人家,要這種名義做什么呢?他們要的是實實在在能賺錢,有飯吃,就行。
她帶著潲桶仔到墟上去挑了一擔籮筐,一根扁擔。
潲桶仔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去挑煤炭的情景。早晨5點鐘,按照約定的時間,他同伙伴們在城邊的義公祠門口會合了。一行人挑著空籮筐,出城門,過石橋,走過一條石板路,進入山邊小道,往張家煤礦走去。那時候已經是秋天,空氣很清涼,天空很高,很藍。有風吹過,路邊的樹葉、莊稼葉,就沙沙沙地響。露水下來了,頭發上,脖頸上都潤潤的,滿含濕意。到了鐘水河邊,一條木船停在渡口,一個船工拄著長竹篙坐在船頭上。他們一個一個跳上船,把籮筐并攏放下,坐在架起的扁擔上。船工過來找每個人收了過河費,拔下篙,把船往對岸撐去。船工長得很瘦小,年紀也不小了,身手卻很敏捷。船工在船幫上來回蹦跳著,一根竹篙在他手里提起,又戳下,提起,又戳下。河水撞擊著船身,“嘩嚓——嘩嚓——”地響。
河水好清亮。
上了一道嶺。那嶺叫貓公嶺。嶺上亂石崢嶸,雜樹叢生。站在貓公嶺上,就看見了張家煤礦巨大的煤堆。一群人像風一樣地刮下山去。
潲桶仔還清楚地記得賣炭賺到錢時的興奮。他在墟坪上剛剛站下,買主就來了。買主是個中年婦女,微胖,穿一件三個口袋的干部裝。過完秤,潲桶仔隨口報出一個錢數。中年婦女在心里默了一陣,點頭說:“沒錯!——你這後生算數好快啊!”就從上衣口袋里掏出錢來,一張一張數給他。一張一塊的。一張五角的。一張一角的。又一張一角的。又一張一角的。最後是一張五分的。潲桶仔一張一張地接過錢來。接住一張,心就興奮地跳一下。以前他都是拿錢出去買東西,這一次是自己賺錢回來了。他把錢接完了,攥在手里,心還咚咚咚地跳了好久。他在心里算了算,這一擔煤賺到了一塊一角六分錢。
他把賺到的錢給母親買了一頂大斗笠。母親經常風里來雨里去,有張大斗笠,給她好遮風雨。
潲桶仔挑煤炭挑了快一年了,已經很熟練,很自如了。初上道時,他只挑80斤,很快就能挑100斤了。他也跟同伴們一樣,學會了一些小小的偷奸耍猾的技巧。他在煤礦裝煤時,會把塊煤先碼在籮筐底下,上面再蓋煤粉(塊煤比煤餅的價錢貴很多)。他知道塊煤該怎樣碼才能躲過檢查的鐵釬。過磅秤時,他知道把煤筐放得盡量靠後,或是用腳尖偷偷地頂在磅秤後面,這樣,一百斤煤往往能多給出一二十斤分量。過渡時,他不再按規矩交船工五分錢,他會用花言巧語,裝窮叫苦,說得船工只收他三分錢。但他不坑買主。有的人為了多賺點錢,故意把煤餅做得又厚又大。厚大的煤餅很難干透,重量也就不一樣。也有的人的煤餅不是風干的,是曬干的。曬干的煤餅里頭還是潮濕的。還有的人,干脆就直接在踩煤炭時多摻黃泥。這類花招,他都不做。打卦婆把新扁擔新籮筐給他時,就囑咐過,我們是本分人家,靠出力賺錢,那種事做了缺德,千萬不能做。潲桶仔也覺得不能做。他年輕,有的是力氣,只要多跑一趟張家煤礦,那點小利就賺回來了,何必哩!所以,他做的事情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清清楚楚。賣煤時,他會讓買主挑出任何一塊煤餅敲開來看。看干沒干透,看黃泥摻得是不是適度。過秤時,他總會讓秤桿尾巴翹得高高的,讓買主歡喜滿意。
潲桶仔長到18歲時,居委會主任把他的名字編進了基干民兵排。基干民兵是要持槍的。(是真槍哎!)他跟隨民兵們去操練過幾次。每次操練,他把槍扛在肩上,跟著隊伍操正步。“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大家走,他也走。大家喊,他也喊。還練臥倒。練瞄準。練突刺——刺!他覺得很興奮,神氣極了。
可惜每次操練以後,槍都要收回去。每次他心里都感覺悵悵的。
二
潲桶仔18歲那年,鬧起了文化大革命。
運動在縣城是轟然而至的。一夜之間,大標語、大字報就貼滿了縣政府的門口。潲桶仔平日不讀書不看報,對國家的事情,知道很少。他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不明白好多人怎么一下子就瘋了,狂了。他更不清楚街上的大標語、大字報,為什么火力都是對著當官的。他看到學生們砸菩薩,砸牌匾,砸石獅子,燒雕花床,爬上屋頂敲龍頭屋檐,感到十分驚奇。有一段日子,到街上去看游行的隊伍成了每天必修的功課。每天挑煤回來,洗過澡,換件干凈衣服,他就上街去了。街上從來沒有這樣熱鬧過。巷子口,商鋪里頭,政府門前,這里那里,都聚著一堆一堆的人,都等著看游行的隊伍。遠遠聽到鑼鼓聲、口號聲,人們知道隊伍要過來了,都興奮起來,倏地轉身,朝前張望。游行的隊伍真是威武雄壯,個個抬頭挺胸,意氣風發。照例是幾十面紅旗打頭,然後是一隊鑼鼓響器,後面才是大隊伍。到了圍觀人多的地方,鑼鼓聲停下,隊伍里就呼起了口號。口號都是有人指揮的。一人領呼,百人呼應,真如山呼海嘯,聲震屋瓦。游行的隊伍真多,從早到晚,接連不斷;游行的人精神真好,天天呼喊口號,聲音總是洪亮。潲桶仔常常在學生游行的隊伍中,看到昔日的同學,個個穿著整齊,左手佩著紅袖章,精神抖擻的樣子,不免神情黯然。有一次看到領呼口號的竟是初中時的同班同學雷仁寶,頓時興奮起來,跟著隊伍一直走到了豐和墟坪。他很難想象這位早先學習成績并不怎么樣的同學怎么竟成了學生領袖。
其實人們最喜歡看的還是牛鬼蛇神游行的隊伍。那些人過去都是有頭有臉有權有勢屁眼里起旋風的角色,現在一下子成了人下人,動不動就拉出來游街示眾,那神情真是狼狽至極,沮喪至極。那些人一律頭戴高帽,胸前掛塊白牌,上書本人名字,名字上用紅筆打了叉。名字上打叉是什么意思呢?潲桶仔以前看過槍斃死刑犯的布告,那些名字上是用紅筆打了叉的。難道這些人都那么壞,都是該死的么?!常常也有例外,胸前掛的不是白牌,是鐵板(怕有三四十斤重吧),是掃把(掃把是特制的,碩大無比),是痰盂,是犁頭,是一串破鞋。有一次一位老頭的胸前掛的是一只尿桶。老頭年紀不小了,頭發都花白了。尿桶也有不少年代了,桶底都被尿鹼漚得已經泛白。尿桶里不至于還存有殘尿,但氣味是濃郁的,不會散的。老頭走不幾步,就吐了。吐得哇哇的。一邊吐,一邊還走。一邊走,一邊還吐。旁觀的人無不掩鼻。看到這些人走過,路邊的人就會指指點點,小聲議論:誰誰誰是縣長,誰誰誰是書記,誰誰誰是部長,誰誰誰是局長,誰誰誰是科長,還有誰誰誰是主任……議論中有驚愕,有惋嘆,有幸災樂禍,有切齒咒罵。也有人只看,不議論,一言不發。這些人的背後,當然都會有一段歷史,有很多故事。這些人潲桶仔都不認識,很陌生,很遙遠。他只是漠然地看著。天天看。看了還想看。看久了就會抬頭看看屋瓦,看屋瓦上面的天空。他有時也會想象他們在位時會是一種什么樣子。不知為什么,他去想象的時候,心里會泛起一絲淡淡的快感。
潲桶仔沒有想到,自己也被卷入到運動的漩渦里去了。
那是個傍晚,天還沒有黑透。潲桶仔已經吃過晚飯,在門口的石板上沖了水,竹躺椅也搬出來了,蚊香也點上了(是一種鋸末摻硫磺搓成的蚊香,拇指粗細,狀如水蛇,對人、蚊都有很強的殺傷力),正準備躺下休息,有人急匆匆來通知他:全體基干民兵到義公祠門口集合。
潲桶仔磨蹭著不太想去。第二天他是要起早床去挑煤炭的,晚上耽誤了瞌睡,找誰要誤工費?後來想想,還是起身去了。
潲桶仔踢踢踏踏走到義公祠門口,基干民兵排已經集合完畢,出發了。他跟在隊伍後面,扯著前面的人問了問,才知道,晚上造反派的人要到縣武裝部搶槍。他立即明白了,這是要我們去守武器倉庫啊。他感到這件事情很大,很神聖,不覺緊了緊步子,小跑起來。
縣武裝部在城東,孤零零的一個院子。院子很大,空地很多。三面是農田,一條馬路從門前經過。院子里全部黑了燈,只能憑夜色勉強分清哪里是辦公樓,哪里是家屬樓,哪里是倉庫。潲桶仔這隊人一進去,大門就在背後關上了。潲桶仔隨著隊伍,經操坪,繞過辦公樓,走下一片洼地,到了武器庫門前。一群人在門前排成了三列橫隊,手挽手,擺出了眾志成城視死如歸的架勢。潲桶仔頓時緊張起來,雙手攥拳,瞪大了眼睛望著前方。他感覺身上的汗直涌出來。
四周很靜。好靜。
天上有星星閃爍。
猛地,他聽到前面大門“?當”一聲倒了,接著就有吶喊聲轟起來。不一會,就見黑壓壓的一大群人像山洪一樣從緩坡上沖下來。看著看著近了。就聽有人發一聲喊:“趕緊跑啊!”潲桶仔還沒有反應過來,眨眼工夫,周圍的人就撒腿跑了。霎時不見了蹤影。
潲桶仔愣在了那里,沒有動。
事實上他再想動也動不了了。洪水一樣的造反派隊伍已經卷到跟前,將他裹挾住,撞門而進。
一進武器庫,造反派們就四散跑開,找槍去了。潲桶仔靠在門框上,瞪眼喘著氣。緊張,害怕,惱怒,各種情緒在他心里交集。有人摁亮了手電筒,在黑暗中晃來晃去。他聽到有撬箱子的聲音。有人低聲叫喊:“這里一箱步槍。”“這是什么?——卡賓槍,卡賓槍!”他看到陸續有人抱著槍跑出門去了。忽然,他聽到一個沙嗓子高聲叫罵起來:“捅他娘的,這槍都沒有槍栓!”他覺得這沙嗓子好熟悉,好像是中學同學雷仁寶的聲音。他睜大眼睛,想要尋找這個聲音。他覺得在這種場合能有個熟人,多少有點依靠。可是這時候身邊“嘩嚓”一響,什么箱子砸破在地下了。有人拿手電筒照了照,興奮地叫起來:“哈!短火!一箱子都是短火!”聽到叫聲,鬼使神差地,潲桶仔一下子撲在箱子上,嘴里直說:“不能搶!短火不能搶!”先前那人逼到眼前,揪住他的頭發,說一聲:“嘿呀!這里還貓了一個死保皇派!”一用力,把他揪起來,掀翻在旁邊。立即過來幾個人將他按住在地上。他聽到那人在叫:“找子彈。趕快找子彈!”就有幾個聲音說:“沒有子彈。什么子彈都沒有!”那人轉身過來,一腳踏在潲桶仔的屁股上,咬牙切齒地問:“子彈在哪里?”潲桶仔怎么知道子彈在哪里?他不知道。那人怒喝一聲:“不說?打!”拳頭和腳板下雨一樣地打下來,結結實實地砸在他身上。他痛得在地上打滾,一雙手死死地抱住腦袋。這時他又聽到沙嗓子說話了。沙嗓子遠遠地說:“還不說?來點重的,抄東西打!”過一會,就有一柄槍托重重地砸在手臂上。他只聽到骨頭“啪嚓——”一響,忍不住慘烈地叫出一聲。
潲桶仔痛死過去了。
潲桶仔醒過來時,四下里寂靜無聲,造反派們早已跑了,無影無蹤。潲桶仔只覺得一身都痛,尤其左手臂痛得無法忍受。他估計是骨頭斷了。他想喊叫,可是不敢出聲。他不知道這武器庫里還隱藏著什么危險。他慢慢坐起來,又站直了身子。黑暗死死地擁裹著他。他突然生出了一種莫名的憎恨。他感到好痛,好累。他萬沒想到事情會變得這個樣子。他想著明天肯定是不能去挑煤炭了。接下去的一段日子都挑不了煤炭了。他不知道以後該怎么辦。但他顧不得那么多了。他現在只想著趕快回家,趕快見到母親。然後,躺到床上睡一覺。
潲桶仔用右手捂著左手臂,慢慢走出庫門。外面有風。風過處,路旁的矮樹“沙啦沙啦”地響。他感覺輕快了許多。武裝部的院子里仍然沒有電,漆黑一片。他踩著一地的夜色,虛虛地順漫坡走上去。他看見了操場上巨大的白色標語牌:“提高警惕,保衛祖國。”他看看右邊的家屬樓,又看看左邊的辦公樓。樓房都不高,都黑著燈。他忽然很想大叫一聲:“有鬼嗎?”張了張嘴,終是沒有出聲。
潲桶仔在大門口撿到一把“短火”。他出門時踢到一塊東西,撿起一看:一把左輪手槍。他在電影里見過,有的特務和國民黨軍隊副官用的就是這種左輪手槍。他心里一陣狂跳,熱血上涌。轉頭看看後面,仍然不見人影。他想了想。又想了想。一咬牙,把短火藏進懷里,緊步出了門。
馬路上的路燈都亮著,照在樹葉上,閃閃地反光。路燈光黃蒙蒙的,但他覺得很晃眼。他真希望一路都沒有燈亮才好。他踩著路邊的樹影往前走。低著頭,彎著腰,腳步散亂。這時候他感覺到手臂沒有那樣痛了。他的心思都集中在懷里的短火上。他覺得像揣了一座山。
可是他還是沒能避得開人。在東門口他被一聲斷喝截住了。抬頭一看,一群紅衛兵擋在面前。都戴著紅袖章,手持棍棒扁擔,有人肩上還扛了一支槍。這里的燈光很明亮,照得他們的臉色很凝重。潲桶仔一時有點慌亂,回答話時結結巴巴。他說自己回家。
紅衛兵問道:“你知不知道現在幾點鐘了?”
潲桶仔沒有手表,不知道時間。他搖了搖頭。
“告訴你吧,快12點了!”
潲桶仔就“哦”了一聲。他沒想到這么晚了。
紅衛兵突然厲聲問道:“你是不是回家?”
潲桶仔本來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就是回家。他也可以以兇對兇厲聲反問,我是不是回家關你們卵事?可是他今天心虛。他懷里藏了把短火,那是露不得的。他有天大的火氣也只有忍。他就怯了聲說:“當然是回家。”
“你家住哪里?”
“小井巷。”
“你叫什么名字?”
“姓李。李火生。”
“你不要騙我們啊!我們會查得清楚的。”
“你們查啊!這條街上,沒有不認識我李火生的。”
潲桶仔到底沒能忍住心里的火氣,一邊說一邊昂起了頭。話音落地,就見黑影里有個人轉身走過來。走近了,潲桶仔忽然高興地叫一聲:“趙—運—生。”
趙運生跟他是初中同學。他一直不明白,趙運生學習成績并不好,表現也一般,卻年年擔任班干部。同學那幾年,他有時看不起趙運生,有時又很佩服他。
潲桶仔沒有想到這時候會碰到他,感到見了救星一樣。
趙運生笑笑地說:“真的是你啊,火生。”
“不是我是哪個?!”潲桶仔委屈地說,“我要回家,他們攔住我的路。”
趙運生就對那些紅衛兵說:“這是我的同學,人家是貧下中農,基干民兵哩!”
潲桶仔抬了抬頭說:“就是,就是,他們還不相信我。”
趙運生撣了撣手說:“走吧,你趕快走吧。”
趙運生看他走出幾步,忽然又叫住他:
“哎,你不能走街上。”
潲桶仔疑惑地回頭望他。趙運生跟過來,小聲說:“前面會要打仗哩。”原來是造反派搶了武裝部的槍,跑到縣政府,占領了辦公大樓。保守派組織和四鄉的農民包圍了縣政府,守住各條大街,準備攻門。現在正街的各個街口都站了崗,閑人免過。——搞不好還會當作造反派捆起來。
“那怎么辦?我不能不回家呀!”
“包點遠路吧。走小巷子。——哎,我送你走一段。”
趙運生拿出一個紅袖章,給潲桶仔套在手臂上。兩人返回原路,下田埂,從城外繞過去。
潲桶仔忽然問道:“你剛才怎么把我的成分都改了?我家是手工業者啊!”
趙運生說:“你蠢啊!手工業者跟貧下中農不是一樣的?說你是貧下中農,省得費口舌解釋。”
潲桶仔覺得趙運生真是很精,暗暗佩服。
到了一處巷口,趙運生站住,潲桶仔點點頭,顧自走了。
潲桶仔回到家,摸摸懷里的短火,還在。短火早已被汗水浸濕了。他褪下手上的紅袖章,在黑暗中望著上面的“紅衛兵”三個字發了一陣呆,就把短火包了,塞進煤堆里。
潲桶仔摸著黑爬到床上,放開了四肢躺下。他忽然聽到城里槍聲大作,像炒豆子一樣好激烈。他想這一定是進城的農民向縣政府里頭的造反派發起進攻了。他不知道子彈能不能把縣政府大門打穿。他不知道會不會死人。他暗暗地慶幸,好在自己回到了家里。
他聽到母親打卦婆被吵醒了。打卦婆窸窸窣窣地起了床,開門出去。好一陣,打卦婆返回來,把門閂死了。打卦婆站在門背後,驚惶地問:“外面是不是在打仗?是不是在打仗?”
潲桶仔惡聲應道:“鬼打架哩!”
他忽然感覺到左手臂鉆心地痛起來。好痛。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