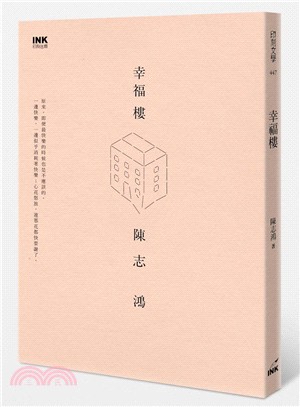再享89折,單本省下24元
商品簡介
電影《心魔》導演何宇恆 小說家賀淑芳 小説家龔萬輝 /推薦
我當時並不知道,要是真的聼了一個人的故事,就會動情,就會捲入故事之中,跟故事中人一起創造更多的故事。(〈傘與塔之間〉)
想必是愛,那熊熊的愛使然吧,女孩不惜老遠來到目前,端看男孩的勇氣罷了。人是到了,祇是還不曾到手。此時,男孩雙手蕩然,像是風推而無人坐乘的鞦韆,誰能止住它的晃動?牽與不牽來者的手,每一刻都是考驗,每一個街角都是可能了。(〈椰腳街紀念日〉)
原來,即便最快樂的時候也是不應該的,一邊快樂,一邊似乎消耗著快樂;心花怒放,連那花都快要謝了。(〈幸福樓〉)
作者簡介
陳志鴻(Tan Chee Hon)
1976年落地即為馬來西亞檳榔嶼第三代「華人」。福建安溪,純屬祖父母墓碑上的刻字而已,那是素未謀面的「原鄉」。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碩士延畢前後,入多所大專學府跑碼頭,負責不下於二十種文史哲課;2010年,改行入影視公司擔任創意總監一職,向各大電視臺兜售故事梗概。兩年後離職,復又離鄉赴韓當老學生,於慶熙大學研修韓語。年少即靠文學獎登壇,曾獲聯合報文學獎、新紀元華文青年文學獎等多項國内外獎項,涉獵多種文體如小説、散文、遊記等。著有一《腿》(2006年,印刻),育有二女,目前與家人生活在吉隆坡,那是樓往上建而生活素質往下掉的城市。
序
身後的追兵(後記)
此集子中有數篇東西,今昔之面目已經有頗大的差異,不能不有點交代,好對得起刊登過的編輯和讀過的讀者。
最初(說得久遠一點,是「上個世紀末」),當然是寫稿,手握圓珠筆,一個個字將〈傘與塔之間〉填入中文系免費供給的大稿紙。那是一九九八年大學長假,回島上父母家短住,香港已經回歸了,戴安娜也在巴黎車禍身亡了。長假開始之前,宿舍已經漸漸冷清,和幾位同學駕電單車上大學後山,看山下高架橋的車流,尚未淪爲過去的美好時光,那時當下便清楚我其實什麽都挽留不了,心裡之難受,彷彿給一隻看不見的巨手押著喝時間的毒藥,然後等著它慢性發作身亡,把我的記憶一起消滅。於是,我寫了〈傘與塔之間〉。
二○一一年又來至一個臨界點,準備赴韓之前,勞煩了學生從大學圖書館影印一份〈傘與塔之間〉,準備要規規矩矩當個打字員,不想,敲敲打打之間卻入戲了,由數千字之短,增至兩萬多字之長。我以爲那已經是化石,卻找到可以複製生物的幹細胞,真是奇蹟。中間,十多年就這樣過去了,砍柴的斧頭也可以拿來砍人(像顧城),許多童話神話早已破碎了,連再婚過的查理王子如今也要閙離婚。
那是二○○五年吧,又是一個關鍵年。才寫完〈椰腳街紀念日〉初稿,乍然便得在吉隆坡此異鄉過起一個人的日子,初獲「自由」便難掩心下的竊喜,卻不知道自由後將繼之以漫漫的寂冷。二○○八年註冊閃婚,往峇里島度蜜月兼趕寫那注定寫不好的舞臺劇,祇好從小説中尋找安慰。椰樹風下好日子,〈椰腳街紀念日〉卻越扯越長了。及至二○○九年長女出生而枕邊人坐月子時,尚未將萬字長稿外投,便知道那分明在爲難編輯大人。赴韓前後又經數次刪減,遂有目前較爲像小説的面目。彷彿菜籃撈水,祇剩下點點滴滴,但願昔日的記憶可以從此凝結其中。
至於〈世界〉呢,最初命名為〈脫〉,赴韓前後各大增刪了一遍,題目也換了。對這篇東西,我獲得的最大教訓:不勞他人,先以讀者的目光來挑剔自己吧。所以,學生寄來的稿件,我非常不負責任地回覆:先擱置一些時候,你就會看見自己的破綻了。有時,好的事物,人類自身總會第一時間感知那是好的;往往對於不太好的事物,我們往往還有一絲妄想,冀望別人會說:你還寫得不錯。
此書其餘諸篇,都屬於不同時空不同住所的產物。在一個愛不進去的城市,我住了十六七年之久,始於香港回歸那一年,時至今日港人佔中,也搬了快十次家,光是婚後就搬了四次家(預期明後年還會再搬一次),彷彿身後有追兵;不然,就是潛意識裡要橫看側看,把吉隆坡的好努力看出來?也許,還可以歸咎於生性怕熱又惹蚊,偏又不肯屈服於冷氣的淫威之下,枕邊人聼怕了我的牢騷,一次次開車兜斑苔谷一帶尋找熱帶清涼境。是的,當初最好的日子已經遠矣。那時,與父母、哥哥四人蝸居檳榔嶼戰前老房子的小後房,打著兩把小風扇便可以度日。如今我住過的戰前房子彷彿變成童話糖果屋,說了,連枕邊人也不相信。我屢次說,不是過去三十年來地球溫度升高了,而是如今的建築商用著劣質建材給我們造悶熱的「火宅」,並且預設我們將鑽牆裝冷氣。
大概,祇有四季國如日韓能讓我稍微安分一點(卻也在韓不得已搬了兩次),除卻夏季,其他月份我安然自適。也許,到韓國,或到每一個地方或長或短居留,都祇是人生的暖身操,誰清楚將來會如何呢?我是在適應大限,還是準備移民?祇要人身還在,不論到了哪裡,可以預期的是:勢必先安了電腦,趕緊「試筆」寫點東西。常常,祇有寫出了第一篇東西,我才對新住所稍微有點信任。換風水學的説法,文昌位算是找到了。
如今,身後追趕我的來敵恐怕已經越來越分明了,是時間,那人人的公敵。變動不居的人生還有夙願可言的話,那就是遠在開始提筆嘗試寫小説之前,便想著,其中一本小説集該以愛情為素材,把愛情當作一頭生物,細細觀察牠的生死、成長、轉折,連皮膚上的細紋都寫出來,那最好。曾想過以「愛有千萬身」命名,那已經是七八年前的舊事了;如今,未能想到更好的書名,且名之為《幸福樓》,但願沒給人標榜幸福之嫌。本來,絕然的幸福就不存在,樓之能起能興能塌,已經是中年人看過的風景。我很早就不相信「五十年不變」。
目次
傘與塔之間
世界
擋路貓
織女
椰腳街紀念日
幸福樓
出手
對岸
佛往深山求
臉
一把吉他的重量
身後的追兵(後記)
書摘/試閱
那時,幸福已經是一塊手中冰,融解中。男人与女孩一起回島一趟,趁女孩出國單飛之前辦理諸事,順便吃上一兩頓那故鄉的味道,好教去者懂得回味,懂得回頭。偏偏那幸福樓比他們快一步,先結束營業了。是一夕之間如此?看起來似乎這樣,其實誰都清楚,是難得回島,身後事物悄然變化,及至三五個月後轉身回頭一看,龐然廢墟乍現目前了。
別家茶樓這一天還開著,獨有幸福樓,他湊身近門面,不聞裡邊一點活動的聲息,也沒有任何的告示,悄悄然,數個月前的上一頓,成了最後的早餐。男人無法就此離去,他比任何時候更需要一點解釋:
爲何幸福樓一夕之間沒了?
店鋪前的走廊上踱來踱去,也許腳步吧,終於引起了鄰人的注意,鐡摺門上的小門洞子打開了,一張老婆婆的大臉露出來,他們一起變成了童話中森林小屋外的小孩。一問之下,卻不是獲得幸福樓所以亡的解釋,而是一則故事了:話說,一個晚上,一隻老鼠從天花板上掉下來,急速地奔跑之間,碗碗碟碟骨牌效應似的,都給打翻了,哪裡有錢再買?就這樣,幸福樓嘩啦啦,在一鼠作祟之下終至一蹶不振了。據那老婆婆這樣說。
門洞子關上,關於幸福樓終結的故事一直還在男人腦中迴蕩,及至與女孩坐車中時,仍將老婆婆的解釋搬出來笑話一遍,那天花板上掉落的老鼠,那碗碗碟碟,一座幸福樓之所以消亡的故事。笑後,空氣中突然靜寂了起來,他們開始不說話了。是的,不得已封在同一個車廂時,他們老早有了一種默契,拿別人冷嘲熱諷沒關係,話裡千萬不能再觸及彼此,那也會是空氣中的一點吻。更別說絮絮愛語,到了分離,愛其實就是妨礙。夜裡,總會有自覺背對,一點肉身的體溫同樣會將計畫砸掉。是如此嗎?不,他們似乎有意無意用各種各樣的距離懲罰彼此,誰叫她要走,誰叫他不留她。
一日收拾一半,女孩看男人一眼,飛速地收回了自己的目光,頭低了,祇見眼皮蓋落,兩彎眼睫毛高翹。此時動起了憐意,也是一種妨礙,前程突然十分之要緊。很長一段時間,他們怕看對方的雙眼,怕看出其中的怨毒。如果未經兩個人的同意,一場生離不會上演。他們都恨對方;他們不能不恨對方。扼殺了無數情感,掉過了一本銀行存摺,奔跑了無數次的英國最高專署,大計進行中,就不能不完成。
一切朝著不可逆轉的方向去了,身子是最後的繩索,椅上男人彎下腰,越肩攀圈住那幾乎久違的溫暖。連那過去熟悉的女孩圓肩,都已經是遙遠的千山萬水了。這時,男人才眞眞切切感受到,抱在一起,終究有需要放手的一刻,而且由他親自放手:眼前人,很快很快,他就要失去她了。他還能騰手拿出些什麽──哪怕是話語?如果一開始就決定由著她走,這時,其實也就沒有資格再緊緊抱住。放得她出走兩年之久,眼前還要一晌貪歡?可笑可悲。萎萎然,一雙手鬆放開來了,她就是一隻可以振飛的鴿子。原來,過去至今,他一直是她的鐵牢籠。
不是那島上幸福茶樓關閉在先,遠在那之前,屬於他們的這一座幸福樓早已慢慢冰解了。先去買一張單人床,撤丟了原先那一張彈簧早告深陷的雙人床。還有約莫一週的時間,飛機就像天外不明飛行物,就要來截走她了。入夜,女孩睡那一張新單人床,男人打地鋪,都已經是咫尺天涯了。其實,又何必搶登新床,她走後,就是他的天下了。難道,她還不如一張新床?就為了她的自由(還是他自己的?),他竟然要放生似的,由著她單飛。
似乎知道男人怕痛,還是得給他趁早習慣,女孩先來一針了。於是,一晚,從外頭參加聚會後獨歸,女孩人處天花板下,站男人背後,見他忙碌敲打電腦鍵盤,女孩用玩笑口吻透露自己愛上了一位個子與她齊高的工程師,是從前中學校友。可惜可惜,那一位工程師還沒有一些意思。男人停下了手指。女孩投擲如此一石,是要激活一湖七八年的死水?女孩意在折磨男人不出口挽留,故用激將法(那他太高估自己在對方心目中的地位了),擠榨出一點一滴的醋意?還是愛男人(又是另一種高估),怕他一人獨留下來有所眷戀,才編造如此的故事先自毀形象,好幫他拔除一顆疼痛的感情蛀牙?男人不曾回過頭來看天花板下的人影,他暫時不回頭。
不知何故,那一刻按照自身的想像,男人益發願意,是的,願意相信一切屬實。那一位陌生男果真要了女孩,也許,她就不必走天涯了。女孩需要的也許是一句話,一雙手臂,甚至,一張臉轉過頭來。沒有。男人和另外一個他──那位陌生男一樣,坐失流年,由著女孩走了,一樣一樣東西慢慢拆解,一座又一座或實或虛的幸福樓,還原瓦磚。光禿禿的情感舞臺上,隱隱有一種枯冷,男人在女孩走後,爬上了那一張還容得下他一個人的自私的單人床:人是遠了的,夢一步步走近,伏在他腳跟上,冰塊又重新凝結了。
*
感情告一個段落,都會找一塊地,立一個碑。當時來此人稀的小鎮,不過以為離別在即,有點不捨了,也需要透一口彼此的悶氣,就來了。其實,是不知那漸漸淪亡的感情,也需要一個可以下葬的地方,他們就來了。日出之後響動引擎,日中之前過鎮不入,到了離鎮約莫三分鐘車程的山坡小屋籬門前一停,費時兩三小時而已。山坡上有一大群的狗,從高處邁動四肢,奔落下來,止於籬門之前徘徊走動,狂吠一聲聲迴蕩草地間。
小屋門開,有人走了下來,慢慢放大了身影,是個老先生。電話中早已聯繫。開了門,車子往上駛,狗紛紛讓出了一條路來,土黃草綠,一條虛線的狀態,說是路,不如說是小徑。及至坡頂,車子不得不往無路的草地別去。車停屋旁草地上,人還是不敢下車,狗在外頭伺候。
屋小,高踞在上,坐擁了一大片的草地,推開門窗,即有綠意入目。連這屋看起來,也不像是主要的,似乎為了看守這一大片草地才建築出來似的,是綠海中的燈塔。下了車回頭山坡下來路,是溪流大小的灰路,劃過了大地的綠面,分出這裡與對過群山乃對峙的。左邊通往來時的小鎮,右邊則不曾前進,不得而知還有一些什麽等著他們。據說,是荒廢了的煤礦。
老先生怯怯然,擠出了一抹笑容。踏入屋內,面向客廳的一房掛滿了字畫,呈現展覽的狀態,據說,是老先生手筆,偶有買家來看;鄰隔的一房,關上,不得窺其內,似乎是工作室。他們兩小的房間在後頭,地板離地甚高,一件行李先放上去,人才跨上,像是捨舟登岸一樣。安頓好,老先生轉身,走的步伐,是一條筆直的線,目不斜視。據說,左傾的緣故,他在獄中度過了二三十年,一年前才獲釋出來,已經是一個對社會構不成威脅的老人了,手無寸鐵,祇有畫筆。
午後出去,再一次驚動了老先生。老先生不發一語,就祇是跺跺腳,用自己一副老朽之身,將一群狗重新逼往牆根下;狗將四肢收擱了起來,摺椅一樣,扁扁平平了,有了貓的溫馴。於是,老少各自轉身,往不同方向去,一往屋內,一往屋外草地上。他們在草地上往下走那一刻,有一種童年的愉悅慢慢爬上腳跟來。
開了籬門回頭山坡小屋,連那小屋,也是沉默的。挨路邊走,久久才有一車經過,拖著獨語的車聲遠去,一道長風拂面,是往那車影追了上去。他走前,她殿後,沉默一直往前推,就這樣,推出一條灰色的公路來。
之前不曾握她的手,待會入鎮,越發沒有可能了。清楚一個月後便要分隔兩地,握她的手,就怕手心所透露的訊息,一握就等同了挽留。公路上不曾握上,待會到了人煙聚集的鎮上,不知民風如何,也許更不可能再握了。
小鎮的黃金色彩早已剝落,來之前早已聽聞了,還需人往鎮上走才能確定一二:此地並無重疊的建設,一間教堂,一間小學,一間中學,一座大草場,一間喜餅店,一座菜市場……沒有重複,祇因人口流失。很明顯,他們不是鎮民,一人頭上一頂帽;鎮民頭盔都不戴,一騎風速,兜出了鎮外的曠地。承認與否,他們一旦暴露陌生的鎮民眼中,就成了彼此唯一熟悉的故人了。他不握她的手,她的手也不曾求索,各自兩袖蕭索,將他們連成一線的,是一團漸漸顯得尖銳而可聞的,沉默。
鎮上顯然不宜久留。別人終究將兩個戴帽人看成一對,一線笑容朝他們而發。走著,找了一家茶室吃一頓的午餐,下手頗重,過多的鹽,畢竟是靠勞力創建起來的小鎮,食物的調味還是從前的遺風。盛況已經遠了,盛況的味道還在舌尖滑過。吃了,就別過小鎮,沿來路往那久已聽聞的礦坑尋去。
那礦口,跟當今地下鐵的入口沒有兩樣,但是周遭別無高樓的襯托,祇有山高列嶂;乍看,又像巨大的海螺,彷彿遠古有個大海洋時代告退了,就擱淺此地岸上。入口的地面上布滿了砂石,不入坑道最底下,不知它有多深,他撿起了地面上的石塊,往坑道中投去。兩個人突然一心站等,半晌,沒有聲息,沒有回應。也許風大了一些,萬般聲響都聽之不聞了。再試,再來一塊石頭。他步離她身邊,走前了幾步,入了坑道之中,猛擲入內。等,等了好長好長一段時間,沒有。也許,坑道很長很長,石子丟了出去,半途落地面上,他祇是將石子移位而已;也許,坑中沒有一潭的積水,掉到了底下,也不會激起分明的回響。他們始終不知坑洞的深淺,那就由著它無言無語吧。連那坑洞,都是沉默的。
如此之礦坑,他們往上走,還碰上了數座。腳下走的是一條波浪路,來車往往乍現眼前,不是平穩地一輛輛從遠而近。在路旁左右一片綠地中,碰上數坑,他卻已經罷手,不嘗試了。地上不缺大小石塊,彎腰隨手一撿,都是可以下賭的籌碼。然而,廢礦又何足以一探再探。如此不屑,又為何要來此地?天之涯地之角,無法共赴,就來此荒荒然的一地,一個一切似乎已經結束的地方,總算一起出走過一趟。
地面上海螺狀的礦口,讓他懂了:那不遠的人煙,過去就靠地下的煤炭點燃興旺起來的。他們走在那路面,有點不眞實,彷彿地底下還有另外一個四通八達的世界,從一坑接連另外另一坑,蜘蛛網狀的脈絡,連土地都給人有點鬆鬆軟軟的感覺了。
綠地上有印度小男孩放牧,點點滴滴的白,流竄開來,是離群的羊兒。滿地殘殼之餘,總算看見了一些生機活物。停採了煤炭,發展跟著停滯了,時間就寄存在原始地貌上:天長地久,在這裡或許還不是神話。踏草地走那一刻,大家都有些愉悅了,祇是,此時是不是應該將心聲吐露作嘴巴上的話?然而,難得的快樂似乎不應該被褻瀆,放在心中許久的話,似乎不應該提上嘴巴來說。難道他就不能給她多一刻的快樂嗎?她在綠地上自由走動了,他還要變成一匹吞噬她的快樂的狼?
入夜之前他們再入鎮吃晚飯,飯後再慢慢走回下榻處,一路就靠來車的照明認路。入夜即臨危,他不能不握她的手了。婦孺當中,她總有可以扮演其中一個角色的時候。這回,是帶一個小孩的樣子,他握她軟小的手。他們不斷抬頭路旁的山坡,搜索一屋的孤燈。有了,過了公路,也還人在山坡下的籬門不敢擅自開門,狗又健跑奔落,用吠聲報知主人聽來客的夜歸。他們照樣得等,等老先生下山搭救。等的當兒,有來車經過,照出她的一張小臉龐;車過遠去,臉龐就消隱暗中。祇有一手的溫度,還是過去的一點聯繫,靜靜傳遞著星火。毫無例外,就跟世間每一對戀人一樣,當初他們也是從牽手開始的。
夜色較有光害的都市還重,徹徹底底,可以醉人了。痛飲了此地的夜色許久之後,人還是清清醒醒橫陳地板上,繼續當世間某座暗屋的不眠人;要是這一刻死了,還有人會以為是殉情。死不了,天明即要開車走,回到了那一間家,祇能繼續收拾,封箱。中間,這一個貌似一切已經結束了的小鎮,是雙方的一次機會。還有什麽要說?
白晝有過太長太長的沉默,此時若是開始第一句,有必要是一句重要的話;若是無關緊要的話,則應該吞下不表。可是,什麽是最重要的話?難道坦白一年前已經結束的,那一場悄然的背叛?不,時而他是感受到,即便不提,她連對象是誰都清楚的。她一直等他說出來。他一直期盼自己不說她能明白,正是好為了維持這一場感情,他沉默。
一時,這一夜的目的清晰起來了,是老天的一次機會,就在眼前供人把握。想必,人人都曾經在某個時空有過一次這樣的機會。他突然害怕事後天明的後悔。暗中,他一邊沐浴在一種天恩的光澤中,一邊挪動了身體往她那一邊靠去。伸手,他所抱住的是一語不發的血肉。高度緊張之下,他說了一句,我希望這一次是我們最後一次分開。
他終究不曾出口挽留,甚至還出語肯定她非走不可,祇是下回歸來之後,就別再走了。突然,他懂了,來到了此地,他越發懂了一點:自己根本不會挽留她──儘管他以為自己還有可能這麼做!她一語不發,沒有反抗,就由著他抱,祇是感覺上,人慢慢縮小又縮小,是一塊融解中的冰。原來,不辭車程老遠,來此荒廢了的小鎮,似乎就祇是為了確定:當剩下兩個人類時,他也會將她放生出去,等她兩年簽證期滿重投羅網,就憑他一個人的自私!她開始融解了,他的手臂感覺到一點濕意。她整個身體慢慢在他擁抱中動搖起來,一挫一挫,冰解中。他緊緊抱住她,話已經多餘了。心眼中浮現了一道風景,是坑口地面上一粒粒待拋擲的石塊日下發亮。他彎身撿取了又一粒,拋了出去,沒有回應。他們始終不知那荒廢了的礦有多深。他們就祇是沉默,似乎風地中默哀一座座煤礦的死亡。往後,那往後根本看不見了。那就讓目前為止的一切,都下葬這裡吧。就這樣,他們似乎找到了一塊地,立了一個碑,銘刻一段情的卒年:2007。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