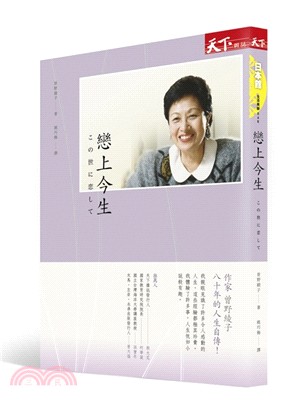定 價:NT$ 290 元
優惠價:90 折 261 元
絕版無法訂購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日本文壇長青樹,曾野綾子八十年的人生!
「我親眼見識了許多令人感動的人生,這些經驗都極其珍貴。
我體驗了許多事,人生恍如小說般有趣。」
人生,沒有白走的路。作家曾野綾子歷經了八十年的人生與長年的寫作經驗,首次提筆撰寫了關於自己的自傳。
堅強的她,其實從小歷經了雙親的不合睦及戰爭的體驗。這些看似人生上的挫折與苦難,在她眼裡卻都是珍貴的經驗。她相信,疾病與不幸都是伴隨人生而來。雖然我們無法避免,但她相信這些事都有其含意。多次受不了父親脾氣的母親,為讓了曾野綾子能夠擁有活下去的心靈支住,讓她就讀由修女執鞭的學校。在那裡,曾野綾子學會了務農、養牛,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讓她了解到身而為人的本質。
年輕時的曾野綾子,為了在緊張的生活壓力中尋求心靈的慰藉,開始沉浸於閱讀的世界。也因此,她認識了在文壇上的朋友,踏上作家之路。為了寫作的素材,她實地採訪了大壩工程的建設案,了解到在社會上做基礎建設的人們的辛苦與偉大的精神。由於天生視力不佳的緣故,中年時曾一度陷於幾乎全盲的危機。手術的奇蹟使她重見光明,也更佳感恩新的人生。
本不喜與人群來往社交的曾野綾子,在一些機緣下被推舉為日本財團的會長。也因此,她接觸了許多慈善相關事業的工作,不僅對第三世界的非洲有了更深的瞭解,更對這世界與人生有了更深的體悟。
作者曾野綾子最完整的人生自序,在本書中溫暖地娓娓道來。
推薦人
天下雜誌發行人 殷允芃
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 柯華葳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講座教授 孫寶年
「我親眼見識了許多令人感動的人生,這些經驗都極其珍貴。
我體驗了許多事,人生恍如小說般有趣。」
人生,沒有白走的路。作家曾野綾子歷經了八十年的人生與長年的寫作經驗,首次提筆撰寫了關於自己的自傳。
堅強的她,其實從小歷經了雙親的不合睦及戰爭的體驗。這些看似人生上的挫折與苦難,在她眼裡卻都是珍貴的經驗。她相信,疾病與不幸都是伴隨人生而來。雖然我們無法避免,但她相信這些事都有其含意。多次受不了父親脾氣的母親,為讓了曾野綾子能夠擁有活下去的心靈支住,讓她就讀由修女執鞭的學校。在那裡,曾野綾子學會了務農、養牛,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讓她了解到身而為人的本質。
年輕時的曾野綾子,為了在緊張的生活壓力中尋求心靈的慰藉,開始沉浸於閱讀的世界。也因此,她認識了在文壇上的朋友,踏上作家之路。為了寫作的素材,她實地採訪了大壩工程的建設案,了解到在社會上做基礎建設的人們的辛苦與偉大的精神。由於天生視力不佳的緣故,中年時曾一度陷於幾乎全盲的危機。手術的奇蹟使她重見光明,也更佳感恩新的人生。
本不喜與人群來往社交的曾野綾子,在一些機緣下被推舉為日本財團的會長。也因此,她接觸了許多慈善相關事業的工作,不僅對第三世界的非洲有了更深的瞭解,更對這世界與人生有了更深的體悟。
作者曾野綾子最完整的人生自序,在本書中溫暖地娓娓道來。
推薦人
天下雜誌發行人 殷允芃
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 柯華葳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講座教授 孫寶年
作者簡介
曾野綾子
生於一九三一年,聖心女子大學英文畢業。一九七九年,獲頒梵諦岡聖十字勳章;一九八七年,以《湖水誕生》獲土木學會著作獎;一九九三年,獲恩賜獎‧日本藝術學會獎。著作有:《無名碑》、《神污髒的手》、《貧困的僻地》、《人的根本》、《熟年的才情》、《人生的收穫》、《站在搖晃大地上 東日本大震災的個人記錄》、《夫婦,這不可思議的關係》、《沖繩戰渡嘉敷島「集體自殺的真實」、《惡與不純的樂趣》、《都市裡的幸福》、《圖解 現在學習聖經》、《我是貓1‧2》《不想勞動的人 不得進食》等。
生於一九三一年,聖心女子大學英文畢業。一九七九年,獲頒梵諦岡聖十字勳章;一九八七年,以《湖水誕生》獲土木學會著作獎;一九九三年,獲恩賜獎‧日本藝術學會獎。著作有:《無名碑》、《神污髒的手》、《貧困的僻地》、《人的根本》、《熟年的才情》、《人生的收穫》、《站在搖晃大地上 東日本大震災的個人記錄》、《夫婦,這不可思議的關係》、《沖繩戰渡嘉敷島「集體自殺的真實」、《惡與不純的樂趣》、《都市裡的幸福》、《圖解 現在學習聖經》、《我是貓1‧2》《不想勞動的人 不得進食》等。
目次
目錄
不眠不休六千萬字(替代序)
父親的身影 學到分辨表面與真實
母親的作文教室
修女的教誨
在戰爭中學到的事
立志成為小說家
一些自負的伙伴們
第一筆稿費五萬日圓
站在垃圾箱旁的命運之人
二十世代執筆與育兒的每一天
失眠、憂鬱 在美國獲得好轉
基督教是我的精神支柱
一個神話的背景
聖經中,也有小說的題材
視力惡化,中止所有的小說連載中止
實現赴撒哈拉沙漠的心願
與失明者一起前往聖地巡禮之旅
支援非洲
母親的死
接受日本財團會長的工作
非洲是偉大的教師
與「私底下的藤森」生活
毫不猶豫的辭退內閣閣員
與皇后交談
日本人的同質性
朋友運八十年
不眠不休六千萬字(替代序)
父親的身影 學到分辨表面與真實
母親的作文教室
修女的教誨
在戰爭中學到的事
立志成為小說家
一些自負的伙伴們
第一筆稿費五萬日圓
站在垃圾箱旁的命運之人
二十世代執筆與育兒的每一天
失眠、憂鬱 在美國獲得好轉
基督教是我的精神支柱
一個神話的背景
聖經中,也有小說的題材
視力惡化,中止所有的小說連載中止
實現赴撒哈拉沙漠的心願
與失明者一起前往聖地巡禮之旅
支援非洲
母親的死
接受日本財團會長的工作
非洲是偉大的教師
與「私底下的藤森」生活
毫不猶豫的辭退內閣閣員
與皇后交談
日本人的同質性
朋友運八十年
書摘/試閱
【內文試閱】父親的身影
在我剛踏入小說界時,曾被稱為「不知人間疾苦的千金」。原本,每個人都難免被貼上標籤,若是為了識別上的方便,倒也挺方便的。因此,我不曾排斥這個標籤,甚至曾經覺得這個與自己不符的稱號還不錯。實際上,我自幼就是勞碌命,任何家事都會做,與千金小姐根本無緣。
五十幾歲時,我開始從事園藝勞動。起初我都自己一個人來,但在六十四歲和七十四歲時,左右腳的腳踝竟雙雙骨折,只好請人代勞。
前些日子,院子裡的小芋頭能摘了。之前芋莖尚未發紅,想不到在最後一刻受到了雨水的恩澤,不僅是芋頭,連芋莖也茁壯得已能食用。替我種植芋頭的人似乎以為我沒吃過芋莖,但我可是任何料理都能勝任的。以前,我常看母親做菜,深信摘自大地的任何食物都是美味可口的。母親做的芋莖料理只加醋和味噌,我則會加美奶滋、芝麻醬,還有搗碎的核桃,很是美味。「不用學也會做」,雖然我很想這麼說,其實自我小時候以來的生活,全都可稱為體驗。
自幼開始,父母的感情不睦,家就像座「火宅」般。即使回家了還是很緊張,未曾有過休息的感覺。我覺得這是我性格彆扭、不易相處的原因。但也因此,我養成了得以與小說兩軍對峙的性格。為了忘卻現實的生活,我曾沉溺在閱讀小說的世界裡。
我的父親在明治二十年代(約一八八○年代)出生於東京京橋八丁堀。家中的長男為了繼承家業,只讀完舊制的中學。身為次男的父親必須出外工作掙錢,因此進入慶應義塾大學的理財系就讀。
畢業後到商社上班的父親,既不飲酒也不賭博。雖然他絕不向人借錢、謹守分寸,卻是個妻子與孩子受苦、軟弱的人。最甚者,他會施暴。我的思緒無時不刻都在想辦法如何不惹他生氣。也因此,我每天過著精神萎靡的生活。
至今,當時留下的後遺症還殘存在我現在的性格裡。不過我心裡覺得,如此扭曲的性格也走過來了,其實還不錯。
父親在外的形象很好,也不會擺架子。所以大家都說:「妳父親個性通達,是個好人呢。」從此,我再也不相信人的外在表現了。
我生於昭和六年(西元一九三一年),當時母親虛齡三十三歲,父親四十歲,是家中的次女。我有個未曾謀面的姐姐,她三歲時病死的六年後,我出生了。
母親認為,若再失去這個孩子,她無法再生育小孩了。據說她當時下定決心:「絕不能讓這小孩死去。」
還沒有抗生素的年代,母親不讓我吃冰淇淋、刨冰。因為當年有細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等疾病。大家都在吃冰淇淋,唯獨我不能吃。當時的怨恨至今還不能平復,所以成年後,即使前往多麼偏僻的地方,任何食物都不忌口。大概只剩螞蟻和北美馴鹿的生肉沒嘗過而已吧。
母親的哥哥開了家製造薄橡膠公司,事業很成功。父親婚後,就在那裡幫忙。當時我們住在南葛飾郡(現在的東京都葛飾區),我體弱多病,時常發燒。當時的葛飾區有許多土地僅需挖一公尺深就能汲水。但現在已成了很繁華的地段,昔日面貌不再。
不久後,雙親在名為田原調布的郊外買了一塊賣剩下來的地,移居過去。當時的田園調布是澀澤榮一(譯註:一八四○年~一九三一年,企業家。創立第一國立銀行、東京證券交易所等,有本資本主義之父之稱)模仿英國的都市計畫,以車站為中心,呈放射線狀排列而成,乍看頗富西洋風味。我家原本是純粹的日式建築,應鎮內會之求,木板籬笆與水泥圍圍牆都禁止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樹籬笆與石牆。託建築規定之福,田原調布在戰爭將結束前,房子雖遇空襲遭炸彈燒燬,卻不至於延燒。
當年,家門前是砂石路。車站前連一輛計程車也沒有,只有人力車並排著。電車僅有東橫線的兩節車廂和目黑線的一節車廂。那像極了玩具的車廂,有人讚譽直到昭和三十年(西元一九五五年)前後,下了車站後有迎面而來的新鮮空氣。
當年買不起麹町和麻布區一帶的年輕夫婦,倒買得起田園調布。我三歲時,舉家遷到這裡。這裡原是麥田,車站前的櫻花很美,空氣也清新。
我家雖不算中產階級,但也僱了傭人,算是一般的中等家庭。由於父親的關係,我學會了的觀察眾生相。在我還是小孩時,當我遇到狀似開朗的人,會自然地想像這個人的背後可能有個悲慘的遭遇。可以說,我是性格彆扭的孩子。雖然彆扭,這也是個可將其運用在社會上的證據。
表象與真相不同。掀開表象、好好理解箇中情況是件好事。後來,我在造訪貧困國家、風俗習慣迴異的國家時,都可以很快地入境隨俗,或許是自己在察顏觀色上訓練有素之故。成長於豪宅、有地位又有錢的人,可能會認為與他際遇不同的人是不幸的。但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任何地方都有它獨特的現實,如此而已。
修女的教誨
幼稚園時,我進天主教經營的聖心女子學院幼稚園部就讀。有許多國外歸國子女,但大財閥的女兒很少,當時並非名校。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小學畢業後,我就讀於舊制的高等女子學校。當年,
有五個年級。由於新制是小學六年、中學三年、高中三年,舊制短了一年。大部份的人,自高等女子學校畢業後就結婚去了。
當時,聖心幼稚園、小學、高等女子學校都位於白金三光町。現在有一條街就稱為白金街,是很高級的路段呢。當時,聖心有兩萬坪,一部份還拿來務農、養牛。這是修道院的規定。修道院修女們從歐洲各地抵達橫濱後,立刻搭乘前來迎接的車子,來到三光町修道院,之後就一輩子再也不離開了。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譯註: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五年。天主教會第二十一次大公會議,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後,制度稍作了修改。修女們雖然可以在七年一次的安息年返國探視家人,但一進修道院就不離開仍是當時的慣例。而修女們的墳墓就建在富士的山腳下。
在我就學期間,正值學校制度的更新,讀到一半的高等女學校要轉入新制。某日,校長宣佈了一則消息:「向各位報告一則令人欣慰的訊息!」正想著是什麼事時,校長說道:「聖心要成立大學了。」
建校的用地,決定購買舊久邇宮的宅邸。獲悉此事後,我並不覺得特別振奮,當時我對學問一點也不感興趣,甚至為賣地的貴族感到悲哀。賣掉長年居住的宅邸,畢竟是不得已的事。
久邇宮是香淳皇后與昭和天皇結婚時居住的宅邸。昔日大門上附有的皇族菊花家徽與氣派的大廳的紙門仍留著。國際系的學生穿著鞋子堂而皇之的跑進大廳讀書,大廳旁就是美軍寄贈的士兵宿舍(Quonset hut),我們曾在那棟士兵宿舍裡聽講。就讀於聖心大學的正田美智子(譯註: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生於東京。日本現任皇后。日本紅十字會名譽總裁)在當年應該也沒料到之後會進入皇室吧。
三光町的修道院之所以養牛,是為了獲取牛奶與肥料。雖然我不清楚當時的日本農業使用多少的硫酸銨等化學肥料,但一般農家都是用人的屎尿當作肥料的。外國的修女們並不這麼做,她們養牛,必定也會使用牛糞吧。所謂的生活,有一部份是耕種、養牛、每日實實在在地勞動。那極富教育意涵的日子,有如米勒的《晚鐘》,深刻地鐫於我心。
由於母親一心想離婚、自殺,讓我就讀基督教學校,或許是想給女兒生存的力量、建立心底的基石。當時的她應該已清楚知道,重要的支柱不在於親人或血緣關係等外在的東西,而是來自內在的力量。
幼稚園的入學考試很簡單。「叫什麼名字?」「幾歲?」,只要能正確回答這兩個問題就合格了,真是個不錯的時代。
幼稚園裡也有修女,我從當時就開始讀英詩。我的導師是位英國籍的修女,聽說她是英國王室圖書館館長的女兒。
那位修女會在黑色的修道服上加穿一件圍裙,若有空就會清掃廁所。在那裡我學到,無關身份或是高等教育,人都必須屈膝跪在地板上掃除。
孩子們如果在廁所裡聊天講話,修女會很生氣地:「噓!」在有目的的場合中,不要做目的以外的事。廁所不是用來聊天的地方。
學校教我們保持沉默。在走廊走路時,需維持靜默。因為走廊是走路的地方,而非交談的地方;在電車裡也要保持沉默,不得大聲喧嘩和奔跑。但是,學生們都不太遵守。所以在電車裡會遭到校友的斥責。
然而,我們從中學到一件重要的事。無法忍受沉默者,勢必無法成材。第一,沒有深思自己的時間。在會話中,我們要看著對方,然後確定自己所處的位置。但沉默無需與誰比較,因為那是在神的面前思考自己,理解自己是怎麼一回事。也不去干擾他人靈魂的靜寂。若耐不住沉默,想必在監獄裡也無法度日了吧。這真是了不起的教育。
時值戰前,學校會示出天皇、皇后的肖像,學生們會在天皇、皇后的相片前行禮。在「人類之王」前,善盡禮儀之舉。不過,由於我深知真正偉大的是神,所以不排斥這樣的鞠躬之禮。
天皇與皇后的相片收納在宛如小神社般的奉安殿中,每所學校都設有這種空間。戰後,文部省的官員前來聖心回收照片及奉安殿時,據說當年身為校長的德國修女說道:「哪有國家不尊敬自己國家元首的呢?如果真想取回,請帶走相片就好。奉安殿是藝術品,就放在這裡吧。」這也是一種抵抗的姿態。
學校教我們:「若想成為國際人,就要成為該國的優秀國民。(譯註:原文為To be international, be national)」不記得自己是否實踐過,但回想一九七五年時,我參加訪問中國的學術文化使節團,我穿著和服,在大民大會堂會面鄧小平先生。其實,在出發前夕,那家幾乎包辦北京旅行的旅遊公司寄來型錄,說明:「由於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所以請各位著以樸素的服裝。」一看完這段文字,我馬上決定把手邊的衣服全換上鮮豔的服飾。因為我是日本人,所以我認為日本人無需理會那樣的指示。而我也特地穿著和服前赴人民大會堂。
駐北京日本大使夫人愉悅的說:「日本代表穿著和服到人民大會堂,還是第一次看到呢。」看來,當時日本的左派,有太過在乎中國的風氣。
在戰爭中學到的事
若要說體驗形成我的人格,戰爭的存在的確是相當大的一部份。現代,人們把人生中的善惡分得過於簡單。雖然每個人都確信,和平比戰爭來得好,但實際上也不盡然如此。
有人因生活中的無聊感到痛苦,也有人為排遣無聊而賭博或與人通姦。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我十三歲那年,夜夜體驗美軍的空襲,過著不知能否活到翌日的生活。因此,和平的定義是很簡單的。即是造出讓每個人都能活到隔日的環境。畢竟在當年的內戰期間,光是去汲水,或是去見個雙親都可能面臨死亡,是很不幸的事。打造生存後的幸福,就是那些人要做的努力。
昭和二十年(西元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我在大田區體驗了東京大空襲。距我家約三百公尺遠的麵包工坊遭到爆彈的直接襲擊,一家九口當場同歸於盡。
只要思及不知能否活到翌日早晨,就令人膽顫心驚。因此我得了炮彈恐懼症,幾乎有一個星期無法開口說話。
死亡、被殺究竟是什麼感覺?戰時,站在右邊五十公分的人被炸死,但站左邊五十公分者卻存活了下來。在那樣的情況下,沒有任何道理。那絲毫之差,牽連著自己無法動搖的命運,了解這樣的事實,就會變得謙虛。
關東大地震(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也是個重大的災難。我無意以死亡人數襯托不幸的程度,然而這不幸是太平洋戰爭無法比較的。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至十日,東京遭到攻勢劇烈的空襲,當晚約有十萬人被燒死。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有人因而失去家人,恐怕連遺體都找不到了。當時沒有DNA鑑定這類的科學,國家也沒有余力在焦黑的屍體堆中辨識身份。
以下是某人說給我聽的故事。一個空襲後的翌日,走在隅田川的橋上時,許多發亮的顆粒隨風拂過橋上而來。那其實是人骨。當時,日本住宅的建材,幾乎沒有不可燃物。畢竟房子盡是木頭和紙。那些建築素材全成了燃料,焚燒著活人。順帶一提,因戰爭災害可獲得國家補償者,除了某些身份特殊的人,一般人都無法獲得補償。聽說,戰死者的家屬、傷兵、從中國撤退回來的士兵、原子核爆的受害者、西伯利亞強制居留者,能獲取少許補償或年金。但我身邊那些家園燒毀的人、父親、兄長或孩子在空襲中受傷的人、財產遭沒收的人,都沒有任何補償措施。
當時的狀況無法像東日本大地震那般,當晚就能配給緊急食物、水;有指定的避難所;有巴士可接送要逃出災區的人們;之後還臨時住宅。東京空襲下的人們是怎麼活下來的?有人暫時躲到友人燒了一半的家;有人在房子燒毀時,揀拾可用的土磚塊,在一旁搭起庇身之處。換言之,他們有如流浪犬似地在焦土茍延殘喘的活著。想必也沒有組織可以對失去雙親的孩子們伸出援手。孩子們只能依賴路過的行人所給予的極少的慈悲,像流浪兒般地生存。
對東日本大地震的災民,我深感同情。但若思及戰爭,現狀擁有的國家、友人、警察軍隊及外國義工團體等的援助,與戰爭的悲慘是不可相比的。畢竟這次震災的情況,除了災區,北海道和中部以西的日本人都能持續過著平日的生活,且有餘力援助他人。而在戰爭期間,任誰都是物資缺乏、貧窮、營養失調,沒有餘力的。
從那年的五月到隔年的二月,我疏散到金澤。雖然東京最猛烈的空襲已暫告一段落,但無法確定是否會有再次的空襲,我無法預知自己的命運。父親因直腸癌動了手術,得以免役,所以戰爭期間我們一家三人都聚在一起。
透過高等女校的介紹,我被動員派至樹脂加工廠當女工,主要製做飛機零件中的絕緣體。十三歲那年,我每天上午七點勞動到傍晚六點,除中午時間稍事休息外,成天勞動。然而,對於生活上的變化,我倒挺樂在其中的。對自己的能力產生信心,原來自己也可以這般地勞動。迄今,面對工場勞動時,我絲毫不會有任何的不安。
戰爭讓每個人都變窮了。不僅頭髮、衣服上長出蝨子,一堆人擠進混濁的浴池裡也是從沒有過的體驗。戰時,大家只能穿上連身式的勞動服。這有兩個意涵。一方面是缺乏物資,一方面是不得穿其他衣服,以免礙了當時戰意高揚的氣氛。無論如何,是自願穿上的。
戰爭結束時,我得到一件華美的棉布洋裝,那是去過上海的日本人送的。然而我沒有機會穿,只覺得若遭空襲燒燬未免也太可惜,因此一直塞在背包裡帶著走。若我拿到甜食,想必也會這麼做。當時,每個人的慾望都是如此,這種想法不足為奇。總之,不至於餓死,也不至於裸身。
第一次發現頭髮長了蝨子,是某次在頭部奇癢時,我戴著工作手套抓癢時發現的。當我看到指頭那邊,手套上的細縫部分有一隻蠕動的蟲子時就知道了。我請工廠裡作業的同事幫我抓蝨子,在那之前,真的很難想像蝨子會存活在自己的頭髮裡。長大的蝨子一經沖洗就會掉落,但產在頭髮裡的蝨卵卻非常棘手。回到東京後,我有一位打扮時髦的阿姨有支燙髮鉗。我請她用那燙髮鉗把附在髮根的卵全都處理掉後,才大大鬆了一口氣。至今都還記得蝨子繁殖旺盛時的慘痛經驗。
最近,我有種想法。體驗過悲慘的底層生活,也是一種財產。現代人一心追求的是奢侈的財富—當然這是很自然的,沒有人會對負債給予好評。不過我們這個世代的每個人,在當時都是負債者。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每個人成長的境遇也各不相同。無論是好的環境或悲慘的生活,都有其教育的意義。
戰時我罹患了砲彈恐懼症,但我從戰爭中學到很多。戰爭是惡的,卻也有教誨的一面。
昭和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三年),新潮社出版了吉田健一翻譯的尼古拉斯的《憤怒之海》(The Cruel Sea)。前些日子,我稍微翻了一下。上、下兩冊,以九號字上下兩段的方式編排,定價兩百五十日圓。
吉田健一是前日本首相吉田茂元的長子,是英文學者。妹妹麻生和子的先生是前首相麻生太郎。
吉田健一氏在這本書的後記寫道:
《西線無戰事》與《戰艦大和之終結》這兩部作品,都在異於常態的戰爭體驗上進行描寫。因戰爭體驗的異常,導致人類的精神產生極大的影響。在那樣的情況下,小說補捉了堪稱為人類精神的光輝。然而,反其道而行的《憤怒之海》實現了另一種,至今在戰爭文學中被遺漏的某種書寫的可能性。它反用了戰爭—使交戰國的全體國民陷入其中的近代戰爭—的性格。面對同樣受到來自戰爭猛烈的衝擊,文中點出團體中每個人不同的反應。以人性的角度理解團體的動向,亦即將那強烈的光線照射在人類的社會生活裡。
以當時的世態,戰爭想必是忌諱之事,且毫無價值可言。畢竟,離戰爭結束還未滿十年。不過,無論是《西線無戰事》或是這本書,我相信,正如吉田所言,有些東西唯有透過戰爭才得以學習,我們不能全面地否定戰爭。這樣的想法在我心中定立了很久,我想這也是幾年後,成為我調查渡嘉敷島的集體自殺、撰寫《一個神話的背景》(後來改題為《沖繩戰.渡嘉敷島「集體自殺」的真相》,由WAC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的動機。
在我剛踏入小說界時,曾被稱為「不知人間疾苦的千金」。原本,每個人都難免被貼上標籤,若是為了識別上的方便,倒也挺方便的。因此,我不曾排斥這個標籤,甚至曾經覺得這個與自己不符的稱號還不錯。實際上,我自幼就是勞碌命,任何家事都會做,與千金小姐根本無緣。
五十幾歲時,我開始從事園藝勞動。起初我都自己一個人來,但在六十四歲和七十四歲時,左右腳的腳踝竟雙雙骨折,只好請人代勞。
前些日子,院子裡的小芋頭能摘了。之前芋莖尚未發紅,想不到在最後一刻受到了雨水的恩澤,不僅是芋頭,連芋莖也茁壯得已能食用。替我種植芋頭的人似乎以為我沒吃過芋莖,但我可是任何料理都能勝任的。以前,我常看母親做菜,深信摘自大地的任何食物都是美味可口的。母親做的芋莖料理只加醋和味噌,我則會加美奶滋、芝麻醬,還有搗碎的核桃,很是美味。「不用學也會做」,雖然我很想這麼說,其實自我小時候以來的生活,全都可稱為體驗。
自幼開始,父母的感情不睦,家就像座「火宅」般。即使回家了還是很緊張,未曾有過休息的感覺。我覺得這是我性格彆扭、不易相處的原因。但也因此,我養成了得以與小說兩軍對峙的性格。為了忘卻現實的生活,我曾沉溺在閱讀小說的世界裡。
我的父親在明治二十年代(約一八八○年代)出生於東京京橋八丁堀。家中的長男為了繼承家業,只讀完舊制的中學。身為次男的父親必須出外工作掙錢,因此進入慶應義塾大學的理財系就讀。
畢業後到商社上班的父親,既不飲酒也不賭博。雖然他絕不向人借錢、謹守分寸,卻是個妻子與孩子受苦、軟弱的人。最甚者,他會施暴。我的思緒無時不刻都在想辦法如何不惹他生氣。也因此,我每天過著精神萎靡的生活。
至今,當時留下的後遺症還殘存在我現在的性格裡。不過我心裡覺得,如此扭曲的性格也走過來了,其實還不錯。
父親在外的形象很好,也不會擺架子。所以大家都說:「妳父親個性通達,是個好人呢。」從此,我再也不相信人的外在表現了。
我生於昭和六年(西元一九三一年),當時母親虛齡三十三歲,父親四十歲,是家中的次女。我有個未曾謀面的姐姐,她三歲時病死的六年後,我出生了。
母親認為,若再失去這個孩子,她無法再生育小孩了。據說她當時下定決心:「絕不能讓這小孩死去。」
還沒有抗生素的年代,母親不讓我吃冰淇淋、刨冰。因為當年有細菌性痢疾、阿米巴痢疾等疾病。大家都在吃冰淇淋,唯獨我不能吃。當時的怨恨至今還不能平復,所以成年後,即使前往多麼偏僻的地方,任何食物都不忌口。大概只剩螞蟻和北美馴鹿的生肉沒嘗過而已吧。
母親的哥哥開了家製造薄橡膠公司,事業很成功。父親婚後,就在那裡幫忙。當時我們住在南葛飾郡(現在的東京都葛飾區),我體弱多病,時常發燒。當時的葛飾區有許多土地僅需挖一公尺深就能汲水。但現在已成了很繁華的地段,昔日面貌不再。
不久後,雙親在名為田原調布的郊外買了一塊賣剩下來的地,移居過去。當時的田園調布是澀澤榮一(譯註:一八四○年~一九三一年,企業家。創立第一國立銀行、東京證券交易所等,有本資本主義之父之稱)模仿英國的都市計畫,以車站為中心,呈放射線狀排列而成,乍看頗富西洋風味。我家原本是純粹的日式建築,應鎮內會之求,木板籬笆與水泥圍圍牆都禁止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樹籬笆與石牆。託建築規定之福,田原調布在戰爭將結束前,房子雖遇空襲遭炸彈燒燬,卻不至於延燒。
當年,家門前是砂石路。車站前連一輛計程車也沒有,只有人力車並排著。電車僅有東橫線的兩節車廂和目黑線的一節車廂。那像極了玩具的車廂,有人讚譽直到昭和三十年(西元一九五五年)前後,下了車站後有迎面而來的新鮮空氣。
當年買不起麹町和麻布區一帶的年輕夫婦,倒買得起田園調布。我三歲時,舉家遷到這裡。這裡原是麥田,車站前的櫻花很美,空氣也清新。
我家雖不算中產階級,但也僱了傭人,算是一般的中等家庭。由於父親的關係,我學會了的觀察眾生相。在我還是小孩時,當我遇到狀似開朗的人,會自然地想像這個人的背後可能有個悲慘的遭遇。可以說,我是性格彆扭的孩子。雖然彆扭,這也是個可將其運用在社會上的證據。
表象與真相不同。掀開表象、好好理解箇中情況是件好事。後來,我在造訪貧困國家、風俗習慣迴異的國家時,都可以很快地入境隨俗,或許是自己在察顏觀色上訓練有素之故。成長於豪宅、有地位又有錢的人,可能會認為與他際遇不同的人是不幸的。但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任何地方都有它獨特的現實,如此而已。
修女的教誨
幼稚園時,我進天主教經營的聖心女子學院幼稚園部就讀。有許多國外歸國子女,但大財閥的女兒很少,當時並非名校。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小學畢業後,我就讀於舊制的高等女子學校。當年,
有五個年級。由於新制是小學六年、中學三年、高中三年,舊制短了一年。大部份的人,自高等女子學校畢業後就結婚去了。
當時,聖心幼稚園、小學、高等女子學校都位於白金三光町。現在有一條街就稱為白金街,是很高級的路段呢。當時,聖心有兩萬坪,一部份還拿來務農、養牛。這是修道院的規定。修道院修女們從歐洲各地抵達橫濱後,立刻搭乘前來迎接的車子,來到三光町修道院,之後就一輩子再也不離開了。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譯註: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五年。天主教會第二十一次大公會議,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後,制度稍作了修改。修女們雖然可以在七年一次的安息年返國探視家人,但一進修道院就不離開仍是當時的慣例。而修女們的墳墓就建在富士的山腳下。
在我就學期間,正值學校制度的更新,讀到一半的高等女學校要轉入新制。某日,校長宣佈了一則消息:「向各位報告一則令人欣慰的訊息!」正想著是什麼事時,校長說道:「聖心要成立大學了。」
建校的用地,決定購買舊久邇宮的宅邸。獲悉此事後,我並不覺得特別振奮,當時我對學問一點也不感興趣,甚至為賣地的貴族感到悲哀。賣掉長年居住的宅邸,畢竟是不得已的事。
久邇宮是香淳皇后與昭和天皇結婚時居住的宅邸。昔日大門上附有的皇族菊花家徽與氣派的大廳的紙門仍留著。國際系的學生穿著鞋子堂而皇之的跑進大廳讀書,大廳旁就是美軍寄贈的士兵宿舍(Quonset hut),我們曾在那棟士兵宿舍裡聽講。就讀於聖心大學的正田美智子(譯註: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生於東京。日本現任皇后。日本紅十字會名譽總裁)在當年應該也沒料到之後會進入皇室吧。
三光町的修道院之所以養牛,是為了獲取牛奶與肥料。雖然我不清楚當時的日本農業使用多少的硫酸銨等化學肥料,但一般農家都是用人的屎尿當作肥料的。外國的修女們並不這麼做,她們養牛,必定也會使用牛糞吧。所謂的生活,有一部份是耕種、養牛、每日實實在在地勞動。那極富教育意涵的日子,有如米勒的《晚鐘》,深刻地鐫於我心。
由於母親一心想離婚、自殺,讓我就讀基督教學校,或許是想給女兒生存的力量、建立心底的基石。當時的她應該已清楚知道,重要的支柱不在於親人或血緣關係等外在的東西,而是來自內在的力量。
幼稚園的入學考試很簡單。「叫什麼名字?」「幾歲?」,只要能正確回答這兩個問題就合格了,真是個不錯的時代。
幼稚園裡也有修女,我從當時就開始讀英詩。我的導師是位英國籍的修女,聽說她是英國王室圖書館館長的女兒。
那位修女會在黑色的修道服上加穿一件圍裙,若有空就會清掃廁所。在那裡我學到,無關身份或是高等教育,人都必須屈膝跪在地板上掃除。
孩子們如果在廁所裡聊天講話,修女會很生氣地:「噓!」在有目的的場合中,不要做目的以外的事。廁所不是用來聊天的地方。
學校教我們保持沉默。在走廊走路時,需維持靜默。因為走廊是走路的地方,而非交談的地方;在電車裡也要保持沉默,不得大聲喧嘩和奔跑。但是,學生們都不太遵守。所以在電車裡會遭到校友的斥責。
然而,我們從中學到一件重要的事。無法忍受沉默者,勢必無法成材。第一,沒有深思自己的時間。在會話中,我們要看著對方,然後確定自己所處的位置。但沉默無需與誰比較,因為那是在神的面前思考自己,理解自己是怎麼一回事。也不去干擾他人靈魂的靜寂。若耐不住沉默,想必在監獄裡也無法度日了吧。這真是了不起的教育。
時值戰前,學校會示出天皇、皇后的肖像,學生們會在天皇、皇后的相片前行禮。在「人類之王」前,善盡禮儀之舉。不過,由於我深知真正偉大的是神,所以不排斥這樣的鞠躬之禮。
天皇與皇后的相片收納在宛如小神社般的奉安殿中,每所學校都設有這種空間。戰後,文部省的官員前來聖心回收照片及奉安殿時,據說當年身為校長的德國修女說道:「哪有國家不尊敬自己國家元首的呢?如果真想取回,請帶走相片就好。奉安殿是藝術品,就放在這裡吧。」這也是一種抵抗的姿態。
學校教我們:「若想成為國際人,就要成為該國的優秀國民。(譯註:原文為To be international, be national)」不記得自己是否實踐過,但回想一九七五年時,我參加訪問中國的學術文化使節團,我穿著和服,在大民大會堂會面鄧小平先生。其實,在出發前夕,那家幾乎包辦北京旅行的旅遊公司寄來型錄,說明:「由於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所以請各位著以樸素的服裝。」一看完這段文字,我馬上決定把手邊的衣服全換上鮮豔的服飾。因為我是日本人,所以我認為日本人無需理會那樣的指示。而我也特地穿著和服前赴人民大會堂。
駐北京日本大使夫人愉悅的說:「日本代表穿著和服到人民大會堂,還是第一次看到呢。」看來,當時日本的左派,有太過在乎中國的風氣。
在戰爭中學到的事
若要說體驗形成我的人格,戰爭的存在的確是相當大的一部份。現代,人們把人生中的善惡分得過於簡單。雖然每個人都確信,和平比戰爭來得好,但實際上也不盡然如此。
有人因生活中的無聊感到痛苦,也有人為排遣無聊而賭博或與人通姦。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我十三歲那年,夜夜體驗美軍的空襲,過著不知能否活到翌日的生活。因此,和平的定義是很簡單的。即是造出讓每個人都能活到隔日的環境。畢竟在當年的內戰期間,光是去汲水,或是去見個雙親都可能面臨死亡,是很不幸的事。打造生存後的幸福,就是那些人要做的努力。
昭和二十年(西元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我在大田區體驗了東京大空襲。距我家約三百公尺遠的麵包工坊遭到爆彈的直接襲擊,一家九口當場同歸於盡。
只要思及不知能否活到翌日早晨,就令人膽顫心驚。因此我得了炮彈恐懼症,幾乎有一個星期無法開口說話。
死亡、被殺究竟是什麼感覺?戰時,站在右邊五十公分的人被炸死,但站左邊五十公分者卻存活了下來。在那樣的情況下,沒有任何道理。那絲毫之差,牽連著自己無法動搖的命運,了解這樣的事實,就會變得謙虛。
關東大地震(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也是個重大的災難。我無意以死亡人數襯托不幸的程度,然而這不幸是太平洋戰爭無法比較的。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至十日,東京遭到攻勢劇烈的空襲,當晚約有十萬人被燒死。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有人因而失去家人,恐怕連遺體都找不到了。當時沒有DNA鑑定這類的科學,國家也沒有余力在焦黑的屍體堆中辨識身份。
以下是某人說給我聽的故事。一個空襲後的翌日,走在隅田川的橋上時,許多發亮的顆粒隨風拂過橋上而來。那其實是人骨。當時,日本住宅的建材,幾乎沒有不可燃物。畢竟房子盡是木頭和紙。那些建築素材全成了燃料,焚燒著活人。順帶一提,因戰爭災害可獲得國家補償者,除了某些身份特殊的人,一般人都無法獲得補償。聽說,戰死者的家屬、傷兵、從中國撤退回來的士兵、原子核爆的受害者、西伯利亞強制居留者,能獲取少許補償或年金。但我身邊那些家園燒毀的人、父親、兄長或孩子在空襲中受傷的人、財產遭沒收的人,都沒有任何補償措施。
當時的狀況無法像東日本大地震那般,當晚就能配給緊急食物、水;有指定的避難所;有巴士可接送要逃出災區的人們;之後還臨時住宅。東京空襲下的人們是怎麼活下來的?有人暫時躲到友人燒了一半的家;有人在房子燒毀時,揀拾可用的土磚塊,在一旁搭起庇身之處。換言之,他們有如流浪犬似地在焦土茍延殘喘的活著。想必也沒有組織可以對失去雙親的孩子們伸出援手。孩子們只能依賴路過的行人所給予的極少的慈悲,像流浪兒般地生存。
對東日本大地震的災民,我深感同情。但若思及戰爭,現狀擁有的國家、友人、警察軍隊及外國義工團體等的援助,與戰爭的悲慘是不可相比的。畢竟這次震災的情況,除了災區,北海道和中部以西的日本人都能持續過著平日的生活,且有餘力援助他人。而在戰爭期間,任誰都是物資缺乏、貧窮、營養失調,沒有餘力的。
從那年的五月到隔年的二月,我疏散到金澤。雖然東京最猛烈的空襲已暫告一段落,但無法確定是否會有再次的空襲,我無法預知自己的命運。父親因直腸癌動了手術,得以免役,所以戰爭期間我們一家三人都聚在一起。
透過高等女校的介紹,我被動員派至樹脂加工廠當女工,主要製做飛機零件中的絕緣體。十三歲那年,我每天上午七點勞動到傍晚六點,除中午時間稍事休息外,成天勞動。然而,對於生活上的變化,我倒挺樂在其中的。對自己的能力產生信心,原來自己也可以這般地勞動。迄今,面對工場勞動時,我絲毫不會有任何的不安。
戰爭讓每個人都變窮了。不僅頭髮、衣服上長出蝨子,一堆人擠進混濁的浴池裡也是從沒有過的體驗。戰時,大家只能穿上連身式的勞動服。這有兩個意涵。一方面是缺乏物資,一方面是不得穿其他衣服,以免礙了當時戰意高揚的氣氛。無論如何,是自願穿上的。
戰爭結束時,我得到一件華美的棉布洋裝,那是去過上海的日本人送的。然而我沒有機會穿,只覺得若遭空襲燒燬未免也太可惜,因此一直塞在背包裡帶著走。若我拿到甜食,想必也會這麼做。當時,每個人的慾望都是如此,這種想法不足為奇。總之,不至於餓死,也不至於裸身。
第一次發現頭髮長了蝨子,是某次在頭部奇癢時,我戴著工作手套抓癢時發現的。當我看到指頭那邊,手套上的細縫部分有一隻蠕動的蟲子時就知道了。我請工廠裡作業的同事幫我抓蝨子,在那之前,真的很難想像蝨子會存活在自己的頭髮裡。長大的蝨子一經沖洗就會掉落,但產在頭髮裡的蝨卵卻非常棘手。回到東京後,我有一位打扮時髦的阿姨有支燙髮鉗。我請她用那燙髮鉗把附在髮根的卵全都處理掉後,才大大鬆了一口氣。至今都還記得蝨子繁殖旺盛時的慘痛經驗。
最近,我有種想法。體驗過悲慘的底層生活,也是一種財產。現代人一心追求的是奢侈的財富—當然這是很自然的,沒有人會對負債給予好評。不過我們這個世代的每個人,在當時都是負債者。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每個人成長的境遇也各不相同。無論是好的環境或悲慘的生活,都有其教育的意義。
戰時我罹患了砲彈恐懼症,但我從戰爭中學到很多。戰爭是惡的,卻也有教誨的一面。
昭和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三年),新潮社出版了吉田健一翻譯的尼古拉斯的《憤怒之海》(The Cruel Sea)。前些日子,我稍微翻了一下。上、下兩冊,以九號字上下兩段的方式編排,定價兩百五十日圓。
吉田健一是前日本首相吉田茂元的長子,是英文學者。妹妹麻生和子的先生是前首相麻生太郎。
吉田健一氏在這本書的後記寫道:
《西線無戰事》與《戰艦大和之終結》這兩部作品,都在異於常態的戰爭體驗上進行描寫。因戰爭體驗的異常,導致人類的精神產生極大的影響。在那樣的情況下,小說補捉了堪稱為人類精神的光輝。然而,反其道而行的《憤怒之海》實現了另一種,至今在戰爭文學中被遺漏的某種書寫的可能性。它反用了戰爭—使交戰國的全體國民陷入其中的近代戰爭—的性格。面對同樣受到來自戰爭猛烈的衝擊,文中點出團體中每個人不同的反應。以人性的角度理解團體的動向,亦即將那強烈的光線照射在人類的社會生活裡。
以當時的世態,戰爭想必是忌諱之事,且毫無價值可言。畢竟,離戰爭結束還未滿十年。不過,無論是《西線無戰事》或是這本書,我相信,正如吉田所言,有些東西唯有透過戰爭才得以學習,我們不能全面地否定戰爭。這樣的想法在我心中定立了很久,我想這也是幾年後,成為我調查渡嘉敷島的集體自殺、撰寫《一個神話的背景》(後來改題為《沖繩戰.渡嘉敷島「集體自殺」的真相》,由WAC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的動機。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