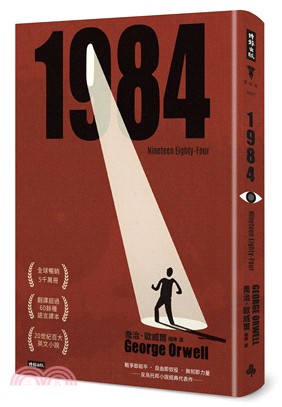商品簡介
全球暢銷5千萬冊
翻譯超過60餘種語言譯本
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
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反烏托邦小說經典代表作
一九八四年,世界劃分為三大超級國家,其中的大洋國,對外,永遠在和另一國打仗;在內,則是人民全都受到嚴密監控,不管是家中各處或是公共場所,到處都設有電屏,「老大哥看著你」。思想警察無所不在,人人互相監視,就連小孩也可以向黨舉報自己的父母思想不正確。
然而,在真理部負責改寫歷史、抹煞過去的黨員溫斯頓.史密斯卻總想了解「真正的」過去,捍衛真理,擁有能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因此,四月晴朗寒冷的一天,當小說部負責維修小說寫作機器的黑髮姑娘茱莉亞主動向他示好,他便決定和她談一場禁忌的婚外情,兩人一起度過了甜蜜的懷舊時光,他們甚至決定加入反黨的組織,兩人義無反顧地向接頭的「內應」宣示叛黨的決心,誰知一切都是精心布置的陷阱……
歐威爾出版於一九四九年的這部反烏托邦小說,既是寓言,也是預言,時至今日讀來,仍然令人戰慄心驚,其中的政治諷喻值得我們深深警惕,缺乏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危險,也令我們反思,在表面開放的今日世界中,內裡是否也暗藏了這樣的政治手段在操控我們的思想,而我們卻不自知呢?
作者簡介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
一九○三年出生於印度,後來搬回英國,一九一七年進入貴族學校伊頓公學就讀,畢業後到緬甸擔任印度帝國警察,這五年的經歷,對歐威爾的人生發展影響至為深遠。
歐威爾離開警察工作之後,就決定成為作家,先是出版了《緬甸歲月》,後來也擔任記者寫作大量報導與評論,因此他的小說讀來像新聞報導一樣,用字精準、條理清晰、發展有力。
他一生窮困潦倒,最早出版的幾部書,並未引起注意。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冷戰開始,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他發表的政治批判小說:《一九八四》、《動物農莊》,才暴得大名。
譯者
楊煉
著名詩人、翻譯家。
一九五五年出生於瑞士,成長於北京,現居倫敦與柏林。
一九八三年,以長詩《諾日朗》轟動大陸詩壇。一九八七年,被中國讀者推選為「十大詩人」之一。作品以詩和散文為主,兼及文學與藝術批評。迄今共出版中文詩集十三種、散文集兩種與一部文論集。作品已被譯成三十餘種外文。
曾獲義大利Flaiano 國際詩歌獎、義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首屆「天鐸」長詩獎、義大利卡普里國際詩歌獎等國際大獎。
名人/編輯推薦
──楊煉
序
無限趨近歐威爾
一九八四年初,我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一號樓一一七室,那個被我命名為「鬼府」的房間牆上,釘上一張一九八四年的布製年曆。這年曆哪兒來的,我全然忘記了。但那畫面倒記得清楚,那是一個澳大利亞原住民,肩頭倚著根長矛,手持一隻回力鏢,坐進一片黃褐相間的空茫,守護著他下面那一年每個為人熟知的日子。
一九八四年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年頭。由於喬治•歐威爾的大作《一九八四》,它早在真正到來之前,就已被寫進(刻進)了歷史。無論在世界哪個角落,也無論大家是否聽說過歐威爾、讀到過他那本書,冥冥之中,似乎早有無數人在等待它,聆聽著它一天天逼近的腳步聲,一個老大哥的世界,跋涉而來,停在門口,跨入屋內,直接抓住我們,這命運毫不留情,甚至不必學貝多芬那樣敲門。
我們都是《一九八四》的一代。中文版的《一九八四》,首先不是用文字,而是用人生寫的。老大哥、真理部新話、一〇一房間等等,既陌生更熟悉,在我記憶裡換名存檔,代替一本書,銘刻下我們稱之為「精神鄉愁」的八〇年代:現實傷痛激發出歷史和文化反思,更進一步,為我們的詩歌寫作找到了人生立足點。
解讀歐威爾的作品,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政治的,思想的,文學的。三個層次層層遞進,在無限趨近歐威爾,直至躍入他剝開的人性淵藪。
一、政治的:意即,批判的。毋庸諱言,這指的是基於二戰和冷戰經驗,對政治專制制度的批判。就如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直接點明的,那具體對象是納粹德國和蘇聯。歐威爾一生窮困潦倒,他最早出版的幾部書,並未引起公眾注意。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不久之後冷戰開始。世界劃分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各自宣稱代表了歷史和人性的正義。這競爭,不僅體現為經濟和軍事,更呈現在思想領域中。正是冷戰語境,使歐威爾相繼發表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迅速獲得了極為具體(過分具體)的解讀,並由此暴得大名。西方讀者和評論界,直接把可見的社會現實「代入」這些作品,由此衍生出一套響亮卻膚淺的理解。歐威爾是個理想主義者,他一生經歷過大英帝國殖民地統治、英國貴族學校的階級歧視、在緬甸殖民地當警官、參與西班牙內戰等,由此訓練出高度的政治敏感,他當然不可能忽略冷戰開始時世界上的現實,任何對人的控制、對人性的摧殘,都是他反思的對象,而他的反思,又正是一種反抗的行動。《動物農莊》中憤起造反,終於又淪為新的奴隸的動物;《一九八四》中勇敢反叛,卻最後在靈魂裡被徹底毀滅的溫斯頓和茱莉亞,恰恰是歐威爾政治的——批判的形象代言人,他們的反抗是一種悲劇,但悲劇的反抗也是反抗,至少在他們決定反叛的一刹那,迸發出了一道覺醒的奪目光芒。因此,歐威爾的政治批判性,聚焦於那種由人建立,卻異化為非人(甚至反人類)的政治制度,他對此的態度毫不妥協。這構成了他創作中第一個層次。
二、思想的:掙脫任何群體思維,真正獨立思考和堅持全方位批判。只有可悲可怕的思維惰性和簡單化,會把歐威爾的思想意義,局限於一名所謂的冷戰作家。那同樣意味著,把他的作品貶低為宣傳工具式的小冊子。我們的老朋友、著名漢學家、作家西蒙•萊斯(Pierre Ryckmans,中文名:李克曼)評論歐威爾時,把他的文章命名為「政治的恐怖」,這裡第一層意思是政治壓迫本身的恐怖,更深一層則是,把一切簡化為政治的恐怖。他把歐威爾的思想主題,表述為「反極權主義」,這要準確、深刻得多。極權主義是一種社會型態,更是一種思維方式,它不受限於某個政治或地理概念,而是存在於一切人類社會中。在歐威爾生活和寫作的二十世紀五〇年代,這一點或許還不甚清晰,幸好,歷史也拒絕停滯,冷戰結束後,人類突然面對了一個叫作全球化的更深困境。冷戰時期的意識型態群體劃分、非黑即白的標語口號,一夜間統統失效。今天這時代,權力和金錢無所不在地緊密糾纏,迫使人類從價值混亂淪入精神真空,再墮落到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和玩世不恭。歐威爾用《動物農莊》、《一九八四》剖析的看得見的極權暴力,被兌換成了今天看不見的極權思維,當代老大哥長著權錢一體的面孔,既從外部系統控制,更滲透進世人的內心甚至潛意識的欲望,從那裡操控著人類,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同一場精神汙染的遊戲。我們誰不是目睹這個見眼前利益就抓的瘋狂世界而無可奈何?歐威爾早在近七十年前,就已經寫下了一部當代精神病理學的教科書。他的深度,體現在《一九八四》那個荒誕而真實的結尾上——「他戰勝了自己,他愛老大哥」,反叛者溫斯頓最終投入了老大哥的懷抱(成為老大哥的一部分),這精神毀滅的「喜劇」,遠比肉體毀滅的悲劇慘痛一萬倍。而環顧全球化時代,到處在肆無忌憚地利益洗腦,走投無路的人,是不是也都戰勝了自己,全心全意愛上了老大哥?甚至在爭當老大哥?歐威爾的噩夢,不僅成真,且無孔不入地深深進入每個人的內心,他地下有知,該會發出怎樣的一絲苦笑?
三、文學的:塵埃落定,歐威爾寫的是小說,一切思考,最終都要落實到文學上——就是說,小說的語言、形式、觀念上。歐威爾是思想大家,更是小說大師,他最鋒利的思想,注入、激發出了最新穎鮮活的小說創作,並因此如一潭深泉,能讓一代代讀者不停從中汲取著滋養。
歐威爾的語言特色,一言以蔽之:精確,清晰,有力。讀他的小說,常常使人感覺像讀一篇新聞報導,細節精準貼切,發展充滿動力,線索毫無雜亂,層次遞進分明。這樣的語言功力,既得益於他早年的記者經歷,也得承認,他深惡痛絕的伊頓公學貴族教育,也從旁助力不少。英語一如中文,語法靈活,可玩可弄,因此入門容易,精深極難,要讓語言純淨而又充滿節奏,全憑作家心、手、耳相通,讓被「聽到的」語言能量,引領筆下寫出的句子。因為有這種精準,所以他敢於抗衡讀者的惰性(和商業化的花稍),而在《一九八四》這部長篇中,僅用三大章的清晰結構,就一氣呵成地把握住全部內在線索,何其簡潔而有力,相比之下,有些譯本把全書拆解分章、加小標題,則不免稍有蛇足誤導之嫌。
歐威爾的小說,常被人提及的是《動物農莊》、《一九八四》,其實,此外還有一部被他作為《一九八四》附錄的論文,標題是〈附錄:新話之道〉。這三部作品,文體截然不同。《動物農莊》是寓言故事,《一九八四》是政治幻想小說,〈附錄:新話之道〉是一篇(貌似)語言學的論文。但如此不同的文體,卻恰恰都是「小說」——在充分開放、豐富的虛構文學理念上。《動物農莊》裡那些孩子熟悉的豬啊狗啊、馬呀鳥呀,依然被描寫得活靈活現,彷彿和給孩子睡前朗誦的其他故事並無二致,但這裡講述的,卻是怎樣一個噬人的噩夢?《一九八四》三大章,結構緊湊如一部中篇小說,其中寥寥可數的人物,每個都滿滿負載著思想,而他們的交錯、相遇、結合、分離,又如此絲絲入扣,情節描寫時動人心旌,懸念緊張如偵探電影,而整部作品的思想推力,則像一張鋼製的邏輯網,張開在人物的內心裡,不停迫近那個哀莫大於心死的「喜劇結局」。歐威爾的創作中,《一九八四》是唯一一部尋常意義上的「小說」,不過,別擔心,幸好還有那部讓它立顯獨特的〈附錄:新話之道〉。
我把〈附錄:新話之道〉作為一部小說創作單獨提出,因為它把歐威爾的小說實驗理念推到了極致。這篇不算長的文章,貌似語言學論文,探討的內容,卻是基於《一九八四》虛構世界的「新話」——一種刻意透過縮減詞彙量而剝奪思想能力的極權語言。這篇文章,堪稱一篇「話語專制」的自白。它透過解析「新話」中ABC詞類的造詞法和用法,詳細闡述了到二〇五〇年人類終將淪入的語言——思想空白的全過程。精彩的是,這篇荒誕得沒來由的「學術」論文,基於虛構、參與虛構,更直抵《一九八四》的虛構核心:深入一種虛構語言的極權本質。由此,它文體上離虛構越遠,反而越深入,打開了小說觀念,一件「作品」,一種真正的文學創造物。歐威爾用〈附錄:新話之道〉,給他的小說三部曲壓軸,從寓言、故事、論文層層推進,直至推出這部極權思維的詞典。一座自覺、有機的文學巨廈,就這樣矗立在我們面前。
歐威爾的小說,是哲學也是文學,是文學卻更飽含哲思。從他寫作之時至今,我覺得,這些作品裡,不停上演著一場詭譎的時間魔術。其中,《動物農莊》發表於一九四五年,《一九八四》發表於一九四九年,對那時而言,一九八四還是地平線那邊遙遙眺望的未來,而他小說裡的所有時態,卻全是事件已然發生的過去完成式。儘管過去完成式是傳統西方小說的常用時態,但用在標明確切日期的《一九八四》上,仍不得不說是對讀者心理的一大挑戰,造成的裂變,足以令人關注、深思其中內涵。隨時間推進,當我在「鬼府」裡掛起一九八四年曆,一九八四的世界,已經結束了漫長的逼近過程,成了我們自身的一部分。文本的過去式,兌換為人生的現在式。從那時再推進到二〇一八年,當我翻譯完歐威爾的作品,那個近七十年前寫下的過去完成式,已被理順得再自然不過了。我們的人生,在不停翻譯歐威爾,多好的巧合啊,這正是中文的時間!我們動詞的非時態性,讓一旦發生的事,就不得不無盡發生下去。由是,歐威爾小說的中文譯文,終於掙脫了現實的捆綁,它一舉還原成了思想本身,或者說是一首詩,宛如屈原寫下的、但丁寫下的,一首古今中外、人類的、人性的、命運、之詩。
一九八四年,當我把那張年曆掛進「鬼府」,從來沒想過,有朝一日我會出國,更沒想到,重譯歐威爾小說的重任,竟會落到我這個當年的英語文盲頭上。好在,剛剛過了的漂泊三十周年紀念日,印證了一段不期而來的人生。沿街「侃」出來的英文(我戲稱為「楊文」——Yanglish),逼著我習慣了逆流而上。而一切之上最重要的,仍是歐威爾的思想和文學力量,不僅沒隨著冷戰結束而褪色,恰恰相反,正對全球化時代的精神蒙昧,發動一次新衝擊。所謂經典,就是指這涵蓋時間、保持鋒利的能力吧?
到現在,當我告訴我的西方朋友,我正在翻譯歐威爾時,對方的反應幾乎都一樣,都是瞪大了眼睛問:「中國能出版歐威爾?」嘿嘿,他們哪裡知道,四十年前,董樂山先生的歐威爾譯文,就已經是我們這一代文學青年的啟蒙讀物了。但,也只在今天,當我坐下,開始一詞詞、一句句翻譯,才發現四十多年前,我們讀到的,最多只能算歐威爾的二手,甚或三手貨。最早的譯者,或許憂慮彼時讀者的理解水準,出於好意,給歐威爾漂亮精美的原文醇酒,兌進了不少中文翻譯文體的白開水,令細究之下,許多句子彎來繞去,拗口囉嗦。而無故添加的十六個細分章節和小標題,更打碎了歐威爾的一氣呵成。還不說全書的有機部分〈新話之道〉,乾脆被留在了書外……所以,我希望這版譯文,盡力還原出一個「中文原版的歐威爾」,結構上,完全遵循歐威爾的思想遞進層次;文體上,讓三部作品各自展示全然不同的個性;語言上,用精確、清晰、有力三原則要求譯文,讓歐氏美學奏響中文的音樂。當然,這些期望,能完成多少,還須讀者、專家給予評定。
老話云:愛之深,痛之切。翻譯完歐威爾全部小說,我對他的概括只能是:一個原版的理想主義者。對人類寄以最深的期望,因而率先躍入人性的深淵,去探測那企圖毀滅我們的黑暗之力。這又讓我想起李克曼,當我們一九八八年到達澳洲雪黎後,一次在他家聚會,問起他最近的工作,竟聽他說:「我在翻譯孔子的《論語》。」「什麼?」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為什麼翻譯《論語》?」「因為它好啊!理解人生好,書寫文筆好,應該有好譯本。」——哈,這就叫大家胸懷!
楊煉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目次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附錄 新話之道
譯後記 無限趨近歐威爾
書摘/試閱
第一章
那個四月天,又亮又冷,時鐘噹噹響了十三下。溫斯頓•史密斯躲著寒風,縮緊脖子,快快溜進勝利大廈的玻璃門,儘管動作不怎麼敏捷,沒能阻止一陣塵土追著他刮進門來。
門廳裡一股熬白菜和腳踏墊的味道。那頭牆上,釘著一張彩色海報,對掛在屋裡來說太大了。畫上是一張巨大的臉,寬度超過一公尺:那是張大約四十五歲左右的男人面孔,蓄著濃密的黑八字鬍,外表粗獷而英俊。溫斯頓走向樓梯,用不著試電梯。就算一切順利的時候,電梯也是很少開的。現在白天停電,這是為籌備仇恨週而實行節約的一部分。溫斯頓住在七樓,他三十九歲,右腳踝上部有靜脈曲張性潰瘍,他慢慢向上爬,停歇了好幾次。每一層樓,迎著電梯門的牆上,都有那張帶巨大臉龐的海報盯視著。這屬於那類圖畫,不管你走到哪兒,畫面上的目光總追著你。它下面一行標題:老大哥看著你。
在他住處裡,一個洪亮的嗓音念著一串和生鐵產量有關的數字。聲音來自一塊毛玻璃似的長方形金屬板,它構成右側牆壁的一部分。溫斯頓扭了一下開關,聲音小了些,但仍能聽清說的每個字。這個設備(它叫電屏)可以調低音量,但不能完全關掉。他走到窗口:那瘦小纖弱的身材,被藍色工作服——黨員制服——襯著,更凸顯出單薄。他的頭髮淡金色,臉色天生紅潤,他的皮膚有點粗,那是被粗肥皂和鈍刀片以及剛過去的寒冬整的。
窗外,即使透過關緊的玻璃窗,世界看起來也寒意凜冽。下面街道上,陣陣小旋風捲著塵土和紙屑的螺旋,雖然陽光明亮,天空湛藍,但除了到處張貼的海報,別的一切看起來全無顏色。那張蓄著黑鬍鬚的臉從每個上方炯炯俯視。這房子正對面就有一張。老大哥看著你,標題說。此刻那雙黑眼睛直視著溫斯頓的眼睛。下面街上還有另一張海報,撕破了一角,被風吹得啪啪作響,輪番蓋住又掀開,露出一個單詞「英社」。更遠處,一架直升機掠過屋頂,綠頭蒼蠅似的逡巡了一會兒,又轉個彎飛去。那是警備巡邏隊,在窺察居民的窗戶。然而,巡邏隊還不算可怕,思想警察才可怕。
溫斯頓身後,電屏的聲音仍喋喋不休放送著生鐵產量和超額完成第九個三年計畫的情況。電屏能同時接收和發送。溫斯頓弄出的任何聲響,只要超過極低的耳語一點兒,都會被它捕捉到,而且,只要他在那塊金屬板的視野內,他的一切舉動都會被看到和聽到。當然,沒法知道,在某一特定時刻你是否被監視著。思想警察何時、用什麼系統監控某人,你就猜吧。甚至能想像,他們時時刻刻盯著每個人。只要他們願意,隨時能接通你的線路。你不得不讓習慣變成本能,活在——徹徹底底就活在這個假設裡:你的每個聲響,都有人偷聽;你的每個動作,都被人監視,除非隱在黑暗中。
溫斯頓繼續背對電屏。這比較安全。雖然他也很清楚,就連背後也能洩密。一公里開外,真理部的雪白大樓高聳於陰暗市景之上,那是他工作之處。這,他帶點模糊厭惡地想——這就是倫敦,一號空降區的首要城市,一號空降區是大洋國第三大省。他試著擠出些許童年記憶,能告訴他倫敦是不是一直這樣。這些朽敗的十九世紀房子始終在這裡?木頭撐著歪牆,硬紙板釘補著窗戶,波紋鐵皮蓋住屋頂,髒亂不堪的花園圍牆倒向四面八方。還有粉塵漫捲、破磚亂瓦間雜草叢生的空襲地帶;還有炸彈清空的大片曠野裡,忽然冒出一堆堆雞籠子似的骯髒木屋。但是不行,他想不起來:除了一串沒有背景、閃閃爍爍、模模糊糊的畫面,他的童年什麼也沒剩下。
真理部——真部,新話這麼說——和視野裡其他一切都迥然有別。它有個碩大的金字塔結構,晶亮的白色水泥沖天而起,平臺疊著平臺,直上三百公尺高空。從溫斯頓立足之處,正好能看到那白色牆面上用漂亮字體寫下的黨的三句口號:
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無知即力量
據說,真理部大樓在地上有三千房間,對稱於地下的相等結構。在倫敦別處,還坐落著另外三座建築,外觀和規模與此類似。因此,從勝利大廈屋頂上,你可以同時看見把周圍建築壓成侏儒的四座龐然大物。它們把整個政府機構分為四部。真理部主管新聞、娛樂、教育、藝術。和平部主管戰爭。友愛部維繫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負責經濟事務。用新話說,它們的名稱是:真部、和部、愛部、富部。
真正可怕的是友愛部。它通體沒有一扇窗戶。溫斯頓從來沒到友愛部裡面去過,也從未踏進它半公里以內。這非公莫入的地帶,要進去得穿過重重鐵絲網、鋼門、隱蔽的機槍陣地。甚至在通向它外部障礙的大街上,也遊曳著身穿黑制服、裝備了連環警棍的凶神惡煞的警衛。
溫斯頓猛轉過身來。他讓臉上現出一片祥和樂觀,面對電屏時,最好穿戴上這表情。他橫穿房間,進了小廚房。在一天的這個時間離開真理部,他得犧牲掉食堂裡的午飯,他知道廚房裡沒什麼吃的,只有一塊烏漆抹黑的麵包,那是省下來給明天當早飯的。他從架子上拿下一瓶無色液體,上面有張簡單的白色標籤:勝利杜松子酒。它有一股讓人難受的油耗味,像中國黃酒似的。溫斯頓倒出差不多一滿茶盅,壯了壯膽,喝藥似的一仰脖吞了下去。
他的臉頓時脹紅了,眼裡流出淚水。這東西像硝酸,而且,喝下時,人會感到後腦勺上像挨了一下橡皮棍。不過,接著他胃裡燒心的難受減退了,世界看起來開始較為歡快了些。他從一個壓癟了的勝利牌香菸盒裡抽出一支菸來,沒注意豎著拿了,菸絲立刻掉到了地板上。再拿第二支,這次比較成功。他回到了起居室,坐在電屏左邊一張小桌旁。他從桌子抽屜裡拿出一支筆桿,一瓶墨水,一個空白的四開厚筆記簿,紅色封底,大理石花紋的封面。
不知為什麼,起居室電屏的位置不同一般。按照常見方式,它該安裝在頂端牆上,那就可以環顧整個房間,但它卻安在了側牆上,對著窗戶。電屏的一邊,有個淺淺的壁龕,溫斯頓就在這兒坐著,當初建造房子時,這個壁龕可能是準備放書架的。溫斯頓坐在壁龕裡,儘量往後縮,可以處在電屏監控範圍之外,但這僅就視覺而言。當然,他還能被聽見,但只要他待在現在的位置,電屏就看不到他。部分是因為這房間與眾不同的布局,促使他想到做此刻要做的那件事。
但這也是剛從抽屜裡拿出的筆記本激發他想做的事。這是本非常漂亮的本子。柔和光潔的紙張,因時間久遠而稍許發黃,這類紙張至少已停產四十多年了。他能猜想,這本筆記本比那還老得多。他在本市某個破敗街區一家邋裡邋遢的小舊貨店櫥窗裡看見它的。究竟哪個街區,他全然忘了,但他一眼瞥見,擁有它的欲望瞬間湧起。黨員照說不該進入普通店鋪(那是「黑市生意」),不過這紀律執行得並不嚴格,因為諸如鞋帶、刀片之類不少東西,沒別的辦法能夠弄到。他迅速掃視了街道兩頭,然後溜進小店,花兩塊五買下了本子。那時並不知要用它做什麼。他把它塞進公事包,帶著負罪感回了家。有這麼個本子已經夠令人起疑了,即便那上面一個字也沒寫。
他要做的事是開始寫日記。這並不違法(沒有違法一說,因為早就沒什麼法律了),但如果被查出來,可以十拿九穩地確信,他將被判處死刑,或至少發配勞改營幹苦役二十五年。溫斯頓把筆尖插上筆桿,吮了一下,吸掉上面的油脂。這種蘸水筆也是老貨了,連簽名也很少用,他好不容易才偷偷買到一支,只因為覺得那麼精美雪白的紙頁,只配讓真正的筆尖去書寫,而不能用墨水鉛筆亂抹胡劃。事實上他已不習慣手寫了。除了那些小小的短便條,通常一切全用聽寫器口授。這對他此刻想幹的事,當然行不通。他蘸了蘸墨水,躊躇片刻。一陣震顫掃過他的腸子。寫第一筆是個決定性的行動。用細小拙笨的字體,他寫下: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身子向後一靠。一種徹底無助的感覺擊中了他。首先是,他簡直沒把握,這究竟是不是一九八四年。一定八九不離十,因為他應該能確定自己的年齡是三十九歲,他可以肯定自己出生於一九四四或一九四五年;但現如今,已絕不可能注明任何日期,而不誤差一兩年。這日記為誰而寫?這也突然令他生疑。為未來、為後代。他的頭腦在紙上那個可疑的日期上徘徊了一會兒,忽然跳出一個新話裡的字詞:「雙重思想」。他頭一回領悟了他要做的事情極其艱鉅。你怎麼和未來溝通呢?就其本質來說,那是不可能的。要是未來類似於現在,它壓根不會聽他的,而要是未來與現在不同,他經歷的困境則毫無意義。
有一會兒,他呆坐在那裡瞪著本子。電屏轉換成刺耳的軍樂了。奇怪的是,他似乎不止喪失了表達自己的力量,甚至忘記了原本想說什麼。過去好幾個星期,他都在為這一刻做準備,他從來不曾想到,做這事除了勇氣還需要什麼。真寫起來應該不難。他只要把多年來腦袋裡不停歇的不安獨白訴諸筆墨就行。但現在,就連獨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靜脈曲張又開始難忍的搔癢。他不敢抓它,因為一抓就會發炎。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他面對著眼前這頁紙的空白,腳踝上皮膚搔癢,音樂喧囂,杜松子酒的些微醉意,喪失了意識。
突然他開始慌亂地寫起來,只約略知曉寫了些什麼。他那纖小而孩子氣的筆跡在紙上踉踉蹌蹌,先略去了大寫字母,最後連句號也省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晚去看電影。全是戰爭片。一部非常好,關於一艘滿載的難民船,在地中海某處遭到空襲。觀眾被一個想游泳逃開追他的直升機的大胖子鏡頭逗樂了,起初你看見他像頭海豚在水裡浮沉,接著從直升機瞄準鏡裡看到他,再後來他渾身槍眼,周圍海水一片殷紅,他猛地沉下去,就像槍眼吸進了海水似的,觀眾看到他沉沒時歡笑著叫好。然後你看見一條裝滿孩子的救生艇,頭上一架直升機在盤旋。一個可能是猶太人的中年婦女,坐在船頭懷抱一個大約三歲的小男孩。小男孩嚇得哇哇大哭,把腦袋塞在她胸前就像要鑽進她似的,而女人摟著他安慰他,儘管她自己也嚇得臉色發青,她一直拚命護著他好像雙手能為他擋住子彈。然後直升機朝他們中間扔了一顆二十公斤的炸彈,現出可怕的閃光,救生艇崩裂成碎片。接下來一隻孩子的手臂向上上上直上到空中的精彩鏡頭一定有一架攝影機裝在直升機頭上追著手臂拍黨員座中響起一片掌聲但劇場無產座中一個女人突然吵嚷起來說他們不該在孩子面前放這部電影他們當著孩子面這麼做是不對的直到員警趕來把她帶走我想她不至於有什麼事沒人在乎無產者說什麼典型的無產者反應他們絕不……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