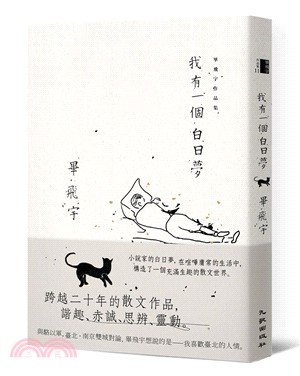商品簡介
與駱以軍,臺北.南京雙城對論,畢飛宇說:「我喜歡臺北的人情。」
畢飛宇寫散文,把自己放入日常生活細節,再喧譁、再無事也妨礙不了一個小說家的白日夢。即使是有關寫作、閱讀的記敘與思考,亦多是文字背後的生活場景,通曉世俗人情的姿態,構造了細微鮮明的散文特質。
回望童年與成長,「時間」是畢飛宇童年最大的敵人,害怕過不完的夏季午後,害怕沒完沒了的夏日黃昏。他直視成長的窘困,幽默自嘲一事無成的人格外敏感,拉風的長髮裡頭蕩漾著九流詩人自慰般的快感與玄幻。最終他放棄哲學、放棄了詩,在〈恰當的年紀〉中寫下:我四十三歲了,寫《推拿》使我已經體會到了和小說中的人物心貼心所帶來的幸福。〈自述〉裡說:「我喜歡許多東西,其中有一樣叫關係」,在與駱以軍的「南京.臺北.我」裡,畢飛宇寫的正是〈我與我的南京〉、〈我與臺北〉的雙城關係,是臺北人的暖心,南京人的淡定,是喜歡臺北的人情,也明白南京人多大的事都不算事。
畢飛宇說:散文主要靠你和生活的關係,要去感受和判斷,它離作者特別近,所以你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它會將你全部暴露出來。透過本書,直擊小說家中的思想家――畢飛宇,跨越二十年的散文作品,諧趣、赤誠、思辨、靈動。
作者簡介
一九六四年生於江蘇興化。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曾任教師,後從事新聞工作。八○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他的文字敘述鮮明,節奏感掌握恰到好處。曾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百花文學獎、郁達夫文學獎、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中國小說學會獎等。
著有《玉米》、《青衣》、《平原》、《造日子》、《推拿》、《小說生活──畢飛宇、張莉對話錄》、《大雨如注》、《充滿瓷器的時代》、《相愛的日子》等書。
目次
輯一 我能給你的只有一聲吆喝
三十以前
我家的貓和老鼠
歌唱生涯
我的野球史
人類的動物園
飛越密西西比
寫滿字的空間是美麗的
一支菸的故事
這個字寫得好
我能給你的只有一聲吆喝
輯二 我有一個白日夢
自述
幾次記憶深刻的寫作
誰也不能哭出來
談藝五則
寫一個好玩的東西
我有一個白日夢
《平原》的一些題外話
《推拿》的一點題外話
恰當的年紀
情感是寫作最大的誘因
我和我的小說
中篇小說的「合法性」
輯三 像我這樣的一個作家
作家身份、普世價值與喇叭褲
手機的語言
記憶是不可靠的
地域文化的價值傾向
文學的拐杖
文人的青春——文人的病
輯四 我和我的朋友
好看的憂傷
青梅竹馬朱燕玲
上海的向黎靜悄悄
王彬彬斷想
輯五 南京.臺北.我—畢飛宇VS.駱以軍
南京
臺北
閱讀
寫作
書摘/試閱
歌唱生涯
是哪根筋搭錯了呢?一九九○年,我突然迷上唱歌了。
一九九○總是特殊的,迷惘突然而至,而我對我的寫作似乎也失去了信心。可我才二十六歲,太年輕了,總得做點什麼。就在那樣的迷惘裡,我所供職的學校突然搞了一次文藝匯演,匯演行將結束的時候,我的同事,女高音王學敏老師,她上臺了。她演唱的是《美麗的西班牙女郎》。她一開腔就把我嚇壞了,這哪裡還是我熟悉的那個王學敏呢?禮堂因為她的嗓音無緣無故地恢宏了,她無孔不入,到處都是她。做為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鄉下人,我得承認,這是第一次在現場聽到所謂的「美聲」,我不相信人類可以有這樣的嗓音,想都不敢想。
我想我已經蠢蠢欲動了。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我悄悄來到了南京藝術學院,我想再考一次大學,專業就是聲樂。我想讓我的青春重來一遍。說明情況之後,南藝的老師告訴我,你這樣的情況不能再考了。我不死心,又來到了南京師範大學的音樂系,得到的回答幾乎一樣。我至今都能記得那個陰冷的下午,我站在南京師範大學東門的草坪上,音樂系的琴房離我並不遙遠,不時飄過來一兩句歌聲。那些歌聲像飛鏢一樣,嗖嗖的,全部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一邊流血一邊遊蕩,我喑啞的一生就這樣完蛋了。
可我並沒有死心。終於有那麼一天,我推開了王學敏老師的琴房。王學敏老師很吃驚,她沒有料到一個教中文的青年教師會出現在她的琴房裡,客氣得不得了,還「請坐」。我沒有坐,也沒有繞彎子,直接說出了我的心思,我想做她的學生。
我至今還記得王學敏老師的表情,那可是一九九○年,學唱歌毫無「用處」,幾乎吃不上飯。要知道,「電視選秀」還要等到十五年之後呢。她問我「為什麼」,老實說,我答不上來。
如果一定要問為什麼,我只能說,在二十歲之前,許多人都會經歷四個夢:一是繪畫的夢,你想畫;一是歌唱的夢,你想唱;一是文學的夢,你想寫;另一個則是哲學的夢,你要想。這些夢會出現在不同的年齡段裡,每一個段落都很折磨人。我在童年時代特別夢想畫畫,因為實在沒有條件,這個夢只能自生自滅;到了少年時代,我又渴望起音樂來了,可一個鄉下孩子能向誰學呢?又到哪裡學呢?做一個鄉下的孩子沒有什麼可抱怨的,然而,如果你有過於亢奮的學習欲望,你的求知欲只能是盛夏裡的狗舌頭——伸出你的舌苔,空空蕩蕩。
謝天謝地,王學敏老師還是收下我了。她打開她的鋼琴,用她的指尖戳了戳中央C,是1,讓我唱。說出來真是丟人,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更別說怎麼唱了。王老師對我失望之極,她的眼神和表情都很傷我的自尊。古人說「不恥下問」,是這樣的。
聲樂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開」,所謂打開,你必須借助於你的腹式呼吸,——只有這樣你的氣息才有力量。王老師告訴我,嬰兒在號哭的時候用的就是腹式呼吸,狗在狂吠的時候也是這樣。但人類文明的進程就是一個節省體力的過程,因為「說話」,人類的發音機制慢慢地改變了,胸腔呼吸慢慢暢通了,腹式呼吸卻一點一點閉合了。這是對的,想想看,兩個外交官一見面,彼此像狗一樣號叫,那成什麼樣子?高級的對話必須輕聲細語的,「見到你很高興」,「見到你我也很高興」,這才像樣。——「汪!」,——「汪汪!」什麼也談不成的。唉,這就是「做人」的代價,像甘蔗,長得越高越沒滋味。
可我已經用胸腔呼吸了二十六年了,要改變一個延續了二十六年的生理習慣,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老師不厭其煩,一天又一天,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她一遍又一遍地給我示範,我就是做不到。王老師也有按捺不住的時候,發脾氣,她會像訓斥學生那樣拉下臉來。我自己也知道的,我早就過了學聲樂的年紀了,是我自己要學的,人家也沒有逼我,除了厚著臉皮,我又能有什麼辦法?
每天起床之後,依照老師的要求,我都要做一道功課,把脖子仰起來,唱「泡泡音」。——這是放鬆喉頭的有效方法。除了唱「泡泡音」,放鬆喉頭最有效的方法是什麼呢?睡眠。可是,因為寫作,我每天都在熬夜。王老師不允許我熬夜,我大大咧咧地說:「沒有哇。」王學敏把她的兩隻巴掌丟在琴鍵上,「咚」地就是一下。王老師厲聲說:「再熬夜你就別學!」後來我知道了,謊言毫無意義,一開口老師就知道了,我的氣息在那兒呢。我說,我會盡可能調整好。——我能放棄我的寫作麼?不能。這件事讓我苦不堪言。
如果有人問我,你所做過的最為枯燥的一件事情是什麼,我的回答無疑是練聲。「練聲」,聽上去多麼優雅,可文藝了,可有「範兒」了,還浪漫呢。可說白了,它就是一簡單的體力活。就兩件事:咪,嘛。你總共只有兩個樓梯,沿著「咪」爬上去、爬下來,再沿著「嘛」爬上去、爬下來。咪、咪、咪,嘛、嘛、嘛;咪——,嘛——;咪——嘛——。還挨駡。我這是幹什麼呢?我這是發什麼癔症呢?回想起來,我只能說,單純的愛就是這樣,投入,忘我,沒有半點功利,就是發癔症。
王學敏老師煞費苦心了。她告訴我,「氣」不能與喉管摩擦,必須自然而然地從喉管裡「流淌」出來。她打開了熱水瓶的塞子,她讓我盯著瓶口的熱氣,看,天天盯著看。為了演示「把橫膈膜拉上去」,她找來了一只碗,放在水裡,再把碗倒過來,讓我往上「拉」,這裡頭有一種等量的、矛盾的力量,往上「拉」的力量越大,往下「拽」的力量就越大。是的,藝術就是這樣,向上取決於向下。上揚的力量有多大,下沉的力量就有多大。老實說,就單純的理解而言,這些都好懂。我能懂。我甚至想說,有關藝術的一切問題都不複雜,都「好懂」——這就構成了藝術內部最大的隱祕:在「知識」和「實踐」之間,在「知道」和「做到」之間,有一個神祕的距離。有時候,它是零距離的;有時候呢,它足以放得進一個太平洋。
小半年就這樣過去了,我還是沒有能夠「打開」。我該死的聲音怎麼就打不開呢?用王老師的話說,我的聲音「站不起來」。突然有那麼一天,在一個刹那裡頭,我想我有些走神了,我的喉頭正處在什麼位置上呢?王老師突然大喊了一聲:「對了對了,對了對了!」我嚇了一跳,怎麼就「對了」的呢?再試,又「不對」了。
按照王老師的說法,有一件事情是毫無疑義的,二十六年前,當我第一次號哭的時候,我的聲音原本是「打開」的,而現在,我在琴房裡,一遍又一遍地,我所尋找的無非是我身體內部的那一條「狗」。我們身體的內部還有什麼?誰能告訴我?
哪有不急躁的初學者呢。初學者都有一個不好的心態,不會走就想跑。我給王老師提出了一個要求,想向她學唱「曲子」。王老師一口回絕了。根據我的特殊情況,王老師說:「先打兩年的基礎再說。」這句話讓我很絕望,我是學唱歌來的,一天到晚「咪咪咪嘛嘛嘛」,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夜深人靜的時候,我一個人來到了足球場。它是幽靜的,漆黑、空曠,在等著我。我知道的,雖然空無一人,但它已然成了我的現場。我不誇張,就在這樣一個漆黑而又空曠的舞臺上,每個星期我至少要開三個演唱會。學生宿舍和教工宿舍離足球場不遠,我想我的歌聲是可以傳過去的,因為他們的聲音也可以傳過來。傳過來的聲音是這樣的——
「他媽的,別唱了!」
別唱?這怎麼可能。唱過歌的人都知道一件事,唱得興頭頭的,你讓他不唱他就不唱了?開玩笑。告訴你,一個人一旦唱「開」了,那就算打了雞血了,那就算鉚足了發條了。刀架在脖子上都不眨眼的。士可辱,不可不唱。
可我畢竟又不是唱歌,那是斷斷續續的,每一個句子都要分成好幾個段落,還重複,一重複就是幾遍、十幾遍。練習的人自己不覺得,聽的人有多痛苦,不要想也知道的。不遠處的宿舍一定被我折磨慘了——誰能受得了一個瘋子深夜的騷擾呢?可有一個祕密他們一定不知道,那個瘋子就是我。
事實上,我錯了。這不是祕密。每個人都知道。老師們知道,同學們也知道。我問他們,你們是怎麼知道的?一個來自湖北的女生告訴我,這有什麼,大白天走路的時候你也會突然撂出一嗓子,誰不知道?就你自己不知道。
——「很嚇人的畢老師。」
——「我們都叫你『百靈鳥』呢。」
我不怎麼高興。我這麼一個成天板著面孔的人,怎麼就成「百靈鳥」了呢?一天夜裡我終於知道了。王學敏老師有一個保留節目,《我愛你,中國》,第一句就是難度很大的高音——「百靈鳥從藍天飛過」。我也想學著唱。夜深人靜,當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百靈鳥」的時候,嗨,我可不就是一隻百靈鳥麼。
寫到這裡我其實有點不好意思,回過頭來看,我真的有些瘋魔。我一個當老師的,大白天和同學們一起走路,好好的,突然就來了一嗓子,無論如何這也不是一個恰當的行為。可我當時是不自覺的,說情不自禁也不為過。難怪不少學生很害怕我呢,除了課堂和操場,你根本不知道那個老師的下一個舉動是什麼,做學生的怎麼能不害怕呢。我要是學生我也怕。
一年半之後,也就是一九九二年的十月,我離開了南京特殊師範學校,到《南京日報》去了。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我的歌唱生涯到此結束。我提了一點水果,去琴房看望我的王老師。王老師有些失望。她自己也知道,她不可能把我培養成畢學敏的,但是,王老師說:「可惜了,都有些樣子了。」
前些日子,一個學生給我打來電話,我正在看一檔選秀節目,附帶著就說起了我年輕時候的事。學生問:「如果你是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你會不會去?」我說我會。學生很吃驚了,想不到他的「畢老師」也會這樣「無聊」。這怎麼就無聊了呢?這一點也不無聊。事情往往就是這樣,不經歷「難以自拔」的人永遠也不能理解,有些人來到這個世界就是為了發出聲音的。我喜愛那些參加選秀的年輕人,他們的偏執讓我相信,生活有理由繼續。我從不懷疑一部分人的功利心,可我更沒有懷疑過發自內心的熱愛。年輕的生命自有他動人的情態,沉溺,旁若無人,一點也不絕望,卻更像在絕望裡孤獨地掙扎。
二十三年過去了,我再也沒去王老師的琴房上過一堂聲樂課。說到這裡我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其實並沒有學過聲樂,充其量也就練過一年多的「咪」和「嘛」。因為長期熬夜,更因為無度吸煙,我的嗓子再也不能打開了。拳離了手,曲離了口,我不再是一條狗了,我又「成人」了。我的生命就此失去了一個異己的、親切的局面。——那是我生命之樹上曾經有過的枝丫,挺茂密的。王老師,是我親手把它鋸了,那裡至今都還有一個碗大的疤。
寫滿字的空間是美麗的
我小學就讀於一所鄉村學校,而我的家就安置在那所學校裡頭。學校有一塊操場,還有三面用土基圍成的圍牆。一到寒假和暑假,那塊操場和三面圍牆就成了我的私人筆記本了。我的手上整天拿著一隻粗大的鐵釘,那就是我的筆,我用這支筆把能寫字的地方全寫滿了。有一次,我用一把大鐵鍬把我父親的名字寫在了大操場上,我滿場飛奔,巨大的操場上只有我父親的名字。父親後來過來了,他從他的姓名上走過的過程中十分茫然地望著我。我大汗淋漓,心中充滿了難以名狀的興奮與自豪。殘陽夕照的時候,我端詳著空蕩蕩的操場和孤零零的圍牆,寫滿字的空間實在是妙不可言,看上去太美。我真想說,我在上小學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很像樣的作家了。
現在想來我的那些「作品」當然是狗屁不通的。但是,再狗屁不通,我依然認為那些日子是我最為珍貴的「語文課」。那些日子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我的表達欲望,這種欲望至今沒有泯滅。天底下沒有比這樣的課堂更令人心花怒放和心安理得的了,她自由,充滿了表達的無限可能性;她沒有功利色彩,一塊大地,沒有格子,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在學校的圍牆上亂塗亂畫,把學校的操場弄得坑坑窪窪,絕對是不可以的。利用小學階段培養孩子們良好的行為習慣,當然也是好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我自然不反對,可我不能同意只有在方格子裡頭才可以寫字,只有在作文本子上才可以按部就班地碼句子。對我們的孩子來說,每一個字首先是一個玩具,在孩子們拆開來裝上,裝上去又拆開的時候,每一個字都是情趣盎然的,具有召喚力的,像小鳥一樣毛茸茸的,啾啾鳴唱的,而在孩子們運用這些文字組成章句的過程中,摞在一起的章句都應該像積木那樣散發出童話般的氣息。
孩子們為什麼想寫?當然不是為了考試。準確地說,是為了表達。一個人不管多大歲數,從事什麼工作,都有表達的願望。孩子們喜歡東塗西抹,其實和老人們喜歡喋喋不休、當官的喜歡長篇大論沒有本質區別,相對於一個「人」來說,它們的意義是等同的。我聽說現在的孩子們越來越不喜歡寫作文了,這真是不可思議。這甚至是災難。孩子們有多少古怪的、斷斷續續的念頭渴望與人分享?他們害怕作文,骨子裡是害怕表達的方式不符合別人的要求。在害怕面前,他們芭蕉葉一樣舒展和潑灑的心智猶如遭到了當頭一棒。他們有許多話想對別人說,他們還有許多話想在沒人的地方說,他們同時還有許多話想古裡古怪地說。表達首先是一種必須、樂趣、熱情,然後才是方式、方法。害怕作文,其實是童言有忌。
所以我想提議,所有的小學都應當有一塊長長的牆面,這塊牆面不是用於張貼三好學生的先進事蹟的,而是在語文課的「規定動作」之外,讓我們的孩子們有一個地方炫耀他們的「自選動作」。它的意義並不在於能培養幾個靠混稿費吃飯的人,它的意義在於,孩子們可以在這個地方懂得,順利地表達自己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是一件讓自己的內心多麼舒展的事。在這個地方,他們懂得了什麼才叫享受自己。如果表達是自由的,那麼,這種自由是以交流作為基礎的。交流是一種前提,最終到達的也許就是理解、互愛。
情感是寫作最大的誘因
與小說有關的一些東西中,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小說的生成,或說小說創作的第一動因。人在寫作時,身體裡會有一些柔軟的部分,這些柔軟的部分一旦被觸動,就會有一些調皮的東西迸發出來,這些迸發出來的東西很可能就是一部作品。從我個人來講,作品的產生大多來自自己身體裡迸發出來的東西,它們是經驗、情感和願望。
經驗是小說創作的根底。沒有經驗,根本就寫不了。經驗對小說家的價值,我覺得怎麼評價都不過分。它在你迷失的時候悄悄地支撐起你的行為,那就是創作。《哺乳期的女人》的寫作來自於一個細碎的小經驗:與哺乳期的女同事短暫的擁抱,一股強烈的氣味刺激了我。這一經驗深深植根在我的心中。不久,我生病住院,躺在病床上怎麼也趕不走那個擁抱、那種氣味。我當時沒想寫作,可我想說的是,經驗在這時表現出了無比可貴的價值。它在我的潛意識中已經爬進了小說創作的進度,換句話說,我自己還沒意識到我要寫小說的時候,經驗已經告訴我你可以開始創作了。後來又結合「空鎮」所見和閱讀經歷,當所有這些聯繫起來以後,幾乎都沒讓我動腦筋,像命運安排一樣,我寫成了《哺乳期的女人》。
再就是情感動因。我把那種看似無用的、沒有物件和沒有來源的情感,放在內心,反復琢磨、考慮,讓這種情感盡可能地和外部發生關係,然後形成一部作品。《青衣》就是一個非常虛擬的情感催動的作品。二十世紀末的時候,我很焦慮,總有一雙女人的手在我的腦子裡晃動,我必須去尋找這個情感的來源,使自己安寧下來。而當我看到一則女演員身患重病,不顧生命危險登臺演出的消息時,我覺得我焦慮的心被安撫了。我假設女演員的這種行為與手有關,或者說跟一個女人內心無法破解的欲望有關,而且這個欲望已經強烈到一個程度,支撐她,使她認為它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從我個人的寫作角度來講,最多的一種小說創作的誘因是情感,它為我提供能量,提供源源不斷地向下寫,往下尋找的動力。我大概寫了一百多部作品,其中六十多部最早由情感誘發,導致我進入寫作。
最後是願望。最初寫《玉米》的時候,就有一個強烈的願望,想寫一個特別的愛情故事,盡可能地讓兩個人處在愛得死去活來同時又緬懷的狀態。這種緬懷不是由距離帶來的,兩個人就生活在一起。但我把這個愛情故事摁住,永遠不讓它挑破,永遠不讓他倆有身體的關係,讓他們處在思念、愛和緬懷之中。我特別想寫這樣一種愛情,因為我癡迷一樣東西:害羞。害羞的底子不是害羞,是珍惜。一個人渴望得到一件東西,可是她不敢輕舉妄動,她知道萬一輕舉妄動就會失去,所以她在情感表達上會呈現害羞的狀態。我覺得害羞的狀態和珍惜的狀態,是我們現當代文學中缺乏的東西,尤其是我們人生當中缺少的東西,也是今天我們的愛情中所缺少的東西。後來這個愛情小說由於其他原因寫成了時代小說,但卻是我想瞭解愛情、呈現害羞、表達珍惜的願望誘發的。
這些都是從我身體裡迸發出來的,與大家分享。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