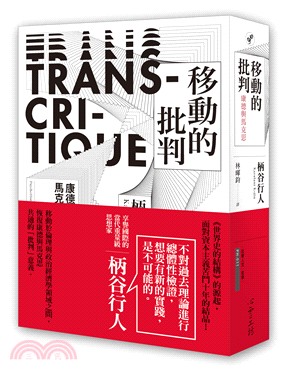移動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
- 系列名:PsyHistory
- ISBN13:9789863571490
- 替代書名:トランスクリティーク:カントとマルクス
- 出版社:心靈工坊文化
- 作者:柄谷行人
- 譯者:林暉鈞
- 裝訂/頁數:精裝/592頁
- 規格:19.5cm*14cm*3.2cm (高/寬/厚)
- 重量:579克
- 版次:1
- 出版日:2019/05/17
再享89折,單本省下87元
商品簡介
不義在遠處發生,沒看見不等於不存在。
突破資本主義的毀滅性漩渦,我們可以怎麼做?
享譽國際的重量級思想家柄谷行人,苦鬥十年以上的經典
精裝書衣版隆重上市
你的行為,永遠不可以把人性──你的人格以及其他所有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僅僅當作手段來運用,必須始終視其為目的。──康德
乍看之下,商品是簡單平凡的東西。然而對它進行分析就會明白,它其實是很麻煩的東西,充滿了形而上學的歪理與神學的偏執。──馬克思
本書是日本當代思想家柄谷行人於2001年出版的劃時代著作,首次提出以交換模式觀察歷史的觀念,更提出「資本-國族-國家」三位一體的視點,以及超越之道,開啟日後《世界史的結構》、《帝國的結構》等重量級著作的思考工作。
柄谷行人深感資本主義帶來貧富不均、社會不公、環境破壞,甚至讓第三世界承受第一世界經濟進步製造的惡果,試圖結合近幾個世紀以來的歷史經驗與哲思,建構出具實踐性的思想體系以改變世局。
全書緊扣「移動的批判」(transcritique)概念,在倫理與政治經濟學領域,以及康德式批判與馬克思式批判之間移動、轉碼(transcoding),試圖回答足以扭轉現今局面的幾個關鍵問題,如:道德有無普遍性?如何超越資本主義?
在本書中,柄谷找到了對抗資本制經濟的可能──從「流通過程」(受雇、購買)下手,將能創造出不同本質的市場經濟。從這理念出發,他鼓勵成立小型共同體,以區域性的生產與消費對抗大財團,以期突破資本主義的重圍。
只有當勞工運動同時也是消費者運動,
才能突破它局部性的限制,具有普遍的意義。──柄谷行人
※鄭重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孫大川|監察院副院長
陳光興|國立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張歷君|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
張鐵志|文化評論家
黃雅嫺|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楊文全|宜蘭「倆佰甲」友善耕作小農社群創辦人
董啟章|小說家
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賴青松|穀東俱樂部發起人
龔卓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我看到一位期盼自己具有行動力的知識人,如何勇敢地踏入古今中外複雜的知識叢林,調度一切可能掌握的資訊,和那些理論巨人對話,為自己開闢出一條實踐的康莊大道。」──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 (監察院副院長、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今天的社會企業、小農經濟、NGO、NPO 組織,隨著傳統勞工運動漸漸失去實質力量,各種新型態的『生產者-消費者』運動,卻逐漸興盛,不論是針對環境保護議題、女性主義問題、少數族群與移工問題、傳統領域運動,新的生產─消費循環過程,都足以在某些時候,撼動『國族─資本─國家』這樣的龐然結構。」──龔卓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作者簡介
柄谷行人 (Karatani Kojin, 1941~)
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理論批評家、思想家、哲學家,及文學評論家,研究主題跨越文學、經濟、歷史、政治、哲學等多元領域。曾任教於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近畿大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加州大學,並長期擔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2006年退休。
柄谷行人出身學運世代,1960年代就參加反安保運動。1969年以討論夏目漱石的〈意識與自然〉獲得第12屆群像新人文學賞。初期以文藝批評為主,1973年日本新左翼運動衰退後,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近年來持續探討「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提出「Association」作為對抗之理念,2000年曾組織NAM(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運動,鼓勵成立各種小型共同體,以區域性的生產與消費,對抗大財團資本怪獸,近10年來更積極參與反核。日本311地震之後,他發表一篇擲地有聲的〈站在震後的廢墟之上〉,並親上街頭遊行。
柄谷行人至今已出版著述30餘種,代表作有《移動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倫理21》、《柄谷行人談政治》、《世界史的結構》、《哲學的起源》、《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以上均由心靈工坊出版)、《邁向世界共和國》(臺灣商務出版)、《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麥田出版)、《歷史與反覆》、《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作為隱喻的建築》等。《定本柄谷行人集》全5卷於2004年由岩波書店出版。
譯者
林暉鈞
畢業於國立藝專,為國內知名小提琴家。醉心哲學與當代思潮,2011年起引介並翻譯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著作,已出版《移動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倫理21》、《柄谷行人談政治》、《世界史的結構》、《哲學的起源》、《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另譯有《源氏物語與日本人:女性覺醒的故事》、《高山寺的夢僧》、《當村上春樹遇見榮格》、《革命的做法》、《孩子與惡》、《青春的夢與遊戲》等書(均由心靈工坊出版)。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序一】一種外行人的閱讀──柄谷行人《移動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讀後感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監察院副院長、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為柄谷行人先生這麼重要的書寫序,對像我這樣一個在理論工作上徹底失敗的人來說,不只是冒險、不適格,恐怕還會辜負許多人的期待。而我之所以一口氣答應,不只是因為我和柄谷先生有數面之緣,聽過他的演講,和他吃過一次飯,對他犀利、細膩的思維深為佩服。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對譯者林暉鈞先生難以言喻的疼惜與尊敬。一位專業小提琴家,竟那麼樣的好學深思,不但認真翻譯了柄谷先生的作品,還曾以具體的行動投入有關維護住宅正義的社會運動中。或許柄谷先生理論的建構裡所隱含的某種實踐召喚,讓他不容自己地願意跳進那混亂的深淵。
誠如柄谷先生在岩波現代文庫版的後記所言,本書是他花了十年時間辛勤工作的成果;之後的作品包括《世界史的結構》、《哲學的起源》、《帝國的結構》等等,都可以說是這本書的續篇和展開。所以要正確解讀柄谷先生本書的深邃內容,恐怕非得一併消化他後來所有的作品不可。對我來說,這是我目前很難做到的事。本書更大的另一個難處是,作者攀爬的理論對象是西方近現代哲學中最複雜、最嚴格的理論體系:康德(Immanuel Kant)與馬克思(Karl Marx)。尤其困難的是,柄谷先生對兩位哲學大師的閱讀,不是從其理論內部演繹、排列而來,而是將他們放進動態的社會歷史脈絡中來剖析。所以討論康德,所面對的就不只是康德思想本身而已,笛卡兒(René Descartes)、休謨(David Hume)和自然科學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以及後來的德國觀念論者,都是我們要對話、交涉的對象。同樣地,對馬克思的閱讀不但要游動在亞當斯密(Adam Smith)、貝里(Samuel Bailey)、李嘉圖(David Ricardo)、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等及其合作夥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和其哲學前輩黑格爾(G. W. F. Hegel)等等大師之間,而且還得掌握馬克思流浪在德、法、英時歐洲各國政治、經濟、社會劇烈變動之現實,柄谷先生將這樣的閱讀稱作「移動的批判」(transcritique)。必須認清的是,如果我們將柄谷先生所謂的「移動」,視為一種思想史式的對話,一種執兩用中,在二者之間協商折衷的思想活動,那就大錯特錯了。柄谷先生對康德和馬克思的閱讀,是抓緊「批判」本身的原動力來的。就康德來說,懷疑論者休謨驚醒他的不是感官所帶來的假象;而是理性的「二律背反」(antinomy)所引發的「強烈視差」,讓他看出理性內省所具有的共犯性。假象來自理性本身,光憑內省無法除去假象。所以,康德的批判是對理性本身限度的批判。根據柄谷先生的解讀,馬克思流放英國倫敦期間最大的震撼和轉向,不是革命,而是「經濟恐慌」造成的「強烈視差」,使他對「資本」的驅力與限度有了更深的理解。透過對李嘉圖和貝里的批判,馬克思在《資本論》(Capital)中,闡明了他們兩位忽略掉的那讓商品經濟得以成立的「超越論」(transcendental)形式。這也正是柄谷先生為什麼在本書中將康德與馬克思擺在一起討論的原因。
坦白講,這麼龐大、多線索的閱讀,我對當中涉及的人、理論和歷史背景,完全沒有足夠的知識與能力做出任何的評斷,這是我的限度,但卻也是閱讀本書時最迷人、最令我愉悅的事。我看到一位期盼自己具有行動力的知識人,如何勇敢地踏入古今中外複雜的知識叢林,調度一切可能掌握的資訊,和那些理論巨人對話,為自己開闢出一條實踐的康莊大道。我雖然對柄谷先生所提出的「Association」瞭解不多,也未能親身參與他二○○○年起所推動的「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NAM),但看到他長年以來一部又一部的知識產出和孜孜不倦的智力勞動,仍興起無比的感動。有時候我不免要去想:知識份子在現代社會還可以有什麼作用嗎?那麼巨大的智力鍛鍊,真能產生等值的實踐效果嗎?其實我非常羨慕笛卡兒、康德、馬克思等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工業革命以來的西方知識份子,他們像夜空中的星斗,聯結自然科學和社會人文科學理論建構的熱情,改造整個世界。五百年來歐美勢力主導人類文明的進展,應該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如今教育普及、資訊發達,滿街都是知識份子,誰能改造誰呢?自然科學與社會人文科學的進展,鴻溝愈來愈深,失衡的情況愈演愈烈;其實我們正面對一個和康德、馬克思時代本質上完全不一樣的局面。
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提問方式,一個新的起點。不是感官,也不是理性,更不是經濟恐慌;「人」,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這可不可以算是柄谷先生所謂的「移動的批判」呢?或是因我的無知無端牽扯的誤讀?!
【推薦序二】合作主義的近未來──移動間的視差.括號間的批判 / 龔卓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儘管哲學搖滾王齊澤克(Slavoj Žižek)在二○○六年的一篇評論中,曾埋怨柄谷行人《移動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這本書,是不是真的該給黑格爾一個機會,而不是把黑格爾當做稻草人來攻擊,但是,齊澤克對於柄谷行人在哲學方法論上,充分運用「視差移動批判法」(transcritique in parallax),或現象學意味下的「置入括號法」(bracketing),在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自我與他者之間,在他個人哲學生涯的日本與美國東岸之間,在康德與馬克思之間,在資本—國族—國家三重結構之間,在四種交換模式之間,進行移動批判式的「超越論還原」(transcendental reduction),仍然津津樂道,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齊澤克念念不忘的,當然是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似乎被柄谷行人的方法論所虧待了。
柄谷行人用杜象(Marcel Duchamp)的小便斗,詮釋康德的「超越論態度」不等於黑格爾式的主奴辯證法,主奴辯證法的主觀論理解方式,在馬克思主義史上,過度簡化了《資本論》的要義,過度忽略了馬克思主義中的倫理態度,也就是忽略了馬克主義中對於「他者的視點」做為主體視點的視差參照點的基本倫理考量:「超越論的態度暗地裡包含著『將它置入括號!』的命令。舉例來說,先前我提到杜象在美術展中展示小便斗的事。他並沒有命令我們把小便斗當作藝術品來看。換句話說,他並沒有命令我們把日常的關心置入括號。但是,『小便斗被放在美術展裡』這件事,『命令』人們把它視為美術作品。人們並沒有察覺這一點。同樣地,超越論的視點包含著這樣的『命令』──不僅如此,超越論的視點本身,就來自一道命令──這件事,人們也忘記了。只要追問超越論的視點來自何處,這件事就很清楚。超越論的視點,根本上來自『他者』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一種倫理的態度。」換句話說,「主奴辯證法」或大家喜歡套用在「資本家與勞工階級意識的辯證」的這種樣版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標籤,柄谷行人認為是過於偏向主觀論的、黑格爾式的馬克思解讀角度,無法真正同時包容主體與他者的視點。
他認為,站在「超越論視點」的視差法,才能夠在主觀的主體之外、主體之間,真正尊重「他者」在倫理上自為目的、不為工具的自由與平等主體地位,還原不同主觀的視點,並在跨越轉換、視差移動這些主觀視點的過程中,不涉入個別主觀的判斷中,而跳到「超越論」的「置入括號」的批判性思考場所,還原出世界史的原本結構樣貌。由於這種哲學思考的工作,只能讓在思想上無家可歸、但汲汲於為人類尋找精神故鄉的世界公民來發揚,因此,在現實中,只能由目的王國中的個體,透過跳脫出「資本—國族—國家」三重結構,化身為德勒茲(Gilles Deleuze)意義下的世界公民「普遍的單獨性」(universal singularity,或可譯為普遍的特異性),在不同的立場間,直接進行普遍論、超越論的批判性特異思考,才不會落入特定主觀的立場去。
而這個思考的場所,如同熟悉柄谷行人提出「四種交換模式」的讀者所可以理解的,正是今日的勞動者可以對抗資本主義的「不認同」場所,當然,這也正是近未來倫理實踐的重要抗爭場所。或許,它們在近未來會以接近信仰的形態顯現:交換模式D。「勞動者有兩個可以對抗資本的地點。第一,就像內格里(Antonio Negri)所說的,『不要工作』。當然,它的意思必須是『不要販售勞動力』(不要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從事雇傭勞動),否則沒有意義。另外一個,就像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所說的,『不要購買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產品』。這些都是在勞動者可以成為『主體』的場合,所進行的抗爭。話雖如此,對『勞動者—消費者』而言,為了能夠『不工作』、『不購買』(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他們必須同時有其他工作、購買的場所。無須贅言,那就是非資本主義體制的『生產—消費合作社』之類組織的 Association。然而,這樣的 Association 要能夠在資本制經濟中形成、擴大,替代性通貨、以及以替代性通貨為基礎的金融體系,是不可或缺的。」
交換模式D會是一種「未來完成式」的交換模式,這中間的勞動交換,會是以信仰某種不同本質的市場經濟來達成。今天的社會企業、小農經濟、NGO、NPO組織,隨著傳統勞工運動漸漸失去實質力量,各種新型態的「生產者—消費者」運動,卻逐漸興盛,不論是針對環境保護議題、女性主義問題、少數族群與移工問題、傳統領域運動,新的生產—消費循環過程,都足以在某些時候,撼動「國族—資本—國家」這樣的龐然結構。這樣的「市民運動」、「生產者—消費者」合作運動,首先面對的當然就是今日已然滲透一切的「資本—國族—國家」新帝國主義,就像杜象的小便斗,許多市民運動其實就是轉換立場之後的勞工運動、生產者運動,只有各種合作主義在進行「普遍的特異性」思考的個體生活中具體發生,具體聯合,這些市民運動才會具有影響力與重要性。反過來說,在可見的近未來社會中,只有當勞工運動、生產者運動同時也是消費者、使用者的市民運動時,只有在合作社團以各種價值信仰型態集結,不以資本的無目的累積為生產消費目的,跳出特定國族、資本、國家的結構時,才能突破它框限於局部的限制,表現出普遍而特異的意義。在這個「未來完成式」的未來尚未實現前,移動間的視差、括號間的批判,做為倫理的方法與態度,或許才是合作主義的近未來道路。
【推薦序三】解構關係形上學──柄谷行人的批判思維 / 黃雅嫺(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1941-)作為生長於日本安保世代(1960-1970)的青年,自就讀於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時期,便投入全學連,對抗美帝運動。自此,以關係連動變化觀點思考國家、社會以及經濟等三方結構,就成了柄谷一生的志業。一九七四年以《夏目漱石論》獲得《群像》雜誌的評論獎之後,柄谷於一九七八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其可能性的中心》一書,獲得廣大迴響,並大抵奠定了其左翼的思路方向。另一方面,他也曾在七○年代後期曾訪問耶魯大學,並與比利時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家保羅.德.曼(Paul de Man)相交,受其理論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熟悉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從事的解構思想,這也是為何我們總能在其著作中屢屢讀到其對既存現象進行思維的形式性的建構之後,又以獨特的方式進行拆解的原因。
儘管,德希達自己曾說,解構(Déconstruction)並非方法論,沒有固定的操作步驟可依循,解構乃是通過閱讀,在文本的內部尋求裂縫,打開那看似封閉的邊界,從而使得文本內部出現多重思想。而無論是對於裂縫的掌握或者文本的邊緣,對德希達而言,可能是文本中的某個概念的梳理,也可能是通過對於多種文字之間的轉換而來,這也是為什麼德希達以為「文本之外,一無所有」。另一方面,柄谷自承閱讀過德希達作品,熟悉解構思想,但他的解構方法卻又全然不同於德希達。
柄谷的解構要比德希達更多一層目的,亦即引入「他者」(l’autrui)的位置與觀點。他的方法是從文本外部引入他者,而不是如德希達一般從內部裂解。進一步來說,柄谷擅長的是先通過形式性的建構,討論概念出現的條件,他以為「解構只有在徹底結構化之後才成為可能,否則它就會止步於語言遊戲的層面。」這一點可以從他對柏拉圖的討論看得出來。從西方哲學史的發展來看,自柏拉圖(Plato)到笛卡兒,一直到康德,莫不以建構穩固的地基(即思想的基礎)為圭臬,一直到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以家族相似性面向開放的世界,柄谷以為這才有了「他者」的出現。這是因為,自柏拉圖以來重視的是生成大於製造,因為製造僅屬於技術層次,而技術總是要服膺於觀念的指導,知識的組成則由觀念指導,而哲學又是所有觀念的基礎,可以說,自柏拉圖之後,所有哲學家莫不是致力於健全知識基礎(fondement),進一步往上建構(construction)思想體系的大廈。很明顯地,思想的建築之所以可能,其知識地基的保證人乃是形上學,是形上思想防止了偶然性的枝蔓雜生,從而保證大廈的穩固性,不致於傾倒。這樣的想法,導致了純思想內部的封閉性,必得還要引入對俗世性的要素,「他者」的位置與觀點才有可能引入。
對當代哲學家來說,他者問題的提出意味著走出自我中心的視角,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壓迫與暴力,因而如何「悅納異己」(l’hospitalité)一直是當代哲學家的課題。對此,柄谷以為,也唯有在思想系統內置入絕對的他者(未來的他者)才可能構成普遍的命題。但「他者」的出現並非出自「對話」,因為能對話僅意味著鏡中的影像,乃是自我的反射而已。有關這一點,柄谷延續了他在《作為隱喻的建築》(Architecture as Metaphor: Language, Number, Money)一書中對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觀點:以語言中的家族相似性,來達到「向外開放」的關係。這樣的語言思想,柄谷以為,那是全然否定「採取『證明』型態的共同主觀性,以及『對話』的唯我論性質」,這是一種「苛刻地將他者內化於自己之中,是一種暗默的政治行為」。柄谷以為,康德哲學的意義也在這裡:《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一方面停留在內省,另一方面又置入了絕對的他者以粉碎內省的共犯性。換言之,康德的哲學之所以具有批判的力量,正是在其哲學內部安置了「絕對的他者」(即未來的他者)的位置,也正是如此其哲學具有普遍性。
另一方面,柄谷引入他者的解構之所以有力量,還在於他所援引的兩位思想家的「之間」的空間性。他在這本書的導論中提及,寫這本書的目的並非分別對康德或者馬克思進行思考,但所謂「『移動的批判』(transcritique),指的是倫理與政治經濟學領域之間,以及康德式批判與馬克思批判之間的『transcoding』(轉碼)。換句話說,就是從康德的觀點閱讀馬克思、從馬克思的觀點閱讀康德的企圖。」柄谷當然無意於以學院的方式,從思想家的內部討論其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缺漏之後,再提出自己的主張;他也不是以馬克思的思想來檢驗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或者以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閱讀馬克思對人的規定性。而是說,往昔學院對康德的閱讀均定位於主體哲學的軸線上,由此討論理性的限度,但柄谷卻要在康德哲學中,提出「他者」(l’autrui)的問題;另一方面,則通過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重新閱讀,為「國家—社會—經濟」三方關係找到超越論的視角基礎。這個視角的基礎就存於康德哲學裡,柄谷稱之為「之間」的移動場所裡,這也是此書標題「trans-」的另一層意義。柄谷以為,正在這個位置上,康德同時解決了「單獨性與社會性」與「自由與自然」兩個問題,如此一來,就為馬克思哲學中的三方關係提供了解釋的基礎。柄谷以為,馬克思的貢獻並不在於什麼歷史唯物論,那不過是膚淺而又表面的解釋方式。在他看來,馬克思思考的焦點乃在於如何解釋資本的衝動與如何得到獲利的位置,而經濟上的恐慌,既來自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也是信用過熱的結果,換言之,恐慌暴露了平時隱藏起來的真相。柄谷以為,馬克思就是從恐慌提供的強烈視差來觀察資本制經濟。這強烈的視差提供了場所,足以使馬克思來回移動,思考其中不透明的商品交換關係與使用關係的轉換,而得出貨幣的必要性,進而思考共同體的未來。
同樣地,當柄谷將其工作放在康德與馬克思之間,也是一種「移動式批判」。對柄谷來說,思想始終不能僅僅滿足於體系內部的解釋,而在於是否能思考出其原有體系的另外(l’autre)。他以獨特的視角將這兩位思想家並置在一起,所產生的強烈視差,既提供了學院之外的閱讀可能性,又擴大了思想本身帶有的批判性。這種批判性不是為了喧囂、博取他人的注視目光,而是提供社會與世界的實踐的可能。
序
【序言】
本書由兩個部分構成,分別是對德國哲學家伊曼努埃.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以及卡爾.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思考。雖然這兩部分看起來好像各自獨立,實際上它們不可分離,以相互作用的方式存在。我所謂的「移動的批判」(transcritique),指的是倫理與政治經濟學領域之間,以及康德式批判與馬克思式批判之間的轉碼(transcoding)。換句話說,就是從康德的觀點閱讀馬克思、從馬克思的觀點閱讀康德的企圖。我想要做的,是恢復康德與馬克思所共通的、「批判(批評)」的重要意義。無須贅言,「批判」的意思並非攻訐對方,而是審思,特別是自我審思。從十九世紀開始,試圖聯結康德與馬克思的思想家不在少數。他們試圖為一般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尋找其所欠缺的主體的、倫理的要素。事實上,康德絕對不是位布爾喬亞哲學家。對康德來說,所謂「道德的—實踐的」,並不是善惡的問題,而是使自己「自由」(自己為因,causa sui),同時將他者視為「自由」的主體。康德的道德法則,是「你的行為,永遠不可以把人性──你的人格以及其他所有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僅僅當作手段來運用,同時必須始終視其為目的」。然而,這不只是抽象的教條。康德認為這是必須在歷史社會中,以漸進的方式逐步實現的課題。我們不妨認為它的具體目標,是在商人資本主義的市民社會中,建立獨立小生產者的聯合團體(association)。當然,這是在德國的產業資本主義尚未興起的時期,所構想的理念。眾所周知,隨著產業資本的興盛,獨立小生產者們無可避免地被迫分崩離析。但是,雖說康德的思考是抽象的,卻預示了後來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以及法國經濟學家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等無政府主義者的想法。因此,德國哲學家科恩(Hermann Cohen, 1842-1918)稱呼康德是「德意志社會主義真正的創始者」。在單純把他者視為「手段」來對待的資本制經濟中,康德所提倡的「自由的王國」或「目的之國度」,顯然意味著共產主義。反過來說,若是沒有這樣的道德性要素,共產主義不可能成立。雖然在歷史上,康德派馬克思主義者被消去了形跡,但這樣的對待是不正當、不公平的。
然而,我之所以將康德與馬克思聯結在一起,和這樣的新康德派沒有任何關係。相反地,我無法不認為康德派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極為膚淺幼稚。無政府主義者(或者說,associationist)也是如此。他們的倫理性與對自由的感覺值得讚賞,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對於強加在人身上的社會關係的力量,缺乏理論性的掌握。因此,他們的努力一直是無力的,始終以悲劇收場。我的政治立場其實是偏向無政府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或國家,一次也沒有讓我感到過共鳴。儘管如此,我對馬克思懷抱著非常深的敬意。年少時期閱讀以「國民經濟學批判」為副標題的《資本論》(Capital)時所感到的驚嘆,經過這麼多年不但絲毫未減,反而日益加深。就讀經濟系的時期,我曾經精讀《資本論》。因此,我對於包括盧卡奇(György Lukács, 1885-1971)與阿圖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1918-1990)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感到不滿。他們事實上並沒有認真研讀《資本論》,只是從中擷取對他們自己的哲學主張有利的部分。同時,那些僅僅把《資本論》視為經濟學著作的經濟學家,也讓我不滿。我逐漸開始了解,馬克思的「批判」與其說是對資本主義或古典經濟學的批判,還不如說是闡明資本的驅力(德: Trieb,英:drive)與極限的論述;而且他在資本驅力的根底,發現了人類的交換行為(或者更廣泛地說,溝通行為)中無可避免的困難。《資本論》並沒有簡單地指出資本主義的出口;相反地,它指出我們為什麼無法輕易地逃脫資本主義。正因為如此,它提供了我們實際介入的可能性。同時我開始意識到,還有一位思想家,試圖藉由明白指出人類理性的極限──而不是透過對形而上學的批判──來提供我們實踐的可能性。雖然大家總是把《資本論》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扯在一起,但我認為足以與《資本論》分庭抗禮的書只有一本,那就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這是我把馬克思和康德聯結在一起的理由之一。
馬克思除了少數幾次批判其他人關於共產主義的言論之外,幾乎不曾談論過共產主義。他甚至說過,談論未來是反動的行為。至於我自己,一直到一九八九年為止,我瞧不起任何有關未來的理念。我曾經認為,反對資本與國家的鬥爭,不需要關於未來的理念;我們需要的,只是反應現實中產生的矛盾,永遠持續鬥爭下去。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後,我改變了想法。在那之前,我對馬克思主義政黨與國家,抱持著批判的態度。然而我批判的前提,是假設它們會強大而穩固地繼續存在。只要它們持續存在,光是保持否定的態度,就彷彿自己有所作為。但是當它們崩潰瓦解之後,我才發現自己其實是以一種弔詭的方式,依賴著它們存在。我開始覺得不得不提出一些積極的主張。我對康德的思考,其實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通常人們認為康德是形而上學的批判者。這種通俗的想法,也不能說是錯的。康德強調,形而上學批判的風氣,是蘇格蘭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的懷疑論引起的。但一般人都忽略了一件事:康德撰寫《純粹理性批判》的時候,形而上學不但不受歡迎,而且還是人們嘲笑的對象。「過去有過那樣的時代,形而上學曾經被稱為所有學問的女王。如果我們不計較它的成效,只從它研究的對象之重要性來看,形而上學的確沒有辜負這個榮銜。然而時至今日,毫不掩飾地對形而上學表示輕蔑,已蔚為風尚。」(《純粹理性批判》)。因此對康德來說,「批判」真正的任務,其實是以實至名歸的形式,恢復形而上學的地位。具體來說,那就是對休謨的批判。
一九八○年代的「回歸康德」,是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這個現象──如同我們在德國政治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先驅性的著作《康德政治哲學講義》(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與法國哲學家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的《狂熱──康德的歷史批判》(L'enthousiasme, lacritique kantienne de l'histoire)中所看到的──是透過《判斷力批判》來重新解讀康德。它的要點是,儘管對鑑賞判斷(judgement of taste)來說,普遍性是必要的,但是在多數的主觀之間,卻是不可能成立的。我們頂多只能找到調節、規範諸多主觀的「共通感覺」(common sense)。這和假定先驗的主體存在的《純粹理性批判》,看起來似乎截然不同。但是,這種對康德的重新評價──包括試圖將理性重新解釋為「公共理性」的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在內──具有顯而易見的政治意涵。那是對作為「形而上學」的共產主義所進行的批判;最後引導出來的結論,就是社會民主主義。
馬克思主義一向被批評為理性主義與目的論的思想(大敘事)。實際上,史達林主義確實是這種思考的產物:掌握歷史法則的知識分子政黨,以理性領導人民。許多人反對這樣的思想;他們質疑理性的權力,否認知識分子的優越性,否定歷史的目的論。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檢討,包含反對理性的集中管理、主張多重語言遊戲之間的「調停」,以及「公共的合意」(public consensus)。同時,相對於理性主義(形而上學)的歷史觀點,他們主張經驗的多樣性與複雜的因果關係;另一方面,一向為了目的而遭到犧牲的「現在」,則因為其性質的多樣性(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的「綿延」)受到肯定。但我注意到的是,基本上這種被稱為「解構」、「知識考古學」等等名稱的思考──我自己也曾經參與其中──只有在馬克思主義支配著許多人民與國家的時期,才具有意義。到了九○年代,它已經失去影響力,僅僅成為資本主義自我解構運動的代言人。懷疑論的相對主義、多重語言遊戲(公共的合意)、美學的「肯定現在」、經驗論的歷史主義、對次文化的重視(文化研究)等等思想,喪失了原先的破壞性,並因此成為「主流思想=支配階級的思想」。如今,這些思想已經成為經濟先進國最保守制度中的官方學說。簡要而言,它們主張經驗論方式的思考──美學也包含在內──優於理性主義。八○年代的「回歸康德」,實際上是「回歸休謨」。另一方面,我可以說是在「批判休謨」的想法下開始閱讀康德的。說得明白一點,我想的是共產主義這個形而上學如何重建的問題。康德這樣說:「因此,為了騰出容納信仰的空間,我不得不否定知識。形而上學的獨斷主義是一種成見,相信理性可以在沒有任何批判的情況下,在形而上學之中得到進步。這樣的成見是一切違反道德性的『不信』之泉源;而實際上,此『不信』始終是非常獨斷的。」(《純粹理性批判》)。當然,康德並不是企圖復興宗教。他所認同的,是宗教賦予我們道德勇氣的一面。
馬克思一貫拒絕將共產主義視為「建構性理念」(constitutive idea)──或者說,將理性用於建構性的目的。因此,他不談論未來。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一書中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所寫的文章之上,添加了這樣的文字:「所謂共產主義,並不是我們必須建立的某種狀態,也不是現實必須達成的某種理想。我們所說的共產主義,是揚棄現狀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所有條件,從當下的前提產生。」但是,這件事和他始終將共產主義視為「整合性理念」(regulative idea)──以整合性的方式使用理性──沒有任何矛盾。馬克思反對的,是將共產主義教條化成為「科學的社會主義」;那是形而上學。他年輕的時候曾經這樣寫道:「宗教批判最終的教義是『對人來說,人是最高的存在』。也就是說,那是一種無條件的命令,要我們廢止一切貶低、奴役、遺棄、侮蔑人類的關係。」(〈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對馬克思來說,共產主義是康德所說的「無上命令」,是實踐的(道德的)問題。馬克思終生不曾改變這樣的立場,即使後來他開始重視實現這「無上命令」所需要的歷史性、物質性條件,也是一樣。然而,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輕視這樣的道德性,標榜「歷史的必然」與「科學的社會主義」,結果正好「建構」了奴隸社會。這不是別的,正是「理性的越權行為」。如果說當今瀰漫著對共產主義的懷疑,那麼這「一切不信的泉源」正來自這種獨斷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不能、也不該忘記,共產主義在二十世紀帶來何等悲慘的結果;它的錯誤絕對不是偶然的。我們絕對不能再天真積極地主張任何理念。這一點對於否定史達林主義的新左翼來說,也是一樣。可是在嘲笑共產主義「蔚為時代風尚」的今天,卻四處可見同樣「非常獨斷」的其他思想。在知識分子公開表明他們「對道德的不信任」的同時,全世界正興起各式各樣的「宗教」。這樣的情況,我們無法一笑置之。
於是在進入九○年代之後,我的想法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立場卻徹底改變了。我開始認為,理論不應該自限於現狀的批判與解釋,而必須提出足以改變現實的積極主張。同時我也了解到,那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無須贅言,社會民主主義對我來說,沒有任何積極的可能性。一直到二十世紀末,我心中才突然出現光明。因為看到了那樣的願景(如本書最後的記述),我在日本發起了全新的associationist運動(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簡稱 NAM)。當然,在世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腳步聲中,世界各地無可避免地發生「揚棄現狀的現實的運動」。但是,我們不可輕視理論。如果沒有理論,沒有 transcritical(交叉批判)的認識,到頭來只是以不同的形態,反覆過去的錯誤而已。
要是不對過去的理論進行總體性的檢證,想要有新的實踐,是不可能的。而這裡所說的理論,並非侷限在政治領域。我認為,康德與馬克思的「批判」涵蓋面如此廣大,沒有一項課題逃出他們的「批判」圈外。因此我在本書中,從數學基礎論到語言學、藝術、存在主義等等,毫不忌避地踏入所有領域,不論它看起來多麼迂遠。我所探討的,幾乎都是除了各領域專家外,無人關心、無人了解的問題。此外,因為我在寫作的當時,就將第一部的康德論與第二部的馬克思論,設定為各自獨立的兩個部分,讀者們或許不容易將它們連貫起來理解。於是我附加了一篇具有說明性質的「導論」。當然,它並不是本書的摘要。
話雖如此,我相信這是一本一般讀者都能理解的書。實際上,本書的前身,是一九九二年開始在日本的文藝月刊雜誌《群像》上連載的文章。當時這些連載文章和小說刊登在一起。換句話說,我不是關在學院主義封閉的圈子裡寫作這本書;我寫作的對象,是不具專門知識的公眾。在這個意義下,這不是一本學術性的書籍。學術性的寫作方式有一種常見的作法──舉例來說,如果是關於馬克思或康德的文章,作者會先承認他們的歷史意義,再指出其侷限,然後敘述自己的主張。但是,我不會為了做這種事,刻意去寫一本書。我只有為了讚揚;為了值得讚揚的事物,才有寫書的動力。在這本書裡,像是挑康德或馬克思的毛病、找他們的缺點這種事,我完全不做。我盡我的可能,將他們置於「可能性的中心」,去解讀他們的思想。但事實上,某種意義下來說,我認為這才是對他們真正的批判。
在這本書裡,我敘述了「資本—國族(Nation)—國家(State)」三位一體的結構。但我必須承認,我對國家與國族的思考,還不夠完全。而且,關於農業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與革命的問題,我的思考也不夠充分。不僅如此,對於我成長的家鄉、一直是我思考對象的日本歷史的脈絡,也幾乎沒有提及。事實上,我的許多考察得自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以及對這個傳統的批判性檢討。缺少了這個部分,我所說的「移動的批判」無法成立。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體驗到日本與西洋諸國、日本與亞洲諸國之間的「差異」,如果沒有經歷過「交叉、橫越」的移動,無法形成「移動的批判」。但我之所以省略這一部分,是因為我正在以這個主題,寫作另一本書。所以本書幾乎沒有觸及這些問題,只集中對康德與馬克思的文本,進行論述。
目次
推薦序二 合作主義的近未來──移動間的視差.括號間的批判/龔卓軍
推薦序三 解構關係形上學──柄谷行人的批判思維/黃雅嫺
譯者前言
序文
導論:什麼是移動的批判?
第一部 康德
第一章 康德的轉向
1. 哥白尼轉向
2. 文藝批評與超越論的批判
3. 視差與物自身
第二章 綜合判斷的問題
1. 數學的基礎
2. 語言學轉向
3. 超越論的統覺
第三章 Transcritique
1. 主體與場所
2. 超越論的與橫越的
3. 單獨性與社會性
4. 自然與自由
第二部 馬克思
第一章 移動與批判
1. 移動
2. 代表機構
3. 作為經濟恐慌的視差
4. 細微的差異
5. 馬克思與無政府主義者們
第二章 綜合的危機
1. 事前與事後
2. 價值型態
3. 資本的驅力
4. 貨幣的神學與形而上學
5. 信用與危機
第三章 價值型態與剩餘價值
1. 價值與剩餘價值
2. 語言學的研究路徑
3. 商人資本與產業資本
4. 剩餘價值與利潤
5. 資本主義的世界性
第四章 移動批判式的對抗運動
1. 國家、資本與國族(nation)
2. 可能的共產主義
定本版後記
岩波現代文庫版後記
謝詞
附錄| 延伸閱讀
書摘/試閱
【導論】
什麼是移動的批判?
康德的哲學被稱為超越論的(transcendental)哲學,和「超越的」(transcendent)一詞有所區別。所謂超越論的態度,簡單地說,就是闡明那些我們沒有意識到的、先於經驗存在的形式。然而,哲學從一開始,不就一直抱持這種反省的態度嗎?而且所謂哲學,不就是透過這樣的反省,以除去謬誤與假象嗎?那麼,康德的思想有什麼特別之處?在康德以前,人們認為假象來自感覺,而理性可以破除假象。然而康德探討的,卻是來自理性本身的驅力而光憑反省無法除去的假象,也就是超越論的假象。因此,康德的反省不是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所批評的那種表層的哲學反省。佛洛伊德認為,「無意識」只存在於分析者與被分析者的關係裡,特別是存在於後者的抵抗之中。在沒有他者的存在、單獨一人的內省裡,看不到這樣的無意識。然而,儘管康德一向被批評為主觀性的哲學家,他的反省始終有「他者」介於其中。
康德獨特的反省方式, 可見於他初期的作品《通靈者之夢》(Dreams of a Spirit-Seer):「從前,我單純只從自己的知性的立場,思考一般人類的知性。如今,我把自己放置在我之外的、他者的理性的位置上,從他人的視點思考自己的判斷,以及這些判斷背後最隱密的動機。兩方面的思考比較起來,確實會產生強烈的視差;但這是避開光學的欺瞞,將有關人類認識能力本質的概念,擺放到其真正位置的唯一方法。」康德在這裡所說的,並非「不要只從自己的視點,也要從『他人的視點』觀看」這種老生常談。康德所說的正好相反。倘若我們主觀的視點是光學的欺瞞,那麼他人的視點(或者說客觀的視點)無可避免地,也是一樣。果真如此,那麼哲學(作為一種反省)的歷史,只不過是「光學欺瞞」的歷史而已。康德帶來的是這樣的反省──它揭露出過去的反省只不過是光學的欺瞞。康德的反省是對反省的批判,只有在我的視點與他人的視點的「強烈視差」下,才能產生。為了說明這件事,我要舉出康德的時代尚未存在的一種科技,作為例子。
人們總是以「鏡中我」,來比喻反省。我們透過鏡子,以「他人的視點」觀看自己的面孔。現在我們可以比較鏡子和照片。不論我們如何試圖採取「他人的視點」,透過鏡子的反省,總是具有某種共犯性。人們總是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觀看自己的面孔。然而,照片具有某種毫不留情的「客觀性」。因為不論拍照的人是誰,和肖像畫不同的是,我們很難談論拍照者的主觀性。當然,照片也只不過是影像(光學的欺瞞)。所以重要的是,鏡中影像與照片影像的差異所帶來的「強烈視差」。據說攝影術剛發明的時候,從照片中看到自己面孔的人,和透過錄音機第一次聽到自己聲音的人一樣,感到無法壓抑的不快。人們認為「這不是我的臉(聲音)」。這和佛洛伊德所說的「抵抗」是同一種東西。但是,人們不久就習慣了照片。也就是說,後來人們開始將照片裡的影像,看作是自己的面孔。不過重要的是,人們初次看到照片時,所感覺到的「強烈視差」。
哲學從「內省—鏡子」開始,而且始終停留於此。不論如何導入「他人的視點」,也無法改變此一事實。原本哲學是從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西元前470-399)的「對話」開始的。對話本身,就是鏡中的影像。許多人批評康德始終侷限在主觀的自我審視,並且希望在導入多數主觀的《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中,找到超脫此一侷限的可能性。但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雖然仍停留在內省之中,卻試圖打破內省所具有的共犯性。這是哲學史上決定性的事件。我們可以看到,這部著作導入了和從前的「內省—鏡子」不同的某種「客觀性—他者性」。康德的方法,一向被批評為主觀的、唯我論的。但是,他的方法始終不曾脫離「他人的視點」。《純粹理性批判》不像《通靈者之夢》那樣,以自我批評的方式書寫。但是「強烈的視差」並未消失,而是以二律背反(antinomy)的形態出現。他的二律背反暴露出,正題與反題都只不過是「光學的欺瞞」而已。
在本書的第一部,我從這個觀點重新閱讀康德。第二部的馬克思論,也是同樣的做法。舉例來說,馬克思在撰寫《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時期,曾經批判黑格爾左派(Young Hegelians);而在那之前,他自己就是黑格爾左派的一份子。恩格斯認為,這本書導入了經濟的觀點以取代觀念論,提出了看待歷史的新視點。所謂德意志意識形態,只不過是一種落後國家的言論,試圖在觀念上實現先進國家英國已經(在現實中)實現的事物。但是對馬克思來說,那是他跨出德意志的言論之外,首次得到的、衝擊性的覺醒體驗。那不是以自己的視點觀看,也不是從他人的視點觀看,而是這兩者的差異(視差)所揭露的「現實」。馬克思正面迎向了這樣的「現實」。他去了英國,一頭栽進古典經濟學的批判裡。但事實上,馬克思還在德國的時候,就曾經對資本主義與古典經濟學進行過批判。那麼,到底是什麼賦予馬克思不同的視點,讓他得以在《資本論》中提出了嶄新的批判?那就是在古典經濟學的論述中,僅僅被視為意外或錯誤的「經濟恐慌」。我們不妨說,經濟恐慌就是那「強烈的視差」。
重要的是,馬克思的批判來自不斷的「移動」,以及移動所造成的「強烈視差」。康德所發現的「強烈視差」,被黑格爾抹滅了──黑格爾批評康德的主觀主義,強調客觀性。同樣地,馬克思看到的「強烈視差」,也被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者消去了蹤跡。結果,形成了康德與馬克思是「建構了強大體系的思想家」這種形象。然而只要細心閱讀他們的著作就會明白,這樣的形象是完全錯誤的。
康德與馬克思不斷反覆地「移動」,而帶來「強烈視差」的,正是朝向其他言論體系的「移動」。關於流亡者馬克思,這一點自不待言;但事實上康德也是如此。雖然在空間上,康德完全沒有任何移動;但是他對移動邀約的拒絕,以及他身為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一事,使他成為某種意義下的流亡者。一般認為,康德在理性主義與經驗論的「夾縫」中,從事超越論的批判。但只要讀過《通靈者之夢》這種怪異而自虐的文章,就很難認為康德只是在「夾縫」中思考。而且,他還一再反覆地以經驗論的立場挑戰獨斷的理性主義,以理性主義的立場挑戰獨斷的經驗論。康德的「批判」就存在於這樣的移動之中。「超越論的批判」並不是某種安定的第三立場。如果沒有橫越的(transversal)或是移位的(transpositional)的移動,這樣的批判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將康德與馬克思超越論且移位的批判,稱為「移動的批判」(transcritique)。
阿圖塞說,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完成了「認識論的斷裂」。但那並不是唯一的一次,也不是最重大的一次。一般認為,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巨大轉變,在於歷史唯物論的確立。但實際上,那是恩格斯率先提出的思想;《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這一部分,實質上也是恩格斯撰寫的。我們應該注意的反而是,馬克思達成這樣的見解,相較是落後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深深涉入恩格斯早已擺脫的問題──「宗教批判」。馬克思這樣說:「對德意志來說,宗教批判已經完成。而對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基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對國家與資本的批判,是他的「宗教批判」的延伸與變形。這並非僅僅是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von Feuerbach, 1804-1872)自我異化論的應用──事實上,不久後他就放棄了費爾巴哈的論點。馬克思執拗地持續批判「宗教」,只不過他批判的「宗教」,採取了國家與資本的形態。
產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使我們能夠以生產的觀點,觀看過去的歷史。因此,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早在十八世紀中,就已提出了歷史唯物論的視點。但是相反地,歷史唯物論卻無法說明資本制經濟。資本主義並不是什麼「經濟的下層結構」這樣的東西。它是一種超越人類意志,規範人類行為,既能夠讓人們分離,也能夠讓他們結合的「力量」。我們還不如說,它是宗教性的東西。無須贅言,馬克思窮其一生想要解明的,就是這個。「乍看之下,商品是簡單平凡的東西。然而對它進行分析就會明白,它其實是很麻煩的東西,充滿了形而上學的歪理與神學的偏執」(《資本論》)。馬克思早已不再處理狹義的「形而上學」或「神學」的問題。可是他卻在「簡單平凡的東西」之中,發現它們。只有真正的思想家,才會有這樣的認識。應該可以這樣說吧──就算沒有馬克思,還是可以出現歷史唯物論。馬克思主義也是一樣。但《資本論》這樣的著作,如果不是馬克思,是絕對不可能存在的。
關於馬克思,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大「轉向」,那就是從他中期的作品《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Karl Marx's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到後期的《資本論》的轉變。具體來說,就是「價值形態論」的導入。造成這個轉變的契機,在於他完成《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之後,遇到一個懷疑論的主張:英國哲學家貝里(Samuel Bailey, 1791-1870)對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勞動價值說的批判。李嘉圖認為,交換價值內在於商品之中,貨幣則是用來表示交換價值的東西。換句話說,貨幣只不過是假象。以這樣的思想為基礎,李嘉圖左派與普魯東主張廢除貨幣,並且提出發行勞動證券(銀行券)與設立交換銀行(國民銀行)的構想。馬克思雖然批判他們,但基本上也是以勞動價值說為立論基礎。但貝里認為,商品的價值只存在於商品與其他商品的關係之中;因此,他批評「勞動價值內在於商品之中」的說法,是一種幻想。
貝里的懷疑論,和英國哲學家休謨對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批判──笛卡兒所說的自我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多數的自我──相似。對於這一點,康德的說法是:自我的確是假象,但有一種超越論的統覺(apperception)X存在。所謂的形而上學,就是將這個X視為某種實體的想法。話雖如此,我們總是想要將這個X當作可經驗的實體;那是我們無法逃離的衝動。因此,所謂的自我不只是假象,而且是超越論的假象。當然,康德的這個想法是後來才形成的;一開始他也認為休謨的懷疑讓他「從獨斷主義的夢中醒了過來」。同樣地,貝里的懷疑顯然予以馬克思重大的衝擊。然而馬克思不僅批判李嘉圖,也批判了貝里;這一點也和康德一樣。李嘉圖因為勞動價值說而輕視貨幣。但其實貝里也同樣輕視貨幣。他一方面主張商品的價值由商品與其他商品的關係決定,另一方面卻忽視商品之間無法直接產生關係的事實。只有透過各自與某種特定商品(貨幣)的關係,不同的商品之間才能產生關係。
正如馬克思所言,在經濟恐慌中,人們突然開始追求貨幣,變回重金主義者。在《資本論》裡,馬克思回溯得比李嘉圖與貝里更遠;他回頭從重商主義開始思考。當然,他對兩個人都進行批判;透過這樣的「批判」,馬克思解明了他們忽略掉的「形式」──讓商品經濟得以成立的超越論的形式。從另外的觀點來說,這種想法重視物品所在的關係位置,勝於物品本身。馬克思沒有用勞動價值說來作為貨幣的根據(像李嘉圖那樣)。商品本身的價值,透過其他商品(使用價值)呈現。在這個場合,前者位於相對價值形態,後者則位於等價形態。而當所有的商品都以排他的方式,透過同一件商品顯示自己的價值時,後者就成為一般等價物,也就是貨幣。
馬克思認為,黃金之所以成為貨幣,並非因為它是黃金,而是因為它被置放到一般等價形態的位置。他想要觀察的,是讓這個位置上的生產物成為一般等價形態、成為貨幣的「價值形式」,也就是相對價值形態與等價形態。任何以排他的方式被置放到一般等價形態的東西就是貨幣,不管它的素材是什麼。被置放到一般等價形態的物品(以及其持有者),擁有得以與其他任何事物交換的「權利」。人們之所以認為黃金是崇高的東西,並非因為它是黃金,而是因為它被置放到一般等價形態之上。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對資本的思考,從守財奴開始。守財奴所固執的,並不是對物品(使用價值)的欲望,而是想要佔有「位於等價形態位置的物品」的「衝動」(德:Trieb,英:drive)──為了和欲望區別,我借用了佛洛伊德的概念。換個說法,守財奴的衝動,不是對物品的欲望,而是即使犧牲物欲,也要站上等價形態「位置」(position)的衝動。如同馬克思所說,這樣的衝動包含著神學的、形而上學的要素。因為,守財奴可以說就是「積財寶在天上」的人。
但是,雖然我們嘲笑守財奴,資本的累積衝動基本上是一樣的。所謂的資本家,就如馬克思所說,不過就是「理性的守財奴」。他們所圖的,是透過商品的買進與賣出,增大「直接交換可能性」的權利。但他們的目的,並不是要使用。因此,資本主義的原動力,並非來自人們的欲望。事實上正好相反。資本的衝動在於獲得「權利」(或者說「位置」),並且為了這個目的,喚起、創造人們的欲望。而這個想要累積「交換可能性的權利」的衝動,來自「交換」這件事內在固有的困難與危險。
歷史唯物論者思考自然與人類的關係,人類與人類的關係,以及它們在歷史上的變遷。但是他們的思考裡缺了一樣東西,那就是對於組織這些關係的資本制經濟的思考。為了思考這一點,我們必須觀察「交換」的次元,以及「交換必須採取價值形態」這件事的無可避免的本質。重農主義者與古典經濟學家從「生產」出發,從他們的視點看來,所有的社會關係都是透明可見的。但是對我們來說,社會性的交換永遠都是不透明的;它顯現為獨立的力量,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廢除的。恩格斯認為,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無政府狀態的,我們只要有意識地控制它就好了。集權式的共產主義,就從這裡產生。而實際上這個想法,只不過是古典經濟學的延長罷了。(全文未完)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