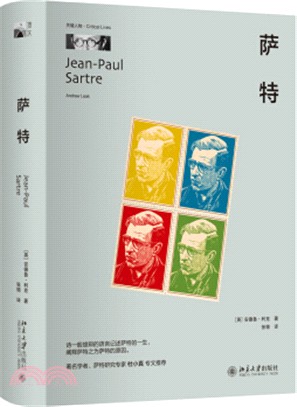商品簡介
直面這個被偶然性和荒誕性支配的世界
他的“存在先於本質”“他人即地獄”的名言眾人皆知;
他是一台“寫作機器”,為寫書注射致幻劑、興奮劑;
他把存在主義哲理帶進了小說和戲劇創作;
他“偶然”的風流韻事與“必然”的愛情讓人唏噓……
《薩特》揭示出與這位文學、哲學巨人的思想發展緊密相關的語境。闡明了薩特是如何被某些當代事件所改變的,其中尤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為甚,此外還探討了薩特與眾多人物——從波伏娃到伽利瑪——的關係。作者提供了一種理解薩特的新方式,解釋了薩特公開行為——有時帶著冒險意味——之中的謎團和表面的矛盾之處。在他著名的公眾形象之下,有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同寫作行為本身的准神經質式關聯。本書在探查薩特生活和創作的關鍵時刻時,就追尋著這條線索。
作者簡介
安德魯•利克(Andrew Leak)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法語系主任,薩特研究專家,曾任英 國薩特研究協會主席。他有關薩特的著述頗豐,著有《乖戾 的意識:性態和薩特》(The Perverted Consciousness: Sexuality and Sartre,1989)等。
譯者簡介
張錦
文學博士,現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主要研究領域為比較詩學、西方文論、福柯研究,著有《福 柯的“異托邦”思想研究》等。
名人/編輯推薦
從別人的眼光中出走,薩特仍是自由
1.薩特,20世紀法國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
2.本書將薩特的思想與經歷如織布般交織在一起,成功挖掘了一個更深刻的薩特,學術性與可讀性皆強。
3.譯文準確考究,簡練中肯,通俗流暢。
4.60克瑞典進口輕型,小開本,輕便易攜帶。
5.圖片豐富,與相應事件對照。
序
《禁閉》上演
1944年5月27日,左岸(Left Bank)的老鴿巢劇院(Théâtre du Vieux-Colombier)是當年文學事件的現場:薩特的新劇《禁閉》在此首演。這也許是他最完美的劇作:一去《蒼蠅》的冗長和史詩式的虛榮做作,取而代之的是幾乎預示了貝克特(Beckett)一樣的簡潔的語言和處境設置。三個人物——一個男的和兩個女的——被判了刑,要在一個非常薩特式的地獄裡共度永恆。沒有鏡子,他們必須依靠彼此的凝視——和語言——來維持和創造他們自身的形象。回到世間生活裡,他們已經永遠地跌落到了公共視域裡;因此,生活將決定他們是誰:加爾森(Garcin)膽小鬼,伊奈司(Ines)女同性戀,埃司泰樂(Estelle)殺嬰犯。然而,在地獄裡,他們仍舊需要為每一件事情而盡力:要獲得“拯救”,每個人必須勸說其他人中的某一個將其看成其希望被看成的人。但是這畢竟是地獄,一切之所以被如此安排就是為了使其不可能:人物們將用他們的永生永世來尋找他們自己的面容。“他人即地獄”,加爾森說——這是許多公眾將以此來“認識”薩特的口號性標語中的第一個。然而,任何那個時候讀過《存在與虛無》的人都應該知道,它並無意對人類的關係做普遍判斷:過分依賴他人去瞭解自己的人,實質上就是把他自己置於活地獄中:我們必須在大寫的他人所擁有的關於我們的客觀知識和我們能有的關於我們自身的不那麼本質性的主觀理解之間達到一種平衡。
要在薩特自身的個案中維持這種特定的平衡,被證明是非常困難的。《禁閉》使他某種意義上變成了一個明星:他立即成為被需要的人;採訪和約稿的要求像雨點一樣湧來;各種委託任務和各種各樣其他的提議每日接踵而至。從這時起,薩特一直不斷地出現在公共視域中,但是他在那裡所能瞥見的他自己的形象並不一致。他引起了人們的欽慕,同樣也招致了人們的輕蔑,每一個讚美都被另一個抨擊所抵消。當他注視這面鏡子時,他必然看到他的形象碎成了上千個碎片。像所有藝術家一樣,也許薩特也在尋找他自己的面龐。這一點自從孩童普魯(薩特小時候的昵稱)發現語言是一面鏡子——同時是通向世界的一扇窗口時,就的確如此了。即將突然到來的名聲僅僅凸顯了他的困境。
《禁閉》上演兩周後,同盟國登陸諾曼底;兩個月後他們到了巴黎。淪陷結束了,“薩特時代”即將開始。
“偶然”的風流韻事與“必然”的愛情
1928—1929學年的某個時候——至於確切是什麼時候,說法不一——薩特開啟了一段影響其後半生的關係。他注意到了一個比他低一級的女生(當然現在他們是同級了),他說這個女生“和藹、漂亮但是穿著十分不講究”。對她來說,她很久之前就知道這位高年級某出名團體的頭頭,此人才華橫溢卻“非常危險”:傳言他酗酒,行為暴躁,甚至沉溺於女色。這位年輕的女性,西蒙娜•德•波伏娃,來自一個天主教資產階級家庭,但是她正處於剔除那陳舊到沉悶而又遮遮掩掩的教養的各種痕跡的時期。在薩特身上,她看到恰恰是這個人能夠幫助她做到這一點。在此判斷這段關係對兩方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彼此相伴持續了接下來的五十一年。這種關係的力量似乎起源於一種強大的知識和情感的互補性。他倆都找到了她/他一直在尋找的對象(double)(薩特最喜歡的一個向他的伴侶示愛的措辭便是“你亦我”[you other myself])。一旦他們發現彼此,其他所有友誼都無關緊要了。該措辭“對象”在此也應全然以精神分析角度去考量:在他們大量已出版的通信中,薩特男性化了波伏娃並女性化了他自己的程度引人注目。她是他的“法官”,他的“嚴厲的審查員”,他的“楷模”。他向她歡快地坦白他的罪行,他似乎希望把自己置於她完全嚴厲的審判下:他是孩子而她是母親。有時候他們的角色被顛倒過來,她變成了他的小女兒。該紐帶的牢固性或許就建立在角色的可逆性上。共同低幼化(mutual infantilization)當然是任何愛情關係的一部分——看看情人節的私人廣告欄就足以確定這一點——但是這裡我們感覺到了一種深深的宣洩:波伏娃的“男子氣”可以使薩特認可他自己女性的一面,這一點在巴黎高師預科班和巴黎高師那種咄咄逼人的男性氛圍中被深深地壓抑了。只有個別情況下它才能被察覺:例如,在《播種與潛水服》中被薩特戲劇化的他和尼藏之間的關係中的那種“難以捉摸的柔情”中,我們可以察覺到這一點。
(薩特和波伏娃)這種關係剛開始不久就被打斷了。1929年秋薩特離開去服兵役。在聖西爾軍校(St-Cyr),他被迫開始瞭解氣象學的奧秘。在分開前,他就制定了一些基本準則,提出了一個為期兩年的“協議”:漫遊、(相互完全誠實)完全透明和多個伴侶!事實上,這是一個絕妙的理性化提議,有效利用了偶然性概念:他給她解釋說他們每個人都可以有“偶然的”風流韻事,但是他們倆之間的愛情是他們唯一“必然的”愛情。至少一開始,薩特比波伏娃更自由地使用這個協議。
……
但這對情侶的穩定關係在1934年被波伏娃以前魯昂的一個學生奧爾加•科薩傑維茨(Olga Kosakiewicz)撼動了,她是白羅斯移民(émigré)男子與法國女子的女兒。一對成了三人,這個模式將在薩特和波伏娃一生的關係中不斷上演。薩特認為對奧爾加的激情能夠使他有力量戰勝過早的中年危機。他因癡迷而扭曲的眼光,外加對自身存在停滯不前的擔憂,能將這個年輕女人身上,在一個更冷靜的看客瞧來,或許幼稚、輕浮、矯飾的東西轉變為隨性、神秘和“真切”的品質。在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說《女賓》(L’Invitée,1943)中,她對這場三人戀關係做了小說化的說明,她暗示到她更清楚地看到了奧爾加的美德,儘管或者也許因為她明顯的嫉妒。從那個冗長詳細的描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在波伏娃的記憶中她認為在這場三人戀中,薩特的情緒強烈地搖擺於迷醉沉溺和嫉妒憤怒之間;他通過堅持和波伏娃一起分析奧爾加的最細小的言語、最精妙的語氣變化、最輕微的一瞥,來擾亂波伏娃。這種心理機能模式接近於偏執,無疑這段時間薩特的精神狀況確實沒因其他無關事件改善。為了他正在寫的關於意象的書,作為研究的一部分,薩特——通過一個醫生朋友——給自己注射了麥司卡林(mescaline)(一種致幻劑),目的是研究幻覺的本性。幻覺狀態持續的時間遠遠多於正常狀態,這給薩特帶來了比他所預期的絕對更可怕的轉變。更糟糕的是,1936年春,《憂鬱》(Melancholia)——現在被叫作“事實性論述”——被伽利瑪出版社退稿。這個打擊對薩特的影響再誇大也不為過。但是事情很快會向好的方向轉化。小說可能是已經被拒絕了,但是他最終付諸印刷了關於意象的書,《想像》(L’Imagination)於1936年出版,《自我的超越性》一年以後出版。後來,1937年4月,多虧了以前的學生雅克-勞倫特•博斯特和以前情人的丈夫——戲劇導演夏爾•迪蘭(Charles Dullin),他已經娶了西蒙娜•若利韋——的努力,《憂鬱》最終被伽利瑪出版社臨時(provisionally)接受出版了。不僅小說被接受了,而且伽利瑪出版社也同意在著名的《新法蘭西評論》(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上刊登一些薩特的短篇小說,以1937年7月的《牆》(“Le Mur”)開始。而且,薩特已經把他的激情從奧爾加轉移到她妹妹萬達(Wanda)身上了,在身體的激情消耗上,最終證明她比她姐姐更合適。最終,從1937年起,薩特和波伏娃都最後“回歸家庭”了,各自在巴黎的巴斯德(Pasteur)中學和莫裡哀(Molière)中學謀到了教職。“小博斯特”後來偶然地(真的是“偶然地”嗎?)娶了奧爾加,同時她仍舊秘密地做了波伏娃十五年多的情人:從外面看,薩特的“家庭”有一種亂倫的和諧(cohesion)。
目次
I 序 言
001 第一章 鏡廳中的孩童
051 第二章 戰爭和人
087 第三章 聲名的代價
125 第四章 真實的震驚
159 第五章 不可多得的全球知識份子
203 第六章 薩特的死亡和生命
215 參考文獻
222 圖片使用致謝
書摘/試閱
寫作推遲死亡到來
關於戰爭年代對個人的重大意義,1975年薩特毫不猶豫地說:“我生命中最清楚的事情是我曾經有過斷裂,這意味著兩個差不多完全分裂的時刻……戰爭前和戰爭後。” 經歷了“二戰”的人大多都可以理解“二戰”作為一個斷裂把他們的生活分成了一個“之前”和一個“之後”,但是薩特這段話要表明的是,這種斷裂是如此的徹底以至於後來的薩特幾乎不能識別以前的自己。
客觀地說,不可能再有比這更殘酷的變化了:他從世界的文化之都,突然被運送到一系列寂靜的阿爾薩斯(Alsatian)村莊:馬爾穆蒂耶(Marmoutier)、布呂馬(Brumath)、莫爾斯布龍(Morsbronn)和布維萊(Bouxwiller)。轉換也發生在時間中,回到一個雖然他個人從未親歷過的“他的”過去:這個地方是母親的家庭施魏策爾家的所在地。在巴黎,欽佩他的女性朋友和情人的小圈子一直圍繞著他,現在他發現自己身處最富侵略性的男人的環境。實際上,直到那時,薩特一直過著沉湎于各種各樣的精英圈子的生活——無論是(在巴黎高師)作為精英中的一名實習生,(在高中)作為未來精英的教育者,還是在伽利瑪出版社作為一個精英的休閒娛樂品的創作者。現在,他只是薩特,一名隸屬於氣象陸戰隊的二等步兵。他發現自己被迫與來自非常不同社會背景和眼界的人共處:法國電話公司的職員、從事服裝業的巴黎猶太人、外省老師。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馬蒂厄•德拉呂——薩特那時正在寫作的小說的主人公——最初面對他的“召集入伍令”時並不怎麼高興,但是至少它把他從完全的無名之輩狀態拯救出來了:“從這裡開始,我開始變得有趣起來了。” 然而,薩特在戰前巴黎的文學和藝術圈子裡已經開始“小有名氣”了。所以小有分歧的是他的軌跡與馬蒂厄相反:他發現自己重新跌入到無名的境地:一開始,至少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他的生命並不比那些他稱為他的“追隨者”的同志們的生命更有價值。可有可無的、可以替代的、可以交換的:他變成了任意的一個普通人。成為一個群眾的經驗——對於戰前那個精英人才的薩特而言是非常討厭的事——後來將被薩特確認為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大家都說,薩特和他的同行者們沒有因軍事職責而過分勞累;他們的工作主要是一天兩次給氣球放氣,觀察它的飛行情況,然後做一些非常簡單的計算得出風速和風向。一天裡其他的時間他們都是空閒的。薩特把這種閒暇利用得很好:他正好繼續做他之前一直在做的事情——也就是大量地閱讀和書寫。當大多數士兵可能都在給他們的愛人寫信,讓她們給他們寄送剃鬚刀片、巧克力和煙草時,薩特要求寄送的東西是書(必須承認還有奇怪的吊煙袋)。從海德格爾(Heidegger)到二流的偵探小說,從佩皮斯(Pepys)的日記到紀德(Gide)、達比(Dabit)和雷納(Renard)的日記,他什麼都讀。他讀“一戰”的歷史,讀納粹興起的分析,似乎嘗試最終理解他是怎樣來到他所在的地方。他閱讀哲學和傳記(他長期著迷的事情之一)。他閱讀歷史和小說。他常常一天一讀就是12個小時,直到他那只好的眼睛“眼冒金星”(自四歲以來,兒童時代的疾病已經使薩特實際上右眼失明了)。他同時也寫作。反思薩特在假戰爭(Phoney War)的九個月中所寫的這些巨量的文字,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基本的真相:他是一台文本製作機器。光他寫給波伏娃的日常信件就占了《給河狸的信》(Lettres au Castor)的500頁。他寫作了並且重寫了將在1945年出版的那本厚厚的小說《不惑之年》(L’Age de raison)的草稿。尤其是他生產了一本戰爭日記;1995年擴充版的這部日記有600頁之長——它只包含了在這一小段表面上“無為”的時間裡他完成的15本筆記本中的6本!可能除了1958—1959年當薩特寫作《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時使用苯丙胺興奮劑而過度活躍之外,這九個月肯定是薩特整個生命中最密集的文學創作時期。他寫作,似乎他的生命都依從於寫作,而且在很多方面,的確如此。
在所有薩特去世後的出版物中,對於他著作的學生而言,《日記》(Carnets)可能是最令人驚奇並且最有價值的。因為在日記裡(薩特)記錄了這些日記產生的方式和情形,它們可以把我們帶到薩特與寫作關係的最核心處。我們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此有效地理解寫作對薩特意味著什麼。當我們閱讀一個日記作者時,我們目睹了日常生活的“再生”(recycling)和變形。例如,我們意識到外部事件正在被某種情感所改變,或者正在被階級化了的視角所改變,或者甚至被日記作者的病理情況所改變。所有這些在日記中都會出現,然而“加工處理”世界和轉化世界的主要過濾器正是智力活動。在“一個人主要通過知解力(而不是情感、身體等)而與世界相關聯”的特定意義上,閱讀戰爭日記可以理解知識分子是什麼這一問題。說一切都是作家工坊裡的穀物似乎太老生常談,但是我們很少有機會看到究竟那個工坊是怎樣運作的。關於這些日記,那種直接讓我們驚訝的東西是主題的不規則變化:它們包含了冗長的薩特對他正在閱讀的書、報紙和雜誌的討論;對他的小說進度的反應;對他的物理環境的描述;包含了他經常對“追隨者們”滑稽的肖像、語言和行為的描述;對痛苦地思索他的女朋友(們)回到巴黎後可能會遇到什麼的“軍人習態”(military mentality)的分析;還包含了最初的、碎片化的、自傳體的草圖;對“存在主義精神分析”的最初嘗試以及許多頁密集的哲學分析。所有這一切都被編織進經緯交叉的、作為一個處在這種“卡夫卡式的戰爭”中的士兵的每日生活的荒謬性中。
他經常重複申明戰爭已經“改變了”他,申明同伴之誼、被囚禁和被佔領的經歷已經把他從一個冷淡的個人主義者“轉換成了”激進主義積極分子,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日記的死後出版,這個申明也可能已經被認為是不言自明的東西了。客觀地講,這些申明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容置疑的:我們只需比較薩特戰前與戰後所做的和所寫的東西就能明瞭。但是日記的意義正在於它使我們能夠目擊改變的過程以及這個過程中的各種變化;使我們問我們自己變化的是什麼,不變的又是什麼,最重要的是,使我們反思在這個自我轉變過程中寫作所扮演的角色:日記既是一種轉變的記錄,同時又是轉變得以發生的必然方式。如果有人仔細核查在這段時間裡寫作對於薩特而言所扮演的各種功能的話,他將深入到藝術家與其媒介關係的核心。
像大多數應徵入伍的士兵一樣,薩特對處境的第一反應是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迷失感和自主權的喪失感。然後,不出意料的是,寫作的日常實踐的第一個功能就在於幫助作家重獲他的位置感,或者“重新定位”他自己並且再度確定他虛幻的獨立性。在“外在”(他人、死亡的可能性、軍隊的等級制、敵人的意圖)非常重要並且威脅要壓倒或者侵入“內在”時,寫作是一種重新確定內在性特權的方式。關於這方面給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本日記本,它包括了在前線的前六周。這本日記差不多全部致力於例如“戰爭的世界”這樣的主題——似乎這種智力行為是神奇地奠定了主體對這個世界控制的一種方式,這個世界的第一個特徵簡單說就是它剝奪了管控的個體性和個人的身份。
這種維持控制的欲望在涉及他人的地方尤其明顯。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記住這些日記本絕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日記。雖然薩特不確定它們是否適合於公眾,但是他寫作它們的時候是有一個特定的公眾在心裡的:當它們完成時,它們被帶給或者寄給波伏娃,然後波伏娃把它們帶到親密的“家庭”小組——主要是博斯特、奧爾加和萬達裡相互傳閱。確切地知道誰將閱讀這些日記,這毫無疑問使薩特能去估計它們的效果。在這一點上它們與薩特寫給波伏娃、萬達和其他人的許多書信非常相似。1939年9月前他已經審理了一小圈女性朋友,並高效而自私地(cynical efficiency)控制著這一小圈人的網絡和信息流。現在他被調離到幾百公里的距離以外,非常不適地置身於多少有些即興的交流線路的末端。寫作現在變成了他唯一的維持對他所謂的“基點”(cardinal points)進行控制的方式。寫作的這種特殊功能,可由兩件附帶小事凸顯出來,先是看出他對他的對話者失去了控制,然後通過他的筆的力量他又重新贏得了控制。
內在遭外在的終極入侵就是死亡本身:“[死亡是]在我自身最內心深處的外在的出場。” 即使死亡不是一種很大的可能性——由於薩特不是一個前線的戰士——它至少是一種可能性,這迫使他反思死亡的意義。非常典型的是薩特把死亡看作是一個敘述的荒謬的中斷。有時候,這種敘述會採取形象化的形式,就像一塊有了草圖的刺繡布料正在等待著被填滿(現在人們可能更多地想到“數字油畫”);有時候這種敘述是一個旅行:“我現在意識到我在生活中起航,似乎我正在開始一個長長的旅行,但是它是一個給定距離的旅程和擁有確定目的地的旅行。在天黑之前我必須到達我的目的地。” 寫作不單是刺繡的圖案之一,也不是沿途中的插曲之一:它是一切事情的根本形式和內容。他認為他的生活與他的作品(oeuvre)和他的生命一樣廣泛——當然得承認,在一開始和結束(嬰兒期和衰老期)時帶著一絲“非生命因素”:“我總是想像我的寫作不是孤獨的產品而是被組織進一個作品。而且這部作品包含了一個人生命的整個範圍。” 因此我們可以進行一系列的推演:寫作(écriture)的日常實踐生產了書寫(écrits),而書寫生產了一部作品;這部作品將只有在合乎“正常的”生命期限的意義上才是完整的;因此,一旦這部作品在生產過程中(也就是說,一旦書寫正在被日常的寫作實踐所生產),死亡就沒有理由進入。這意味著,是寫作不斷地推遲著死亡的過早到來。就像一個現代的(latterday)山魯佐德一樣,薩特通過講述/寫作來活命。正是據此,我們也許可以理解他用以描述他對他的旅程的完成狂熱地迷戀的那些措辭:“我不希望感到疲憊或者要停止。我全部的意願就是向著目標而努力。沒有任何可能去懶散或分心,我決不讓自己隨波逐流,每件事情都是這個旅程上的一個要素。” 這就是促使薩特在那場假戰爭中一天寫作12個小時的必然性。知曉了潛藏的死亡,也許它僅露端倪,薩特也可能會像羅岡丹一樣說:“真相是我害怕鬆開我的筆。”寫作是他的護身符:“我還沒有到死亡的時間[……]神奇的是它使我確定在我已經到達旅程的終點之前我不會死亡。” 他只是用寫作來“打發時間”,這種反對意見實際上與其說是一種異議不如說是一種確證。當他寫作時,他把自己從真實的時間中抽離(在這種真實的時間中人類生存和死亡):時間被轉化成空間,而且這個空間可以被信件與詞語、語句與語行、紙頁與筆記本[……]的不斷積累來測量。這種時間的空間化在戰爭日記中隨處可見。例如在1940年3月27日,仿佛急切地希望召回久遠的時間偏差,他寫道:“我對真實性或者大寫的虛無的思慮,到現在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了。” 實際上,僅僅兩周前他才剛好寫了關於這些主題的一則長長的日記(entry),但那兩則日記被17000個詞匯的文本“時間”相互區分開。正如他自己評述的:“我總是把充裕作為美德!”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