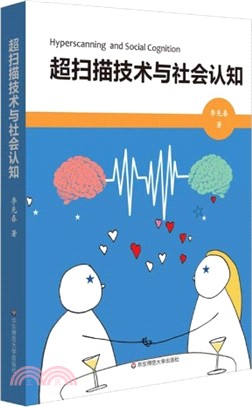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前言1
第一章 腦―腦耦合: 創造和同享社會世界的一種機制
第二章 超掃描技術及其發展現狀
第三章 超掃描研究的數據分析方法
第四章 超掃描視角下的合作與競爭行為
第五章 超掃描視角下的人際交流
第六章 超掃描視角下的社會決策
第七章 超掃描視角下的人際互動與親社會行為
第八章 超掃描視角下的自閉症人群社會交往缺陷
第九章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會功能障礙及超掃描技術的潛在應用
第十章 超掃描視角下的社會溝通系統產生機制
第十一章 超掃描研究的困境與未來
書摘/試閱
摘要
認知活動在人際空間中得以豐富化,不同個體基於特定的規則在行動上進行協同,繼而產生複雜行為。已有的大多研究只考察了個體層面上的認知活動,但他人的思維活動已被證實對所考察個體的行為及腦活動具有明顯的塑造作用,這就意味著研究技術和觀察視角需要轉變,即實現從單一腦到群體腦的轉變。通過環境中特定的信息傳遞發生的不同個體腦活動的連接稱為腦―腦耦合。腦―腦耦合制約和塑造著同一社會世界中每個個體的行為,導致複雜認知行為的產生,而這種複雜的認知行為不可能在獨立的個體上產生。
第一節 社會互動的普遍性需要群體腦考察
一、 社會互動的普遍性
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互動很普遍,如傳授知識與技能、指揮與演奏以及與他人聊天等。個體的行為可以明顯地被周圍人所改變或塑造,同時個體也期望與周圍人發生社會互動,以至於遭到周圍人的隔離被視作一種懲罰或折磨,如最近的一項元分析顯示,社會隔離和孤獨是引發高死亡率的重要風險因素(HoltLunstad等,2015; Tanskanen和Anttila, 2016)。
我們經常與他人一起開心或悲傷,會因直接的相互感染而產生共同的情感體驗。然而,對這種體驗程度進行客觀衡量是非常困難的。研究發現,一個人的情緒可能讓他人產生完全不同的情緒,比如一個充滿攻擊性的人會讓周圍的行人產生恐懼的情緒體驗;而在母嬰之間經常發生的行為同步,可能反映了兩者的情緒調節,而不是共享相同的情緒狀態。
人們可以有意識或下意識地將感知到的他人的表情、手勢、身體姿勢、行為以及語調信息作為社會互動線索。繼而,從多個方面自動地協調各自的行動,包括從身體動作的同步到擁有相似的興趣或注意的傾向。這些在人際間發生的認知對準有助於判斷和理解他人的意圖和即將發生的行為。一個很恰當的例子是談話過程中的話語輪換。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下,話語輪換的時間間隔一般在幾百毫秒內,甚至可以發生交叉重疊(Stivers等,2009)。輪換間隔不只反映前一個講話者何時發音結束,實際上,談話雙方都會相互調准各自的行為,以至於能夠預測前一個講話者何時結束該輪次的講話。除此以外,相當部分的人際互動是以非言語形式發生的,比如眼神交流等。與這些明顯的具身性互動相對應,現代社會中還存在大量借助於科技工具實現的非具身性互動方式。如果配以具身性互動的情緒符號,可增強言語交流介導的社會互動。
他人的行為對於個體的認知活動發展有著重要作用,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言語溝通(verbal communication)。特定詞語的含義是由實際用法決定的,但是詞語的正確使用卻會隨時代、文化以及背景的變化而變化。詞語的正確使用依賴於群體內部(即言語溝通成員群體)所共有的一系列規則。為了掌握一門語言,個體必須與群體中其他成員在不斷的互動中,逐漸學會詞語的正確使用方法。因此,群體內部發生的人際互動將會從根本上塑造個體的思維與行為方式(Boroditsky和Gaby, 2010)。這種塑造作用還存在于諸如求愛行為、工具使用等非言語性的社會互動中,表現在個體以及群體內其他成員基於共同規則或習慣協調各自行為。
鑒於人類或高等動物的高度社會性特點,與他人進行互動對於個體的認知發展和幸福感,甚至整個社會發展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目前來看,隨著各種影像學技術和分析方法的飛速發展,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領域不斷擴展,極大地促進了人們對多種認知活動腦機制的理解,甚至已經將部分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大大地改變或改善了我們的生活水平。然而,絕大多數已有的神經科學實驗研究都忽視了社會互動的重要性,所涉及的研究範式僅關注了單個被試在完成認知活動時所對應的神經機制。該類實驗的典型特徵是,將人類個體或實驗動物從所處的自然環境中分離出來,置於一個密閉的實驗空間內,令其對研究者事先設計好的計算機程序進行反應或者單向互動。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研究框架就好比太陽系中托勒密體系的地心說一樣,認為各種星系都不可以影響地球物理過程(geophysical processes)。而現代對地球重力、運動軌道以及潮汐等的理解卻是建立於哥白尼的學說之上,該學說認為地球只是複雜的、相互作用的行星系中的一員。相同道理,若認知神經科學領域僅關注單個個體的認知活動,勢必會掩蓋腦―腦互動(braintobrain interaction)對認知活動的塑造作用。我們認為導致研究者忽視社會互動的重要性的可能根源在於: (1)社會互動所具有的極度複雜性、時間上的不可預料性;(2)在不斷變化的社會背景下採集影像學數據的挑戰性等。與此同時,人際互動過程中的刺激信息(比如瞬息萬變的面部表情等)不僅具有感覺信息特徵,而且人們對這類刺激的解釋可遠遠超出對該材料的即刻反應(Hari等,2015)。總之,僅考察社會互動中的單個大腦活動,而不去考察群體腦活動及其互動情況是不可能全面的理解社會互動,乃至單個個體認知過程的內在機制(Hari和Kujala, 2009)。
二、 腦―腦耦合
有機體從周圍環境中獲取信息是基於外部刺激與腦活動間的耦合,即刺激―腦耦合(stimulustobrain coupling)。不同刺激擁有不同形式的能量,如機械能、化學能以及電磁能等。有機體的感受器具有將不同形式的刺激信號轉換為神經衝動,繼而對環境中的信息進行編碼的能力。與此同時,有機體不僅僅是被動感知環境中的感覺信息,還可以通過移動感受器所在的相對位置去主動感知環境中的有效信息,如揮動手臂、轉動眼睛等(Schroeder等,2010)。有機體在獲得特定信息後,經過腦內複雜的整合過程,然後指導接下來的行為活動。
腦―腦耦合(braintobrain coupling)是指個體的大腦活動通過環境中特定信息的傳遞與另一個體的大腦活動發生的關聯。它也依賴於刺激―腦耦合所提供的信息。但是,腦―腦耦合的信息產生於另一個大腦或有機體,而非物理環境中無生命的物體。腦―腦耦合發生的另一個前提是發生耦合的個體必須具有在結構和功能上相同或相似的大腦。腦―腦耦合就好比是無線通訊裝置,兩個(或多個)大腦間可通過共享的自然環境以特定的信號進行溝通,如光、壓力以及化學物質等(Hasson等,2012)。信息傳遞過程中,發送者和接收者在行為上的協調伴隨著腦―腦耦合的產生,但其產生方式並不適用於人與周圍環境中的無生命物體間的單向互動方式。對發送者動作、感知覺或情緒變化的覺察可以誘發接收者產生相應的腦網絡激活水平的變化,該現象被稱為替代激活(vicarious activations)(Keysers和Gazzola, 2009)。如果發送者具有和接收者相同或相似的大腦或機體,接收者的替代激活模式會和發送者的激活模式相似,進而表現出明顯的腦―腦耦合現象。相反,如果接收者擁有與發送者完全不同的大腦或機體,則接收者的替代激活模式將會明顯有別於發送者的激活模式,也就無法呈現顯著的腦―腦耦合現象。因此,替代激活理所當然就成為不同個體間腦―腦耦合的特有機制。當然,接收者的腦活動可能會以更為複雜的規律與發送者的腦活動發生耦合(Riley等,2011)。
三、 腦―腦耦合在社會互動過程中產生
我們以社會溝通系統產生為例,試圖闡述腦―腦耦合現象產生的過程。任何溝通系統的出現或產生需要群體成員在特定情境下對特定信號所表達的含義持有共同的理解,而這種共同的理解必須通過互動式學習才能逐步建立起來。這種觀點得到越來越多科學發現的支持。聯合行為(joint behaviors)依賴于群體成員間對社會信息的精確感知。與群體內其他成員的互動情況會強烈影響著成員的行為發展,直至這些行為趨於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與此同時,通過替代激活以及更為複雜的模式產生腦―腦耦合。接下來,我們將嘗試以來自鳥類、人類嬰幼兒以及成年人的溝通系統產生的研究證據來描述社會互動介導的腦―腦耦合產生過程。
首先,以往關於鳥類鳴聲學習(song learning)的研究通過播放成年鳥鳴聲的錄音讓幼鳥逐步習得鳴聲技能。這種研究範式只能驗證幼鳥的歌唱學習是基於印記(imprinting)機制的假設。然而,這些研究非常明顯地排除了社會因素的影響,掩蓋了鳴禽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會通過與其他夥伴的互動來促進與提高學習效率的事實。鳴禽只有通過真實互動而非錄音才能學會鳴叫聲(Baptista和Petrinovich, 1984)。可以證實社會互動介導禽類鳴聲學習的最好例子來自對八哥的研究(White, 2010)。雄性八哥通過觀察雌性八哥的反應逐漸學會發出具有潛在吸引力的鳴叫聲(West和King, 1988)。另一方面,在聽到雄性八哥具有吸引力的鳴叫聲或部分元素時,雌性八哥會立刻揮動翅膀以示響應。對上述響應的感知進一步強化雄性八哥的行為,使其盡可能重複那些可以引起雌性八哥揮動翅膀的鳴叫聲元素,最終使得較為複雜的、更具吸引力的歌聲能夠成功吸引更多的雌性八哥。而雌性八哥則通過觀察和聆聽群體內其他雌性八哥的反應,而獲得自身對特定雄性八哥歌聲的喜好與偏好(FreedBrown和White, 2009; West等,2006)。因此,鳴禽的叫聲與偏好都是在社會互動過程中逐步衍生出來。
其次,人類嬰幼兒溝通系統的產生是另外一個能說明在社會互動中習得語言的例子。一個7~12個月大的嬰兒所發出的咿呀聲就表現出和環境語言(ambient language)的音高、節律乃至音節組成相匹配的特點。從咿呀聲到環境語言的聲學轉變是在幼兒及其照料者之間的互動中發生的。照料者對咿呀聲所做出的一致反應可以明顯強化特定的聲學構成,使得幼兒從中習得環境語言。對於這種類型的社會學習,包括了兩個互惠互動的過程,即(1)照料者必須對幼兒咿呀聲的聲學特徵比較敏感,並給予一致的響應;(2)幼兒必須能感知到照料者的響應,並相應地調整他們的發聲行為。事實上,照料者早在幼兒1歲時就已經對幼兒的咿呀聲給予響應,比如面對面模仿幼兒的發聲以及確立發聲―響應間的話語輪換等。接下來,照料者會給予幼兒特徵更為豐富的發聲作為響應,比如由元音―輔音構成的音節(GrosLouis等,2006)。通過綜合瞭解幼兒所關注的照料者的反應,我們得知照料者的反應對嬰幼兒的語言發聲具有非常顯著的影響(Goldstein等,2008)。
再次,研究表明成年人可通過互動產生一套全新的符號系統,並以此在群體內進行溝通,這也是社會互動介導社會溝通系統的強有力的證據。此類研究要求成對被試合作完成社會溝通系統產生任務,進而考察溝通系統產生的過程。由於被試彼此隔離,不能相互看見,也不能聽見對方的聲音以及觸摸到對方,唯一的溝通途徑就是通過計算機呈現特定的(反饋)信息,但這些信息不能是已有的信息呈現方式(比如字母、詞語以及數字等)(Hasson等,2012)。因此,為了達到溝通的目的,他們只有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視覺溝通符號系統。研究發現兩個(或多個)被試在積極互動時,很快就形成了用於溝通的全新視覺符號(Fay等,2008; Galantucci, 2005; Garrod等,2007; Healey等,2007)。隨著雙方不斷的互動,所創造出來的用於溝通的視覺符號的抽象性逐漸增強(Fay等,2008)。但是,被試間如果缺乏積極互動(即被試單獨而非在互動中創造出視覺符號)時,這些符號將不具備溝通的功能(Garrod等,2007)。另外,旁觀者雖然目睹了用於溝通的視覺符號產生的整個過程,卻因為沒有積極參與互動過程,不能有效地使用該視覺符號進行人際溝通(Fay等,2008; Galantucci, 2009)。這些研究證據充分表明行為上的互動對於新溝通系統的產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二節 言語交流與腦―腦耦合
一、 言語產生於耦合振盪
語言介導了眾多典型的人際交流活動。但是,在兩個個體的交流過程中,語言信號是如何傳遞和接收的?值得注意的是,個體間大腦信息的傳遞方式與個體內大腦不同部位間的信息傳遞方式很相似。單腦不同部位間的信號傳遞需要解剖學上的結構連接,表現為某部位的神經活動通過該結構連接去影響另外一個腦部位的活動。比如,一個自言自語的人可以根據特定背景下對自己聲音的監控進而調整自身的言語方式,即使自身意識不到這種調節方式的存在。在此過程中,運動皮層發出言語的一系列神經衝動,控制有機體產生相應的聲音信息,與空氣中的噪音混雜在一起。這種混雜在一起的聲音信息將返回到說話者的耳朵裡,進而激活聽覺感知系統,在需要時可作為一種反饋信息進一步指導運動系統調整語音的輸出。這就是人類(或靈長類動物)在嘈雜環境中會反射式提高自身聲音強度的原因。在這種情景下,大腦的運動系統和聽覺系統間的相互交流是通過空氣中傳播的聲音信息進行協調。而這種觀點自然而然地可以擴展到對話情景中的雙方,即說話者和傾聽者。
在言語交流過程中,兩個大腦通過特定的振盪信號建立明顯的耦合現象(如圖1-1)。就世界上的各種語言來說,言語信號在幅度上都有其各自的調整方式,如在強度上的增強與減弱等,這種幅度調整就構成了3~8赫茲頻率的節奏(Chandrasekaran等,2009; Drullman, 1995)。這種節奏正好與講話者的音節發音所需要的時間相匹配,即每秒說3到8個音節。研究顯示大腦中尤其是新皮層也可以產生相應的振盪或節律(Buzsaki和Draguhn, 2004)。眾多言語知覺理論認為言語的幅度調整節律很好地與3~8赫茲的theta頻段振盪匹配(Schroeder等,2008)。這就提示我們講話者的言語信號可以與傾聽者聽覺皮層的振盪活動發生耦合或共振(Giraud等,2007; Lakatos等,2005),該耦合可以顯著增強神經信號的信噪比,進而有助於改善聽覺。另外,多項研究顯示8赫茲以上的振盪破壞了言語信號,從而顯著降低了個體對言語的辨別能力(Saberi和Perrott, 1999; Shannon等,1995; Smith等,2002),並且減弱了聽覺皮層的參與度(Ahissar等,2001; Luo和Poeppel, 2007)。
上述耦合假說也可以擴展到視覺模態。人類經常以面對面的形式進行談話,在這個過程中同時使用了聽覺和視覺兩種模態。Sanders和Goodrich(1971)的研究結果證實了觀看講話者的面部可以明顯增強言語的理解性。在很嘈雜的環境下,如雞尾酒舞會上,觀看講話者的面部相當於將聲音的強度升高15分貝。這種視覺增強語音的原因是講話者嘴部的運動與言語信號的幅度調整緊密耦合在一起。因此,講話者嘴部3~8赫茲的運動振盪信息被傾聽者的視覺系統所捕獲,進而通過多感覺通道整合系統增強傾聽者大腦中由聲音誘發的腦活動水平(Luo等,2010; Schroeder等,2008)。
在上述情景中,講話者就像是播放言語信號的廣播站,所播出的信號以及背景音被傾聽者所感知。傾聽者事先進行了預調製以便於匹配講話者所具有的特異言語頻率,進而通過產生振盪起到放大言語信號的效果。言語信號遵從3~8赫茲的調製規律,正好大腦聽覺系統的振盪頻率也在3~8赫茲。為了進一步在噪音環境中放大言語信號,大腦發揮了將嘴部運動和具有共振特徵的言語聲音波相耦合的長處。因此,嘴部運動有助於將言語信號劃分成不同的音節,以便於傾聽者的大腦能有效地從信號中提取有意義的信息。基於腦―腦耦合框架,言語交流是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在互動過程中以產生腦活動振盪的方式出現。
二、 言語過程中的協調而等級化的對準
一旦大腦間通過言語信號實現了相互耦合,信息就可以被分享,人類可以有效地進行交流。人類交流方式可以分成兩種: 獨白(僅一個講話者發送信號,同時有一個或多個傾聽者接收信號)和對話(兩個或多個談話者必須在時間上進行各自行動的精確協同)。總體來講,人類交流(尤其是對話)很容易發生,原因是談話者間在時間上的互相對準(interactive alignment)過程中含有非常豐富的無意識成分(Garrod和Pickering, 2004; Pickering和Garrod, 2004)。在這種框架下,兩個談話者自然而然地將不同言語信號互相對準,其途徑是通過相互模仿來選擇言語聲音(Pardo, 2006)、語法結構(Branigan等,2000)以及詞語和意義(Garrod和Anderson, 1987)。例如,當Peter對Mary說:“我遞給兒子(John)午餐盒”時,Mary更可能說:“我遞給兒子外套”,而不是“我把外套給兒子”。然而,上述兩種說法體現出的意思是相同的。
互相對準的發生有以下兩個原因。首先,講話者的言語發生和傾聽者的言語理解之間相互耦合,這取決於兩者間共有的語言表徵。其次,講話者產生特定的言語表徵會啟動或激活傾聽者的言語理解並產生相應的言語表徵,致使傾聽者更可能在其言語過程中使用該言語表徵(Pickering和Garrod, 2004)。重要的是,互相對準可以發生在各種語言水平,從語音和語法到語義和語境等。此外,一種水平上的對準可以導致其他水平上更大的互相對準(Branigan等,2000)。例如,相對低水平的字或語法水平的對準可以導致情景模型中的關鍵水平上的對準(即談話者雙方對相同表徵的理解水平)。這種互相對準是通過將講話者在言語產生時的大腦活動與傾聽者言語理解時的大腦活動相耦合實現的。
第三節 實現腦―腦耦合的方式
一、 言語交流介導的腦―腦耦合
採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以下簡稱fMRI)技術,Stephens等人(2010)分別採集了講話者敘述一個自身真實的故事以及傾聽者在聽到這個故事的音頻材料時的腦活動,並通過時間鎖相的方法分析交流雙方腦―腦耦合的變化情況。結果顯示在交流成功條件下,講話者和傾聽者的腦活動在時序上呈現顯著的相關關係,即表現出明顯的腦―腦耦合現象。然而,在交流不成功條件下(即講話者使用傾聽者完全不懂的語言講相同的故事),上述發現的腦―腦耦合消失。更為有趣的是,傾聽者腦活動和講話者腦活動具有明顯的時間延遲,該時間延遲正好與談話者之間的信息流動所需的時間相同(Stephens等,2010)。這些結果表明講話者在言語時產生的腦活動誘發和塑造了傾聽者的腦活動。換句換說,兩者的腦活動存在一個明顯的因果關係。令人驚異的是,傾聽者的某些腦區活動早於講話者的大腦活動,這種期待相關的腦活動提示傾聽者能主動地預測講話者即將產生的發音。這種預測可以對較為嘈雜或模糊的信息輸入起到補償作用(Garrod和Pickering, 2004)。的確,傾聽者的這種期待相關的腦活動與講話者的腦活動間的耦合程度越高,行為上傾聽者的理解水平越好(Stephens等,2010)。講話者―傾聽者的腦―腦耦合揭示了談話者間具有時序對準的神經基礎。已有研究顯示在自由觀看電影或傾聽故事時,共享的外部信息輸入可以導致不同被試表現出相同的腦活動(Golland等,2007; Hanson等,2009; Hasson等,2004; Hasson等,2008; Jaaskelainen等,2008; Wilson等,2008)。總起來說,刺激―腦耦合是與特定環境事件中某一時刻的鎖相進行比較的,而言語交流介導的腦―腦耦合則解釋了時間和空間上相隔甚遠的信息是如何傳遞的。這種信息傳遞機制起作用的方式使得言語而非其他的外部刺激直接誘發交流雙方相似的腦活動。這是一種與物理環境相比更為自由,且極大地有利於人類交流系統的發展。
二、 非言語交流介導的腦―腦耦合
腦―腦耦合也可以通過手勢或面部表情等非言語信息實現。最早的相關實驗性研究來自于一項fMRI研究(Schippers等,2010)。研究者要求被試在掃描儀中完成看手勢猜字謎遊戲,信息發送者需要向接收者傳遞能體現詞語特徵的非言語性線索(如手勢),與此同時記錄其大腦活動,並視頻錄製信息發送者的手勢過程。接下來,信息接收者觀看相關錄像,同時記錄其大腦活動。運用格蘭傑因果分析(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 GCA)方法分析兩個大腦活動間時序上的關係,研究者發現接收者大腦活動在時序上的變化與發送者腦活動的時序變化呈現共變關係。進一步發現,接收者―發送者的腦―腦耦合存在於兩個神經網絡,即鏡像神經元系統相關腦區和心理理論相關腦區。該發現同時支持了在社會知覺過程中上述兩個神經網絡間相互協作的觀點(Keysers和Gazzola, 2007)。更有意思的是,對發送者和接收者在單腦上的分析沒有發現上述兩個神經網絡的活動,這展現了腦―腦互動分析在理解高級腦功能方面的長處(Schippers等,2009)。在另外一項研究中,Anders等人(2011)讓女性被試在磁共振掃描儀中表達特定的情緒,實時將錄像展示給其男朋友觀看。結果同樣發現了明顯的腦―腦耦合現象(Anders等,2011)。該研究提供了探討真實情景下的情緒識別以及情緒感染的神經基礎的有效研究手段和方法。
在手勢和情緒表達介導的人際交流研究中,每對被試都是自由選擇信息傳遞的內容,這就確保了人際互動的唯一性。研究顯示真實互動個體間的腦―腦耦合要遠高於沒有互動的個體間(即不同組被試的隨機分組)的腦―腦耦合(Anders等,2011; Schippers等,2010)。因此,腦―腦互動分析可以為考察交流背景下的特異性互動提供一種非常強有力的研究手段。
三、 聯合行動介導的協同作用
相互耦合的群體腦系統可以產生彼此分離的大腦所無法控制的複雜行為,很多種行為都需要成員間嚴苛的時空協作,如打籃球或駕駛帆船等。即使有些行為可以單獨執行,比如演奏一種樂器或獨舞等,但若置於一個群體執行的環境中,將會又快又好地完成。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聯合行為過程中,人們會內隱地在動作、知覺以及認知水平等多個方面發生耦合。比如在群體運動水平方面,在搖椅上的兩個人隨著搖椅節奏的耦合,其搖擺行為變得越來越一致(Richardson等,2007);兩個鋼琴演奏家在二重奏過程中手部的運動將趨近同步;當成對的吉他手一起演奏同一曲子時,人際間的行動協同伴隨著腦―腦耦合(Lindenberger等,2009)。在知覺水平上,當兩個人從不同的視角觀察同一個物體,並要求他們進行心理旋轉時,他們會逐漸相互適應對方的視角(Bockler等,2011)。
四、 聯合決策
已有研究充分表明個體的選擇行為經常會受到他人決策行為的影響而改變。Hampton等人(2008)發現在完成策略性遊戲過程中,決策者不僅要時刻觀察對方的行為,而且也要留意對手
如何應對自己的選擇,進而實時地調整自己的決策行為以達到最優化的決策後果(Hampton等,2008)。例如,在玩“石頭―剪刀―布”遊戲時,玩家會自動地模仿對手的策略性決策行為,即使這種模仿實際上會降低贏的概率(Aczel等,2015; Cook等,2012)。採用基於fMRI或腦電(以下簡稱EEG)的超掃描技術,記錄共同完成策略性遊戲任務時兩個人的大腦活動,可以探討遊戲雙方大腦受到彼此的影響(Babiloni等,2006; Montague等,2002; Tomlin等,2006)。信任遊戲中,受委託人的決策行為及其腦活動將會受到投資人所表達的社會性信息的影響。經過幾輪遊戲後,受委託人的尾狀核活動水平就可以預測投資人的期待行為,這種特性甚至可以出現在投資人揭示他的決策結果之前(KingCasas等,2005)。
然而,兩個大腦並不總是好於單個大腦(Bahrami等,2010; Kerr和Tindale, 2004; Yousefi和Ferreira, 2017)。Bahrami等人(2010)要求兩個被試共同完成一個低水平的知覺決策任務,考察兩個被試的視覺敏感度差異對決策任務成績的影響。研究發現當兩個視覺敏感度相同的被試在完成知覺決策任務時,成績顯著高於單個人的成績。而且,即使在沒有任何反饋信息存在的情況下,任務成績的提高也是存在的。但是,當兩個視覺敏感度有著較大差異的被試共同完成知覺決策任務時,其合作的任務成績反而顯著低於單個被試的任務成績(Bahrami等,2010)。該研究揭示了具有相同視敏度的兩人間的共享信息可以提高任務成績,而具有不同程度視覺敏感度的兩人間的共享信息則降低任務成績。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