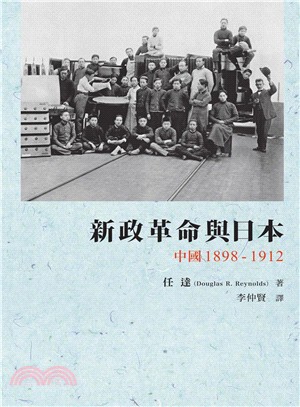商品簡介
本書對中國近代革命的分析框架作了根本性的修正。作者認為粉碎了經歷二千多年中國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學基礎的,不是以孫中山及其同伴為中心的1911 年政治革命,而是1901-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為中心的思想和體制的革命。
通過分析大量中日文第一手資料以及引證相關研究著作,本書對1898至1912年間中日兩國在司法體制、軍事體制、教育體制、翻譯出版等方面深入的合作與交流作了細緻的考證和比較研究。
在這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日本各界積極地給中國提供直接且實質性的幫助,使中國可以快速打破傳統控制而向現代化邁進,其速度之快甚至一度超過日本明治維新的進程。結束帝制後的中國,也正是以新政革命及其成就作為基石才得以決定思想和體制的發展方針。檢視這段歷史將有助於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的風雲變化。
本書特色:
1. 作者將1898至1912稱為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從日本自身的軍事和非軍事的變革及其背景入手,作者論述了現代化的日本在思想上以及政治體制上對中國的影響。思想上包括中國人赴日留學、日本學者在中國進行教學和顧問活動以及學界對翻譯和出版工作的促進。體制上則提到在中國開展的日本式的教育改革;軍事現代化、警察、監獄系統及至法律、司法和憲政改革都以日本的模式為藍圖。
2. 作者為繁體中文版作了新序,對本書英文版1993年出版以來清末新政研究取得的新的進展進行了梳理和綜述。
作者簡介
目次
繁體中文版序
前言
英文版序 概念的形成
導言
第一編 日本的作用及其背景
第一章 「黃金十年」?新政革命?
第二章 「黃金十年」的序曲
第三章 兩面開弓的日本戰略:軍事的和非軍事的
第二編 新政思想革命:新載體,新概念
第四章 中國學生及其入讀的日本學校
第五章 在中國的日本教習和顧問
第六章 翻譯及現代詞彙
第三編 新政體制革命:新的領袖,新的管理
第七章 中國的教育改革:日本的模式
第八章 中國軍事現代化與日本
第九章 中國新的警察及監獄系統
第十章 中國的法律、司法和憲政改革:日本的藍圖和顧問
結束語
附錄 I
附錄II
註釋
譯後記
書摘/試閱
導言
本研究建構在實證基礎上,這些實證主要取自原始材料及引證日本和中國的學術成果,把長期受忽視或大量遺忘的事實第一次集中起來。這些事實表明了令人吃驚的情況,並要求按如下線索,對中國近代革命的分析架構作根本性的修正。
粉碎了經歷2,100年中國帝制政府模式及其哲學基礎的,不是以孫中山(1866—1925)及其同伴為中心的1911年政治革命,相反地卻是1901—1910年以晚清政府新政為中心的思想和體制的革命。按本書分析,1911年革命的主要意義,是保證了新政年代的思想和體制改革繼續存在──既不後撤,也不走回頭路。同時,新政革命及其成就,自1911年後一直成為實際的基石,雖然不受承認卻也沒有公開宣告。結束帝制後的中國,正是在這基石上決定思想和體制的方針,以至今時今日。
如果以人們更為熟悉的方式表達,那就是中國僅僅在12年內──從1898年百日維新的「失敗」到1911年革命的「失敗」──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按本書研究,1898年的百日維新運動與其說是失敗的,毋寧說是中國經受了一次世紀之交的轉變、「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第一大步跨進。在不少重要方面,保守的改革努力都取得了成就。1899—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後,慈禧太后(1835—1908)不得不下定決心,發起並推動了徹底的新政改革。從朝廷到各省,一批官員把改革推向前進,他們主要有張之洞(1837—1909)、袁世凱(1859—1916)、慶親王奕劻(1838—1917)、張百熙(1847—1907)、趙爾巽(1844—1927)、端方(1861—1911)、岑春煊(1861—1933)和沈家本(1840—1913)等。這些重要的和其他成千上萬次要人物的事業和成就,為結束帝制後的中國,以至今日奠定了基礎。為了強調其影響超越1911年,本研究至1912年止。
新政革命主要有思想和體制兩方面,如果不以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為比較,對兩者都難於理解。事實上,日本是作任何分析的關鍵參照對象。如果沒有日本在各種各樣的幌子下、在不同的層面上表示合作,中國不可能打破傳統控制而向現代道路邁進。中國思想和體制轉變得非常順利快速,甚而一度超過日本明治維新的進程。日本所扮演的角色、中國對日本模式和對個別人士令人驚奇的信心,將在本書第一、二、三章逐一解釋。
理解近代中國在學術上的主要障礙,是對革命的定義規限得太狹窄,這蒙蔽了學者們的眼睛,難於理解延續最長的中國近代革命、靜悄悄的新政思想和體制革命。1500年以來的世界史不斷地提醒人們,革命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大多是非暴力的、不流血的。正如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中指出的,革命可能悄悄地進行,令人感覺不到,從農業、商業、經濟革命,擴展到思想、科學、技術革命,以至政治、社會革命。就中國而論,晚清時期不僅有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而且有更具深遠影響的思想和體制的轉變。把清王朝的最後十年,從有關1911年革命的因循思想中解脫出來,從那些對革命粉飾之言中解脫出來,對中國帝制後期和帝制結束以後的真正革命轉變,便較為容易理解了。
1911年後,置身舞台中央的激進分子和革命者改寫了歷史,藉清王朝突然崩潰而索取榮譽。他們,無論是清朝的對立者或充其量只是沾了點邊的人,對晚清改革既無認識也並不感興趣。真實的歷史紀錄還未來得及詳細查證或整理前,中國已陷1916—1928年狂暴的軍閥混戰中。由於混亂被弄得稀里糊塗,由於清王朝在人民記憶中迅速消失,因而極少有人能清楚地看到,中國軍閥和晚清的創新改革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在軍閥混戰的十年中,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他至死仍忠於他的信念,要擺脫軍閥和帝國主義,鼓勵人們支持他的事業。他生前是「受挫折的愛國者」,死後仍是受挫折的愛國者。
孫的逝世,促使人們更熱切地尋求困惑了孫一生的答案:如何填補結束帝制後在精神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絕望的真空。那些早期的親密夥伴如汪精衛(1883—1944)、胡漢民(1879—1936)和蔣介石(1887—1975)等,他們宣傳孫,只是把孫看作團結全國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獨一無二的有效的象徵;更重要的是把孫視為基石,他們在此基礎上為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成為正統而下賭注。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期,孫因1911年革命獲得哀榮,被尊為「國父」,以至於把那次革命也變成「孫的1911年革命」。這觀點成了中國的信條。
在因循襲舊的歷史上,那些站在「孫的1911年革命」之外的人們,總被視為革命的對立者或敵人。頭號敵人是袁世凱,他是新政改革的骨幹人物,1912—1916年的民國總統。他沒有大吹大擂,卻在結束帝制後的中國繼續進行改革。在1915—1916年,他企圖建立君主制而沒有成功,這就注定了他要貼上民國叛徒的標籤;由於他和新政改革關係密切,那些改革和改革支持者們也成了協同犯而埋進墳墓。至於日本,它在新政期間所起的核心作用完全被遺忘了。在1915年不光彩的21條要求後,任何回憶都只能起相反的作用,遭受批駁。
在歷史上有過重大成就、使人驚歎的中國新政變革,就這樣被遺忘了。教科書和專題著作,都沒有把清朝革命性的轉變,看作從1898年傳統的中國政治形態,到1911—1912年近代的,調和日本—西方—中國的政治形態的飛躍。新的政治形態儘管有缺陷和實施時搖擺不定的軟肋,它終究是應時而生的。事實上,我們所認識的今日(而且在可以預見未來的)中國,正是完全以新政年代的思想和體制為基礎。離開新政革命,20世紀的中國是不可想像的。
本書第四章以後逐章為日本參與新政革命提供證據。本研究僅僅是個開端。差不多每一章都需要單獨的專著加以發揮。希望這一研究能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第一章
「黃金十年」?新政革命?
中國在1898—1910年這12年間,思想和體制的轉化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在整個過程中,如果沒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為中國的樣本和積極參與者,這些成就便無從取得。和慣常的想法相反,日本在中國現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設性而非侵略的角色。不管怎樣,從1898—1907年,中日關係是如此富有成效和相對地和諧,堪稱「黃金十年」。這黃金十年的關係,一再證明了對中國新政改革的成功具有何等作用。本章以回顧這一概念開始,於第二、三章詳述日本扮演的角色及其背景,進一步為「黃金十年」這一概念提供確證。
中國的新政改革的結果很不平衡,也的確帶着缺陷,但多方面同時舉行、迅速而不動聲色的改革,徹底地粉碎了中國2,000多年的帝制歷史,把中國置於延至今日的帝制後的過程。對中國而言,成效是革命性的,或者可稱之為「新政革命」。本章的第二部分,將檢核「新政革命」這一概念。
「黃金十年」?
表面看來,「黃金十年」的概念似乎不可理喻。在慘烈的中日戰爭和簽訂《馬關條約》之後不久,中日雙方似乎不可能有密切的關係。這概念與一切邏輯都背道而馳,而這些邏輯又已深深地植根於中日人民心中。在中國人民心中,它觸發起1937—1945年日本野蠻地侵略中國所引起的全面戰爭的焦灼回憶;在日本人民心中,則觸發起在戰爭中累積的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感。時至今日,中日學者仍未能從這些往事中擺脫出來。
某種懷疑主義當然是必要的。例如,從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整段時間內,完全可以不加遲疑地視之為是日本從未間斷對中國和中國周邊侵略的時期。在19世紀末期,從1874年開始,日中之間的軍事對抗幾乎每十年必會爆發一次:1874年,日本對台灣懲罰性的遠征;1884年,中日軍隊在朝鮮發生衝突;1894—1895年,日中爆發全面戰爭。
到了20世紀,衝突的步伐加快了,日本每五年左右便挑起一次軍事行動:1900年,日本參加反義和團的八國聯軍,及由於日本的阻攔造成「廈門事件」慘敗;1904—1905年日俄戰爭,日本取得在中國東北和朝鮮的特權;1910年日本完全吞併朝鮮;1914—1915年,日本軍隊接收了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和特權,和德國在太平洋的領土;1918—1922年,日本遠征西伯利亞;1927—1928年,日本在山東武裝干涉,反對中國北伐軍;1931年滿洲事件;1932年日本軍隊攻擊上海;1933—1937年,日本在華北發動一連串軍事行動,導致1937—1945年中日全面戰爭,為時長達八年,毀滅性的戰爭遍及全中國,在戰爭中犧牲者數以百萬計。
然而即使在日本侵略擴張的20世紀30年代,仍有個別人回憶當時中日關係較為美好的時光。1936年,研究中國的日本學者神崎清在《支那》月刊作了相當詳細的描述,他寫道:
日本在義和團事件中參加了八國聯軍,使日本在中國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得以提高,它在處理軍事和國際關係方面的公正態度,贏得了中國人的信任。日本主要通過在軍事、警務和教育方面的領導,直接參與了清政府的改革,擴展了新的日支關係。清政府正想方設法避免西方侵略,日本政府也正千方百計遏制西方的滲透。在日俄戰爭前後,圍繞着這一共同利益,出現了日本人稱之為對支外交的黃金時代。
1943年,實藤惠秀把1896—1905年間稱為中國「純粹的親日時代」。而在四年前,1939年,實藤就寫道:「只要注意現代時期,特別是日清戰爭後到日俄戰爭之間的年份,是日、中兩國無比親和的時期。關係密切得使其他外國人妒忌。」
他最後一句說得絕不誇張,那是事實,在20世紀初期西方刊物中就說得非常明顯。例如早在1901年7月,在上海的潘慎文牧師(Rev. A. P. Parker)在題為《日本對中國新的侵略》一文中就提出:
思想的侵略取代武器的侵略,教育的宣傳取代壓迫。狡獪地企圖以思想力量多於物質力量以征服中國。
簡言之,這就是在日本人的佈置下,現正迅速地擺到中國面前的事態,在過去短短幾年中,日本人的行徑已經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潘慎文的文章特別注意到日本學生在上海(1901年5月底)開設的東亞同文書院(後升格為大學)的開學典禮,報道了中國官員發表的熱情洋溢的歡迎詞,預期書院對中國長遠的價值是「反抗白種人對東亞統治的重要支持」。東亞同文書院的確發展為出色的學院,不過從根本上說,日本的得益是遠遠超過中國的。西方的嫉妒和焦慮,在喬治‧林奇(George Lynch)《中國的日本化》一文中,表露無遺。無獨有偶,雷里‧賓茹(Rene Pinon)也寫了《中國的日本化》,文章宣稱,「這個新的中國將是日本人的中國」,他繼而解釋道:
在日本影響下,(中國)已決定進行改革並付諸實施,(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有關「大清國之教育改組」的報告……是直接受日本體系啟發的……是宣佈除外語教員外,全部教員都應在日本選聘。事實上,最近成立的師範學堂,所有外籍教習都是日本天皇的臣民……是不用說,這些日本人的教育使命必定產生巨大的影響。
上海德國總領事1905年的秘密報告,同樣讓人感到憂心忡忡:
除了日本商業和工業的發展足以令人吃驚外,我僅指出兩方面以提高我們的警覺:第一,日本以龐大的國庫補助,促進海運繁榮,保護並獎勵貿易擴張;第二,通過東亞同文會等機構,熱心發展中國教育,同時通過開辦上海東亞同文書院,銳意培養能在中國活動的自己人。為了對抗這一切,德國政府必須提供大量補助,積極保護航海,並在揚子江地區,嘗試大規模設立培養華人的學校,放手傳教。
再引述一段,就足以代表消息靈通的西方輿論對當時日本在中國的看法。與清廷聯繫密切的著名的英國新教徒、教育學家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於1906年著文稱:
然而,北京可能注視着東京,很明顯,日本對中國18省的影響在不斷地擴大,日本遊客、商人、教員、軍事教官,在帝國無遠弗至。中國貴族和統治階級成千上萬的子孫在日本受教育,回國後按在日本所學,依樣畫瓢。中國本地最好的報紙是日本人控制的,而本地報業蓬勃發展,本身就是所有革命現場中最具重要性的……我們希望日本影響的擴張不會令人猛然一驚,相信日本真正的政策不是要強迫中國成為西方文化或思想的虛偽模仿者,而是使用西方的配件,以保存東方生活和政體的根基。
在這種西方(通常是傳教士的)評論的背後,表明了西方(首先是與傳教有關的)對中國改革影響迅速減弱的嚴重關注。在1895—1898年間,西方的影響曾達頂峰,而結果卻是中國耻辱地戰敗於日本。立志改革的中國愛國人士,曾經向具有改革思想的或以前的傳教士們請教,例如李提摩太、林樂知(Young J. Allen(1836—1907))、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傅蘭雅(John Fryer, 1839年生)及丁韙良(W. A. P. Martin(1827—1916))等。他們正像歷史學家柯文(Paul Cohen)寫的,「在動盪不定的時刻」,欣賞那「超出了他們最狂熱夢想」的影響。
構成這些影響的原因之一,是某些老傳教士視野開闊了。例如,李佳白於1897年就中國政府和外國顧問的問題,提出一些老於世故的想法。鄒明德綜合如下:
李佳白認為中國改革需要向西方學習,因為中國已經進口了不少西方的機器,出版了西方的科學著作,他說有必要評估其有利和不利方面。他還強調,遴選足具資格的西方人擔任中國官員的重要性,這是李提摩太已經提過的⋯⋯李佳白強調,指派外國人為中國官員時,除他們的能力、威望和德行外,不應擔當令中國人敏感的職位,而必須對「中國古代仁政」有充分理解,樂於堅守「中國的聖道」。他們還應有能力區別哪些是中國應該向西方學習的,哪些是不合適的。
這明智的忠告馬上面對一個無從解決的難題:中國政府到哪裏一下子找那些具有專業資格、文化修養甚高、通曉中國語言和經典的西方人士呢?
在1899—1900年義和團之亂期間及以後,西方傳教士的影響驟衰。柯文指出的兩點有助於了解這一變化。首先是政治分裂事件出現,老一輩的改革者反對激進派和革命分子,導致大多數傳教士及其他人黯然離去;其次,更具決定性的是,「要獲得中國以外世界的訊息,還有可供選擇的途徑(也是大多數中國人較易接受的途徑)」,突然出現。
本書驗證了「可供選擇途徑」的開通和它的驚人後果。必須強調的是,那些「可供選擇的途徑」遠超過僅向中國提供「訊息」。隨着訊息而來的,還有方針、具體實施和協助訓練。最好的「選擇途徑」,十居其九是日本人。那些個人兼具專長與文化素養,完全符合李佳白的要求。的確,除了日本人之外,還有誰符合李佳白提出的標準呢?李佳白的忠告,不妨讀作「非日本人毋庸問津」。中國官員們對此是充分認識的,在1901—1911年間,僱用了數以百計的日本人,卻將大量的西方人拒於中國新政改革之外。
僱用了日本人,西方人的恐懼便接踵而來,擔心日本人取代了白種人和他們的思想在中國的優勢,甚而想像出黃種人聯合起來反對白種人的畫面。不要忘記,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這樣的年代,總過分擔心着白種和有色人種大規模的種族鬥爭迫在眉睫。「黃禍」之說在德國盛行;日本自身早在1898年1月,就宣揚種族戰爭的思想。高貴的近衛篤麿公爵(1863—1904),就在當時日本發行量最多,影響最大的雜誌《太陽》40上發表煽動性的文章,文章的題目就是劍拔弩張的《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的必要》。
近衛寫道:「我認為,東亞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未來人種競爭的舞台。外交策略雖然可能發生一時的變化,但也僅是一時的變化。我們注定有一場白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將被白人視為盟敵。有關未來的一切計劃,都必須把這一難點銘記心中。」這位作者是一位信念堅定的日本公爵,與日本和國外聯繫甚廣,是中日緊密合作鼓吹者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這就掀開了「黃金十年」的面紗,不但履及劍及,而且賦予深意。
針對日本人在華取得的成就,英、美、法、德改變策略,對中國發動強大的文化外交和文化爭奪。1908年1 月,美國即將離任的羅斯福總統參與爭奪,他宣稱「治療『黃禍』的藥方,不管它叫甚麼?」,都必須使「(中國人的)教化和生活準則」依循美國的教育和基督的教義。為了付諸實施,羅斯福於
西方在中國利益的增長和主動進取的增強,構成了對日本在中國特殊地位的挑戰。離開當時西方的進取和追求,就難以理解中國何以於1908—1909年決定在尋求先進的教育和訓練方面,由依靠日本轉向依靠西方。
新政革命?
西方歷史學家運用「革命」一詞時,含義是相當廣泛的。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血腥的戰爭──反對英國統治的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靜悄悄的」革命──農業革命、商業革命、科學及思想革命、工業革命,以至性革命和通訊革命,不那麼具有戲劇性,但重要性卻毫不遜色。
撇開不同的情況,怎樣才能使用「革命」一詞,湯瑪斯‧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了基本論點。他認為,人類思維以特殊方式構建世界,這就是典範(paradigm)。科學革命的結果,是「相對新的典範全部或部分取代舊的典範」。把這論斷延伸到政治領域,孔恩認為,政治革命源於「增長中的觀念……現存的架構已不足以應付存在的問題……在政治和科學發展中,失靈的觀念導致危機,是革命的先決條件」。孔恩甚而把各章的標題都使用「危機」、「對危機的反應」、「世界觀轉變的革命」,革命的「無形性」及「革命的解決」等。
換句話說,革命涉及事情被認知的方法的結構,或是實際關係的結構(例如政治的或社會的),或者完成事情的方法的結構,例如在農業和商業領域,上述幾種結構的巨變。變化可能突然而來,但卻無需暴力,例如今日的通訊革命;又或者變化來的既突然又充滿暴力性,例如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本研究的焦點是1911年前夕中國「靜悄悄的革命」,在1898—1912年,特別是1901—1910年間,中國在思想和體制方面,把長期形成的典範變為不同質的外來典範。中國統治階層的精英,方向轉變得如此激烈和持久,人們可以毫不猶疑地把它定性為革命,或者說是「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併,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內悉條議以聞。
梅里貝斯‧卡梅倫(Meribeth Cameron)稱之為「改革運動憲章」的、雄心壯志的上諭,在精神、意圖和成就上,都堪與大名鼎鼎的、簡潔的1868年明治《五條御誓文》相匹敵。後者的第五條內容,便是「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訂定《五條御誓文》以後,便開始明治維新時政治上的掃蕩,社會及思想上的轉化,明治維新其實應稱為「明治轉變」或「明治革命」。
明治《五條御誓文》和晚清的改革上諭,都是尋求外國知識以加強「皇基」,絕非削弱他們既得的成就。日本現代史學者普遍把1868年的《五條御誓文》作為日本向外部世界開放的精神信號,確立了延續到今天江戶時代以後的進程。另一方面,中國近代史學者卻忽視1901年的改革上諭,雖然它所完成的恰恰是帝制後中國所要做的事:向外部世界發出中國開放精神的信號,把中國置於帝制後的進程。它的結果是革命性的,它把中國歷史的進程根本且永久地改變了。
才華出眾的梁啟超(1873—1929)於1898—1912年流亡日本,在14年間,撰寫了當時幾乎所有最重要的論著。他在1904年4月發表的《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寫道:「革命主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此前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兵力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的革命。」他探討中國歷史上的革命類型,把革命規限於武裝起義反對政府的最狹義上,因而對本研究毫無補助,但他的意見仍然是恰當的。本書論及的新政革命,介乎梁論述的第一和第二種定義之間:開闢了新紀元,超出了狹隘的政治範疇,包括思想和體制根本轉變的革命。
清廷從未提「新政」一詞,也未對改革的目的系統地解釋,其真實含義近似於「新的政治體制」,包括教育、軍事、警務、監獄、法律、司法和立憲政府。新政改革的成就,遠遠超過了發起者的意圖或想像。雖然未能達到梁啟超提出的革命最廣義,改造「社會一切無形有形」的因素。無論如何,它終歸提供了理解新世紀中國的必不可少的基線。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