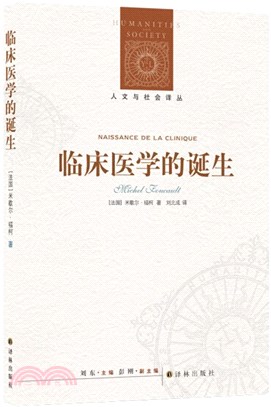臨床醫學的誕生(簡體書)
- 系列名:人文與社會譯叢
- ISBN13:9787544715782
- 替代書名: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 作者:(法)米歇爾‧福柯
- 譯者:劉北成
- 裝訂/頁數:平裝/222頁
- 規格:21cm*14.8cm*1.1cm (高/寬/厚)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20/08/0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法國思想家福柯重要作品,從哲學層面深刻剖析現代醫學誕生史
福柯以“空間、語言、死亡”為線索追溯現代醫學的起源,指出在十八世紀的後幾年,歐洲文化勾畫了一種新的結構,此後它一直構成“我們經驗的陰暗而堅實的網”。
從家庭到醫院,從“健康”到“正常”,解剖知識的應用,科學的“凝視”……我們習以為常的就醫方式背後,是認知和社會結構的一系列深刻變化。受疫情洗禮的21世紀人類,反思這些文化轉變的影響,或能獲得更多啟示。
------------
作為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創立者,米歇爾·福柯首先是一位文化理論家。他的研究遍及社會科學和人類學的各個領域,並且產生極一為廣泛的影響,瘋癲、性、醫學史、著作活動本質、文學及犯罪、編史實踐、教養所之發展、現代社會的權力及話語的本質,這些僅僅是福柯極有見解和見識地著述過的眾多課題中的一部分而已。
——安德魯·薩克爾(烏爾斯特大學)
作為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創立者,米歇爾·福柯首先是一位文化理論家。他的研究遍及社會科學和人類學的各個領域,並且產生極為廣泛的影響,瘋癲、性、醫學史、著作活動本質、文學及犯罪、編史實踐、教養所之發展、現代社會的權力及話語的本質,這些僅僅是福柯極有見解和見識地著述過的眾多課題中的一部分而已。
――安德魯·薩克爾(烏爾斯特大學)
序
前言
這是一部關於空間、語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論述的是凝視。
十八世紀中期,波姆在治療一個癔病患者時,讓她“每天浸泡十到十二個小時,持續了十個月”。目的是驅逐神經系統的燥熱。在治療尾聲,波姆看到“許多像濕羊皮紙的膜狀物……伴隨著輕微的不舒服而剝落下來,每天隨著小便排出;右側輸尿管也同樣完全剝落和排出”。在治療的另一階段,腸道也發生同樣的情況,“腸道內膜剝落,我們看到它們從肛門排出。食道、主氣管和舌頭也陸續有膜剝落。病人嘔出或咯出各種不同的碎片”。
時間過去還不到一百年,對於醫生如何觀察腦組織損傷和腦部覆膜,即經常在“慢性腦膜炎”患者腦部發現的“假膜”,有如下描述:“其外表面緊貼硬腦膜蛛網層,有時粘連不緊,能輕易地分開,有時粘連很緊,很難把它們分開。其內表面僅僅與蛛網膜接近,而絕不粘連……假膜往往是透明的,尤其當它們十分薄時;但它們通常是微白色、淺灰色或淺紅色的,偶爾有淺黃色、淺棕色或淺黑色的。同一片膜的不同部位往往顏色深淺不一。這些非正常產生的膜在厚度上差異很大,有的如蜘蛛網那樣纖薄。……假膜的組織也呈現出很大的差異:纖薄的呈淡黃色,像雞蛋的蛋白膜,沒有形成特殊的結構。另外一些在其某一面呈現出血管縱橫交錯的痕跡。它們可以被劃分成相疊的層面,各層之間常有不同程度退色的血塊凝集”。
波姆把舊有的神經系統病理學神話發展到了極致,而貝勒早在我們之前一個世紀就描述了麻痺性癡呆的腦部病變。這兩種描述不僅在細節上不同,而且在總體上也根本不同。對於我們來說,這種差異是根本性的,因為貝勒的每一個詞句都具有質的精確性,把我們的目光引向一個具有穩定可見性的世界,而波姆的描述則缺乏任何感官知覺的基礎,是用一種幻想的語言對我們說話。但是,是什麼樣的基本經驗致使我們在我們確定性知識的層面下、在產生這些確定性知識的領域裡確立了這樣明顯的差異呢?我們怎麼能斷定,十八世紀的醫生沒有看到他們聲稱看到的東西,而一定需要經過幾十年的時間才能驅散這些幻想的圖像,在它們留下的空間裡揭示出事物真實的面貌?
實際發生的事情不是對醫學知識進行了“心理分析”,也不是與那種想像力投入的自發決裂。“實證”醫學也不是更客觀地選擇“客體”的醫學。也不能說,那種讓醫生和患者、生理學家和開業醫生在其中進行交流的想像空間(拉長或扭曲的神經,灼熱感,硬化或燒焦的器官,由於涼水的有益作用而康復的身體)喪失了所有的權力。實際情況更像是,這些權力發生位移,被封閉在病人的異常性之中和“主觀症狀”的領域中。對於醫生來說,這種“主觀症狀”不是被定義為知識的形式而是被定義為需要認識的客體世界。知識與病痛之間的那種想像聯繫不僅沒有被打破,反而被一種比純粹想像力的滲透更複雜的手段強化了。疾病以其張力和燒灼而是在身體裡的存在,內臟的沉默世界,身體裡充滿無窮盡的無法窺視的夢魘的整個黑暗淵藪,既受到醫生的還原性話語對其客觀性的挑戰,同時又在醫生的實證目光下被確定為許多客體。病痛的各種形象並沒有被一組中立的知識所驅逐,而是在身體與目光交彙的空間裡被重新分佈。實際上發生變化的是那個給語言提供後盾的沉默的構型:即在“什麼在說話”和“說的是什麼”之間的情景和態度關係。
從什麼時候起、根據什麼語義或語法變化,人們才認識到語言變成了“理性話語”?把假膜說成是非同一般的“濕羊皮紙”的描述,與同樣富有隱喻地把它們說成是像蛋白膜一樣覆蓋在腦膜上的描述,這二者是被什麼分界線截然分開的呢?難道貝勒所說的“微白色”和“淺紅色”假膜就比十八世紀醫生所描述的鱗片具有更大的科學話語價值、有效性和客觀性?一種更精細的目光,一種更貼近事物、也更審慎的言語表達,一種對形容詞更講究、有時也更令人迷惑的選擇,這些變化僅僅是醫學語言風格的延續,即自蓋倫醫學以來一直圍繞著事物及其形狀的灰暗特徵而擴展描述的領域的風格的延續嗎?
為了判定話語在何時發生了突變,我們必須超出其主題內容或邏輯模態,去考察“事物”與“詞語”尚未分離的領域——那是語言的最基礎層面,在那個層面,看的方式與說的方式還渾然一體。我們必須重新探討可見物與不可見物最初是如何分配的,當時這種分配是和被陳述者與不被說者的區分相聯繫的:由此只會顯現出一個形象,即醫學語言與其對象的聯結。但是,如果人們不提出回溯探討,就談不上孰輕孰重;只會使被感知到的言說結構——語言在這種結構的虛空中獲得體積和大小而使之成為充實的空間——暴露在不分軒輊的陽光之下。我們應該置身於而且始終停留在對病態現象進行根本性的空間化和被言說出來的層次,正是在那裡,醫生對事物的有毒核心進行觀察,那種饒舌的目光得以誕生並沉思默想。
現代醫學把自己的誕生時間定在十八世紀末的那幾年。在開始思索自身時,它把自己的實證性的起源等同於超越一切理論的有效的樸素知覺的回复。事實上,這種所謂的經驗主義並不是基於對可見物的絕對價值的發現,也不是基於對各種體系及其幻想的堅決擯棄,而是基於對那種明顯和隱蔽的空間的重組;當千百年來的目光停留在人的病痛上時,這種空間被打開了。但是,醫學感知的甦醒,色彩和事物在第一批臨床醫生目光照耀下的複活,並不僅僅是神話。十九世紀初,醫生們描述了千百年來一直不可見的和無法表述的東西。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擺脫了冥思,重新恢復了感知,也不是說他們開始傾聽理性的聲音而拋棄了想像。這只是意味著可見物與不可見物之間的關係——一切具體知識必不可少的關係——改變了結構,通過目光和語言揭示了以前處於它們的領域之內或之外的東西。詞語和事物之間的新聯盟形成了,使得人們能夠看見和說出來。的確,有時候,話語是如此之“天真無邪”,看上去好像是屬於一種更古老的理性層次,它似乎包含著向某個較早的黃金時代的明晰純真的目光的回歸。
一七六四年,梅克爾JFMeckel,德國解剖學家。——譯註對某些失常(中風、躁狂、肺結核)引起的腦部變化進行研究;他使用理性的方法,稱算同樣大小的腦組織的重量加以比較,從而判定腦組織哪些部分脫水了,哪些部分膨脹了,病因何在。現代醫學一直幾乎不利用這項研究成果。腦組織病理學是在比夏、尤其是雷卡米埃爾和拉勒芒之時才達到這種“實證”形式。比夏等人使用“帶有又寬又薄頂端的著名小槌。如果連續地輕輕打擊,因為頭顱是充實的,就不會造成腦震盪。最好是從頭顱後方開始敲擊,因為在必須打破枕骨時,枕骨會滑動,使人打不准。……如果是一個非常小的孩子,骨頭會很柔軟,難以打破,而且骨頭又很薄,無法使用鋸子。那就只能用大剪子來剪斷”。硬果被打開了。在精心分開的外殼下面露出灰色的物質,裹著一層黏滯的含有靜脈的薄膜:一團嬌嫩而灰暗的肉團,它隱藏著知識之光,最終獲得解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破顱者的手工技藝取代了天平的科學精密性,而我們的科學自比夏之時起就與前者合而為一;打開具體事物充實內容的那種精細但不加以量化的方式,再加上把它們特性的精緻網絡展現給目光,對於我們來說,反而產生了比武斷的工具量化更科學的客觀性。醫學的理性深入到令人驚異的濃密感知中,把事物的紋理、色彩、斑點、硬度和黏著度都作為真相的第一幅形象展現出來。這種實驗的廣度似乎也是目光所專注的領域,只對可見內容敏感的警覺經驗的領域。眼睛變成了澄明的保障和來源;它有力量揭示真實,但是它只是感受到它能夠揭示的範圍;眼睛一旦睜開,首先就揭示真實:這就是標誌著從古典澄明的世界——從“啟蒙運動時代”——到十九世紀的轉折。
對於笛卡兒和馬勒伯朗士來說,看就是感知(甚至在一些最具體的經驗中,如笛卡兒的解剖實踐,馬勒伯朗士的顯微鏡觀察);但是,這是在不使感知脫離其有感覺的身體的情況下把感知變得透明,以便讓頭腦的活動通行無阻:光線先於任何凝視而存在,它是理念——非指定的起源之地(在那裡事物足以顯示其本質)——的要素,也是事物的形式(事物借助這種形式通過實體的幾何學達到這種理念);按照他們的觀點,觀看行為在達到完美之後,就被吸收到光的那毫不彎曲和沒有止境的形像中。但是,到十八世紀末,觀看則意味著將最大限度的實體透明性交給經驗;封閉在事物本身之內的堅實性、晦暗性和濃密性之所以擁有真實之力度,不是由於光,而是由於緩慢的凝視,後者完全憑藉自己的光掃視它們,圍繞著它們,逐漸進入它們。弔詭的是,真相之深居事物最隱晦的核心,乃是與經驗凝視的無上權力相聯,後者將事物轉暗為明。所有的光亮都進入眼睛的細長燭框,眼睛此時前後左右地打量著物質對象,以此來確定它們的位置和形狀。理性話語與其說是憑藉光的幾何學,不如說是更多地立足於客體的那種逼人注意的、不可穿透的濃密狀況,因為經驗的來源、領域和邊界以模糊的形式存在於任何知識之前。凝視被動地係於這種原初的被動性上,從而被迫獻身於完整地吸收經驗和主宰經驗這一無止境的任務。
對於這種描述事物的語言而言,或許僅僅對於它而言,其任務就是確認一種不僅屬於歷史或美學範疇的關於“個人”的知識。對個人進行定義應該是一項永無止境的工作,這種情況不再構成某種經驗的障礙。經驗承認了自身的限度,反而把自己的任務擴展到無限。通過獲得客體的地位,其特有的性質、其難以捉摸的色彩、其獨特而轉瞬即逝的形式都具有了重量和堅實性。此時,任何光都不能把它們化解在理念的真理中;但是投向它們的凝視則會喚醒它們,使它們凸現在一種客觀性的背景面前。凝視不再具有還原作用了。毋寧說,正是凝視建構了具有不可化約性的個人。因此我們才有可能圍繞著它組建一種理性語言。話語的這個客體完全可能成為一個主體,而客觀性的形象絲毫沒有改變。正是由於這種形式上的深度重組,而不是由於拋棄了各種理論和陳舊體系,才使臨床醫學經驗有可能存在;它解除了古老的亞里士多德的禁令:人們終於掌握了一種關於個人的、具有科學結構的話語。
正是通過這種接近個人的方式,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從中看到了一種“獨特對話方式”的確立,以及一種老式醫學人道主義——與人的同情心一樣古老——的最凝練的概括。各種“無頭腦的”知性現象學將其概念沙漠的沙子與這種半生不熟的觀念混合在一起;帶有色情意味的詞彙,如“接觸”、“醫生?患者對偶關係”,竭盡全力想把婚姻幻想的蒼白力量傳遞給這種極端的“無思想”狀態。臨床經驗在西方歷史上第一次使具體的個人向理性的語言敞開,這是處於人與自己、語言與物的關係中的重大事件。臨床經驗很快就被接受,被當做是一種凝視與一個面孔、或一種掃視與一個沉默的軀體之間簡單的、不經過概念的對質;這是一種先於任何話語的、免除任何語言負擔的接觸,通過這種接觸,兩個活人“陷入”一種常見的卻又不對等的處境。最近,為了一個開放市場的利益,所謂的“自由主義”醫學恢復了舊式診所的權利,這種權利被說成是一種特殊契約,是兩個人之間達成的默契。這種耐心的凝視甚至被賦予一種權力,可以藉助適度——不多不少——添加的理性而聯結到適用於所有科學觀察的一般形式:“為了給每一個病人提供一個最適合他的疾病和他本人情況的治療方式,我們力求對他的情況獲得一個完整客觀的看法;我們把我們所了解的有關他的信息都匯集到他的捲宗裡。我們用觀察星象和在實驗室做實驗的方法來'觀察'他”。
奇蹟不會輕易出現:使病床有可能成為科學研究和科學話語的場域的那種突變——每一天都在繼續發生——並不是某種古老的實踐與某種甚至更古老的邏輯混合後突然爆炸的結果,也不是某種知識和某種奇特的感覺因素,如“觸摸”、“一瞥”或“敏感”的混合產物。醫學之所以能夠作為臨床科學出現,是由於有一些條件以及歷史可能性規定了醫學經驗的領域及其理性結構。它們構成了具體的前提。它們今天有可能被揭示出來,或許是因為有一種新的疾病經驗正在形成,從而使人們有可能歷史地、批判地理解舊的經驗。
如果我們想為有關臨床醫學誕生的論述奠定一個基礎,那就有必要在這裡兜一個圈子。我承認,這是一種奇怪的論述,因為它既不能基於臨床醫師目前的意識,甚至也不能基於他們曾經說的話。
可以說,我們屬於一個批判的時代,再也沒有什麼第一哲學,反而每時每刻使我們想到那種哲學的昔日顯赫和致命謬誤。這是一個理智的時代,使我們不可彌補地遠離一種原始語言。在康德看來,批判的可能與必要是通過某些科學內容而係於一個事實,即存在著像知識這樣的事物。在今天這個時代——尼采這位語言學家對此做出見證——它們是係於這樣的事實,即語言是存在的,而且,在一個人所說的數不勝數的言詞中——無論這些言詞有無意義、是說明性文字還是詩——形成了某種懸於我們頭上的意義,它引導我們這些陷入盲目的人前進,但是它只是在黑暗中等待我們意識到之後才現身於日光和言說中。我們由於歷史的緣故而注定要面對歷史,面對關於話語之話語的耐心建構,面對聆聽已經被說出的東西這一任務。
相當於英文speech。——譯註,難道我們注定不知道它除了評論以外還有別的什麼功能?評論對話語的質疑是,它究竟在說什麼和想說什麼;它試圖揭示言說的深層意義,因為這種意義才使言說能達到與自身的同一,即所謂接近其本質真理;換言之,在陳述已經被說出的東西時,人們不得郴重述從來沒有說過的東西。這種所謂評論的活動試圖把一種古老、頑固、表面上諱莫如深的話語轉變為另外一種更饒舌的既古老又現代的話語——在這種活動中隱藏著一種對待語言的古怪態度:就其定義而言,評論就是承認所指大於能指;一部分必要而又未被明確表達出來的思想殘餘被語言遺留在陰影中——這部分殘余正是思想的本質,卻被排除在其秘密之外——但是,評論又預先設定,這種未說出的因素蟄伏在言說中,而且設定,人們能夠借助能指特有的那種豐溢性,在探詢時可能使那沒有被明確指涉的內容髮出聲音。通過開闢出評論的可能性,這種雙重的過剩就使我們注定陷入一種無法限定的無窮無盡的任務:總是會有一些所指被遺留下來而有待說話,而提供給我們的能指又總是那麼豐富,使我們不由自主地疑惑它到底“意味著”(想說)什麼。能指和所指因此就具有了一種實質性的自主性,分別獲得了一種具有潛在意義的寶藏;二者甚至都可以在沒有對方的情況下存在,並開始自說自話:評論就安居在這種假設的空間裡。但是,它同時又創造了它們之間的複雜聯繫,圍繞著表達的詩意價值而形成一個交錯纏繞的網絡:能指在“翻譯”(傳達)某種東西時不可能是毫無隱匿的,不可能不給所指留下一塊蘊義無窮的餘地;而只有當能指背負著自身無力控制的意義時,在能指的可見而沉重的世界裡,所指才能被揭示出來。評論立足於這樣一個假設:言說是一種“翻譯”(傳達)行為;它具有與影像一樣的危險特權,在顯示的同時也在隱匿;它可以在開放的話語重複過程中無限地自我替代;簡言之,它立足於一種帶有歷史起源烙印的對語言的心理學解釋。這是一種闡釋(Exégèse),是通過禁忌、象徵、具象,通過全部啟示機制來傾聽那無限神秘、永遠超越自身的上帝聖言。多少年來我們評論我們文化的語言時的出發點,乃是多少世紀我們徒勞地等待言說原文作Parole,相當於英文Word。——譯註的決定的所在之處。
從傳統上看,言說其他人的思想,試著說出他們所說的東西,就意味著對所指進行分析。但是,在別處和被別人說出的事物難道必須完全按照能指和所指的遊戲規則來對待,被當做它們相互內含的一系列主題嗎?難道就不能進行一種話語分析,假設被說出的東西沒有任何遺留,沒有任何過剩,只是其歷史形態的事實,從而避免評論的覆轍?話語的種種事件因而就應該不被看做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應被當做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斷,能夠逐漸匯集起來構成一個體系。決定陳述的意義的,不是它可能蘊含的、既揭示它又掩蓋它的豐富意圖,而是使這個陳述與其他實際或可能的陳述聯結起來的那種差異。其他那些陳述或者與它是同時性的,或者在線性時間系列中是與它相對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現一種全面系統的話語史。
直到今天,思想史幾乎只有兩種方法。第一種為美學方法,是一種類推法,每一種類推都是沿著時間的線路擴展(起源、直系、旁系和影響),或者是在既定歷史空間的表面展開(時代精神、時代的世界觀、其基本範疇、其社會文化環境結構)。第二種為心理學方法,是內容否定法(這個世紀或那個世紀並不是像它自己所說的和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理性的世紀或非理性的世紀),由此發展出一種關於思想的“心理分析”,其結果完全可以顛倒過來——核心的核心總是其反面。
這裡我要試著分析十九世紀偉大發現之前那一時期的一種話語——醫學經驗話語。當時這種話語在內容上的變化遠遠小於在體系形式方面的變化。臨床醫學既是對事物的一種新切割,又是用一種語言把它們接合起來的原則——這種語言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實證科學”語言。
對於任何想清理臨床醫學諸多問題的人來說,臨床醫學(clinique)的概念無疑負載著許多極其模糊的價值;人們可以分辨出一些毫無光彩的畫面,例如疾病對病人的奇怪影響,個人體質的多樣化,疾病演變的或然性,敏銳知覺的必要性(有必要時時警覺最輕微可見的變化),對醫學知識無限開放的累積型經驗形式,以及從古希臘時代就成為醫學基本工具的那些古老而陳腐的觀念。在這個古老的武器庫裡,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告訴我們在十八世紀的那個轉折點究竟發生了什麼。從表面現像看,對舊臨床醫學主題的質疑“造成了”醫學知識的根本性變化。但是,從總體機制看,對於醫生的經驗來說,當時出現的臨床醫學乃是關於可感知者與可陳述者的新圖像:身體空間中離散因素的重新配置(例如,組織這種平面功能片段被分離出來,與器官這種功能物質形成對比,並形成矛盾的“內表面”),病理現象的構成因素的重新組織(徵候語法學取代了症狀植物學),對於病態事件的線性序列的界定(與疾病分類表相反),疾病與有機體的接合(過去用一般疾病單位把各種症狀組合在一個邏輯格式中,現在一般疾病單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局部狀態,即在一個三維空間中確定疾病之存在及其原因與後果)。臨床醫學的出現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應該被視為這些重組過程的總體系統運作。這個新結構體現在一個細小但決定性的變化上(當然這種變化並不能完全代表它):十八世紀醫生總是以這樣一個問題開始與病人的對話:“你怎麼不舒服?”(這種對話有自己的語法和風格),但是這種問法被另一種問法所取代:“你哪兒不舒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臨床醫學的運作及其全部話語的原理。從此開始,在醫學經驗的各個層次上,能指與所指的全部關係都被重新安排:在作為能指的症狀與作為所指的疾病之間,在描述與被描述者之間,在事件與它所預示的發展之間,在病變與它所指示的病痛之間,等等。臨床醫學經常受到讚揚,因為它注重經驗,主張樸實的觀察,強調讓事物自己顯露給觀察的目光,而不要用話語來干擾它們。臨床醫學的真正重要性在於,它不僅是醫學認識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種關於疾病的話語的存在可 能性。對臨床醫學話語的限制(拒絕理論,拋棄體系,不要哲理;否定所有這些被醫生引以為榮的東西)所體現的無語言狀況正是使它能夠說話的基礎:這種共同的結構切割出並接合了所見與所說。
因此,我所進行的這項研究也就刻意地兼有歷史研究和批判的性質,因為除了各種不能免俗的意圖外,它關心的是如何確定醫學經驗在現代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條件。
我要預先說明的是,本書無意於褒貶某種醫學,更無意於指責所有的醫學和主張廢除醫學。本研究與我的其他研究一樣,旨在從厚實的話語中清理出醫學史的狀況。
在人們所說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們想的是什麼,也不是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們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麼從一開始就把它們系統化,從而使它們成為新的話語無窮盡地探討的對象並且任由改造。
目次
第一章 空間與分類
第二章 政治意識
第三章 自由場域
第四章 臨床醫學的昔日凄涼
第五章 醫院的教訓
第六章 征候與病例
第七章 看與知
第八章 解剖一些尸體
第九章 可見的不可見物
第十章 熱病的危機
結論
書摘/試閱
第一章空間與分類
對於我們來說,人的肉體天然有權界定疾病的起源空間和分佈空間:這種空間的線條、體積、表面和通路都是根據一種迄今人們熟悉的地理學,按照解剖圖來規定的。但是,堅實而可見的肉體的這種秩序僅僅是人們將疾病空間化的醫學的一種方式,既不可能是第一種方式,也不可能是最基本的方式。過去曾經有過,將來還會有其他的疾病分佈方式。
我們將在何時能夠界定在隱秘的肉體裡決定了過敏性反應過程的那些結構?是否曾經有人勾畫出病毒在某一生理組織的薄層裡擴散的特定幾何圖?在一種歐幾里德式的解剖學中,能否找到支配著這些現象空間化的法則?說到底,人們所能回憶起的只是,舊的交感理論使用過一套所謂對應、毗鄰、同系的語言;而被感知的解剖學空間幾乎不可能提供一種連貫一致的詞彙。病理學領域裡的每一偉大的思想都給疾病規劃了一種構型,但是這種構型的空間要素不一定是經典幾何學的要素。
疾病的“實體”與病人的肉體之間的準確疊合,不過是一件歷史的、暫時的事實。它們的邂逅僅僅對於我們來說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們現在只是剛剛開始想客觀地看待這種邂逅。疾病構型的空間與病患在肉體中定位的空間,在醫療經驗中疊合,只有一段較短的時間,在這個時期,十九世紀的醫學同時發生,而且病理解剖學獲得特權地位。正是這個時期,凝視(regard)享有主宰權力,因為在同一感知領域,循著同樣的連續性或同樣的斷裂,經驗“一下子”就能讀出機體的可見病灶以及各種病理形式的聯繫;疾病準確地表現在肉體上,其邏輯分佈也同時按照解剖學組織而展開。這“一瞥”不過是在它所揭示的真理上的運作,或者說這是在行使它握有全部權利的權力。
但是,上面所說的這種權利怎麼會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自然的權利呢?顯示疾病存在的那個位置為什麼能夠以如此專橫的方式決定那種把各種因素組合在一起的圖形?奇怪的是,疾病的構型空間絕不比分類醫學更自由,更獨立於疾病定位空間。分類醫學這種醫學思想形式在編年史上僅先於解剖臨床醫學方法一步發生,並且在歷史上創造了後者出現的可能性條件。
基利貝爾說:“在沒有確定疾病的種類之前,絕不要治療這種疾病。”基利貝爾,《醫學的無政府狀態》(Gilibert, L'anarchie médicinale),納沙泰爾,1772年版,第1卷,第198頁。從索瓦熱的《系統的疾病分類學》(1761年)到皮內爾的《哲學疾病分類法》(1798年),分類原則支配了醫學理論和醫療實踐:它顯得好像是疾病形態的內在邏輯,解讀疾病形態的原則以及定義疾病形態的語義學原則:“不要在意那些對著名的索瓦熱的著作散佈不敬的嫉妒者……要記住,在古往今來的醫生中,他或許是惟一使我們的全部教義都從屬於健全邏輯的無誤規則的人。請注意,他在確定他的用語時是多麼小心謹慎,他在限定每一種疾病的定義時是多麼嚴格仔細。”在疾病被人們從濃密的肉體中抽取出來之前,它已經被賦予了一種組織,並被劃歸進科、屬、種的等級系列。表面上,這不過是一幅幫助我們了解和記住疾病的衍生領域的“圖像”。但是,在這種空間“比喻”背後的更深層次,為了造成這種圖像,分類醫學預設了疾病的某種“構型”(configuration):它從來不會自己明確表達出來,但是人們可以事後確定它的基本要素。正如一棵家庭系譜樹,在這種相關的比喻和它的全部想像主題之下的層次,是以一種空間作為其前提的。在這個空間裡,其血緣關係是可以圖示出來的。疾病分類學圖像也包括一種疾病構型,它既不是因果系列,也不是事件的時間系列,也不是疾病在人體內的可見軌跡。
這種安排把有機體內的定位當做從屬的問題,但卻定義了一種涉及包容、從屬、區分和相似等關係的基本體系。這種空間包括一個“縱向”維度和一個“橫向”維度。縱向維度用於描繪疾病的含義——熱病是“一種冷與熱的持續交匯”,可能發作一次,也可能發作多次;二者的交替出現可能不間歇,也可能有間歇;這種間歇可能不超過十二小時,也可能維持一天或持續兩天,也可能按照一種難以界定的節奏索瓦熱,《系統的疾病分類學》(F. Boissier de Sauvages, Nosologie méthodique),里昂, 1772年版,第2卷。;在橫向維度,同系現象相互轉移——在痙攣的兩大子系統裡可以發現完全對稱的“局部強直”和“全身強直”,“局部陣攣”和“全身陣攣”同上書,第3卷。;或者,在排泄系列裡,黏膜炎與咽喉的關係相當於痢疾與腸道的關係卡倫,《實用醫學制度》(W. Cullen, Institutions de médecine pratique)法譯本,巴黎,1785年版,第2卷,第39至60頁。;這個空間是一個有深度的空間,先於一切感知而存在,而且從遠處控制著感知;正是以這個空間為基礎,通過疾病所交織穿行的線條以及疾病所配置和安排等級的肉體組織,疾病出現在我們的凝視之下,體現在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中。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