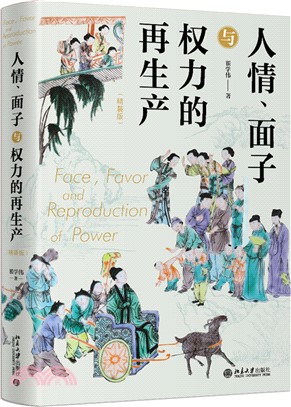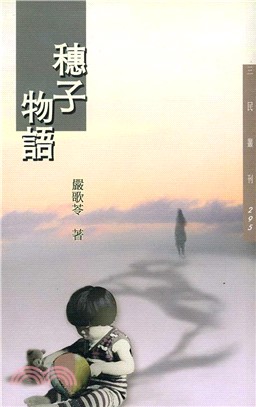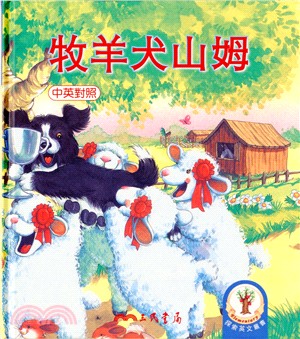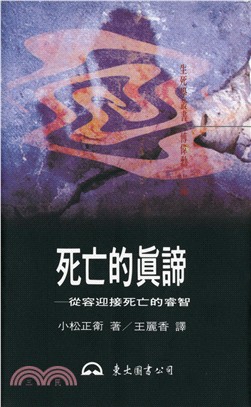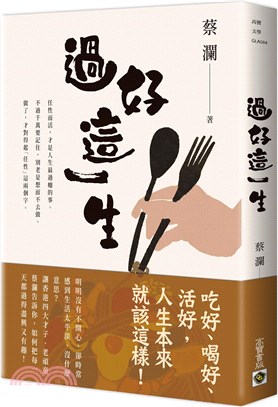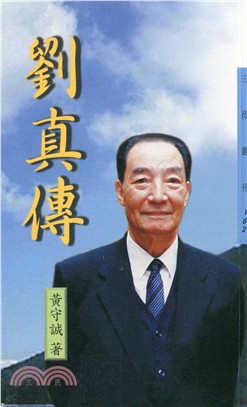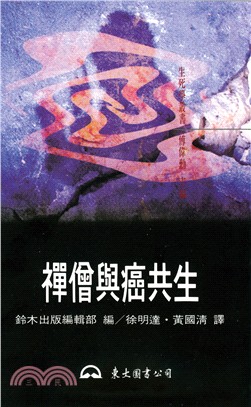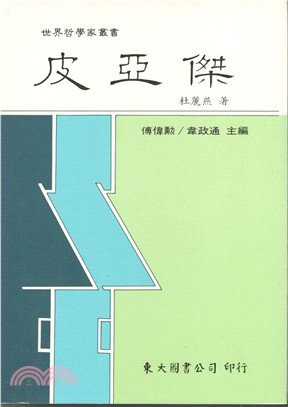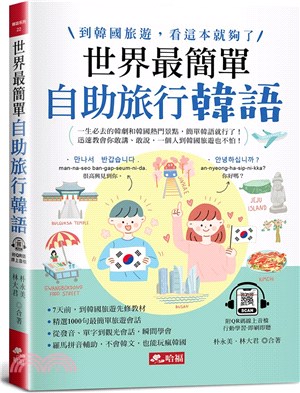商品簡介
關於“人情”與“面子”,中國人似乎“一聽就懂,所以細想的人大約不很多”(魯迅語),然而它們是認識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基礎。通過對其進行深入探討,我們可以得到一種本土分析框架,以此分析它們在社會、經濟、政治、教育與日常生活等各領域的重要影響,並尋求到一種與西方相關領域對話之可能。至於它們與“權力”如何關聯,以往的社會學研究並未給出答案。本書從“關係”及其網絡建構的特點出發,指出兩者結合將形成“權力的再生產”,即指權力因關係會發生轉移,導致一些原本沒有權力者獲得權力。
總之,本書以社會學本土化的視角,在理論與經驗兩個層面,對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運行方式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並針對一些學理問題與西方社會科學形成觀照,較為完整地勾勒了中國社會之文化脈絡與中國人關係運作的全景圖,也充分體現了作者在此領域為構建中國社會科學話語體系而做出的努力。
作者簡介
翟學偉,男,1960年生於南京。自1986年考入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班起,開始研習社會學,1988年入職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其間獲法學碩士學位和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於2015—2020年入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長期致力於社會學本土化研究,曾兩次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課題。代表作有《人倫、恥感與關係向度——儒家的社會學研究》《中國人的社會信任:關係向度上的考察》《中國人行動的邏輯》《中國人的關係原理:時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變》等,作品被譯成英文、法文、日文及阿拉伯文,並在新加坡等地有繁體字版。
名人/編輯推薦
三十年深耕:作者三十余年研究中國社會關係,且影響廣泛。
生活化智能:基於民間智能和默會知識,對“關係”“人情”“面子”及其運行,進行了學術性闡釋和分析。
獨創性概念:從“關係”及其網絡建構的特點出發,指出兩者結合將形成“權力的再生產”,即指權力因關係會發生轉移,導致一些原本沒有權力者獲得權力。
目次
研究視角與方法篇
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研究的反省、批判及出路
儒家的社會建構
——中國社會研究的視角與方法論的探討
心理學本土化之我見
——從本土概念向本土研究方法的轉化
事實再現的文學路徑
——建構社會與行為科學中的人文方法
關係模式研究篇
中國人際關係模式
中國人關係網絡中的結構平衡模式
社會流動與關係信任
——也論關係強度與求職策略
臉面與人情研究篇
中國人臉面觀的同質性與異質性
在中國官僚作風及其技術的背後
——偏正結構與臉面運作
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
——情理社會中的社會交換方式
社會運作理論篇
“土政策”的功能分析
——中國地方與組織領導的權力遊戲
中國人在社會行為取向上的抉擇
——中國人社會行為變量的考察
個人地位
——中國日常社會學理論的建立
社會系統、關係運作與權威結構
——在北京大學的講演
索 引
書摘/試閱
中國社會是一個講人情與面子的社會。眾多的研究成果和文化比較研究已證實了這一點,亦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研究中國社會時開始使用“人情”與“面子”這兩個概念。但由於大部分學者對它們各自的含義、彼此的關係及其在中國社會如何發生作用等,都還缺少理論的推演和概念上的邏輯整合,因而也就很難獲得對中國社會關係運作的解釋。近年來,受西方諸多理論和概念,特別是社會交換理論、社會資源理論及社會網絡理論的影響,有些學者逐漸傾向將人情和面子作為一種關係資源,附加在西方的相關理論框架內進行研究或建構模型。看起來,後面這種研究思路似乎使前者的不足得到了解決,但如果認真追究便可以發現,這種附加方式在把中國人的社會交換方式硬套於西方有關理論的同時,已迷失掉了其概念自身所具有的運作方向。其實,中國人運作關係的策略和思路同西方社會理論中的旨趣和指向有諸多不同,需要我們認真而細致地一一加以區分和討論。
一、什麼是情理社會?
在本研究展開之前,我首先將中國社會預設為一種“情理合一”的社會,從而使此種社會中發生的人情與面子全然不同於西方人那些看上去相似的心理和行為。在中國社會,我們在經驗中便可以發現,大多數人的辦事和處世原則既不會偏向理性,也不會偏向非理性,而是希望在兩者之間做出平衡與調和。為了說明這一點,我的研究先從這一預設開始。
回溯儒家經典,中國先秦時期的“情”不同於我們後來所講的“人情”,前者的含義是人之常情和性情,諸如:
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禮記·問喪》)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禮記·禮運》)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禮記·禮運》)
從這些議論中,我們可以看到,早期儒家所講的“人情”同心理學裡所講的情緒和情感沒有什麼區別,其原意是指人的天然和自發的感情,即“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禮記·禮運》)。但是,伴隨著儒家對人倫的規範及其影響作用,中國人後來所講的“人情”已不再指人的本能情感。或許儒家認為這種意義上的“人情”會隨心所欲,沒有節制或放肆胡來,而有仁心的“人情”,必須在一種符合社會之義理的路在線來表達和控制,進而實現了人情的內涵從心理學認識向社會學認識的重要轉化。
一個人如何讓這些感情在生活中從心所欲不逾矩呢?儒家認為其間需要有一套做人的規則,這個規則在儒家看來就是“禮”。所謂“克己復禮”就是要人克制自己的欲望,讓自己的感情不要隨意發泄。關於這一點,我們從“禮”字的起源可以看出一點端倪。禮(禮)字最早的意思是祭鬼神的器皿,後由此發展出莊嚴肅穆的祭祀節目和儀式之義,以表達順天承運的使命感。《禮記·禮運》上說: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因此儒家在構思“禮”的時候,是用它來連接天人之間的關係的。在“天理人情”的說法中,“理”是指天的運作規則,這個規則是自然規則,人不能改變,也不能反抗,因此是命定的;而原初的“情”又是個人化的,能改變的,隨意的。在連接這個不變與變的過程中,先王(聖人)承天之道制定了“禮”,就是以天的名義規範人的七情六欲,也就是想以“人情”順從“天意”。但規範也罷,順從也罷,它們都不是制裁,不是消滅。所謂存天理滅人欲,不是儒家的初衷。在儒家看來,只要人情能夠順應天意,就應將立足點放在調適過的人情上。比如“孝”,它本來不過是作為生物性的後代對生養者之自然感情的流露,可是儒家卻把它變成一種義務和倫理化的原則。如果一個人能對自己父母有這樣一分感情,然後將此感情再彌漫到長輩乃至君王身上,最後就可以達到盡心知天命的境界,最終便可以達到天下之大治。從這裡,我們看到,“天理”偏重秩序(道),而“人情”偏重個人情緒。“天理”作為一種自然的自身運化,具有普遍主義的色彩,而“人情”則帶有無數的個人差異,具有特殊主義的特徵。只有“禮”一方面講究秩序,另一方面又照顧到個人的特殊性,才能將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糅合到一起。這樣一來,“天理”與“人情”這兩個原先分開來講的概念,在“禮”的作用下就逐漸簡化為“情理”的說法,而這一提法暗含了這樣的意味:中國社會對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不做二元對立的劃分,以期待人們做人辦事的時候兩者都不偏廢。
於是,這樣的社會對做人、做事及其判斷不是單從理性的、邏輯的思維和條文制度規定的角度來考慮的,而是從具體的、情境的和個別性上來考慮問題。所謂“合情合理”“入情入理”“通情達理”“酌情處理”和“情理交融”或“於情於理如何如何”,都是希望人們做人做事時在情和理上都要兼顧,在其中取得平衡。“得理不饒人”是不對的,太感情用事也是不對的。雖說理是整體的、普遍存在的,情是部分的、個別的、特殊的,但這兩者之間這種整體和部分的關係沒有孰輕孰重的意思。
我國學者在研究中國傳統法律時注意到,“情理法兼顧”或“合情合理合法”這兩個常用語正表達出一個十足的中國式觀念:情、理、法三者合起來,通盤考慮,消除互相衝突處,才是理想的、真正的法律;但三者中的任何一者,卻不可以作為完整意義上的法來理解。此即三位一體。日本著名學者滋賀秀三通過對明清案件的研究,對中國人的這種“情理”也有很好的領悟。他說:
所謂“情理”,簡單說來就是“常識性的正義衡平感覺”。這裡不得不暫且借用“正義衡平”這一在西洋已經成熟的概念。但什麼被感覺為正義的,什麼被感覺為衡平的呢?當然其內容在中國和西洋必然是不同的東西……概言之,比起西洋人來,中國人的觀念要顧及人的全部與整體。也即是說,中國人具有不把爭議的標的孤立起來看而將對立的雙方——有時進而涉及周圍的人們——的社會關係加以全面和總體考察的傾向;而且中國人還喜歡相對的思維方式,傾向於從對立雙方的任何一側都多少分配和承受一點損失或痛苦中找出均衡點來,等等。這些說法大概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所謂“情理”正確說應該就是中國型的正義衡平感覺。無論如何,所謂情理是深藏於各人心中的感覺而不具有實定性,但它卻引導聽訟者的判斷。
這段話裡面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如果情與理處在二元對立的關係中,那麼任何一種對理的放鬆和退讓都意味著理不再為理,而受到了情的干擾。因此,如果一個社會要重視理的作用就得排除情的干擾,同一切非理(情)的因素劃清界限。史學家唐德剛對此感慨道:“‘法律’最講邏輯,律師則盡是邏輯專家,而他們在社會(西方)中的地位更是了得。哪像我們傳統的中國人,最瞧不起所謂寫藍格子的‘紹興師爺’和‘狗頭訟師’。‘我們的“仲尼之徒”一向是注重“為政以德”的。毫無法理常識的“青天大老爺”動不動就來他個“五經斷獄”。斷得好的,則天理、國法、人情、良心俱在其中;斷得不好的,則來他個“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滿口革命大道理,事實上則連最起碼的邏輯也沒有了。西方就適得其反。西方的律師,訴訟起來,管他娘天理、人情、良心,只要邏輯上不差,在國法上自有“勝訴”。因而他們的邏輯,也就愈加細密了。’”在中國,人們認為得理還做了讓步,那才更加合理,也合乎人性。
二是,平衡的含義是一種主觀的感受和分寸,並沒有一種客觀的尺度。它屬於一種個人心理上的掂量(所謂中國人假設因人心本善而具有的良心),或者是中國老百姓喜歡講的“人人心裡都有桿秤”。表面上看,這句話中包含一種公道自在人心的意思,而實際上這桿公平秤是由情誼或親密的程度來決定的,也就是說它成為“公秤”的可能性最小,成為“私秤”的可能性最大。因為作為公秤,我們或者要有一種公共的正義感或者要有一套大家必須公認的法規條例。可遺憾的是,這種正義感不是法律制度,而是天理。天理卻又只能回歸到人的主觀認定上來。由主觀到主觀,大大增強了平衡性上的情理合一與個人感受。假如儒家所謂的“仁”的本質是等差之愛,社會關係是差序格局,生活單位是家族、宗族,那麼這個客觀的基礎就很難找到了。因此中國人所講的“人情”,更多的是一種私交狀態下的感情,即人們常說的“交情如何”或“私交如何”。當然,中國社會在禮的潛移默化下也不會全然不顧天理,更不會輕易傷天害理。因此無論什麼情況發生,在情與理之間總是存在著回旋的余地。
那麼,公共的情感在中國社會是否完全不存在呢?也不是。我認為,它的存在基礎就是由個體的將心比心而來的同情心。同情心是推己及人的結果,即是將自己的“徇私情”合理化為“哪個都免不了有求人”的時候之共同感情。所以,中國人在為自己的私情辯護時往往會說“誰不會遇到點難事”“誰都有難處”“誰都有落難的時候”“誰都有在別人屋檐下的時候”等,一種將心比心的方法獲得了普遍主義,進而使中國人的人情總是以特殊性始而以普遍性終,以實現用自己的私情換來他人的同情。有趣的是,即使以上這種從特殊到一般的推論本身,在知識社會學上也得接受符合情理的演繹方式,而非一種純粹學理的嚴密邏輯可以推導出來。
二、人情交換的含義及其類型
當人情中含有了理和義的成分後,人情的意思就發展成了中國人的主要交往方式。人情中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相結合而產生的原則就是《禮記·曲禮》中所說的:“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但如何把握這個原則,則要根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情況來定了。而且在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情況下也沒有什麼一定的原則。楊聯陞說:“中國社會中還報的原則應用交互報償於所有的關係上,這原則在性質上也可被認作是普遍主義,但是這個原則的行使卻是傾向於分殊主義,因為在中國任何社會還報絕少只是單獨的社交交易,通常都是在已經建立個別關係的兩個個人或兩個家庭之間,一本由來已久的社交收支簿上又加上一筆。”這一筆是多少,我們姑且不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人情的運作期待不是直接利益最大化,而是互惠的最優化,即裡面有許多非(直接)利益上的考慮。直接利益最大化是以“理性人”和“經濟人”為假設的社會所追求的目標,而以“性情中人”和“社會人”為假設的社會,追求的是另一種目標。
比較“理性人”和“性情人”這兩種人性假設的不同點,我們發現:“經濟人”所追求的最大利益化是可以預期的,從一個人投入的精力、技能和資本中就可以預計獲得多少回報;情理社會中的人情往來雖能預期應該會得到回報(這是理的含義),否則這在倫理和道理上是說不過去的,可複雜性在於,一個人無論投入多少,也不能預計會獲得多少回報(這是情的含義)。但關鍵問題在於,情理社會的人雖不直接追求利益最大化,但不能把人情交換理解成非理性,以為他們的人情交換中沒有利益,只有情感。其實,人情交換過程的委婉和迂回更有利於獲得比理性計算多得多的回報,也比赤裸裸的利益談判更具人情味。否則,中國市場中出現的大量人情投資便沒有必要。當然,由於它不可預計,因此也不排除回報較小或一無所獲的可能,這也是造成當今中國社會在市場經濟下傳統交易方式失靈的原因之一。顯然,這種人情交換中的利益大小是由回報者根據人情的具體認定來實施的,無法一概而論。中國社會的人情交往中之所以發生這樣的不確定性,是因為人們在根本上認為“情義”是無價的(但也可以根據情況定價),“回報”也不過是一種心意而已,而不能被理解成一般性的交易。
為什麼說人情交換不是一般性的交換呢?提到社會交換,人們通常想到的是交換者之間在社會資源上的等價交換關係,其最典型的表現形式是通過所謂一報還一報,即“禮物的流動”來實現。抽象一點講,“禮物”就是交換的貨物。西方人類學家長期以來將研究禮物的流動方式、饋贈方式作為重點;而西方社會學家歸納出可以交換的資源除了貨物外,還有地位、感情、服務、信息、金錢等共六種。受西方社會資源理論的影響,中國學者根據中國社會的特徵將關係本身也當作一種資源,即關係資源,相當於我們比西方人多了一種交換資源。而下面的故事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
9世紀前期的一個宰相崔群以清廉著稱,以前他也曾擔任考官,不久以後,他的妻子勸他置些房產以留給子孫,他笑著說道:“我在國中已有了三十個極好的田莊,肥沃的田地,你還要擔憂房產做什麼?”他的妻子很奇怪,說她從未聽說過。崔群說:“你記得前年我任考官時取了三十個考生,他們不是最好的財產嗎?”他妻子道:“如果這樣說,你自己是在陸贄底下通過考試的,但你任考官時,卻特別派人去要求陸贄的兒子不要參加考試,如果說考生都是良田的話,至少陸贄家的地產之一已經荒廢了。”崔群聽了這話,自覺非常慚愧,甚至幾天都吃不下飯。
在這個故事中,崔群當時要求陸贄的兒子不要考,是怕人說他徇私情。可見,崔群的確可以被認為是個清官。可當他對妻子說他有三十個極好的田莊時,我們終於發現,清官雖然表面上可以兩袖清風,但他們仍認為只要有了關係資源,就等於有了一切。這個故事似乎在告訴我們,關係在中國的確是一種資源,但這樣的理解實際上是有失偏頗的。
中國人所講的人情中固然有利益交換的一面,但其更為重要而根本的原因卻是由報恩推動的,或者說後者的實現才能達成前者的實現。前文中這個故事的真正含義不在於崔群同考生有師生關係,就可以讓學生的資源流動到他那裡,而是在於這三十個考生的資源是崔群給他們的。在中國人的邏輯思維中,如果沒有崔群這個“伯樂”,就沒有考生這些“馬”。而這些學生也深知自己能有今天,幸虧有了崔群,既然如此,還有什麼不能用來報答崔群的?這才是崔群可以不置田產的根本原因。基於此種報恩式的人情,假使崔群過分一點,告訴妻子他還想要更多的田產,他的學生即使心存不滿,也仍無法拒絕。這就是報恩的力量。從妻子對崔群的責備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崔群在做清官和諳熟人情交換法則之間的內心糾結和徘徊,並為自己的前後行為衝突感到慚愧。回到我們前文的假設中去,如果我們對人情交換的討論只圍繞著資源來進行,就等於假定中國人的人情資源是可以計算的,也等於將無價的恩情或報恩轉化成了有價的資源交換。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即恩情的本質含義在於一個人因有社會資源,且為他人解決了人生難題而導致的他人理應持有的感激及回報。其中的價值之所以不可計算,是因為中國人不希望就事論事,而希望受恩者能理解這一事情的意味和用心。價值計算是理性的,而恩情報答是情理交融的。情理社會在人情往來上所構成的非對等性,導致其間產生的交換關係不能一次(或若干次)性地完結,或結束一次新生下一次,只能是發生了一次之後就得連續性地循環下去。從理性上講,資源交易需要在價值上得到衡量,甚至於訴諸法律來解決,包括精神賠償、人身保險等都可以換算成價格。但人情來往上的失敗,諸如知恩不報或恩將仇報,卻是沒有什麼價格可談的。比如,一個女人是否忠貞或一個人有沒有背信棄義,在傳統中國人看來都不是價格或賠償的問題。因為在中國人的價值觀念中,有些東西不能折算成貨幣,卻要訴諸道德譴責或付出生命代價,比如讓一個無情無義之人在輿論或良心譴責中一輩子心理不安,在眾人面前一輩子抬不起頭來或以命相拼來保全自己的名聲。傳統中國人喜歡道德,不喜歡法律,主要是因為法律裁決具有感情無涉的或換算價格的特徵,而中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將感情強烈地帶入。電影《秋菊打官司》就表明了中國鄉民在傳統的情與現代的法面前產生的困惑。
中國人的人情交換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感恩戴德型”,即某人在遇到危難或緊急關頭時得到了他人的幫助,這在人情交往中屬於“恩情”的範疇,而對此困難提供幫助的人叫“恩人”。第二種是比較有目的的“人情投資型”,通常也叫“送人情”或“送禮”。“送人情”會導致接受方有虧欠或愧疚感(也是中國老百姓常講的“不好意思”),造成雙方構成一種“人情債”關係,以迫使當送禮的一方提出要求時受禮的一方不得不按其要求給予回報。第三種是一般性的“禮尚往來型”,也就是熟人之間的有來有往的請客或過節時的送禮行為等,以加強彼此的感情聯絡。
感恩戴德也好,人情投資也好,禮尚往來也好,它們總是同“欠”相聯繫的。比較而言,恩情中的“欠”最具中國特點,即無價可以衡量。如“欠”可以計算清楚,那便回到理上來,且可以用馬上結清的辦法來了清彼此的關係。可見,中國人關係中的“欠”字不在理上,而在情上。比如,甲救過乙的命,或在乙餓得不行的時候甲給過他一碗湯,我們不能問乙回報多少價值的禮物才算夠,更不能問一碗湯值幾個錢,這樣的問法都是不通人情的。因此,甲和乙唯有構成恩情關係,才符合中國人的關係交往法則。自此,當甲有任何需要時,乙都義不容辭地去滿足,才算報答了甲的大恩大德。同樣,即使有目的的人情投資,或一般性的送禮,也並不出於對等原則。等值回禮在中國的意思就是不想欠人情。費孝通對此有過很好的見解:
親密社群的團結性就倚賴於各分子間都相互地拖欠著未了的人情。在我們社會裡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間搶著回帳,意思是要對方欠自己一筆人情,像是投一筆資。欠了別人的人情就得找一個機會加重一些去回個禮,加重一些就在使對方反欠了自己一筆人情。來來往往,維持著人和人之間的互助合作。親密社群中既無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帳”。“算帳”“清算”等於絕交之謂,因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無須往來了。
三、人情引起的權力再生產
大體說來,中國人如此看重人情是因為人情可以給個人生活帶來正向便利和改進,比如個人的成長和發跡、家族的興旺和發達等都需要人情來打點和疏通。其運作背景同中國社會自身的構成及運作——以家鄉共同體生活和互相支持、儒家倫理和中國傳統法律對個人義務的規定等——緊密相連。可其中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深究,而尤為重要的問題是人情與權力的關係。因為在中國,上述種種社會支持莫過於權力的支持。“靠山”“撐腰”“走後門”和托人、求情已成為中國人司空見慣的日常行為。這些行為看起來紛繁多變,但其核心不外是人情與權力。我們知道,在中國人的政治運作中,往往是權力不受約束,而職位受約束。權力被理解為(或被賦予)可以在一特定位置上對其所管轄資源做任意的控制和分配,其中既有(事在)人為的意思,也有情理不分、公私界限不分之義。假如權力的界定不能由權力者任意定奪,就說明該社會的權力操作是在制度的規範中運行的,而官員也就成為制度的執行者,而非弄權者。這樣的社會自然也就不會成為一個官本位的社會。錢穆說:“中國人稱‘權’,乃是權度、權量、權衡之意,此乃各官職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屬外力之爭。故中國傳統觀念,只說君職、相職。凡職皆當各有權衡。設官所以分職,職有分,則權自別。”正因為權力在中國社會存在任意性(當然也不能胡來),因此操作權術本身就是合情合理的,進而用人情攀上權貴就可能在其任意的一面獲得權力的轉讓,實現權力的再生產,我曾稱這一現象為中國社會中的日常權威。前文中提到的三種人情交換方式都有可能成為權力的再生產。比如,李佩甫小說《羊的門》中的呼家堡當家人呼天成為什麼能四十年不倒,呼風喚雨,傲視其他大小官員呢?原因十分簡單,就因為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幫助過一位落難的北京首長。後來該首長官復原職,自然對他感激不盡,所以就會有求必應。人情與權力之間的交換關係顯然不是指權力的正式移交,也不是指有權者正式授予此人該權力,而是說因為有了人情或私交,便意味著,一個原本無權者也可以行使與有權者類似的權力。他可以越過各種規範,不受制度管轄或者指使他人按自己的意願辦事,讓他人在想象的空間和關聯邏輯思維中認為,相關者的意願就是權威者的意願,或反過來說,得罪了相關者就等於得罪了權威者。
在中國,欠了別人的人情意味著受惠人有義務為投入者提供服務,或者受有恩於他的人的指使。中國諺語“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無功不受祿”“受人錢財,與人消災”“滴水之恩,定當涌泉相報”,以及“您的大恩大德,我就是做牛做馬也要報答”等說法之共同點就是,日常生活中扯不清的恩惠將導致相關權威者義務性的介入。總而言之,所謂權力的再生產可表述為,一種正式的權力通過關係的聯結或運作,可以讓原本沒有權力的人因關係的聯結而擁有權力,從而導致權力在關係中蔓延。從人情交往的類型來看,送人情和禮尚往來是許多人連接官場的常見手段,而真正發揮作用的則是感恩戴德型。
可是按照儒家的忠恕原則,我們能否將人情的交換做另一種方向的思考呢?比如,一個人做事不喜歡求別人,那麼他能不能同樣推出別人做事也不要來求他,或者說一個人做事不喜歡求人,不喜歡欠人情,他能不能同樣也要求別人像他這樣呢?金耀基似乎對此持肯定的態度,比如他說:“‘不可欠人人情’幾乎是中國最重要的社會格言或教訓。”但這話充其量是因擔心還不起人情債(因為無價)而勸人不要輕易地欠人情的意思,它絕構不成中國社會關係的基礎。單純而孤立地抽離出忠恕原則來看,也許前文的反向推論是講得通的。但如果將其放回到儒家的社會脈絡裡面來看,便講不通了,因為儒家思想和中國家族生活實踐都不會給個人這樣的思考余地。在中國人看來,且不論個人的交往方式如何建立,單是一個個體的出生這一事實本身就已經包含了父母的養育之恩,也就是說一個人的生命已拜父母所賜,那麼這個人該怎麼回報其父母呢?回報是天理,而如何回報,就看人情了。這也是每個人都不得不欠人情的理由。但我們能否認為,一個人可以欠父母的,但不用欠別人的,父母的養育之恩怎麼可以同社會上的人情往來同日而語呢?然而,中國的事情就是這麼複雜:賦予人生命在中國往往可以等同於救人一命(後者叫“再生父母”),一旦有了“再生父母”這樣的例外,我們就有理由讓人情交往有更多的例外。其實對制度的運作而言,人情本身都是例外。
理解了人情的施報關係不可用理性計算,並且以個人關係為紐帶後,那麼我們再看一下林語堂講給我們的20世紀30年代的事例,就能體會更多:
在這種氣氛中產生的恩惠,它來自當權者和需保護者之間的私人關係。然而,它可以取代法律,事實上也往往如此。一個中國人被捕了,或許是錯捕,他的親戚本能的反應不是去尋求法律的保護,在法庭上見個高低,而是去找長官的熟人,去求他的“恩典”。由於中國人非常重視個人關係,重視“情面”。這個去求恩典的人如果“面子”足夠“大”,他的說情往往能夠成功。這樣,事情總是很容易,比那耽延時日的官司花錢要少得多。於是,在權勢者、富人、有關係的人與那些不太幸運的、沒有關係的窮人之間產生了一種社會的不平等。
幾年前,在安徽有兩位大學教授,不小心說了幾句不當說的話,其罪責微不足道到荒謬的地步。就這樣,他們冒犯了當局,被抓去監禁了起來,親戚沒有什麼好法子,只得到省會去向該省的最高軍事長官乞求“恩典”。另一方面,同一省裡的一些年輕人,因賭博被當局抓獲。因為他們與省裡某一有勢力的團體有關係,他們不僅獲釋,而且還到省會去要求解雇那些抓他們的警察。兩年前,揚子江畔某大城市的警察搜查了某鴉片館,並將其所截鴉片沒收。然而,某地方要人的一個電話,警察局就不得不為自己的失禮而道歉,並且在警察的護送下將鴉片送回。一位牙醫曾為一個很有權勢的將軍拔了一次牙,將軍大悅,授了一個頭銜給他,所以他的一生就可以享受一點將軍的榮譽。有一次,某部的電話員請他接電話,直呼了他的姓名,而沒有稱呼他的頭銜。他來到部裡,找到那位電話員,當著軍事參謀部成員的面,扇了電話員的巴掌。1934年7月在武昌,一位婦女因為天熱穿短褲睡在戶外而被捕,監禁幾天之後便死去了。這位婦女原來是位官太太,那位警察於是被槍斃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四、人情與面子:權力再生產的不同方式
現在我們涉及了與人情概念密切相關的面子問題。人情同面子的相關性,使得我們很難區分它們之間的差別,至少目前在學術界尚沒有人做過這樣的努力。可我認為,這兩個概念之間雖然存在許多模糊地帶,但各自的側重點還是有所不同。
“面子”這個詞在我看來是人頭部所謂顏面、面目的一個轉喻。本來,顏面和面目就是指一個人的面孔。可是轉喻之後,其含義則大放異彩,變成了中國人的思維與行為模式上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中國社會,個人是家族鏈條上一個擺脫不掉的分子,因此他的言行舉止、為人處世、事業功名、做官掌權的問題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家族期待並因此可以沾光的問題。如果一個人做的事業符合家族眾人的期待,那麼不僅他自己感到非常榮耀,他的家人也會為他感到驕傲,並因此能分享他的榮譽和資源;反之,如果他做的事業或選擇違背了家人對他的期望或雖然努力了,但以失敗而告終,那他就會感到羞恥,也就是丟臉的意思,無法回到其家人群體中去,這時的表達是“以免讓家人羞辱”或“讓家人在當地感到無地自容”。這就是“有臉見”“無顏見”“羞見”及“有何面目見”的最初含義。因此,在中國社會,許多事情不是個人想不想做的問題,而是家裡人想不想他做以及他做了後會給家人帶來什麼後果的問題。這樣我給“臉”“面目”“顏面”等在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層面上的定義是:“臉是一個體為了維護自己或相關者積累的,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圈內公認的形象,在一定的社會情境中表現出的一系列規格性的行為。”後來我又把這個定義修改為:“臉是個體為了迎合某一社會圈認同的形象,經過印象整飾後表現出來的認同性的心理和行為。”由此比較臉面和人情的區別便可以發現,“臉面”是一個輻射性或推廣性的概念,它的動力和行為方向都是以與相關者的共享為特徵,即同所謂光宗耀祖、光大門楣、沾光等心理和行為相聯繫。否則,“臉面問題”只成了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理論中的個人“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問題,而失去了更深層次上的動力源或眾望所歸的行動方向。關於面子的分享性導致的權力問題,中國臺灣社會學家文崇一做過專門的研究。他說:
在中國社會,特別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政治體系中,親屬和權力表面上是兩個不同的範疇,實際卻是在一個範疇中運作。所謂一個範疇是指,有時候家族支配權力,有時候又反過來,權力支配家族。家族與權力之間一直是互相支援,形成一種特權。這種特權,通常都在地位上表現出來。有權的人,除了自己享受特權外,還會把權力分享給關係密切的家族和姻親,由近及遠;家族和姻親也會聯合起來分享權力,或要求分享權力。這已經變成一種習俗或社會規範,因為有些法律條文也承認這種分贓式的瓜分權力。這種透過家族和姻親關係獲取或保障既得利益的手段,是權力關係中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我們通常把這種情形叫作裙帶關係。中國人做了官或發了財,如果不給親戚朋友一點好處,那才叫不懂人情世故。一個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在中國社會是很難立足的,不要說為自己的事業打天下了。這就是權力分配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關鍵地位,它跟親屬結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性。
我認為,在中國社會,單憑自己的目標和興趣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情,或表現得知書達禮、彬彬有禮,不能算真正的臉面行為,這不過表明個人奮斗成功或行為得體而已。其實,中國人講究的臉面總是傾向把相關者的有關心理和行為考慮進來,因此具有層層輻射出去的作用。而“人情”則是一個相對排斥性的或封閉性的概念,它主要表現在有形和無形資源的交換上。顯然,有交換關係或恩惠關係才有人情關係,沒有交換關係就沒有人情關係。一個人不同另一個人進行人情交換,不能說他同此人有人情關係。可見,人情的封閉性表現在,人們彼此之間可以分清誰欠誰的人情或誰不欠誰的人情。而在臉面方面,一個家族或家鄉裡出了一位名人,家族和家鄉的人們根本不需要這位名人的首肯,就已經沾到他的光了。
因此,單靠人情同權力的關係可以發生交換關係,比如錢權交易、徇私情,即所謂的尋租。但臉面則不同,它涉及的是個人的資源無論自己願意與否都會有他人來分享。比如,“爭臉”和“爭面子”的意思是一個人獲得了令人羨慕的學識、人品、才華、德性、情操、職務之類,或有了當地人認同的行為和事跡,結果那些沒有這些成就的人只要同此人有特定的關係,就可以分享這些特徵。再比如,“給面子”就含有讓那些相關的他人分享自己的榮譽、名聲以及由此而來的物品、財富、地位、權勢等的意思。總體上看,臉面作為一種擴散性資源,是以他人正面的評價作為回報的。比如,他人對施與資源者的接受、感謝、感激、頌揚等會讓有臉者同時感到自己有了面子。可見,有臉者用人情與相關者共享因臉產生的資源,就是在賞臉給他,而他所要的回報,有時不是物質幫助,而是多多的恭維、抬舉和捧場。所謂給他人面子就是對他人重要性的承認,也就是對他人的成功、德性或善舉的肯定、羨慕、欣賞、尊重、敬佩等。如果一個人雖有物品、財富、地位等臉面資源,但在他想找人分享時,別人都表示出輕蔑、不願搭理或拒絕要他的東西,那就叫不給他面子。在中國,一個人不給面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涉及道德問題,要麼他或她過去可能傷害過此人的感情或自尊心,要麼人們不認同他或她的資源的來路。比如,一個人靠偷盜得來錢財,即使他再富有,也仍然沒有面子。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沒面子的行為的影響也同樣會波及他或她的相關者,如他們的家人、家族、同鄉,最後他或她只能退出或逃離其為之奮斗過的群體。這樣我們就知道了,面子是在臉出現後而獲得的他人的評價。從理想上講,它經受著一個人的臉是否被某一群體或社會圈承認的檢驗和考驗。由此,面子是一個為臉活著、為臉奮斗的人最想得到的東西,當然比金錢和財富更為重要,因為是它賦予了金錢和財富以社會和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也使奮斗者感受到了為之奮斗的幸福感。這樣,我給“面子”下的定義是:面子是由個體在做出臉的行為後帶來的他人判定而在他人心目中形成的序列地位,即所謂心理地位。所謂他人評價或判定及其在他人心目中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因此,面子在根本上是一種個人表現出來的形象類型導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為。費正清對此有相當的見地。他說:
中國式的人文主義包括關心個人尊嚴的問題,但那是從社會的觀點來關心的。“面子”是個社會性的問題。個人的尊嚴來自行為端正,以及他所獲得的社會贊許。“丟面子”來自行為失檢,使別人瞧不起自己。人的價值,並不像西方所認為的那樣是每個人固有的質量,而是需要從外界獲得的。
從這一點來看,面子雖然以他人評價為皈依,但因為它是從臉的表現出發的,所以它是有“裡子”的。不過,這是把臉和面子從中國文化中抽離出來分析的結果。如果把這個分析再放回到我們上文所討論的中國人的關係中來看,特別是介入關係的輩分、孝悌、忠恕,我們就會發現,這些關係運作讓中國人的臉開始式微,而面子開始突顯。也就是說,輩分高的、地位高的或在倫理上應當受到尊重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無論自己的德行(臉)如何,都希望他人給他面子。而按照忠恕原則,如果他這樣做了,當他人出現同樣的情況時,他也會給別人面子。由此一來,無論對方是否表現出色,“給面子”都是最重要的。據此,中國社會發展出了一套很成熟的恭維他人的言辭。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說:
外國人對中國人的“要面子”覺得很可笑。殊不知只有這樣才能在社會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風氣。每個人,都有面子,即使最卑賤的乞丐。如果你不想違反中國人的倫理準則,那就連乞丐也不能侮辱……
……中國人的生活,即便是最現代化的人,比起我們也要有禮得多。這當然影響效率,但同樣(更重要的是)也影響了人際關係的真誠。
總之,人情偏向的是交換上的一種一對一關係,因此它的回報方式就不是正面評價的問題,而是實惠和實質性的幫助;而面子偏向的是賦予交往關係以價值判斷。兩者的相關性在於,平時多做人情,就會得到較大的面子,平時不講人情,就得不到面子。
但人情和面子能夠在中國社會混合使用,也表示它們的確有共同之處,這主要是在不考慮第三方的情況下體現的。比如,A和B之間建立了人情關係,這時B對A說“看在我的面子上”,也可以說“看在我們的情分上”,這裡的“面子”和“情分”在A和B之間是沒有區別的,即人情就是面子,面子就是人情。但如果在A、B和C三人之間,A和B之間有人情關係,B和C之間也有人情關係,A和C之間沒有人情關係,那麼A和C之間本來是不會因為B分別同兩人有人情關係而建立共同的人情關係的。但我們在中國社會的經驗中發現,A和C之間事實上也有人情關係,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面子在中間起了連接的作用。比如,C因為同B的關係,對A說“看在我的面子上”,通常A不會給C面子;但如果C對A說“看在B的面子上”,A就會因為要給B面子而給C面子。所以在中國社會,辦事的關鍵不是看事情本身好不好辦或能不能辦,而是看由什麼人出面。
現在我們將權力的問題帶進來討論。假如在上述A、B、C三者中,A是一個權威者,當他自己的權威介入同B和C構成的網絡時,這個權威如果只同A和B之間有人情交換,那A和B之間只是一個徇私情的問題。這點在中國、西方都有,只是中國社會可能更嚴重罷了。但如果A的權威也能被C借到,那麼B就成了傳遞權力的中間人,而這個傳遞的成功是通過面子實現的。同理推出,如果C同D有私交,C也可以成為中間人,再將權力借給D,那麼網絡之間的日常權威不但形成且流通起來。當然,離權力源頭越遠,日常權威的威力也就越弱。有一點需要表明,在許多情況下,權威的流通未必需要那麼多中間人的人情串聯。如果臉面概念本身就包含個人不但是為自己,而且是為家族和鄉裡等相關者爭取的話,那麼除了臉面獲得者A以外,其他的相關者就都是B。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當然,這種輻射出去的相關者最終會有一個邊界或一個定義。邊界或定義之外的人如果想借到A的權威,只能向這些“雞犬”求情。
五、結 語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人情、面子如此受到中國人的重視,是因為它的運作方式同情理社會相契合。這種社會中的人在行事的時候總是力圖在情理上找到一條平衡的中間路線,並通過同情心實現特殊主義向普遍主義的過渡。可以設想,在一個偏重以法規、制度和理性構建起來的社會裡,人情、面子即使想發揮作用也沒有多少用武之地。因此,當“人情”和“面子”作為一對概念進入西方人的視野時,他們(不包含人類學家)所能理解及衍生出來的理論不過是個人印象整飾的策略(或人際溝通的一種話語策略,通俗地講似乎是一種禮貌用語的策略),因為他們實在意識不到它所具有的一種巨大無比的社會能量。回到中國自身,雖然有的中國學者看到了這一點,但由於受到社會交換理論、社會資源理論等的影響,傾向把關係作為一種交換資源,進而不可能發現,中國人的交換行為因情和理的共同作用而不可預期和不可計量。這種不可預期和不可計量一方面使得交換關係潛在的回報價值更大,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實現對制度和權力的再建構,並使參與交換者得到原本無法具備的支配力量和威力。另外需要澄清的是,在中國社會,人情和面子同權力的勾連是有差異的。人情是在報和欠的過程中獲得的權力,是交換的結果(比如送禮),具有封閉性的特點,而面子是在關係的關聯中獲得的權力,是無交換的結果(比如沾親帶故)。但它們彼此之間的聯繫之處是,無論它們如何運作,其結果都是建立與他人的特殊關係(有私交和交情),並將社會生活的意義寄托於此。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可以籠統地認為,中國人在情理社會中借助人情和面子的運作,放棄的是規則、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卻是不可估量的社會資源、非正式的社會支持和庇護及以勢壓人的日常權威。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