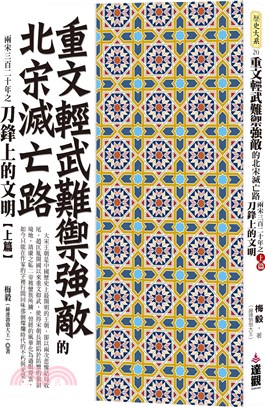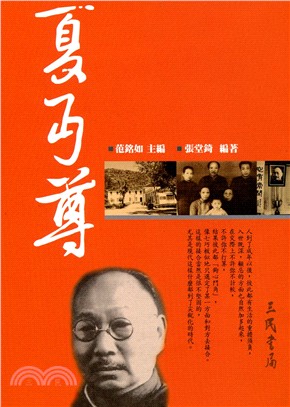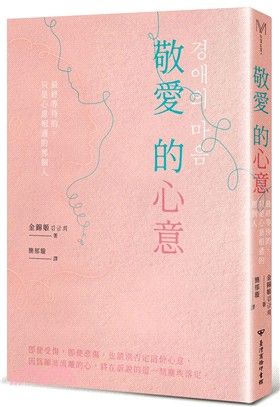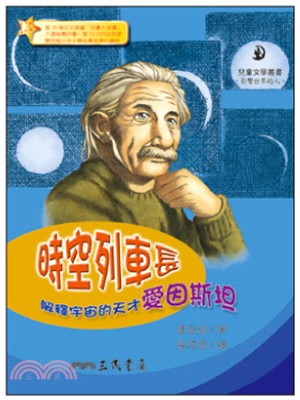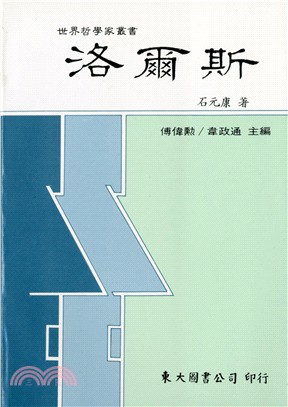重文輕武難禦強敵的北宋滅亡路:兩宋三百二十年之刀鋒上的文明上篇
- 系列名:歷史大系
- ISBN13:9786267199886
- 出版社:達觀
- 作者:梅毅(赫連勃勃大王)
- 裝訂/頁數:平裝/286頁
- 規格:23cm*16.8cm*1.4cm (高/寬/厚)
- 重量:420克
- 版次:1
- 出版日:2023/07/05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以獨特視角,大量考據史實演繹北宋的崛起至盛極而衰的過程。
大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開明的王朝,卻以兩次悲慘結局收尾。趙匡胤開國以來重文抑武的國策,使得宋朝長期陷於防禦的狼狽境地,靖康之恥二帝被蠻族所擄,昔日繁華成為深埋於地下的廢墟,曾經的風華化為過眼煙雲,如今只能在作家的字裡行間回味那個燦爛時代的不朽與光榮。
大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開明的王朝,卻以兩次悲慘結局收尾。趙匡胤開國以來重文抑武的國策,使得宋朝長期陷於防禦的狼狽境地,靖康之恥二帝被蠻族所擄,昔日繁華成為深埋於地下的廢墟,曾經的風華化為過眼煙雲,如今只能在作家的字裡行間回味那個燦爛時代的不朽與光榮。
作者簡介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研究生畢業後,從事金融工作十餘載,致力於資本市場研究工作。
2004年起,以「赫連勃勃大王」為筆名,開始「中國歷史大散文」的寫作,相繼出版有長篇歷史散文集《隱蔽的歷史》、《歷史的人性》、《華麗血時代》、《帝國的正午》、《刀鋒上的文明》《帝國如風》、《大明朝的另類史》、《亡天下》、《極樂誘惑》、《鐵血華年》(世界知識出版社、陝西師大出版社、同心出版社等)。香港中華書局出版有《歷史長河的悲喜英雄》、《帝王將相的博弈真相》繁體字版。上述諸種著作的繁體字版和韓文版也陸續面世。
2004年起,以「赫連勃勃大王」為筆名,開始「中國歷史大散文」的寫作,相繼出版有長篇歷史散文集《隱蔽的歷史》、《歷史的人性》、《華麗血時代》、《帝國的正午》、《刀鋒上的文明》《帝國如風》、《大明朝的另類史》、《亡天下》、《極樂誘惑》、《鐵血華年》(世界知識出版社、陝西師大出版社、同心出版社等)。香港中華書局出版有《歷史長河的悲喜英雄》、《帝王將相的博弈真相》繁體字版。上述諸種著作的繁體字版和韓文版也陸續面世。
序
【作者序】不朽的斑斕回憶──說不盡的兩宋文明
宋人筆記《蓼花洲閑錄》中,有這樣一則記載:
宋神宗因陝西方面對西夏用兵失利,遷怒於一個主管運糧的漕官。憤憤之下,他親自書寫御批,命令中書處斬此人。轉日,宰相蔡確率群臣上朝。宋神宗問:「昨日御批斬人,今已行否?」蔡確回答:「為臣我正想向陛下奏告此事。」宋神宗聞言不悅:「又有何疑?」蔡確回答:「祖宗以來,未曾殺士人,臣等不欲陛下開此先例。」神宗皇帝沈吟半晌,說:「那就把此人刺面,流放偏遠惡地。」時任門下侍郎的章惇當廷接言:「如此,不如殺掉此人。」宋神宗感到奇怪,問:「卿何出此言?」章惇回言:「士可殺不可辱!」一句話,激得神宗皇帝勃然大怒,聲色俱厲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龍顏雷霆之下,當朝的宰相、群臣不僅沒有在「天威」下震懾惶恐,傲然頂嘴的章惇反而不鹹不淡回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宋神宗默然。
這樣的場景,只是大宋王朝三百多年間一個小小的片斷和插曲,但它包含著無盡的寓意。
首先,可以見出,大宋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開明的王朝。即使口含天憲的帝王,也並非能夠為所欲為、肆無忌憚。其次,時為侍郎的章惇,日後被史臣赫然列入《奸臣傳》,此人黨同伐異,「老奸擅國」。同時,他又是大文豪蘇東坡最好的朋友之一,證明了歷史人物的立體多面性:「壞人」不一定全壞,「好人」也不一定是完人。
當然,時人言起宋朝,自然首先會想起「靖康之恥」的奇辱和「崖山之役」的慘敗。相較大漢盛唐、朱明滿清,兩宋的領土小得可憐,北宋最盛時也只有2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特別是趙匡胤開國以來「重文抑武」的國策,使得宋朝長期陷於「防禦」的狼狽境地,積弱至亡,甚至出現同樣的悲劇上演兩次這種超奇怪的現象。
其實,在我們撫膺歎息之時,大多數人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自晚唐以來,中原王朝的崩潰所導致的大分裂,致使北中國一直戰亂頻頻。沙陀人石敬瑭更是把燕雲十六州獻奉給契丹人,深植下其後北宋王朝的滔天大禍。而後,契丹、党項、女真、蒙古諸族相繼登上歷史舞臺,刀光閃閃,血肉翻飛。
從現在的眼光看,殘殺、爭鬥自然是波瀾壯闊的「民族大融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就當時來講,宋代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劍影之下遭受了毀滅性的摧殘。
連年不斷的戰爭所造成的巨大消耗,以及兩次亡國的痛苦過程,使得宋朝人民辛勤創造出的財富一而再地化為烏有。最重要的是,戰爭使無數百姓死於非命。13世紀初,金朝佔據的北中國有五千多萬人口,南宋所占的南中國有六千多萬人口。蒙古號角吹響後,經過七八十年間的殺伐,至南宋滅亡時,江南及中原地區的人口竟然從原來的一億多人變成只剩下不到六千萬人,這還有賴於元臣耶律楚材的一句勸說,蒙古大汗才沒有施行把北中國「漢人」殺盡以其地盡作牧場的政策。
由此可見,文明,尤其是刀鋒之上的文明,是何等的脆弱!
漢文明自身的發展總是依據「盛極而衰」的規律脈動,宋王朝也避免不了這種刻骨的悲劇。它的文化水平在當時來講太先進,文明程度太讓人過於陶醉其中。即使囿於一隅,士大夫頭腦中仍覺得自己所居之地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自戀至極的宋朝中國人(當然他們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級而自戀),像極了一個酒足飯飽、事業有成而又身體虛弱的中年男人,他太關注自身精神層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記體內的衰落和「高度發展」所引致的遲鈍。
最讓人恐懼的是,野心勃勃、充滿活力的野蠻人垂涎於文明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逐水草而居之餘,他們如同窺視獵物的群狼,隨時會蹴然一躍,撲向這些定居的、文明的、軟弱的好鄰居。
野蠻毀滅文明,於野蠻人而言,是一種莫大的成長;於文明人而言,卻是萬劫不復的、可悲的停滯。
暫時忘卻那些宿命般的悲劇歷史,回顧三百餘年的文明成就,確實讓我們對偉大的宋朝有駭然驚歎之感。遙想先輩,他們發展高度文明的能力一次又一次被摧毀,國家一次又一次遭受慘烈的災難,但華夏人民充滿激情的創造力、勇往直前的理智力以及百折不撓的意志力,皆給我們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物質遺產和精神遺產。
昔日的繁華,早已成為深埋於地下的廢墟;從前的風華,也化為過眼煙雲。我們卻無法否認那一個燦爛時代的不朽與光榮。往事越千年,我們的鼻孔中仍能嗅到那三個多世紀汴梁與臨安傳來的梅花香氣,還能依稀聽聞詩人詞家那一歎三疊的華麗詠歎。正如一位高盧詩人回憶羅馬的輝煌那樣:「不可能沈沒的身軀,會以不可抗拒的活力重現。它們從深水中反彈而起,將躍得更高!火炬傾翻,反而燃得更亮!你,不朽之城,沈沒之後反而更加光芒四射!」(納馬提阿努斯《循環往復》)
是的,偉大的宋朝,並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它崩潰的瞬間,也如流星隕落一般,照亮了野蠻的黑暗,驅散了內心的恐懼,足以啟發後人的心智。在我們民族的記憶中,宋朝,偉大的宋朝,已成為永恆。
為此,我們需要重新回顧一下那個與野蠻為鄰的偉大時代的方方面面,藉此把記憶的碎片黏合起來,重組三百多年間我們不屈不撓的先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思想方面,隨著佛老在中原的失勢,宋朝科舉制相比唐朝更加注重公平競爭。在《宋史》中入傳的近兩千人中,平民或庶族中小地主出身的人士竟然高達近60%。言論寬鬆,議論自由,是那個時代的大趨勢。同時,宋朝經學,即兩漢以來的對儒家典籍的闡釋之學,日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士人把章句訓詁改為義理闡發。由此,性理之學蔚然大觀,北宋有王安石新學、周敦頤濂學、張載關學、二程洛學,南宋有朱熹道學、陸九淵心學、葉適事功學等等。雖然宋儒理學在日後逐漸發展成為國人的思想桎梏,但就當時來講,正是對兩漢經學和盛唐佛學的推陳出新,粲然形成了一種嶄新的、以儒學為根本的、兼收佛老及諸子學說的新儒學體系,成為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
文學方面,宋詞一洗晚唐浮豔之風,或豪放,或婉約,大放異彩,其中以歐陽修、蘇軾、李清照、辛棄疾、陳亮為代表;宋詩也不可小覷,其多於用典的濃郁書卷氣,使得中華文化精髓每每躍然紙上,尤以陸遊、范成大、楊萬里、劉克莊昂然執其牛耳,悲沈激盪,膾炙人口。
藝術方面,由於宋朝諸帝皆留意文翰,貴族士大夫亦步亦趨,繪畫、書法方面人才濟濟,甚至徽宗皇帝本人就是一個真正的大畫家、大書法家(北宋連銅錢上的鑄字原體也由皇帝親自書寫)。拋開細膩華貴的「院體畫家」不講,蘇軾、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等人所崇尚的「士大夫畫」,使豪爽、性靈的「尚意」審美意境貫穿以後數個朝代,長盛不衰。在這種藝術風氣影響下,宋代在製瓷、建築、雕塑、舞蹈、工藝美術等多個領域,皆達至登峰造極的地步。對此,陳寅恪不無感慨:「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
科技方面,國人一向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其中竟有三項皆肇自宋代: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培根在《新工具書》中這樣寫道:「這三種東西曾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與這三種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能產生更大的力量影響。」自然,在農業、數學、天文、航海、地理、醫學等方面的發明和創造,宋代先人更是不遑多讓,一部《夢溪筆談》,不經意間已記述了數項獨佔鰲頭的「新科技」。
政治方面,宋太祖進一步以皇權為中心加強中央統治集權,巧妙地分散宰相之權。而後,宋朝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科舉考試、官員銓選以及監察制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體制最開明的時代。因此,南北兩宋三百多年,先前與其後各個王朝屢見不鮮的女禍、宦禍、外戚之禍、藩鎮之禍、權臣篡逆之禍、流賊覆國之禍,在宋代基本杜絕。即使在皇權至上的年代,宋帝也承認天下「道理最大」,而並非口口聲聲「朕即國家」。外朝官員能夠以「祖宗家法」的名義限制皇權,大體可按規矩依程序辦事。宰相可把皇帝的「御批」攢至數十封一併退還不辦(杜衍與宋孝宗),最終,皇帝不僅不惱,反誇獎對方「卿等如此守法極好」。這種君臣溫情,在漢唐明清那些所謂的大一統、大有為君王的統治期間是全然看不見的。
經濟方面,兩宋更是那個時代最先進的商業社會,其多種經濟模式均在世界上開一代風氣之先。特別是城市的發展,「屋宇雄壯」,「駭人聞見」。經濟活動「每一交易,動輒千萬」。瓦舍、勾欄,熙熙攘攘,娛樂、休閒通宵達旦,市民生活水平在當時世界絕對是首屈一指。而且,中國首創的紙幣交子、會子均在宋代出現並發展定型,這種革命性的貨幣形式比歐洲要提前六個多世紀。同時,一反前代重農輕商的傳統觀念,宋代商人不僅經濟地位得到提高,甚至可以入仕為官,極大地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士大夫還得出「商人眾則入稅多」的嶄新價值觀。
至於英雄豪傑,兩宋王朝更是層出不窮,撼人心魄──楊業、寇準、狄青、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韓世忠、劉錡、岳飛、虞允文、辛棄疾、孟珙、余玠、李庭芝、姜才、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等等,這些忠臣義士,耿耿精忠,求仁得仁,求義得義,不以成敗利害動其心,不以生死貧富移其志,才節兩全,代表了我們民族至高至偉的精神境界。他們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一心為國,或感激赴義,或慷慨就死,或臨難不屈,或捐軀殉國,功雖有不成,名卻彪炳千秋!
當然,在歷數了宋王朝的輝煌成就之後,我們不得不回到沈重而不能迴避的話題,即兩宋驚人相似的兩次滅亡。
「本朝(宋朝)懲五季(五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庸悔何及!」
文天祥之語,觸及的正是宋初矯枉過正的「抑武」國策。當然,王朝滅亡的原因多種多樣,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某個領袖人物的死亡甚至會改變整個歷史進程,比如釣魚城上飛擲而下的、那塊擊中蒙哥汗的石塊,它就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軌道。但除卻天時、地利以外,人是歷史行為的最關鍵因素。正是人為的懈怠,文怡武嬉,不思進取,才最終導致兩宋的滅亡。
南宋亡國有三要素:民窮、兵弱、財匱,正如王應麟分析的那樣,皆源自當國士大夫的無恥。特別令人慨歎的是,大敵當前,南宋朝野上下那種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態,讓人切齒扼腕。
宋金隆興和議後,雙方和平狀態保持了大約四十年之久。為此,金世宗獲得「小堯舜」的美名,宋孝宗也被當時後世腐儒讚為「仁恕」之主。然而,大儒王夫之對此很有洞見:
「嗚呼,此偷安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於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宴寢不忘者興復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雍(金世宗)雄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顧江左而不垂涎者。故(議)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始以息民為名。貿貿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
細究歷史,會有驚人的發現:宋金兩國,相踵亡於蒙古,其實最早的禍因正是肇於兩國當時的和平「善舉」。
金世宗史稱為明主,但其實也是篡弒之君,因此,他心中肯定認為自己能為眾人推立為帝已屬天幸,所以,他對南宋的「退忍」和一切「和平」努力,其實出於無奈。至於他「息禍養民」一說,只是腐儒和馬屁精的諛詞。
「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窺之」,野蠻民族只要確定了開始想向「文明」邁進,他就會忘掉身邊又會有像「昔日之我」的更野蠻民族蠢蠢欲動,「一息之餘,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禍,亙百餘年而不息!」
由此,我們從歷史的經驗中深刻認識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一旦金戈鐵馬的女真人習慣了風花雪月,蒙古部族的嗷嗷叫聲就肯定由遠而近,金朝、南宋,就會在血火之中化為文明的碎片。
確實,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假設:如果南宋對金國不搞姑息議和那套投降伎倆,不斷深入進擊,派軍隊攻伐中原,這樣的話,不僅可以練兵鼓舞士氣,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後起少數民族聞之驚惕,對宋朝心存畏懼之心。反過來講,宋金爭鬥不歇,金國一方也會持志不懈,日習於戰,不會逐漸消淪其昔日的勇武好鬥。
倘若宋金持戰不歇,即使是金人兵強佔據優勢,每年都乘秋高馬肥之際逼臨江淮,「宋亦知警而謀自壯之略,尚不至蒙古之師一臨,而疾入於海以亡」。歷史中可以得見的是,金兀朮昔日南侵最大的「結果」,就是使南宋湧現了岳飛、韓世忠、劉錡這樣的忠勇大將,福兮禍兮,實相倚依。於金國而言,恰似當年南北朝時代的北魏,待其一息方新之銳氣,通好南朝,安宴於洛陽享天下之際,六鎮之禍正由此肇始。彬彬文治,最後的結果是拓跋氏赤族無遺之禍。因此,在血與火的時代,在危機四伏的世界,最怕的就是整個國家「乍然一息」。那些「以兩國人民和平意願出發」的自欺如果欺瞞了人民的頭腦,長此以往,忘兵忘戰,國民肯定會溺於安樂享受,一切忽然之禍,正是種於「緣飾文雅」之時。
可悲的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我們從來不汲取歷史的經驗!
時下的許多歷史書籍,皆以「恢宏」的煽情修辭或對歷史晦澀的「解構」當成賣點,常把《萬曆十五年》那樣以「偏門」剖析歷史的準歷史研究當作模仿對象,各顯身手,紛紛從經濟、軍事、氣候等「專業」刃面「切入」歷史研究。可惜,這些「大部頭」著作往往忽略了歷史細節的描述,而有些作者功底的不紮實又使這些「大歷史」敘述錯謬百出,或張冠李戴,或弄混朝代,或把演義人物當成歷史真實,凸顯出急於求成的浮躁心態。
此外,歷史「剖析者」們在鋪陳華麗語句大談特談歷史的「規律」時,他們往往故意忽略偶然性在歷史進程中所起到的戲劇性、決定性作用:釣魚城下王堅所率宋朝守軍扔下的一塊石頭,如果離蒙哥汗的身體偏上十公分,不僅僅是中國歷史,全部世界歷史都將被重寫!所以,在學者們以詰屈聱牙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等因素試圖重新詮釋歷史的時候,那些真正對歷史產生決定性意義的個人和事件,卻被不善於注意歷史細節的學者們有選擇性地「遺忘」了。
作為一個甘於坐「冷板凳」的歷史守望者,筆者總是試圖突破「歷史樣板戲」寫作的桎梏,仔細勾沈,復活那些淹沒於茫茫時光中的血肉人生,把已被「格式化」的歷史文字,轉化為鮮活的、生動的、甚至是「現場的」!我的目的只有一個:恢復我們民族偉大的、不朽的記憶!
最後,我想以南宋遺民林景熙一首《京口月夕書懷》作結:
山風吹酒醒,秋入夜燈涼。萬事已華髮,百年多異鄉。遠城江氣白,高樹月痕蒼。忽憶憑樓處,淮天雁叫霜。
是為序。
宋人筆記《蓼花洲閑錄》中,有這樣一則記載:
宋神宗因陝西方面對西夏用兵失利,遷怒於一個主管運糧的漕官。憤憤之下,他親自書寫御批,命令中書處斬此人。轉日,宰相蔡確率群臣上朝。宋神宗問:「昨日御批斬人,今已行否?」蔡確回答:「為臣我正想向陛下奏告此事。」宋神宗聞言不悅:「又有何疑?」蔡確回答:「祖宗以來,未曾殺士人,臣等不欲陛下開此先例。」神宗皇帝沈吟半晌,說:「那就把此人刺面,流放偏遠惡地。」時任門下侍郎的章惇當廷接言:「如此,不如殺掉此人。」宋神宗感到奇怪,問:「卿何出此言?」章惇回言:「士可殺不可辱!」一句話,激得神宗皇帝勃然大怒,聲色俱厲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龍顏雷霆之下,當朝的宰相、群臣不僅沒有在「天威」下震懾惶恐,傲然頂嘴的章惇反而不鹹不淡回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宋神宗默然。
這樣的場景,只是大宋王朝三百多年間一個小小的片斷和插曲,但它包含著無盡的寓意。
首先,可以見出,大宋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開明的王朝。即使口含天憲的帝王,也並非能夠為所欲為、肆無忌憚。其次,時為侍郎的章惇,日後被史臣赫然列入《奸臣傳》,此人黨同伐異,「老奸擅國」。同時,他又是大文豪蘇東坡最好的朋友之一,證明了歷史人物的立體多面性:「壞人」不一定全壞,「好人」也不一定是完人。
當然,時人言起宋朝,自然首先會想起「靖康之恥」的奇辱和「崖山之役」的慘敗。相較大漢盛唐、朱明滿清,兩宋的領土小得可憐,北宋最盛時也只有2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特別是趙匡胤開國以來「重文抑武」的國策,使得宋朝長期陷於「防禦」的狼狽境地,積弱至亡,甚至出現同樣的悲劇上演兩次這種超奇怪的現象。
其實,在我們撫膺歎息之時,大多數人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自晚唐以來,中原王朝的崩潰所導致的大分裂,致使北中國一直戰亂頻頻。沙陀人石敬瑭更是把燕雲十六州獻奉給契丹人,深植下其後北宋王朝的滔天大禍。而後,契丹、党項、女真、蒙古諸族相繼登上歷史舞臺,刀光閃閃,血肉翻飛。
從現在的眼光看,殘殺、爭鬥自然是波瀾壯闊的「民族大融合」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就當時來講,宋代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劍影之下遭受了毀滅性的摧殘。
連年不斷的戰爭所造成的巨大消耗,以及兩次亡國的痛苦過程,使得宋朝人民辛勤創造出的財富一而再地化為烏有。最重要的是,戰爭使無數百姓死於非命。13世紀初,金朝佔據的北中國有五千多萬人口,南宋所占的南中國有六千多萬人口。蒙古號角吹響後,經過七八十年間的殺伐,至南宋滅亡時,江南及中原地區的人口竟然從原來的一億多人變成只剩下不到六千萬人,這還有賴於元臣耶律楚材的一句勸說,蒙古大汗才沒有施行把北中國「漢人」殺盡以其地盡作牧場的政策。
由此可見,文明,尤其是刀鋒之上的文明,是何等的脆弱!
漢文明自身的發展總是依據「盛極而衰」的規律脈動,宋王朝也避免不了這種刻骨的悲劇。它的文化水平在當時來講太先進,文明程度太讓人過於陶醉其中。即使囿於一隅,士大夫頭腦中仍覺得自己所居之地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自戀至極的宋朝中國人(當然他們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級而自戀),像極了一個酒足飯飽、事業有成而又身體虛弱的中年男人,他太關注自身精神層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記體內的衰落和「高度發展」所引致的遲鈍。
最讓人恐懼的是,野心勃勃、充滿活力的野蠻人垂涎於文明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逐水草而居之餘,他們如同窺視獵物的群狼,隨時會蹴然一躍,撲向這些定居的、文明的、軟弱的好鄰居。
野蠻毀滅文明,於野蠻人而言,是一種莫大的成長;於文明人而言,卻是萬劫不復的、可悲的停滯。
暫時忘卻那些宿命般的悲劇歷史,回顧三百餘年的文明成就,確實讓我們對偉大的宋朝有駭然驚歎之感。遙想先輩,他們發展高度文明的能力一次又一次被摧毀,國家一次又一次遭受慘烈的災難,但華夏人民充滿激情的創造力、勇往直前的理智力以及百折不撓的意志力,皆給我們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物質遺產和精神遺產。
昔日的繁華,早已成為深埋於地下的廢墟;從前的風華,也化為過眼煙雲。我們卻無法否認那一個燦爛時代的不朽與光榮。往事越千年,我們的鼻孔中仍能嗅到那三個多世紀汴梁與臨安傳來的梅花香氣,還能依稀聽聞詩人詞家那一歎三疊的華麗詠歎。正如一位高盧詩人回憶羅馬的輝煌那樣:「不可能沈沒的身軀,會以不可抗拒的活力重現。它們從深水中反彈而起,將躍得更高!火炬傾翻,反而燃得更亮!你,不朽之城,沈沒之後反而更加光芒四射!」(納馬提阿努斯《循環往復》)
是的,偉大的宋朝,並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它崩潰的瞬間,也如流星隕落一般,照亮了野蠻的黑暗,驅散了內心的恐懼,足以啟發後人的心智。在我們民族的記憶中,宋朝,偉大的宋朝,已成為永恆。
為此,我們需要重新回顧一下那個與野蠻為鄰的偉大時代的方方面面,藉此把記憶的碎片黏合起來,重組三百多年間我們不屈不撓的先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思想方面,隨著佛老在中原的失勢,宋朝科舉制相比唐朝更加注重公平競爭。在《宋史》中入傳的近兩千人中,平民或庶族中小地主出身的人士竟然高達近60%。言論寬鬆,議論自由,是那個時代的大趨勢。同時,宋朝經學,即兩漢以來的對儒家典籍的闡釋之學,日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士人把章句訓詁改為義理闡發。由此,性理之學蔚然大觀,北宋有王安石新學、周敦頤濂學、張載關學、二程洛學,南宋有朱熹道學、陸九淵心學、葉適事功學等等。雖然宋儒理學在日後逐漸發展成為國人的思想桎梏,但就當時來講,正是對兩漢經學和盛唐佛學的推陳出新,粲然形成了一種嶄新的、以儒學為根本的、兼收佛老及諸子學說的新儒學體系,成為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
文學方面,宋詞一洗晚唐浮豔之風,或豪放,或婉約,大放異彩,其中以歐陽修、蘇軾、李清照、辛棄疾、陳亮為代表;宋詩也不可小覷,其多於用典的濃郁書卷氣,使得中華文化精髓每每躍然紙上,尤以陸遊、范成大、楊萬里、劉克莊昂然執其牛耳,悲沈激盪,膾炙人口。
藝術方面,由於宋朝諸帝皆留意文翰,貴族士大夫亦步亦趨,繪畫、書法方面人才濟濟,甚至徽宗皇帝本人就是一個真正的大畫家、大書法家(北宋連銅錢上的鑄字原體也由皇帝親自書寫)。拋開細膩華貴的「院體畫家」不講,蘇軾、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等人所崇尚的「士大夫畫」,使豪爽、性靈的「尚意」審美意境貫穿以後數個朝代,長盛不衰。在這種藝術風氣影響下,宋代在製瓷、建築、雕塑、舞蹈、工藝美術等多個領域,皆達至登峰造極的地步。對此,陳寅恪不無感慨:「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
科技方面,國人一向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其中竟有三項皆肇自宋代: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培根在《新工具書》中這樣寫道:「這三種東西曾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與這三種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能產生更大的力量影響。」自然,在農業、數學、天文、航海、地理、醫學等方面的發明和創造,宋代先人更是不遑多讓,一部《夢溪筆談》,不經意間已記述了數項獨佔鰲頭的「新科技」。
政治方面,宋太祖進一步以皇權為中心加強中央統治集權,巧妙地分散宰相之權。而後,宋朝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科舉考試、官員銓選以及監察制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體制最開明的時代。因此,南北兩宋三百多年,先前與其後各個王朝屢見不鮮的女禍、宦禍、外戚之禍、藩鎮之禍、權臣篡逆之禍、流賊覆國之禍,在宋代基本杜絕。即使在皇權至上的年代,宋帝也承認天下「道理最大」,而並非口口聲聲「朕即國家」。外朝官員能夠以「祖宗家法」的名義限制皇權,大體可按規矩依程序辦事。宰相可把皇帝的「御批」攢至數十封一併退還不辦(杜衍與宋孝宗),最終,皇帝不僅不惱,反誇獎對方「卿等如此守法極好」。這種君臣溫情,在漢唐明清那些所謂的大一統、大有為君王的統治期間是全然看不見的。
經濟方面,兩宋更是那個時代最先進的商業社會,其多種經濟模式均在世界上開一代風氣之先。特別是城市的發展,「屋宇雄壯」,「駭人聞見」。經濟活動「每一交易,動輒千萬」。瓦舍、勾欄,熙熙攘攘,娛樂、休閒通宵達旦,市民生活水平在當時世界絕對是首屈一指。而且,中國首創的紙幣交子、會子均在宋代出現並發展定型,這種革命性的貨幣形式比歐洲要提前六個多世紀。同時,一反前代重農輕商的傳統觀念,宋代商人不僅經濟地位得到提高,甚至可以入仕為官,極大地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士大夫還得出「商人眾則入稅多」的嶄新價值觀。
至於英雄豪傑,兩宋王朝更是層出不窮,撼人心魄──楊業、寇準、狄青、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韓世忠、劉錡、岳飛、虞允文、辛棄疾、孟珙、余玠、李庭芝、姜才、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等等,這些忠臣義士,耿耿精忠,求仁得仁,求義得義,不以成敗利害動其心,不以生死貧富移其志,才節兩全,代表了我們民族至高至偉的精神境界。他們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一心為國,或感激赴義,或慷慨就死,或臨難不屈,或捐軀殉國,功雖有不成,名卻彪炳千秋!
當然,在歷數了宋王朝的輝煌成就之後,我們不得不回到沈重而不能迴避的話題,即兩宋驚人相似的兩次滅亡。
「本朝(宋朝)懲五季(五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庸悔何及!」
文天祥之語,觸及的正是宋初矯枉過正的「抑武」國策。當然,王朝滅亡的原因多種多樣,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某個領袖人物的死亡甚至會改變整個歷史進程,比如釣魚城上飛擲而下的、那塊擊中蒙哥汗的石塊,它就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軌道。但除卻天時、地利以外,人是歷史行為的最關鍵因素。正是人為的懈怠,文怡武嬉,不思進取,才最終導致兩宋的滅亡。
南宋亡國有三要素:民窮、兵弱、財匱,正如王應麟分析的那樣,皆源自當國士大夫的無恥。特別令人慨歎的是,大敵當前,南宋朝野上下那種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態,讓人切齒扼腕。
宋金隆興和議後,雙方和平狀態保持了大約四十年之久。為此,金世宗獲得「小堯舜」的美名,宋孝宗也被當時後世腐儒讚為「仁恕」之主。然而,大儒王夫之對此很有洞見:
「嗚呼,此偷安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於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宴寢不忘者興復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雍(金世宗)雄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顧江左而不垂涎者。故(議)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始以息民為名。貿貿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
細究歷史,會有驚人的發現:宋金兩國,相踵亡於蒙古,其實最早的禍因正是肇於兩國當時的和平「善舉」。
金世宗史稱為明主,但其實也是篡弒之君,因此,他心中肯定認為自己能為眾人推立為帝已屬天幸,所以,他對南宋的「退忍」和一切「和平」努力,其實出於無奈。至於他「息禍養民」一說,只是腐儒和馬屁精的諛詞。
「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窺之」,野蠻民族只要確定了開始想向「文明」邁進,他就會忘掉身邊又會有像「昔日之我」的更野蠻民族蠢蠢欲動,「一息之餘,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禍,亙百餘年而不息!」
由此,我們從歷史的經驗中深刻認識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一旦金戈鐵馬的女真人習慣了風花雪月,蒙古部族的嗷嗷叫聲就肯定由遠而近,金朝、南宋,就會在血火之中化為文明的碎片。
確實,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假設:如果南宋對金國不搞姑息議和那套投降伎倆,不斷深入進擊,派軍隊攻伐中原,這樣的話,不僅可以練兵鼓舞士氣,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後起少數民族聞之驚惕,對宋朝心存畏懼之心。反過來講,宋金爭鬥不歇,金國一方也會持志不懈,日習於戰,不會逐漸消淪其昔日的勇武好鬥。
倘若宋金持戰不歇,即使是金人兵強佔據優勢,每年都乘秋高馬肥之際逼臨江淮,「宋亦知警而謀自壯之略,尚不至蒙古之師一臨,而疾入於海以亡」。歷史中可以得見的是,金兀朮昔日南侵最大的「結果」,就是使南宋湧現了岳飛、韓世忠、劉錡這樣的忠勇大將,福兮禍兮,實相倚依。於金國而言,恰似當年南北朝時代的北魏,待其一息方新之銳氣,通好南朝,安宴於洛陽享天下之際,六鎮之禍正由此肇始。彬彬文治,最後的結果是拓跋氏赤族無遺之禍。因此,在血與火的時代,在危機四伏的世界,最怕的就是整個國家「乍然一息」。那些「以兩國人民和平意願出發」的自欺如果欺瞞了人民的頭腦,長此以往,忘兵忘戰,國民肯定會溺於安樂享受,一切忽然之禍,正是種於「緣飾文雅」之時。
可悲的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我們從來不汲取歷史的經驗!
時下的許多歷史書籍,皆以「恢宏」的煽情修辭或對歷史晦澀的「解構」當成賣點,常把《萬曆十五年》那樣以「偏門」剖析歷史的準歷史研究當作模仿對象,各顯身手,紛紛從經濟、軍事、氣候等「專業」刃面「切入」歷史研究。可惜,這些「大部頭」著作往往忽略了歷史細節的描述,而有些作者功底的不紮實又使這些「大歷史」敘述錯謬百出,或張冠李戴,或弄混朝代,或把演義人物當成歷史真實,凸顯出急於求成的浮躁心態。
此外,歷史「剖析者」們在鋪陳華麗語句大談特談歷史的「規律」時,他們往往故意忽略偶然性在歷史進程中所起到的戲劇性、決定性作用:釣魚城下王堅所率宋朝守軍扔下的一塊石頭,如果離蒙哥汗的身體偏上十公分,不僅僅是中國歷史,全部世界歷史都將被重寫!所以,在學者們以詰屈聱牙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等因素試圖重新詮釋歷史的時候,那些真正對歷史產生決定性意義的個人和事件,卻被不善於注意歷史細節的學者們有選擇性地「遺忘」了。
作為一個甘於坐「冷板凳」的歷史守望者,筆者總是試圖突破「歷史樣板戲」寫作的桎梏,仔細勾沈,復活那些淹沒於茫茫時光中的血肉人生,把已被「格式化」的歷史文字,轉化為鮮活的、生動的、甚至是「現場的」!我的目的只有一個:恢復我們民族偉大的、不朽的記憶!
最後,我想以南宋遺民林景熙一首《京口月夕書懷》作結:
山風吹酒醒,秋入夜燈涼。萬事已華髮,百年多異鄉。遠城江氣白,高樹月痕蒼。忽憶憑樓處,淮天雁叫霜。
是為序。
目次
【一】不老實的「厚道人」
【二】雄龍雌鳳相對決
【三】懦弱與妥協:一種心理距離
【四】過於嚴肅的滑稽劇
【五】賀蘭鐵馬徹地來
【六】一個人的「改革」
【七】皇后「偷漢」的政治性後果
【八】浪子皇帝流氓臣
【九】殘山剩水留半壁
【二】雄龍雌鳳相對決
【三】懦弱與妥協:一種心理距離
【四】過於嚴肅的滑稽劇
【五】賀蘭鐵馬徹地來
【六】一個人的「改革」
【七】皇后「偷漢」的政治性後果
【八】浪子皇帝流氓臣
【九】殘山剩水留半壁
書摘/試閱
「性情中人」宋徽宗
宋神宗崩後(西元一○八五年),其生母高太后立神宗第六子、自己的孫子趙煦為帝,即宋哲宗,時年僅十歲。
其後九年多,宋朝最高權力機構中實際掌權的是高太后。高太后一直憎惡王安石的「新法」,她召司馬光入朝,盡廢新法,即後世所謂的「元佑更化」。
由於王安石黨羽蔡確以詩文影射高太后為「武則天」,宋廷大起獄案,黨親名單成冊成集,朝中洛黨、朔黨和蜀黨人士心照不宣,大打出手。
宋朝黨爭,至此到達一個小高潮,其惡劣程度一點也不比唐朝「牛李黨爭」要弱。
高太后病逝,乖乖做了九年「孫子」的真孫子宋哲宗終於親政,他對祖母心中非常怨恨。繼位後,這位年輕皇帝一反其道,把老奶奶的所有政治綱領全部顛個,回到其父宋神宗的「改革」路線。
哲宗皇帝任章惇為宰相,把司馬光一黨打為奸佞,全力打擊元佑重臣,司馬光本人還差點被刨棺掘墓。「元佑黨人」,成為當時群臣恐懼的一個羅織罪名。北宋朝廷經這麼大折騰,元氣盡傷。
宋哲宗本人的宮闈生活也亂七八糟。他自己身子骨弱不說,內宮又鬧厭魅之案,無數宮女和太監搭上性命,正宮孟皇后也牽連被廢。
元符三年,年僅二十五歲的宋哲宗一病不起。折騰六年,國事沒有絲毫起色,他自己先「駕鶴西歸」了。可悲的是,宋哲宗死後無子。由此,他同父異母弟弟端王趙佶被推到前臺,是為宋徽宗。
宋徽宗趙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封端王。宋哲宗駕崩,當時,哲宗的嫡母是向太后,就勸哲宗生母朱太妃,說哲宗臨崩表示要立自己的弟弟端王。
朱太妃善良婦人,沉浸在喪子的悲痛中,對此不置可否。
於是,向太后垂簾問政,詢問繼承人問題,執政大臣章惇「厲聲」答道:「依據禮律,應立母弟簡王(即哲宗的同母弟)。」
向太后不願再立哲宗的母弟,就不接章惇話頭,繼續對下面其他大臣說:「神宗諸子,申王年紀最長,但他有目疾,再往下就是端王當立。」
在場的幾位大臣如曾布、蔡卞、許將都很討厭章惇。他們私下各自心中打小算盤:章惇沒有和別人商量就公然在朝堂上自己單獨提出候補帝王人選,倘若哲宗母弟簡王為君,日後新帝追念「擁立」之功,肯定又是這位本是宋哲宗寵臣的章惇莫屬。
為此,幾位大臣們紛紛附和向太后。
章惇一下子在朝堂上成為孤家寡人,剛才的洶洶氣勢也融冰般消解,只能「為之默然」。
「先帝(宋神宗)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不同諸王。」
向太后終於在大宋皇廷上為新君趙佶做出總結性的推舉評語,使得這位本來一心喜愛詩詞書畫的王爺能夠兄終弟及,登上本來離他並不很近的皇帝寶座。
「徽宗未立,(章)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宋史‧徽宗本紀》的結尾讚語中有此言語。
章惇是歷史上有名的奸佞之臣,但他確有「識君」之才。
章惇這個人,並非高俅那樣的浮浪子弟,也不是蔡京那樣的輕薄之才,此人年輕時代就以豪俊著名,博學善文,當時與大文豪蘇軾相交甚厚。宋仁宗時,章惇與其侄章衡中同中進士,由於他侄子當時是殿試第一的狀元,章惇一氣之下竟不去接敕令任官,重新再考下一科。
宋哲宗繼位後,章惇自恃有擁立功,大行因擾民而被廢止的王安石「新法」(王安石是提拔章惇的「恩公」),詆毀司馬光等大臣,勸說宋哲宗對司馬光、呂公著等死去大臣剖棺掘屍,株連親族,可謂是窮兇極惡。
章惇公報私仇,朋比為奸,屢興大獄,並在西北與西夏挑起邊釁,屢戰屢北,喪兵失地。章惇如此不堪,卻有兩件事還值得稱道,其一,就是他執掌朝權時從不濫封親友,四個兒子都是籍籍無名的小官;其二,就是他有超凡的識人之明,深感趙佶不能繼統為君。
宋徽宗繼位不久,即貶章惇出外。不久,這位權臣就於貧困之中死於睦州。死後被列入《宋史‧奸臣傳》。
宋徽宗趙佶繼位後不久,馬上重用與他氣味相投的一幫文人哥們兒和宵小,其中以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面力等人最為「知名」,時人稱之為「六賊」。
奇怪的是,大名鼎鼎的高俅在《水滸傳》中雖名列奸臣第一,但《宋史》中根本沒有他的單獨傳記。在南宋作家王明清的史料筆記《揮塵後錄‧卷七》中,有如下記載:
「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劄頗工。東坡在翰苑出師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曾布),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王)晉卿為樞密都承旨時,佑陵(宋徽宗)為端王,在潛邸日已自好文,故與晉卿善。在殿廬待班,邂逅。(端)王云:『今日偶忘帶篦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端)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高)俅賚往。值(端)王在園中蹴鞠,俅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之意,大喜,呼奴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既謝篦刀之況,並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逾月,王登寶位。上優寵之,眷渥其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云:『汝曹爭如彼好腳跡邪!』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衛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自(高)俅始也。父(高)敦復,復為節度使。兄(高)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座。子侄皆為郎。潛延閣恩幸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蘇東坡一家),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候甚勤。靖康初,佑陵(宋徽宗)南下,(高)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為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高)俅獨死於牖下。」
可見,高俅還是大文豪蘇東坡的門下,而且為人還算忠厚,富貴後對蘇氏子弟也很照顧。他憑機緣,加之一腳好球技攀龍附鳳,平生好似無甚大惡,而且善終於家,死的非常是時候,免去赴北國和徽宗一起風霜勞苦。
宋神宗崩後(西元一○八五年),其生母高太后立神宗第六子、自己的孫子趙煦為帝,即宋哲宗,時年僅十歲。
其後九年多,宋朝最高權力機構中實際掌權的是高太后。高太后一直憎惡王安石的「新法」,她召司馬光入朝,盡廢新法,即後世所謂的「元佑更化」。
由於王安石黨羽蔡確以詩文影射高太后為「武則天」,宋廷大起獄案,黨親名單成冊成集,朝中洛黨、朔黨和蜀黨人士心照不宣,大打出手。
宋朝黨爭,至此到達一個小高潮,其惡劣程度一點也不比唐朝「牛李黨爭」要弱。
高太后病逝,乖乖做了九年「孫子」的真孫子宋哲宗終於親政,他對祖母心中非常怨恨。繼位後,這位年輕皇帝一反其道,把老奶奶的所有政治綱領全部顛個,回到其父宋神宗的「改革」路線。
哲宗皇帝任章惇為宰相,把司馬光一黨打為奸佞,全力打擊元佑重臣,司馬光本人還差點被刨棺掘墓。「元佑黨人」,成為當時群臣恐懼的一個羅織罪名。北宋朝廷經這麼大折騰,元氣盡傷。
宋哲宗本人的宮闈生活也亂七八糟。他自己身子骨弱不說,內宮又鬧厭魅之案,無數宮女和太監搭上性命,正宮孟皇后也牽連被廢。
元符三年,年僅二十五歲的宋哲宗一病不起。折騰六年,國事沒有絲毫起色,他自己先「駕鶴西歸」了。可悲的是,宋哲宗死後無子。由此,他同父異母弟弟端王趙佶被推到前臺,是為宋徽宗。
宋徽宗趙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封端王。宋哲宗駕崩,當時,哲宗的嫡母是向太后,就勸哲宗生母朱太妃,說哲宗臨崩表示要立自己的弟弟端王。
朱太妃善良婦人,沉浸在喪子的悲痛中,對此不置可否。
於是,向太后垂簾問政,詢問繼承人問題,執政大臣章惇「厲聲」答道:「依據禮律,應立母弟簡王(即哲宗的同母弟)。」
向太后不願再立哲宗的母弟,就不接章惇話頭,繼續對下面其他大臣說:「神宗諸子,申王年紀最長,但他有目疾,再往下就是端王當立。」
在場的幾位大臣如曾布、蔡卞、許將都很討厭章惇。他們私下各自心中打小算盤:章惇沒有和別人商量就公然在朝堂上自己單獨提出候補帝王人選,倘若哲宗母弟簡王為君,日後新帝追念「擁立」之功,肯定又是這位本是宋哲宗寵臣的章惇莫屬。
為此,幾位大臣們紛紛附和向太后。
章惇一下子在朝堂上成為孤家寡人,剛才的洶洶氣勢也融冰般消解,只能「為之默然」。
「先帝(宋神宗)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不同諸王。」
向太后終於在大宋皇廷上為新君趙佶做出總結性的推舉評語,使得這位本來一心喜愛詩詞書畫的王爺能夠兄終弟及,登上本來離他並不很近的皇帝寶座。
「徽宗未立,(章)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宋史‧徽宗本紀》的結尾讚語中有此言語。
章惇是歷史上有名的奸佞之臣,但他確有「識君」之才。
章惇這個人,並非高俅那樣的浮浪子弟,也不是蔡京那樣的輕薄之才,此人年輕時代就以豪俊著名,博學善文,當時與大文豪蘇軾相交甚厚。宋仁宗時,章惇與其侄章衡中同中進士,由於他侄子當時是殿試第一的狀元,章惇一氣之下竟不去接敕令任官,重新再考下一科。
宋哲宗繼位後,章惇自恃有擁立功,大行因擾民而被廢止的王安石「新法」(王安石是提拔章惇的「恩公」),詆毀司馬光等大臣,勸說宋哲宗對司馬光、呂公著等死去大臣剖棺掘屍,株連親族,可謂是窮兇極惡。
章惇公報私仇,朋比為奸,屢興大獄,並在西北與西夏挑起邊釁,屢戰屢北,喪兵失地。章惇如此不堪,卻有兩件事還值得稱道,其一,就是他執掌朝權時從不濫封親友,四個兒子都是籍籍無名的小官;其二,就是他有超凡的識人之明,深感趙佶不能繼統為君。
宋徽宗繼位不久,即貶章惇出外。不久,這位權臣就於貧困之中死於睦州。死後被列入《宋史‧奸臣傳》。
宋徽宗趙佶繼位後不久,馬上重用與他氣味相投的一幫文人哥們兒和宵小,其中以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面力等人最為「知名」,時人稱之為「六賊」。
奇怪的是,大名鼎鼎的高俅在《水滸傳》中雖名列奸臣第一,但《宋史》中根本沒有他的單獨傳記。在南宋作家王明清的史料筆記《揮塵後錄‧卷七》中,有如下記載:
「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劄頗工。東坡在翰苑出師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曾布),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王)晉卿為樞密都承旨時,佑陵(宋徽宗)為端王,在潛邸日已自好文,故與晉卿善。在殿廬待班,邂逅。(端)王云:『今日偶忘帶篦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端)王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高)俅賚往。值(端)王在園中蹴鞠,俅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之意,大喜,呼奴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既謝篦刀之況,並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逾月,王登寶位。上優寵之,眷渥其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援以祈恩,上云:『汝曹爭如彼好腳跡邪!』數年間建節,循至使相,遍歷三衛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事,自(高)俅始也。父(高)敦復,復為節度使。兄(高)伸,自言業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座。子侄皆為郎。潛延閣恩幸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蘇東坡一家),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候甚勤。靖康初,佑陵(宋徽宗)南下,(高)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為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高)俅獨死於牖下。」
可見,高俅還是大文豪蘇東坡的門下,而且為人還算忠厚,富貴後對蘇氏子弟也很照顧。他憑機緣,加之一腳好球技攀龍附鳳,平生好似無甚大惡,而且善終於家,死的非常是時候,免去赴北國和徽宗一起風霜勞苦。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