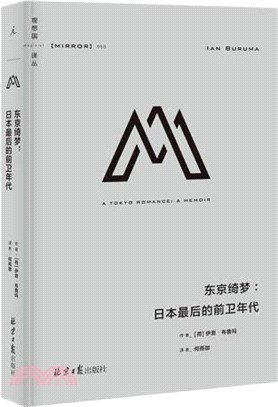東京綺夢:日本最後的前衛年代(簡體書)
- 系列名:理想國譯叢
- ISBN13:9787547740163
-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北京日報)
- 作者:(荷)伊恩‧布魯瑪
- 譯者:何雨咖
- 裝訂/頁數:精裝/256頁
- 規格:21cm*14.5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21/08/01
商品簡介
20世紀70年代,日本剛剛結束洶涌激蕩的戰後重建。此前的十多年間,日本人口激增,經濟起飛,制造業繁榮發達,文學、電影等藝術文化領域一片欣欣向榮。而若是稍往後看,彼時的日本又處在經濟泡沫時代的前夜,即將被卷入全球化的旋渦中。夾在其間、看似不怎麼起眼的70年代,實則繼承了戰後之初的輝煌發展成果,又昭示了日本文化大繁榮、走向世界的進步潮流,擁有承前啟後的地位。
1975年,20歲出頭的伊恩·布魯瑪來到了日本。他憑借過人的嗅覺,迅速發掘出70年代異彩紛呈卻不為世界所知的日本前衛文化,深入到深層的角落、前沿的現場和核心的文化藝術圈:東京淺草的雜亂小巷和破敗劇院、下町的文身工作室、京都的真人色情秀,還有黑澤明的電影拍攝現場、寺山修司的實驗劇團、唐十郎的巡演帳篷。他以一個“外人”的身份,遊離於戲劇、電影、攝影等領域和東京地下文化生活的邊緣,好奇而冷靜地觀察和接觸身邊的一切。
離開日本數十年後,布魯瑪基於對這段親身經歷的回憶,結合長期的研究思考,敏銳犀利地捕捉到日本懷念傳統又敢於革新、迷戀異邦又封閉排外、注重秩序又崇尚暴力的復雜文化氣質,從時代與民族的外部描摹出一副迷人獨特的日本面貌。
作者簡介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生於荷蘭海牙。曾擔任《遠東經濟評論》和《旁觀者》雜志記者與《紐約書評》主編,為《紐約時報》《新聞周刊》等報刊撰寫關於亞洲的政治和文化評論,並曾任教於牛津、哈佛、普林斯頓、格羅寧根等大學。現為紐約巴德學院保羅·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權和新聞學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零年:1945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創造日本:1853—1964》等。2008年被授予“伊拉斯謨獎”以表彰他“在歐洲對文化、社會或社會科學做出的重要貢獻”,同年因其以卓越的著作幫助美國讀者理解亞洲的復雜性而獲得“肖倫斯特新聞獎”。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雜志選為“全球頂jian思想家”。
名人/編輯推薦
追溯東京奧運開幕式舞蹈表演形式的誕生與興盛 詮釋“暗黑舞踏”何以被稱為日本獨有的藝術
森山未來在東京奧運開幕式上的“舞踏”被觀眾吐槽為“陰間鬼舞”,而伊恩·布魯瑪在1970年代留學日本期間,恰巧結識了演繹“暗黑舞踏”的大師大野一雄,精妙地講述了這種“怪誕”藝術形式的產生過程與欣賞之道!
實驗劇團、真人色情秀、文身工作室…… 日本文化絕不止動漫、日料與歌舞伎
作者在本書中介紹的日本文化領域迥異於人們對日本的一般認識,深入發掘了這個國家較不為人知的文化面貌。它能讓讀者發現,日本文化的魅力不只是流行與傳統,還有先鋒藝術在傳統與前衛之間的大膽探索,以及日本文化在這方面體現出的矛盾性和復雜性。
零距離接觸日本文化藝術名家 重溫大師群集英雄輩出的黃金時代
給寺山修司的劇團幫忙,與舞踏大師土方巽喝酒聊天,在黑澤天皇的電影裡跑龍套,跟著唐十郎去日本各地與紐約巡演……布魯瑪以一介留學生的身份,結識了無數當代日本大師。在本書的字裡行間,你隨時隨地都可能碰到一個今天已享譽全球的名字。
留學多年後的再回首 站在民族與時代的外部觀察日本
這本書是伊恩·布魯瑪在留學日本數十年後,根據他的回憶和後來對日本的長年研究寫成的,因此不僅極具外部視角的客觀性與回憶體的歷史色彩,而且富含日本文化學者獨有的深度,篇幅雖小,但回味無窮。
目次
圖片列表
一 結緣:“浪漫”的日本
二 初見東京:在幻夢與現實間遊走
三 “情色、怪誕與無意義”
四 銀幕後的夢幻殿堂
五 對他者的迷戀
六 真實藏身於有意的丑陋
七 寺山修司和唐十郎:兩種前衛日本
八 人形玩偶與肉體叛亂
九 藍眼睛裡看日本
十 文化休克:當日本人遭遇西方
十一 從神的後裔到世界遊民
致謝
索引
書摘/試閱
1975年秋天,我與東京見了第一面,叫我震驚的是,這裡太像天井棧敷的劇場布景了。我本以為寺山修司的戲劇場景是出自一個詩人極度狂熱的想象,是瘋狂而夸張的超現實主義幻夢。誠然,我並沒有遇到穿著19世紀法式服裝的腹語者被裹著皮衣的女施虐狂鞭打。但東京的都市風光本身就有種戲劇感,甚至讓人產生幻覺,沒有任何東西是樸素低調的;處處都是風格鮮明的產品、場所、娛樂、餐館、時尚等等,無一不在以自己的方式尖叫吶喊,吸引關注。
我曾在萊頓大學苦心學習過的漢字,此時以塑料或霓虹燈的形式,高懸在高速公路之上或火車站外面,出現在從高高的寫字樓垂掛而下的條幅上,還出現在電影院和被稱為“卡巴萊”的歌舞廳用油漆塗寫的標識中—標識上承諾,該場所會提供各式各樣的娛樂項目。在大部分的西方城市,這些娛樂項目都是不見光的,而東京似乎很少會有什麼是不見光的。
我後來得知,唐納德·裡奇不認識漢字,也不會日語。這對他來說是一件幸事,正如他的朋友、杰出的日本文學學者愛德華·賽登施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曾經略帶尖刻的評論所說,那些用油漆書寫得優美雅致或以五彩斑斕的霓虹燈形式呈現的漢字,很多都有著非常古老的起源,看上去頗具異域之美;但前提是你不知道它們的意思—比如說,軟飲廣告,或者專治痔瘡(這種病在日本常見得出人意料)的診所的宣傳。
日本的視覺密度可以把人淹沒。最初的幾個星期,我在一副茫然而孤獨的外國人軀殼中到處走,隨著穿著整潔的黑發人組成的人流顛簸起伏。在還沒學會說或讀日語之前,我先用雙眼吸收周圍的一切。我就那樣走啊走啊,常常會在新宿或澀谷迷宮般的街巷中迷路。很多廣告都有著和初秋蔚藍的碧空一樣鮮明的色彩。我終於明白,那些古早日本版畫中的色彩,完全沒有進行什麼非寫實的藝術加工,而是對日本光線的如實描繪。狹窄的商業街兩旁掛上了連串的鮮橙色和金色塑料菊花,表示秋季已至。霓虹燈、深紅的燈籠、電影海報,一切都像密集的視覺炮火,撲面而來,還配上了刺耳的機械噪聲—來自日本流行音樂、廣告歌曲、唱片店、歌舞廳、劇院和火車站的廣播系統,還有咖啡館、酒吧和餐館裡那些整日不曾關閉的電視機發出的巨響。這些聲音讓J. A. 西澤為天井棧敷所配的演出背景音樂都顯得幾乎安寧肅靜了。
我並沒有立即深入到日本的生活中去。在和女友澄江一起找到公寓定居之前,有那麼幾個星期,我都待在一個“緩衝區”,那是在不同文化之間的歇腳之地。我有一位名叫阿什利·雷伯恩(Ashley Raeburn)的英國親戚,在日本做“殼牌”的商務代表,他和妻子內絲特(Nest)住在青葉臺的一座大宅子裡。那一片丘陵地帶是豪華上等社區,高高地凌駕於東京城幾大商業中心的喧囂之上。他們家宅的後面有一片寬大的草坡,有人打理,四季常青。每到星期天,我們就在上面打門球,噴灌器澆水的聲音讓我想起自己在海牙度過的童年。司機會開勞斯萊斯送阿什利去上班。宅子裡有一群穿著制服的仆人,其中一位會把餐食端到栗木長桌上,那桌子經過精心的打磨,閃著耀眼的光澤。每道菜吃完,搖一下鈴鐺,仆人就會應聲端上下一道菜。這一切和我白天看在眼裡、聽在耳內的那座城市形成了極端鮮明的對比。只要我和阿什利與內絲特住在一起,東京就仍然只是一場盛大的演出,一個某種意義上的劇院,我可以在每天晚上退場,進入青葉臺那與殖民地別無二致的富足優裕之中。
我在阿什利的豪宅中窺見的屬於日本的世界是完全位於“樓下”(belowstairs)的(“樓下”這個說法來自從前的英國鄉村大莊園)。和阿什利與內絲特一起坐在爐火邊,一邊享用餐後的威士忌,一邊討論日本和日本人,這日子的確舒坦。但我更喜歡在廚房裡一杯接一杯地喝著綠茶,拼命捋順我磕磕絆絆的日語,和司機攀談—他曾經做過警察,很愛開玩笑。我也跟廚師聊天,跟為我們提供晚餐服務的那些善良女士們聊天。被人開著殼牌公司的公派勞斯萊斯接送,讓我覺得過於引人注目,還略微有點尷尬。但我對“樓下”的偏好並不是“逆向勢利”,而是出於洞察日本那些神秘謎團的渴望。如果我想要融入,就最好迅速地學習。正是在廚房裡,我接受了最早的日語禮儀教育:根據與我對話的人而使用不同的語式。司機和廚師對我可以不說敬語,因為我比他們年輕很多,但我對他們就必須說敬語。除了慣用語之外,人稱代詞甚至是動詞的結尾,都會因為年齡、性別和社會地位而變化。這是日語中不可或缺的關鍵部分,不僅一開始很難掌握,還會隨著語言技能的提升變得越來越重要。我面對的難題之一是,我模仿女友學了很多日語裡的女性用語,這讓我聽起來有點像個總在癡笑的“變裝皇後”。我後來很快了解到,一個人日語說得越流利,他言語中的失禮之處在當地人聽來就會越刺耳。不過當時我的日語還處於相當基礎的水平,所以我在青葉臺的不當言辭也就得到了原諒。
日間,我漫步東京,想起初到洛杉磯時感受到的文化衝擊,那種感覺如同身處一個巨型電影場景;這場景被迅速地搭建起來,又迅速地倒塌,其中包含的建筑幻想有都鐸王朝風格、墨西哥摩爾式風格、蘇格蘭男爵風格和法國學院派風格。當時我受到震驚,是因為以前我從未見過那樣的城市—習慣於歐洲各個歷史古城那種踏實牢固的我,既為洛杉磯著迷,又有那麼一點自鳴得意,似乎在一個更為古雅的環境中長大就賦予了我某種清高的道德優越感。東京和很多亞洲戰後城市一樣,那無處不在的廣告牌和沿公路林立的單排商業區,都對南加州的模式多有借鑒。但東京的那種密度—人群、噪聲、擁擠的視覺衝擊—讓洛杉磯相形之下顯得沉靜保守。
有這麼一家咖啡館在我心中揮之不去,算是我在20 世紀70 年代中期初見的那座城市的典型範例。這家咖啡館叫“凡爾賽”,位於地下,在日本最大的車站之一—新宿站的東口附近。要去那家店,你得走下陡峭的混凝土臺階,耳中還轟鳴著一家著名相機店吵鬧的廣告歌。突然之間,你就到了,身處於一個18世紀法國莊園的會客廳,裡面裝飾著枝狀大燭臺、大理石墻壁,鍍金的家具是路易十四時期的風格,巴洛克音樂飄散在店內。自然,這一切都是塑料和膠合板制成的。人們會在這以冒牌貨構建的壯麗與美妙之中一坐就是幾個小時,抽煙、看漫畫,聽著理乍得·克萊德曼(Richard Clayderman)用音色清脆的鋼琴彈奏莫扎特的《G大調弦樂小夜曲》(Eine kleine Nachtmusik)。“凡爾賽”在很久以前就被拆除了,那時候大部分的咖啡館都難逃這樣的命運。如今,原址上可能有家星巴克,或者一家提供日本與意大利北部融合菜的餐館。
1975年我初次觀察到的東京,大部分都是在20世紀60年代修建的,那時候經濟加速發展,蓄勢起飛。目之所及沒有太古老的東西,除了一些廟宇和神社,和少數在熊熊烈火和槍林彈雨中幸存下來的20世紀早期磚石建筑。19世紀末,東京循著西方的軌跡完成了現代化;1923年,一場地震將其半毀,到1945年它又被美軍轟炸得滿城瓦礫碎石。60年代是廉價夢幻建筑的大好時候。戰爭毀滅了一切,之後人們經歷了多年的樸素艱辛,大家渴望真正的(但多半仍然是想象的)奢侈。那時候鮮有日本人能找到路子出國旅遊,因此日本修建了一個想象出來的“國外”,迎合人們的夢想,於是就有了路易十四風格的咖啡館、德國啤酒館,還有一家壽命不長的著名酒店,名為“伊麗莎白女王二號”,用混凝土修成遠洋客輪的形態,還配上了錄音的霧號聲。
在美國境外修建的第一座迪士尼樂園就在日本,時間是1983 年,選址於離成田國際機場不遠的地方。唐納德·裡奇曾寫道,根本沒有修建的必要,因為日本人已經有了一個迪士尼樂園,名叫東京。這個城市的非住宅區確實有主題公園那種轉瞬即逝之感。激賞裡奇的英國小說家克裡斯托弗·伊舍伍德戰前住在柏林,之後在洛杉磯安家,他為那座“收養”他的城市寫了如下文字:“一百年前,在這海岸上,有些什麼呢?如今這些脆弱的建筑,又有哪些能在一百年後依舊矗立?也許一座也不會剩下。唔,我喜歡這個想法。這很現實,令人振奮。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比較容易牢記並接受一個事實,就是一百後你自己也不存在了。”
這樣的情緒之中飽含著濃厚的日本色彩,即沉默地接受世事短暫的現實。2014 年,諾曼·米本在洛杉磯去世,我在他的追悼會上引用了伊舍伍德的上述文字。
我想,伊舍伍德應該會喜歡20 世紀70 年代的東京。戰時的陰暗憂鬱已經一掃而空,狂熱的享樂主義取而代之。最重要的是,那種幻覺感會吸引他,因為他向往東方神秘主義,喜歡事物稍縱即逝的概念。然而,東京和洛杉磯之間有個重要的區別。洛杉磯從未有過悠久深邃的歷史,而東京,或從前所稱的江戶,在12 世紀就已經是個小小的城邑。18 世紀,江戶是世界第二大城市,僅次於北京。因此,1975 年我遇到的那個充斥著塑料夢幻的東京,雖然有著東拼西湊、風格混雜的建筑物,借鑒了全世界很多地方的風格,在形式上做出了很大改變,但它其實是修建在一層層厚重的歷史之上的。
經過擦除和重寫的現代東京,仍然顯露出過去時光的蛛絲馬跡,比如街道的布局。但歷史基本只是活在流行文化對歷史記憶的表達之中,作為神話存在著。在東京,就連很臨近的過去都浸潤在傳奇之中。新的70年代開始還不到幾年,60年代就已經成為懷舊的云煙,人們紀念著那時年輕人的反叛和實驗。“那時候你應該來看看。”那些過來人如是說。啊,1968年的學生示威、花園神社的地下戲劇表演、新宿站附近那些“偶發事件”—被稱為“瘋狂部落”的本土嬉皮士們總在那裡廝混。還有大島渚早期的電影作品,橫尾忠則設計的海報,筱山紀信的攝影作品,以及土方巽開創的“舞踏”*。
我到東京的時候,“瘋狂部落”已經是過去時了。在新宿站,相比抱著吉他撥弦的嬉皮士,你更有可能遇到碩果僅存的二戰老兵,在戰火中殘廢了,穿著白色和服,拖著木質假肢,用手風琴演奏著悲傷的戰時歌謠。有些人會說,時代的狂歡在1970年仿佛計好時間一般戛然而止,終止的標志就是三島由紀夫的自殺。這位小說家在東京中部一個軍事基地發動政變,失敗後便上演了武士切腹自盡的慘烈之死,自殺時他身邊還圍著手下那群穿著軍服、年輕帥氣的士兵。其實,文化並無“終止”一說,只是有所變化。到了1975年,之前那些年代的反叛者,包括寺山修司在內,都變成了備受尊敬的大人物,獲得了權威獎項,受邀參加各種國際盛會。
也許,喚起人們懷舊情緒的,是東京毀滅和建設的速度。總有個“那時候”供人們強烈地懷想。在並不算特別久遠的過去,整個城市還是運河交錯,木頭房子林立;那時候,所謂“江戶之花”的大型火災頻發,木房子常常被付之一炬。很少有建筑是致力於永久留存的;沒有大型的石質教堂,紀念碑式的不朽建筑也並非日本的風格。東京的歷史只能在碎片中略窺一二:這兒有座殘垣斷壁的貴族花園,那兒有座重建的神社,或者一個小小的酒館,那時三島在這裡受人矚目,現如今它們卻都已被廢置了。
1947 年,唐納德·裡奇還是美國軍方報紙《星條旗報》(Stars and Stripes )的年輕記者,他在淺草的街巷中漫步,就在兩年前,那裡剛被美國空軍轟炸。淺草位於東京東端的平民聚居區,在隅田川一側,約100 年間,那裡是全城最具活力的大眾娛樂區域,處處是電影院、滑稽戲院、咖啡館和酒館、妓館和歌舞廳、街市和廟會。川端康成最早那些關於“咆哮的20 年代”的黑幫匪徒與舞女的故事,就常常以淺草為背景。那是被很多人傷懷哀悼的歲月,其主旨是“エロ·グロ·ナンセンス”—情色、怪誕與無意義。
裡奇爬上淺草老舊的地鐵站塔樓,與他同行的是川端康成,穿著一件簡單的冬季和服。兩人對彼此的語言都一竅不通,只能無言地指著戰後早期的東京那破舊混亂的風景。裡奇提到川端早期小說中一個人物的名字,於是作家微微一笑,指著一個地方,那是他想象中人物曾居住的地方。川端的城市遭遇毀滅,但他似乎並未因此倉皇焦慮;那座城市依然存活於他的想象中。
60年代,寺山修司最喜歡進行的實驗之一,就是在街頭上演他的戲劇。他有一部著名的劇作,名字就叫《扔掉書本上街去》(書を捨てよ町へ出よう)。他想要打破藝術表演和普通生活場景之間的障礙。他的演員們穿著各種行頭,打扮成來自不同年代的人—20世紀20年代的誘惑妖婦、19世紀的花花公子、20世紀60年代的嬉皮士—混入人群之中,打破人們的生活常規,讓他們震驚不已。那時候,天井棧敷並非唯一嘗試將現實生活與幻想融合的劇團,巴黎、紐約或阿姆斯特丹也在進行類似的實驗;而東京的不同之處在於,這座城市需要打破的幻想與現實的障礙,並沒有那麼大。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