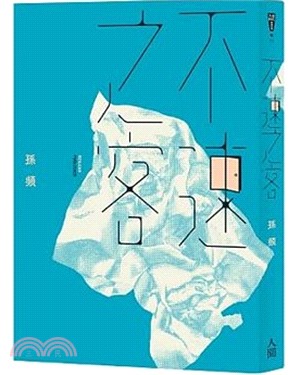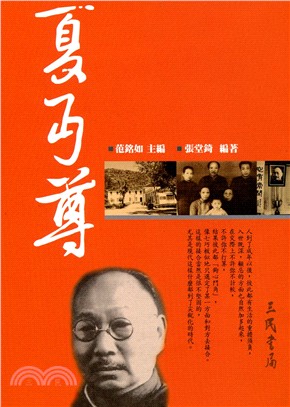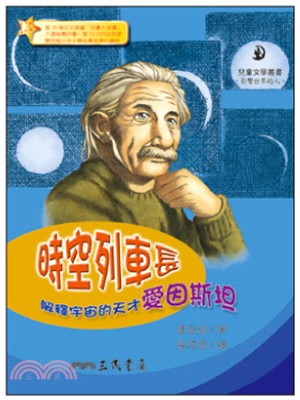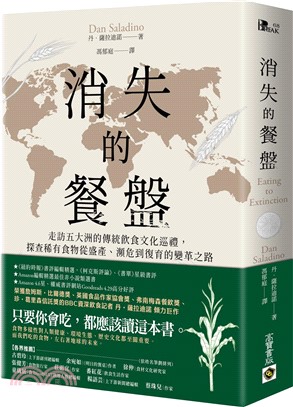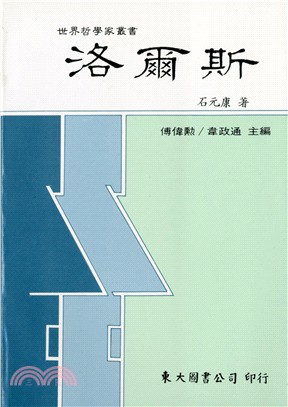再享89折,單本省下34元
商品簡介
八○後出生的孫頻是近年來中國文壇中頗為亮眼的小說家,她的文本無視於一般婉約細緻的女性氣質,亦無視於眾人對於罪惡、毀滅、苦難接受的底線。她寫作懷著強烈的「自殘」與痛覺,卻也清明而警醒地再現出人為蟲豕、天地不仁的荒涼視域,那些底層的,殘酷的生命之苦難與掙扎,是血,是骨,是殘破的肉身,泛漫一地的跡痕。然而,奇特的是,在這苦難人間煉獄的背後,孫頻闡釋的出黑暗與光明的高度反差,血而後的重生,罪孽後的潔淨,毀滅後的救贖,這也形成孫頻式的敘述美學與文字魔魅,令人低迴不已。
──王鈺婷(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有時候我覺得作家的職業與敦煌千佛洞裡的畫工很相似,與其說他們在那洞裡畫出了一幅幅不朽的壁畫,不如說他們為人類畫出了一盞盞心燈,因為,當時的洞裡有多黑啊。為人類畫出的心燈其實就是作家用文字爭取來的人存在的更高尊嚴和意義。所以我一直覺得文學是最具有宗教氣質的藝術形式。宗教消退之後,文學便吸收了宗教所產生的大量情感和情緒,再把它們傳達給人類。文學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體現。所以文學必定會帶有補償與救贖的性質,它生來就是要與黑暗和絕望抗爭的,是用來消解苦難的,對於人們來說,這種生才是文學中的生。
──孫頻
作者簡介
女,1983年生,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系,現供職於太原文學院。2008年開始小說創作,發表有小說兩百餘萬字,有小說集《隱形的女人》、《九渡》、《三人成宴》出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合同製作家。
序
〈生之慾,愛之慾〉
王鈺婷(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八○後出生的孫頻是近年來中國文壇中頗為亮眼的小說家,她的文本無視於一般婉約細緻的女性氣質,亦無視於眾人對於罪惡、毀滅、苦難接受的底線。她寫作懷著強烈的「自殘」與痛覺,卻也清明而警醒地再現出人為蟲豕、天地不仁的荒涼視域,那些底層的,殘酷的生命之苦難與掙扎,是血,是骨,是殘破的肉身,泛漫一地的跡痕。然而,奇特的是,在這苦難人間煉獄的背後,孫頻闡釋的出黑暗與光明的高度反差,血而後的重生,罪孽後的潔淨,毀滅後的救贖,這也形成孫頻式的敘述美學與文字魔魅,令人低迴不已。在《不速之客》裡,孫頻反覆質問的是生命的本質,抑或是活著的意義,最終她想從她筆下這些掙扎的靈魂中逼臨出生之慾,與愛之慾,而愛與生所展現的強大力道,讓我們看到絕望人生所抱持著與生命搏鬥的尊嚴,及其愛之信仰。
《不速之客》篇首之作為〈不速之客〉,是亡命之徒的殺手與「賢良」妓女相遇的故事,也是剖析真愛的佳構。殺手與妓女,在社會底層掙扎求生的倆人,同具卑微的生存本質,是本質上命運相同的畸零人。沒錢沒本事的女主角紀米萍自言從沒有人將其視為人,像雞一樣陪酒,睡覺是其和男人打交道的方式,然而「傻逼」的紀米萍視接吻比做愛重要,內心深處渴望做一回好女人,有人愛她一回,而她將一股腦兒全心投入,如同獻祭的肉品。懷抱這樣信念,不惜作踐尊嚴的紀米萍也成為男主角蘇小軍眼中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在一次蘇小軍動了惻隱之心收留紀米萍後,紀米萍也長成蘇小軍家門的怪樹,一點一點秏光蘇小軍對其的喜愛,卻也挖掘出蘇小軍「十惡不赦」外表下易感、「文物」似的自己。蘇小軍不忍搬家,為紀米萍留條活路,也為自己開啟生路,小說的結局受到仇家尋仇而成為殘疾人的蘇小軍,最終與渴求照顧人的紀小萍聚首,孫頻寫出另類羅曼史,畸零人在卑微人生中共處的「歲月靜好」,現世並不安穩,卻也洋溢真摯動人的生命情調,紀小萍也以她綿密不盡的纏鬥闡釋愛,愛是只求照顧對方,愛是不求回報與不問結果,愛是殘缺生命所超脫的幸福之花,而愛的前提是,對方直視到她卑微形體下作為「人」所具有的價值。
〈乩身〉則是《不速之客》中最獨特的作品,展現出孫頻揮灑淋漓的創作能量,將卑微生命所淬煉的「生之本質」,提升到更高、更深遠的層次。〈乩身〉的場景落在山川阻隔的千年古城交城,女主角常英從小瞎眼,遭父母遺棄,在祖父扶養下成人,祖父為保護瞎女,將其改名常勇,並塑一男人肉身,而後常勇成為鄉野中奇特的風景—男形女身、雌雄同體的陰陽人,祖父並口授算命問吉凶的訣竅以求常勇活路,而祖父離去後,常勇果然無以營生,成為隱遁黑暗之中的拾荒者。以冷筆寫熱情的孫頻,她對於人世的炎炎熱腸,在於書寫常勇與楊德清的聚合,同具悲劇性命運的常勇與楊德清,同是非人,同是困守在蟲豕一樣人生的弱勢們,孫頻將兩人比喻為戰友,為世界上之親人。
楊德清畸零的人生遭遇,孫頻寫得最透徹之處,在於他想「蹭死人一碗飯」而不可得的遭遇,以及其後形同閹割的人生。原本在喪事中捧童女童男紙牛紙馬的楊德清,因為二十幾歲從沒有女人,貪戀弔喪人豬肉上肉質的洞,當他瀕臨高潮之時,被眾人打罵,從此一蹶不振的一幕,是如此殘酷荒謬又無比寫實,一則小人物的悲歌。小說描述被閹割的男人和被閹割的女人的結合,恐懼沒人知道她是女人的常勇,在楊德清的強姦中,感受到體內禁錮的「女性」借屍還魂的喜悅,作一回「真正」的女人,也在意外懷孕墮胎的過程中,體認到兩人相互依存的「同體感」。小說最見功力之處,在於書寫兩位最不潔底層的人,藉由迎神賽會中扮演馬裨,展現與自己生命最後翻身機會的搏鬥姿態,以自殘和自虐活成一個人。在大雪紛飛中以鋼釬穿腮的兩個紅衣人,上神做了乩身,贏得敬畏與尊嚴,鬼神之間的「中間物」,也活出了蟲豕一樣的人生,但這也諭示兩人的死亡。半人半神的楊德清雖贏得虛幻的崇高感,不敵以肉身幻化金身的侷限,他臨死前,以手與常勇交媾的肢體,是血腥的標本,也是復返子宮的嬰孩之「迴光返照」;而在眾人圍觀進行一場場華麗扶乩演出的常勇,也在街道拓寬、拆掉老宅的抗議中,以肉身火焚,解救蒼生,常勇首次在眾人面前於金色火焰中,活成一個婀娜女人的身影。這展現了孫頻寫作的格局,弱者超脫自身的苦難,衝出自己的地獄,以渡眾人,甚而面對現代性或是文明開發的侵襲,她以肉身啟蒙世人的種種寓意。
而弱者超越自身苦難用以渡人的主題,同樣於〈九渡〉中得以觀之。較諸〈乩身〉,〈九渡〉的敘述形式和語氣皆舒緩許多,〈九渡〉的男主角王澤強是被父母遺棄的私生子,從小被祖母拉拔長大,祖母臨死前,將十歲的王澤強託付給村中古怪孤僻的小學老師劉晉芳,王澤強經歷劉晉芳兩次自殺未遂的過程,體認到自我生滅的孤寂感,十六歲因為心儀女生曾小麗被學校小混混王兵糾纏,因而砍殺王兵,背著殺人未遂的罪名度過八年的苦牢,在苦牢中支撐他活著的動力,來自於母親劉晉芳的一月一信。〈九渡〉中劉晉芳和王澤強都先後成為他人生命的擺渡人,對生命絕望的劉晉芳在死後,交託摯友以信件「擺渡」王澤強,以度過監獄失去時間感的苦行;王澤強出獄後選擇手刃殘廢乖戾的王兵,以解救曾小麗受困於王兵拖磨的無望人生,王澤強雖過不了他在監獄中的「第九渡」,人生的長河,由此岸到彼岸,終結自己無限苦難的生命,以開啟他人新生的契機,才是理解何謂真正的苦難,以及理解何謂苦難後的救贖。
〈月亮之血〉是透過血的意象,闡釋出尹家人三代掙扎求生的故事,天地儘管不仁,眾生自有活路。尹家第一代父親尹太東,為了孩子,走上賣血之路,因此罹患愛滋病,在眾人歧視眼光中猥瑣至死;哥哥尹來川為了妹妹,自願退學,出外掙錢養家,也換來陰暗的過往與殘疾的身軀,並體現出變形環境對純良人性的扭曲。妹妹尹來燕為了父親的病體,以肉體與雜貨店老闆易物,生下尹東流此一罪孽的孩子。孫頻如此刻畫尹東流,是與尹太東血肉相連的孩子,她一部分的血是父親的血,尹家三代人也是各自殘缺生命下所相互啃食而造就的「血肉之軀」,如同孫頻所言,死去廢掉的親人一如養料,「她們其實不過都是從他們的軀體的廢墟長出來的植物」。
嗜血而生,血後重生,以自己的血肉之軀餵養他人,再換回再無罪孽的潔淨之軀,重要的是,它開啟他人僅存的一條卑微活路。這樣象徵的新生╱重生,也是孫頻在文學中特地保留給這世上人們安養生息的一線生機,並護持人們往生的方向前去。
目次
序 生之慾,愛之慾 王鈺婷(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不速之客
乩身
自由故
九渡
月亮之血
後記 寫作中的生
附錄 孫頻創作年表
書摘/試閱
一
大約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又是三聲敲門聲從天而降。羞怯,篤定。敲在門上像落進了一只空桶裡,那回音一落進去就迅速破土而出,直長得蓊鬱妖嬈,陰森森得爬滿了整間房子。
蘇小軍扯開被角翻身坐起,緊張惱怒地盯著那扇門。三聲敲門聲無聲無息地落下去了,空氣裡出現了一段短暫的空白,然而,這空白倒像是一只緊閉的櫃子立在他面前,有裝滿了敲門聲的嫌疑,似乎只要他一打開,它們就會立刻占領他的整個房間。一定又是那個女人。他下床,光著腳輕輕走了幾步,無聲地把燈關掉了。然後,他赤著腳戳在黑暗中,靜靜地等待著。果然,一分鐘之後,又是三聲同樣質地的敲門聲響起。篤。篤。篤。蘇小軍站在原地一動不動,他從最下面的門縫裡窺到了樓道裡一線昏暗的燈光和那個正守在門前的影子,那影子也一動不動,像是本來就長在他門口的一株植物。他希望它能走開,可是,它因了黑暗和絕望的澆灌反而長得更葳蕤了。它簡直要在他家門口繁衍出一片森林來。
又是幾秒鐘的空白,門外的影子不動,門裡的蘇小軍也不動。雖然身體沒動,蘇小軍卻覺得他整個人都被一口氣提起來了,正懸在空中。他等待著一秒鐘之後再次拔地而起的敲門聲,果然,又是三聲敲門聲。只是比剛才煩躁了些,急促了些,似乎是果子成熟,急於要落到地上來。蘇小軍發現自己居然還是一動沒有動。在那一瞬間,他都有點驚訝於自己的殘忍了,他居然能在九聲敲門聲後還待在屋子裡裝死,只是為了不讓門外這個女人知道他在裡面。
屋裡的這團黑暗比外面的夜色更加堅硬,盔甲一樣裹著他,讓他聞到了一種生鐵的冷硬,還有一縷細若游絲的血腥味。他有些恐懼,但這恐懼裡還夾雜著一種奇異的快樂。他看著自己的那雙手,在黑暗中,它們看起來面目模糊,安詳殘忍。
就在這時候,他的手機忽然響了,該死,他忘記關機了。就在他撲到床頭要摁住活蹦亂跳的手機音樂時,門外的人已經聽到了。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傾巢而出向那扇門砸過來,這樣再砸下去所有的鄰居都會被砸醒,大家披著睡衣揉著眼睛出來看熱鬧,說不來還會有人報警。他知道,如果今天不開門,她會一直砸門砸到天亮。這個可怕的女人。他扔下手機走過去,開了門。屋裡還黑著燈,猛一開門,他有些不適應樓道裡的燈光,然後他瞇著眼睛看到了燈光夾裹著的那個女人,她身上披著一輪光暈。果然是紀米萍。她敲第一聲門的時候他就知道是她了。
除了她還有誰會在深夜裡死不罷休地敲他的門。
他站在那扇門裡,像個邪惡的門童一樣守護著背後滿滿一屋子的黑暗。借著黑暗的庇護他仔細地打量著她,她頭髮散亂,眼角淚痕未乾,就著灰塵和成了兩粒黑色的眼屎,肩上又背著那只鼓鼓的黑色大挎包。肯定又是坐火車長途跋涉過來的,和以往每次都沒什麼不同。她終於敲開了門,卻不敢與他對視,彷彿他是坐在教室裡的威嚴的老師,而她是犯了錯誤的學生。她歪著一隻肩膀,那只包可能太重了,扯著她的肩膀,露出了一只黑色的胸罩帶,她也不打算把它收進去。她歪著肩膀低著頭站在他面前,一縷油膩的頭髮垂下來遮住了她的眼睛。
這已經不知道是第幾次了,每次都這樣,她事先連個招呼都不打就跑過來找他,坐七八個小時的火車,如果買不到坐票,她就一路站到太原來找他。然後,她就站在他門口一遍一遍開始敲他的門,如果他真的不在,她就在他家附近找個最便宜的小旅店住下來,幾天幾夜安營扎寨專職等他。以至於他每次一走到樓下就有一種踩上了蜘蛛網的恐懼感,似乎這蛛網是專門為他布下的。他要是不撞到這網上來都有點對不起她了。
他陰沉沉地立在那裡不說話,她也不動,以固定的姿勢垂著眼睛,只讓自己躲在那縷油膩頭髮的門簾後。那只大包正從她肩膀上往下滑,每滑一次便把她的衣服往下扯一點,彷彿地下有什麼神祕的力量正把那只包連那隻胳膊拉向深淵。她不抗拒。漸漸地,她的整個肩膀都露出來了,她上身偏胖,肩膀本有些肥膩,又箍著那根黑色的胸罩帶,倒也有幾分蕭條的肉欲。她似乎是在以此刻意提醒他,衣服下面,這衣服的下面還有別的,好比超市的貨架,你要用什麼隨時可以來拿。他盯著那肩膀心裡一酸,嘆了口氣,往後退了一步,說了聲,進來吧。
她像剛剛被赦免的犯人一樣,誠惶誠恐地跟著他進了屋,關上門他順手開了燈。黑暗中轟然炸出一片雪亮,像座剛剛浮出來的島嶼,她仍然不敢放下那只大包,拖著它站在島上等候發落。他像個觀眾一樣又看了她幾秒鐘,然後又嘆了口氣說,把包放下吧,你也不嫌累。她得了指令便怯怯地把包放在牆角,似乎那桌子上是收費的。頭依然垂著,他看到她那隻扯衣角的手在習慣性地抽搐著,他知道她一緊張就這樣,一隻手放在腿上抽搐的時候就像她正在練習彈鋼琴。她怕他看見了,忙使勁往下拽衣角。他假裝沒看見,只說,快去洗把臉吧,這都幾點了。
她終於抬起臉來看了他一眼,她看上去並不痛苦,準確地說,她的五官都像泡在某種溶液中一樣,呈現出一種誇張的休眠狀態,似乎它們是某種海底生物,可以幾千年地蟄伏著不動。
紀米萍從包裡取出自己的毛巾,然後借著臉上那縷頭髮的掩護向衛生間走去,好像這樣護著自己,他就暫時不會看到她了。他看著她的背影,她走得很慢,佝僂著背,抱著自己肥碩的毛巾,整個人看起來忽然變得很小很小。她進了衛生間,把門關上了。蘇小軍再次倒在床上,他腦子裡一遍又一遍地想,這個女人,這個可怕的女人,簡直好像隨身攜帶著棺材一樣,好像隨時準備著一死,好像她壓根就不打算活長久。真是比他還要亡命徒,他最多被人雇來做臨時打手討討債,出出氣,殺人的事還從來沒幹過。他簡直不是她的對手。
過了一會,紀米萍從衛生間出來了,蘇小軍感覺她慢慢走到床前了,她似乎從自己的包裡又掏出了什麼,她站在床邊低聲對他說,這是給你買的衣服。他並沒往她身上看一眼,她每次不找招呼跑過來的時候都會給他一件東西,衣服,圍巾,襪子,沒有什麼牌子也看不出價格,和她身上的衣服如出一轍。他從來不會穿,但也無法阻止她。他皺著眉頭說,先關掉燈睡覺吧。她聽話地關掉燈,整間屋子咣噹一聲再次掉進了黑暗的箱底,在他們掉進箱底的一瞬間,那種恐懼在黑暗中忽然再次甦醒了,好像它本來就蹲在河流的上游,現在隨時會隨著黑暗順流而下,流到他們面前。他只覺得黑暗的空氣裡全是她,站滿了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她,她們像千佛洞裡的佛像一樣向他擠壓過來。
就在這時,被子被掀開一角,她無聲地爬進了他的被子裡。在這張床上她睡過不是一次兩次了,她很熟稔地躺在他身邊,把半張被子蓋在了自己身上。她身上冰涼滑膩,還掛著水珠,像一尾剛剛撈上岸的魚。她躺在那裡慢慢蠕動著,好像要在這床上給自己刨出一個坑來,在這個過程中她和他有幾處短暫的肢體接觸,這些接觸很細小很輕微,小心翼翼的,好像從她身上長出了無數氣根一樣的小手,這些小手試探著觸摸著他,見無處生根便又自己縮回去了。他靜靜躺著不動,好像已經睡著了。她終於停止了蠕動,也靜靜地躺在那裡,他感覺到她把臉側到了一邊,好像在黑暗中都怕他會看到她的臉。兩個人像兩具屍體一樣並列在床上。
不知過了多久,他嘆了口氣,終於伸出了一隻手,這隻手準確無誤地放在了她的一只乳房上。她上身是光的,他繼續往下摸,她全身都是光的。在上床之前她就把自己脫光了,像是要祭獻給他的一盤肉。他仍然是那個姿勢,懶懶地躺著,那隻手從她上面摸到下面,又從下面摸到上面。在這緩慢的撫摸中她開始了低低的抽泣,他每摸她一次,她的抽泣聲便大一點,似乎是在給他計件付報酬。她的乳房肥碩鬆軟,一躺下來便流得到處都是,他慢慢摸著那只乳房,像是要耐心地把它們都收集起來,收好了像雪人一樣堆成一堆,他慢慢摸到中央,她變得冰涼而堅硬。與此同時她忽然便大聲抽泣起來,這驟然響起的哭聲在黑暗中聽起來鮮豔凜冽,像塊剛揭了皮的傷口。他下意識地把手抽出來,像是怕不小心碰到了這鮮紅的皮肉。她的哭聲像玻璃碎片一樣四處碾著他,在這張床上他幾乎沒有容身之地了。
他知道他再沒有別的辦法可對付她。黑暗中,就著這裂帛似的哭聲,他鞭策自己一躍而起,趴在了她身上,他像給汽車加油似地又使勁揉了她兩把乳房,下面好歹硬了,可以發動了。可是他進不去,她下面太乾了,乾到了銅牆鐵壁,連絲縫隙都沒有。她沒有聲息了,在屢次實驗中他的臉碰到了她的臉,他感到她無聲地躺在那裡卻是在比剛才更汹湧地流淚,她的整張臉都是濕的,她在那無邊無際地流淚、流淚。他把手放在她的眼睛上,想把那淚水堵回去,可是他的那隻手很快就被淹沒了,淚水從他指縫間湧出來。他簡直像趴在一眼泉上汲水。
他像被大雨澆透一樣再沒了心情,可是他剛要從她身上下去又被她死死抱住了,她一邊抽噎一邊啞著嗓子乞求,和我做一次,就一次,好嗎?她一邊乞求一邊流淚一邊揉搓著他下面,他也快流淚了,但是他知道他現在唯一該做的就是進去,進去了才是對她的安慰,好像只要他一進去她就可以把他整個人都霸占住了。她才不會這麼恐慌,這麼神經質。
為了接納他,她幾乎攤開了身上的每一個毛孔,似乎要給他一道永久免費的通行證,他什麼時候想進去就可以進去。可是,他還是進不去,她那該死的眼淚還在不停地決堤不停地淹沒他。他隨手打開檯燈,幾乎要求她了,求求你不要再哭了行嗎?燈光下他看到她兩隻眼睛已經哭得紅腫,眼淚鼻涕糊了她一臉,脖子裡也全是淚,再往下是那兩只四處流淌不成形的大乳房。她使勁嗯了一聲,伸手撕了一塊衛生紙狠狠擦了擦鼻子,眼睛,然後,她腫著兩隻通紅的眼睛,大義凜然地對他說,我不哭了,來吧。好像她是屠宰場上那隻洗乾淨的牲畜,就等著他一刀子下來了。
他也急於想進去,不是他多想要,而是,他知道,若不進去今晚便沒完。可是他軟了硬硬了又軟還是徒勞,果然,她的淚又出來了,她又一次無聲地流淚,兩道淚水在她臉上閃閃發光,像兩把利刃對準了他。他不想再看,又伸手把檯燈關了。她在黑暗中抽噎著說,你吻我一下好嗎?你都不吻我。就一下……你知道的,你不吻我,我是不行的……就一下,讓我知道你還是愛我的。他沒有說話,嘴唇也沒有向她的嘴唇伸過來。她忽然再次大聲抽泣起來,你明明知道,你都知道,你就是不肯吻我一下,吻一下就那麼難嗎。
我知道什麼?
你撒謊,你知道的,從第一天起你就知道,不接吻我根本不能做愛,我不是妓女,我得接吻,你不吻我的時候你根本就進不去。你早知道的,你從一開始就知道。
你和其他人不接吻又不是沒做過。
她歇斯底裡地哭號起來,那不算那根本就不算,那是做愛,那就不是愛。愛一個人就是要接吻的。
那你不照樣也做了。
…………
她不再說什麼,只是把自己攤在黑暗中歪著頭無聲流淚,他的手碰到枕頭,那裡已經濕了一大片。他的眼睛一陣酸澀,淚差點也下來了。這個女人啊。他使勁掰過她的臉,終於對著那張濕漉漉黏糊糊的臉吻了下去。在他的嘴唇觸到她的臉的一瞬間裡,她把自己整個人都送了上去,忙不迭的,唯恐過時不候的。在找到他的嘴唇之後,她貪婪地吮吸著,恨不得把他整個人都吸進去,嚥下去。她嘴裡滿是濃烈的牙膏味,好像刷個牙便擠掉了半管牙膏。他知道,為了迎接他,她恨不得把自己身體裡的每個角落都打掃乾淨。這牙膏味像鞭子一樣抽在他身上,使他忽然便生出了很多蠻力,他一使勁,總算進去了。這次的任務好歹是完成了。他知道,只要進去了,哪怕只有一分鐘,她對他也會感激涕零。
她痛苦地叫了一聲,然後便更緊地抱住了他,她緊緊緊緊地抱著他,好像生怕他會消失了,會忽然跑了。他在這馥鬱濃烈的擁抱中幾乎動不了,就像身上馱著一個人試圖要飛起來一樣,兩具沉重的肉身壓著他拖著他,只三分鐘就結束了。他趴在她身上想對她說一句對不起。卻發現她還是那麼緊那麼不顧死活地抱著他,他開始感到一陣強烈的恐懼,他知道她又要說什麼了。可是晚了,他根本攔不住她,她抽噎著在他耳邊斷斷續續說了三個字,謝謝你。他憤怒著,抓狂著,想大吼一聲,不說這句話會死人嗎?他沒吼出來,淚卻下來了。他趴著不動,靜等著那兩滴淚水自己風乾。
兩個人又恢復了原來的姿勢,像兩具屍體一樣平躺在黑暗中。她的身體在黑暗中悄悄蔓延,試圖向他偎依過來,他便坐起來,點了一支菸,靠在床頭上一明一滅。他抽了兩口菸之後還是開口了,這次你打算待幾天。
她慌忙說,我不會待久的,就和你待兩天,待兩天我就走。她急切地強調只要兩天,似乎兩天是不算數的,是可以被忽略的。
你那邊也不扣你工資?
我請假了,反正也不忙。
你怎麼老是招呼都不打一個就跑過來了?我和你說過多少次了?
誰讓你不理我了。
你跑過來又怎樣?你覺得有用嗎?我早和你說過了,不要再來找我,找我也沒有用的。
你真的不愛我了嗎?
是的。
……你撒謊,我不信,你心裡對我還是有感情的,我能感覺到。
我原來是喜歡過你,可是現在真的耗光了。你這樣每跑來一次我對你的厭惡就多一點,現在我已經很怕看到你了,你知不知道?
……我不信……我不信……你剛才還吻我的。我知道,不愛是不能接吻的,我和其他人都不接吻的,就只和你一個人接吻……
夠了。你和別人又不是沒睡過,睡都睡了,還一定要裝做根本沒接過吻,從來沒有和人接過吻,這有意思嗎?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