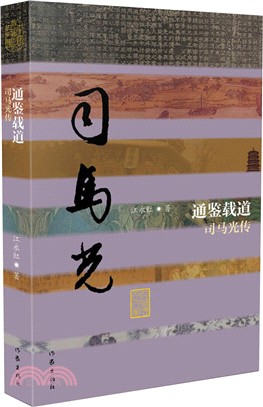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歷史上的司馬光不僅是一位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的歷史學家。本書以詳實的歷史資料和客觀的視角,用生動幽默的文學語言為讀者再現了一個立體的司馬光的形象。
作者簡介
江永紅,1947年生,湖北天門人,解放軍報原副總編輯,高級記者,中國作協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曾獲“中國新聞獎”、范長江新聞獎”?、“全國報告文學作品獎”。出版有《藍軍司令》《中國師》《名將解甲》《王猛》《誰毀了大明王朝》《灰霾1950:新中國大剿匪秘密檔案》(上、下部)等著作14部。
名人/編輯推薦
前言?我的司馬光 在歷史的天空中,閃耀著無數顆璀璨的文化。儒學如孔、孟,楚辭如屈、宋,唐詩如李、杜,宋詞如蘇、辛……星列河漢,看得見,數不清。他們的地位由自己的杰出貢獻而奠定,此固然也,但給其作傳,為其揚名者,史家也。史筆恰似運載火箭,把衛星發射升空。沒有《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我們將永遠無法讀懂《離騷》;沒有《三國志》,我們就只知道戲臺上的曹操…… 史學家在為他人定位時,也把自己安放在歷史的經緯度內。史學界歷來有“兩司馬”之說,即《史記》的作者司馬遷,《資治通鑒》的主編司馬光。他們是中國史海之旗艦,史林之巨擘。司馬遷開紀傳體史書之先河,成正史編撰之圭臬,其后之《二十四史》無不遵之;司馬光登編年體史書之**(發端于《左傳》),引發了編年體的寫作熱,后繼者不乏其人,可惜只有望塵之憾。對“兩司馬”,許多人即使沒有讀過《史記》,至少也知道司馬遷;而對后者,大多數人只知道“司馬光砸缸”,至于他的《資治通鑒》,大抵沒有走出學者的書齋,一些大官大款的書架上也擺著,附庸風雅而已。司馬光先生,對不住了!現在是商品經濟時代,互聯網時代,快餐文化時代,沒時間讀您的大書了。況且,您的書能幫我賺錢嗎?聽到這些,老先生一定會一臉茫然。你對他有多么茫然,他對你就有多么茫然。 不錯。司馬光時代已遠去九個多世紀,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語了。要認識他,需要有人介紹。寫作本書,就是想為介紹司馬光盡綿薄之力。在本書動筆前,我曾到山西夏縣司馬光墓園憑吊。與一些熱門旅游景點人頭攢動、嘈雜喧囂的情形不同,這里安靜得讓人仿佛一下變成了聾子。園外的停車場上,只有送我來的一輛車,園中的訪客只有我和陪同我的一個人。我問工作人員,一直這樣嗎?答曰:放長假時人不少。國家投資重修了司馬光墓園,意在傳承歷史文化,發展人文旅游,卻門前冷落車馬稀,咋啦?轉念一想,倘使一個人連司馬光是誰都不知道,他會“到此一游”嗎?他也許寧愿去尋訪所謂西門慶與潘金蓮的幽會處,津津有味地聽導游帶咸味的瞎掰,興奮地發出哧哧的傻笑,然后一步三回頭地離開。我頓時感到,介紹司馬光的責任好沉好沉…… 《資治通鑒》是司馬光進入中國百位歷史文化名人殿堂的入場券。這部長達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萬字的史學巨著,自北宋元豐七年(1084)修成,至今已印行七十余版,且形成了專門的通鑒學。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讀之入迷,一生通讀達十七遍之多,乃至書頁殘破,且在書中留下不少批語。他曾多次向干部推薦這部書,對書中的史實更是能隨手拈來為自己的觀點服務。在與歷史學家吳晗談話時,他說:“《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汲取經驗教訓。” 《資治通鑒》的主題思想(“天子之職莫大于禮”)與毛澤東思想格格不入,可毛澤東卻說它寫得好,理由是“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一語中的,內行。我們知道,紀傳體史書的優長在于寫人,但要弄清某一事件的本末,須將多人的紀、傳以及表、志反復對照,且因紀、傳中往往時間概念模糊,屢有相互矛盾之處,要捋清一件事談何容易,此其所短。而紀傳體之短正是編年體史書之長,它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來龍去脈,一清二楚,但其短處是人物不如紀傳體完整。從三家分晉至北宋開國前(前403—959)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歷史,紀傳體的正史約有三千余萬字,而《資治通鑒》用三百余萬字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如此精煉,故事完整曲折,人物栩栩如生,難怪毛澤東要贊揚了。濃縮不易,在濃縮中增加信息量更是難能可貴。在《資治通鑒》中,南北朝部分新資料占十分之一,唐以后新資料占到一半,因此它絕非正史的改寫版,而是再創作。據通鑒學者統計,除正史以外,司馬光所參閱的野史、碑帖、家譜之類超過三百種以上,達三千余萬字。而被他引用的書籍,今天大多已亡失。如此旁紹遠求,細大不遺,卻考證精當,前所未有。司馬光是孔子的忠實信徒,而在修史上背棄了孔子“為尊者隱”的《春秋》筆法,對暴君、昏君秉筆直書,對明君如唐太宗的批評也直言不諱。總而言之,《資治通鑒》是一部文字*精煉、史料*豐富、考證*準確、敘事*生動的編年體通史。雖然以帝王為讀者對象,但普通人也值得一讀。為啥?它能讓我們從歷史經驗中領悟上自國家興替,下至為人處世的大智慧。大智慧是管小智慧的,沒有大智慧的人終難擺脫浮躁與淺薄。 寫司馬光,自然要寫他編撰《資治通鑒》的故事,但他不僅是史學家,還是政治家、思想家。如果不了解政治家、思想家司馬光,就讀不懂史學家司馬光,甚至讀不懂他的《資治通鑒》,特別是其中的史論——“臣光曰”。史書固然是寫歷史,但即使*嚴謹、*客觀的史書,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治史者所處時代的或隱或顯的印記。《資治通鑒》的絕大部分撰于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1068—1085),這是一個風云變幻的年代,是變法與反變法生死較量的時期,而王安石和司馬光分別是變法派和保守派這兩個對立營壘的旗手。他倆從能在一起洗澡、能互相調侃的老朋友變成了無事不對立的老冤家,分別主導了王安石變法和清算變法的元祐更化這兩大歷史事件。司馬光的后半生就是與王安石斗爭的后半生,他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的主要活動就是與王安石做斗爭。他倆死斗到死,斗到死后,功過是非,爭論至今。 他倆都是北宋知識分子的精英。司馬光考進士列甲科第六名,王安石禮部試**(準狀元),只因宋仁宗反感其試卷中有“孺子其朋”四字,降到第四名。他們都飽讀詩書,才華橫溢,少年得志,名聲顯赫,而生活簡樸,私德高尚得近乎圣潔。僅舉一例,他們的夫人都曾給他們買過妾,但都被果斷拒絕,這在大官妻妾成群的宋代,恐怕神仙也難以做到。他們的性格一樣的倔強,一個人稱“司馬牛”,一個被指“拗相公”。 按現在的說法,他們都是干部子弟,司馬光是“官三代”,因父親司馬池官居四品(天章閣待制),可以靠“拼爹”恩蔭當官,但恩蔭的官因無功名(進士),被人鄙視,所以司馬光與許多有志氣的干部子弟一樣,在恩蔭得官后又參加了科舉考試。王安石是“官二代”,父親王益官銜只是從六品(都官員外郎),不夠五品以上恩蔭子弟的杠,他沒法“拼爹”,要當官只能靠科舉。在宋代,官員五品和六品雖只差一品,但六品是低級官員,著綠袍,五品是中級官員,著緋袍。這是關鍵的一級,升為五品標志著進入了特權階層的行列。因此,司馬光和王安石入仕前的生活環境包括家庭的社交圈是大不一樣的。入仕后,他們的基層任職履歷也差別較大。司馬光只代理了幾天縣令,追隨龐籍做過州通判,而王安石當知縣政績突出,不僅做過州通判,而且做過提點刑獄,對下情的了解更多。 司馬光是北方人,任職基本在北方;王安石是南方人,入朝前任職一直在南方。宋朝士大夫中的南北矛盾由來已久。因趙氏皇帝起家于北方,加上有視中原政權為正統、而視南方割據政權為僭偽的傳統觀念,所以北宋官僚集團中北方人占優勢,而且在南方人面前有一種征服者的優越感。科舉考試中,南北方的錄取標準區別很大。太宗時,開始是認分不認人,但中第者大多為南方人。北方河北、河東等五路(太宗時全國分十八路)幾乎推了光頭,舉子因而敲登聞鼓請愿。太宗于是以北方拙于詞令為由,令北五路單獨再考,后來雖不另設考場,但把錄取指標劃撥到北五路。如此優待的結果是北五路的錄取標準越來越低。熙寧三年(1070),也就是司馬光的養子司馬康以明經科登第的那年,神宗在殿試中看到第四甲黨镈的卷子文句不通,不禁大笑說,這樣的人是怎么通過的?考官答曰:五路人按分數取末名通過。五路有專用指標,管你合格不合格,錄夠指標為止。神宗也不便取消指標,只好將其降到第五甲。這個對北方的優惠政策一直實行到北宋滅亡。南北方的賦稅標準也不一樣,宋初為穩固竊取來的政權,大幅度減免后周規定的賦稅,三畝按一畝征收,而新征服的南方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按原割據政權的標準收稅,實際上是南北兩制,南方推后甚至沒有享受到減賦的恩惠。故北方的大地主多,南方的中小地主多。這些對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立場、觀點不可能沒有影響。 宋朝可以說是精英治國的朝代,知識分子的地位之高****。趙宋的皇冠強取于后周的孤兒寡母之手,為防止他人仿效,同時鑒于五代實行武人政治,致使兵連禍結的慘痛教訓,趙匡胤通過杯酒釋兵權、文臣知州事等舉措,確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公開宣布“與士大夫治天下”,而且規定了不殺讀書人和言事者的祖訓。宋朝大興科舉,不問門第貧富,考取即授官。從太宗趙光義開始,錄取率是唐代的數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宰相須用讀書人”(太祖語),歷任宰相都是進士甲科出身。這是一個破天荒的歷史性進步。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和優養,使歷數千載的華夏文化,“造極于趙宋之世”(陳寅恪語),涌現了燦若星河的思想家、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唐宋八大家,六個在北宋,且與司馬光同時代。與他同時代的還有被稱為道學“北宋五子”的思想家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教育家胡瑗,科學家畢升、沈括,詩詞名家更是難以數計,總之是人文薈萃,濟濟焉,浩瀚焉。從太宗趙光義開始,歷任皇帝幾乎都是書法家,有的還是詩人、音樂家、畫家,文臣與皇帝唱和詩詞,交流藝術,歌舞升平,其樂融融。 然而,重文抑武在帶來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的同時,卻讓宋朝患了軟骨病。自趙光義收復幽州遭高粱河(今北京市內)之敗后,宋便一蹶不振,再無國威軍威可言。真宗趙恒畏敵如虎,在軍事占主動的情況下與遼國簽訂了“澶淵盟誓”,每年對遼國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慶歷二年九月,又增歲賜銀十萬兩,絹十萬匹,合計五十萬),不久后宋仁宗又承認了由節度使獨立的西夏的國家地位,丟失大片土地,“歲賜”銀、茶、絹二十五萬五千(兩、斤、匹)。開始,士大夫除少數佞臣外,普遍都有恥辱感,但隨著真宗偽造天書、東封泰山、西祀后土、大興宮觀的鬧劇開演后,士大夫從中得到了茍安的“紅利”,許多人就反過來為花錢買平安制造理論根據了。時間一長,身在恥中不知恥,形成了一種茍安文化。士大夫在歌舞升平中揮麈清談,盡情享受。但遼國哼一聲,宋就發抖;西夏一挑釁,宋就慌神。可惜危機一過,又復茍安。 茍安文化的基礎是茍安的物質利益。真宗寫《勸學詩》,公開以“黃金屋”、“千鐘粟”、“顏如玉”來誘人讀書。讀書——當官——發財,是皇上指引的陽關大道。官員特別是高官的俸祿、賞賜優厚。宋代不禁止土地兼并,官員余錢主要投資田產,所以大地主幾乎可以與大官畫等號,即便本人不是大官,其父輩、祖輩必有大官。對他們來說,這樣的日子太好了,要什么改革?要什么收復失地?到仁宗時,宋朝建國已近百年,沉疴在身,積重難返,*突出的問題是“三冗”:冗官、冗費、冗兵。“三冗”使國家財政捉襟見肘,寅吃卯糧,國家窮,平民窮,而大官僚地主富得流油。面對危機,范仲淹曾主持“慶歷新政”,改革首先從冗官開刀,僅此一舉,就激起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抗。仁宗妥協了,新政如曇花一現,剛剛起步便無疾而終。司馬光和王安石就是在這期間高中進士,走上政治舞臺的。 脫離了這幅北宋風俗畫,就讀不懂士大夫階層,也就讀不懂司馬光和王安石。 他倆都以天下為己任,面對宋廷這個“病人”,都堅信自己是**的“醫生”,堅信只有按自己開的“藥方”才能挽救朝廷。但兩人開出的“藥方”正好相反。 王安石要變法。南宋朱熹說:“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程顥)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熙寧變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王安石)所變更者,東坡(蘇軾)亦欲為之。及見荊公做得紛擾狼狽,卻去攻他。”當時改革是大勢所趨,王安石是一顆*耀眼的政治、學術新星,不只是程顥、蘇軾,包括后來成為保守派中堅的呂公著、韓維等人開始也是支持變法的,但改革就意味著利益的調整,就會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拼死反抗,這一點王安石早有犧牲的思想準備,其他人卻沒有這個準備。而王安石的新法確實有些超前,如青苗法用金融借貸扶持貧窮農戶,市易法用金融借貸扶持中小商戶,這些都帶有資本主義性質(黃仁宇語),把俗儒們驚得目瞪口呆,但他們很快就發現,王安石是要抑制大地主、大商人的兼并。于是乎,原來擁護變法的也倒向保守派,加入反變法的行列。他們聯合宗室、后黨向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施加壓力,神宗讓步了,變法派分裂了,王安石*后被外放金陵賦閑,但新法大多堅持下來。 按王安石的說法,“始終言新法不便者,司馬光一人也”。不可否認,司馬光是既得利益集團中的一員,但他不是那種靠兼并而富甲一方的豪強地主,而是一個學者。正因為此,他被保守派推到了旗手的地位。他固然是在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更是一個禮治的殉道者。他似乎是一個天生的反對派,變法前,他對社會弊端的抨擊比王安石還要激烈,因為現實不符合他禮治理想;而變法開始后,他反對變法又比誰都積極,因為變法與他的禮治理想背道而馳。禮治的核心是等級制。與許多所謂純儒一樣,他企圖在維持原有利益格局不變的前提下,靠皇帝和朝臣的道德示范和用君子、貶小人,達到等級有序、上下相安的太平盛世。他打著禮治的大旗,不經意間卻為兼并辯護。所以王安石寫《兼并》詩說:“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在王安石變法時,他拒絕了神宗任以執政大臣的“收買”,辭掉了樞密副使這個士大夫夢寐以求的職務,*后到洛陽完成了他的《資治通鑒》。神宗逝世,高太后垂簾。奉高太后之召,他一手高舉著反變法的旗幟,一手緊握著禮治之劍,殺氣騰騰地回朝執政。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一年多時間就閃電似的廢掉了新法。可惜,他的禮治之劍已銹跡斑斑,本人已病入膏肓,廢新法廢成了一鍋“夾生飯”。 “”中“評法批儒”,司馬光被作為儒家,王安石被作為法家,硬是把他們納入儒法斗爭的軌道。其實,他們都是儒家,其分歧不在儒法,而在對儒家經典的不同界定和解讀,在如何發展儒學才能使之適應社會需要。王安石崇孟(子),司馬光《疑孟》崇揚(雄);司馬光注古本《孝經》,王安石處處質疑。王安石吸收諸子百家的合理成分,完成了“荊公新學”,成為北宋之宋學中**的學派,而司馬光則成為“道學六先生”之一。他們的學術論戰不僅與變法反變法的實踐相始終,而且先于其前,延于其后,乃至于今。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逝于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晚走四個多月。從表面上看,王安石死在失敗的挽歌聲中,司馬光死在勝利的凱歌聲中,其實他們都是在憂愁中帶著遺憾走的。王安石之憾自不待言,司馬光何憂?“元祐更化”前途未卜也。他們沒有一個是贏家,給我們留下兩個殉道者的故事,留下一場沒有演完的時代悲劇。他倆逝世后僅四十年,北宋滅亡了。 對中晚期的北宋來說,不敢說改革就一定能復興,而不改革則注定要滅亡,對改革進行反攻倒算必然加速其滅亡。 本書不是**本寫司馬光的書,力求寫出一個真實的我的司馬光,而避免重復他人的司馬光。 我的司馬光是北宋特殊政治、文化氛圍中的司馬光。比如,常有人說,宋代士大夫*有氣節。不錯,但可別忘了,那是因為有“不殺讀書人和言事者”的政策兜底。司馬光以氣節名世,屢與皇帝當面斗氣、頂牛,若非北宋,不可想象。他是北宋社會風俗畫的一部分,只有在這幅畫中他才是“真”的“活”的。 我的司馬光是一個以帝師為己任的司馬光。“國之治亂,盡在人君”,是他政治觀的核心,本著“責君嚴”和君臣相反相成、以成皇極的為臣之道,他幾乎總是在“責君”。他官歷四朝,仁宗、英宗、神宗,他都“責”了,唯有哲宗小皇帝和垂簾聽政的高太后例外(恰恰是哲宗親政后否了他的“元祐更化”)。即使在與王安石的搏殺中,也重在勸諫神宗。至于《資治通鑒》則事事著眼于教育皇帝。因此,他即使在著書立說時,也始終處于社會矛盾的沖突之中。 我的司馬光是俯視下的司馬光。好比一座雕像,仰視只能看到正面而看不到反面,只能看到表面而看不到里面。雕像是經過藝術處理的,有人仰視后自己也當開了化妝師和整容師,于是一個“高、大、全”的司馬光出現在神壇上,而真實的司馬光遠去了。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對歷史人物哪怕是明君賢臣也始終是俯視,而且手里拿著一把解剖刀。我寫他,當然首先要向他學習。 因此,我的司馬光,是一位的**歷史學家,一位私德高尚、獻身禮治理想的保守思想家,一位鞠躬盡瘁但不及格的政治家(更確切地說,是不及格的宰相)。這也許會讓某些人感到不快,但觀點可以爭論,事實沒法改變。司馬光逝世后,有人對其高足劉安世說:“三代以下,宰相學術,司馬文正一人而已。”劉安世回答說:“學術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圖回四海者,未敢以為**。蓋元祐大臣類豐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馬公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諫大夫執法殿中,勸講經帷,用則矣。’”事實上,當宰相是司馬光人生悲劇的高潮,不僅是因為“廉于才智”吧? 宋代營造了知識分子的“天堂”,而升入“天堂”的人們卻親手毀掉了這座“天堂”。不亦悲乎!
書摘/試閱
章金榜题名时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三月。首都东京(又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春风抚摸着汴河两岸的隋朝柳,摸出一片翠绿,柳枝软绵绵、娇滴滴、懒洋洋地卖弄着它的婀娜,远远望去,如烟如幻。河湖之畔,城墙内外,草色青青,百花竞放。碧桃红,红得妖;玉兰白,白得娇;连翘黄,黄得俏……各路花仙张开笑脸,敞开心扉,在向你招手;鸟儿双双,在空中追逐,在林间呢喃。喜鹊筑新巢,燕子衔新泥。开封的“市民(坊郭户)”有游春之俗,或坐车坐轿,或骑马骑驴,或安步当车,一团团,一伙伙,涌出城门,涌向郊外,投入春的怀抱。大自然的春天令人陶醉,但这一年,还有另一个春天更令人神往。文人的春天本年是大宋王朝的科考之年,来自全国的数千名举子,此时已经过了礼部试,千余名通过者的名单新鲜出炉。虽然他们还只是准进士,但只要再过一关,即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廷试),就正式成为进士了。在唐朝、五代和北宋初年,殿试尚未成为定例,礼部试一榜定乾坤,因此,进士把主考官目为座师,官僚中也容易形成以座师为中心的小集团。有鉴于此,宋太祖从开宝五年(972)开始恢复殿试,目的是以此证明进士乃“天子门生”,而非座师学生也。宋代科举分三级:为发解试(相当于明、清之乡试),在各州或太学举行;录取者“发解”赴京参加礼部试(又称省试,相当于明清的会试);录取者后参加殿试。殿试只考“策”一道,除太祖曾淘汰过两人外,以后再没有一人被淘汰,但皇帝多半会找一个理由将礼部试的头名(省元)降等。总之,状元是要由皇帝钦点的。本年是宋朝建国第七十八年,本届科考是第三十九届,是仁宗(赵祯)朝的第五次开科。我们的主人公司马光就在这批准进士之中。他二十岁,陕州(今山西夏县)人,今年首次参加科考。与他同时录取的还有范镇、石扬休、庞之道、吴充、孟翔等人。在礼部试与殿试之间,有近一个月的间隔。这段间隔正是游春赏景的大好时光,准进士们岂能放过!种种原因让司马光、庞之道、范镇和石扬休等凑在一起,到哪里去玩呢?原后周宗室柴宗庆诗曰:“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却梁园总是村。”梁园是开封之代指(另指商丘),意思是与开封相比,其他地方再繁华也是村庄。《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则用“花阵酒池,香山药海”来形容其市井之繁华。当时开封已有“十厢一百二十坊”(厢、坊为行政单位,约分别相当于今之区和街道),常住人口超过一百万,是中国和世界大的城市,有的是好玩的去处。全城有八大瓦子,在瓦子里,可以召妓陪酒,欣赏“百戏”。宋代妓女有官妓(营妓)、民妓(私妓)之分。民妓档次较低,俗称“猱儿”(猴子名),只可骑驴而不可乘马、坐轿;官妓即“女伎”,是在官府注册了“乐籍”的歌舞演员,俗称“弟子”。“弟子”只为官府服务,但举子们只要发一个邀请函(“仰弟子某某到某处祗直本斋燕集”)就可随叫随到。因文人地位高,靓女傍文人恰似今之傍大款。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弟子”的要价之高,连宰相寇准的爱妾蒨桃也为之咋舌,作诗云:“一曲轻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所以,不掂量口袋里的银子,是不敢给“弟子”发请柬的。状元楼下的朱雀门至保康门一溜都是秦楼楚馆,一般的举子会去那里找“猱儿”。“猱儿”虽然价格便宜,但颇善解人意,很会看客唱曲,自从礼部之后,一阕《鹧鸪天》成为当家节目。词曰:五百人中仙,等闲平步上青天。绿袍乍著君恩重,黄榜初开御墨鲜。龙作马,玉为鞭。花如罗绮柳如绵。时人莫讶登科早,自是嫦娥爱少年。成何体统?司马光对一些举子的放浪形骸而感到脸红。他在笔记《涑水记闻》中批评此年科考“举子多不如仪”。“不如仪”就是不讲规矩,除举子行为不端外,还有跨州“发解”(类似今之高考移民)的,有非举子硬闯考场的。大相国寺也是文人常去的地方。此寺规模宏大,仁宗时有六十四院。去那里可参禅拜佛,可在幽静的单间品茶饮酒,还可逛全国大的文化市场。新书出版先在此上市。寺东“荣六郎印书馆”印书质量上乘,深受文士喜爱。但这里更像老北京的天桥,花鸟虫鱼,卖唱卖艺,卜卦算命,坑蒙拐骗,各色俱全,尤以小偷名冠天下。仁宗曹皇后来寺进香,刚上台阶,挂在脖子上的一串念珠竟不翼而飞。此物价值千缗,仁宗闻讯大怒,将皇后的随行人员全部抓捕,终未能破案。相国寺虽然好玩,但举子们考前去求过神,考上后去谢过神,不必再去了。眼看早发的红杏已开始凋零,落英纷纷,春光不等人,而殿试一过,大家就要各奔东西,这可是大家在一起的后一个阳春。司马光等人决定去郊外踏青,登古吹台。赏春古吹台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