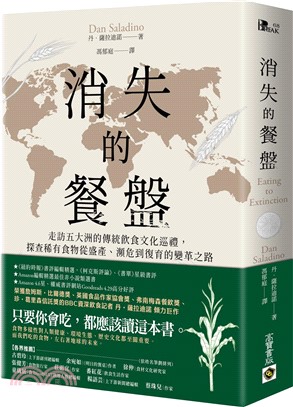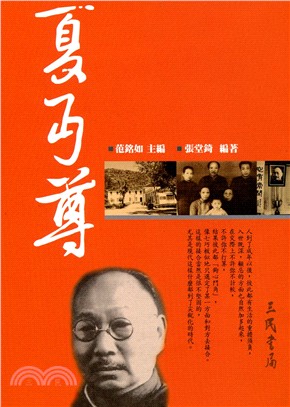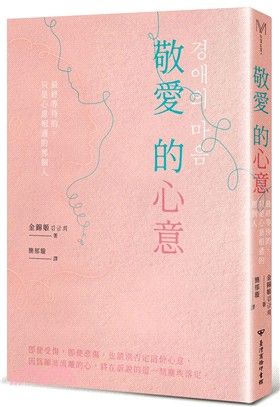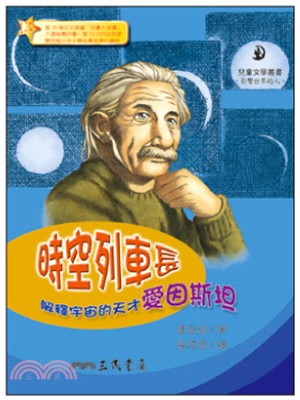定 價:NT$ 1800 元
優惠價:90 折 1620 元
領券後再享88折
領
團購優惠券B
8本以上且滿1500元
再享89折,單本省下178元
再享89折,單本省下178元
領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可得紅利積點:48 點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若經學與儒學以人性善道為本,那從詩人所見,亦為人個體生命所致力人性之美。詩是平實的,故較思想更真。中國傳統純然立於「文」此一人性向度,詩就在這樣向度下為存在及人最懿美之體現。詩人對世界存在美麗的傳述,使人見人(詩人)與存在仍有之懿美可能。這樣的美麗,往往只在生命點滴間浮現,為詩以簡約與單純直接方式捕捉。生命片刻微漸之美麗、世界本然平凡之真實,構成詩人心懷之感動與懿美,及詩所有最高境界。--譚家哲
作者簡介
【譚家哲】
作者少年就讀香港華仁中學,在耶穌會會士鮑善能神父指導下,對哲學有所嚮往。大學期間曾受業於牟宗三先生,並於1976年以榮譽甲等成績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1979年碩士學位後,放棄德國學術交流總署獎學金,改赴法國巴黎深造。1982年獲巴黎第一大學哲學研究所現代思想體系史部哲學史博士,年僅二十八歲。
留法期間師事Jean Deprun與Julia Kristeva教授,並從學於Levinas, Maurice de Gandillac, Vernant, Levi-Strauss, Roland Barthes, Foucault, Derrida, Serres, Boulez等學者。作者多年隱居授業,以文本微細分析為志,盡力於東西方思想之根源與價值重訂,亦曾任教於東海大學哲學系。著有《形上史論》、《論語與中國思想研究》、《孟子平解》、《論語平解選篇》。
作者少年就讀香港華仁中學,在耶穌會會士鮑善能神父指導下,對哲學有所嚮往。大學期間曾受業於牟宗三先生,並於1976年以榮譽甲等成績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1979年碩士學位後,放棄德國學術交流總署獎學金,改赴法國巴黎深造。1982年獲巴黎第一大學哲學研究所現代思想體系史部哲學史博士,年僅二十八歲。
留法期間師事Jean Deprun與Julia Kristeva教授,並從學於Levinas, Maurice de Gandillac, Vernant, Levi-Strauss, Roland Barthes, Foucault, Derrida, Serres, Boulez等學者。作者多年隱居授業,以文本微細分析為志,盡力於東西方思想之根源與價值重訂,亦曾任教於東海大學哲學系。著有《形上史論》、《論語與中國思想研究》、《孟子平解》、《論語平解選篇》。
序
(……)
在正文中論詩學一章雖已把詩與哲學對比地討論,但在這裡仍想就此作點補充,作為對詩之序言。
若撇開所謂使用價值,人類從存在言所有價值,始終不外真善美三者。而在三者中,人一般所重視的,先是真。無論透過知識或對事實其所謂客觀性之重視,背後都只是一種真之向度;特別當「真」所涉往往為事物世界本身。無論是否單純出於利益關係,人類都幾近只把心力放置於對物世界之開發上,因而就算對價值多麼不以為然,真始終永遠保有其獨特地位。就算世俗不重視或明白哲學之所以然,但作為真理之代言,哲學於歷史中仍至高無上。但我漸漸感到,事情不應這樣。
作為真雖統攝著一切,然若從人類作為人言,善與美始應是更高價值。這兩種價值,一從人必有所行動作為言,另一則因人確有對外在事物之感受,兩者都從人自身方面,非如真往往只從事物這另一方面言。正因存在先為人類存在,而我們也只是作為人而活在世上,故縱然是真,都仍應先立於美與善上;若非從美善而言真,真無以為真。一方面,若人類自身不真(美與善),其他一切事物、事情之真實性頓時失去意義,甚至失去真實性,行動與作為者只在人故。人類作為若虛妄,只使事物之真變為偽而已。另一方面,就算單純從事物方面言,真若只為事實性或客觀性,無論多真,都非為價值或有真實意義。人類存在先在其向往,非在事實;而使人類有所向往,若非美與善,再無其他可能。就算眼前世間再無美善,對人類美善之向往,這始終仍為唯一真實;捨此而求其他向往,如求超越性或現實性等,終仍虛妄而已。事實上,真本只事物之是其所是,只是事實,非價值。善雖為價值,但因非可有可無地必然,故往往再不從向往言。能從向往言者,故唯美而已。構成人類存在意義之終極,只在美這一價值向度上。當然,若連善也闕如時,人類必先求善道而非美;甚至,若連事物也變得虛假不實,人必自然以真實者為價值。但這些都只不得已而已,非人類存在終極與充足意義所在,唯美始是。當然,作為終極意義,美必須亦盡善,並以存在整體為背景,如「里仁為美」那樣,否則若只為一孤立事物之美,是無以為存在意義者。人類存在之意義、一切事物之意義,亦美與善兩者而已,再無其他。意義與美善故為同義語;無美無善,直與虛無無意義等同;甚至,若非美與善,作為必終毫無價值。因而相關人類存在言若唯美與善始為價值,那真之能為價值,除非這時之真體現出美與善,否則是無以為真理而只落為事實。
若我們從這角度反觀哲學,古代哲學始終仍以善與美為至真實者所有,無論是理形抑上帝均如是,唯這時之美與善,因對象非在眼前又為超越世間,故只能虛說,非能實指、實見。這只有美善之名而無其實,是日後美善作為價值顯得虛妄之根本原因:人都以此為過於理想,不以之為能真實。但若不從使美善落為虛偽這方面言,這些表面以美善為價值之哲學思想,單純從其所立理論本身言,實多非由於善。如我們所說,美與善二者只能相對人而言,非能從其自身或單純從事物本身言,故一理論能為善,仍只能因相關於人而有。舉例說,如馬克思,縱使表面只為對資本主義世界之批判,因而顯得單純負面,然這批判因仍為人之存在,故仍見其善。又如盧梭,雖把人性限定在一種感受性上,未能以人為有更高向度,從這點言作為人之道理雖不足,然其對人感受之重視,視之為人性與人道所在,並明白文明不能漠視或不顧人此感受性,從這點言,其思想仍善。至於尼采,雖然深惡人性中卑微性格,以此為對事實中人性之批評,然從其終為人之能更高尚,不為虛假形式制限而更能自由,縱使有錯或有過,但因所關懷仍是人,故仍有善意。相反,如康德表面上對人性有所敬重,然一旦以人只為理性存有,非作為人(人性之人)言,因而只知以理性自律、或以法律般性格為德性之本,如此對人之所謂敬意,並非善。黑格爾之精神及柏拉圖之理性更如是。甚至如當代海德格爾,只以人為彰顯存有之「此在」,只為在世中之存在者,非如萊維納斯,真切對人性存有向度有所關懷並分析,像海德格爾這樣思想,故未見絲毫善意。從這角度言,哲學思想可分為兩類:一仍以人之美、
善為最終價值; 二非是,故必以其他以為更真之超越者或超越性為對象與價值,如存有、理形、神、主體、精神甚至潛意識等;因若非為超越者,是無以如價值般為人所追慕。但若從與人美善有關這方面言,單純從超越性言之真,始終毫無價值,甚至顯得只是虛構。哲學傳統這(虛構的)超越性,故常為當代哲學所解構。以為藉超越性而為價值,這只虛妄而已。一方面這與人類美善之真正價值無關,另一方面往往因以為超越,故反對人類及人性有所壓抑與低貶,使真與偽者(人與超越體)顛倒,甚至使人類因對超越者盲目追求而流為自我奴化,都與人其美善之建立背道而馳,毫無助益而有害。尼采深明這樣西方真理傳統其終必為虛無主義,使一切價值最終全然崩壞。其本正在超越性及相對如此超越性時、不自由之人性事實上,二者都非真實。但對我們而言,二者正由於移離真實人性價值始如此,非人性存在必為虛無。
哲學思想之超越性,除否定一切人性價值與真實性外,作為真理,因再無人性真實性作為參照,只能從虛構而建立。哲學及思想之推論性格,實虛構藉以建立時之過程而已。哲學這虛構性,可從以下兩方面明白:一、對象之虛構性:一切非眼前人與物之對象,如存有、神、理形、實體、以致超驗主體、絕對精神等,均全然為虛構。二、從思想本身或從方法方面言,除如辯証法等明顯為虛構外,連笛卡爾對簡單體之直觀與演繹、柏拉圖之辯証、康德之超驗分析、甚至當今德里達之解構,均全然為虛構。如解構之所以仍為虛構, 因由於被解構為超越者,而超越者又正是超越地涵蓋一切,故解構也只能相對一切而解構,不能有所例外,亦不再容許絲毫肯定,恐重為超越性所滲透。如是一切價值、語言概念、存在者都為解構視為超越,無一例外,無一事一物能在超越性或解構之外。如是解構已使自身轉化為一種超越方法,亦使一切對象轉化為超越者,故一方面任誰都為解構所駕馭、分析,但另一方面任誰都為超越者,再無例外。解構如是實已絕對化超越性本身,既不見人性與道之平實,所見全然為超越者而已。對我們而言,除非單純回歸平視及正視事物,否則無以真正遠去超越性。中國中庸之道在此。
從這對哲學及真理簡略反省可見,在人世存在中,唯一能真實者,亦為人而已,不能有其他。而人之真實,亦在其美與善而已,再無其他。人類存在中之價值,故亦為美與善兩者,更無其他。似以人為絕對,這亦由於我們自身只是人而已;但縱使如此,我們仍從無以人為超越者。甚至,以人性為本而發展之一切,都非超越者,此中國思想或道所在。並非因而說人已或必為美善,正好相反:由於人非超越者,故非必為美善。對人美善之致力,故為一種向往,唯一人性之向往,亦唯一正確而真實的向往。而人所以偉大,亦由於懷著這樣向往致力而已,致力於人性真實世界而已。若非如此,若非懷抱著人類美善之真實而致力,此時所以為之其他善,如一理性、正義、民主法治之社會,若非相關人性本身美善言,縱使能成一秩序化存在,仍不能視為成就人自身美善之正道。
所謂人性,應從兩方面言:一為人心,另一為人實然之存在有限性;一內一外。正因從存在事實人為有限,如必有父母、有對人之思念、有期盼人與人之和睦、情感與敬重、甚至有對異性之情愛等等,故人性非一超越之真實性,作為本性既有其內在(心)亦有其外在事實(如人倫關係),「性」是從這內外關係而言的。關係越是內在或內化,越見人之美與善;人性善是從此而言。性善故非只指行為上之善而已,更是人性內外一致而具體之體現(如和睦、敬重、雅正,甚至儉簡等)。性本善故是相關於人存有這內在真實性與外在有限性而言者。正因有此外在一面,故亦不為人所能任意,如能不孝或不以禮行。人性故是人內外一體之存有樣態,從人外在存在之有限性及從有他人等事實性而言的。人性是在外在必然性與內在美善真實性之間,既非單純事實,亦非有其超越性可能,如無視人倫實然有限性時超越之自我個體或「我思」主體。人故非能單純從自由而言,非由有國家或社會之約制,而更先因有人倫而已。人性是從人倫這本然限制而言者。又因如是人性之存有事實,故任誰超越性均無以能對人言為超越;而人自身亦只能順隨這內在美善價值及外在人性事實而立,亦無以圖索神聖而否定自身人性之可能。人性這內外存有事實,對人而言故為必然,不能為超越者所替代、取代。人真實而平實之有限性在此,故非如死亡只是存在事實上之有限性那樣。人性故非超越之事,亦不能超越地觀。置於天地間,人性故是一種以人美善為本之樣態、一種人存在美善之模態;亦對人世言唯一真實之樣態。
當人以人性為惡時,這單純只能從事實言,只為存在事實,一種最外在事實,非從人本身言。甚至,對人視作性惡而否定時,實只是對人存在模態之否定,試圖代之以其他模態而已。若存在非人類之存在,這亦無不可。但若存在只是或先是人類之存在,那存在只能以人性模態與方式為道,不能再以其他仍能為美善者。任何其他方式,無論自身多美善,相關於人,只能為惡,亦只致人為奴役,因違逆其人性事實故。相反,若從人性為本向外推廣,是可及存在整體而仍人性地美善者。以人性為善抑為惡,故除了與人之倬立或其行為之善惡有關外,直是存在整體樣態或模態之事。人性善抑性惡,同即存在為人性存在抑為超越存在這樣的差異;甚至,即以存在為為人之存在抑非為人之存在這樣的差異;故孟子稱性惡論為賊害人者,非只是與非問題而已。人類面對自身及面對存在,因而也只有二可能,一正一非:或順承人性而存在,或另求超越或他者以塑造存在。人性善抑性惡,其最終義在此。
今人因已在超越存在氛圍下,故只知懷著現實,極求自我膨脹,毫不以價值為重,只圖索種種外在表面利益,或權力與物質之佔有,置人類與世界於貧乏與無識;從一己之所是重複著人性本惡,於人與人間只求自我權利,或以為公平正義即人道義之全部,甚或以其名而爭鬥,追求著虛假的自由民主,以這為充份人性存在所繫,鞏固著上位者對高位無道之霸佔,首肯著法制對人之壓迫;又或以為一切價值只為時代與現實所定斷,順承著貴賤及強弱之勢利心衡量真偽及能與無能,以為思想浮泛之新穎與多彩多姿即真理所在,不知思想之正道應先回歸人身上,並應致力對人性之建立。類如這樣想法及存在姿態,既空乏如無知幼稚,亦實重複地虛構虛無,無法有絲毫價值或真實感。每見人對人性有所貶抑、或重複著現實之所是而以為存在只能如此、心中除利益外再無所向往、使存在及人類自身越形狹隘及渺小,如此種種,往往使我感到厭煩,只覺其人毫不認真思想與反省,亦未見對價值有所向往,都只視現實只為現實,以個己最大利益為生命全部所是,再不見人性與道義,或有為人付出與德性之致力。
對人性美善之致力,因而應為人類生命之全部。無論從那一存在層面言均如此。若人能靜下心來擺開個己,是應明白種種新穎、新奇都只浮光掠影而已,不如人性平實真實。人性及其美善對人作為人言始終根本。當然,我們今日似最不以美善為真理,無論因害怕其限制,或以事實之名而否認其存在。對如後者,事實可能如此;但正因如此,自己之所是,就也正在:仍有對人美善之向往並致力,抑一己只如現實般自我盲目自視而已,問題都非先在他人而在自己。人類非超越之存有者,也只人而已;雖可事實地無美善,但始終仍應是懷著對人美善之期盼的,人性亦在此而已。而對前者,美善並沒有對人努力作規限;相反,人以為對反美善而作為時,所成就只表面及非價值而已。如古代詩人所體現,作為美善始終仍可無窮。非美善對人有所限制,反而助人更能真實地偉大。若擺開現實利害之心,擺開思想與技術現代性之假像,是不難見古代真正之懿美的。從真正價值言,唯美與善為唯一真實,亦有無限可能。人類單憑思想之創意,對深識者言,終也只重複地貧乏而已,非確為創新。故如美,仍必須嚴格言是真實及單純地美,甚至為人存在深邃之美,不能以藝術概念之名或炫目般之技術以為能越過人性對美直觀之感受,及由對懿美之體會而有所啟發。美學故確只是對美之明白,但更是對人類存在中懿美之體會,非其他種種以為之概念與立論,分散人對美真正之感見。同樣,善應直從人言,單純回歸人自身、及人對人之善言,非從社會公德或對環境關注等外在境況言。無論似多大效益,都只忽略善真實之究竟而已。
若中國經學與儒學所言為人性此根本善道,那從詩人所見,亦人作為個體生命時所致力人性之美而已。思想仍可只由於自我、仍可只超越地虛構,但詩只能是平實的,只能是對眼前世界之美言。超越性正因為超越,故既不善亦再無美之可能。從這點言,詩故較哲學與思想更真,既發自人心自己,亦向往著美與善之真實。此二者,亦詩之全部存有,及其所以懿美。若從人作為人這根本性言,文學故非只文學,實真理本身。若中國傳統純然立於「文」這人性向度,那詩亦就在這樣向度下,為存在及人最懿美心懷之體現,亦個體可有最高存在與真實。在概念與世界所有美麗兩者間,最終使我感動而視為生存意義,仍只後者而已。詩人對世界存在美麗的傳述,使人見人(詩人)與存在仍有之懿美可能。這樣的美麗,往往只在生命點滴中浮現,故最能真實地傳述,也只為如詩之簡約,其他如小說般散文長篇,已有構造,亦遠去美呈現時之單純直接,詩文體之必然簡約,源起於此:以至單純真實之方式捕捉生命片刻中微漸之美麗,極力保存世界美麗本然單純平凡之面貌,及詩人自身亦有之心懷感動與懿美,再無絲毫思想造作。此詩與美必然簡約及詩所以至為真實之原因。
(……)
在正文中論詩學一章雖已把詩與哲學對比地討論,但在這裡仍想就此作點補充,作為對詩之序言。
若撇開所謂使用價值,人類從存在言所有價值,始終不外真善美三者。而在三者中,人一般所重視的,先是真。無論透過知識或對事實其所謂客觀性之重視,背後都只是一種真之向度;特別當「真」所涉往往為事物世界本身。無論是否單純出於利益關係,人類都幾近只把心力放置於對物世界之開發上,因而就算對價值多麼不以為然,真始終永遠保有其獨特地位。就算世俗不重視或明白哲學之所以然,但作為真理之代言,哲學於歷史中仍至高無上。但我漸漸感到,事情不應這樣。
作為真雖統攝著一切,然若從人類作為人言,善與美始應是更高價值。這兩種價值,一從人必有所行動作為言,另一則因人確有對外在事物之感受,兩者都從人自身方面,非如真往往只從事物這另一方面言。正因存在先為人類存在,而我們也只是作為人而活在世上,故縱然是真,都仍應先立於美與善上;若非從美善而言真,真無以為真。一方面,若人類自身不真(美與善),其他一切事物、事情之真實性頓時失去意義,甚至失去真實性,行動與作為者只在人故。人類作為若虛妄,只使事物之真變為偽而已。另一方面,就算單純從事物方面言,真若只為事實性或客觀性,無論多真,都非為價值或有真實意義。人類存在先在其向往,非在事實;而使人類有所向往,若非美與善,再無其他可能。就算眼前世間再無美善,對人類美善之向往,這始終仍為唯一真實;捨此而求其他向往,如求超越性或現實性等,終仍虛妄而已。事實上,真本只事物之是其所是,只是事實,非價值。善雖為價值,但因非可有可無地必然,故往往再不從向往言。能從向往言者,故唯美而已。構成人類存在意義之終極,只在美這一價值向度上。當然,若連善也闕如時,人類必先求善道而非美;甚至,若連事物也變得虛假不實,人必自然以真實者為價值。但這些都只不得已而已,非人類存在終極與充足意義所在,唯美始是。當然,作為終極意義,美必須亦盡善,並以存在整體為背景,如「里仁為美」那樣,否則若只為一孤立事物之美,是無以為存在意義者。人類存在之意義、一切事物之意義,亦美與善兩者而已,再無其他。意義與美善故為同義語;無美無善,直與虛無無意義等同;甚至,若非美與善,作為必終毫無價值。因而相關人類存在言若唯美與善始為價值,那真之能為價值,除非這時之真體現出美與善,否則是無以為真理而只落為事實。
若我們從這角度反觀哲學,古代哲學始終仍以善與美為至真實者所有,無論是理形抑上帝均如是,唯這時之美與善,因對象非在眼前又為超越世間,故只能虛說,非能實指、實見。這只有美善之名而無其實,是日後美善作為價值顯得虛妄之根本原因:人都以此為過於理想,不以之為能真實。但若不從使美善落為虛偽這方面言,這些表面以美善為價值之哲學思想,單純從其所立理論本身言,實多非由於善。如我們所說,美與善二者只能相對人而言,非能從其自身或單純從事物本身言,故一理論能為善,仍只能因相關於人而有。舉例說,如馬克思,縱使表面只為對資本主義世界之批判,因而顯得單純負面,然這批判因仍為人之存在,故仍見其善。又如盧梭,雖把人性限定在一種感受性上,未能以人為有更高向度,從這點言作為人之道理雖不足,然其對人感受之重視,視之為人性與人道所在,並明白文明不能漠視或不顧人此感受性,從這點言,其思想仍善。至於尼采,雖然深惡人性中卑微性格,以此為對事實中人性之批評,然從其終為人之能更高尚,不為虛假形式制限而更能自由,縱使有錯或有過,但因所關懷仍是人,故仍有善意。相反,如康德表面上對人性有所敬重,然一旦以人只為理性存有,非作為人(人性之人)言,因而只知以理性自律、或以法律般性格為德性之本,如此對人之所謂敬意,並非善。黑格爾之精神及柏拉圖之理性更如是。甚至如當代海德格爾,只以人為彰顯存有之「此在」,只為在世中之存在者,非如萊維納斯,真切對人性存有向度有所關懷並分析,像海德格爾這樣思想,故未見絲毫善意。從這角度言,哲學思想可分為兩類:一仍以人之美、
善為最終價值; 二非是,故必以其他以為更真之超越者或超越性為對象與價值,如存有、理形、神、主體、精神甚至潛意識等;因若非為超越者,是無以如價值般為人所追慕。但若從與人美善有關這方面言,單純從超越性言之真,始終毫無價值,甚至顯得只是虛構。哲學傳統這(虛構的)超越性,故常為當代哲學所解構。以為藉超越性而為價值,這只虛妄而已。一方面這與人類美善之真正價值無關,另一方面往往因以為超越,故反對人類及人性有所壓抑與低貶,使真與偽者(人與超越體)顛倒,甚至使人類因對超越者盲目追求而流為自我奴化,都與人其美善之建立背道而馳,毫無助益而有害。尼采深明這樣西方真理傳統其終必為虛無主義,使一切價值最終全然崩壞。其本正在超越性及相對如此超越性時、不自由之人性事實上,二者都非真實。但對我們而言,二者正由於移離真實人性價值始如此,非人性存在必為虛無。
哲學思想之超越性,除否定一切人性價值與真實性外,作為真理,因再無人性真實性作為參照,只能從虛構而建立。哲學及思想之推論性格,實虛構藉以建立時之過程而已。哲學這虛構性,可從以下兩方面明白:一、對象之虛構性:一切非眼前人與物之對象,如存有、神、理形、實體、以致超驗主體、絕對精神等,均全然為虛構。二、從思想本身或從方法方面言,除如辯証法等明顯為虛構外,連笛卡爾對簡單體之直觀與演繹、柏拉圖之辯証、康德之超驗分析、甚至當今德里達之解構,均全然為虛構。如解構之所以仍為虛構, 因由於被解構為超越者,而超越者又正是超越地涵蓋一切,故解構也只能相對一切而解構,不能有所例外,亦不再容許絲毫肯定,恐重為超越性所滲透。如是一切價值、語言概念、存在者都為解構視為超越,無一例外,無一事一物能在超越性或解構之外。如是解構已使自身轉化為一種超越方法,亦使一切對象轉化為超越者,故一方面任誰都為解構所駕馭、分析,但另一方面任誰都為超越者,再無例外。解構如是實已絕對化超越性本身,既不見人性與道之平實,所見全然為超越者而已。對我們而言,除非單純回歸平視及正視事物,否則無以真正遠去超越性。中國中庸之道在此。
從這對哲學及真理簡略反省可見,在人世存在中,唯一能真實者,亦為人而已,不能有其他。而人之真實,亦在其美與善而已,再無其他。人類存在中之價值,故亦為美與善兩者,更無其他。似以人為絕對,這亦由於我們自身只是人而已;但縱使如此,我們仍從無以人為超越者。甚至,以人性為本而發展之一切,都非超越者,此中國思想或道所在。並非因而說人已或必為美善,正好相反:由於人非超越者,故非必為美善。對人美善之致力,故為一種向往,唯一人性之向往,亦唯一正確而真實的向往。而人所以偉大,亦由於懷著這樣向往致力而已,致力於人性真實世界而已。若非如此,若非懷抱著人類美善之真實而致力,此時所以為之其他善,如一理性、正義、民主法治之社會,若非相關人性本身美善言,縱使能成一秩序化存在,仍不能視為成就人自身美善之正道。
所謂人性,應從兩方面言:一為人心,另一為人實然之存在有限性;一內一外。正因從存在事實人為有限,如必有父母、有對人之思念、有期盼人與人之和睦、情感與敬重、甚至有對異性之情愛等等,故人性非一超越之真實性,作為本性既有其內在(心)亦有其外在事實(如人倫關係),「性」是從這內外關係而言的。關係越是內在或內化,越見人之美與善;人性善是從此而言。性善故非只指行為上之善而已,更是人性內外一致而具體之體現(如和睦、敬重、雅正,甚至儉簡等)。性本善故是相關於人存有這內在真實性與外在有限性而言者。正因有此外在一面,故亦不為人所能任意,如能不孝或不以禮行。人性故是人內外一體之存有樣態,從人外在存在之有限性及從有他人等事實性而言的。人性是在外在必然性與內在美善真實性之間,既非單純事實,亦非有其超越性可能,如無視人倫實然有限性時超越之自我個體或「我思」主體。人故非能單純從自由而言,非由有國家或社會之約制,而更先因有人倫而已。人性是從人倫這本然限制而言者。又因如是人性之存有事實,故任誰超越性均無以能對人言為超越;而人自身亦只能順隨這內在美善價值及外在人性事實而立,亦無以圖索神聖而否定自身人性之可能。人性這內外存有事實,對人而言故為必然,不能為超越者所替代、取代。人真實而平實之有限性在此,故非如死亡只是存在事實上之有限性那樣。人性故非超越之事,亦不能超越地觀。置於天地間,人性故是一種以人美善為本之樣態、一種人存在美善之模態;亦對人世言唯一真實之樣態。
當人以人性為惡時,這單純只能從事實言,只為存在事實,一種最外在事實,非從人本身言。甚至,對人視作性惡而否定時,實只是對人存在模態之否定,試圖代之以其他模態而已。若存在非人類之存在,這亦無不可。但若存在只是或先是人類之存在,那存在只能以人性模態與方式為道,不能再以其他仍能為美善者。任何其他方式,無論自身多美善,相關於人,只能為惡,亦只致人為奴役,因違逆其人性事實故。相反,若從人性為本向外推廣,是可及存在整體而仍人性地美善者。以人性為善抑為惡,故除了與人之倬立或其行為之善惡有關外,直是存在整體樣態或模態之事。人性善抑性惡,同即存在為人性存在抑為超越存在這樣的差異;甚至,即以存在為為人之存在抑非為人之存在這樣的差異;故孟子稱性惡論為賊害人者,非只是與非問題而已。人類面對自身及面對存在,因而也只有二可能,一正一非:或順承人性而存在,或另求超越或他者以塑造存在。人性善抑性惡,其最終義在此。
今人因已在超越存在氛圍下,故只知懷著現實,極求自我膨脹,毫不以價值為重,只圖索種種外在表面利益,或權力與物質之佔有,置人類與世界於貧乏與無識;從一己之所是重複著人性本惡,於人與人間只求自我權利,或以為公平正義即人道義之全部,甚或以其名而爭鬥,追求著虛假的自由民主,以這為充份人性存在所繫,鞏固著上位者對高位無道之霸佔,首肯著法制對人之壓迫;又或以為一切價值只為時代與現實所定斷,順承著貴賤及強弱之勢利心衡量真偽及能與無能,以為思想浮泛之新穎與多彩多姿即真理所在,不知思想之正道應先回歸人身上,並應致力對人性之建立。類如這樣想法及存在姿態,既空乏如無知幼稚,亦實重複地虛構虛無,無法有絲毫價值或真實感。每見人對人性有所貶抑、或重複著現實之所是而以為存在只能如此、心中除利益外再無所向往、使存在及人類自身越形狹隘及渺小,如此種種,往往使我感到厭煩,只覺其人毫不認真思想與反省,亦未見對價值有所向往,都只視現實只為現實,以個己最大利益為生命全部所是,再不見人性與道義,或有為人付出與德性之致力。
對人性美善之致力,因而應為人類生命之全部。無論從那一存在層面言均如此。若人能靜下心來擺開個己,是應明白種種新穎、新奇都只浮光掠影而已,不如人性平實真實。人性及其美善對人作為人言始終根本。當然,我們今日似最不以美善為真理,無論因害怕其限制,或以事實之名而否認其存在。對如後者,事實可能如此;但正因如此,自己之所是,就也正在:仍有對人美善之向往並致力,抑一己只如現實般自我盲目自視而已,問題都非先在他人而在自己。人類非超越之存有者,也只人而已;雖可事實地無美善,但始終仍應是懷著對人美善之期盼的,人性亦在此而已。而對前者,美善並沒有對人努力作規限;相反,人以為對反美善而作為時,所成就只表面及非價值而已。如古代詩人所體現,作為美善始終仍可無窮。非美善對人有所限制,反而助人更能真實地偉大。若擺開現實利害之心,擺開思想與技術現代性之假像,是不難見古代真正之懿美的。從真正價值言,唯美與善為唯一真實,亦有無限可能。人類單憑思想之創意,對深識者言,終也只重複地貧乏而已,非確為創新。故如美,仍必須嚴格言是真實及單純地美,甚至為人存在深邃之美,不能以藝術概念之名或炫目般之技術以為能越過人性對美直觀之感受,及由對懿美之體會而有所啟發。美學故確只是對美之明白,但更是對人類存在中懿美之體會,非其他種種以為之概念與立論,分散人對美真正之感見。同樣,善應直從人言,單純回歸人自身、及人對人之善言,非從社會公德或對環境關注等外在境況言。無論似多大效益,都只忽略善真實之究竟而已。
若中國經學與儒學所言為人性此根本善道,那從詩人所見,亦人作為個體生命時所致力人性之美而已。思想仍可只由於自我、仍可只超越地虛構,但詩只能是平實的,只能是對眼前世界之美言。超越性正因為超越,故既不善亦再無美之可能。從這點言,詩故較哲學與思想更真,既發自人心自己,亦向往著美與善之真實。此二者,亦詩之全部存有,及其所以懿美。若從人作為人這根本性言,文學故非只文學,實真理本身。若中國傳統純然立於「文」這人性向度,那詩亦就在這樣向度下,為存在及人最懿美心懷之體現,亦個體可有最高存在與真實。在概念與世界所有美麗兩者間,最終使我感動而視為生存意義,仍只後者而已。詩人對世界存在美麗的傳述,使人見人(詩人)與存在仍有之懿美可能。這樣的美麗,往往只在生命點滴中浮現,故最能真實地傳述,也只為如詩之簡約,其他如小說般散文長篇,已有構造,亦遠去美呈現時之單純直接,詩文體之必然簡約,源起於此:以至單純真實之方式捕捉生命片刻中微漸之美麗,極力保存世界美麗本然單純平凡之面貌,及詩人自身亦有之心懷感動與懿美,再無絲毫思想造作。此詩與美必然簡約及詩所以至為真實之原因。
(……)
目次
【卷一】
序論
論表象與文之存在形態
論詩學
〈孔子詩論〉
《文心雕龍》樞紐與文術論
【卷二】
《詩經》
屈原〈九歌〉與〈離騷〉
班固〈兩都賦〉
曹植
陶淵明
謝靈運
【卷三】
王維
杜甫
書摘/試閱
論詩學
本章為對詩學總體論述嘗試。我們先從西方詩學說起。
一、西方詩學回顧一:古典詩學
在美學與詩學兩者間,西方始於詩學而非美學,原因有二:一、自然界之美因順承人本性而明顯,幾近無可討論或解釋。相反,作品之美並不顯然,有待探討與解釋,此美學始於詩學之原因。二、美學作為感性之學,必須有待主體性甚至感性有被建立後始能深入;西方早期多為客體存有論,非主體哲學,故鮮有對美學作為門類討論。
作品問題主要有兩類:一為其構造、構成問題,二更基本,為作品之價值問題。作品之價值與意義問題至為基本,亦一切詩學及美學之根本。我們的討論即參照這一問題進行。
首先仍需從柏拉圖開始。柏拉圖著名詩學論,為對一切詩作品劃分為形式(lexis)與內容(logos)兩方面。因一切詩作品對柏拉圖甚至希臘言均為敘述(récit),為一種表象模式,故其形式主要有三種可能:或為直述(純敘述diègèsis)、或為摹倣(mimèsis)、或為兩者之混合。柏拉圖只肯定直述一模式,而否定另外兩者。在這表象模式三分中,柏拉圖舉以下文體(genre)為例:直述式如酒神頌(dithyrambe)、摹倣式如悲劇及喜劇,而混合式如荷馬史詩。酒神頌今已不存在,內容無從考究,從記錄觀應為對酒神之歌頌。
柏拉圖詩論引發出大問題,是因後來亞里士多德著名《詩學》沒有跟隨這劃分法,而柏拉圖這一劃分法其真正意義亦不為人所知;西方詩學史之後只單純跟隨亞里士多德,沒有再理會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詩學之修改或改變,正在把三種表象模式全收攝在「摹倣」一模式下,因而使一切詩敘述性表象直等同摹倣。無論此時敘述是虛構抑真實,一切作品對亞里士多德言均為摹倣(=表象),這是作品唯一之方式。亞里士多德把柏拉圖三分完全內化於摹倣(表象)一模式下表示:一切作品只從其表象性界定,直述抑戲劇只其模式而已。這一轉變結果嚴重。
首先,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最大差異在是否接納敘述為根本獨立模式,抑只從屬摹倣下。柏拉圖之視敘述為獨立,正因對柏拉圖言唯敘述一模式為真實,摹倣非是。亞里士多德之做法,明顯為反對柏拉圖如此詩學。但若撇開反對不談,柏拉圖劃分法之所以能為亞里士多德所取代,確因在敘述一模式下,柏拉圖所舉例子為酒神頌,而酒神頌因其對象性,縱然非如戲劇般摹倣,然始終仍是表象;因而當亞里士多德把摹倣意思擴大等同表象時,自然可把敘述亦收攝於摹倣下,一切形式始終只是對象性而已,因而為表象,亦為摹倣。
柏拉圖以敘述而不以摹倣為詩文學之本,其洞見本深刻,唯錯誤以酒神頌為例而已。讓我們先從結論說起:
敘述這一模式,實等同「詩言志」中「言」一模態,而這是一切詩學甚至作品創制應視為根本的。柏拉圖之錯誤只因不從「志」言,而舉酒神頌為例。本來舉酒神頌為例仍可,因假若把酒神頌對等《詩》之「頌」,這仍是「言志」;唯若被歌頌者本身為神人二分下之神靈,始使「言志」成份不見,故為亞里士多德視同「表象」:一種基於對象而有之作品,與「志」無關,因而亦無須保留敘述或「言」為獨立模式,致使詩學及一切作品創制均為表象或摹倣,表象亦為詩唯一模式。若明白這點,我們便可看到,中西方詩學之全部差異與關鍵,就源於此而已:中國以「言志」為詩之本,而自亞里士多德詩學,詩全為摹倣或表象。
若我們跳躍至西方浪漫主義詩學,浪漫主義詩學把詩文體三分為悲劇、史詩與歌詩(lyrique)。當代詩學家Gérard Genette指出,無論是柏拉圖抑亞里士多德,從沒有提及歌詩,更沒有把歌詩視為文體模式。希臘時期詩學如柏、亞二人那樣,從不以歌詩為真正作品,不以歌詩為詩,因而從不對歌詩予以討論。亞里士多德《詩學》(或詩)所排掉的,除沒有節奏、旋律、語句構造之散文外,即為歌詩。原因明顯在:歌詩非表象或摹倣故。如是我們可清楚看到,西方在浪漫主義出現前之古典詩學,在亞里士多德影響下,對表象作為詩或作品之根本模式,多麼地看重。
如Genette指出,歌詩之被接受為詩學文體,歷史漫長。在十六、十七世紀前,歌詩都被混同種種非表象性形式;而構成大文體,只有悲劇、史詩甚至喜劇,無歌詩在內。直至1559年意大利Minturno於其De Poeta中,始有把詩分為場景、歌詩及史詩三者。Cervantes後來分為四:史詩、歌詩、悲劇、喜劇。至英國Milton(1644)始有史詩、戲劇、歌詩三分。又如Baumgarten(1735)在其Esthétique有曾提及歌詩、史詩、戲劇及其細分這樣分類,但因從無理論基礎與說明,故這樣劃分法始終無代表性,歌詩始終被視為只是對想法之虛構(fabula構造)。至1746年Batteux始試圖對亞里士多德摹倣論與歌詩兩者在理論上作協調:一如戲劇與史詩中人物均有其感情甚至激情,詩人若有對自身感情之抒發,也應視作對情感之摹倣;在情節進行或行動中即為戲劇與史詩,而在行動中止後,單純對心靈感受之描繪則為歌詩;歌詩因而並沒有違背摹倣這一原則。 如是而歌詩一文體只作為對情感感受之摹倣而呈現或被接納,只是對象內容不同,非形式或手法不同。
於此我們始明白,之所以柏拉圖必須區分敘述與摹倣,及二人之忽略歌詩,其關鍵在詩人是否能直述自身這一事情上:柏拉圖以直述為對神靈讚美故以直述模式為至真,摹倣因非以神靈為對象故必然偽;亞里士多德則以摹倣為表象客觀對象時唯一之方式,縱使虛構仍有其對象真實性在,非如直述自身情感之歌詩,其內容因只為人主觀感受故無真理性;二人始終以對象之客觀真實性甚至真理性為詩唯一可有之依據。
西方這古典詩學既對人心志所有之人性與真實完全否認,始有以詩為外在真實或事實之摹倣。因而全部西方古典詩學之所由起,正為對「詩言志」之否定與對立;其關鍵全在人心是否能有真實,或人自身是否能有真實性而已。
當亞里士多德以摹倣為對「在行動中人」之摹倣,我們不應誤會以為此已涉及人而再非是神靈,並非如此。所謂「在行動中之人」,其關鍵在行動而非人,因而為戲劇(drama)。這行動所對反的,實為「志」或「心」;而其背後所關涉的,只為人之欲望及其想法、智力等之錯誤,始終非人性或其心志之真實。在對人行動作表象時,所表象者均為人之錯誤與過失,只如此錯誤有大小之分而已,一為悲劇,另一為喜劇。正因是對如此重大至為悲劇錯誤之表象,故其中所言之人,乃顯要個體;其作為個體,又為自身性格(èthè)與想法(dianoia)所左右,行動之全部錯誤由此而生。詩學所對之對象,如是由向內而言之人心轉移至向外有所欲求而行動時之個體,以此個體之事實為真實。作為行動,其情節或故事(mythos)必須虛構或構造;正是如此虛構或構造,構成亞里士多德《詩學》之本。於此我們始明白西方詩學其源起之究竟。
本章為對詩學總體論述嘗試。我們先從西方詩學說起。
一、西方詩學回顧一:古典詩學
在美學與詩學兩者間,西方始於詩學而非美學,原因有二:一、自然界之美因順承人本性而明顯,幾近無可討論或解釋。相反,作品之美並不顯然,有待探討與解釋,此美學始於詩學之原因。二、美學作為感性之學,必須有待主體性甚至感性有被建立後始能深入;西方早期多為客體存有論,非主體哲學,故鮮有對美學作為門類討論。
作品問題主要有兩類:一為其構造、構成問題,二更基本,為作品之價值問題。作品之價值與意義問題至為基本,亦一切詩學及美學之根本。我們的討論即參照這一問題進行。
首先仍需從柏拉圖開始。柏拉圖著名詩學論,為對一切詩作品劃分為形式(lexis)與內容(logos)兩方面。因一切詩作品對柏拉圖甚至希臘言均為敘述(récit),為一種表象模式,故其形式主要有三種可能:或為直述(純敘述diègèsis)、或為摹倣(mimèsis)、或為兩者之混合。柏拉圖只肯定直述一模式,而否定另外兩者。在這表象模式三分中,柏拉圖舉以下文體(genre)為例:直述式如酒神頌(dithyrambe)、摹倣式如悲劇及喜劇,而混合式如荷馬史詩。酒神頌今已不存在,內容無從考究,從記錄觀應為對酒神之歌頌。
柏拉圖詩論引發出大問題,是因後來亞里士多德著名《詩學》沒有跟隨這劃分法,而柏拉圖這一劃分法其真正意義亦不為人所知;西方詩學史之後只單純跟隨亞里士多德,沒有再理會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詩學之修改或改變,正在把三種表象模式全收攝在「摹倣」一模式下,因而使一切詩敘述性表象直等同摹倣。無論此時敘述是虛構抑真實,一切作品對亞里士多德言均為摹倣(=表象),這是作品唯一之方式。亞里士多德把柏拉圖三分完全內化於摹倣(表象)一模式下表示:一切作品只從其表象性界定,直述抑戲劇只其模式而已。這一轉變結果嚴重。
首先,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最大差異在是否接納敘述為根本獨立模式,抑只從屬摹倣下。柏拉圖之視敘述為獨立,正因對柏拉圖言唯敘述一模式為真實,摹倣非是。亞里士多德之做法,明顯為反對柏拉圖如此詩學。但若撇開反對不談,柏拉圖劃分法之所以能為亞里士多德所取代,確因在敘述一模式下,柏拉圖所舉例子為酒神頌,而酒神頌因其對象性,縱然非如戲劇般摹倣,然始終仍是表象;因而當亞里士多德把摹倣意思擴大等同表象時,自然可把敘述亦收攝於摹倣下,一切形式始終只是對象性而已,因而為表象,亦為摹倣。
柏拉圖以敘述而不以摹倣為詩文學之本,其洞見本深刻,唯錯誤以酒神頌為例而已。讓我們先從結論說起:
敘述這一模式,實等同「詩言志」中「言」一模態,而這是一切詩學甚至作品創制應視為根本的。柏拉圖之錯誤只因不從「志」言,而舉酒神頌為例。本來舉酒神頌為例仍可,因假若把酒神頌對等《詩》之「頌」,這仍是「言志」;唯若被歌頌者本身為神人二分下之神靈,始使「言志」成份不見,故為亞里士多德視同「表象」:一種基於對象而有之作品,與「志」無關,因而亦無須保留敘述或「言」為獨立模式,致使詩學及一切作品創制均為表象或摹倣,表象亦為詩唯一模式。若明白這點,我們便可看到,中西方詩學之全部差異與關鍵,就源於此而已:中國以「言志」為詩之本,而自亞里士多德詩學,詩全為摹倣或表象。
若我們跳躍至西方浪漫主義詩學,浪漫主義詩學把詩文體三分為悲劇、史詩與歌詩(lyrique)。當代詩學家Gérard Genette指出,無論是柏拉圖抑亞里士多德,從沒有提及歌詩,更沒有把歌詩視為文體模式。希臘時期詩學如柏、亞二人那樣,從不以歌詩為真正作品,不以歌詩為詩,因而從不對歌詩予以討論。亞里士多德《詩學》(或詩)所排掉的,除沒有節奏、旋律、語句構造之散文外,即為歌詩。原因明顯在:歌詩非表象或摹倣故。如是我們可清楚看到,西方在浪漫主義出現前之古典詩學,在亞里士多德影響下,對表象作為詩或作品之根本模式,多麼地看重。
如Genette指出,歌詩之被接受為詩學文體,歷史漫長。在十六、十七世紀前,歌詩都被混同種種非表象性形式;而構成大文體,只有悲劇、史詩甚至喜劇,無歌詩在內。直至1559年意大利Minturno於其De Poeta中,始有把詩分為場景、歌詩及史詩三者。Cervantes後來分為四:史詩、歌詩、悲劇、喜劇。至英國Milton(1644)始有史詩、戲劇、歌詩三分。又如Baumgarten(1735)在其Esthétique有曾提及歌詩、史詩、戲劇及其細分這樣分類,但因從無理論基礎與說明,故這樣劃分法始終無代表性,歌詩始終被視為只是對想法之虛構(fabula構造)。至1746年Batteux始試圖對亞里士多德摹倣論與歌詩兩者在理論上作協調:一如戲劇與史詩中人物均有其感情甚至激情,詩人若有對自身感情之抒發,也應視作對情感之摹倣;在情節進行或行動中即為戲劇與史詩,而在行動中止後,單純對心靈感受之描繪則為歌詩;歌詩因而並沒有違背摹倣這一原則。 如是而歌詩一文體只作為對情感感受之摹倣而呈現或被接納,只是對象內容不同,非形式或手法不同。
於此我們始明白,之所以柏拉圖必須區分敘述與摹倣,及二人之忽略歌詩,其關鍵在詩人是否能直述自身這一事情上:柏拉圖以直述為對神靈讚美故以直述模式為至真,摹倣因非以神靈為對象故必然偽;亞里士多德則以摹倣為表象客觀對象時唯一之方式,縱使虛構仍有其對象真實性在,非如直述自身情感之歌詩,其內容因只為人主觀感受故無真理性;二人始終以對象之客觀真實性甚至真理性為詩唯一可有之依據。
西方這古典詩學既對人心志所有之人性與真實完全否認,始有以詩為外在真實或事實之摹倣。因而全部西方古典詩學之所由起,正為對「詩言志」之否定與對立;其關鍵全在人心是否能有真實,或人自身是否能有真實性而已。
當亞里士多德以摹倣為對「在行動中人」之摹倣,我們不應誤會以為此已涉及人而再非是神靈,並非如此。所謂「在行動中之人」,其關鍵在行動而非人,因而為戲劇(drama)。這行動所對反的,實為「志」或「心」;而其背後所關涉的,只為人之欲望及其想法、智力等之錯誤,始終非人性或其心志之真實。在對人行動作表象時,所表象者均為人之錯誤與過失,只如此錯誤有大小之分而已,一為悲劇,另一為喜劇。正因是對如此重大至為悲劇錯誤之表象,故其中所言之人,乃顯要個體;其作為個體,又為自身性格(èthè)與想法(dianoia)所左右,行動之全部錯誤由此而生。詩學所對之對象,如是由向內而言之人心轉移至向外有所欲求而行動時之個體,以此個體之事實為真實。作為行動,其情節或故事(mythos)必須虛構或構造;正是如此虛構或構造,構成亞里士多德《詩學》之本。於此我們始明白西方詩學其源起之究竟。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