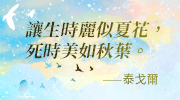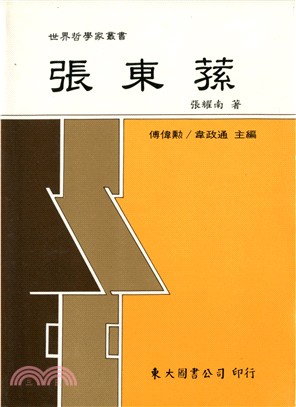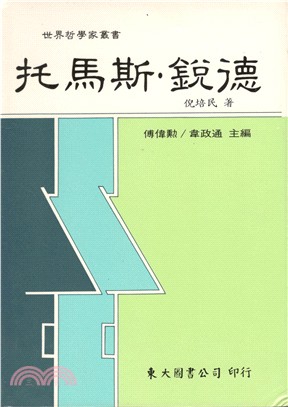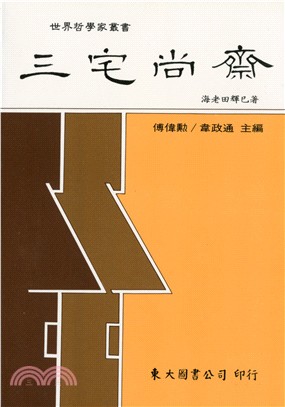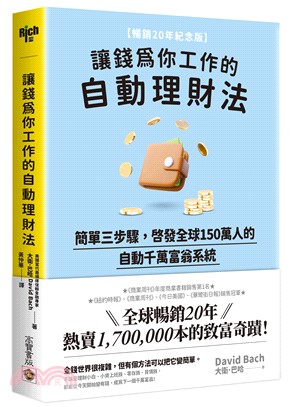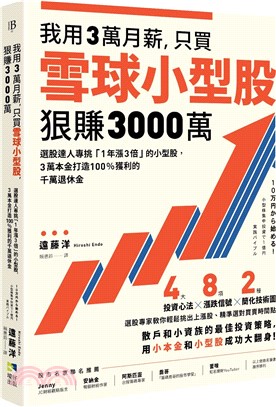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北大老五屆,是指北大理科1960—1965級,文科1961—1965級的學生。這個九千多人的群體,在1968或1970年間被集體發配到基層,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個人命運由此發生重大轉折。本書收錄了北大老五屆學子的61篇回憶文章,來自當年北大18個系中的15個系,講述了這一代北大人在畢業之后不同的人生軌跡,和共同的精神堅守。在逆境中抗爭,在順境中奮發,老五屆學子的獨特行跡,構成了北大百年歷史不可或缺的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編輯推薦:在逆境中抗爭,在順境中奮發,老五屆學子的獨特行跡,構成了北大百年歷史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序
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的,1958年并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60年畢業,被分配到貴州安順的衛生學校任語文教員。這樣,我和本書的作者北大老五屆的同學,就有了一種特殊的關系:據本書的《跋》介紹,老五屆包括‘‘理科1960一1965級,文科196l一1965級”的同學,那么,他(她)們都是在我畢業以后入學的,是我的學弟與學妹;他(她)們又在1968或1970年被發配到了基層,其中就有到貴州的,而我已經在那里生活、丁作了近十年了,在這個意義上,我似乎又是他(她)們的先行者。因此,我讀這本(《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就感到特別親切,不僅引發了許多記憶,還有更多的感慨與感想。
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僅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無意遺忘的歷史,先后對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和1980年北大“校園民主選舉運動”作了專門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時,對北大“文革”前的歷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這次讀到北大老五屆同學的回憶,我才發現了一個重大的遺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屆作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集體下放,他們也書寫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而且如書中一位作者所說,他們在北大1949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的(盧達甫:《老五屆大學生》)。就我的研究范圍而言,他們上承1957年的校園民主運動:不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運動與“五一九運動”有著復雜的關系(這還有待于研究),而且當年的北大右派同學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發配勞改,現在老五屆也以一種“原罪”發配農場和基層改造,盡管彼此處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歷程卻是相通的。而正是因為有了底層的經驗與反思,“文革”結束后回到北大,才會有1980年校園競選運動對中國改革問題的大討論。本書編者說,老五屆的“獨特行跡,是北大百年歷史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這是有充分理由的。盧達甫同學還談到:“我們的歷史學家與文學家、藝術家,似乎都遺忘了老五屆大學生。中國的知青文學鋪天蓋地,老五屆文學幾乎是空白。”(盧達甫:《老五屆大學生》)這確實是歷史研究、文學書寫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課題,這是一段“不可遺忘的歷史”。現在,北大老五屆的同學回憶當年親身經歷,用“自己描寫自己”的方式,開拓了一個新的歷史研究領域,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我們這些歷史研究者,應該是一個啟示與挑戰。我寫本文,也算是一個回應吧。
所謂“不可遺忘的歷史”,在我的理解里,應該有三個層面的意思。
一、不可遺忘的苦難記憶
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在當下中國思想界、學術界,有一種刻意美化“文革”歷史的傾向。有人就宣稱,“文革”是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最輝煌的一頁”,那些苦難都是知識分子虛構與夸大的,即使有苦難,也是推動歷史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有關的知青生活的回憶和文學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來描述那段歷史,過分地強調所謂“青春無悔”。這樣的對歷史血腥氣的著意遮蔽與抹殺,對在“強迫遺忘”的文化、教育環境里長大的中國年輕一代的欺騙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嚴重的。因此,今天,當事人的苦難記憶,說出歷史真相,是具有“拒絕遺忘,抗拒謊言”的現實意義的。
因此,我讀本書,最感驚心動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憶:470名部隊官兵、83名大學生,“十八至二十三歲剛剛踏進社會的稚嫩青年,在當時狂熱高壓的政治氛圍里,為了政治口號而赴湯蹈火”,犧牲了寶貴的生命(白嘉薈:《殤痛牛田洋》);1963年技術物理系的高材生聶永泰,因為被社會所不容,只能到高山雪原尋求心靈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陳煥然:《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淚》);同樣是技術物理系放射化學專業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罰到山西汾西礦務局煤礦當“煤黑子”,而且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被視為“從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心靈折磨比肉體傷害更難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這都是不容掩飾的血淋淋的事實。
問題是,這樣的從肉體到精神上摧殘人的生命,是當時的一個既定方針、政策。老五屆畢業前,有過一場關于分配方針的爭論。有同學提出“分配應該考慮專業對口”的要求,卻被執掌權力的工宣隊斥為“修正主義分配路線”,公開批判說:“什么專業對口?就是要槍口對炮口,一切專業只對階級斗爭這個口!”(陳煥然:《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當時“階級斗爭這個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為了打擊官僚體系,放出了青年學生這些“小鬼”,讓他們大鬧中華。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開始讓他們回到學校,此即所謂“復課鬧革命”。無奈“小鬼”們野性已成,還留在社會繼續鬧,只得干脆把他們全部趕到農村去,讓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農村,再無聯合造反的可能。其二,這是實現民粹主義理想的需要:不僅將農民、農村理想化,更把知識分子視為打擊,甚至消滅的對象,因此,他們不僅號召中學生“上山下鄉”,把大學生發配農村、工廠,而且也把教師、老知識分子都打發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這是一個全面地、有目的地、有組織地改造與消滅知識分子的大戰略、大計劃。當時,姚文元發表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便是這個思想路線的典型文本。本書編者把老五屆和他們的老師都稱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是點出了要害的。他們的意圖就是要一舉而最后消滅中國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完全自覺的反知識分子、反知識、反文化的運動。這樣,本書的“苦難記憶”,大學生發配到底層,遭遇到從精神到肉體的無情摧殘,就絕非偶然,也不是具體執行者的道德、水平問題,而是一個根本性的指導思想和體制的問題。
這里,我還想就個人的經驗,作一個補充。前面說過,我比老五屆的同學要早十年到基層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處,不僅在肉體的傷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靈的控制,把專制的邏輯滲透到你的靈魂深處,在“奴隸生活中尋m‘美’來,贊嘆,撫摩,陶醉”,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魯迅語),久而久之,“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與消滅”,就成了知識分子自身的自覺要求。這樣的主動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殘酷的。因此,我說過:“在我的苦難記憶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頁頁,全是關于在外在壓力下,內心的動搖、屈服,以至叛變,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惡,以至變態……這樣一些慘不忍睹的記錄,我無法抹去這一切,它夢魘一般壓在我的心上,無時無亥q咬嚼著我的靈魂。”(錢理群:《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
這一切,怎么能夠隨意、輕率地遺忘!我們年輕時候流行一句話:“忘記,就是背叛”;如果遺忘了這一切,不僅背叛了當年的犧牲者,更背叛了我們自己的青春年華。李建宇同學說得好:我們必須追問“誰之罪”,“希望這種噩夢不要重演”(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這就必須從觀念上到體制上進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國民性的弱點,以及我們自己的責任。導致悲劇的觀念、制度不變,悲劇就會重演。要知道:當我們遺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學生的時代”,以至今天的年輕人已經不相信曾經有過這樣的年代,這就意味著那個時代正在回歸:今天,各種形態的“狼吃人”的悲劇,難道還少嗎?
二、不可遺忘的精神堅守
歷史總是兩面的:有壓迫,就有反抗;有消滅“臭老九”的險惡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堅守自己的知識分子傳統。對于從來就懷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覺。記得我自己在貴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饑荒與“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亂的年代,就從來沒有動搖過對知識的追求和“知識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讀本書,最感欣慰,也最為感佩的,也是老五屆同學和我一樣的堅定信念和堅守。聶永泰同學之所以讓我們永遠懷念,不僅是因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劇凝結著歷史的血的教訓,更因為他身上那股永遠不改、永不放棄的知識分子的“臭氣”和“傻氣”:“不注重世俗的人情世故和關注生存發展的關系”,只是“執著亡命地不斷追求”知識,“除了追求學問,他從不妨礙別人,雖然面對艱苦嚴峻的環境,仍然毫不消極”,可以說,他是因為這樣的堅守,才被狼,也被社會吞噬的。陳煥仁同學說“他的英魂變成了跑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永遠地留在了康藏草原”(陳煥然:《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遠留在我們每一個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這樣的堅守,不是聶永泰一個人,而是老五屆一代人。像馬云龍同學,一輩子都堅持“腦袋里亂想,嘴上亂說”的北大人的“壞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關押了四年;改革開放以后從事新聞工作,又因為堅持說真話,而“兩次被辭職,一次自動辭職”,始終“不合時宜,不合領導胃口”,卻從不知悔(馬云龍:《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學,被下放到江西一所縣中學,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氣,受到學校“土皇帝”的誣陷,就拍案而起:“陳伯達都敢反了,你這個小小的劉××算何東西!”不料想,從此與劉××和整個地方獨立王國結仇,在“文革”中被批斗一千場不說,“文革”結束后,他要報考研究生,也被百般阻撓,他不屈不撓抗爭到底,終于大難不死,逃出虎穴,還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俞肇智:《突破重圍》)。大多數同學即使沒有什么“出格”的行為,但如奚學瑤同學所說,雖然歷經磨難,也沒有被社會“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學生時代的正義感、朝氣和銳氣”,到了晚年,“無官薄祿”一身輕,“當年豪氣換來兩袖清風,一絲慰藉”(奚學瑤:《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藝,不竭的創造力,在晚年習武練舞,演奏琵琶,騎車游遍全國,創造了“輝煌的黃昏”(馬以釗:《琵琶弦上說相思》,孔繁鐘鑫:《十年磨一劍》,以及曾軍、蔡華江的壯舉)。記得我們前后幾代人,都熟知前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段關于“如何度過人的一生”的名言;現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時候,我們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爭,在順境中奮發”,我們也做到了“無悔一生”(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我還想談談老五屆北大人的這種堅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義。我發現,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師生在校期間對北大傳統的繼承與創造,而較少關注“出校以后”對北大傳統的堅守與發展。其中一個具體原因,就是學生畢業以后,就處于分散的個體狀態,難以有整體的關注與描述。在這個意義上,就顯示出北大老五屆的特殊性:他們是北大歷史上唯一在離開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種“群體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書的編者是將老五屆命名為一個“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的。在“特殊的時代”里,他們遭遇的“群體性磨難”和群體性堅守,就構成了北京大學歷史上堅苦卓絕的一頁(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在我看來,像聶永泰同學以及其他一些同學的命運與精神,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屆對北大傳統的堅守和發展,是應該進入北大校史的歷史敘述的。
三、不可遺忘的底層體驗
我在閱讀本書時,特別注意到一個細節:李建宇同學回憶說,他被發配為“煤黑子”,盡管是“閻王”(各級領導)和“小鬼”(積極分子)的“肉中刺”,卻得到了隊里工人的善待,他們“不大關心政治,不具備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覺悟,對偉大領袖沒有表現出那么多的熱愛,對階級敵人也沒有那么多的痛恨”,“他們不會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難,他們會不聲不響地過來幫你;你身處險境,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搶救你”。正是這些“真誠、善良”的底層民眾幫助他們稱為的“北京家”度過了人生險境(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時所發現的:“無論政治的統治力量多么強大,在底層的父老鄉親那里,還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標準,即人們通常所說‘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桿秤’。”盡管各級領導都把知識分子視為“臭老九”,普通礦工還是把李建宇這樣的大學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難”而下放到他們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難人”的民間倫理,用最大的善意對待他。這就意味著,即使是把階級斗爭發展到極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善待人”的民間倫理,仍在底層社會發揮作用,并神奇地保護了體制的“敵人”,有人執意要消滅的“臭老九”。在這個意義上,底層社會的民間倫理,就構成了“體制的控制的反力,對體制統治的有效性形成無形的破壞和削減”(錢理群:《“活下去,還是不活?——我看紀錄片《<和鳳鳴>》)。這大概是體制懲罰“末代臭老九”,將他們趕下基層接受“改造”時,所未曾料到的:反而為這批老五屆的大學生提供了一個接觸與了解底層社會和人民的機會,他們由此而獲得的新經驗、新體驗、新認識,是體制所控制不了的。
奚學瑤、張從同學說得好:“歪打正著的是,我們從堂皇的學術殿堂,沉入艱辛的社會底層,與底層民眾零距離接觸,知道了他們的所愛、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間疾苦,與他們交了朋友,從而深層次地了解了中國,了解了人民大眾,變得不那么書生氣了。”(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這里談到的底層經驗,對于北大人或許是更為重要的。
盧達甫同學在他的回憶中,提出要“放下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并進一步提出“還是放棄北大的貴族意識,做一個平民,也許活得更快活更充實更輕松”(盧達甫:《老五屆大學生》)。這就涉及“如何看待北大人及其傳統”的問題,引起了我的討論興趣。北大人無疑是有精英意識的,前面提到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就是這樣的精英意識。在我看來,這樣的責任感、使命感,以及追求“最高最好最強”的高遠目標、理想,開闊的視野,等等,都構成了北大精神傳統的重要方面,也是彌足珍貴的。但不可忽視的是,這樣的北大精英意識也是自有弱點的,最主要的,就是容易將自我懸空,脫離現實,脫離普通民眾,也容易形成“眼高手低”,甚至“志大才疏”的毛病。因此,北大人需要從空中落到地上,用我這些年經常和在校北大學生交談時的話來說,就是要“認識腳下的土地”,和中國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建立起生命的血肉聯系。這是北大人在自我成長過程中必須完成的“功課”。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要因此而消弭精英意識,而是要在其中注入對國情、現實的深刻體認,注入底層理解與關懷,也就是將精英意識與平民意識有機結合起來,達到既“仰望星空”,又“腳踏大地”的新的精神境界。“文革”中將北大老五屆學生強制下放,如前文所分析,其目的是在消滅知識分子及其應有的精英意識,是歷史的反動;但它卻用這樣的扭曲的方式,逼迫北大人落到了地上,而且一下子沉入了社會最底層。這就在北大老五屆學生的精神上,既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與扭曲——這是絕對不能遮蔽、否認的事實;同時也使他們因此獲取了新的精神資源——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李檀同學在回首往事時說得很好:“盡管我后來漂洋過海,到美國當了假洋鬼子,盡管農村那段教書生涯的細節,我已經漸漸淡忘,但是它對我的影響,已經化人我的血液,進入我的機體,永遠成為我的一部分”(李檀:《我的農村教師生活》),“命運雖然有時殘酷,但過去的時光都很美好,人生留給我們許多刻骨的回憶,都是自己的年華,都是財富,都很溫馨。”(李橦:《我是插隊大學生》)——他應該是說出了北大老五屆同學的共同感受。
這里需要專門說說剛剛離世的劉蓓蓓同學的經驗,也算是對她的在天之靈的一個紀念吧。1977年11月,劉蓓蓓還在農村中學教書,看到了《人民文學》上新發表的劉心武的《班主任》,從中讀出了文學的,也是歷史的新時期來臨的信息,立即寫了評價文章。發表后,一時“洛陽紙貴”,因此有人說她“引領了傷痕文學的潮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劉蓓蓓是北大老五屆的第一個“歸來者”。當時就有人猜測她是“通天的高干子弟”,才有如此的膽識。劉蓓蓓在回憶文章里,對此發出了“無限感慨:光通天不立地,對社會弊病和民間疾苦沒有切膚之痛,大概也寫不出哪怕像我那樣一篇沒有多少學術性、也就是篇讀后感類的小文來!我不過是個傻大膽,說出了別人想說但不敢說的話。這‘傻’來自于使命感和責任感,可能是老北大人的‘通病”’(劉蓓蓓:《離開未名湖的日子》)。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像劉蓓蓓這樣的北大老五屆,既堅守了北大的傳統(“通病”),又有了底層經驗和體驗,對中國問題有了切膚之痛,就能夠做到“通天立地”,這也就標示著北大人的真正成熟。這是此后許多北大老五屆同學能夠作出特殊的貢獻的秘密所在。許多人功成名就以后,一定要回到當年生活的基層尋根(劉慶華:《借得東風好揚帆》),原因也在于此。
這也涉及到一個重要問題:“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首先,我們需要小心地將這一命題和民粹主義區分開來:這絕不意味著對苦難的美化,我們在前文已經說得很清楚:苦難本身就是對人的肉體和精神的摧殘,它是不會自然就成為“精神資源”的。相反,在現實生活里,大量存在的事實,是許多人都被苦難所壓垮,毀了一生:這人為的苦難的罪惡,是永遠不能原諒,不容遮蔽的。只有人們走出了苦難,才有可能將其轉化為精神資源。所說的“走出”,應該有兩個含義。在前文引述的《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的文章里,我曾經提出,首先要正視苦難,正視苦難造成的精神創傷,包括前文說到的,在苦難中的精神自傷,知恥而自悔,這才能走出奴隸狀態,獲得對歷史、社會、他人和自身的清醒。然后,還要超越一己的苦難,進行歷史的反思,追問造成苦難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的原因,揭示觀念的失誤,體制的弊端。這樣,才能真正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苦難也就轉化成了資源。這里,我還想補充一點,就是要正確對待自己發配期間的底層生活。將其簡單的視為不堪回首的過去,逃離了就永不回歸,這樣的心情和心理,可以而且應該予以理解的同情;但如果因此輕易地將或深或淺,或多或少的底層經驗全部忘卻,把已經建立的和底層的生活與精神聯系完全斬斷,就會失去了轉化為精神資源的機會,是十分可惜的。我在總結自己的一生時,最感欣慰的,就是在離開貴州以后,幾十年來,一直把貴州視為“第二故鄉”,與之保持密切聯系,從而建立起了“北京大學”與“貴州”兩個精神基地,我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頂層與基層,中心和邊緣,精英和草根之間,形成了良性的互動。我每次在北京遭遇打擊,陷入困境,都到貴州去尋求支持,吸取力量,獲得精神庇護:那是我的真正“根”之所在。我也經常把自己的這一人生經驗,告訴今天的北大學子和其他學校的大學生,也都引起了他們的強烈反響。在本書里,很多同學都談到,歷經苦難的北大老五屆學子,應該把自己的經驗教訓“留給母校,留給后人,留給歷史”。這大概就是我們最后的歷史責任吧。這或許也是本書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僅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無意遺忘的歷史,先后對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和1980年北大“校園民主選舉運動”作了專門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時,對北大“文革”前的歷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這次讀到北大老五屆同學的回憶,我才發現了一個重大的遺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屆作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集體下放,他們也書寫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而且如書中一位作者所說,他們在北大1949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的(盧達甫:《老五屆大學生》)。就我的研究范圍而言,他們上承1957年的校園民主運動:不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運動與“五一九運動”有著復雜的關系(這還有待于研究),而且當年的北大右派同學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發配勞改,現在老五屆也以一種“原罪”發配農場和基層改造,盡管彼此處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歷程卻是相通的。而正是因為有了底層的經驗與反思,“文革”結束后回到北大,才會有1980年校園競選運動對中國改革問題的大討論。本書編者說,老五屆的“獨特行跡,是北大百年歷史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這是有充分理由的。盧達甫同學還談到:“我們的歷史學家與文學家、藝術家,似乎都遺忘了老五屆大學生。中國的知青文學鋪天蓋地,老五屆文學幾乎是空白。”(盧達甫:《老五屆大學生》)這確實是歷史研究、文學書寫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課題,這是一段“不可遺忘的歷史”。現在,北大老五屆的同學回憶當年親身經歷,用“自己描寫自己”的方式,開拓了一個新的歷史研究領域,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我們這些歷史研究者,應該是一個啟示與挑戰。我寫本文,也算是一個回應吧。
所謂“不可遺忘的歷史”,在我的理解里,應該有三個層面的意思。
一、不可遺忘的苦難記憶
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在當下中國思想界、學術界,有一種刻意美化“文革”歷史的傾向。有人就宣稱,“文革”是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最輝煌的一頁”,那些苦難都是知識分子虛構與夸大的,即使有苦難,也是推動歷史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有關的知青生活的回憶和文學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來描述那段歷史,過分地強調所謂“青春無悔”。這樣的對歷史血腥氣的著意遮蔽與抹殺,對在“強迫遺忘”的文化、教育環境里長大的中國年輕一代的欺騙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嚴重的。因此,今天,當事人的苦難記憶,說出歷史真相,是具有“拒絕遺忘,抗拒謊言”的現實意義的。
因此,我讀本書,最感驚心動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憶:470名部隊官兵、83名大學生,“十八至二十三歲剛剛踏進社會的稚嫩青年,在當時狂熱高壓的政治氛圍里,為了政治口號而赴湯蹈火”,犧牲了寶貴的生命(白嘉薈:《殤痛牛田洋》);1963年技術物理系的高材生聶永泰,因為被社會所不容,只能到高山雪原尋求心靈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陳煥然:《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淚》);同樣是技術物理系放射化學專業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罰到山西汾西礦務局煤礦當“煤黑子”,而且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被視為“從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心靈折磨比肉體傷害更難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這都是不容掩飾的血淋淋的事實。
問題是,這樣的從肉體到精神上摧殘人的生命,是當時的一個既定方針、政策。老五屆畢業前,有過一場關于分配方針的爭論。有同學提出“分配應該考慮專業對口”的要求,卻被執掌權力的工宣隊斥為“修正主義分配路線”,公開批判說:“什么專業對口?就是要槍口對炮口,一切專業只對階級斗爭這個口!”(陳煥然:《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當時“階級斗爭這個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為了打擊官僚體系,放出了青年學生這些“小鬼”,讓他們大鬧中華。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開始讓他們回到學校,此即所謂“復課鬧革命”。無奈“小鬼”們野性已成,還留在社會繼續鬧,只得干脆把他們全部趕到農村去,讓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農村,再無聯合造反的可能。其二,這是實現民粹主義理想的需要:不僅將農民、農村理想化,更把知識分子視為打擊,甚至消滅的對象,因此,他們不僅號召中學生“上山下鄉”,把大學生發配農村、工廠,而且也把教師、老知識分子都打發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這是一個全面地、有目的地、有組織地改造與消滅知識分子的大戰略、大計劃。當時,姚文元發表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便是這個思想路線的典型文本。本書編者把老五屆和他們的老師都稱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是點出了要害的。他們的意圖就是要一舉而最后消滅中國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完全自覺的反知識分子、反知識、反文化的運動。這樣,本書的“苦難記憶”,大學生發配到底層,遭遇到從精神到肉體的無情摧殘,就絕非偶然,也不是具體執行者的道德、水平問題,而是一個根本性的指導思想和體制的問題。
這里,我還想就個人的經驗,作一個補充。前面說過,我比老五屆的同學要早十年到基層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處,不僅在肉體的傷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靈的控制,把專制的邏輯滲透到你的靈魂深處,在“奴隸生活中尋m‘美’來,贊嘆,撫摩,陶醉”,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魯迅語),久而久之,“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與消滅”,就成了知識分子自身的自覺要求。這樣的主動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殘酷的。因此,我說過:“在我的苦難記憶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頁頁,全是關于在外在壓力下,內心的動搖、屈服,以至叛變,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惡,以至變態……這樣一些慘不忍睹的記錄,我無法抹去這一切,它夢魘一般壓在我的心上,無時無亥q咬嚼著我的靈魂。”(錢理群:《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
這一切,怎么能夠隨意、輕率地遺忘!我們年輕時候流行一句話:“忘記,就是背叛”;如果遺忘了這一切,不僅背叛了當年的犧牲者,更背叛了我們自己的青春年華。李建宇同學說得好:我們必須追問“誰之罪”,“希望這種噩夢不要重演”(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這就必須從觀念上到體制上進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國民性的弱點,以及我們自己的責任。導致悲劇的觀念、制度不變,悲劇就會重演。要知道:當我們遺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學生的時代”,以至今天的年輕人已經不相信曾經有過這樣的年代,這就意味著那個時代正在回歸:今天,各種形態的“狼吃人”的悲劇,難道還少嗎?
二、不可遺忘的精神堅守
歷史總是兩面的:有壓迫,就有反抗;有消滅“臭老九”的險惡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堅守自己的知識分子傳統。對于從來就懷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覺。記得我自己在貴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饑荒與“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亂的年代,就從來沒有動搖過對知識的追求和“知識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讀本書,最感欣慰,也最為感佩的,也是老五屆同學和我一樣的堅定信念和堅守。聶永泰同學之所以讓我們永遠懷念,不僅是因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劇凝結著歷史的血的教訓,更因為他身上那股永遠不改、永不放棄的知識分子的“臭氣”和“傻氣”:“不注重世俗的人情世故和關注生存發展的關系”,只是“執著亡命地不斷追求”知識,“除了追求學問,他從不妨礙別人,雖然面對艱苦嚴峻的環境,仍然毫不消極”,可以說,他是因為這樣的堅守,才被狼,也被社會吞噬的。陳煥仁同學說“他的英魂變成了跑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永遠地留在了康藏草原”(陳煥然:《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遠留在我們每一個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這樣的堅守,不是聶永泰一個人,而是老五屆一代人。像馬云龍同學,一輩子都堅持“腦袋里亂想,嘴上亂說”的北大人的“壞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關押了四年;改革開放以后從事新聞工作,又因為堅持說真話,而“兩次被辭職,一次自動辭職”,始終“不合時宜,不合領導胃口”,卻從不知悔(馬云龍:《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學,被下放到江西一所縣中學,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氣,受到學校“土皇帝”的誣陷,就拍案而起:“陳伯達都敢反了,你這個小小的劉××算何東西!”不料想,從此與劉××和整個地方獨立王國結仇,在“文革”中被批斗一千場不說,“文革”結束后,他要報考研究生,也被百般阻撓,他不屈不撓抗爭到底,終于大難不死,逃出虎穴,還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俞肇智:《突破重圍》)。大多數同學即使沒有什么“出格”的行為,但如奚學瑤同學所說,雖然歷經磨難,也沒有被社會“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學生時代的正義感、朝氣和銳氣”,到了晚年,“無官薄祿”一身輕,“當年豪氣換來兩袖清風,一絲慰藉”(奚學瑤:《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藝,不竭的創造力,在晚年習武練舞,演奏琵琶,騎車游遍全國,創造了“輝煌的黃昏”(馬以釗:《琵琶弦上說相思》,孔繁鐘鑫:《十年磨一劍》,以及曾軍、蔡華江的壯舉)。記得我們前后幾代人,都熟知前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段關于“如何度過人的一生”的名言;現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時候,我們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爭,在順境中奮發”,我們也做到了“無悔一生”(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我還想談談老五屆北大人的這種堅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義。我發現,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師生在校期間對北大傳統的繼承與創造,而較少關注“出校以后”對北大傳統的堅守與發展。其中一個具體原因,就是學生畢業以后,就處于分散的個體狀態,難以有整體的關注與描述。在這個意義上,就顯示出北大老五屆的特殊性:他們是北大歷史上唯一在離開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種“群體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書的編者是將老五屆命名為一個“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的。在“特殊的時代”里,他們遭遇的“群體性磨難”和群體性堅守,就構成了北京大學歷史上堅苦卓絕的一頁(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在我看來,像聶永泰同學以及其他一些同學的命運與精神,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屆對北大傳統的堅守和發展,是應該進入北大校史的歷史敘述的。
三、不可遺忘的底層體驗
我在閱讀本書時,特別注意到一個細節:李建宇同學回憶說,他被發配為“煤黑子”,盡管是“閻王”(各級領導)和“小鬼”(積極分子)的“肉中刺”,卻得到了隊里工人的善待,他們“不大關心政治,不具備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覺悟,對偉大領袖沒有表現出那么多的熱愛,對階級敵人也沒有那么多的痛恨”,“他們不會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難,他們會不聲不響地過來幫你;你身處險境,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搶救你”。正是這些“真誠、善良”的底層民眾幫助他們稱為的“北京家”度過了人生險境(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時所發現的:“無論政治的統治力量多么強大,在底層的父老鄉親那里,還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標準,即人們通常所說‘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桿秤’。”盡管各級領導都把知識分子視為“臭老九”,普通礦工還是把李建宇這樣的大學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難”而下放到他們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難人”的民間倫理,用最大的善意對待他。這就意味著,即使是把階級斗爭發展到極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善待人”的民間倫理,仍在底層社會發揮作用,并神奇地保護了體制的“敵人”,有人執意要消滅的“臭老九”。在這個意義上,底層社會的民間倫理,就構成了“體制的控制的反力,對體制統治的有效性形成無形的破壞和削減”(錢理群:《“活下去,還是不活?——我看紀錄片《<和鳳鳴>》)。這大概是體制懲罰“末代臭老九”,將他們趕下基層接受“改造”時,所未曾料到的:反而為這批老五屆的大學生提供了一個接觸與了解底層社會和人民的機會,他們由此而獲得的新經驗、新體驗、新認識,是體制所控制不了的。
奚學瑤、張從同學說得好:“歪打正著的是,我們從堂皇的學術殿堂,沉入艱辛的社會底層,與底層民眾零距離接觸,知道了他們的所愛、所憎、所愿、所求,知道了民間疾苦,與他們交了朋友,從而深層次地了解了中國,了解了人民大眾,變得不那么書生氣了。”(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這里談到的底層經驗,對于北大人或許是更為重要的。
盧達甫同學在他的回憶中,提出要“放下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并進一步提出“還是放棄北大的貴族意識,做一個平民,也許活得更快活更充實更輕松”(盧達甫:《老五屆大學生》)。這就涉及“如何看待北大人及其傳統”的問題,引起了我的討論興趣。北大人無疑是有精英意識的,前面提到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就是這樣的精英意識。在我看來,這樣的責任感、使命感,以及追求“最高最好最強”的高遠目標、理想,開闊的視野,等等,都構成了北大精神傳統的重要方面,也是彌足珍貴的。但不可忽視的是,這樣的北大精英意識也是自有弱點的,最主要的,就是容易將自我懸空,脫離現實,脫離普通民眾,也容易形成“眼高手低”,甚至“志大才疏”的毛病。因此,北大人需要從空中落到地上,用我這些年經常和在校北大學生交談時的話來說,就是要“認識腳下的土地”,和中國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建立起生命的血肉聯系。這是北大人在自我成長過程中必須完成的“功課”。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要因此而消弭精英意識,而是要在其中注入對國情、現實的深刻體認,注入底層理解與關懷,也就是將精英意識與平民意識有機結合起來,達到既“仰望星空”,又“腳踏大地”的新的精神境界。“文革”中將北大老五屆學生強制下放,如前文所分析,其目的是在消滅知識分子及其應有的精英意識,是歷史的反動;但它卻用這樣的扭曲的方式,逼迫北大人落到了地上,而且一下子沉入了社會最底層。這就在北大老五屆學生的精神上,既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與扭曲——這是絕對不能遮蔽、否認的事實;同時也使他們因此獲取了新的精神資源——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李檀同學在回首往事時說得很好:“盡管我后來漂洋過海,到美國當了假洋鬼子,盡管農村那段教書生涯的細節,我已經漸漸淡忘,但是它對我的影響,已經化人我的血液,進入我的機體,永遠成為我的一部分”(李檀:《我的農村教師生活》),“命運雖然有時殘酷,但過去的時光都很美好,人生留給我們許多刻骨的回憶,都是自己的年華,都是財富,都很溫馨。”(李橦:《我是插隊大學生》)——他應該是說出了北大老五屆同學的共同感受。
這里需要專門說說剛剛離世的劉蓓蓓同學的經驗,也算是對她的在天之靈的一個紀念吧。1977年11月,劉蓓蓓還在農村中學教書,看到了《人民文學》上新發表的劉心武的《班主任》,從中讀出了文學的,也是歷史的新時期來臨的信息,立即寫了評價文章。發表后,一時“洛陽紙貴”,因此有人說她“引領了傷痕文學的潮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劉蓓蓓是北大老五屆的第一個“歸來者”。當時就有人猜測她是“通天的高干子弟”,才有如此的膽識。劉蓓蓓在回憶文章里,對此發出了“無限感慨:光通天不立地,對社會弊病和民間疾苦沒有切膚之痛,大概也寫不出哪怕像我那樣一篇沒有多少學術性、也就是篇讀后感類的小文來!我不過是個傻大膽,說出了別人想說但不敢說的話。這‘傻’來自于使命感和責任感,可能是老北大人的‘通病”’(劉蓓蓓:《離開未名湖的日子》)。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像劉蓓蓓這樣的北大老五屆,既堅守了北大的傳統(“通病”),又有了底層經驗和體驗,對中國問題有了切膚之痛,就能夠做到“通天立地”,這也就標示著北大人的真正成熟。這是此后許多北大老五屆同學能夠作出特殊的貢獻的秘密所在。許多人功成名就以后,一定要回到當年生活的基層尋根(劉慶華:《借得東風好揚帆》),原因也在于此。
這也涉及到一個重要問題:“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首先,我們需要小心地將這一命題和民粹主義區分開來:這絕不意味著對苦難的美化,我們在前文已經說得很清楚:苦難本身就是對人的肉體和精神的摧殘,它是不會自然就成為“精神資源”的。相反,在現實生活里,大量存在的事實,是許多人都被苦難所壓垮,毀了一生:這人為的苦難的罪惡,是永遠不能原諒,不容遮蔽的。只有人們走出了苦難,才有可能將其轉化為精神資源。所說的“走出”,應該有兩個含義。在前文引述的《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的文章里,我曾經提出,首先要正視苦難,正視苦難造成的精神創傷,包括前文說到的,在苦難中的精神自傷,知恥而自悔,這才能走出奴隸狀態,獲得對歷史、社會、他人和自身的清醒。然后,還要超越一己的苦難,進行歷史的反思,追問造成苦難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的原因,揭示觀念的失誤,體制的弊端。這樣,才能真正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苦難也就轉化成了資源。這里,我還想補充一點,就是要正確對待自己發配期間的底層生活。將其簡單的視為不堪回首的過去,逃離了就永不回歸,這樣的心情和心理,可以而且應該予以理解的同情;但如果因此輕易地將或深或淺,或多或少的底層經驗全部忘卻,把已經建立的和底層的生活與精神聯系完全斬斷,就會失去了轉化為精神資源的機會,是十分可惜的。我在總結自己的一生時,最感欣慰的,就是在離開貴州以后,幾十年來,一直把貴州視為“第二故鄉”,與之保持密切聯系,從而建立起了“北京大學”與“貴州”兩個精神基地,我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頂層與基層,中心和邊緣,精英和草根之間,形成了良性的互動。我每次在北京遭遇打擊,陷入困境,都到貴州去尋求支持,吸取力量,獲得精神庇護:那是我的真正“根”之所在。我也經常把自己的這一人生經驗,告訴今天的北大學子和其他學校的大學生,也都引起了他們的強烈反響。在本書里,很多同學都談到,歷經苦難的北大老五屆學子,應該把自己的經驗教訓“留給母校,留給后人,留給歷史”。這大概就是我們最后的歷史責任吧。這或許也是本書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目次
序 不可遺忘的歷史
第一輯東北原野
離開未名湖的日子
北大歸去來
蒼茫北大荒
我與李丹林
告別康平
遼北軼事
在刀蘭套海村
昌圖十年風雨路
杏壇第一站
盤錦往事
第二輯華北大地
雁落塞北
部隊農場的一年
在衡水的日子里
我是“插隊”大學生
我的農村教師生活
未名湖情思
“畢業”后的那些事
我們是北大人
我的頭發,我的心
我的“煤黑子”生活
我的文學,或日文化之路
十年磨一劍
向母親湖的匯報
旅痕
蹣跚的腳步
第三輯華東山川
我的四十年
琵琶弦上說相思
突破重圍
齊魯三部曲
我的電視緣
日出
悲愴離北大 江淮多磨難
百感流水訴衷腸
望斷博雅塔之后
老五屆大學生
難忘武山學生連
在“土圍子”里的日子
第四輯中南海岳
殤痛牛田洋
四海為家
電視生涯二十年
“未名湖小魚”沉浮錄
票友人生
曲線歸口
改行
一個北大人的經歷與感悟
第五輯西南叢莽
往事并不如煙
使命狂想小人物
雅安雜憶
貴州八年
借得東風好揚帆
騎行在彎彎的山路上
一朵溜溜的云
雪山淚
苦難與夢想
只身上路
第六輯西北嶺塬
中美杏壇四十年
追憶高原
漢中歲月
漸入佳境
憶與思
新疆“再教育”紀事
跋 韶華如水憶逝年
第一輯東北原野
離開未名湖的日子
北大歸去來
蒼茫北大荒
我與李丹林
告別康平
遼北軼事
在刀蘭套海村
昌圖十年風雨路
杏壇第一站
盤錦往事
第二輯華北大地
雁落塞北
部隊農場的一年
在衡水的日子里
我是“插隊”大學生
我的農村教師生活
未名湖情思
“畢業”后的那些事
我們是北大人
我的頭發,我的心
我的“煤黑子”生活
我的文學,或日文化之路
十年磨一劍
向母親湖的匯報
旅痕
蹣跚的腳步
第三輯華東山川
我的四十年
琵琶弦上說相思
突破重圍
齊魯三部曲
我的電視緣
日出
悲愴離北大 江淮多磨難
百感流水訴衷腸
望斷博雅塔之后
老五屆大學生
難忘武山學生連
在“土圍子”里的日子
第四輯中南海岳
殤痛牛田洋
四海為家
電視生涯二十年
“未名湖小魚”沉浮錄
票友人生
曲線歸口
改行
一個北大人的經歷與感悟
第五輯西南叢莽
往事并不如煙
使命狂想小人物
雅安雜憶
貴州八年
借得東風好揚帆
騎行在彎彎的山路上
一朵溜溜的云
雪山淚
苦難與夢想
只身上路
第六輯西北嶺塬
中美杏壇四十年
追憶高原
漢中歲月
漸入佳境
憶與思
新疆“再教育”紀事
跋 韶華如水憶逝年
書摘/試閱
那個年頭,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天天提醒人們要準備打仗,第三次世界大戰似乎頃刻就會爆發,20世紀70年代仿佛注定將是個打仗的年代。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的軍旅生活基本上就是白天干活,晚上拉練。在6377部隊一年,生活節奏之緊張,勞動與拉練消耗體力強度之大,可能在我一生中再也沒有經歷過。在最緊張的夏秋農忙季節,我們都是凌晨3點多鐘就起床干活,一直干到太陽下山天黑才收工。回到營地,到井邊倒一桶水沖一下涼,倒頭就睡,因為睡不了一會兒又要起床干活了,我們經常是在地頭迎來晨曦、曙光和日出。
最有意思的是連吃飯也要爭分奪秒與蘇修搶時間,那解放軍連長天天親自主持比賽誰吃得快。我本來吃飯的速度就快,加之在農場勞動強度極大,那白米飯吃起來就格外香。哨子一吹,我很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狼吞虎咽扒了三大碗,我常常是最早吃完飯放下碗筷的人之一。我雖然干活干不過別人,但吃飯經常能搶個第一,心理上終于找到了一個平衡點,為此我常常很得意。8月份后,六大院校的戰友加入到我們這個行列,中國人民大學的陳賢忠接替北大陳忠寶當了事務長,把伙食搞得更加有聲有色。陳賢忠性格直率開朗,極具鼓動天才,與前任不同的是,每到我們吃飯時,他就加念一篇革命大批判文章給大伙兒鼓勁,把吃飯問題直接與批蘇修、批劉少奇掛起鉤來,給82分隊戰友們吃飯又增添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也許是革命大批判真的發揮了神奇的威力,我們吃飯的速度又加快了許多,一桶飯幾分鐘便被大伙兒一掃而空了。
軍墾農場勞動如此緊張,而我們周邊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們則呈現出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勞動場景。上午9點多,太陽已升得老高,我們已干了半晌活,那邊生產隊的社員們才在紅旗的指引下懶洋洋地上了工。更為奇怪的是,他們到了地頭不是先干活,而是先坐下來休息,有的還橫躺著,一邊抽旱煙,一邊神侃,幾袋煙抽畢,開始動工時已是10點多鐘,太陽已快升到正中了。稀稀拉拉干了不到一個鐘頭活,這支隊伍又在紅旗的指引下收工,打道回府吃午飯。我從小生長在蘇南太湖之濱,阜陽那一帶人民公社社員們的這番勞動生活場景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我從實地朦朧感覺到,那里的貧困與生產關系出了問題似乎有著密切關系。
到夏收季節,更為令人沒有想到的一幕發生了。就在我們搶收辛辛苦苦耕耘了幾個月的麥子的時候,臨近傍晚,黑壓壓的社員隊伍把我們包圍了,他們要當“摘桃派”,搶奪農場夏收的果實。戰友們不得不擺出護麥的“龍門陣”,嚴陣以待。我原先只在電影《青春之歌》中見到過農民在中共的領導下搶割地主老財麥子的鏡頭,地主在麥子被搶后躺倒在田頭哭喊:“我的麥子啊!”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優惠價:87
260
海外經銷商無庫存,到貨日平均30天至4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