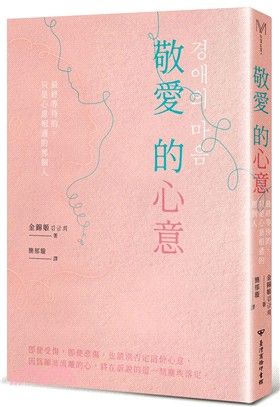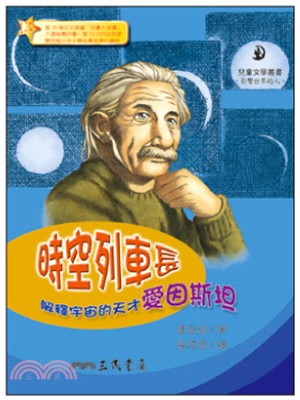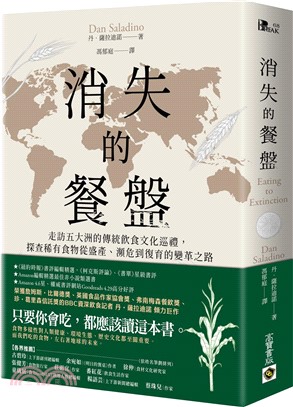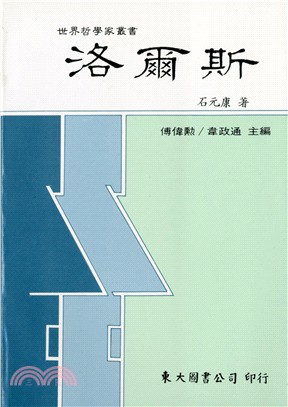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在紀念季羨林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際,為了將他的平凡而偉大的形象再次展現在廣大讀者面前,我們編選了這部《季羨林精選文集》。全書總共七集,即《問學論道》《人生感悟》《故人情深》《新紀新語》《學人箴言》《燕園偶寄》《病房客話》。書中所選文章均為季先生坦蕩心懷、直抒胸臆、對百載人生經歷的真實記錄和深刻體驗。其中,有懷舊文稿、四海游記以及與新朋舊友交往的美好回憶;有文采斐然的散文名篇和耄耋之年黃鐘大呂式的文化隨筆;有對學術研究的真知灼見和經驗之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季先生一生的最後十年,在病榻上依然難得糊涂,時刻承載著天下大事,守望著祖國人民,他的那支筆一直揮舞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堪稱風流倜儻、可喜可賀的佳話。
“君子尊德性而道學問”,季羨林先生為我們留下了上千萬字的著述,其中不乏講道德談學問的精彩論述。或許,有的讀者至今仍然百看不厭地讀著他的書,儼然成了他的“粉絲”;有的讀者雖然讀過他的書,卻覺得似懂非懂,不甚了了;有的讀者甚至只是知道他的大名卻未曾讀過他的書;而這部《季羨林精選文集》,正好應時而生,在季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際與讀者喜相逢,它會讓你一睹“世紀老人”的獨特風采,聽他講述遙遠而現實的娓娓動聽的故事。由此,你會真的“識破廬山真面目”——看這些故事背後有著怎樣的歷史背景,主人公備嘗多少艱辛、苦澀和歡愉;在深邃與優雅相間、嚴肅與幽默同步、小情愫與大胸懷兼具的字里行間,怎樣透射出季先生對人情世事、學術道德的公正謹嚴、詼諧有趣的思考,閃耀著啟迪人們心智的燦爛光輝。
序
在紀念季羨林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際,為了將他的平凡而偉大的形象再次展現在廣大讀者面前,我們編選了這部《季羨林精選文集》。全書總共七集,即《問學論道》《人生感悟》《故人情深》《新紀新語》《學人箴言》《燕園偶寄》《病房客話》。書中所選文章均為季先生坦蕩心懷、直抒胸臆、對百載人生經歷的真實記錄和深刻體驗。其中,有懷舊文稿、四海游記以及與新朋舊友交往的美好回憶;有文采斐然的散文名篇和耄耋之年黃鐘大呂式的文化隨筆;有對學術研究的真知灼見和經驗之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季先生一生的最後十年,在病榻上依然難得糊涂,時刻承載著天下大事,守望著祖國人民,他的那支筆一直揮舞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堪稱風流倜儻、可喜可賀的佳話。
“君子尊德性而道學問”,季羨林先生為我們留下了上千萬字的著述,其中不乏講道德談學問的精彩論述。或許,有的讀者至今仍然百看不厭地讀著他的書,儼然成了他的“粉絲”;有的讀者雖然讀過他的書,卻覺得似懂非懂,不甚了了;有的讀者甚至只是知道他的大名卻未曾讀過他的書;而這部《季羨林精選文集》,正好應時而生,在季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際與讀者喜相逢,它會讓你一睹“世紀老人”的獨特風采,聽他講述遙遠而現實的娓娓動聽的故事。由此,你會真的“識破廬山真面目”——看這些故事背後有著怎樣的歷史背景,主人公備嘗多少艱辛、苦澀和歡愉;在深邃與優雅相間、嚴肅與幽默同步、小情愫與大胸懷兼具的字里行間,怎樣透射出季先生對人情世事、學術道德的公正謹嚴、詼諧有趣的思考,閃耀著啟迪人們心智的燦爛光輝。
季羨林先生生前反復強調說:
“我只有一個信念、一個主旨、一點精神,那就是:寫文章必須說真話,不說假話。上面提到的那三位師友(指冰心、巴金、蕭乾——編者)之所以享有極高的威望,之所以讓我佩服,不就在于他們敢說真話嗎?我在這里用了一個‘敢’字,這是‘畫龍點睛’之筆。因為,說真話是要有一點勇氣的,有時甚至需要極大的勇氣。古今中外,由于敢說真話而遭到厄運的作家或非作家的人數還算少嗎?然而,歷史是無情的。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為人所欽仰頌揚的作家或非作家無一不是敢說真話的人。說假話者其中也不能說沒有,他們只能做反面教員,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套書,即可還原季羨林先生的真情、真思、真美,而絕非偶像或符號式的人物。文章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季先生發自肺腑的聲音,而絕無任何矯揉造作。正如印度婆羅門教經典所言:“真實是至高無上的,至高無上的是真實。有了真實,人絕不會從天界墮落下來。”讀了這套書,你會發現季先生并非是神話中頂天立地的英雄,而是大地上實實在在的人。讀了這套書,你會感受到季先生靈魂中的真誠的美。
斗轉星移,物是人非,季羨林先生在生命的彼岸漸行漸遠,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中。“代際”之間存在的失憶、遺忘、模糊、隔膜,會使人們對他似曾相識終不認;而他又是“後五四優秀知識分子”中晚近謝世的一位,從此人們只能與他保持著象征性的聯系,或若縹緲的春夢般的尋蹤。然而,季先生畢竟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做出巨大的貢獻,對20世紀我國學術有著重要的影響。他的人格魅力和學術品格受到全社會的認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尤其對青少年的心智生命成長將會長時間地起到教育、鼓舞和啟迪作用。我們編選這套書的目的正在于通過重溫季先生的道德文章,引起人們對其為人風范和為學精神的思考、探究、評斷和闡示,以便直接或間接地受益,并希望其影響扎根于一代代人心中。總之,季羨林先生不愧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面永不倒的旗幟,他的道德文章為後人留下了無比豐厚的精神遺產,讓我們伸開雙手接受這份遺產吧!
借此機會,我們感謝季羨林先生之子季承先生親自授權編輯出版此套文集。感謝資深出版人吳昌榮先生的鼎力相助,感謝世文圖書為此套文集所付出的努力和創意以及承擔的前期編校工作;感謝金城出版社具有戰略眼光的決策及為出版此套文集所付出的辛勞。同時,我們也感謝季先生的山東小老鄉、原聊城大學本科生、現遼寧大學碩士生高源、靳慶柯兩位先生,他們為收集整理季先生的文稿與圖片做了大量的工作。
本書采用季羨林先生的一些照片以及與其相關的圖片,如他的一些師友的照片,左圖右史,相映成趣,使讀者產生直觀的立體感,從而構成本書的一大特色。在此,我們向為季先生及其師友拍照的有關人士表示感謝。
我們深感學殖之瘠薄,能力之不逮,編選這部《季羨林精選文集》自然會存在不當和紕漏之處,敬請同行專家及廣大讀者賜教。
目次
書摘/試閱
他實際上不是我的第一位老師。在他之前,我已經有幾位老師了。不過都已面影迷離,回憶渺茫,環境模糊,姓名遺忘。只有他我還記得最清楚,因而就成了第一了。
我這第一位老師,姓李,名字不知道。這并非由于忘記,而是當時就不注意。一個九歲的孩子,一般只去記老師的姓,名字則不管。倘若老師有“綽號”——老師幾乎都有的——則只記綽號,連姓也不管了。我們小學就有“Shao qian”(即知了,蟬。濟南這樣叫,不知道怎樣寫)、“賣草紙的”等等老師。李老師大概為人和善,受到小孩子的尊敬,又沒有什么特點,因此逃掉起“綽號”這一有時頗使老師尷尬的關。
我原在濟南一師附小上學,校長是新派人物,在山東首先響應五四運動,課本改為白話。其中有一篇《阿拉伯的駱駝》,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寓言故事。我叔父忽然有一天翻看語文課本,看到這一篇,勃然大怒,高聲說:“駱駝怎么能會說話!荒唐之至!快轉學!”
于是我就轉了學,轉的是新育小學。因為僥幸認識了一個“騾”字,震動了老師,讓我從高小開始,三年初小,統統赦免。一個字竟能為我這一生學習和工作提前了一兩年,不稱之為運氣好又稱之為什么呢?
新育校園極大,從格局上來看,舊時好像是什么大官的花園。門東向,進門左拐,有一排平房。沿南墻也有一排平房,似為當年仆人的住處。平房前面有一片空地,偏西有修砌完好的一大圓池塘,我可從來沒見過里面有水,只是雜草叢生而已。池畔隙地也長滿了雜草,春夏秋三季,開滿了雜花,引得蜂蝶紛至,野味十足,與大自然渾然一體。倘若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來到這里,必然認為是辦學的最好的地方。
進校右拐,是一條石徑,進口處木門上有一匾,上書“循規蹈矩”。我對這四個字感到極大的興趣,因為它們難寫,更難懂。我每天看到它,但是一直到畢業,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石徑右側是一座頗大的假山,石頭堆成,山半有亭。本來應該是栽花的空地上,現在卻沒有任何花,仍然只是雜草叢生而已。遙想當年鼎盛時,園主人大官正在輝煌奪目之時,山半的亭子必然彩繪一新,聳立巍然。山旁的隙地上也必然是栽滿了姚黃魏紫,國色天香。納蘭性德的詞“晚來風動護花鈴,人在半山亭”所流露出來的高貴氣象,必然會在這里出現。然而如今卻是山亭頹敗,無花無鈴,唯有夕陽殘照亂石林立而已。
可是,我卻忘記不了這一座假山,不是由于它景色迷人,而是由于它腳下那幾棵又高又粗的大樹。此樹我至今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它春天開黃色碎花,引得成群的蜜蜂,繞花嗡嗡,綠葉與高干并配,花香與蜂鳴齊飛,此印象至今未泯。我之所以懷念它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當年連小學生也是并不那么“循規蹈矩”的——那四個字同今天的一些口號一樣,對我們絲毫也不起作用。如果我們覺得哪個老師不行,我們往往會“架”(趕走也)他。“架”的方式不同,不要小看小學生,我們的創造力是極為豐富多彩的。有一個教師就被我們“架”走了。采用的方式是每個同學口袋里裝滿那幾棵大樹上結的黃色的小果子,這果子味澀苦,不能吃,我們是拿來做武器的。預備被“架”的老師一走進課堂,每人就從口袋里掏出那種黃色的小果子,投向老師。宛如舊時代兩軍對陣時萬箭齊發一般,是十分有威力的。老師知趣,中了幾彈之後,連忙退出教室,卷起鋪蓋回家。
假山對面,石徑左側,有一個單獨的大院子,中建大廳,既高且大,雄偉莊嚴,是校長辦公的地方。當年恐怕是大官的客廳,布置得一定非常富麗堂皇。然而,時過境遷,而今卻是空蕩蕩的,除了墻上掛的一個學生為校長畫的炭畫像以外,只有幾張破桌子,幾把破椅子,一副寒酸相。一個小學校長會有多少錢來擺譜呢?
可是,這一間破落的大廳卻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至今歷歷如在眼前。我曾在這里因為淘氣被校長用竹板打過手心,打得相當厲害,一直腫了幾天,胖胖的,刺心地痛。此外,廳前有兩個極大的用土堆成用磚砌好的花壇,春天栽滿了牡丹和芍藥。有一年,我在學校里上英文補習夜班,下課後,在黑暗中,我曾偷著折過一朵芍藥。這并不光彩的事,也使我憶念難忘,直至今天耄耋之年,仍然恍如昨日。
大廳院外,石徑盡頭,有一個小門,進去是一個大院子,整整齊齊,由東到西,蓋了兩排教室,是平房,房間頗多,可以供全校十幾個班的學生上課。教室後面,是大操場,操場西面,靠墻還有幾間房子,老師有的住在那里。門前兩棵兩人合抱的大榆樹,葉子長滿時,濃陰覆蓋一大片地。樹上常有成群的野鳥住宿。早晨和黃昏,噪聲鬧嚷嚷的,有似一個嘈雜無序的未來派的音樂會。
現在該說到我們的李老師了。他上課的地方就在靠操場的那一排平房的東頭的一間教室里。他是我們的班主任,教數學、地理、歷史什么的。他教書沒有什么特點,因此,我回憶不出什么細節。我們當時還沒有英文課,學英文有夜班,好像是要另出錢的,不是正課。可不知為什么我卻清清楚楚地回憶起一個細節來:李老師在我們自習班上教我們英文字母,說f這個字母就像是一只大蜂子,腰細兩頭尖。這個比喻,形象生動,所以一生不忘。他為什么講到英文字母,其他字母用什么來比喻,我都記不清了。
還有一件事情讓我至今難以忘懷。有一年春天,大概是在清明前後,李老師領我們這一班學生,在我上面講到的圓水池邊上,挖地除草,開辟出一塊菜地來,種上了一些瓜果蔬菜一類的東西。我們這一群孩子,平均十一二歲的年齡,差不多都是首次種菜,眼看著亂草地變成了整整齊齊、成壟成畦的菜地,春雨沾衣欲濕,杏花在雨中怒放。古人說:杏花、春雨、江南。我們現在是杏花、春雨、北國。地方雖異,其情趣則一也。春草嫩綠,垂柳鵝黃,真覺得飄飄欲仙。那時候我還不會“為覓新詞強說愁”,實際上也根本無愁可說,渾身舒服,意興盎然。我現在已經經過了八十多個春天,像那樣的一個春天,我還沒有過過,今後大概也不會再有了。
所有這一切,都是同李老師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此,眾多的小學老師,我只記住了李老師一個人,也可以說是事出有因了吧。李老師總是和顏悅色,從不疾言厲色。他從來沒有用戒尺打過任何學生,在當時體罰成風、體罰有理的風氣下,這是十分難得的。他住的平房十分簡陋,生活十分清苦。但從以上說的情況來看,他真能安貧樂道,不改其樂。
我十三歲離開新育小學,以後再沒有回去過。我不知道,李老師後來怎樣了,心里十分悔恨。倘若有人再讓我寫一篇《賦得永久的悔》,我一定會寫這一件事。差幸我大學畢業以後,國內國外,都步李老師後塵,當一名教師,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我當一輩子教員已經是注定了的。只有這一點可以告慰李老師在天之靈。
李老師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1996年7月
我和濟南
——懷念鞠思敏先生
說到我和濟南,真有點不容易下筆。我六歲到濟南,十九歲離開,一口氣住了十三年之久,說句夸大點的話,濟南的每一寸土地都會有我的足跡。現在時隔五十年,再讓我來談濟南,真如古話所說的,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
我想先談一個人,一個我永世難忘的人,這就是鞠思敏先生。
我少無大志。小學畢業以後,不敢投考當時大名鼎鼎的一中,覺得自己只配入“破正誼”,或者“爛育英”。結果我考入了正誼中學,校長就是鞠思敏先生。
同在小學里一樣,我在正誼也不是一個用功勤奮的學生。從年齡上來看,我是全班最小的之一。實際上也還是一個孩子。上課之余,多半是到校後面大明湖畔去釣蛙、捉蝦。考試成績還算可以,但是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名、第二名。對這種事情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但是鞠思敏先生卻給了我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個子魁梧,步履莊重,表情嚴肅卻又可親。他當時并不教課,只是在上朝會時,總是親自對全校學生講話。這種朝會可能是每周一次或者多次,我已經記不清楚,他講的也無非是處世待人的道理,沒有什么驚人之論,但是從他嘴里講出來,那緩慢而低沉的聲音,認真而誠懇的態度,真正打動了我們的心。以後在長達幾十年中,我每每回憶這種朝會,每一回憶,心里就油然而起幸福之感。
以後我考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校址在北園白鶴莊,一個林木茂密、綠水環繞、荷池縱橫的好地方。這時,鞠先生給我們上課了,他教的是倫理學,用的課本就是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書中道理也都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從他嘴里講出來,似乎就增加了分量,讓人不得不相信,不得不去遵照執行。
鞠先生不是一個光會賣嘴皮子的人。他自己的一生就證明了他是一個言行一致、極富有民族氣節的人。聽說日本侵略者占領了濟南以後,慕鞠先生大名,想方設法,勸他出來工作,以壯敵偽的聲勢,但鞠先生總是嚴加拒絕。後來生計非常困難,每天只能吃開水泡煎餅加上一點咸菜,這樣來勉強度日,終于在憂患中郁郁逝世。他沒有能看到祖國的光復,更沒有能看到祖國的解放。對他來說,這是天大的憾事。我也在離開北園以後沒有能再看到鞠先生,對我來說,這也是天大的憾事。這兩件憾事都已成為鐵一般的事實,我將為之抱恨終天了。
然而鞠先生的影像卻將永遠印在我的心中,時間愈久,反而愈顯得鮮明。他那熱愛青年的精神,熱愛教育的毅力,熱愛祖國的民族骨氣,我們今天處于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中國人民,不是還要認真去學習嗎?我每次想到濟南,必然會想到鞠先生。他自己未必知道,他有這樣一個當年認識他時還是一個小孩子,而今已是皤然一翁的學生在內心里是這樣崇敬他。我相信,我決不會是唯一的這樣的人,在全濟南,在全山東,在全中國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懷有同我一樣的感情。在我們這些人的心中,鞠先生將永遠是不死的。
1982年10月12日
憶念胡也頻先生
胡也頻,這個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學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閃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者很多很多,但在腦海中尚能保留其生動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
我有幸是後者中的一個。
我初次見到胡先生是六十年前在山東濟南省立高中的講臺上。我當時只有十八歲,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個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時日軍剛剛退出了占領一年的濟南。國民黨的軍隊開了進來,教育有了改革。舊日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改為省立高中。校址由綠柳紅荷交相輝映的北園搬到車水馬龍的桿石橋來,環境大大地改變了,校內頗有一些新氣象。專就國文這一門課程而談,在一年前讀的還是《詩經》《書經》和《古文觀止》一類的書籍,現在完全改為讀白話文學作品。作文也由文言文改為白話文。教員則由前清的翰林、進士改為新文學家。對于我們這一批年輕的大孩子來說,頓有耳目為之一新的感覺,大家都興高采烈了。
高中的新校址是清代的一個什么大衙門,崇樓峻閣,雕梁畫棟,頗有一點威武富貴的氣象。尤其令人難忘的是里面有一個大花園。園子的全盛時期早已成為往事。花壇不修,水池干涸,小路上長滿了草。但是花木卻依然青翠茂密,濃綠撲人眉宇。到了春天、夏天,仍然開滿似錦的繁花,把這古園點綴得明麗耀目。枝頭、叢中時有鳥鳴聲,令人如入幽谷。老師們和學生們有時來園中漫步,各得其樂。
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園門口旁邊,常見他走過花園到後面的課堂中去上課。他教書同以前的老師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講《古文觀止》,好像連新文學作品也不大講。每次上課,他都在黑板上大書“什么是現代文藝”幾個大字,然後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直講得眉飛色舞,濃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難懂了。下一次上課,黑板上仍然是七個大字:“什么是現代文藝?”我們這一群年輕的大孩子聽得簡直像著了迷。我們按照他的介紹買了一些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那時候,“馬克思主義”這個詞兒是違禁的,人們只說“普羅文學”或“現代文學”,大家心照不宣,誰都了解。有幾本書的作者我記得名叫弗里茨,以後再也沒見到這個名字。這些書都是譯文,非常難懂,據說是從日文轉譯的俄國書籍。恐怕日文譯者就不太懂俄文原文,再轉為漢文,只能像“天書”了。我們當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懷著朝聖者的心情,硬著頭皮讀下去。生吞活剝,在所難免。然而“現代文藝”這個名詞卻時髦起來,傳遍了高中的每一個角落,仿佛為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輝。
我們這一批年輕的中學生其實并不真懂什么“現代文藝”,更不全懂什么叫“革命”。胡先生在這方面沒有什么解釋。但是我們的熱情卻是高昂的,高昂得超過了需要。當時還是國民黨的天下,學校大權當然掌握在他們手中。國民黨最厭惡、最害怕的就是共產黨,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後快。在這樣的氣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張膽地宣傳“現代文藝”,鼓動學生革命,真如太歲頭上動土,國民黨對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胡先生卻是處之泰然。我們閱世未深,對此完全是麻木的。胡先生是有社會經歷的人,他應該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只見他那清瘦的小個子,在校內課堂上,在那座大花園中,邁著輕盈細碎的步子,上身有點向前傾斜,匆匆忙忙,倉倉促促,滿面春風,忙得不亦樂乎。他照樣在課堂上宣傳他的“現代文藝”,侃侃而談,視敵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沒有敵人的敵人陣中。
他不但在課堂上宣傳,還在課外進行組織活動。他號召組織了一個現代文藝研究會,由幾個學生積極分子帶頭參加,公然在學生宿舍的走廊上,擺上桌子,貼出布告,昭告全校,踴躍參加。當場報名、填表,一時熱鬧得像是過節一樣。時隔六十年,一直到今天,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如在眼前,當時的笑語聲還在我耳畔回蕩,留給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見了。
有了這樣一個組織,胡先生還沒有滿足,他準備出一個刊物,名稱我現在忘記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現代文藝的使命》。內容現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類。以我當時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從“天書”中生吞活剝地抄來了一些詞句,雜湊成篇而已,決不會是什么像樣的文章。
正在這時候,當時蜚聲文壇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濟南省立高中,看樣子是來探親的。她是從上海來的。當時上海是全國最時髦的城市,領導全國的服飾的新潮流。丁玲的衣著非常講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裝。相對而言,濟南還是相當閉塞淳樸的。丁玲的出現,宛如飛來的一只金鳳凰,在我們那些沒有見過世面的青年學生眼中,她渾身閃光,輝耀四方。
記得丁玲那時候比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濟南比不了上海,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內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況是高跟鞋。看來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難”的問題。胡先生個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維艱”,有時要扶著胡先生才能邁步。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看了這情景,覺得非常有趣。我們就竊竊私議,說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們其實不但毫無惡意,而且是充滿了敬意的。我們心中真覺得胡先生是一個好丈夫,因此對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對丁玲我們同樣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樣處之泰然,國民黨卻并沒有睡覺。他們的統治機器當時運轉得還是比較靈的。國民黨對抗大清帝國和反動軍閥有過豐富的斗爭經驗,老謀深算,手法頗多。相比之下,胡先生這個才不過二十多歲的真正的革命家,卻沒有多少斗爭經驗,專憑一股革命銳氣,革命斗志超過革命經驗,宛如初生的犢子不怕虎一樣,頭頂青天,腳踏大地,把活動都擺在光天化日之下。這確實值得尊敬。但是,勇則勇矣,面對強大的掌握大權的國民黨,是注定要失敗的。這一點,我始終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識到了。這個謎將永遠成為一個謎了。
事情果然急轉直下,有一天,國文課堂上見到的不再是胡先生那瘦小的身影,而是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師。全班學生都為之愕然。小道消息說,胡先生被國民黨通緝,連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秘密殺害,身中十幾槍。當時他只有二十八歲。
魯迅先生當時住在上海,聽到這消息以後,他怒發沖冠,拿起如椽巨筆,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兇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斗爭。”(《二心集》)這一段話在當時真能擲地作金石聲。
胡先生犧牲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如果他能活到現在,也不過八十七八歲,在今天還不算是太老,正是“余霞尚滿天”的年齡,還是大有可為的。而我呢,在這一段極其漫長的時間內,經歷了極其曲折復雜的行程,天南海北,神州內外,高山大川,茫茫巨浸;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在“空前的十年”中,幾乎走到窮途。到了今天,我已由一個不到二十歲的中學生變成了皤然一翁,心里面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胡先生的身影忽然又出現在眼前,我有點困惑。我真愿意看到這個身影,同時卻又害怕看到這個身影,我真有點誠惶誠恐了。我又擔心,等到我這一輩人同這個世界告別以後,腦海中還能保留胡先生身影者,大概也就要完全徹底地從地球上消逝了。對某一些人來說,那將是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在這里,我又有點欣慰:看樣子,我還不會在短期中同地球“拜拜”。只要我在一天,胡先生的身影就能保留一天。愿這一顆流星的光芒盡可能長久地閃耀下去。
1990年2月9日
我的老師董秋芳先生
難道人到了晚年就只剩下回憶了嗎?我不甘心承認這個事實,但又不能不承認。我現在就是回憶多于前瞻。過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師友,現在卻頻來入夢。
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濟南高中時的國文教員,筆名冬芬。胡也頻先生被國民黨通緝後離開了高中,再上國文課時,來了一位陌生的教員,個子不高,相貌也沒有什么驚人之處,一只手還似乎有點毛病,說話紹興口音頗重,不很容易懂。但是,他的筆名我們卻是熟悉的。他翻譯過一本蘇聯小說:《爭自由的波浪》,魯迅先生作序。他寫給魯迅先生的一封長信,我們在報刊上讀過,現在收在《魯迅全集》中。因此,面孔雖然陌生,但神交卻已很久。這樣一來,大家處得很好,也自是意中事了。
在課堂上,他同胡先生完全不同。他不講什么“現代文藝”,也不宣傳革命,只是老老實實地講書,認真小心地改學生的作文。他也講文藝理論,卻不是弗里茨,而是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都是魯迅先生翻譯的。他出作文題目很特別,往往只在黑板上大書“隨便寫來”四個字,意思自然是,我們愿意寫什么,就寫什么,愿意怎樣寫,就怎樣寫,絲毫不受約束,有絕對的寫作自由。
我就利用這個自由寫了一些自己愿意寫的東西。我從小學經過初中到高中前半,寫的都是文言文;現在一旦改變,并沒有感到有什么不適應。原因是我看了大量的白話舊小說,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魯迅、胡適、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說和散文幾乎讀遍了,自己動手寫白話文,頗為得心應手,仿佛從來就寫白話文似的。
在閱讀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在無意識中形成了自己對寫文章的一套看法。這套看法的最初根源似乎是來自舊文學,從《莊子》《孟子》《史記》,中間經過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都給了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靈感。這些大家時代不同,風格迥異,但是卻有不少共同之處。根據我的歸納,可以歸為三點:第一,感情必須充沛真摯;第二,遣詞造句必須簡練、優美、生動;第三,整篇布局必須緊湊、渾成。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文章的開頭與結尾,更是至關重要。後來讀了一些英國名家的散文,我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我有時甚至想到,寫文章應當像譜樂曲一樣,有一個主旋律,輔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後照應,左右輔助,要在紛紜變化中有統一,在統一中有錯綜復雜,關鍵在于有節奏。總之,寫文章必須慘淡經營。自古以來,確有一些文章如行云流水,仿佛是信手拈來,毫無斧鑿痕跡。但是那是長期慘淡經營終入化境的結果,如果一開始就行云流水,必然走入魔道。
我的這些想法形成于不知不覺之中,自己并沒有清醒的意識。它也流露于不知不覺之中,自己也沒有清醒的意識。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課堂上,我在“隨便寫來”的啟迪下,寫了一篇記述我回故鄉的作文。感情真摯,自不待言。在謀篇布局方面卻沒有意識到有什么特殊之處。作文本發下來了,卻使我大吃一驚。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頁上面的空白處都寫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這樣的話:“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等等。我真是如撥云霧見青天:“這真是我寫的作文嗎?”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認。“我為什么沒有感到有什么節奏呢?”這也是事實,不容否認。我的苦心孤詣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卻為董先生和盤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這決定了我一生的活動。從那以後,六十年來,我從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與文章寫作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劇烈的震動,所謂“心血來潮”,則立即拿起筆來,寫點什么。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積習難除,鍥而不舍。這同董先生的影響是絕對分不開的。我對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將伴我終生了。
高中畢業以後,到北京來念了四年大學,又回到母校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然後在歐洲待了將近十一年,1946年才回到祖國。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內,我一直沒有同董秋芳老師通過信,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情況。50年代初,在民盟的一次會上,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竟見到了董先生,看那樣子,他已垂垂老矣。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也非常激動。但是我平生有一個弱點: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董先生看來也是如此。我們每個人心里都揣著一把火,表面上卻頗淡漠,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概了。
我生平還有一個弱點:我曾多次提到過,這就是,我不喜歡拜訪人。這兩個弱點加在一起,就產生了致命的後果,我同我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師的關系,看上去有點若即若離了。
不記得是什么時候了,董先生退休了,離開北京回到了老家紹興。這時候大概正處在“十年浩劫”期間,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自顧不暇,沒有余裕來想到董先生了。
又過一些時候,聽說董先生已經作古。乍聽之下,心里震動得非常劇烈。一霎時,心中幾十年的回憶、內疚、苦痛,驀地抖動起來,我深自怨艾,痛悔無已。然而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無法挽回的。看來我只能抱恨終生了。
我雖然研究佛教,但是從來不相信什么生死輪回,再世轉生。可是我現在真想相信一下。我自己屈指計算了一下,我這一輩子基本上是一個善人,壞事干過一點,但并不影響我的功德。下一生,我不敢,也不愿奢望轉生為天老爺,但我定能托生為人,不致走入畜生道。董先生當然能轉生為人,這不在話下。等我們兩個隔世相遇的時候,我相信,我的兩個弱點經過地獄的磨煉已經克服得相當徹底,我一定能向他表露我的感情,一定常去拜訪他,做一個程門立雪的好弟子。
然而,這一些都是可能的嗎?這不是幻想又是什么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悵望青天,眼睛里溢滿了淚水。
1990年3月24日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