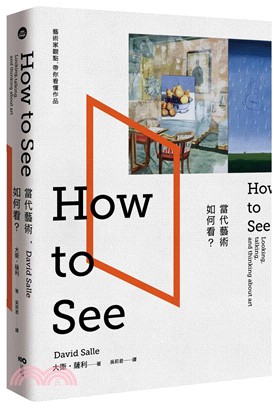當代藝術,如何看:藝術家觀點,帶你看懂作品
- 系列名:Plus art
- ISBN13:9789579072021
- 替代書名:How to See:Looking, talking, and thinking about art
- 出版社:原點
- 作者:大衛‧薩利
- 譯者:吳莉君
- 裝訂/頁數:平裝/304頁
- 規格:23cm*17cm*2.2cm (高/寬/厚)
- 重量:477克
- 版次:1
- 出版日:2018/02/06
- 適性閱讀分級:597
商品簡介
好藝術,如何看?
當代藝術就是布滿專業術語的地雷區
該相信你的眼睛?藝評評價?藝術史論斷?還是市場賣價?
紐約最前線、美國80年代新表現主義大將
塗鴉藝術家巴斯奇亞、凱斯˙哈林同代人、普普大師李奇登斯坦好友
重返20世紀藝術現場,說出藝術家們的激辯、交心、回憶與自白
歷經觀念|行動藝術洗禮後的新觀看之道
繼約翰˙伯格《觀看的方式》,又一精彩觀點的經典之作
關於藝術的「如何」論戰,沒人比大衛˙薩利探索得更棒。──作家˙魯西迪
◎什麼因素讓當代藝術滴答運作?什麼因素讓它變成好藝術?又是什麼因素讓它顯得有趣?
自杜象1917年在小便斗上簽名後,撼動了繪畫主導的藝術世界。視覺藝術的變化速度日益加快,未來主義、構成主義、新地理、機制批判、非具象主義、表現主義、抽象表現主義、低限主義、新表現主義等新名詞大量繁殖,當代藝術成了布滿專業術語的地雷區,這些術語就像是為了將欣賞者淘汰出局而設計的。
◎近五百年後,再度挑戰「藝術家談藝術家」
美國80年代最重要的新表現主義大將:大衛•薩利(David Salle),試圖扭轉一般人被藝評家阻隔於現代藝術之外的現況。身為塗鴉藝術家巴斯奇亞和凱斯˙哈林的同代人,及普普大師李奇登斯坦的好友,他想用藝術家聚在一起聊天的語言談論當代藝術,說出一位創作人面對藝術世界這四十年來天翻地覆驟變的真心話。他是繼1550年義大利藝術家瓦薩利,時隔近五百年後,再度挑戰藝術家談藝術家的後繼者。文集收錄的主題,從當代指標型人物到歷史人物皆有。許多是作者的同代人,有些更是認識幾十年的好友、同學。
藝術家講話的方式與記者不同,記者習慣把焦點擺在周圍脈絡、市場、觀眾等等,也跟學術評論不同,評論家會根據理論宣稱自己說法的正當性。這兩種都是宏觀敘事。但藝術家不一樣,他們談的是什麼有效,什麼沒效,為什麼。他們的焦點比較微觀;是由內往外推。
◎假如藝術會說話,如何區別哪些是真話?
大衛˙薩利在書中舉例:
「Case 1.──曾經有個電視節目叫做《信不信由你!》。其中一集,令人印象深刻,內容是有個傢伙說他把自己的車子吃掉了。他花了四年的時間,方法是把車子剁成碎片,每天吃掉一小塊,這個傢伙想辦法把整輛車都吃進肚子,包括方向盤、鉻鋼、輪胎,全部。用現在的觀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創造藝術。」
「Case 2.──今天當代藝術分成兩大陣營。一邊是存在好幾百年不曾間斷的圖像性藝術;另一邊是數量正在增加的展演性藝術。我們不願面對的真相是:展演藝術比創作藝術容易。挑選比創新容易。想做出真正吸引目光的東西,需要獨一無二的充沛活力把知識、視覺和文化的面向整合起來。迴避這項整合工作的藝術,不太可能長久吸引人們的關注,因為它下的賭注比較少。當你心存僥倖,不敢繃到極限,情感的力道就會減弱。」
吃車子是藝術嗎?面對觀念藝術,繪畫究竟太傳統,抑或更凸顯其獨有唯一性,仍具突破空間?複製品、模仿作,與原作有差別嗎?為什麼我們對某些藝術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對被評論的藝術家來說,是否認同藝評人的專家眼力?當我們欣賞一件當代作品時,要如何看出好壞?普普藝術大師李奇登斯坦,私底下如何評價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如何的「很不」安迪˙沃荷?市場價格等於藝術價值嗎?藝術家Jeff Koons被諷刺媚俗,他的作品是否只是譁眾取寵?與英國藝術家Hirst比起來,在話題之外,誰的藝術性耐久?這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疑問,該怎麼說,怎麼想?
關於這些思考,作者歷經了四十年的寫作摸索。從1975年初到紐約,用寫作支付房租,到1980、1990年代,改以一種懶人版的書寫形式進行採訪。最後,他採用最老派的方式,不採訪,純粹獨立書寫。「我發現,書寫可以幫助我理解對某件事情的真正想法,最後變成一種習慣,很難戒除。」
本書的架構分為四部分:「如何為想法賦予形式」、「當個藝術家」、「世間藝術」和「教學與論戰」。
最後一篇也可稱為「給年輕藝術家的建議」,包含一些可在課堂上或私下進行的習作。設計這些習作的目的,期待讀者從自身的連結、描述和類比中找到樂趣,帶領「一般讀者」摸清藝術家心思,不需太多專業配備,就可抵達藝術意義的核心。
◎國內專業推薦、名家推薦語(按姓氏筆畫排序)
胡朝聖∣胡氏藝術公司執行長
張世倫∣藝評人
張君懿∣藝術家、策展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兼任助理教授
陳敬元∣藝術家
黃亞紀∣亞紀畫廊負責人
劉惠媛∣策展人、藝術評論作者、臺灣數位文化科技與藝術學會執行長
龔卓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卸下當代藝術令人諱莫如深的專業術語,以直接、自然的口吻提供讀者欣賞藝術天馬行空的表現。」──胡朝聖(胡氏藝術公司執行長)
「透過大衛直觀又透澈的筆尖,揉合充滿溫度和歷史厚度的色彩。我似乎進入每個創作者的意識,用他們的筆觸描繪出一幅幅世代繪畫的圖像。」──陳敬元(藝術家)
「我經常說,好懂的藝術只有很貴的與很差的兩種,因多數人只關心「什麼」而非「怎麼」。本書讓你擦亮眼睛。」──黃亞紀(亞紀畫廊負責人)
「假使藝術會說話,我們要如何學會區別那些是真話?除了好奇、觀看與直覺,我們所認識的藝術大多是來自於藝術家本人、評論、媒體、策展人和收藏家的口耳相傳,透過作者幽默機智的文筆,重返藝術現場,聆聽二十世紀現代藝術精彩的談話。」──劉惠媛(策展人、藝術評論作者、臺灣數位文化科技與藝術學會執行長)
「本書以親密對話的文體,讓讀者猶如置身小酒館、咖啡屋與工作室,聆聽藝術家們對當代藝術的激辯、交心、回憶與自白。」──龔卓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國外如潮佳評
「如果說約翰•伯格的《觀看的方式》是藝術評論的經典,探究了藝術是『什麼』,那麼大衛•薩利的《當代藝術,如何看》就是藝術家給的答覆,告訴觀者該『如何看』。篇篇精彩的文章談論藝術家在創作時,他們想什麼? 關於藝術的『如何』論題,或許從來沒人比他探索得更棒。」──作家˙魯西迪
「一流的藝評有很多是由藝術家所寫的,是那種最不掉書袋,也不會只把藝術家當成棋子來看待的評論文章。大衛•薩利正是這類藝評者,他不問這是不是藝術?屬於哪種派別?而是問它讓我有什麼感受和思考?他的藝術作品經常被標籤為前衛,一種概念上的立場聲明,他巧妙地且以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提醒我們,所有的藝術,即使表面上看來桀驁不馴,也都等著被觀看,而藝術家做的正是教我們怎麼觀看。」──美國作家˙亞當•高普尼克 Adam Gopnik
「大衛•薩利被認為是創作前衛且聰明的畫家,但他的這本書帶給我們的驚喜更多。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是一場場精闢且近身的觀察手記。他認為新藝術源自古藝術,他在書中將不可親近的大師召喚前來,(當他提到他當代的朋友Alex Katz和Jeff Koons時),讓他們有了生動的形象和親近感。身為畫家,薩利似乎以身為藝術家大家庭的一員而感動且自豪,並從他所謂的『共享的藝術DNA』中推導他的繪畫形式,提升了所有傑作其實都是同一組創作的可能性。」──藝評家˙Deborah Solomon
作者簡介
大衛‧薩勒|David Salle
作品獲MoMA、惠特尼美術館、古根漢美術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倫敦泰德美術館等,永久典藏。
生於1952年,他是20世紀最重要的美國新表現主義畫家之一,八○年代回歸具象派的領軍人物。1972年獲瓦倫西亞加州藝術學院碩士學位。1975年首度於洛杉磯舉辦個展。
他的具象作品大膽融合互不相關的因素,「打破圖像(Image)與意義(Meaning)的隔閡」。這些被齊聚一起的形象,來自各種大眾傳播媒體,在他雙幅畫布構成的作品中,形成對立性的主題和宏大的氣勢。
【譯者簡介】
吳莉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譯有《觀看的方式》、《觀看的視界》、《我們在此相遇》、《持續進行的瞬間》、《建築的法則》、《包浩斯人》、《設計是什麼?》、《當代建築的靈光》、《好電影的法則》、《光與影》、《建築的危險》、《建築的語言》、《剖開世界現代建築》等書。任職出版社多年,現為自由工作者。
序
導言
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除了是德庫寧之外,也是個英語天才,他曾把賴瑞‧李佛斯(Larry Rivers)的一幅畫比喻成「把你的臉壓在濕草地裡」。亞歷克斯‧卡茨(Alex Katz)是另一位形容大師;他那些脫口而出的觀察真是既大膽又精準。一件失敗的畫作可能會被診斷為「沒有內在能量」;為富麗堂皇傷腦筋的畫家是「第一流的裝潢師」;而國際舞台上的知名玩家則是在創作「披薩店藝術」。並不是所有藝術家都這麼口才便給或直言無諱,但我認識的藝術家,多半都很會講話——除了在座談會上,他們害怕學歷不夠會讓自己的看法聽起來有點蠢。我知道,因為我就是這樣。
這本書的構想,是想用藝術家聚在一起聊天時會用的語言來談論當代藝術。我們講話的方式跟記者不同,記者習慣把焦點擺在藝術周圍的脈絡、市場、觀眾等等,也跟學術評論不同,評論家會根據理論宣稱自己的說法具有正當性。這兩種都是宏觀敘事(macronarrative),關心的都是整體全貌。藝術家就不一樣了,他們談的是什麼有效,什麼沒效,為什麼。他們的焦點比較微觀;是由內往外推。偉大的反骨影評人曼尼‧法柏(Manny Farber)在〈白象藝術vs.白蟻藝術〉(White Elephant Art vs. Termite Art)這篇文章裡,簡明扼要地說出兩者的差別。法柏用白象藝術來形容那些充滿自覺的傑作,披掛著偉大的主題和滿滿的內容。例如,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Antonioni)的《情事》(L’Avventura)。白蟻藝術家則是化身為導演山繆‧富勒(Samuel Fuller),他在1950和1960年代拍過好幾十部亂七八糟的低成本電影。富勒原本是個漫畫家,他自己寫劇本,用的是實景、B咖演員和手邊現成的東西。他電影裡那種瘋狂的美,簡直就像是急切難耐的副產品。不用說,法柏當然是站在鑽土的白蟻那邊。他偏愛的藝術家,往往都是在黑暗中獨自挖掘地道,通往他們的目標,並不怎麼關心地面上發生的事。
自從杜象(Duchamp)在上個世紀初讓藝術與視網膜經驗斷開關聯之後,人們對於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關係就有了誤解。過去四十年的評論文章,主要都是關心藝術家的意圖(intention),以及這樣的意圖如何闡明了當時的文化關懷。藝術被當成意見書,藝術家則是扮演落魄哲學家(philosopher manqué)的角色。雖然這種尊崇是某些人應得的,但是把意圖當成關注焦點,卻造成了許多混淆和一廂情願。今天,你去拜訪任何一所名列前茅的藝術學校,都會發現一個共同現象:藝術家的意圖比他們的實踐能力重要多了,也比作品本身重要多了。理論說得頭頭是道,具體的視覺感受卻低靡不振。在我看來,意圖不僅被高估了,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就像把馬車擺在馬匹前面老遠的地方,讓馬匹感覺到自己無能為力,乾脆放棄,直接躺在街上算了。「意圖」是一個彈性十足的字眼;它可以代表各式各樣的目的和野心。對風格影響更大的,是藝術家如何維持自身與意圖之間的關係。這聽起來有點複雜,其實不然。一個人如何拿筆刷會決定很多事情。意圖確實重要,但是牽引藝術家之手的那股脈動(impulse),往往和展示牆上的說明不同,甚至是完全無關的類型。我把這稱為實用主義(pragmatism)。就像紐約學派詩人法蘭克‧歐哈拉(Frank O’Hara)用他的招牌熱情在《個人主義宣言》(Personism: A Manifesto)裡所寫的:「這只是常識:如果你打算去買一條褲子,你會希望它夠緊,緊到每個人都想跟你上床。這裡頭沒有任何形上學。」
長久以來,藝術家一直和各形各色的想法概念有關,但是真正的大想法大概念(big idea)並不多見,久久才會出現一回。美國芭蕾之父喬治‧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編的舞碼密覆著滿滿想法,關於現代性、音樂性、節奏、時尚、抽象、信仰、新女性,等等,但他不愛談論這些。他跟傳記作者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要對方想像自己正在撰寫「一匹賽馬」的故事。他的想法全都顯現在風格裡。在我們這個時代,一般大小的想法,也就是大多數的想法,其實都很簡單。再次引用法蘭克的說法:「就只是想法而已。」閃過我們腦海的想法,經過仔細檢查之後,會發現很多都是宣傳——是某人想要某樣東西,想要推銷某樣東西。難的是如何找到形式。最引人注目的作品,往往都是思維(thinking)與作為(doing)無法分割的作品。
我們當中不乏有大想法的人,但那些想法通常都是說給好騙的收藏家或自己聽的。大想法沒什麼錯,但它們和找出有效的做法沒多大關聯——或根本沒關聯。我很懷疑,有誰曾經因為一幅畫可能蘊含的想法而愛上它,但反過來的情況倒是有一大堆。有能力解釋一件藝術作品,以它為中心編出一則故事,並不會讓它變成好作品。好意圖同樣也沒多大幫助。藝術沒這麼簡單。已故雕塑家肯‧普萊斯(Ken Price)說得最好:「不管我說什麼都不可能讓它看起來更好。」
有時,我們所謂的想法其實更像是一種熱情,一種短暫的知性氣象。藝術家是好奇寶寶,會追求各式各樣晦澀難解的知識。有些人喜歡做研究,而藝術似乎就跟其他所有地方一樣,是展現自身興趣的好所在。持久有力的想法,都是和藝術家喜愛的形式有交集的想法,能夠加深它,擴張它,就像你把紙花放進水裡就會綻放那樣。對的想法,也就是可以和才華同步生產的想法,能打開一整個世界觀。如果那個想法碰巧又是文化大環境或時代精神正在塑造與傳播的感性的一部分,在加乘效應的運作之下,藝術就能跟觀看大眾產生強烈共鳴。我們會覺得,藝術表達了我們。
對於這種同步感的渴望,會促使某些藝術家還有藝評家,想要預先找出那個大想法。在實務層面上,其實不可能事前規劃出這樣的共鳴,因為裡面牽涉到太多因素。基於性格關係,我對那種太過直接想要表現當下文化的藝術,都會有所警戒。此外,當那個時刻過了,還有什麼能留下呢?大多數藝術都會投射出一種活力感,回應當下情境的某一部分,文化的、歷史的或知識的,因為藝術家在裡頭看到自己;幾乎不可能有別種情況。不過這種呼應很少是一對一的。藝術如果是用來支持某個得到認可的立場,或是用來闡述今天的頭條新聞,賞味期通常都很短。如果好的藝術真有闡述任何事情,大概也就是一則故事,一則你甚至不知道有必要講的故事。
那麼藝術到底是什麼?我們需要知道嗎?難道我們不能滿足於約翰‧巴德薩利(John Baldessari)的名言:「藝術就是藝術家做的東西」,別再去追究嗎?這定義確實有點廣。收錄在這本文集裡的文章,就是從這個前提開始:藝術是某人做的某樣東西。藝術就在事物裡(Art in Things),這是建築師查爾斯‧沃伊塞(Charles Voysey)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為美術與工藝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打造的信條,今日聽起來還是很不錯。因為藝術,即便是所謂的觀念藝術,也都是一種事物。某人做出某樣東西,或讓那樣東西製作出來,都具有某些特質。那些特質和藝術家的意圖有關,但因為它們是寄存在物質形式裡,所以說著不同的語言。
如果你覺得這似乎有點反智,我會告訴你,我們這個物種(在這點上,其他生物也是)有很多不同類別的聰明才智,而你在舞者的舞句組合、詩人的格律運用、畫家的筆刷運轉和音樂家的即興創作裡所能發現的聰明才智,並不比知識上聰明才智更不重要,它們只是更難描述罷了。勉強能做出描述的,只是那些可感知的效應,擴大我們對藝術的整體感覺。藝術不僅是文化符號的總和:它是一種既直接又有聯想性的語言,而且跟其他的人類溝通方式一樣,有它的文法和語法。仔細觀察某人製作出來的東西,觀察它的所有細節,這樣才能激發出真誠由衷而非有條件的回應。
自從十九世紀現代主義問世以來,視覺藝術的變化速度日益加快,需要用比較廣泛、正式的類別來說明風格問題。就像球賽的記分卡一樣,可用來追蹤球員的表現。有些時候,名稱是藝術家自己選的,例如未來主義(futurism)或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但是,有誰想被叫做野獸(fauve)呢?至於「新地理」(neo-geo)或「機制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這類複合名詞,根本就是用來懲罰和羞辱人的。今日聽到的藝術談話,大多是以類別(category)做為導航,而這些類別都是源自於某種歷史決定論,認為風格多少都是有意識的,有黨派觀念的,表現出對於不斷變化的藝術本質或功能的想法。我們都有過一張風格版的王朝遞嬗表,每一個風格都取代了前面的風格:非具象主義(nonobjectivism)、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低限主義(minimalism)、觀念主義(conceptualism)、新表現主義(neo-expressionism)——這張清單還可一直列下去。此外,還要加上許多當前正在使用的非視覺類別,源自於法國批判理論和它的諸多變體: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酷兒理論,等等。如果藝術是名詞,那些批判理論的字眼就是形容詞。這些類別全都有用,甚至具有啟發性,但是沒有一個可以告訴我們,卡茨口中的藝術內在能量有什麼特別,唯有仔細觀察一件作品的具體細節,你才能接觸到那股能量——緊身褲和諸如此類的。
由於這些廣義的風格根深柢固,有點難想像其他替代品。倘若不借助這些「主義」,或不訴諸一般性,是要怎麼談論藝術呢?要去哪裡尋找一個詞彙來傳達觀看的滋味呢?美國記者和小說家凱薩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在1928年寫過一篇文章,談論葛楚德‧史坦(Gertrude Stein)這位偉大的典範轉移者,她觀察到,敘事並不是史坦小說的驅動力量。波特認為這點很有趣。史坦關心的是她所謂的人的底蘊(bottom nature);一種存在於其他屬性之下的特質,對史坦這位作家而言,底蘊非常重要,因為它會大致決定一個人在世上的作為。波特用神來一筆的批判性自由聯想,拿史坦和十六世紀的日耳曼煉金師和神學家雅各‧伯麥(Jacob Boehme)做比較,伯麥依照基本元素把人分門別類。他根據一種早期的週期表把人性做了排列,用一個物理實體或現象來對應一種個性。「伯麥識人為鹽或汞,濕或乾,燃或煙,苦或酸或甜。」四百年後,史坦把人描述為「攻擊或抵抗,依賴或獨立,有木芯或有泥芯」。對她而言,好壞、對錯都是屬性,就像腰身或小下巴;強和弱則是活在人體內的真實東西。史坦的寫作是以極為個人化的觀察形式為基礎,她的一生都在觀察人們如何行為,觀看事情如何運作,根據這樣的人生經歷做出推斷。一個人戴帽子的方式和他是哪種人只有些微差異。唯有「咄咄逼人的人」才會戴這種帽子。唯有「聰明的人」才會畫出那種作品。我認為,史坦描述性格的方法很適合用來談論藝術。
三十年後,畫家暨典範評論家費爾菲德‧波特(Fairfield Porter,和凱薩琳‧安妮‧波特無關)說得更精準:「對繪畫和雕刻而言,真實而普通的反應通常都非常準,就像你對初識者的第一印象。」這是他在1958年寫的,至今依然適用。我們常常把某些畫形容成老朋友,不是沒有原因的。藝術會跟我們說話,這是怎麼一回事?怎麼解釋我們對藝術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簡直就像是作品正在等我們,因為它預料到我們可以跟它的深層音樂結合?這跟你可以直覺感受到的某種東西有關,就像你遇到任何人時可能會有的那種直覺。欣賞畫作的方法之一——這裡我用畫作代表所有視覺藝術——就是在你打量它時,注意你對它的真實想法是什麼,這可能跟你原本以為你會有的想法不一樣。許多寫藝術或談藝術的人,眼力並沒特別好,以前這讓我很驚訝,但現在不會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針對藝術應該告訴我們什麼發表一些誇大的說法;你要學會篩選。展牆上的說明牌可能告訴你,這件作品是藝術家針對表演策略的符號學所做的調查,而你發現你正在想,不知道咖啡館的食物好不好吃。我們要關注的是,藝術作品真正做了什麼——不管它原本的意圖可能是什麼。那麼,我們要如何學會區別?我學到的有關藝術的一切,大多是來自於觀看、創作、再次觀看,也來自於聆聽一些非常精彩的談話,這些談話總是會讓藝術圈的空氣充滿活力。
1975年,我來到紐約,開始用寫作支付房租。我追隨唐納‧賈德(Donald Judd)之類的前輩藝術家,為現在已經停刊的《藝術雜誌》(Arts Magazine)撰寫短評。評論的稿費一篇三十美元;我的租金是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你可以一個月寫幾篇評論,接一些安裝石膏板的工作,勉強餬口。當時的雜誌編輯叫做理查‧馬丁(Richard Martin),長的有點像時尚設計師聖羅蘭(Yves St. Laurent):三件式西裝、飛行員眼鏡、有層次的髮尾。他後來變成流行設計學院(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策展人,在那裡辦了幾場石破天驚的展覽,包括為克萊兒‧麥卡德(Claire McCardle)策畫的第一場博物館展出,她是美國女性運動服飾的設計先驅。理查很會鼓勵人,把我當大人看(我當時二十二歲)。那本雜誌其實沒做什麼編輯,只是把文章匯整起來而已。我想評什麼都可以,印象中我的文章都沒被修改過。那些文章寫得很糟,很費力,很難懂——本書只收錄其中一篇有關維多‧阿孔奇(Vito Acconci)的——但它們是我最早的嘗試,企圖找出一條獨立的道路來談論藝術。
1980和1990年代的大多數時間,我都是用一種我所謂的懶人版書寫形式進行採訪,但那種形式限制很多。最後,我開始用老派的方式寫作,也就是說,得不到對談者的幫忙。我發現,書寫可以幫助我理解我對某件事情的真正想法。書寫以某種方式完成這個循環。最後它變成一種習慣,很難戒除。(我八成有個祕密願望是要當專欄作家——就是那種幼稚荒謬、浪漫無疑的奇想之一,就像我八歲時的抱負是要當鋼琴作曲家,雖然我沒有半點音樂天分。那個時候,別說彈鋼琴了,我甚至沒跟鋼琴待在同一個房間過。)然後有天一覺醒來,發現我真的是個專欄專家了,有交稿日期為證。就某方面而言,這是一種奇怪的野心——書寫其他藝術家的作品,特別是同一個時代的藝術家。這種事在文學界幾乎算是一種社交禮儀,非做不可,但是在視覺藝術圈就不一樣,自從1550年喬吉歐‧瓦薩利(Giorgio Vasari)試過身手之後,幾乎沒什麼後繼者。不用說,當一個藝術家坐下來書寫另一個藝術家時,他當然也是在書寫自己。他必然是用自己的感性書寫,如果他夠誠實的話,也一定會把自己放在故事裡的某個地方。
本書收錄的文章大多是幫雜誌寫的:《城鎮與鄉村》(Town & Country)、《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採訪》(Interview)、《藝術新聞》(ARTNews)和《藝術評論》(Artforum)。其他則是為展覽專刊寫的。收錄在「教學」裡的那幾篇,包括課堂練習和演講,則是首次出版。不管發表在哪裡,我都試圖提供一條通道,讓讀者進入作品的感覺和意義核心,一如我自己對它們的體驗,也希望在藝術家的創作內容和我們的生活經驗之間指出一些相同之處,一些我們都能體認或想像的情感交流。這些文章以不同方式提出以下問題:什麼因素讓藝術作品滴答運作?什麼因素讓它變成好藝術?又是什麼因素讓它顯得有趣?再一次,不必把問題想得太複雜。我知道有些人覺得,當代藝術就是布滿專業術語的地雷區,那些術語根本就是為了把他們淘汰出局設計的。我希望「一般讀者」,也就是對這主題略有興趣的任何人,能在這些文章裡找到反證:不需要太多專業配備也可抵達藝術意義的核心。
◎架構註記
這本文集收錄的主題從指針型人物到歷史人物都有,前者像是約翰‧巴德薩利和亞歷克斯‧卡茨,後者包括安德烈‧德漢(André Derain)與法蘭西斯‧畢卡比亞(Francis Picabia)等。其中有許多是我的同代人,有些更是認識好幾十年的藝術家。有幾位是同學,幾位是朋友。(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可以寫熟識之人的作品。)這本書的架構分為四部分:「如何為想法賦予形式」、「當個藝術家」、「藝術究竟」和「教學與論戰」。最後一篇也可稱為「給年輕藝術家的建議」,包含一些可以在課堂上或私下進行的習作。設計這些習作的目的,是要讓讀者從自身的連結、描述和類比中找到樂趣。何不做做看?
目次
導言
第一篇 如何為想法賦予形式
亞歷克斯‧卡茨:「怎麼」和「什麼」/愛咪‧席爾曼:當代行動畫家/克里斯多夫‧伍爾:自備麥克風的繪畫/德國奇蹟:西格馬‧波爾克作品/羅伯‧戈柏:心不是隱喻/阿爾伯特‧厄倫:好學生/黛娜‧舒茲:法蘭克那傢伙/羅伊‧李奇登斯坦:改變是困難的/童年藝術:傑夫‧昆斯在惠特尼/約翰‧巴德薩利的電影劇本系列/成功基因:韋德‧蓋頓和蘿絲瑪麗‧特洛柯爾
第二篇 當個藝術家
維托‧阿孔奇:身體藝術家/約翰‧巴德薩利的小電影/卡蘿‧阿米塔姬和合作的藝術/攝影機眨眼睛/老傢伙繪畫/摔角選手:馬斯登‧哈特利、菲利浦‧加斯頓和克里福德‧史提爾/烏爾斯‧費舍爾:廢物管理/傑克‧戈德斯坦:抓緊救生艇/悲傷小丑:麥克‧凱利的藝術/法蘭克‧史帖拉:在惠特尼/沒有首都的地方風格:湯瑪斯‧豪斯雅戈的藝術/費特列克‧圖頓:挪用的藝術
第三篇 世間藝術
安德烈‧德漢與庫爾貝的調色盤/畢卡比亞,是我/小貝比的大巨豆/美妙的音樂:芭芭拉‧布魯姆的藝術/結構興起/皮埃羅‧德拉‧法蘭契斯卡
第四篇 教學與論戰
1980年代,到底好在哪?:密爾瓦基美術館講座/開學日致詞/藝術不是比人氣:2011年紐約藝術學院畢業演講/沒有答案的問題:獻給約翰‧巴德薩利
◎版權出處
書摘/試閱
〈1980年代,到底好在哪?〉
我差不多七、八歲的時候,有個電視節目叫做《信不信由你!》(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其中有一集我印象特別深刻,內容是有個傢伙說他把自己的車子吃掉了。他花了四年的時間,方法是把車子剁成碎片,每天吃掉一小塊,這個傢伙想辦法把整輛車都吃進肚子,包括方向盤、鉻鋼、輪胎,全部。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創造藝術。
這就是今天的情況。當代藝術可分成兩大陣營。其中一邊存在連綿好幾百年不曾間斷的作品,我稱為圖像性(pictorial)藝術;另一邊的數量正在增加,在態度上比較是展演性的(presentational),也就是說,因為意圖和傳遞系統或藝術脈絡而顯得特別的藝術。在這兩種世界觀裡,一種把藝術界定為自我表現,另一種則主要是把藝術解讀為一組文化符號。這聽起來有點像是杜象對於視網膜和大腦的老派分法,但是這個天平的傾斜程度,是六十年前的杜象很難想像的。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因為強調理論而讓藝術的一條基本誡規失去功效,或說受到嚴重侵蝕,那就是以往所謂的臨在(presence),或靈光(aura)。說得直白一點,一件藝術作品之所以能散發靈光,是因為藝術家把能量轉移到作品上,一種美學版的熱力學原則。今天,很少人會去捍衛這種說法。問題是,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替代呢?
最近,我去蘇黎世造訪友人布魯諾‧畢曉夫伯格(Bruno Bischofberger)的宅邸,他是位大收藏家,也是挪用派藝術家麥克‧畢德羅(Mike Bidlo)的經紀人。在布魯諾的客廳,有一扇窗戶面對蘇黎世湖的景色,窗戶旁邊擺了畢德羅模仿杜象的腳踏車輪。你知道嘛,就是那個上下顛倒安裝在一張簡單木凳上的車輪。杜象的原作本來就是用可以買到的商業品組裝而成,畢德羅仿製的腳踏車輪雖然和原作一模一樣,但卻缺乏「臨在」;事實上,它就跟釘死的門釘一樣死。奇怪——為什麼會這樣?它明明就是一模一樣的摹製品啊!我們站在布魯諾的客廳,看著畢德羅的這件雕刻時,布魯諾的太太幼幼(Yoyo)提出一項精闢觀察:「藝術家的作品有的有臨在感,有的沒臨在感,雖然任何東西都可以有臨在感,但沒有任何東西必然會有臨在感。」這聽起來好像魔法,但是看著杜象的腳踏車輪原作——在這個案例裡,原作是個有趣的字眼——你會感到滿足。它有一種靈光。但這個摹製品就不然。單用脈絡,以及隨之而來的預期,真的足以解釋其中的差異嗎?
老派觀點和後來追隨杜象的許多徒子徒孫的觀點,兩者的差異不只是表現的藝術和抽離的藝術,或是暖藝術和酷藝術之間的分別;酷藝術也可能是極為圖像式的,而許多藝術,也許該說我們記得的大多數藝術,都會設法讓自己同時具有圖像性和展演性。就跟生命中的許多事物一樣,這是把重點放在哪裡的問題,換句話說,是一種感性問題。藝術經常是想法的產物;關於空間和物質性;文化史和認同;時間和敘事;再現風格和影像本質等等。在我們今天依然會談論的藝術裡,這些想法都是由形式來體現。當然,在藝術裡沒有什麼東西是非此即彼;甚至連這個說法本身都可以是矛盾的。大多數的圖像性藝術也都包含某種展演性的成分。展演性會以某種方式包含在裡頭。成熟洗練的繪畫都是具有自覺的,它們會表現自我。事實上,我會說,藝術就是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彼此牽制。
然而,自從1968年杜象去世隨之被奉為聖人之後,展演性的藝術開始暴增;開始取得上風。隨著當代藝術的觀眾逐漸增長,受過大學教育的藝術家快速膨脹,以傳輸系統(delivery system)本身做為努力目標的藝術,開始蓋過傳輸內容的風采。這種藝術走向之所以繁榮興盛,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跟簡單的人口統計學有關:去唸藝術學校和參與策展工作的年輕人大幅增加。另一個原因也是受到人口統計學影響,那就是國際藝術博覽會和雙年展的旅遊模式興起——藝評家彼得‧施捷爾達(Peter Schjeldahl)把這稱為「節慶主義」(festivalism)。藝術的脈絡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形塑了它的產物。
我們也看到有種藝術大量繁殖,該種藝術的功能就是用來傳輸某種具體清晰的內容。你們聽過那個笑話,有人問畫家他的作品有什麼意含時,畫家回答:「如果我想傳送訊息,我會打電話給西聯電報(Western Union)。」在1930年代的社會寫實主義繪畫裡,我們對作品的評斷,是根據它對階級衝突發表了什麼樣的看法。今天的視覺元素已經改變,但我們還是習慣用作品承載了哪些訊息做為評判標準。
坦白說,展演式藝術的大量增生讓我的心情隨之下沉。我們不願面對的真相是:展演藝術比創作藝術容易。挑選藝術比創新藝術容易。這麼說可能會把你們搞糊塗,因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幾個圖像創新者,例如安迪‧沃荷等,看起來除了挑選之外什麼也沒做——但這是錯覺,借用美容業的說法,你在化妝椅上畫了半天,就是為了化出看似沒化的自然妝容。想做出真正能吸引目光的東西,特別是要讓人重複觀看的東西,需要用獨一無二的充沛活力把知識、視覺和文化的面向整合起來。迴避這項整合工作的藝術,不太可能長久吸引人們的關注,原因很簡單,因為它下的賭注比較少。當你心存僥倖,不敢繃到極限,情感的力道就會減弱。久而久之,這樣生產出來的作品就會有點評論的味道。
有時我覺得,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想要哪種藝術家,而你們會問:「我們為什麼要想?」永遠都有那種藝術家,把自己展演成我們這個文化時刻的化身,彷彿那就是他的工作內容。對某些人而言,這的確是。今日,大多數的展演模式都進一步演化成圖符奇觀(iconic spectacle),非但不否認藝術靈光的存在,甚至還把靈光閃閃的概念轉化成可以把某樣東西搬上舞台供人拍照。也許它本身就是一種新形式,一種藝術,它的圖像價值就是要被人理解,也許只能在雜誌或螢幕這類框架下被理解。我指的並不是普受推崇的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的編導式攝影(staged photography)。我指的是更受限於社交和編輯傳輸系統的圖像運用。我發現,現在的藝術系學生不願在藝術與廣告之間做出任何區分。可能有點以偏概全,但這的確是個明顯的轉變。今天的藝術系學生分不太出兩者的差別,也不認為有必要去區別。也許這只是一種不一樣的靈光。例如義大利裝置藝術家莫里奇歐‧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在西西里島巴勒摩(Palermo)的山丘上重新翻製了好萊塢的標誌;《藝術論壇》(Artforum)上的那張照片讓我們發笑;我們可以領會那種複雜多層的厚顏無恥。但有多少人真的覺得有必要跑去西西里看它呢?
從不逃避戰鬥也不怕說刻薄話的法蘭克‧史帖拉(Frank Stella)說:因為讀了杜象,過去二十五年來,如實主義的藝術(literalist,即低限主義)透過展演行為來界定自己。藝術家試圖小題大作,歌頌自己有能力從日常生活中挑出一些物件和活動,把它們擺放到不同的脈絡裡,也就是美術館或藝廊的脈絡。如實主義認定,展演的藝術和創造的藝術可以平起平坐,藉此對繪畫提出挑戰,但我們必須認知到它的輕率不認真。我很想把這種如實主義的變種打發走,但它已經變成藝評家的新寵兒,因為藝評家一眼就可以認出來。也就是說,藝評家很快就發現,他們可以輕輕鬆鬆處理這種藝術,因為那種藝術很積極地想用打字技巧來界定自己。
1980年代,紐約藝術市場繁榮了一段時間,吸引了主流媒體的注意。當時,藝術圈已經有一陣子沒被當成有趣的話題,枯燥的觀念藝術讓人覺得自己是個笨蛋,而現在,終於有些東西可以拿來妝點了。八卦很有娛樂價值,有些人的個性也很鮮明。與1980和1990年代藝術有關的話題,多半都是把藝術圈當成某個社交系統來閒聊,這雖然也有點趣味,但藝術圈不等於藝術,也不像藝術本身那麼有趣。當時的藝術市場在一段長到被視為常態的寂靜期之後,出現過短暫的茁壯,等到情況轉壞時,有些人不願把眼光放遠,反而開始大發牢騷。他們不再關注作品。我記得在1990年代初,有個《北歐藝術評論》(Nordic Art Review)曾對我提出一個非常直白的問題:「1980年代;到底好在哪裡?」
至少從文藝復興開始,藝術圈一直住滿了怪人和一些奇異甚至令人害怕的個人習慣——例如,據說義大利矯飾主義畫家羅索(Il Rosso)跟一隻人猿住在一起,把牠當成家人。卡爾文‧湯姆金斯(Calvin Tomkins)在他的杜象傳記裡,也舉了一些比較近期的案例,他把紐約1920年代末杜象圈子裡一個比較外圍的藝術家形容成「神經不正常」,她是一位原型行為藝術家,習慣把活鳥別在裙子上,沿著第五大道閒逛。我不覺得,我們希望藝術以其他模樣出現。就像我前面說過的,也許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想要哪種藝術家。藝術作品取得意義的途徑之一,是當它的形式和圖像模式能與大環境的關注系統產生共鳴。另一種途徑,是當藝術家的傳奇性格發揮相同的作用。當某樣東西被認為過時,真正的意思是,編碼在那些樣式裡的藝術家形象不合時宜。裙擺不是太長,就是太短。
流行變來變去。藝術圈令人沮喪的一點是,它願意容忍人身攻擊,假裝是在捍衛某種價值。對1980年代藝術的批判,大多都是赤裸裸的菁英主義。人們不喜歡某幅畫,是因為不喜歡畫畫的人。藝評家羅伯‧修斯(Robert Hughes)對1980年代藝術的惡意攻擊,還包括對收藏家的蔑視,而那句自鳴意滿到處亂噴的「為新貴打造的新藝術」,說得好像法爾內塞(Farnese)或波各塞(Borghese)家族在他們那個時代有什麼不同似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出,修斯那些修辭的本質就是討人厭的勢利眼。
不過,讓我們回到再現的問題。一件作品複製得好不好,對它的普及度有很大的影響力,這種情形已經維持了一段時間,至少從畢卡索開始;例如1960年代以來最受好評的藝術家,他們的複製品看起來都很棒。這並不表示,那些作品沒有同樣強大的實體臨在感,而是說,大多數民眾主要還是透過複製品來熟悉藝術品;有幸能親炙畫作的人畢竟是少數,而那些奢侈到可以和畫作一起生活的人,更是有如鳳毛麟角。不過這種情形和我接下來要說的並不相同:有些具體存在於三度空間裡的藝術,出現在雜誌裡的模樣似乎比在實體更吸引人。兩者到底差在哪裡?把藝術當成一種奇觀是來自不同脈動,特別是藝術總監(art director,藝術指導)的脈動,可說是觀念藝術的遺澤和圖像反諷的融合。
藝術指導是一門指導關注力的科學,但往往是騙人的;那個地方往往會讓人以為你比真實的你更聰明或更有吸引力。藝術指導的大獲全勝,讓藝術界越來越受到它的束縛,讓藝術淪為替反諷服務,替反諷式的形式展演服務,兩者的差別就在於藝術的訊息。就像我先前指出的,現在藝術學校裡的孩子根本不在乎廣告和藝術的差別。你也許會問,他們為什麼該在乎?特別是其他人都不在乎的話。
在1970年代初加州藝術學院的承平時期,當時學校還很有錢,學生可以申請補助金,進行專案計畫。有次我擔任評審,負責挑選優勝者。有個傢伙申請三千美元,在當時這是很大一筆錢,他計畫把一部電視和一台發電機搬到遙遠的山頂上,在那裡看完影集《豪門新人類》(The Beverly Hillbillies)的重播,然後用一把十二口徑的散彈槍把電視螢幕轟掉。我們給了他三百美元,並建議他在洛杉磯下城找間最糟糕的廉價旅館住進去,用BB槍射電視螢幕就好。有些時候,少就是多。自從那個純真時代結束之後,世事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博物館現在會定期付錢給藝術家,讓他們飛到世界各地創作作品,然後拍下照片,透過藝術刊物和社交媒體散播出去。就像俗話說的,如果你能拿到那真是好差事,而留給我們的,就只有雜誌上的一張照片。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