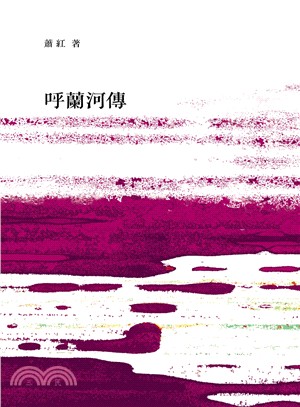再享89折,單本省下31元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序 呼蘭離香港有多遠(節錄)
記不清十幾歲的時候,第一次去到呼蘭,唯一去看的景點就是蕭紅故居。知道蕭紅是因為小學課文《火燒雲》,句子簡單純粹,想像力很好,很適合拿來教比喻,後來知道,就是出自《呼蘭河傳》。蕭紅的作品不多,最愛的是《呼蘭河傳》、《商市街》和她的詩作。三者都表現了蕭紅的不同側面:《呼蘭河傳》是她生命、記憶與語言的原型;《商市街》裏哈爾濱波西米亞文藝青年生活是她的蕩拓之筆;詩作雖在她全部作品裏最直白、最少女,卻能看到她的文藝氣質的基礎。
小時候去看蕭紅故居,用《呼蘭河傳》裏的話來說,「我家是荒涼的」。是典型的東北滿族民居,灰瓦青磚紅窗櫺,只是有些空空的,櫃子、牀和有雕花的風板都方正而大,算不上我小時候心中的「古色古香」。院子裏一尊她的雪白雕像,也沒什麼特別,只是那石頭眼珠看著遠方,令你想起「洞然」兩個字。大了又去過一次,那時已讀過她的傳記和所有作品,已離開家鄉去過一些地方,回轉身再看那陽光,透過大窗照在她們家的大炕(東北農村家裏不用牀,而是建築了這種裏面可以燒火取暖的臥具,炕上可以鋪蓆)上,再看她家裏那簡單得有些直白的空院落,突然想起蕭紅在《呼蘭河傳》裏反覆說的,「沒有什麼了」。
「沒有什麼了」,然而已是一切。蕭紅文字世界的魅力由這裏來。
一
曾把《蕭紅全集》借過給一個香港的朋友,他老老實實說,雖然知道她是名作家,但那些北方農村的故事,讓香港島長大的他難以進入。這很可理解,算時間幾乎一百年前了;論地理與文化,呼蘭河同香港實在有些遠,它是中原文化中心之外的邊陲小城,漢滿文化雜糅。《呼蘭河傳》中多次描述的「跳大神」就是滿族原始宗教薩滿教在民間的遺留形式,直到我小時候,也還聽聞東北農村有零星實在迷信的人家有請大神來驅魔祛病的舉動。
中原文化之外,黑龍江本是滿族的發祥地,白山黑水,森林礦藏,先有漁獵,而後有農耕。那裏的漢人多是移民來到這裏的,所謂「闖關東」—十九世紀至民國年間,中原漢人向山海關以東的大片沃土山林,闖蕩和討生活的一段歷史。這些移民多是墾荒、狩獵、去金礦淘金,要麼是入山林挖人參,無常流離冒險的生活要求的是勇氣、孔武,和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豁達,他們由此形成的東北漢族文化,很天然地具有開拓、遠行、粗獷與豪邁的邊疆氣質。《呼蘭河傳》裏蕭紅家的租客,開粉房的和養豬的那幾戶,常唱陝西民歌《五更天》和拉秦腔的,大概就是一些新來闖關東不久的「新移民」,他們遠道而來,住漏水房子,而能樂天安命:
他們一邊掛著粉,也是一邊唱著的。等粉條曬乾了,他們一邊收著粉,也是一邊地唱著。那唱不是從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著眼淚在笑似的。
逆來順受,你說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卻不在乎。你看著很危險,我卻自己以為得意。不得意怎麼樣?人生是苦多樂少。
那粉房裏的歌聲,就像一朵紅花開在了牆頭上。越鮮明,就越覺得荒涼。
他們雖然是拉胡琴、打梆子、歎五更,但是並不是繁華的,並不是一往直前的,並不是他們看見了光明,或是希望著光明,這些都不是的。
他們看不見什麼是光明的,甚至於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陽照在了瞎子的頭上了,瞎子也看不見太陽,但瞎子卻感到實在是溫暖了。
他們就是這類人,他們不知道光明在那裏,可是他們實實在在的感得到寒涼就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想擊退了寒涼,因此而來了悲哀。
他們被父母生下來,沒有什麼希望,只希望吃飽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飽,也穿不暖。
逆來的,順受了。
順來的事情,卻一輩子也沒有。
這些屬於東北文化的氣質,固然培養了許多粗野,但對此地天性敏感聰穎多情的人來說,卻有另一種好處,就像唐代的邊塞詩那樣—困在這闊大而無常、直接逼近生與死的最邊緣中生活,而能體悟人之存在的無限悲涼,進而具有一種大而深沉的悲憫。
而蕭紅,當然也屬於這天性敏感、聰穎、多情者中的一人,更何況她是大戶人家的掌上明珠,自小看盡家裏家外、富戶與貧民迥然不同的處境和命運。她不僅得到相對精細文雅的培養,也能接通那粗亂原始求生存的世界的另一端。另一方面,這樣的環境,她雖懂得如何在文字裏任性和示弱,但她絕非弱女子,而是有著強悍與「狠」的一層天性。她由此鍛鍊了一種特別的視角:她的文字,生死往往混於一處,描述生無時不在講死,甚至越生動越透出死的寂味;而反之亦然。這是她相當獨特的世界觀,她不執著於生/死任何一邊的細節,她為自己挑選了一個兩者之上的高度,同時敘述。
目次
序
呼蘭離香港有多遠? 曹疏影 ii
第一章 2
第二章 38
第三章 64
第四章 96
第五章 116
第六章 164
第七章 194
尾聲 224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嚴冬一封鎖了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著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尺長的,一丈長的,還有好幾丈長的,它們毫無方向的,便隨時隨地,只要嚴冬一到,大地就裂開口了。
嚴寒把大地凍裂了。
年老的人,一進屋用掃帚掃著鬍子上的冰溜,一面説:
「今天好冷啊!地凍裂了。」
趕車的車夫,頂著三星,繞著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剛一矇亮,進了大車店,第一句話就向客棧掌櫃的説:
「好厲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樣。」
等進了棧房,摘下狗皮帽子來,抽一袋煙之後,伸手去拿熱饅頭的時候,那伸出來的手在手背上有無數的裂口。
人的手被凍裂了。
賣豆腐的人清早起來沿著人家去叫賣,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盤貼在地上拿不起來了,被凍在地上了。
賣饅頭的老頭,揹著木箱子,裏邊裝著熱饅頭,太陽一出來,就在街上叫喚。他剛一從家裏出來的時候,他走的快,他喊的聲音也大。可是過不了一會,他的腳上掛了掌子了,在腳心上好像踏著一個雞蛋似的,圓滾滾的。原來冰雪封滿了他的腳底了。他走起來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著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這樣,也還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饅頭箱子跌翻了,饅頭從箱底一個一個的跑了出來。旁邊若有人看見,趁著這機會,趁著老頭子倒下一時還爬不起來的時候,就拾了幾個一邊吃著就走了。等老頭子掙扎起來,連饅頭帶冰雪一起揀到箱子去,一數,不對數。他明白了。他向著那走不太遠的吃他饅頭的人説:
「好冷的天,地皮凍裂了,吞了我的饅頭了。」
行路人聽了這話都笑了。他措起箱子來再往前走,那腳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結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難,於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鬍子上的冰溜越掛越多,而且因為呼吸的關係,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掛了霜了。這老頭越走越慢,擔心受怕,顫顫驚驚,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場似的。
小狗凍得夜夜的叫喚,哽哽的,好像牠的腳爪被火燒著一樣。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凍裂了;
井被凍住了;
大風雪的夜裏,竟會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來,一推門,竟推不開門了。
大地一到了這嚴寒的季節,一切都變了樣,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風之後,呈著一種混沌沌的氣象,而且整天飛著清雪。人們走起路來是快的,嘴裏邊的呼吸,一遇到了嚴寒好像冒著煙似的。七匹馬拉著一輛大車,在曠野上成串的一輛挨著一輛的跑,打著燈籠,鬼著大鞭子,天空掛著三星。跑了兩里路之後,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這一批人馬在冰天雪地裏邊竟熱氣騰騰了。一直到太陽出來,進了棧房,那些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馬吃飽了之後,他們再跑。這寒帶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遠又來了一村,過了一鎮,不遠又來了一鎮。這裏是什麼也看不見,遠望出去是一片白。從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見的。只有憑了認路的人的記憶才知道是走向了什麼方向。拉著糧食的七匹馬的大車,是到他們附近的城裏去。載來大豆的賣了大豆,載來高粱的賣了高粱。等回去的時候,他們帶了油、鹽和布匹。
呼蘭河就是這樣的小城,這小城並不怎樣繁華,只有兩條大街,一條從南到北,一條從東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華。十字街上有金銀首飾店、布莊、油鹽店、茶莊、藥店,也有拔牙的洋醫生。那醫生的門前,掛著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畫著特別大的有量米的斗那麼大的一排牙齒。這廣吿在這小城裏邊無乃太不相當,使人們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因為油店、布店和鹽店,他們都沒有什麼廣吿,也不過是鹽店門前寫個「鹽」字,布店門前掛了兩張怕是自古亦有之的兩張布幌子。其餘的如藥店的招牌,也不過是:把那戴著花鏡的伸出手去在小枕頭上號著婦女們的脈管的醫生的名字掛在門外就是了。比方那醫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藥店也就叫「李永春」。人們憑著記憶,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們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裏。不但城裏的人這樣,就是從鄉下來的人也多少都把這城裏的街道,和街道上盡是些什麼都記熟了。用不著什麼廣告,用不著什麼招引的方式,要買的比如油鹽、布匹之類,自己走進去就會買。不需要的,你就是掛了多大的牌子,人們也是不去買。那牙醫生就是一個例子,那從鄕下來的人們看了這麼大的牙齒,真是覺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邊,停了許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麼道理來。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絕對的不去讓那用洋法子的醫生給他拔掉,也還是走到李永春藥店去,買
所以那牙醫生,掛了兩三年招牌,到那裏去拔牙的卻是寥寥無幾。
後來那女醫生沒有辦法,大概是生活沒法維持,她兼做了收生婆。
城裏除了十字街之外,還有兩條街,一條叫做東二道街,一條叫做西二道街。這兩條街是從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長。
這兩條街上沒有什麼好記載的,有幾座廟,有幾家燒餅舖,有幾家糧棧。
東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紅色的好磚砌起來的大煙筒是非常高的,聽説那火磨裏邊進去不得,那裏邊的消信可多了,是碰不得的。一碰就會把人用火燒死,不然為什麼叫火磨呢?就是因為有火,聽説那裏邊不用馬,或是毛驢拉磨,用的是火。一般人以為盡是用火,豈不把火磨燒著了嗎?想來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塗。偏偏那火磨又是不准參觀的。聽説門口站著守衛。
東二道街上還有兩家學堂,一個在南頭,一個在北頭。都是在廟裏邊,一個在龍王廟裏,一個在祖師廟裏。兩個都是小學:
龍王廟裏的那個學的是養蠶,叫做農業學校。袓師廟裏的那個,是個普通的小學,還有高級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學。
這兩個學校,名目上雖然不同,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也不過那叫做農業學校的,到了秋天把蠶用油炒起來,教員們大吃幾頓就是了。
那叫做高等小學的,沒有蠶吃,那裏邊的學生的確比農業學校的學生長的高,農業學生開頭是念「人、手、足、刀、尺」,頂大的也不過十六七歲。那高等小學的學生卻不同了,吹著洋號,竟有二十四歲的,在鄉下私學館裏已經教了四五年的書了,現在才來上高等小學。也有在糧棧裏當了二年的
這小學的學生寫起家信來,竟有寫到:「小禿子鬧眼睛好了沒有?」小禿子就是他的八歲的長公子的小名。次公子,女公子還都沒有寫上,若都寫上怕是把信寫得太長了。因為他已經子女成羣,已經是一家之主了,寫起信來總是多談一些個家政:姓王的地戶的地租送來沒有?大豆賣了沒有?行情如何之類。
這樣的學生,在課堂裏邊也是極有地位的,教師也得尊敬他,一不留心,他這樣的學生就站起來了,手裏拿著「康熙字典」,
西二道街上不但沒有火磨,學堂也就只有一個。是個清真學校,設在城隍廟裏邊。
其餘的也和東二道街一樣,灰禿禿的,若有車馬走過,則煙塵滾滾,下了雨滿地是泥。而且東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個,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漿好像粥一樣,下了雨,這泥坑就變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頭,衝了人家裏滿滿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陽一曬,出來很多蚊子飛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時那泥坑也就越曬越純淨,好像在提煉什麼似的,好像要從那泥坑裏邊提煉出點什麼來似的。若是一個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質度更純了,水分完全被蒸發走了,那裏邊的泥,又黏又黑,比粥鍋漱糊,比漿糊還黏。好像煉膠的大鍋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那怕蒼蠅蚊子從那裏一飛也要黏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歡水的,有時誤飛到這泥坑上來,用翅子點著水,看起來很危險,差一點沒有被泥坑陷害了牠,差一點沒有被黏住,趕快的頭也不回的飛跑了。
若是一匹馬,那就不然了,非黏住不可。不僅僅是黏住,而且把牠陷進去,馬在那裏邊滾著,掙扎著,掙扎了一會,沒有了力氣那馬就躺下了。一躺下那就很危險,很有致命的可能。但是這種時候不很多,很少有人牽著馬或是拉著車子來冒這種險。
這大泥坑出亂子的時候,多半是在旱年,若兩三個月不下雨這泥坑子才到了真正危險的時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越下雨越壞,一下了雨好像小河似的了,該多麼危險,有一丈來深,人掉下去也要沒頂的。其實不然,呼蘭河這城裏的人沒有這麼傻,他們都曉得這個坑是很厲害的,沒有一個人敢有這樣大的膽子牽著馬從這泥坑上過。
可是若三個月不下雨,這泥坑子就一天一天的乾下去,到後來也不過是二三尺深,有些勇敢者就試探著冒險的趕著車從上邊過去了,還有些次勇敢者,看著別人過去,也就跟著過去了。一來二去的,這坑子的兩岸,就壓成車輪經過的車轍了。那再後來者,一看,前邊已經有人走在先了,這懦怯者比之勇敢的人更勇敢,趕著車子走上去了。
誰知這泥坑子的底是高低不平的,人家過去了,可是他卻翻了車了。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