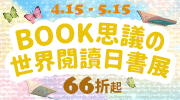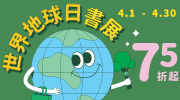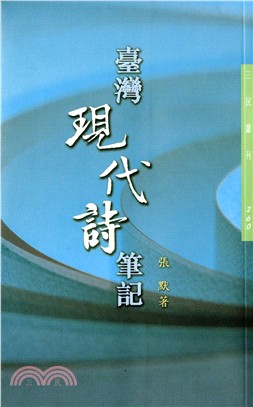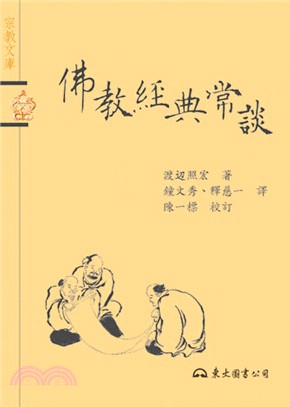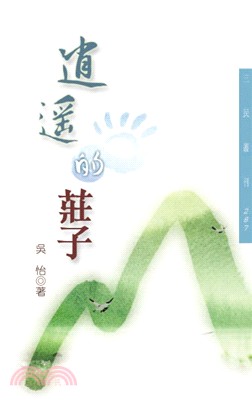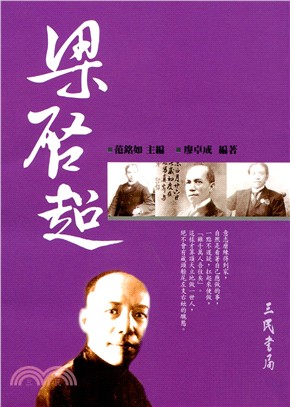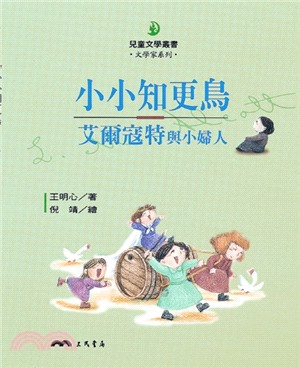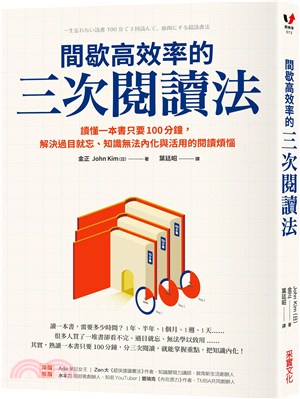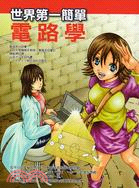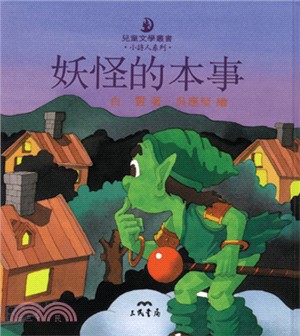五山文學與中國文學(簡體書)
- 系列名:比較文學研究學術叢書
- ISBN13:9787511720412
-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 作者:張曉希
- 裝訂/頁數:平裝/293頁
-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14/04/24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第一章五山文學與五山文化1
一禪宗東移入扶桑1
二宋學思想的傳播及根植4
三日本漢文學的巔峰——五山文學5
四從唐式茶會到日本的茶道8
五從宋元的山水畫到日本的山水畫9
結語11
第二章虎關師煉的詩學思想 13
一《濟北詩話》與中國詩話14
二唯理之適17
三醇全之意23
四盡美盡善28
五志、性情和雅正40 目錄
第一章五山文學與五山文化1
一禪宗東移入扶桑1
二宋學思想的傳播及根植4
三日本漢文學的巔峰——五山文學5
四從唐式茶會到日本的茶道8
五從宋元的山水畫到日本的山水畫9
結語11
第二章虎關師煉的詩學思想 13
一《濟北詩話》與中國詩話14
二唯理之適17
三醇全之意23
四盡美盡善28
五志、性情和雅正40
結語47
第三章夢窗疏石的造園思想與風格52
一禪式庭園的開拓者——夢窗疏石54
二自然風景與造園55
三庭園樣式的轉變與造園59
四庭園主題的表現63
五造園思想——禪與隱逸70
結語75
第四章中巖圓月的儒士風骨77
一憂國憂民之真情77
二守道與固窮的君子人格87
三待時而動的儒家隱逸觀95
結語103
第五章義堂周信的文學觀107
一道理與文章109
二恬靜超脫的漢詩121
三義堂的文學思想137
結語148
第六章絕海中津的文人風致154
一坦率之性與脫俗之心155
二源于中華的傳世詩作165
三澤被禪林的書畫藝術176
結語191
第七章景徐周麟的禪儒一致思想195
一對求道精神的堅持198
二禪儒一致與政治理想211
三“身不隱心隱”的思想220
結語234
第八章一休宗純的特異性238
一對儒家思想的繼承239
二對淡泊質樸的古禪風的堅守246
三“身隱心不隱”的思想256
結語264
第九章漢詩與文化交流268
一遣明使及其必備的條件268
二策良周彥與漢學修養269
三漢詩與景觀271
四漢詩與宗教276
五漢詩與外交279
結語 283
第十章中日古代流散漢詩及其特點285
一流散者遠離故土的思鄉性286
二流散者在異質文化中遭遇的思想碰撞與文化沖突289
三流散文學在異質文化中的融合與傳播291
結語292
后記294
書摘/試閱
日本中世初期,連年的戰亂使社會經濟文化受到了嚴重破壞,莊園制瓦解,各地的守護大名控制了所管轄的土地和民眾,舊佛教腐敗衰微,掌握了政權的武家與舊貴族之間的矛盾呈多元化狀態,因此,幕府希望用新興的禪宗來代替舊宗教勢力,模仿南宋禪宗寺院體制建立了五山十剎五山是當時日本朝廷模仿南宋所制定的禪寺的等級,將鐮倉的建長寺、圓覺寺、壽福寺、凈智寺、凈妙寺,京都的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萬壽寺列為最上位的五山,而將南禪寺定為五山之上。將凈妙寺、禪興寺、圣福寺、萬壽寺(京都)、東勝寺、萬壽寺(乾明山、相模)、長樂寺、真如寺、安國寺(山城、北禪寺)、萬壽寺(蔣山、豐后)列為十剎。的官寺制度,從而奠定了禪宗的主導地位,也使五山禪僧接觸中國的新佛教、新儒學和先進文化成為可能。五山禪僧中有赴宋元明求法的日本禪僧,也有渡日傳法的中國高僧,還有幕府派遣的勘和貿易遣明船的遣明使僧,這些禪僧以其高度的文化修養成為幕府的外交、文化顧問,五山文學的創作主體和外來文化的傳播者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擬從宗教、思想、文學、藝術幾個方面論述五山禪僧如何傳播中國文化,進而對日本中世多元化文化形成和發展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一 禪宗東移入扶桑
南宋社會經濟發達,是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發展的興盛時期,對外開放程度較高,尤其是造船技術的提高,為海外貿易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因此,南宋統治者積極鼓勵對外貿易。南宋初期,時值日本白河法皇主持院政太上皇或法皇(出家的太上皇),日本中世執政的一種政治形態。后期,政權由外戚藤原氏家族移于武家平氏之手。由于平清盛在保元之亂保元元年(1156年)7月日本朝廷中發生的內亂。崇德上皇與后白河天皇、攝政、關白家的藤原賴長與藤原忠通的對立激化,崇德、賴長一方以源為義的軍隊為主,后白河、忠通一方以平清盛的軍隊為主展開了激戰,結果崇德大敗,被流放到讚岐。保元之亂成為日本武士登上政治舞臺的契機。中助后白河天皇平亂有功,升任大宰府太貳大宰府的次官。掌九洲政務,因見日宋貿易有利可圖,對外采取積極推進政策,獎勵海外貿易,此外還修筑兵庫港,整備瀨戶海峽等,以利于船舶的往來,使日僧大批入宋成為可能。據梅應發、劉錫撰《開慶四明續志》卷八中記載:“倭人冒鯨波之險、舳艫相銜、以其物來售”,而隨商船求法渡宋的僧人也絡繹不絕。僅史料中有姓名記載的入宋僧就有一百二十余人,其中大部分為五山禪僧。最著名的當屬日本禪宗的開山之祖明庵榮西。榮西曾于1168年、1187年兩度入宋,師從臨濟宗黃龍派第八代傳人虛庵懷敞,參禪問道。1191年孝宗皇帝賜其“千光法師”之號。歸國后,榮西以九州為中心,在肥前(佐賀、長崎縣)、筑前(福岡縣西北部)、筑后(福岡縣南部)、薩摩(鹿兒島西部)等地興禪布教,開創了圣福寺等多所寺院。禪寺多模仿宋代叢林清規,其建筑也為宋代禪剎之樣式,由于榮西在宋時曾營造天臺山萬年寺三門的兩廊、智者大師的塔院,還襄助過天童山千佛閣等建筑工程,獲得許多建造寺院的經驗,這給日本禪寺建筑以很大影響。此外,他還撰述世稱日本禪宗創立的宣言書《興禪護國論》,闡明禪宗宗旨,介紹唐宋禪宗的特色,并申明興禪“護國”的道理。在新興的鐮倉幕府皈依、支持和保護下,創建了壽福寺,在京都創建了臺、密、禪三宗兼學的道場建仁寺,為日本禪宗的全面展開奠定了基礎。榮西對禪的大力提倡給當時的日本佛教界以極大的刺激,引起了人們對禪宗的興趣,因憧憬南宋的禪風而入宋者接踵而至。其弟子道元1223年入宋求法,登天臺山萬年寺,歷游天童、阿育王、徑山等著名寺院,學禪于天童山如凈禪師。回國后,1227年在日本深草建興圣寺,為日本最初的禪堂。1243年在越前(福井縣東部)開創永平寺,成為日本曹洞禪宗的開山之祖。其法孫圓爾辨圓1235年入宋,巡游于天童、凈慈、靈隱諸寺,復登徑山,學禪于徑山無準師范,1241年回國開創東福寺,弘揚教禪一致之學。為弘揚臨濟正宗禪的宗旨,圓爾曾先后向后嵯峨天皇進講中國五代宋時高僧延壽纂輯的禪學名著《宗鏡錄》,為執權幕府政權中輔佐將軍的最高長官,源實朝時任命北條時政為此職,后由北條家族世襲。北條時賴、后嵯峨上皇、龜山上皇等授禪戒,對日本臨濟禪的興隆、發展和臨濟宗的獨立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些禪僧在宋長期學禪,學成歸國時,帶回大量的佛書、禪書、僧傳等。榮西于1168年初次入宋攜歸天臺新論章疏三十部六十卷;泉涌寺不可棄法師入宋僧俊芿于1211年歸國時攜帶佛教典籍1008卷、世俗典籍919卷;俊芿的弟子聞陽湛海嘉禎末年初次入宋,歸國時攜經論疏數千卷。這些經書和典籍不僅對日本的佛典研究產生了極大影響,還直接刺激了日本印刷業的發展。通過五山禪僧的努力,在京都、鐮倉等諸禪院相繼出現了宋元刻本的仿刻板。印刷了如《虛堂和尚錄》、《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等大量的高僧語錄和禪籍等。《景德傳燈錄》、《禪林類聚》、《五燈會元》、《宗鏡錄》、《佛祖傳記》等宗教史上的重要經典也是這個時代出版的。鐮倉、室町期間刊行的五山版包括禪籍在內的佛教書籍共195種,佛教以外的經史子集等78種同上。,這極大地促進了禪宗及中國文化、文學在日本的傳播。
宋、元、明的求法僧歸國后對禪宗的傳播,使日本朝野對中國盛行的禪宗有了初步了解。他們仰慕中國佛教,積極勸請中國高僧渡日直接傳法。因此,五山禪僧中不乏宋、元、明的渡日傳法僧。首位渡日傳法僧是宋代陽山無明慧性法嗣的蘭溪道隆。他于1246年應日本入宋僧明觀智鏡之邀,攜弟子義翁紹仁、龍江等人乘船渡日傳授佛教文化,仿宋禪寺之貌,建成臨濟宗建長寺派大本山,為鐮倉五山第一大寺,成為日本最初的純禪道場。1260年,宋南禪福圣寺僧兀庵普寧渡日后,當時的執政北條時賴受其感化,達到大徹大悟之地,對鐮倉武士政權與禪的結合作出了很大貢獻。后來大休正念、無學祖元等高僧接踵渡日,舉揚臨濟禪風。1299年,元代佛教界首屈一指的禪僧一山一寧作為元朝外交使節渡日,在日二十年,先后住持過南禪、建長、圓覺等大寺,在鐮倉、京都大張法筵,大振禪風,并創立了“一山派禪學”。一寧在日期間,弘揚佛法,傳播宋學。因其人格高尚、博學多才,深受日本朝野上下各階層的尊信,給予日本國民精神上的影響甚大,后宇多法皇在其示寂后特賜“國師”稱號,贊曰“宋地萬人杰,本朝一國師”。經過他堅持不懈的努力,極大地改變與加深了日本朝野、佛教界對臨濟禪的認識,有力地促進并擴大了臨濟禪在日本的弘揚與傳承,奠定了日本禪宗獨立的基礎。
二 宋學思想的傳播及根植
中世的日本,由于貴族階級在政治和經濟上失去了實力,思想領域里曾經占主導地位的儒教也呈現出衰微的征兆。然而此時,中國的南宋正處于文化高峰期,儒學高度發達,理學風靡學術界和思想界。宋學的理念和方法論與禪宗十分接近,禪與宋學相互影響,三教一致思想認為儒教、佛教、道教其本質是相同的。宋代以后很多禪僧宋學修養很高,并將宋學作為傳教的手段。受此思潮的影響,入宋僧在傳入禪宗的同時,也自然將這種“宋學”思想引入日本。日本禪宗史上著名禪僧圓爾辨圓(圣一國師)回國時攜帶中國經籍數千卷,收藏于京都東福寺,從其藏書目錄中可見許多與宋學相關的書目。后來,幾乎所有的五山禪僧在修禪的同時都不斷提高自己的宋學修養,并將其作為傳教的手段。由于五山禪僧的努力而興盛起來的新儒教后來逐漸普及到全國各地,在與日本固有思想的融合過程中,逐步成為獨立的學術思想。
入元僧中巖圓月少年時代剃發為僧,學習密宗,后隨東明慧日、虎關師練習禪宗。1325年渡海到元,游歷禪山名剎,歷時7年之久。其勤奮好學,精通程朱理學,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陰陽五行無所不曉。元代僧人竺仙梵仙稱其“學通內外”。歸國后向將軍足利義滿和攝政關白二條良基講儒學的新舊兩義,力說儒學的意義。所著《中正子》一書,提倡儒佛一致,論諸子百家,被日本學者譽為古代日本哲學思想史上的鴻篇巨擘。東褔寺的岐陽方秀是一名徹底的宋學信奉者,他講朱子的《四書集注》,并為其標注日文讀法,使一般人也能理解原著內容,為儒學在日本的普及開拓了新局面。了庵桂悟曾任東福寺、南禪寺的住持,師從云章一慶,習禪宗經典及莊子等外典,向舟橋宗賢學詩傳四書等舊注儒學,潛心研究《宗鏡錄》,與禪、凈一致的思想產生了共鳴。晚年應后土御門天皇(1442—1500)之命,在宮中宣講金剛經、般若心經等,并以83歲的高齡作為遣明正使率第八次遣明船入明,受到明武宗的厚待,在明期間還與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王陽明往來,深得陽明學精髓。桂庵玄樹代表了日本當時宋學繁榮和普及的最高水平。其9歲入南禪寺,師從蘭坡景茝,又隨建仁寺云龍庵的惟正明貞和東褔寺的景召瑞棠學習《四書》的新注。1467年隨遣明使天與清啟入明,在明7年,受憲宗之寵,遍游蘇杭,歷訪諸儒探究程朱之學,其中最崇《尚書》。1473年歸國,恰逢應仁大亂1467年(應仁元年)至1477年發生的內亂。因足利將軍家和畠山?斯波兩管領家的繼承問題,細川勝元的東軍和山名宗全的西軍分別率領諸大名在京都展開了激戰。戰亂擴大到了地方,出現了戰國時代。從此,幕府失去了權威。,因難以在京都弘教,遂到九州、肥后(熊本)、薩摩(鹿兒島)等西部地方,向武士及庶民傳播儒學,以至達到宋學風靡西部邊陲的盛況。1481年刊行的桂庵玄樹的朱子《大學章句》是日本歷史上出版的第一部朱子新注,此書在1492年再版,成為極珍貴的藏書。另外,玄樹還著有《家法倭點》一書,對岐陽方秀標注的《四書》“漢籍和點”加以修正,辨新古。《四書》的讀法、標點符號在其《家法倭點》中得到統一。桂庵玄樹的學問被弟子們所繼承,為日本近世朱子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三 日本漢文學的巔峰——五山文學
以偈頌或佛教法語為主的宗教文學始于唐代。到了南宋,以詩文揚名的禪僧輩出,形成了禪宗文學的黃金時代。由于五山禪僧將禪宗傳入日本,宋、元、明文學也隨之船載以入,中國大陸禪林尊重文筆的風習也直接傳入日本。但是,這種“以文為本,學道其次”的傾向最初在五山禪林內被認為是“邪道、俗人所為,忘記了禪僧的本分”而受到責難。后來,詩文的功效逐漸被認可。竺仙梵仙認為“道如主食,詩文如副食,詩文可助學道”,桂庵玄樹主張“詩熟則文必熟,文熟則禪必熟”,禪與詩是表里一致的關系。這種文學觀逐漸風靡整個禪林,禪僧們開始關注和學習大陸禪僧和文人的詩文集,并對詩文的著述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五山文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
當時,五山禪僧中流行以內外典兼通為尚的禪林學術理念,“朝經暮史晝子夜集”蔚然成風。五山求法僧崇尚中國文化,在中國體驗叢林生活、參禪求法的同時,云游山川大剎,結交中國博學俊穎之士,究儒學、弄詩文,回國時帶回了大量的禪僧詩文集,廣傳至禪林之中。除中國禪僧的詩文集以外,僧侶們涉獵的范圍逐漸擴大到中國文人的詩文集。主要作品有《詩經》、《楚辭》、《文選》、晉代陶淵明、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的詩;韓愈、柳宗元的文章;宋代蘇軾、黃庭堅、王安石、陸游、歐陽修等的詩文;元代黃溍、虞集、程鉅夫,明代的宋濂、張楷等的詩文。還有賦詩撰文所需的《禮部韻律》、《古今韻會舉要》、《韻府群玉》等韻書以及《太平御覽》、《事文類聚》、《皇朝類苑》、《記纂淵海》等,這些典籍在五山禪僧漢詩文的研習和創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山文學中,宋元明的渡日傳法高僧的影響極大。他們對日本五山禪林界進行了直接指導,成為五山文學創作的源流。如鐮倉末期渡日元僧一山一寧被稱為五山文學的始祖,其博學多才,不僅精于禪學,而且從儒道百家,到詩文、小說、鄉談、俚語、書法、繪畫無不精通。慕名來掛塔的修行者絡繹不絕,一山只好通過作偈頌的考試進行選拔。以古詩、律詩、絕句等詩歌形式作偈頌需要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功底。因此,此舉被禪林視為促進五山禪僧提高漢詩文修養的重要契機。一山之后,東明慧日、清拙正澄、明極楚俊等元代高僧相繼渡日。竺仙梵仙在將元代的禪林文學新風傳入日本發揮了重要作用。梵仙的影響力極大,據說五山的文筆僧幾乎都與其有過交流,他的《天柱集》、《來來禪子集》、《東渡集》等多部著作的問世,促發五山文學興起的機運得以成熟。
在一山一寧的直接指導下,五山禪林中優秀詩僧輩出。有入元僧雪村友梅、龍山德見、虎關師煉等。虎關師煉被尊為五山文學翹楚,是集漢學之大成者,經史子集無所不通,完成了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僧人傳記《元亨釋書》(30卷),其詩文全部收錄于《濟北集》(20卷),文風洗練,縱橫奔放。中巖圓月個性率真,曾入元求法,精通程朱理學,仰慕李白、杜甫的詩風,所著《東海一漚集》(30卷)內容豐富,說、論、雜文、詩兼備,由元代百丈山禪師東陽德輝作跋,贊為“疑是大唐人作”,被譽為五山文學興盛期里程碑式的作品。絕海中津和義堂周信為五山文學的雙璧,絕海中津曾作為遣明使入明9年,回國前明太祖接見了他,其應制所賦熊野三山之詩被稱為千古絕唱,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明僧錄道衍曾為其詩文集《蕉堅稿》作序時說:“禪師得詩之體裁,清婉峭雅,出于性情之正,雖晉唐休徹之輩,亦弗能過之也”,贊嘆其技法、詩風。義堂周信的漢文、漢詩卓越超群,是“五山文學”之集大成者,其所著的《空華集》(20卷)洗練、純熟,為五山文壇帶來了新風。五山文學后期的代表詩人一休宗純著有詩集《狂云集》和《續狂云集》,其自由奔放的詩風和放蕩不羈、嫉惡如仇的性格在當時的五山禪林獨樹一幟。五山文學的棹尾,最后一名遣明使僧策彥周良博學多識,熟悉中國文化,擅長漢詩文,著有《謙齋詩集》、《城西聯句》等,明人稱“讀其文有班馬之余風,誦其詩有二唐之遺響也”。五山文學后期,禪僧們的熱情轉移到了中國詩文集的鑒賞和研究,留下了大量的注釋書。這些注釋書雖然缺少獨創性,但對漢詩文的鑒賞和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說五山文學除文學史價值之外,文化史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作為禪宗史豐富的史料,儒學史上重要的成就,具有多重豐富的內涵。
四 從唐式茶會到日本的茶道
中國的吃茶之風盛行于唐代,據考證,在奈良時代遣唐使就將此風習和唐代其他文化一起傳入日本。《日本后紀》以及平安時代的敕撰漢詩集《凌云集》、《文華秀麗集》和《經國集》中就有很多描寫當時上流文人間流行吃茶的漢詩。遣唐使廢止后,這種風習也逐漸消失芳賀幸四郎:《芳賀幸四郎歴史論集Ⅳ,中世文化とその基盤》。
日本與中國茶文化的再次相遇是在宋朝。中國宋朝時禪法已甚流行,而茶具有遣困、養生之功效,故禪林逐漸有吃茶的風氣。吃茶的禮儀、行法更成為禪門生活中重要的一環,于是有“茶禪一味”的說法。《栂尾明惠上人傳記》中寫道:“建仁寺長老(榮西)贈茶,關于醫師,知茶有遣困、消食、快意之效,然此物日本不多,乃尋得其實,植兩三株,誠有醒眠,舒氣之功,亦使眾僧服之或謂此茶子,乃建仁寺僧正禦房(榮西)由大唐攜來植育而成者”。榮西在華多年,受天臺山寺廟茶禮影響很深,兩次入宋,都將茶種帶回日本。歸國后在他開創的鐮倉壽福寺、博多圣福寺、京都建仁寺等寺院設立每日修行中吃茶的風習。他帶回的茶種傳到各地,諸國也流行起了飲茶風。榮西在《吃茶養生記》中說:“茶者,養生之仙藥也,延齡之妙術也;山谷生之,其地神靈也;人倫采之,其人長命也。天竺唐上同貴重之我朝,日本曾嗜愛矣,古今奇特之仙藥也。”說明茶可去病醒神、養生延齡、益于人生。又從《太平廣記?茗部》上引用33條關于茶的說明,從茶的名稱、功效、采摘、制作等方面全面介紹了中國茶。1215年榮西獻上二月茶,治愈了源實朝將軍的病,自此,飲茶之風更為盛行。
到了南北朝時期,興起了唐式茶會(類似中國唐宋時期的茶宴、茶會)。這種唐式茶會由入元禪僧傳入日本,最初在禪林中進行,后來在與禪宗關系最為密切的武士社會流行開來。當時流行著“眾人聚之,品茶催興”,榮西在《吃茶往來》中寫道:眾人來集,請于客殿,以饗點心,然后“水織酒三獻,次索面茶一返,以山珍海味勸飯,以林園美果甘哺”。用過點心,眾人“其后起席,或對北窗之筑山、避暑于松柏之陰,或臨南軒之飛泉,披襟于水風之涼”。點茶儀式在可以眺望周圍風景的茶亭二樓進行。室內的裝飾有出自思恭、牧溪等中國名畫家之手的釋迦、觀音、文殊、普賢等佛畫,桌上鋪著金襕,古銅花瓶中插有紅花、青蓮,燭臺、香爐中插著香匙、火箸等。在房間的一角,放置屏風、設置茶爐煮茶,旁邊裝點著許多有名的茶壺、茶碗等,用的是中國的青峰、雅州、茂山等名茶,客位、主位之席放置交椅、竹椅。此外,還有點茶儀式、斗茶游戲以及宴會歌舞等,從形式到內容完全是豪華復雜的唐式茶會風格。茶會的這種奢華風習到了室町中期開始改變。當時流行書院茶,書院茶的主要特點是摒棄了斗茶以勝負為目的的游戲性以及娛樂性,重視對精品唐物的欣賞和系統的茶禮的制定,形成了風雅而又莊嚴的茶會風格。后來村田珠光在書院茶的基礎之上吸收了民間茶簡素的風格,將禪的思想導入茶道,奠定草庵茶的基礎。茶會的人數從多到少,從茶亭到簡單的茶室,從復雜的室內裝飾到簡素的陳設,茶已從單純的趣味、娛樂性質發展到一種精神上的追求。這與當時日本社會的政治形勢、文藝思潮和藝術審美觀有密切的關系。中世后期,上層社會一方面追求優雅艷麗、情趣和官能上的感覺美,另一方面向往簡素枯淡、閑凈清雅的情趣,這兩種文化現象互相影響,互相融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審美的特點是在閑寂清素中追求雅趣,豪華復雜的唐式茶會就這樣逐漸發展成閑寂清素的茶道。
唐式茶會不但為日本茶道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期間與茶道相關的諸藝術領域,如庭園、建筑、室內裝飾、書法、繪畫、香道、花道等都呈現出相同的發展軌跡。可以說茶道承載了諸多的文化藝術內涵,同時也反映了中國文化與日本傳統文化、禪宗文化和貴族文化之間的對立和融合。
五 從宋元的山水畫到日本的山水畫
隨著入宋、入元僧與渡日禪僧的頻繁往來,宋元的許多文化傳至日本。其中之一便是宋元的名畫。包括人物畫、山水、花鳥畫等。宋元畫分為院體寫生畫和水墨畫兩種。其中,渾然一色的水墨畫所含的特殊畫境與禪宗的悟境及思想背景一脈相通,因此,宋元水墨畫傳到日本后立即成為貴族、寺院競相追逐收藏的對象。鐮倉時代末期至南北朝初期,僅鐮倉圓覺寺的一所小寺院佛日庵就收藏了牧溪等宋元畫20余件。由于皈依禪宗,武士、貴族與寺院禪僧來往密切,加之執政的武家逐漸貴族化,其興趣愛好也深受其影響。因此,宋元畫逐漸被武士們所重視,從山僧的寺院傳到了武將、又變成了武將向將軍進獻的禮品或武將之間的贈答品。1481年大內政弘向將軍獻畫時,一次就進獻了三十二幅名畫。武家之間形成了宋元畫的收藏熱,自足利義滿起,歷代將軍都利用其手中的權力大量收藏,室町將軍家收藏總計90件,279幅名畫。其中人物畫114幅、花鳥畫91幅、山水畫74幅,包括名畫家30余人的作品。據說這只是其收藏的一部分,足見宋元畫流入日本的數量之驚人。
隨著禪林界、上層武士社會對宋元名畫的理解和鑒賞的深化,社會上興起了收藏、鑒賞熱。到了室町時代中期,名畫的價格飛漲,因此,五山十剎的禪寺中出現了許多臨摹宋元名畫的畫僧。開始是給禪詩配畫,后逐漸出現了專門的畫家。如相國寺禪僧如拙,其畫屬于道釋畫向山水畫發展的最初階段,1410年前后完成的《瓢鮎圖》,簡潔的構圖技巧和雄勁的筆法被認為是深受南宋著名畫家馬遠的影響。道釋畫至天章周文時已發展為水墨山水畫,周文筆法學自于南宋的馬遠、夏圭,但其題材仍為日本的自然觀,經過禪的修養醇化達到清淡雅逸的意境,形成了日本水墨山水畫的主要風格,代表作有《山色巒光圖》、《竹齋讀書圖》、《三益齋圖》等。確立日本水墨畫的獨立地位,開創水墨畫新紀元的是被稱之為“畫圣”的雪舟等楊。雪舟自幼入寶褔寺修禪,天生好畫。后入相國寺,敬仰如拙,師從周文,也臨摹傳入日本的宋元畫。1468年雪舟隨大內氏的遣明船渡明,在明期間,他入“天下禪宗五山”之一的四明山天童禪寺修禪,被推為天童禪寺禪班第一座。期間還應明人之邀,畫了富士山、三保之松原和清見寺三絕景圖。不久,他離開天童寺上京,在北京禮部院制作壁畫,深得明朝宮廷贊賞。在明一年多的名山勝景游歷,使他有機會接觸到曾經在宋元畫中憧憬的中國山水風物,并認為“明國的山川草木皆我師”。之前的周文等一流山水畫家只能通過宋元畫的想象來間接表現大陸風景,雪舟的收獲是可以將大陸的山川景色直接入畫,這也反映在他的《夏冬山水圖》等作品中。歸國后,他不再拘泥于取法一兩家,而是兼收并蓄,除了繼續習夏圭、梁楷、牧溪、玉澗等畫風,還廣泛吸收中國宋元畫樣式,開創了根植于現實土壤,洗練、暢達、雄勁、富有生命力的新畫風。雪舟的畫題材豐富、畫風多樣,主要作品大多出于南宋院體的嚴謹筆法中,同時強調水墨淋漓、豐富的空間構成和強烈的個性。如他的《潑墨山水圖》具有抽象的意蘊,從其潑墨法即可看出明代畫家張有聲或李在的畫風,也能窺出玉澗、牧溪山水畫的筆法。另外,他還一改前人只畫大陸風景的作法,將日本本土山水風景繪入畫中,完成《天橋立圖》等巨制。雪舟從宋元摹本到師法中國自然風物,再到師法日本自然風物的過程中,完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點的水墨畫——漢畫。以他為代表的新繪畫潮流奠定了室町時代繪畫的主流——漢畫派的基礎,并給即將到來的日本近世繪畫以極大的影響。至此,在宋元山水畫的影響下,與禪宗密不可分的日本山水畫逐漸脫離了對宋元山水畫的單純模仿,形成了清淡雅逸、氣韻自然的日本獨特畫風。
結語
日本中世文化是在沒落貴族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武家文化框架,由禪僧為其充實了內容。由于當時其自身文化還沒有成熟,使日本社會產生了渴望汲取和掌握宋元明先進文化的心理需求。為適應這種時代的要求而登場的便是以鐮倉、京都的五山十剎為中心的五山禪僧。他們當中無論是到中國直接體驗禪林生活的日本禪僧,還是渡日傳法的中國禪僧,帶到日本的禪宗其物顯示了新宗教的魅力,船載以入的學問、藝術、趣味等均是當時最為流行的宋、元以及明代的先進文化。這些禪僧中許多人歷任于京都、鐮倉五山等大寺的住持,接受朝廷、武士政權的支持和崇信,確保了作為特殊文化形態的宗教在日本中世佛教界獨占鰲頭的地位,成為當時社會的精神指導者。尤其是五山勢力在幕府的大力保護下,得到了經濟上的安定,取得了文化形成的最基本條件之一,即具有充分的物質基礎和閑暇、充裕的精神。除佛學以外,作為當時的文人,五山禪僧還潛心多方面的學問,具有極高的文化修養。因此,屬于知識階層中最上層、最優秀的禪僧聚集在五山,他們要以學問和教養來滿足社會,尤其是要滿足保護者——當時執政者的期待,便以極大的熱情積極地傳播并介紹中國文化。這種外來文化中的積極因素與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日本民族特色、新的文化體系。可以說,五山禪僧是當時先進文化的代表者,也是日本中世文化形成、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和中堅力量,而這種文化由于它自身的價值,又成為日本近世文化的母體。
參考文獻
1.竹田和夫,(2007),《五山と中世の社會》,協友社。
2.西尾賢隆,(1999),《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禪僧》,吉川弘文館。
3.芳賀幸四郎,(1981),《芳賀幸四郎歴史論集Ι東山文化の研究》,思文閣出版。
4.愈慰慈,(2004),《五山文學の研究》,汲古書院。
5.芳賀幸四郎,(1981),《中世文化とその基盤》,思文閣出版。
6.山口修,(1996),《日中交流史》,東方書店。
7.梶谷宗忍訳注,(1976),《絶海和尚語録》,思文閣出版。
8.釋東初,(1989),《中日佛教交通史》,東初出版社。
9.楊曾文,(1996),《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