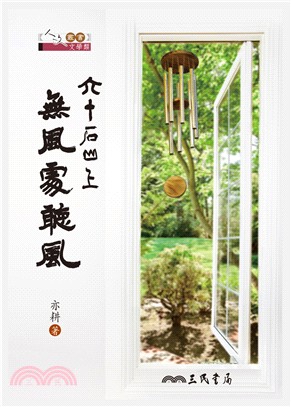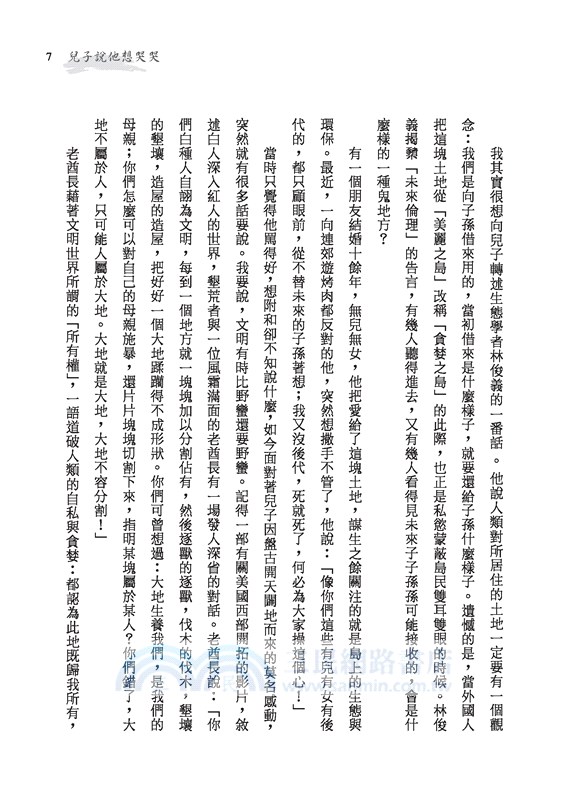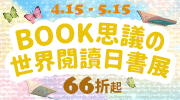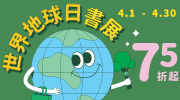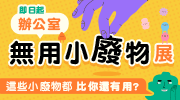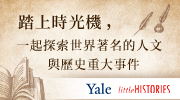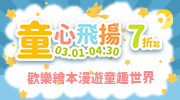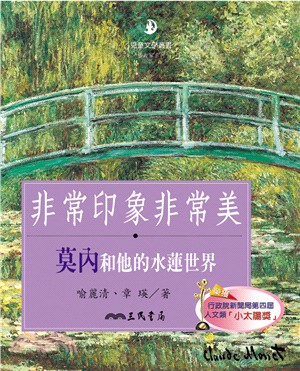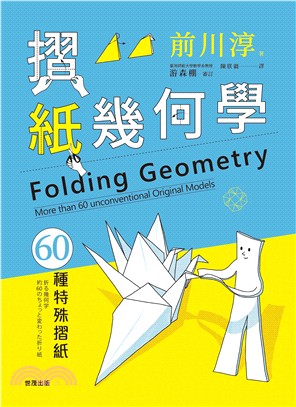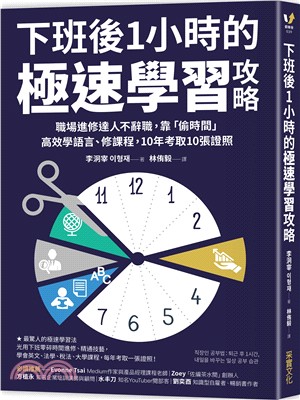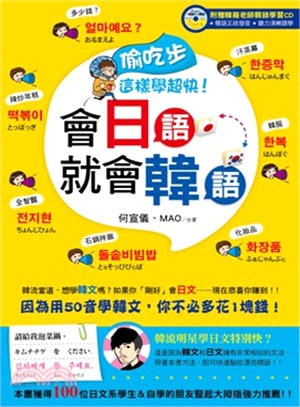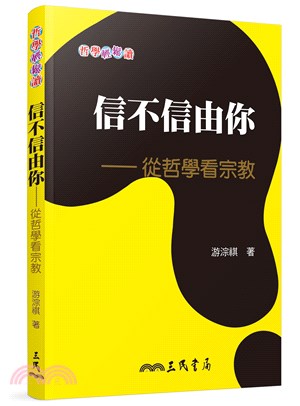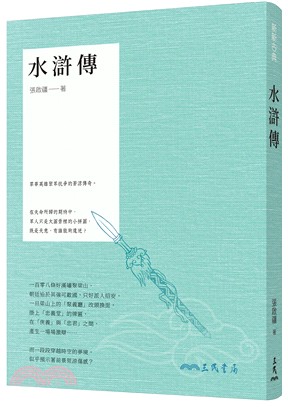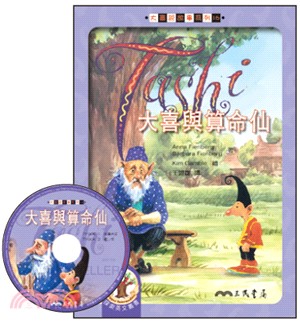商品簡介
亦耕先生筆耕一向有原則:其一,選擇無人耕耘之田而深耕;其二,但問耕耘,不問收穫。
無人耕耘之田,意思是沒人這樣寫或者沒人寫這個。因此凡所筆耕皆能戛戛獨造,言人之所未言,發人之所未發。
又由於深耕,故筆鋒所及,每能穿透社會、文化、教育、政治乃至人倫親情的表相,直指人心,入情入理。
這樣的文章,只要是有心人,讀了沒有不共鳴的。筆耕而能引發讀者共鳴,便是作者「但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最大收穫了。
《六十石山上無風處聽風》輯錄的正是如此思想性藝術性兼具的文章。你可以好整以暇,拿它當文藝小品漫讀輕覽;也可以嚴陣以待,以多疑慎思的態度,與它正面碰撞,能撞出思想火花,便是讀者最大的收穫了。
總之,「開卷有益」此書足以當之。
作者簡介
亦耕
本名洪邦棣,桃園人,一九四九年生。少時即有志於教育工作與文字工作,以第一志願考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就讀,畢業後先後執教於臺北市私立復興初中及市立建國高中。舌耕之餘兼事筆耕,因號「亦耕」。其中以任教復興時筆耕最力,收穫的量不多但質精,第一本散文集《尋夢與問津》即獲頒中山文藝獎(一九八四年)。在三民書局出版的著作,尚有論集《語文深淺談》。
序
六十石山的「石」指容量,臺語讀本音,國語讀作「擔」。此山座落在花蓮海岸山脈,每當夏秋之交,嶺上一片金針花海,蔚為奇觀。我一向對字詞語句敏感,六十石山吸引我的,毋寧是命名取義既形象化又飽含臺灣土味(數字地名多與先民移墾有關,如三張犁、五塊厝、七股、九份、十八甲寮、三十張……)。據傳早期這裡種稻每甲地可收穀六十石,而別的地方至多四五十石;「六十石」於此見出不凡,當地人常掛嘴邊以自豪,久而久之遂成專名,一直叫到今天改種金針的年代。
這本散文集收錄的作品,大都草創於時代是苦悶時代、生命是青壯生命之際,而今活過了古人所稱「耳順」的年歲,頂著花白頭顱回顧這些蛙鳴蟬噪之作,不免有一種無風處聽風雷的感覺。於是便結合六十石山的意象象徵人生到達六十之年的收成與負擔定下「六十石山上無風處聽風」這樣的書名。看似曖昧,實則較諸以篇名為書名更具概括作用。
距離前一本散文集《面對赤子》,二十幾年了。此時出版此書,有如晚年生屘子,從催生到接生,其過程既曲折又艱辛。書中〈情緣〉一文對此有所述及,這裡就不贅了。
封面題簽出自杜忠誥教授手筆;小書得此大家墨寶,蓬篳也生輝了。
二○一三年二月於碧潭面壁之居
目次
輯一 島國觀風
觀音山遙想
兒子說他想哭哭
大嵙崁溪的嗚咽
防風林的地方沒有防風林
純不純
名人巷
雙面人與假面人
可怕的陌生人
情的文化
人情與保險
期待鄭板橋
安步不能當車
超前者
開車上路,原形畢露
從醬缸到冰箱
烏鴉與喜鵲
美麗之國之美
斷想錄 十九章
弱者/希望/大嗓門/報/猜/偽/智慧/殉情/不守法/有辦法/講道德/泛道德/歷史/
無名氏/英雄/大男人/唐玄宗/長城/七矮人
輯二 校園發聲
早報與晨考
ㄍㄛㄍㄛㄍㄛ與ㄐㄧㄐㄧㄐㄧ
過度學習與不學習
從近視到短視
要記過,還是捱打
最難侍候國三生
窗外
如果你們是蠶
七月之什
老部長的眼淚
向僧侶學習
硯臺上的農夫
追尋天地間不滅的明師──書法家杜忠誥的閱讀之旅
體道之心,放膽之文──序杜忠誥《池邊影事》
斷想錄 七章
受教育狂/變態教育/教育媽媽/英語教學/書呆子/榜樣/祕訣
輯三 浮生掠影
好花看到半開時
人生道上
遊戲人間
插翅難飛
鷓鴣你到底說些什麼
所謂隱者
癮君子的告白
其一 自欺又欺人
其二 所以我贊成立法
純純的愛
愛的故事
從五倫到八倫
情緣
斷想錄 十八章
品味/執著/得失/慎獨/找伴/遇合/離別/改過/賭博/小人/小偷/年齡/時間/知識/
電影/趕時髦/田園文學/零感
輯四 人子問心
千年拉鋸
幼吾幼
與子偕行
阿甘
母親的銀髮
含笑
一個半媽媽
斷想錄 九章
人之初/人子/一神教/老人/說話/婚姻/怕老婆/世間男女/同床異夢
書評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