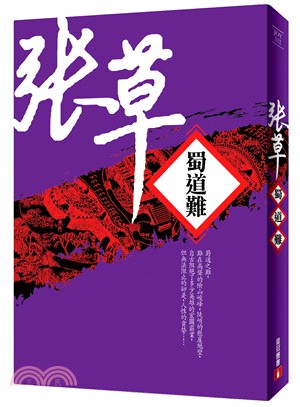商品簡介
這不只是一部武俠小說,更是一部「超乎想像」的武俠小說!
夜夢天庭,凶星降世!
究竟誰才是橫掃人間的凶殘惡星?
作家星子、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所助理教授陳國偉、作家張國立、財經部落客「總幹事」黃國華、「給我報報」總編輯馮光遠 熱血推薦!●依姓名筆劃序排列
蜀道之難,
難在高聳的險山峻峰,陡峭的懸崖絕壁,
自古阻絕了多少英雄的宏圖霸業,
但無法阻止的卻是,人性的貪婪……
明朝末年,皇家道士范羽在一場夢中預見了張獻忠、李自成之亂。他不忍天下生靈塗炭,遂命大徒弟谷中鳴尋找能夠阻止這場禍事的太白金星。
不負師父所託,谷中鳴發現線索就在張獻忠的大本營裡。然而途中他卻必須先通過攸關生死的考驗,很可能還沒找到太白金星,就會與成都一同淪陷。
另一方面,谷中鳴的師弟、都江堰總工頭姜人龍,則召集各路好漢,決心死守張獻忠欲搗毀的都江堰和二郎廟。但在與亂軍對峙之際,他卻意外發現廟中埋藏了千年的祕密,更發現師父夢中大殺天下的凶星,竟然似乎不是張獻忠?
盛衰興敗總是輪迴不斷,在張獻忠、李自成之外,難道還有更大的凶星?然而可以為混亂的天下局勢畫下句點的星君,又究竟身在何處?
三個不會武功的主角要如何演出武俠小說?張草延續《庖人誌》的創新風格,糅合歷史、奇幻、推理乃至奇門遁甲、五間兵法,重新定義什麼叫「欲罷不能」!不看武俠的人,會因為這本書而愛上;看武俠的人,也會因為這本書而打開全新的視野!
作者簡介
張草
第三屆「皇冠大眾小說獎」首獎得主,他以《北京滅亡》獲得評審壓倒性的青睞,並與之後的《諸神滅亡》及《明日滅亡》構成「滅亡三部曲」,成為華文科幻的經典之作。
張草成長於馬來西亞沙巴州,從小就廣讀群書,被戲稱為「人肉百科全書」,小學五年級即以超齡之姿贏得馬來西亞丘陶春盃文學獎公開組冠軍。後赴台灣就讀台大牙醫系,二十四歲在《皇冠雜誌》發表《雲空行》系列,一鳴驚人,之後即創作不輟,並致力於各種小說類型的創新,他的極短篇《很餓》、《很痛》,以及奇幻靈異作品《雙城》也均備受好評。「庖人三部曲」則是張草前後耗時十二年才終於完成的最新代表作,並開創了「職人武俠」的新風格。
目前張草一邊回鄉開業當牙醫,一邊參加合唱,至於手上的小說計畫,則據說再寫二十年也寫不完。
名人/編輯推薦
名家推薦:
張草筆下,三名道士雖全無武功,卻憑著道術與張獻忠派進四川的間諜部隊展開搏血戰。這個安排使故事由奇幻,更加血淋淋的真實。
我沒寫成茅山道術沒關係,張草寫得精采,於此再得強調一下,我,張某,真的是茅山張小道士的兒子,在此推薦《蜀道難》,絕對貨真價實。
──作家張國
〈推薦文〉茅山道術的成都會戰
文◎張國立
我父親來自江蘇省金壇縣(如今是市),母親則是鄰縣的句容市,聽老媽說起以前談戀愛的故事,老爸得翻過橫亙在兩縣中間的一座山才能約會。
嗯,有點勞累。
中央的那座山就叫茅山。
父親早逝,做兒子的我偏又是好奇寶寶,成天問老媽關於老爸的事,最常出現的問題是:
「把拔以前是做什麼的?」
「中央造幣廠呀,文書科的。」
「再之前呢?」
「中央銀行。」
「再之前呢?」
「念書。」老媽開始煩了。
「再之前呢?」
這時老媽放下手中的毛線,朝我瞪圓兩顆大眼珠,用威嚇的口吻吼我:
「當道士。」
厚厚厚,我爸是,師公?
事情是這樣的,我爸的家鄉在金壇茅山腳下的一個小村子,按照幾百年來的傳統,十多歲時的男生都得上山服義務役,當道士。想想看,老爸是師公,能填在家庭連絡簿內表揚一番嗎?
直到高中我終於搞清楚,茅山是道教的聖地之一,而且茅山最厲害的是降魔抓鬼的道術,名聞兩岸三地的電影界。於是問老媽的問題就有了變化:
「老爸以前是茅山道士喔。」
「小道士,當了兩三年。」
「他會不會道術?」
「什麼道術?」
「就是驅鬼降魔,什麼灑豆成兵,把死人從棺材裡叫出來之類的。」
「亂七八糟,你爸只會念書寫字。」
「真的,書上說的,電影裡也有演,茅山道士一手拿木劍,一手搖鈴,嘴裡念咒語,鬼就現身和他比武功,大部分都是道士贏。」
「在茅山混了這麼久,你爸也許會法術吧。」
好極了,說不定老爸留給我什麼《茅山法術一百種》、《降鬼十八招》之類的世不二出寶典,然後我苦練三個月,就成了當代頭號法師,不必考什麼屁大學,受盡數學的煎熬。甚至我給自己起了個法號:張一刀。
「你爸可能會抓鬼。」
老媽總算有記憶了,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生了你這個討債鬼。」
大約幾年前我還回江蘇老家去看茅山,它在群山之中,要下雨的樣子,只見雲霧飄渺,瑞氣千條,也見到穿道服的道士,不過老道士抓著我說:
「來,算個命,一條命二十人民幣。」
這不影響我對茅山道術的憧憬,一直想寫本以茅山道術為背景的小說,不過一時陷入推理旋渦之中不可自拔,一延再延,現在不必延了,因為張草的《蜀道難》寫了,而且寫得很武俠,將道術與武術結合在一起,面對張獻忠入侵成都的這場世紀大戰。
明末的流寇裡面,李自成最英雄,張獻忠則最殘酷,殺人如麻,《明史》裡明確指出他以殺人多寡做為記功的標準,他的部隊一共殺了「六萬萬有奇」,就是六億多人,顯然過於誇張,但至少殺了幾百萬。其中記錄最詳細的是他攻進朱元璋的故鄉鳳陽(如今江蘇北部與安徽接壤處),《明史》裡說:
「士民被殺者數萬,刨孕婦,注嬰兒於槊,焚公私廬舍二千六百五十餘間。」
殘忍至極。
張草筆下,三名道士雖全無武功,卻憑著道術與張獻忠派進四川的間諜部隊展開搏血戰。這個安排使故事由奇幻,更加血淋淋的真實。
我沒寫成茅山道術沒關係,張草寫得精采,於此再得強調一下,我,張某,真的是茅山張小道士的兒子,在此推薦《蜀道難》,絕對貨真價實。
序
上一部作品《庖人誌》費時九年方成,當出版社知道尚有續集時,他們也不禁頭皮發麻了:讀者等得了這麼久嗎?我不太擔心,因為《蜀道難》是從前作衍生出來的故事,應該可以寫得比以往快一些,因為手頭上都已經備足了資料,乍看沒什麼難處。這部作品是我在寫〈弈士誌〉時,發現筆下一發不可收拾,趕緊懸崖勒馬,將一大塊寫好的部分切去一旁,打算另開一條線,好讓《庖人誌》的主線更加明顯。其實兩部小說在時空和人物上皆相連,甚至重疊,所以我相信可以在一年內整理出來。
無奈事與願違,我碰上了最大的難題,亦即貫穿故事最重要的人物:張獻忠。我應該寫多少張獻忠,才不至於變成一部《張獻忠傳》?我應該在交待一件歷史事件時,如何避免將來龍去脈寫成教科書?張獻忠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他一定跟普通人一般有複雜的個性,而歷史中有關他的行為紀錄有多少真實性?如何分辨?如何才能找到最接近他原貌的文獻?
我對「張獻忠屠川」,乃至於後來滿清人「湖廣填四川」一直有高度興趣,張獻忠真的殺光了四川人嗎?在十年研究中,我漸漸看出歷史紀錄有趣的一面:隱藏在文字表面底下的「第三種歷史」(「滅亡三部曲」語),那是一種隱藏的訊息。比如有一段野史文字紀錄說,張獻忠自謂「其實我一生最大的願望是當個商人」,這句自白說明了什麼?透露了他多少心事?我不敢說發現了真相,但真相的確可以從不同文獻的矛盾衝突中浮現。即使是今日的新聞事件,都可以出現羅生門式的各說各話,所以我們又如何強求這些久遠的舊聞,有辦法完全還原真相?官方歷史不免為政治喉舌,但草民自有草民的觀點,因此民間野史多少道出了庶民角度的歷史(當然,也可能只是未經證實的八卦)。
寫這故事時,不免引發我的思緒:當天下大亂,前朝已滅,後朝未穩,國不成國,家不成家的時刻,試問該如何選擇效忠對象?忠義該如何定義? 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由個人至天下逐步擴大,此刻該選擇何者為重?自身、家園、國家或更大的,天下?
當然,各人有各人的選擇,有人選擇為已亡的國家盡忠,被評為愚忠,我看也沒什麼不對,畢竟這是他個人的抉擇,因為惟有如此方能令他的觀值觀臻於完美。但若我們不再立足於政治中心的高度來看待家國,除去忠義的包袱後,以低姿態站在民間環顧四方,看見的會是個人的掙扎求生,還有為大節的捨生取義,此時的義,不為自我而為他人,才是人性的最大光輝。
書摘/試閱
甲申年,清明。
大清早,岷江兩岸人山人海。
大家期待的,是始自北宋,七百年來相沿不絕的祀水儀式,是灌縣每年的大事,因此連山坡上、樹頭上都擠滿了觀眾。
東岸的觀眾中有名老道,白髮稀疏,勉強梳了個髮髻、戴了頂道冠,披了件老舊道袍,正睜著一對精目,緊瞪江邊。
江邊搭起了彩棚,裡頭布置妥當,但比起往年,顯得有些寒酸。也難怪,今年正月,也只不過是上個月,張獻忠已經攻進了史稱「易守難攻」的四川,全蜀各地人心惶惶,生怕哪天張獻忠打來了家門,哪有心情費心去布置?
雖然如此,成都府還是來了一位大官,他身邊有隨從數人,在灌縣的縣令、縣丞、主簿等諸大小官員陪同下,在彩棚下守候著。
老道緊盯的,正是彩棚裡的這位官兒。
那位大官面貌頗有威嚴,不怒而威,其名喚劉之渤,來頭不小,乃朝廷派來四川代天子巡狩的「巡按御史」,陝西寶雞人氏,為官剛正不阿,頗有聲名,在民間的風評不惡。
老道真正注意的,乃劉之渤的印堂。
「可惜呀,印堂黑重,恐怕過不了秋天。」老道不是在喃喃自語,他身邊有一名男子也正環視著觀看祀水的人群。
那男子三十來歲,年近四十,身穿儒服,原本容貌清正,卻留了滿面鬚碴,蓬髮胡亂紮起,不修邊幅,顯得十分老態。他對老道點頭,贊同道:「不只是他,這裡有不少人,眼看都過不了秋天。」
「那麼……」老道促狹地問:「老夫過得了秋天嗎?」
男子微笑道:「師父您頑皮了,您要敢問,弟子有膽子說嗎?弟子要有膽子說,您又敢聽嗎?」
老道摸摸頭上薄薄的一層白髮,笑道:「為師道行不高,聽了只怕日夜不安,還是免了吧。」兩人望了江邊一陣子,老道又問:「你呢?你看過自己嗎?」
男子依然微笑,但已經笑得有點不自在了。
他不喜歡光滑的表面。
不論是銅鏡、水面、漆器,只要是能令他看見自己面貌的光滑表面,他都會避免去看。
為了預防萬一,他還刻意不打理儀容,弄得自己髒兮兮的,即使不小心看見了,也看不清楚。
他和師父繼續觀察巡按劉之渤。
劉巡按知道,他是這場年度好戲的要角,一定要演得好看,贏得喝采,尤其在這種時局,更是需要一點振奮人心的事。
早在前一日,他已自成都府啟程,途中先在郫縣停歇,那裡有座「望叢祠」,祭祠著蜀國古帝「望」、「叢」二人,他按照習俗祭拜了古帝,直到午後才抵達灌縣,夜宿縣城裡頭的行台衙門。
次日,劉巡按在禮樂隊伍開路下,依規定到「伏龍觀」、「二郎廟」等處一一祭拜了,才來到河岸邊搭好的彩棚,準備主持放水儀式。
他將要主持的這場放水儀式,是灌縣每年春天的壓軸戲。
灌縣緊鄰著岷江,江上有世間最古老的水量控制系統「都江堰」。每年休耕後,灌縣都會召集河工,截斷河水,對都江堰進行一年一度的「歲修」,然後擇日放水。
眼前的岷江,分成內、外二江,外江正滾滾而流,內江則被一道泥埂截斷了流水。這泥埂乃由整列榪槎(三腳架)圍成,許許多多的木製榪槎排成一列,朝著上游的那一面墊上竹笆、抹上黏土,便成了截閘用的泥埂,河水斷流後,河工們便能下到河床去清理河沙、築高堤堰。
這是灌縣每年長達五個月「歲修」的尾聲,只待劉巡按一聲令下,拆除榪槎,江水便會洶湧的衝向內江,灌溉下游的成都平原十七縣,農民們就可以開始插秧了。
與此同時,劉巡按也要準備好馬車,在江水沖毀榪槎的同時,飛奔往成都府,務必要趕在水頭之前到達,否則就會被認為不吉祥,會影響這年的灌溉水量,進而造成收成減少。
在一陣鼓樂聲過後,劉巡按焚香祭祀,拜過水神,開始唸起一長篇祭文,感謝秦朝建造都江堰的太守李冰,感激二郎神的守護等等。
老道拉長耳朵,無奈距離很遠,身邊水聲潺潺,實在聽不清楚劉巡按在唸些什麼,於是轉身問徒弟:「昨晚你有觀星嗎?」
「有。」
「紫微垣黯淡,你可見否?」
「見,不特此也,將星無光,星宿撩亂,只怕……」
「只怕什麼?」
「應在春天。」
「徒弟說得蹺蹊,今天是清明,春天都快完了,什麼應在春天?給我說明白些。」
男子搖頭道:「十天半月以後,驛道上必有噩耗傳來。」
「所以,這一盤棋,你該怎麼下?」
「弟子胸中已在布局。」
老道微微頷首,道:「老夫這一生無甚作為,最欣慰就收了你們這兩位好徒弟,青出於藍,不枉我一生。」
男子微微作揖,道:「弟子還要感恩師父教得妙、教得巧,這日夜下棋積來的工夫,可是沒白費的。」
「你師弟已經在這頭守住了,可以放心,」老道甩了甩頭,「你且去吧。」
男子點頭,隨即拱手拜別老道,走向繫在樹下的一匹老馬。
這馬原本是匹驛馬,平日在驛站服務,後來年老力衰,足有扭傷,驛夫商量了要賣與屠戶,另購新馬,正巧這男子路經驛站,聽驛夫說要牽去屠戶家,老馬淚眼直視男子,男子一時動了憐憫之心,便問了價錢,盡掏所有,連師父的酒錢也交了出來。
他將老馬牽回山上時,告訴馬兒道:「師父問起酒錢時,你可千萬幫我。」
果然師父勃然大怒:「徒弟你好糊塗,老夫喝了半月齋酒,好不容易存下些子兒解饞,怎奈你自作主張買匹賤馬,真是雞肋!」
「何謂雞肋?」
「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師父云,「不特此也,還白養一口吃飯的。」
「師父放心,咱山上雖說拮据,惟獨不缺草料。」
老馬也識人性,兀自踱到外頭,在久未打理、雜草叢生的院落大快朵頤起來。
今日灌縣放水,老馬難得下山,見到年輕時走過的舊路,心中不禁躍動,腳下也不安分了起來。尤其當男子鬆開樹幹上的繩子,作意要騎上時,老馬更是鼻子兩孔噴氣。
「稍安勿躁,」男子道,「路還長呢。」
那邊廂,劉巡按已經唸完了祭文,完成了一切繁文縟節,觀眾們開始躁動起來,他們等待已久的時刻終於來臨了。
劉巡按舉起令牌,幾名壯碩的河工隨即跳上榪槎,舉起手斧,等待著。
只聞劉巡按大喝一聲,將令牌拋出彩棚,河工總工頭一聲令下,大漢們在眾人歡聲雷動中揮動手斧,斬斷連結榪槎的繩索,榪槎馬上鬆動,被江水推得蠢蠢欲動,格格作響。河工們再將粗繩綁在幾棟榪槎的頂端,由十餘名大漢在岸上合力拉扯,口中邊唱〈開水號子〉:
喝呀,喝呀,莫壞良田,莫毀橋堰。
喝呀,喝呀,安流順軌,造福百姓。
不一會,幾棟榪槎被拉倒,江水從決口湧入,沖毀了整列榪槎,泥埂隨之解體,木架、竹笆、泥塊悉被江水吞噬,捲入河底,水頭如同狂奔的巨龍翻滾入河床,一路朝成都府湧去。
河工們舉起竹竿猛打水頭,嘶喊著號子,叮嚀水頭要注意前面的路,因為這一年的收成就靠它了,兩岸民眾放聲歡叫,年輕人沿江奔跑,邊喊邊用小石子投向水頭,老人們則伸長了手,要用勺子接住「頭水」,拿回去祀神祈求豐收。
劉巡按早在榪槎未被沖倒前,業已登上馬車,沿江岸平路直奔成都府,前頭有兩位健卒騎馬開路,後面有八騎護衛,由成都府驛站最好的驛卒駕御馬車,馬車也是成都府驛站最好最平穩的一輛,專供他這種大官乘坐。
劉巡按不時回頭,生怕被水頭追上,只見水頭在遠處滾動,端的有如碧藍色的巨獸在嘶吼追逐著他。
男子見劉巡按出發,便用力一拍老馬後頸,老馬隨即拔腿飛馳。
經男子悉心調養,老馬的足傷早已痊癒,飛跑起來不輸當年。
老馬四蹄如勁風,意氣風發,暢快呼吸著透過清晨露水撲鼻而來的草香,那是牠往日在驛道上來往熟悉的氣味。
岷江沿岸有許多民眾爭舀頭水,也有小孩手握石子,興奮的等待要擲向水頭。
為劉巡按開路的驛卒不停呼喝,提醒岸邊的人們讓開路,免得受傷。
忽然,前頭路上冒出一個小孩,拖著兩行鼻涕,手中握著石頭,看見兩匹軍馬和馬車衝將前來,小孩目瞪口呆,不管驛卒怎麼呼喊驅逐,小孩依然被嚇得忘了躲避。
御車的驛卒心中大呼不妙,他不能停下,否則劉巡按會被水頭追上,他可擔當不起,心念至此,他更發起狠來抽打馬匹,無暇顧及小孩生死了。
正當驛卒奮力抽鞭,身邊倏地掠過一匹快馬,搶到前方,馬背上有儒服男子弓腰,身體半吊在馬兒側邊,只見他長袖一甩,不知使了什麼手法,小孩便滾去一旁的草叢,這才嚇得放聲大哭起來。
雖然如此,小孩毫髮未傷,哭了一回,水頭將至,岸邊歡呼聲響起,小孩又興沖沖的跑向河邊去了。
那男子這一闖,令馬車前後騎馬的護衛大驚,齊聲喝道:「大膽!」
那男子不理會護衛,策馬趕在前頭,似乎在為他們引路,劉巡按見了方才驚險一幕,忙問驛卒:「前面的是什麼人?」
「小人不知!」驛卒回道。
「莫非是縣裡另有派人保護本官?」
「小人沒聽說!」驛卒兩眼直瞪前方,不敢回頭。
劉巡按驚疑不定,而今流寇四竄,他擔心是強人攔路剪徑,又聞張獻忠已從廣西攻進了四川,正一路朝西推進,不知何時會兵臨城下。他深覺趕不回成都府事小,失了性命事大,心中不禁祈求諸佛菩薩庇佑,能平安回到家才好。
那前頭騎馬的男子拐過一個彎,馬蹄聲漸行漸遠,很快就消失了蹤影。
等了些時,劉巡按仍不見男子再在前方出現,心中又是忐忑不安。
此刻驛卒呼喝馬兒,馬車依舊直走,河道則漸漸遠去。
看官需知,這一路從灌縣至成都府,並非緊貼河岸而行,只因這江水分支甚多,左彎右拐,而驛道則大多有橋樑直接跨過河面,直行無礙,以利公文迅速傳遞,是以水流雖疾,馬車也仍舊有可能追過水頭。
馬車過了六七道橋時,終於經過郫縣,表示路途已過了一半,此刻晨霧盡散,日頭已從山後爬出,只消跨過洗腳河上的八里橋,便是一路無阻直抵成都府城了。
八里橋兩側也站了不少民眾,見水頭自遠方滾來,眾人紛紛舉臂歡呼。
此時,劉巡按又見到那名男子了。
男子亂蓬蓬一頭褐髮,很是惹人注目,他騎馬立在橋頭,臉色凝重的眺望橋上群眾,沒理會劉巡按的馬車。
劉巡按忍不住轉頭看看那男子正望著什麼,但男子又再次上路,策馬慢行,慢慢跟在後頭,不知在打些什麼主意。
前方是一座猛惡林子,過了林子,就能望見成都府城牆了。
林邊是大片田地,有兩個農夫頭戴竹笠,正整著田,準備即將開始的耕季。
林子樹木漸行漸密,前面的路被大片翠綠壓下,只聞前面的護衛大喊一聲,劉巡按一驚,這才看見路中央站了個綠衣客,眾人被林子的綠色花了眼,爭些兒看不見他。
「閃開!」前頭護衛嚷道。
眾人看清,原來綠衣客手中還橫了把長刀,這長刀含木柄有一丈長,前端二尺利刀,不見刀光,只因刀身被乾硬血色染暗了。
綠衣客眼神迷茫,似是久睡初甦,見馬車衝來,不躲不閃,不疾不徐,掄起長刀,將迫近眼前的軍馬前肢一刀斬斷,這下馬失前蹄,那護衛滾下地來,綠衣客又將長刀順勢一帶,護衛的頭顱則骨碌碌滾去一旁,頭顱的面上依舊一臉茫然,不知自己已赴黃泉。
突變橫生,劉巡按嚇得六神無主,他日憂夜怕的就是這樁事,偏生果真遇上,頭頂先寒了一片,胸口頓時緊悶,只覺死期就在眼下了。
馬車後面的八名護衛也抽出大刀,策馬前來,圍著綠衣客,他們恃人多馬高,只圖嚇跑綠衣客。
沒想到,綠衣客正是不要命的,他冷笑三聲,長刀一揮,割傷馬鼻,馬兒受驚,前肢高舉嘶叫,將一名護衛摔下背來,還來不及舉刀,就被綠衣客一刀結果了性命。
護衛們根本沒料到他們轉眼就失了兩名夥伴,目睹夥伴慘死,綠衣客又氣勢洶洶,他們鬥志盡失,更別說性命相搏了。
「好大狗膽!你是什麼人?! 」倒是劉巡按當慣官兒的,驚怕之餘還記得問話。
綠衣客咧嘴笑道:「我是來送你一程的。」
對方回答了,劉巡按就壯了幾些膽子,高聲道:「咱昨日無冤,明日無仇,奈何要我性命?死也該有個明白。」
「老子也不曉得你名姓,只認得你是個巡按,」綠衣客啞聲笑道,「老子只知道要殺巡按,若是殺得稱手,有陪死的也不賴。」
御馬的驛卒面無人色,顫聲道:「好漢別殺我,我沒刀沒劍,只管策馬。」
「少囉嗦!」綠衣客叱著,揮刀要殺。
護衛們知道恫嚇無效,眼前只有努力進擊,說不定還有機會活命。
為免綠衣客再傷馬匹,令他們在馬背上無法揮刀自如,他們於是跳下馬來,朝綠衣客一擁而上,舉刀便斬。
綠衣客嗤道:「趕死!」兩手握柄,左斬右劈,護衛們竟完全招架不住,一時腥風血雨,路面鮮血浸足,斷肢狼藉,六名護衛登時斷送性命,餘下兩人也殘缺不全,倒在血泊中呻吟。
綠衣客正待結果他們,劉巡按只聽一聲怒吼自後頭傳來:「該死!」巡按大驚之際,一匹老馬掠過馬車旁,馬背上正是方才的蓬髮男子,他未待拉停馬足,早已跳下地來,綠衣客長刀朝他揮來,他只彎身一躲,就錯入綠衣客鼻前,奮力刮了他一巴掌。
這巴掌極響,綠衣客竟措手不及,整個人倒地。
「畜生!畜生!」蓬髮男子焦急的嚷道,「遲來一步,教你傷了許多人命!」
綠衣客何曾受此大辱,怒不可遏,一勢「推山塞海」直殺蓬髮男子,要將他切個稀爛。
蓬髮男子口中依舊罵著「畜生!」欠身一躲,一手拉住長刀把柄,止住來勢,又賞了綠衣客兩巴掌,打得他兩臉紅腫,口角流血。
此時驛卒透過林子發現大路旁的田地趕過來兩個農夫,忙向劉巡按說:「大人,你看。」劉巡按見了,直喊道:「救我!救我!我是朝廷命官!救我有賞!」
沒想到,兩個農夫從身後亮出斧頭,兇狠的瞪著劉巡按,滿臉殺氣。
蓬髮男子抽空回了一下頭:「聽著!」接著又回頭與綠衣客糾纏起來,口中邊說:「你們快趕路!莫錯過了水頭!」
驛卒如夢初醒,忙抽馬鞭,馬兒嘶叫幾聲,啟步前行,其他無人坐騎的軍馬也要跟上,綠衣客急了,朝田地趕來的農夫嚷道:「快來!雞要飛了!」一面揮刀衝向馬車。
蓬髮男子撿起地上的一把刀,舞了個刀花,阻擋綠衣客。
綠衣客血絲脹紅了眼,狠命攻擊,蓬髮男子凝神迎戰,兩人各有心事,一人要殺劉巡按,一人要讓開路令劉巡按逃走,雙方一時僵持不下。
蓬髮男子忽然一個閃神,守勢全失,中門大開,眼看長刀便要斬至頸上,綠衣客心中大喜,不料正中其計,蓬髮男子一哈腰,從下方搶上前去,將刀尖直捅綠衣客。綠衣客心下一寒,忙倒退三步,讓出了一大片空位,馬車逮到機會,飛馳而過,其他失去主人的軍馬也嘶鳴著跟上,幾將綠衣客撞倒踩傷。
兩名執斧農夫正好趕到,他們丟開頭頂竹笠,露出修羅也似惡相,哪裡是農夫模樣?其中一人臉上刀疤劃過鼻梁,幾乎將鼻子分開兩段。
他們手上的不是小斧,而是一揮就可斬斷牛頭的大斧,見蓬髮男子放走劉巡按,兩人怒喝著上前,雙斧並使,要將男子劈個粉碎。蓬髮男子冷笑一聲,道:「正角兒已去,你們還有什麼戲唱?」
說話間,利斧已到,蓬髮男子腳下一移,直瞪他們雙目,兩農夫未及回神,已翻過林子滾了兩三個筋斗。
「你是什麼人?壞我大事?」綠衣客又怒又驚,心下好生疑惑。
「時候未到,」蓬髮男子道,「巡按之命不在此時此地斷送。」
「老子不殺你,難消心頭之恨!」
「你也別急,今天也還不是你的死期。」
綠衣客更困惑了:「你究竟是誰?」
地面傳來一聲呻吟,原來方才有兩名護衛還活著,惟傷口流血不止,面色越來越蒼白,恐怕難有生機,在意識模糊間微弱的哀叫著,似在呼喚娘親。
或許在彌留之際,他們憶起了些許往事。
蓬髮男子眼中泛現淚光,懊悔著因為他遲到而平添幾條冤魂。
眼中有淚,視線不清,正是攻擊良機。
綠衣客撚刀撲前,兩名農夫也早已爬了起來,三人一起圍攻男子。
忽然,三人皆停止了攻擊。
因為那名男子不在了,不在他們的包圍之中了。
男子已經走到林邊老馬處,邊拭淚邊上馬。
他們甚至不知道男子是何時脫出他們三人掌控的。
蓬髮男子吆喝一聲,老馬展開四蹄,取路望成都府奔去,留下不知所措的三人。
這綠衣客和蓬髮男子最後一次決生死時,已是入秋時分,其時成都府以南悉成鬼域,天府之國,古蜀之地,成了一片血海汪洋。
這話頭且先按下不表,且說巡按劉之渤的馬車趕至成都府,正好趕上水頭,眾人聚在河邊歡呼,一片喜氣洋洋,然而劉巡按驚魂未定,仍不時回首觀望有無追兵。
成都令吳繼善與一眾官員站在城門,見劉巡按神不守舍,又見護衛軍兵並未一同回來,只有數匹軍馬跟回,心知出事,忙上前追問究竟。
劉巡按面色蒼白,直道:「禍事!禍事!」他剛逃過一劫,總算鬆了一口氣,身體才開始發寒,不由自主的全身顫抖,驚懼得一個字也說不出口。
吳繼善忙問御馬車的驛卒,驛卒也抖著唇道:「大人恕罪,小……小人腿軟,走不下馬車,沒向您下跪。」
「他來了!」劉巡按忽然叫道。
吳繼善一瞧,大路上來了匹老馬,坐著位形色可疑的邋遢男子,忙叫身邊兵馬上前:「拿下那廝!」
「吳大人且慢!是救命恩人!」劉巡按急忙步下馬車,面迎蓬髮男子,那男子也下了馬,唱了個喏,劉巡按忙道:「好漢何名?救了本官,必有重賞!」
「大人,重賞且免,留作與方才那幾位死難軍兵家人好了。」蓬髮男子道,「還請大人加派兵馬,回大路上去收屍。」
劉巡按不住點頭:「壯士仁義,不知乃何方人氏?可知道那幾位剪徑者是何人,武功恁般了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蓬髮男子用力搖頭道,「我不知道他們是何人,也不知道我是何人。」說著,快步走向老馬,上馬前又回頭道:「總之,大人千萬別忘了去收屍,生逢亂世已是可憐,落得無主冤魂更是悽苦。」
蓬髮男子不願留名,口中吆喝,驅了老馬回大路而去。 成都令吳繼善見男子相貌不凡,急問身邊眾人:「誰人認得那位好漢?」
「回大人,小人見過,」一名官軍忙道,「小人記得是青城山上的道士。」
「道士?」
「小人在青城山巡視時見過,但不記得是何觀何院。」
「可以了,退下。」吳繼善兀自沉思著,不再理會那名官軍。
可是在官軍心中,已然緊烙上蓬髮男子的形貌,他拚命尋思見到那男子的道觀,他萬萬沒想到的是,四個月後,他們會並肩作戰。
在場所有人更萬萬沒想到的是,三個月後,驛道上才會傳來一則遲到的噩耗:遠在北京的皇上駕崩,而且沒有後繼者。
皇帝是自縊的,是在流寇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後,眾叛親離,走投無路下,走到皇城後山去上吊的。
這等於說,大明滅亡了。
灌縣放水節的這時節,距離大明被李自成滅亡尚有二十來天。
追本溯源,需先由老道士在三十九年前、也就是萬曆三十三年的一場夜夢講起。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