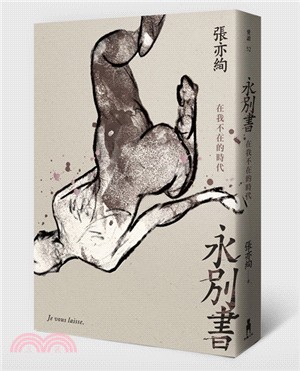商品簡介
內容簡介
認同,有那麼難嗎?無論是族群的、性別的......
奇形怪狀的台灣歷史,慘絕人寰的愛慾重生
今年最駭人的小說
這是屬於女孩的必經之路嗎?這是屬於台灣的國族寓言嗎?
張亦絢長篇小說代表作
孫梓評:書中人物之鮮明,心理地景之立體,又讓我感覺它能不只屬於同女,而剝除了性別,像十四歲的賀殷殷竭耗心神求得的一悟:「基本的人性」。(……)它更廣泛寫出了人在感情裡可能的殘忍和容忍,屏息讀著那些流淌過皮膚表面的高溫情感熔漿,使人隱隱想起某些久遠之事(……)啟蒙同時也是(開)啟盟(誓),無論守約或背棄都是艱難。
張亦絢:把這個方法跟你說到的「國族寓言」併看,我更傾向說它是「國族欲言」;設計的是一整套的退化與退行,在這裡說「死外省人」是OK的,「歷史讓人頭痛」也是OK的﹝……﹞如果說「代言」,應該不太是 「代言」,而是「帶言」。因為我關心的是語言的可能性,而不是完好的論述。
——摘錄自《永別書》附錄〈別後通訊:在揮手的時間裡〉
這終究是一個關於愛的故事。
記憶會傷人── 這是賀殷殷,從出生始,就難逃的命運。父親告訴她:「賀殷殷的殷,是殷海光的殷。」──但是這故事,並不單單勾起早期的民主運動記憶,有一天,它還要溯及日治時期閩客通婚的變形家庭。在此誕生的賀殷殷之母,將是文學中非常難以消化的角色──口口聲聲保衛客家文化的她,能把最簡單的台灣事,都說得破爛不堪。然而這,全只因為國民黨政權,施加於台灣島的噤聲歷史使然嗎? 除此之外,透過私密、甚至是檯面下的小恩小怨小彆扭,作者刻畫了,比使命感更複雜的,那些催生,或延誤同志書寫的頡抗因素。那些,文學史絕對不會告訴你的事……。「雖然我個人有點不甘願,但我最後還是發現,這終究是一個關於愛的故事。──認同,有那麼難嗎?無論是族群的、或是性別的認同......我的答案是,沒有錯,認同有夠難,難上還加難。──但這不代表我們會轉身離去。這本書的企圖,仍然是種共患難,一個『我在這裡』的認真回聲。關於寂寞及其未被毀滅。」張亦絢道。
本書特色
◎收錄孫梓評×張亦絢書信往返〈別後通訊:在揮手的時間裡〉,看見小說家究竟在想什麼。
作者簡介
張亦絢
1973年出生於台北木柵。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及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台灣文學選。另著有《我們沿河冒險》(國片優良劇本佳作)、《小道消息》,長篇小說《愛的不久時:南特 / 巴黎回憶錄》(台北國際書展大賞入圍)。
目次
致讀者
第一部 在妳的心裡有風景,還有暴風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二部 如果你看得到我的記憶,你會吃不下飯。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後記
附錄一 別後通訊:在揮手的時間裡╱孫梓評•張亦絢
附錄二 情不自禁及其他:答編輯問
書摘/試閱
第一章
我真的打算,在我四十三歲那年,消滅我所有的記憶。
這是個狂野的夢想?是嗎?我倒沒想到可以用幽默感來面對這事。幽默感啊,總是不錯的。是我喜歡的東西。這背後有個悲劇吧?這一點我還沒開始想呢。或許吧,但我還不知道呢,究竟什麼可以稱為悲劇──。什麼可以不稱為悲劇。說是悲劇好像有點太唬人了,簡直像穿了戲服,在轟隆轟隆的音樂裡面。
或許有些政治意味吧?別嚇我,消滅記憶怎麼會是政治呢?一向就只有記得、不忘記,才稱得上政治呀。更何況,我是自願地、自動自發地,消滅我的記憶,這不牽涉到任何別人,不,這跟政治絕對扯不上什麼關係,至少在政治這詞的高尚意涵上 。
這麼說來,你不打算政治也不打算高尚──或許你是打算犯罪吧?哎呀呀,事情說得越來越有趣了,真令我煩惱。如果是,你打算告發我嗎?去那裡告發呢?告發一個消滅記憶的人,這可是比消滅記憶更困難的事吧?尤其是我將消滅的,不是任何其他人的,而是專屬於我一人獨有的記憶。
說起來,不高尚或是犯罪的事, 人人都在不知不覺中進行。說真的,我想我要做的事是很普遍地,不同的人,因為不同的原因,每天都做上一點。但是像我這樣,把計畫訂得如此明確,又如此重視過程,或許,就沒那麼普遍了。
我想把話說得更清楚些。我八十六歲的老阿嬤在世時得了失憶症,她既認不得家門口的街道,也分不清我們這些孫子孫女誰是誰,變得非常麻煩──我所想要的,不是這種。當然我也不打算拿根棍子敲昏自己,或是把腦袋往牆上撞那樣,這或許會使我腦震盪,或是變傻,但未必會真的消滅我的記憶。我對我的目標是認真的,消滅記憶是多麼要緊的一件事,要是我變傻了,我看恐怕成功率就不大了。我要消滅最特殊的成份,不是像記得自己的住址,或是如何騎自行車這樣的記憶。
在我的理想藍圖中,記憶消滅後的我,可以跟一般人無異地生活與社交,可以工作,也可以說笑話,或許還更博學多聞,可以背誦莎士比亞的長句,再加上五湖四海中所有的水壩名稱──為什麼要記得水壩的名稱?我也不一定要記得水壩的名稱,把它換成別的東西也成。總之,我想我可以在外觀上打扮成一個有記性的人,但就是不需要有「我的記憶」了。這很難了解?難懂?讓我先說說,我是怎麼發現這件事是可能的:我完全是無意之中發現的。
我第一次夠有意識到這件事,是在惠妮休斯頓死去的那幾天。
惠妮休斯頓是誰,現在你很容易可以在網路上查到,如果你想知道她這部份,你自己去查就是了。假如資料有錯,我也沒辦法,畢竟我對她知道得也不多。雖如此,我這一生至今為止,卻一直小心翼翼提防著她,彷彿她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敵人,那樣提防她活了過來。但是她始終陰魂不散。我想想看,這要打那裡說起呢?
惠妮休斯頓唱過一首歌,叫做〈心碎者何去何從?〉。在我十三歲時,有個人,提示了我這個歌名:我說提示,真的是種提示。這人說:如果妳想聽英文歌,妳可以聽這四首。然後有張字條就交到我手上,上面用英文字寫了四首歌的歌名與歌手名。
這四首歌分別是芝加哥、混、皇后合唱團以及那首我說的惠妮之歌。我之所以把它們都交代出來,是因為這些歌與我的記憶關係錯綜複雜。混與皇后合唱團的主唱,他們竟然都同志甚深──皇后的弗萊迪,我之後還會提到,他因為愛滋去世,還是這四個歌手中最長年陪伴我,成為我整個精神上美學空氣的一個──一個聲音。
弗萊迪是個在英國的帕西人,他跟坦尚尼亞和印度都有些關係,我們談了那麼多的後殖民大師霍米巴巴,巴巴的帕西背景什麼孟買雜燴之類,但是天啊天啊──啊不是的,我的重點並不是同性戀或後殖民,何況,我雖然知道一個男人的樂團,叫自己皇后叫自己QUEEN,大概不會正常到那裡去。但要說我就嗅出什麼同性戀的東西,可就差遠了。我沒特別感覺到這部份,就像「性」一樣,我不是不知道它的存在,也不是全無聽聞或經驗,但它終究是很混沌。當一切還在我年紀輕輕的生命裡時。
QUEEN對那時的我來說,自自然然地──只等於音樂──當我崇拜地說到,QUEEN的人聲與配器真是無與倫比,我從沒想到什麼同性戀或是後殖民東西。直到有天,我已經過了三十歲,我在上完床後,在床上提到QUEEN的音樂特殊性,從當時男人深受傷害的臉色,我才忽然意識到:我可真是漏掉某些許多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了。附帶一提,當時我人不在台灣。我雖然離QUEEN的所在地只有一個海洋,只要坐個什麼之星的火車就會到達,但我對它的認識仍完好地以台灣青少女的記憶所保存,我的地理位置並沒讓我新學到什麼,我想到有個「理所當然之事」,是在床上發言不慎之後。
理所當然的東西,是什麼東西呢?我之後也許會說到,也許不會。但現在讓我回來說惠妮休斯頓。在我的青春期,我沒聽過其他三人的事蹟,我喜歡音樂,但我是對流行慢半拍的那種青少女。一直到「混」解散了,我才知道有這個樂團。我可以說一件事,讓你明白我是多麼經常不在狀況內:當我讀國中時,我的國中發起過美化廁所的運動,是真的,不只是運動,而且還是全校競賽。敝班級還拿了冠軍。那個國中那麼無聊?就是台北市的一個國中。你覺得這很無聊?那我很慶幸地告訴你,我對這個競賽一點貢獻都沒有,但我還記得這事,是因為在美化廁所的過程中,我得罪了班上的一個同學。她把心愛的「杜蘭杜蘭樂團」的海報帶來,深情地將她的偶像指給我看,因為我是一個樂意與人為善的好同學,我於是認真地看了那海報,並以同樣深情地回答她:「這人的臉長得像小鳥的臉耶!」──結果導致這個同學,氣得一星期都不願意跟我說話。
大家崇拜的都是歐美的樂團歌手嗎?也不盡然。那時還戒嚴啊。現在的七年級 對戒嚴是怎麼回事,一點概念都沒有。有天有個七年級告訴我:「『戒嚴』這兩個字只會讓我們想到,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發生的事,就像『古早味』一樣。」我差點沒翻臉:「台灣戒嚴三十八年,是全世界戒嚴最長時間的國家,別的不知道,至少這點妳要記得呀。」但她會記得什麼呀?就算她如我所說,記得「戒嚴三十八年以及破世界紀錄」,你說這就算記得嗎?那不過就是一堆字罷了。不可能地,記得──是不可能地。
所以我說記憶這事不是那麼簡單,用文字記起來的東西,或許是最空洞的。七年級的絕不會像我們六年級的那樣記得戒嚴,但四五年級的,你知道嗎?我覺得,他們又記得太牢了,有時會讓我想說:難道你們都忘記,已經解嚴過了嗎?真的。去年我碰到個四年級的做紀錄片的,他說到二二八,竟然還很噤寒,他說到王添燈的弟弟,卻不敢把王添燈的名字說出來。散場後我忍不住去找他,問:「你說的王姓二二八受難者,是不是就是王添燈呢?」果然就是。
我為什麼知道?我告訴你,這裡面有個很美的東西,我始終忘不掉。王添燈是開茶行的(紀
錄片的主題是茶不是二二八,但茶和紀錄片說真的也不是我的興趣,我在因為走錯地方才聽到這
場演講的),他們說,王添燈女兒小的時候,茶行的工人們會把她擲到茶行中的茉莉花茶叢裡讓
她玩,當然這一切是發生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啊,我真是忘不了這個意象,茉莉花茶叢我從來沒見過,茶我也老實告訴你,我沒什麼研究。不過這個把小女孩丟到茉莉花叢裡的故事,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忘不了,如果有天我忘記了,我真希望有人能記得。就是因為我記得這個茉莉花叢的故事,我推論出那個四年級的,說到的人是王添燈,那個四年級的人,說了真多有關茶的事。我跑去說「王添燈」這三個字,可以說都是因為茉莉花叢的關係。
為什麼?因為我猜,我只能猜,那個小女孩,你想想,之後她能多麼記得茉莉花叢嗎?我想是不能。她或許還記得。但是你想想,之後發生了那麼多事,父親失蹤且被殺害,且這一切都是在很侮辱人的惡性沉默中進行地,就算她記得了童年時代純粹的感官與愉悅,你能想像,那份純粹,不被後來的悲傷與苦難,弄得變形扭曲嗎?茉莉花香可能還是那麼香嗎?所以說,茉莉花叢中小女孩的記憶,嚴格來說,或許是不存在的。說它是記憶,不如說它是種「不可能的記憶」。
記憶是最殘酷之神,不在於有殺戮與不公正,而是我們從來沒有「一個」記憶。總是會有第二第三或第四,如果一個人非常非常幸運——這種異常的人我沒有碰過,如果你碰到不妨介紹我認識,這種人要不他很早死,就是很呆,再不然就像我打算實驗的,有計畫地消滅了記憶——讓我回來說「幸運」這事,我想只有非常幸運的人,他的一二三四記憶可以彼此不相互下毒、吞噬與侵害——。這種事,我想是不可能的。最可能是這人很呆,一生既不經過什麼,也不存取什麼。但一個人縱使被囚禁或癱瘓在床,也無法達到這境界。人就是人,除了腦病變,總是有記憶的。這真是個大不幸。
這麼說來,難道,妳是為了得到某種幸運,才決定要消滅妳的記憶?是啊,不然你以為是怎樣?你不要因為我打算消滅記憶,就把我想成個齜牙裂嘴的劊子手或狠心的人。我自認,是個相當愛惜自己的人呢。如果你願意,你也可以稱我為「追求幸福的人」。這你,或是任何人都不能反對吧?你沉默,表示你對此有意見卻難以表達。這也好,任何一種態度最好都有一個沉默的反對者,這可以使一種態度,不至於成為絕對。
我國中時,紅星都是香港的,劉德華或郭富城,不過你不能寄望一個少女時代在男歌手臉上會看到鳥臉的人如我太多,你可以去查查什麼流行歌曲社會史的東西,為什麼那年代少女崇拜的都是香港或歐美歌手。我想你可以得到驚人的發現。我記得劉德華和郭富城,也是因為廁所美化比賽的關係。因為後來有女生抗議,在偶像的眼神凝視下,會尿不出來。我?我不會。我不會尿不出來。我當時有很多煩惱,連去上洗手間時,都是心不在焉的。我甚至沒有注意過那些海報。但是對其他的女生,事情就不是這樣啦。所以啊,最後那些被費心貼在洗手間的明星海報,又被費心撕了下來。
這樣的事妳也記得,妳記性可真好。當然囉,如果我是要消滅毫無價值的東西,你想這事又有什麼意思呢?
記憶,或許是我最擅長的事情了。我從很小、很小、很小開始,就非常有意識地鍛鍊自己。
我可以告訴你,我的前半生啊,都是在「我絕不忘記」這五個字的鐵律下度過的喔。只是有天,
我的想法改變了——。徹徹底底改變了。
回來說QUEEN,我沉浸在他們的音樂裡,卻連他們的臉都沒好奇過,更不要說他們的性傾向或性生活了。但是惠妮,一直有人告訴我,她「其實是女同性戀」。也不知道這能不能說是奇特的同性戀文化,總是會有人不停告訴妳,孔子或耶穌「其實是同性戀」;白雪公主或媽祖也都「其實是同性戀」。但是沒有人知道,「其實是同性戀」,到底是不是同性戀。或說除了「其實是同性戀」之外,有沒有誰是「其假是同性戀」。你問我是不是?是不是同性戀嗎?
那要看你認為,一個人有沒有可能了解他自己。我可以告訴你,我贊成某些事、不贊成某些事,那是一個意見或想法,可是關於「我」這個東西,「我」這個奇怪的東西,我可以說的是,每當我要在它之後加上等號,等號之後往往就還有括弧,而括弧之後,又有小括弧——有時還有無盡的問號。這就是我的問題。我想我是一個記憶大於定義的人。當定義想要推翻某些記憶時,我總不讓記憶倒下,你知道,就像希臘神話裡的薛西佛斯,石頭滾下來,我推上去。你放心,我並不像你想像地,對這問題刻意保持沉默,因為我正要說到,關於惠妮的那首歌。說真的,一直以來,我都毫不關心惠妮其實或其假是個同性戀,她不是我生活中的人,關於她的謠傳,我聽到時,也不過是在心裡「哦」了一聲。完全說不上相信,或是不相信,因為我並沒有那種需求。她對我的影響是在另一方面:她讓我想到,那個遞紙條給我的人。
你曾經要某人去聽某音樂嗎?或者如今日,你會從YOUTUBE寄歌給某個人嗎?這種事,我至今也還在做。有時我寄,有時我收,用網路語言來說,這叫做「分享」。這是一種友好,或是尋找同類的表示,我想。這一點都不嚴重。事情本身可以說是平淡無奇的。
但是當我十三歲時,這事被我賦予了特殊意義,之後這份意義如滾雪球般跟隨了我前半生。我接受那紙條如接受愛情。幾乎是幼稚的、完全是天真的——但是既然我已打算消滅我所有的記憶,我也就不需保護顏面地告訴你——我愛那個寫紙條的人,愛得一塌糊塗。這是我人生最不堪的秘密,我知道那種東西:那種下流的、失心瘋的、動刀動槍血濺四處上了社會版的狂愛——與那些社會版的主角們唯一的不同是——我沒有表現出來我真正的感覺——取代成為一個尊嚴掃地為愛瘋狂的人的是,我苦苦地成了一個,一心一意,聽音樂的人。
你在我的事蹟上看不到這個部份,我所做的最不優雅的事都在我心中:那些我的記憶。
***
別後通訊:在揮手的時間裡
孫梓評╱張亦絢
亦絢:
在很多地方讀《永別書》:與你所在之地隔一座小山的窗前,將睡的枕邊,打烊的辦公室,快速移動的高鐵上,老家已不屬於我的房間……讀到將近一半時,心跳得很快,我想我不能繼續下去,得喘口氣,在夜半像個鬼魂,摸黑點亮書房燈,找出《壞掉時候》和《最好的時光》──我必須把上游搞清楚。整個讀完《永別書》,我又取下《愛的不久時》,倚著枕頭,驚心動魄重讀一次。這迂迴的閱讀路線,有心人若跟著跑一遍,或許可以探出你小說裡幾個大主題的重複編織與變奏:家庭創傷、女性主義、同性戀(及其他)……但會否就不漏接《永別書》裡,由你輪番拋擲而來之物?我不確定。
乍讀《永別書》(尤其第一部),以為它是一本別開生面的啟蒙小說:關於愛情。 雖你曾私下表示《愛的不久時》為典型「戀愛小說」,然而真正無法脫逃的,畢竟還是像〈幸福鬼屋〉的傾訴者與傾聽者;〈性愛故事〉的純青與黃鳳;〈在灰燼的夏天裡〉的許幼棉與賈心媛;來到《永別書》,賀殷殷和小朱。 章憾文為《最好的時光》作序時,曾爬梳台灣同女小說脈絡──《永別書》著無庸議是「女同性戀」小說,不過書中人物之鮮明,心理地景之立體,又讓我感覺它能不只屬於同女,而剝除了性別,像十四歲的賀殷殷竭耗心神求得的一悟:「基本的人性」。 除了女性情欲、姊妹情誼、女研社文化,在愛情的支線上,它更廣泛寫出了人在感情裡可能的殘忍和容忍,屏息讀著那些流淌過皮膚表面的高溫情感熔漿,使人隱隱想起某些久遠之事,那或是獨屬於青春的。也正因其感情與關係,「在人世間是稀罕的」,小朱被殷殷勉強說成「初戀」,其實是孤獨者一起孤獨?啟蒙同時也是(開)啟盟(誓),無論守約或背棄都是艱難,為使痛苦的水位下降,得用盡多少努力,才能獲贈那忽然記憶強度減弱的「完美時刻」,在那之前,「記憶的別無選擇,是人生的最高刑罰。」但我不能忽略的還有,賀殷殷關鍵的發問:「那些我們打算忘掉的事,我們曾經──一度以正確的方法,記得過嗎?」萬一我們將自己置入的,是一座假牢獄,該怎麼辦?這是小說中,特別提出「當定義想要推翻某些記憶時,我總不讓記憶倒下」的原因?但為何她有此把握?
就像,相較於小朱這段強悍的「原型」或「天敵」戀愛,書中鋪陳了另一段為時較長的伴侶關係:賀殷殷和何萱瑄。兩人在生活中相伴跳格子,直到非關背叛的謊言,病毒般覆蓋了殷殷的記憶體──假記憶真實地覆蓋掉了真實。她們原本可以繼續走下去的吧,賀殷殷疑似有過日子的本事,只要她願意「犧牲掉直覺,犧牲掉神奇時刻」,忍受 「在關係中長期的孤單感」?但是我對萱瑄沒信心(沒有讚美誰貶抑誰的意思)。
比較好奇的是,書中著墨最多的兩段愛情╱關係,都因賀殷殷特出的書寫能力,而有了微妙變形:殷殷和小朱,兩人競賽誰能將對方變成「讀者」;殷殷和萱瑄,則較量彼此「想成為作家的欲望」。 何以如此?究竟,作家身分的「光環」是什麼?才華這份禮物,又為何令人如此垂涎?竟使愛情關係,因摻入「寫作者身分」而有巨大變數?
還有一個不太重要的好奇:賀殷殷「意義非凡」的木頭盒子裡,收藏的電影票是哪幾部電影啊?
梓評
主題書展
更多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